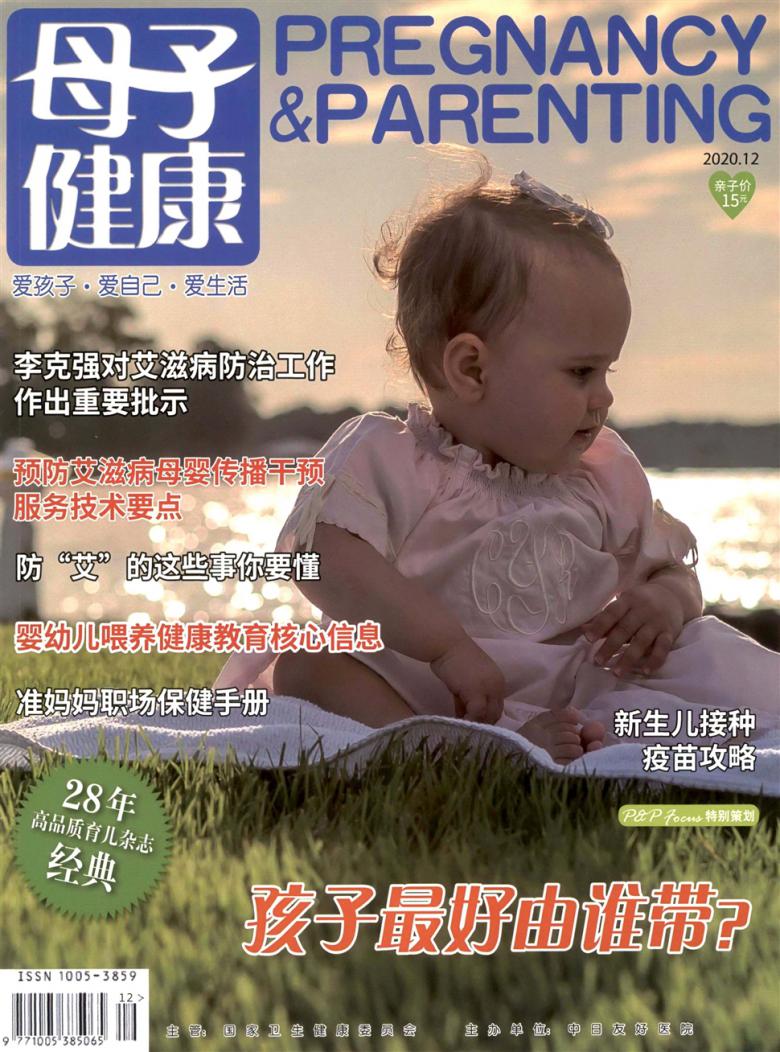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另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
黃宗智
內卷與工業發展
這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英國與長江三角洲農業體系的差異對于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型意味著什么?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史凸顯出內卷化農業的兩大主要涵義:家庭農場對節約勞動的資本化與農業規模效益的抵制,以及類似的家庭農場的手工業生產對“原始工業”和現代工業中節約勞動的資本化的抵制。
(一) 對節約勞動的資本化農業的抵制
我們知道,內卷體系的一個后果就是排擠掉畜牧業,從而也消除了單位勞動上更多的畜力畜肥形式資本的投入。內卷農業可以造成這樣的境況,即人力的使用變得比耕畜更經濟,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節省人力勞動,而只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無論是因為生產周期中的工作強度,還是由于時間緊迫所致。
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長江三角洲農業只能一步步走上勞動密集化和內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節約勞動的資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說哪條道路更為可能,哪條道路更為艱難。在勞力如此廉價以至可取代資本以減少成本的情況下,提高單位勞動資本化程度的激勵何在?
近年來的中國農業現代化歷史有具啟示性。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當現代機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機的使用)以及化學革命帶來的化肥使用降臨到長江三角洲農業時,該地區的農業生產仍舊沿襲著勞動密集化的內卷的道路而沒有出現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機引入長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實現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種第二茬“晚稻”,發展更趨內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麥)。拖拉機之所以帶來這一變化,是因為它使在收獲早稻與栽插晚稻間的短短數天內完成犁地工作成為可能。正如農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當于頭茬種植所需的勞動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產出卻有減少。結果,現代農業革命帶來收成三倍的增長,伴隨的卻是勞動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農業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對婦女從事農業勞動的充分動員——從占農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勞動日數量的增加所致——據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國整體的估計,從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結果,即使在長江三角洲這個中國的最“發達”地區,農村單位勞動日收入也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 時至今日,農業收入低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大障礙。
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小家庭農場對大規模(資本主義)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適合內卷經濟的生產單位,事實上是其中樞所在。婦女、兒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納到那些勞動力市場中男人所不愿從事的工作當中。再以家庭布匹生產單位為例:紡紗的報酬僅為種田所得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從事的工作。家庭生產單位可以通過家庭成員機會成本很低的輔助勞動來吸納此類“副業”。這一事實,實際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資勞動為基礎的大“資本主義”農場——勞動成本較高——更具競爭力。由于運作成本較低,家庭農場事實上得以維持比資本主義農場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價,從而擠除了后者。結果自17世紀以后,明代早期曾經存在的使用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場在長江三角洲消失殆盡。[2]
小家庭農場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諸如18世紀的英國農業那樣的規模效益的可能性。農作物生產以及農村手工業與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及個體農戶維系在一起,而單位勞動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這與英國拓展了的圈地農場以及農牧業的結合構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而彭慕蘭卻對此熟視無睹。
這并非說諸如長江三角洲這樣的農業體系就沒有勞動生產率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現代農業勞動密集度同樣很高,但整個18世紀那里基本沒有出現人口增長,這與中國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徑庭。[3] 而且,20世紀上半期那里的現代農業機械與化學革命是在農業勞動人數沒有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實現的。[4] 結果農場勞動生產率通過增進單位勞動的資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隨之農業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現代農業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長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國必須探索一條不同的道路。中國農村走出的一條特色道路就是“農村工業化”,即是以村莊和城鎮為基礎的現代工業(不同于傳統手工業)的廣泛發展,它最初始于一種廢品舊貨工業和對城市貨物的勞動密集加工,但經過20年的發展也有了推進勞動生產率的資本密集型工業。從1978年到1997的20年間,這場農村“集體”部門的工業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長率,最后其生產總值超越了強大的國有工業20%。[5]
在這一過程中,被“鄉鎮企業”吸收的勞動力總數達到1.29億之多。無論以什么標準來衡量,這都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變中國總的農業就業實質上的低水平,因為這一時期勞動力總數的增加超過了非農就業的人數。直至1991年,中國農業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從農村工業迅速擴展前夕的1978年時的2.85億,增加到最高峰3.42億。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來浮動在3.2億左右。[6]
結果,盡管農村工業化在東南沿海等最發達地區導致了明顯的“去內卷化”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大多數其他地區仍處于僅能維持生存的水平。不過,擺脫內卷的途徑已經非常清晰地展示出來。農村工業企業及其他企業的持續發展,與中國人口總數長期趨勢的遏止與扭轉(通過前20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盡管在農村由于兒子養老問題而進行了必要妥協)相呼應,理應帶來農村經濟的“去內卷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7]
(二) 對節約勞動的農場工業資本化的抵制
從農村手工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邏輯,即內卷對資本化的抵制。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徐新吾的有關研究深刻地揭示出這一涵義。在多個研究小組和幾十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之上,他出版的資料集以及對江南土布業的系統分析被公認為目前最為權威的。[8] 徐表明,三個錠子的腳踏紡車在長江三角洲18世紀時就已經出現。這種技術先進的紡車,其工作效率是單錠紡車的兩倍。然而,它并未在長江三角洲真正流行開來,甚至直到20世紀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東端的幾個縣(清松江府東部棉花種植最集中的地區,而沒有在該府的西部,或者蘇州、常州、嘉興、湖州府,也沒有在太倉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簡單:便宜的家庭輔助勞動投入此類副業,使得裝置價格較高的多錠紡車不劃算。三錠紡車必須基本由壯年人操作,而單錠紡車則可以由老人孩子來操作。這樣一來,繼續在兩臺單錠紡車上使用兩人紡紗,比購置一臺三錠紡車并只能交由一個人操作要更加經濟。因此,三錠紡車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區使用。
然而,彭慕蘭又一次完全無視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這些基本事實。于是,他設想,成年紡紗女工全都使用三錠紡車,只有那引起無力操作腳踏輪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單錠紡車。以此為基礎,他選取三錠紡車和單錠紡車產紗量的中間值而得出了他認為的平均日產出,一舉把18世紀紡紗工的一般產出夸大了50%,盡管徐新吾已經表明在長江三角洲三錠紡車的使用非常有限。這是彭慕蘭對布匹生產中相對于紡紗的織布所花費時間以及商品紗流通程度的誤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錯誤。由此他認為長江三角洲婦女參加棉花生產的所得超過了男性農業雇工,按他的話講:“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農業雇工的1.6倍到3倍。”盡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認紡紗這一棉花經濟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僅僅能提供“一個成年婦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頁)。
在這里,彭采用的價格數據取自各種二手文獻。那引起數據實際上針對的是不同等級的棉與布,而且地區各不相同:或為長江三角洲最東部的幾個縣,或為整個長江三角洲或華北,或全國。雖然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價格變動的長期趨勢,但在估計農民收入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價值。因為這些材料缺乏內在一致性,而且它們大都是城鎮里商人所得的零售價而非農民所得到的價格。然而彭慕蘭卻將這些散亂矛盾的數據組合起來,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結論,即婦女紡紗織布的年收入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遠遠高于維持一個成人生存基本的糧食需求(約3石),并且是男性雇農收入為的“1.6倍到3倍”(第316——323頁)。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權威性研究沒有采用可疑的價格數據,而是在了解基本生產狀況的前提下估計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為1.0石[10] ;按彭慕蘭估計的每年工作210天這一數字計算,則工人的年收入為3.0石。彭慕蘭完全忽視了徐的估計。
另一個問題是長江三角洲家庭農場的家庭工業與英國“原始工業化”之間的區別。正如戴維·勒凡(David Levine)所示,英國的原始工業,因其給農民提供了可以替代耕作的就業機會,從而真正改變了人口模式,促成早婚和高結婚率。結果人口有了實質性增長,這一模式的典型例證就是塞普塞德(Shepshde)社區。勒凡的假設后來得到劍橋人口與社會結構中研究小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and Social Structure )的證實,這項認證基于對404個教堂記錄的嚴格而精確的使用。[11]
然而,長江三角洲的家庭農場手工業卻沒有導致人口行為的任何劇烈變化。在徐新吾的資料中可以找到解釋:對農民們而言,長江三角洲的農村手工業實際上從未成為一種耕作之外的替代性選擇,而始終是作為耕作的補充的“副業”活動。原因不難找到:如上所示,紡紗是新的生產活動最大的部分,占去每匹生產所需7天時間中的4天。此項工作的報酬非常之低,僅僅有提供成年婦女大約一半的生存所需。即使再加上報酬較高的織布,一個紡織工的年收入也只有3石稻米,剛夠滿足一個人的糧食需要而已。這樣一來,要維持一個家庭,布匹生產本身并不能成為耕作的可行替代。長江三角洲農戶一般生產型式是把糧食生產、棉花種植與棉手工業結合起來。正如我在1985上的著作中闡述的,對于掙扎在生存邊緣的農戶而言,這一型式就好比一個人靠耕作和手工業兩條拐杖支撐著謀生。[12] 農作的低收入意味著農民必須靠手工業收入的補充才能維持生存,反之亦然。
大量證據表明,種地與手工業提供給農戶的不是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補的生存資源。[13] 我只征引兩個特別有說明意義的當時的論述。第一個出自18世紀中期的無錫縣,該地是長江三角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錫金識小錄》記載:
鄉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還租已畢,則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歸典庫,以易質衣。春月則闔戶紡織,以布易米而食,家無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則又取冬衣易所質米歸……及秋稍有雨澤,則機杼聲又遍村落,抱布貿米以食矣。故吾邑雖遇兇年,茍他處棉花成熟,則鄉民不致大困。
繅絲情況也是一樣。正如17世紀名儒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就三角洲南部的嘉興所言:
崇邑(嘉興府崇德縣)田地相埒,故田收僅足民間八個月之食。其余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洽,惟蠶是賴……凡借貸契券,必期蠶畢相嘗。即冬間官賦起征,類多不敢賣米以輸,恐日后米價騰踴耳。大約以米從當鋪中質銀,候蠶畢加息取贖。
由于農村家庭手工業并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所以毫不奇怪,類似英國塞普塞德地方的演變邏輯難以在長江三角洲實現。在那里,原始工業逐漸提供了獨立于耕作的就業機會,從而使子女得以在繼承農場前結婚。據斯考菲爾德(Schofield)研究,18世紀英國人口的增長,主要是平均婚齡沿著勒凡揭示的邏輯從約26歲降低到24歲的結果。[14] 相反在中國,由于家庭工業作為農場收入的補充而與之緊密地維系在一起,所以也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變化。
內卷的家庭手工業對于現代工業發展的意涵,在以往研究中已經得到詳細記錄。手工織業20世紀仍頑強地存在。甚至直到1936年,手工織品仍占有中國布匹消費總量的38%[15] 。手工織業之所以能夠抗衡勞動生產率4倍于己的機織,全賴其低成本的家庭勞動。[16] 與此不同,在紡紗業中,手工紡紗與機紡的勞動生產率之間1:40的懸殊差距擠垮了手工紡紗。因為在這樣一個比率上,紗價已經降至與皮棉價格非常接近的水平,即使依靠低成本的輔助家庭勞動力,手工紡紗也難以存活。[17]
18世紀長江三角洲農村家庭工業與18世紀英國原始工業之間的不同,也延伸到兩地不同的城市化歷史當中。那時候的長江三角洲興起了一些新的棉、絲加工和銷售的城鎮[18] ,但與瑞格里描述的英國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語。據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估計,1843年“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人口(有2000以上的居民生活的城鎮)只占7.4%。[19] 這與瑞格里的數據形成尖銳的對比,到1801年,英國已經有27.5%的人口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鎮中。[20]
原因顯而易見。長江三角洲沒有像英國那樣經歷過農業革命,而正是英國農業革命使食品供應增加以滿足大量非農人口的需求成為可能,進而原始工業化逐漸地越來越以城鎮為基礎,而不再束縛在家庭農場。農業革命與以城鎮為基礎的原始工業化乃是瑞格里所示城市化的基石。
據詹·德·弗雷斯(Jan de Vries)的研究,這種“新型城市化”應與前近代的城市化模式,即古老的大型行政—商業城市(擁有4萬以上的人口,包括巴黎和倫敦)的成長區分開來。新型城市化主要發生在較小的城鎮和城市(規模在5000——30000人之間)。在德·弗雷斯看來,這是一個始自約1750年的波及全歐洲的現象。從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歐洲人口保持穩定(這一階段僅增長0.2%),而小城市和城鎮的人口卻突增了4倍。[21] 瑞格里提練了德·弗雷斯關于英國的數據和討論,用以揭示這一“新型城市化”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一個英國現象,它可以溯源到1670年前后以來城鎮的興起與拓展。[22] 而中國則要到20世紀80年代現代工業在農村得到發展,才經歷這種蓬勃的小城鎮的興起。[23] “勤勉的革命”?
德·弗雷斯在回顧過去20年來研究歐洲經濟史的成果時,特別指出四個卓有成就的領域:首先,工業革命之前一個世紀里發生的農業革命;其次,上述勒凡、瑞格里以及斯考莫菲爾德等提出的那種人口轉變;第三,“新型城市化”,它建立了“工業增長得以發生的區域經濟發展框架(而不是該工業化進程的產物)”;最后,原始工業化,它提供了吸納婦女兒童勞動力的亞就業機會并導致上述人口變遷。[24] 這些聚起來的研究成果構成了德·弗雷斯所說的“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他們將工業革命的根源追溯到近代早期,從而拓寬了我們對工業革命的理解。
德·弗雷斯進而提出了“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這一假設,意在上列成果之上樹立第五個新認識領域。首先,這一模型旨在解決由較低平均工資而較高總消費有關的證據所提出的經驗難題。他認為,婦女兒童以較低的平均工資參與生產但卻增加了家庭總收入。由于婦女兒童以及男人們在農村和城鎮從事非農工作,一方面18世紀“勤勉的”農戶向城市供應了更多的農產品,另一方面他們也對城市商品有了更大的消費需求。特別是消費方面的變化,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做好了準備。換言之,這場“勤勉的革命”及其所引發的消費變化(或稱為“消費革命”),與“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提出的其他變化一道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動力。
德·弗雷斯假設的意圖和內容既然如此,那么,彭慕蘭把長江三角洲的情況跟德·弗雷斯“勤勉的革命”等同起來的企圖就不能不讓人莫名其妙了,因為19世紀的中國畢竟沒有發生需要我們去解釋的工業革命。然而彭卻意欲為之,其思路與王國斌(R. Bin Wong)較早的簡要論述如出一轍。[25] 在他們看來,基于婦女兒童的就業以及平均工資的降低,兩個地區情況雷同是很顯而易見的情況。因此他們主張,我所提出的長江三角洲的內卷實際上應該理解為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
然而,要想將兩者等同起來需要做一系列相當復雜的論辯。首先,必須從18世紀的歐洲歷史中去掉“革命”部分,否則就不能把它與中國等同起來。因此,彭慕蘭抹掉了農業革命和新型城市化。盡管德·弗雷斯在論述勤勉的革命同一篇文章中著重提到這兩大變遷,彭對它們卻只字未提。其次,必須使歐洲原始工業化看起來純粹是內卷的而非革命的,以使其看起來與長江三角洲更為類似。于是,彭慕蘭將勒凡的重要著作縮減為對沒有出路的內卷式變化的簡單論述(第93頁),忽略了勒凡的主要貢獻。根據勒凡揭示的邏輯:原始工業化創造了城鎮就業機會,使早婚和更普遍的婚姻變得可能,進而改變人口型態,并為工業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彭慕蘭把勒凡的“初生資本主義”論題置換言之成只是內卷的論點。這樣,他試圖把“革命”從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中剔除掉。
通過對12—17世紀內陸的南部“低地國家”(即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的總稱)與沿海的北部“低地國家”的比較研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已經對內卷型和資本主義興起型的原始工業做了非常清晰的區分。就前者而言,手工業仍與小農生產聯系在一起,主要是一種通過收入遞減的內卷型生產而維持生存。就后者而言,它逐漸與耕作分離開來,完全趨向市場和利益,并預示了資本主義的到來。[26] 彭慕蘭完全忽視了荷蘭及英國手工業的革命的一面。
接著,為了自圓其說而且不至于太背離德·弗雷斯的主題,彭意識到他必須提出長江三角洲婦女紡織者擁有高收入,因此,出現了我們在前面講過的數據拼湊。他以為有必要把長江三角洲塑造成一個比實際情況更為市場化的環境,因而想像出違背事實的高度發達的棉紗市場,以及長江三角洲紡織者對三錠紡車的普遍使用——事實上絕大多數人仍在使用單錠紡車。最后,他在此基礎上剪貼出了一個所謂典型的婦女紡織者肖像,她掙得的工資竟然幾倍于男性農業雇工。
不出所料,彭著避開了為什么長江三角洲沒有出現類似歐洲的城市化這一問題,盡管拙作中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因此,他忽視了英國原始工業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 )方面與內卷的(involutionary )中國小農家庭工業之間的重要差別:前者逐漸成為一個城鎮現象;后者則基本上只是家庭農場的副業。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則依然主要是農村的現象,即使在長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雖然極度扭曲了德·弗雷斯的論題,但彭慕蘭還是想效仿德·弗雷斯同時關注消費以把需求經濟學整合進來,盡管他并不把這些變化看成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在第3章中只是試圖簡單地論證在消費方面中國和英國并無實質區別。與前面所討論的其他論題一樣,這里他想做的是盡量使18世紀英國及歐洲更趨向內卷而非革命,以使之能與中國等同。同時,為了使長江三角洲可以與英國及歐洲等同,則盡量使長江三角洲顯得不像我主張的那樣趨于內卷。
首先,他忽視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學者提供的證據,這些證據記錄了17、18世紀不只是城鎮而且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消費型式的巨大變遷。德·弗雷斯本人根據遺囑檢驗法庭的記錄研究了荷蘭共和國的弗理西亞群島(Friesian Islands)的農民。如其所言,這些農民“逐漸購置了各種‘城市商品’——鏡子、油畫、書籍、鐘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質量”。遺囑記錄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簡單的木制儲藏箱,陶器以及(荷蘭)代爾伏特精陶(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簾在16世紀時似乎還無關緊要;到1700年則已經很普及了”。此外,“銀器展品的收藏越來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經》書鉤以及男女個人的裝飾品。”[27]
勞娜·韋澤利爾(Lorna 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國存在著基本相同的形式。該書處理了3000件法庭檢驗遺囑記錄,范圍包括8個地區的城鎮鄉村。她的“關鍵”物品清單和德·弗雷斯的類似,包括書籍、鐘表、鏡子、臺布、以及銀器。她證明,在1675—1725年間,這些東西在鄉村人口越來越普及。[28]
正是在這些證據基礎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說:婦女兒童加入就業行列擴大了農產品向城鎮的供應,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鄉村對城市商品的消費。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勤勉的革命”)導致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論述的典型城鄉交換,在斯密看來它將會引發二者的螺旋式經濟發展。[29]
所有這些彭慕蘭都置之不顧,相反他要獨自去論證英國和長江三角洲(以及歐洲和中國)在消費方面的等同。他用大量篇幅討論茶和糖的消費,而實際上與糧食、棉花、棉布、蔬菜、鹽、肉及食用油(這里按它們在家庭賬目中所占比例排列)比較起來,這些東西在農民家庭支出中只是很次要的。20世紀的實地調查表明,茶與糖合起來只占長江三角洲農民全部購買商品的5%(第117—223頁)[30] 彭慕蘭考慮的關鍵項目是棉布消費,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進行了一項極具有誤導性的比較:他的主題是消費,但在對英國與長江三角洲做布匹比較時卻轉換成平均產量。這使他在英國和長江三角洲之間找到了大略的對等:長江三角洲每人平均生產14.5磅棉花和2.0磅蠶絲,而英國在1800年每人大約12.9磅(棉花、羊毛及亞麻)。他給予讀者的印象是平均消費接近于這個水平(第138頁)。然后,彭試圖對全國平均消費進行估計。他令人難以置信地認為,中國在1750年的棉花產出已經相當于1870年或1900年的水平。而1750年的人口較少,因此這一年的平均棉花消費必定是后來的一倍。在此基礎上,他得出每個中國人年均消費6.2—8.0磅 的數字,而英國為8.7 磅,法國為6.9磅(第140—141頁及附錄F)。盡管他在前面提到了“每平方英尺亞麻和羊毛通常較棉花為輕,把這幾種紡織品混同起來與中國比較會出現偏差”,但他而是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的紡織品消費總量大致相當于18世紀中后斯的歐洲”(第138、142頁。)
這里彭慕蘭再一次無視普通常識。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棉花布匹的主要輸出地,正所謂“衣被天下”。一個平均擁有7.5畝土地并把其中20%—50%(亦即1.5—3.75畝)種植棉花的農戶,可以生產40—112.5斤皮棉(每畝30斤),這些足夠生產34—85匹布(每匹布需皮棉1.32斤,見本文附錄)。我們知道,長江三角洲農民棉花種植高度集中的原因,是嚴重的生存壓力之下 要盡可能把單位土地的產出最大化,進而用棉花和布交換糧食來維持家庭生存。根據徐新吾的估算,在松江府棉花生產最為集中地區,農民出售掉70%—90%的棉花與布匹,主要向中國其他地區輸出。因此,將他們的生產與消費混同起來完全是誤導性的做法。按照彭慕蘭的數字與看法,長江三角洲農民每年會消費超過10匹棉布以及2匹絲綢,這可是足夠裁制十多件新棉衣以及兩件絲綢衣服的!
徐新吾的數據表明,帝國主義進入中國之前全國的棉布消費平均約為每人1.5匹,即2斤皮棉(2.2磅),再加上人均0.6斤(0.66磅)棉絮。由于棉花總產增加、機紡棉紗的大量流通以及較之土布而言機織布的不耐穿(根據徐的資料,土布可穿三年而機織只能穿兩年),這一數字到1936年增加到人均兩匹。在精確可靠的1936年數據基礎上,徐提供了1840年、1860年、1894年、1913年、1920年以及1936年的詳細估計。[31] 在我看來,他的描繪遠比彭慕蘭假設的1750年產出與1870年和1900年相當來得可靠,因為彭根本沒有任何一年的可靠數據。為什么人口增長在1800年以后對布匹消費構成巨大的消極影響,而在此之前卻產生擴展性的影響?急于提出自己觀點的彭慕蘭,竟連他所倚重的李伯重也加以批駁(第332頁)。他批評李過多依賴徐新吾,并引吳承明編的書支持他的觀點,卻沒有意識到徐本人就是吳所編書中棉花一節的作者。[32] 當然,徐的數字表明全國人均紡織品消費只有彭慕蘭所提數字的1/3到1/2。
關于中國人消費的其他方面還少有系統的著述。彭慕蘭參引的方行1996年的論文是首批嚴肅研究此問題的嘗試之一。方行頗具創新意義地使用了三本來自17世紀和19世紀的農書。[33] 他的意圖是要論證長江三角洲生活水準從17世紀早期到18世紀有實質性的提高。他采用了每年人均消費兩匹布的合理數字,在這期間沒有變化,有關生活水準提高的論證主要集中在“副食”(主要是肉、魚和家禽)消費的增加。他認為,17世紀食物花費占家庭總收入的76%,而在18世紀占到83%。這是由于副食消費增多,而糧食消費則基本保持穩定(前斯為55%,后來為54%)。所增加的部分主要是農民在比較多的節慶期間消費肉、魚以及家禽。而在過去,農民只在諸如新年這樣幾個有限的節日里才有這類消費。到18世紀,長江三角洲農民每年以這種檔次來慶祝的節日約20天。即使如此,方承認有證據表明存在某種降低,即糧食消費從農民只食用大米這種價格較高的“細糧”變為混合消費大米(60%)和大麥及大豆等價格較低的“粗糧”[34] .方所論證的小額提高,我認為在長江三角洲內卷體制下是可能的,但它決不是德·弗雷斯所謂“勤勉的革命”中勾勒的那種變化。
在與歐洲的消費進行比較之前,我們還需要就中國的消費做許多研究。中國人的分家單,再輔以地方志的仔細搜尋,也許可能提供類似于歐洲的遺囑檢驗記錄關于耐用品繼承那樣的信息。但更為重要的也許還是方行所強調的糧食、副食品以及衣服等日用品的消費。另一重要的消費品可能是燃料。對長江三角洲農民來說根本就沒有取暖的燃料可言,只有用于炊事的稻稈。用煤取暖是罕見的事情,而木柴取暖也只是極少數人的奢侈享受。這與英國的差異之大應不亞于肉類消費。
注釋
[1] 關于勞動投入的增長,參見D. Perkins, S. Yusuf ,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aryland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 pp.58,66,210;并參數Huang, Yangzi Delta,pp.236——241、黃宗智《長江》第238——242頁、P. Huang ,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July 1991]), p.330。
[2] Huang, Yangzi Delta,pp.58——69;黃宗智:《長江》,第58——69頁。在這一方面與旱作的華北平原很不一樣。那里的家庭生產單位沒有像長江三角洲地區那么高度徹底地展現,這是因為農場經濟(旱地作物而非水稻,棉花播種比例較低,而且幾乎完全不種植蠶桑)的內卷程度較低。在華北,使用雇工的“經營式農場”相對家庭農場的競爭力較強,以致在18世紀及其以后“經營式農場主”與富農逐漸占了華北平原眾多村莊中富戶的大多數(Huang North China ,pp. 90——95,72——79;黃宗智:《華北》,第90——96、68——78頁。)不過在那種情況下,無論大小農場中農場勞動者的低報酬仍然構成對農業資本化——增加畜力投入——的強大抵制。這是華北的內卷模式。
[3] T. Smith , Nakahara : Family Farming and Population in a Japanese Village , 1717——1830. St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4] C.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 lifornia Press, 1963, pp. 130——143.
[5]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第423、424頁。
[6] 除工業以外,這一數字還包括了建筑、運輸以及其他非農企業。《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第137、380頁。
[7] 另一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在中國人口比較稀少的西北、西部以及西南發展大規模的畜牧業,輔以現代的投入,從而形成就國民經濟整體而言(即使不是就個別家庭農場而論)的農牧結合型體系(鄧英陶等:《再造中國》,文匯出版社,1999年)。
[8] 資料包括所有可用的文檔與對農民和紡織工人們的訪談,均收集在徐新吾《土布史》。徐的系統分析及定量估算,見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第258——332頁。
[9] 徐新吾:《土布史》50——52頁;亦見吳承明編前引書第386——387頁。在關于江南地區“早期工業化”的新著當中,李伯重引用了徐新吾研究小組在1963年做的一次關于20世紀三錠紡車使用情況的訪談,旨在提出三錠腳踏紡車在清代的普及程度遠比徐新吾的估計要高。他的這一論斷并無直接證據,而只是靠推論得出:現代技術應該對更為發達的傳統技術比對欠發達的傳統技術有更大的影響。這樣,如果20世紀時三錠紡車在長江三角洲某些地區得到相當廣泛使用的話,那么它在現代工廠到來之前的清代必定曾經得到更為廣泛的使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以下簡稱《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8—50頁,引自徐新吾《土布史》第46頁)。李忽視了徐新吾提供的證據,它表明三錠紡車的使用幾乎完全局限于松江的東部地區(即黃浦江以東的上海、川沙、南匯三縣),而沒有在松江西部或者三角洲地區的其他府縣得到應用。例如,1917年的《青浦縣志》中提到只有松江府的東鄉使用多錠紡車。1884年的《松江府志》中也提到這一點(徐新吾《土布史》,第50—51頁)。與此類似,道光年間常熟縣的鄭光祖寫道:他在上海見到三錠紡車后,“覓一車以回[常熟],多年人莫能用”。即使在清代最負盛名的“謝家車”也是單錠紡車(吳承明編前引書,第386—387頁。
[10] 徐新吾:《土布史》,第88頁以后。
[11] D. Levine ,Family F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7. R. Schofield, British Population Change ,1700——1871.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 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_1860. Cambridge , Eng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1,87.
[12] Huang , North China ,第191頁以下;黃宗智:《華北》,第193頁以下。
[13] 參見徐新吾《鴉片戰爭前中國棉紗織手工業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1頁。
[14] Schofield 前引文,第74、87頁。
[15] 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4,第319頁;參較Huang , Yangzi Delta , p. 98;黃宗智《長江》,第100頁。
[16] 而且也依賴新改進了的“改良土布”——機巧地使用紡紗(即洋紗)作經紗,而用“土紗”(或手工紗)來作緯紗——這一革新。比較粗糙的手工織的布比精細的機織布耐用,因而仍然為農民們所歡迎(Huang , Yangzi Delta , p.137;黃宗智:《長江》,第139——140頁)。
[17] 徐新吾前引文(1990年),表B.5,第320頁。參較Huang , Yangzi Delta , p.98;黃宗智《長江》第100頁。
[18] Huang , Yangzi Delta , pp.48——49;黃宗智:《長江》,第47——48頁。
[19]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p. 229。曹樹基在最近的著作中得出比施堅雅要高的估算,但仍然只有瑞格里對英國的估算的1/2。而且,如果把2000人的城鎮去掉使曹的計算跟瑞格里的計算——只包括5000人以上的市鎮——相對應的話,則不容地更低許多(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第17章,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施堅雅后來在其1986年對四川的數據的研究中指出,他可能必須把7.4%這一數字上提到9.5%(G. Skinner, Sichuan’s Populatoin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7, 2(December 1986): p.75, n.43)。
[20] Wrigley 前引文,第688、700—701、723頁。
[21] J. de Vries,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Pre —Industrial Europe , 1500—1800. In H. Schmal (ed .), Pattern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Since 1500. London : Croom Helm , 1981, pp. 77—109; J. de Vries , 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 Wrigley 前引文。
[23]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48—49,264;黃宗智:《長江》,第47—48、265—266頁。這自然與李伯重將中國的“早期工業化”與英國及歐洲的“原始工業化”等同起來的意圖相抵觸。李沒有考慮如下事實:即英國原始工業演變成為基礎并與耕作分離開來,從而促成了德·弗雷斯所謂的“新型城市化”;而長江三角洲的棉紡織以及繅絲則一直與農作維系在一起(李伯重:《早期工業化》)。
[24] J.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Jrue 1994):251——252. 參較J.de Vries, Between Purchasing Power and the World of Goods: Understanding the Household Aeconom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dd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3, pp. 85——132。
[25] R. Wong , China Transformed :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p. 30—31。
[26] R. Brenner,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Peter Hoppenbrouwers and Jan Luitenvan Zanden (eds.), Peasants into Farmers ?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Low Countries (Middle Ages —19th Century ). Turnhout , Belgium: Brepols ,2001, pp. 275—338.
[27] J. de Vries 前引文(1993年),第100頁。
[28] L. Weatherill,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Behaviour in Late Seventeenth—and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r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特別是10.2,第219頁,及表10.4,第220頁。
[29] A. Smith ,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1776],pp.401—406。
[30] Huang Yangzi Delta , pp. 96—97;黃宗智:《長江》,第97—99頁。
[31] 徐新吾前引語言(1990年),第314——315頁。
[32] 徐新吾前引語言(1990年),第258——332頁。
[33] 這些農書是1658年的《補農書》、1834年的《浦泖農咨》、1884年的,《租覈》。
[34] 方行:《清代長江三角洲的農民的消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