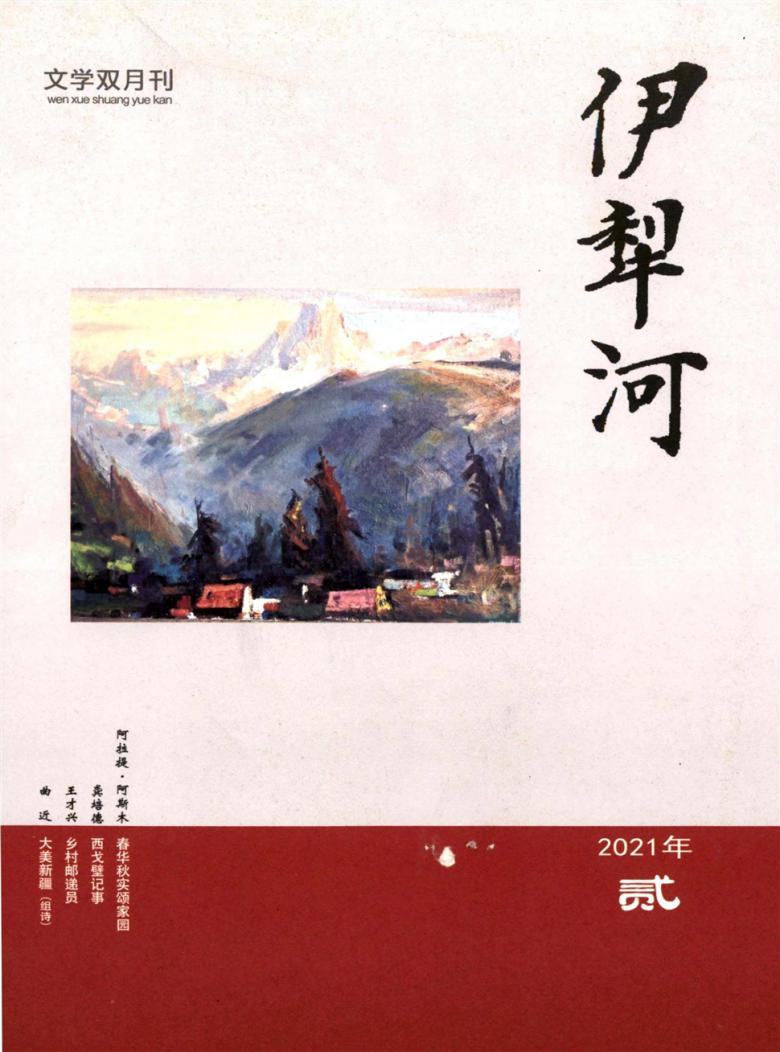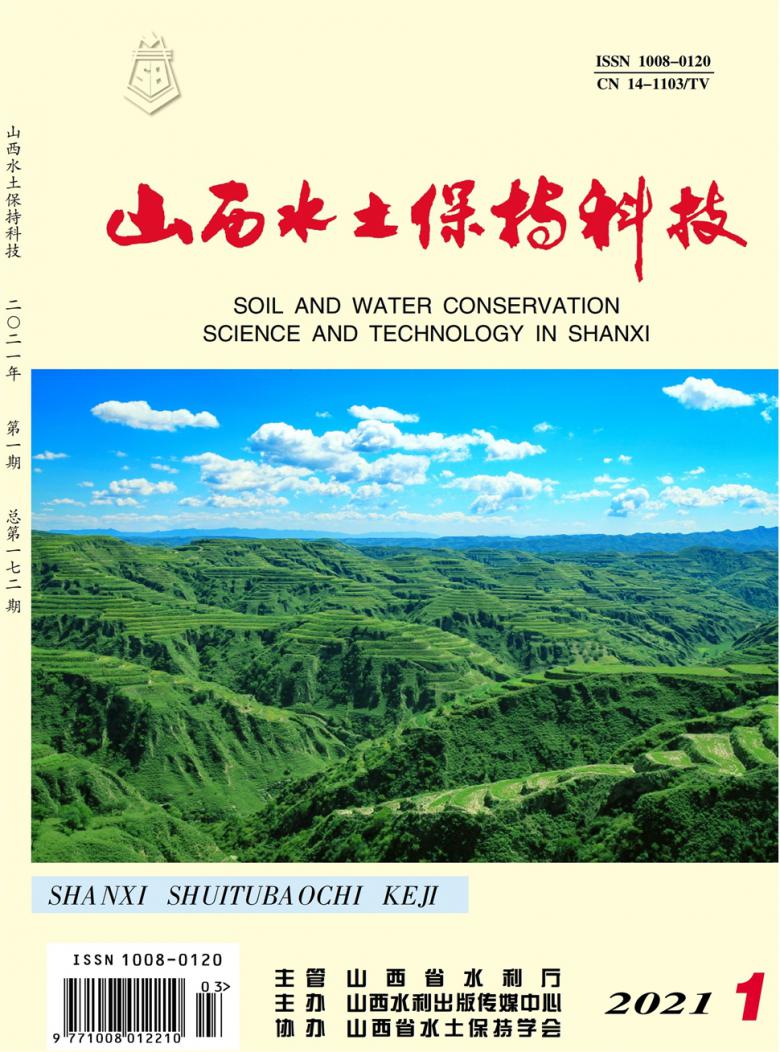增長理論與發展經濟學——關于在增長理論基礎上重建發展經濟學的若干思考
佚名
【提要】學在二戰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對于發展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取向,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然而,所有這些見解看來都忽略了兩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第一,發展經濟學如何建立自己的統一性;第二,假定實現了理論上、上的統一性,發展經濟學如何建立自己的經驗基礎。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新方向,其兩個基本觀點是:第一,發展經濟學應當并且能夠在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重建,也就是說,發展經濟學可以作為增長經濟學的一個學科來建立。從形式化的角度,發展可以作為一類特殊的增長問題來處理。這樣,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統一性問題便可以獲得解決。第二,發展經濟學的重建可以以東亞的發展經驗作為參照,因為東亞提供了二戰后發展家通過與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實現了成功的經濟發展的相對完整的經驗。作者以增長理論作為框架,以東亞經驗作為參照,提出了重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初步綱要。
【關鍵詞】收斂理論;東亞模式;發展經濟學
一、引 言
在過去近二十年中,增長理論在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后,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再度恢復了其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與此同時,發展經濟學則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發展經濟學的衰落,并不是因為發展問題已經過時,或對于所有已知的重大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都已經給出了理論上完滿的解答。恰恰相反,發展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遠未過時,對于現實中重大的發展問題,我們在發展經濟學中能夠找到的理論解答是極貧乏的。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克魯格曼①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即形式化分析模型發展的滯后。不過,這明顯地不能解釋為什么在增長理論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再度恢復了其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發展經濟學仍處于衰落境地。發展問題較之單純的一般增長問題更為復雜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對于發展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取向,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然而,所有這些見解看來都忽略了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第一,發展經濟學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論統一性;第二,給定理論上、方法上的統一性,發展經濟學如何建立自己的經驗基礎。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這兩個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問題。我們的兩個基本觀點是:第一,發展經濟學應當并且能夠在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重建,也就是說,發展經濟學可以作為增長經濟學的一個應用學科來建立。從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發展問題可以作為一類特殊的增長問題來處理。這樣,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統一性問題便可以獲得解決。第二,發展經濟學的重建可以以東亞的發展經驗作為參照。東亞提供了二戰后發展中國家通過與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實現了成功的經濟發展的相對完整的經驗。這樣,我們既可以在東亞的發展經驗中找到豐富的發展問題,也可以利用東亞的經驗檢驗和擴展我們提出的相關理論。
本文的討論涉及以下問題:重建發展經濟學的若干基本問題;提供討論的經驗背景;提出在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重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方法論路線(“收斂”方法);進一步討論理論建模的經驗基礎;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結論。
二、增長與發展:若干基本的事實及問題
增長理論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是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的原因,發展理論關心的主題則是后進國家的經濟增長及不同國家間經濟增長差別的原因。持續的人均收入增長及與之相關聯的全面的、顯著的結構變動構成經濟增長的一個基本特點。眾所周知,現代經濟增長是從18 世紀英國革命開始的,其后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正是這種首先開始于西方國家的現代經濟增長在其后一個半世紀內導致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劇擴大,從而使得世界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整個世界經濟與格局的演變,在現代經濟增長的傳播上帶來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變化。第一,現代經濟增長進一步擴展到了大多數的屬于非西方世界的發展中國家。②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經濟增長成了一種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現象。第二,同二戰前相比,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發生了顯著的加速。③ 第三,少數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行列。
在任何意義上,二戰后的世界經濟增長現象都是史無前例的、極其豐富和復雜的,并且提出了許多具有深遠的問題。就我們當前的目的而言,我們可以將二戰后世界經濟增長的情況,特別是同發展中國家相關的情況為以下5 個基本的“程式化的”(“stylized”)事實。④
事實1:二戰后初期,在當時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事實2:在二戰后的半個世紀內,世界經濟整體上實現了持續的增長, 其增長率超過二戰前任何一個時期。
事實3:在發展中國家整體與發達國家整體之間,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發生顯著的縮小。
事實4:少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位于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省和香港地區)在追趕發達國家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并且,所有這些國家、地區都是開放的市場經濟。
事實5:大多數實行計劃經濟的主義國家在追趕西方發達國家方面最終都失敗了。⑤
由上述事實,我們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問題:第一,為什么東亞成功了,而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失敗了?第二,成功的發展必須依賴于建立在私人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嗎?第三,成功的發展必須依賴于開放的經濟政策嗎?
我們以上討論的現象包含著與現代經濟增長相關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后進國家能否比先進國家增長得更快,從而最終趕上先進國家。如果我們將這種情況稱之為“收斂”(“convergence”),那么,先前的觀察說的是,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并沒有發生顯著的“收斂”。不過,類似的“收斂”現象確實發生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集團內,那就是,若將美國作為基準,OECD 集團內大多數國家都比美國增長得更快。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OECD 集團內的國家具有兩個顯著的相似點:第一,它們均屬于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二,它們彼此間均具有密切的經濟聯系(相互開放,包括商品貿易、技術轉讓及資本和人員的流動等)。⑥
這樣,從上述觀察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基本的結論:第一,在初始條件相似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增長可以發生極大的差異;第二,在開放的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后進國家有可能通過對外貿易、技術轉讓等途徑趕上先進國家。后一結論構成本文其后整個討論的基本前提。三、重建學:一個基本的論路線(“收斂”方法)
本文的討論所依據的一個基本信念是:發展經濟學應當并且能夠在增長的基礎上重建。首先,發展的核心是人均收入的增長,而這正是增長理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其次,增長理論發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技術,這可以幫助我們將發展理論轉化為一個嚴格的理論。本節簡要地探討在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重建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路線。我們的基本想法是:“發展問題”可以形式化地歸結為開放條件下后進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相應地,理論建模可以歸結為發展出一類特殊的開放條件下后進國家的增長模型。我們先前考察的發展事實表明,在開放的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后進國家有可能通過對外貿易、技術轉讓等途徑趕上先進國家。這樣,理論建模可以進一步具體化為構造出一類特殊的開放增長模型,其中貿易、技術轉讓引致后進國家的長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斂”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以下,我們扼要地闡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論思想。
一般認為,增長理論開始于索洛在1956 年發表的一篇經典性文章。⑦ 早期增長理論關注的中心問題是發達市場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其核心概念是“穩態”(常數增長狀態)。當然,所謂穩態不過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動態意義上的一個擴展。在這一背景下,增長經濟學被看做是一門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學科。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發展經濟學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單獨學科出現有兩個背景原因:第一,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發展家存在著一些基本上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殊性,因此在發達國家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完全適用;第二,發展中國家作為落后國家存在著一個發達國家不存在的問題,即擺脫不發達狀態、進入發達狀態的問題,具體地說包括擺脫貧困、實現化等等。然而,在發展經濟學的定義上卻發生了持續的混亂。首先,人們沒有嚴格區分專注于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與等同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當人們談論發展經濟學時,人們常常明顯或隱含地集中關注于發展方面。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按照主流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的學科分類范式,顯然只能理解為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各個有關經濟學科的一個集合。其次,人們在談論發展問題時,又沒有嚴格區分一般的﹑、普遍的發展問題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特殊的發展問題。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發展經濟學需要重新定義。我們認為,重新定義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合理的路線是:(1)嚴格地區分發展經濟學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將后者理解為關于發展中國家的不同經濟學科的一個集合;(2)將發展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發展的經濟學科,在廣義上也包含增長經濟學在內;(3)將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學科定義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或簡稱為后發展經濟學。
重新定義發展經濟學后,顯然整個發展經濟學需要重建。這里,我們的考慮僅限于先前定義的后發展經濟學。在不會引起混淆的情況下,我們也仍然使用發展經濟學這一人們慣用的稱呼。若將“發展”限于常規的、可用數量描述的變動,則很明顯地,從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發展與增長本質上是同一件事。這樣,后發展問題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后發展國家(或后進國家) 的經濟增長問題。這里,增長須做廣義的理解,包含常規的結構變動、資源變動等等。于是,后發展分析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一類特殊的增長分析,即一般增長分析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應用。這樣,重建發展經濟學便可歸結為如何將增長理論應用于后發展這一特定場合。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考慮理論建模問題。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增長理論最初是在發達國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當然,在現實中,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是在孤立的狀態下進入和保持現代經濟增長的。不過,在發達國家的場合,孤立狀態下的增長至少對于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的發達國家是一個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發達國家或后進國家的場合,孤立狀態下的增長顯然不能看做是一個可接受的近似了。有關后進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后進國家進入和保持現代經濟增長完全依賴于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及與之相關的與后者的商品貿易。這樣,從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將后進國家的增長作為一類特殊的開放條件下的增長問題來處理。我們知道,增長理論已經解決的問題是:長期經濟增長怎樣聯系于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⑧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發展出一類適當的模型能夠再現這樣的一個增長過程,其中,后進國家能夠通過與發達國家的商品貿易及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實現較發達國家更快的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從而最終在長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
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定義為開放條件下的“收斂”問題,即在開放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能否通過與發達國家間的貿易達到與發達國家相同的長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論建模上便意味著,我們需要構造這樣的開放增長模型,該模型能夠再現上述收斂過程。我們將此方法稱為“收斂”方法,將按照這一方法建立的理論稱之為收斂理論。現實中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并非總是處于收斂過程。收斂分析作為對現實中的增長現象的一種理想化分析,可以為現實中處于收斂過程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提供一個近似,同時也可以為偏離收斂的各種復雜的非收斂增長提供一個方便的參照。
我們知道,一般增長理論通常以索洛模型作為一個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一般靜態貿易理論則以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作為基準模型。鬼木-宇 (Oniki 和Uzawa)⑨ 提供了結合索洛模型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一個嚴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過,他們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貿易這一特殊情況給予特別的考慮。筆者將他們的模型進一步修改為一個應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貿易的模型。⑩ 引入技術是公共產品的假設后,該模型可以產生出一個漸進的收斂過程。該模型的一些基本特點是:第一,在封閉的條件下,兩國將處于相同的長期增長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將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開放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實現較快的增長依賴于與發達國家的基于比較利益的商品貿易及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第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開放的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不同于在封閉的條件下的結構變動,特別是,一個發展中小國有可能實現高度的經濟專業化。這樣,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模型作為收斂分析的一個方便的基準模型。原則上,在收斂分析的背景下對這一模型的修正和擴展和在一般增長理論的背景下對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擴展,可以沿著相似的路線進行。
如我們先前的討論所指出的,增長理論是在發達國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斂理論則顯然需要在發展中國家的背景下來建立。既然東亞提供了迄今為止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顯然收斂理論可以以東亞的經驗為參照來建立。事實上,我們先前的討論僅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線,具體的建模顯然還需要依賴于對東亞的具體經驗做深入細致的了解。四、收斂的經驗基礎:的東亞模式
我們先前的討論建立了收斂理論建模的一般路線。當然,我們不能在脫離經驗現實的條件下考慮理論建模。相反,理論建模應當與對經驗現實的考察緊密地結合起來。理論為經驗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為前者提供驗證、提出和提供素材。如我們先前指出的,二戰后東亞成功的發展經驗,提供了后進國家通過與發達國家的貿易追趕發達國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的,我們可以以東亞的經驗為依據來考慮收斂理論建模。本節中,我們簡略地討論作為東亞的實際發展經驗的一種“程式化的”(“stylized”)表述的所謂“東亞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長理論解釋和回答的有關東亞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問題。
關于東亞模式的代表性國家和地區及東亞模式本身,在中可以看到極其不同的規定。首先,Kuznets ⑾ 將東亞模式的代表性國家和地區限定于日本、韓國與省。世界銀行⑿ 的范圍則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及東盟3國(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度尼西亞)。本文中,我們采用Kuznets 的選擇,依據的理由是:第一,迄今為止,只有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創造了相對完整的成功的發展經驗;第二,中國香港和作為“城市國家”的新加坡,其經驗不具代表性。按照這樣的處理,我們也可以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看做是東亞模式的領頭者,而將中國及東盟3國看做是東亞模式的追隨者。事實上,在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及東盟3國之間,依照它們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別,通過貿易及直接投資,發展出了一種動態的國際分工關系,即所謂“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⒀ 較先進的國家和地區把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至較后進的國家和地區。
其次,給定關于東亞模式的代表性國家和地區的選擇,關于東亞模式的闡述在文獻中也是極不一致的。本文中,從理論建模與經驗比較研究的需要出發,我們將東亞模式理解為對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創造的相對完整的成功的發展經驗的一個系統的表述。⒁
東亞發展的經驗是極其豐富、非常復雜的。從理論建模的角度將這些經驗為一個或一組系統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圍。這里,我們將僅僅指出有關東亞發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實,這些事實應當看做是有關東亞發展經驗的任何理論建模均需要考慮的一些基本前提。
事實1:東亞的經濟增長同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貿易存在著密切的、積極的聯系。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是東亞的主要出口市場;另一方面,東亞化所需的資本設備及中間投入也主要依賴于從西方發達國家的進口。在這期間,出口在本國GDP 中比重的迅速上升與出口在國際市場上份額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聯。
事實2:東亞產出的高增長緊密地聯系于高的資本積累。儲蓄率在東亞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的上升過程,直至儲蓄率顯著地超過發達國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時間內,東亞的國內投資主要依賴于國內儲蓄。東亞產出的高增長及迅速的資本積累依次伴隨著從初等、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個層次上教育的迅速發展。
事實3: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進步主要依賴于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在大部分時間內,東亞在技術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創新。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 的比重至工業化中期開始上升,其后逐漸達到或接近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
事實4:東亞工業化的過程依次經歷了下述3 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進口替代主要發生于輕工業,出口主要由農產品組成;并且,農業是一個主要的凈出口部門(農產品出口超過農產品進口加用于農產品國內生產的資本品進口)。第二階段開始的基本標志是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輕工業品組成)取代農產品出口成為主要的出口產品。此外,該階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1)工業取代農業成為經濟的主導部門;(2)進口替代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3)輕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要的凈出口部門。第三階段開始的基本標志是重工業產品出口取代輕工業產品出口成為主要的出口產品。此外,在整個工業中,重工業亦取代輕工業成為占支配地位的產業。
上述三個階段,產業與貿易的結構變動的主要特征可以總結如下:首先,出口方面的結構變動由初級產品出口主導轉移至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導再轉移至資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導。其次,工業中的進口替代由輕工業的進口替代開始,逐漸發展到重工業的進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結構變動緊密地聯系于制造業的出口擴張(出口在國內生產中的比重的上升)。
從理論建模的角度,我們可以將上述事實及其他一些相關事實總結為幾個基本的有待增長理論解答的問題:第一,貿易怎樣聯系于增長。傳統的貿易理論是靜態的,完全不能解釋在動態的條件下,貿易怎樣能夠支撐后進國家持續的增長。事實上,直到20 世紀70 年代中期,發展經濟學中流行的是“貿易悲觀論”,即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利用同發達國家的貿易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這正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背后的理論依據。第二,東亞的經濟增長怎樣聯系于技術進步,怎樣從完全的模仿轉向創新。傳統的增長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問題,很難直接于東亞的場合。東亞面臨的問題不是怎樣創造完全新的技術,而是怎樣從發達國家引進現成的技術,并加以模仿與改進。第三,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長怎樣引致儲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傳統的儲蓄理論關注的是儲蓄的動機,完全不能解釋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長的過程中,儲蓄率會經歷一個由低到高的演變。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儲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確定的。第四,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哪些力量推動各個產業部門依次經歷由進口依賴、進口替代直到出口擴張的漸進的演變。毫無疑問,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釋上述演變作為一種普遍現象的發生。如果說進口替代在二戰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那么出口擴張則可以說是東亞的一項獨特的成就。
我們看到,迄今發展起來的增長理論模型還難以從模型內部再現上述事實,并對相關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這也造成了對東亞經驗的解釋的分歧與混亂,如,東亞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技術進步還是資本積累,⒂ 進口替代在東亞成功的工業化過程中是否也起著積極的作用,東亞工業化過程中產業與貿易結構的演變能否僅僅用比較利益法則來解釋,⒃ 等等。我們相信,一旦我們能夠建立起適當的理論模型再現這些事實,我們便能夠為對后發展問題的研究建立起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將后發展分析與增長理論完全地結合起來。
五、結 論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增長理論與發展經濟學基本上是相互分離的。這既有理論上的原因,也有現實中的原因。然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種狀況不應當再繼續下去了。我們的基本看法是,發展經濟學應當也能夠以增長理論為基礎,以東亞經驗為背景重建。從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發展與增長是完全可以合二為一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當追求將發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數量化,但重要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我們要求發展理論達到足夠令人滿意的嚴格性與精確性,那么,我們就必須接受將發展理論完全納入到增長理論的框架中。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與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中國離趕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中國的發展經驗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許多重大的問題。可以說,中國已成為研究發展問題的一個最好的“實驗室”。我們相信,對中國的發展經驗及中國未來發展將面臨的實際問題的研究,將為發展經濟學的復興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推動。注 釋:
① P. Krugman,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 關于家進入“增長”的一項系統的,參看L. Reynolds,“ Spread of Economic Growth to the Third World:1850-1980,”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1983。關于15 個發展中國家自1900 年以來的一些主要的長期增長數據,參看R. Barro 和X. Sala-i- Martin, Economic rowth, McGraw-Hill,Inc.,1995,pp.367-369。
③ 關于二戰后世界經濟增長加速原因的,參看M.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④ Parente 和Prescott 于1993 年提出了二戰后發展的四項基本“事實”:任何時點上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收入分布整體上的穩定性、收入分布的上移及個別國家、地區間巨大的差異。見E. Parente and E. C.Prescott,“Change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Quarterly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sota,Spring,1993,pp.3-16。我們提出的事實同他們的陳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過,我們特別強調了東亞的成功與蘇聯式主義經濟的失敗。另見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同注①,pp.2-4),其中提出的100 多個國家1960~1990 年的人均收入變動數據同Parente 和Prescott 于1993 年建立的4 項基本“事實”也是一致的。
⑤ 有關二戰后東亞與若干低增長國家的一項比較統計分析,參看Barro 和Sala-i-Martin(1995,同注①,pp.446-450)。
⑥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關于“收斂”的經驗分析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領域。關于這方面的,參看W. J. Baumol,“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1986,pp.1072-1085;J.B.DeLong,“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1988,pp.1138-1154;R.Barro,“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1991,pp.407-443;R.Barro and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1992,pp.223-251;J.Temple,“The New Growth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1999,pp.112-156。基本上,這些作者得到的幾個較一致的結論是:(1)不存在普遍的、絕對意義上的“收斂”;(2)OECD 集團內存在顯著的收斂;(3)儲蓄率與人力資本水平對收斂具有重要的。
⑦ R. M.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 1956,pp.65-94.
⑧ 關于經典的資本積累模型,參看R. M.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1956,pp.65-94;R.E.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1988,pp.3-42;關于20 世紀90 年代初以來流行的內生技術進步模型,參看P.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Part II,1990,pp.S71-S102;G.M.Grossman and E.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MIT Press,1991;P.Aghion,and P.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March,1992,pp.323-351。
⑨ H. Oniki and H. Uzawa,“Pattern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 Dynamic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anuary,1965,pp.15-38.
⑩ 賴平耀:《貿易與發展:為什么后進國家能夠趕上先進國家》,載《世界經濟》,2001 年第5 期,第8~16頁。
⑾ P. Kuznets,“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il,1988,Suppl.:pp.S11-43;P.Kuznets,“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re a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No.4,199.
⑿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⒀ 這是最早由日本經濟學家提出的日本化與貿易的“雁行模式”運用于國際分工的說法。參看T. Ito, “Japan and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a‘Miracle’in Transi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2,1996。
⒁ 關于“雁行模式”類型的東亞模式,參看J. Kojima,“The‘Flying Geese’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No.11,2000,pp.375-401;K. Ohkawa and H. Kohawa, Lectur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9;I.Yamazaw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Japanese Model, Honolulu, Hawaii: East-West Center,1990。該模式集中關注的是東亞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與貿易經歷的一系列系統的結構性變化。
⒂ 例如,見P. Krugman,“The Myth of the Asian Miracle,” 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4。
⒃ 有關該的討論,參看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