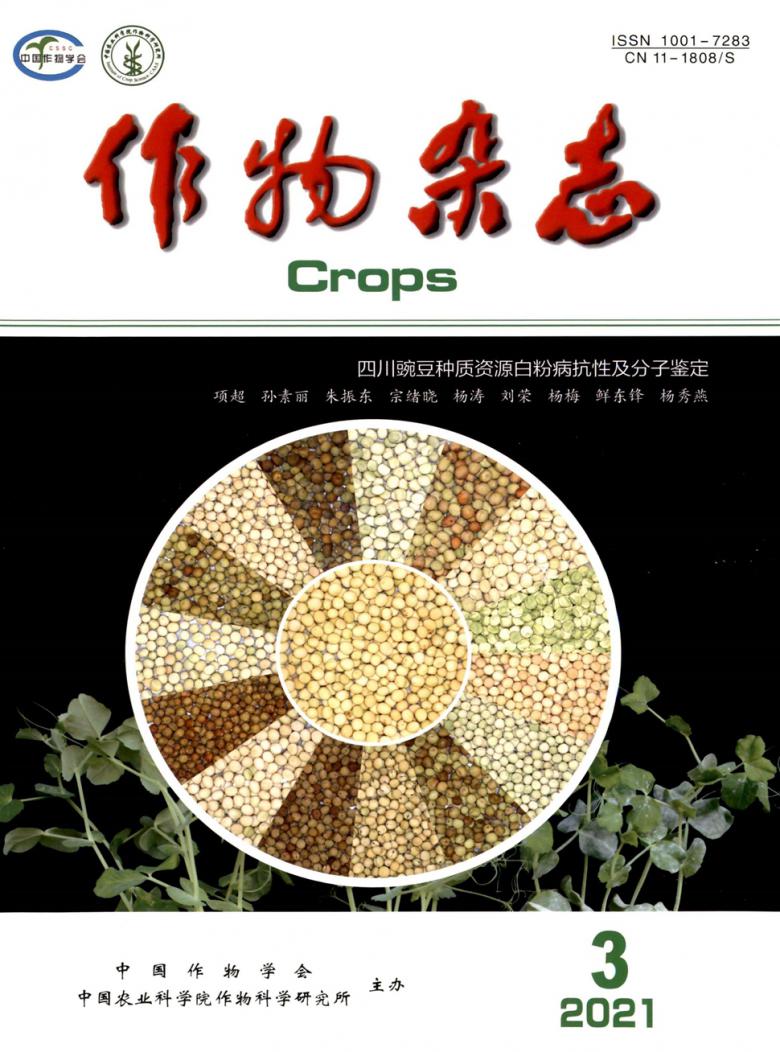17世紀英國憲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程漢大
中文提要:英國以議會制度為核心的獨特的混合君主制在17世紀的形成,彰顯出英國憲政革命出濃厚的博弈色彩。從革命初期到“光榮革命”前的幾十年中,先是國王對議會采取不合作策略,繼而是革命陣營內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間互不妥協;再后是議會妥協過度,君主專制復辟,博弈過程總是以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結束。最后在“光榮革命”中,國王、輝格黨、托利黨以及兩黨內部各派,對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綜合權衡,并在關鍵時刻和問題上適時地做出必要而適度的讓步,終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現代憲政的歷史偉業。這一過程啟示我們,努力避免負和與零和博弈,爭取實現正和博弈,是一條迅速取得立憲成功的便捷之道。
關鍵詞:英國憲政革命 “光榮革命”英國國王 英國議會 博弈論
一、引言
17世紀英國革命實質上是一次憲政革命。這次革命歷時近一個世紀,整個過程雖然沒有法國革命那樣劇烈的跌宕起伏,但也有“起承轉合”,也充滿了斗爭與妥協、曲折與反復。以往的有關論著因受極左思潮和片面僵化的階級斗爭理論的影響,總是過分強調社會的矛盾性、對立性,而忽視社會的統一性、合作性。在描述英國革命時,總認為革命陣營議會和反革命陣營國王之間的對抗具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不可調和性,因而往往絕對地肯定議會一方的斗爭,而且斗爭越激烈、要求越激進,肯定的力度就越大,而對于革命陣營中的溫和派、保守派及其試圖與國王妥協的要求和行動,總是大張撻伐。所以,學習完英國革命后讀者往往得到這樣一種思想教育:只有死不妥協、斗爭到底才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否則就是不齒于人類的懦夫、叛徒。這種邏輯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我們對斗爭也不能持絕對否定的態度,因為沒有斗爭社會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應該否定的只是無限制、無休止的斗爭。另一方面,妥協也不能絕對的肯定,如果放棄原則,妥協過頭,就可能錯過一次歷史發展機會,甚至會導致歷史倒退,所以,只有適度合理的妥協才是應該肯定的。總之,斗爭也好,妥協也好,都應該注意分寸,掌握好一個“度”,也就是將斗爭與妥協、沖突與合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不過,要恰當地把握好二者的“結合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既需要必要的客觀環境條件,更需要歷史經驗的積累和科學理論的指導。所幸的是,近年來出現的博弈論能夠為我們提供方法論方面的幫助,因為這種理論本身就是以沖突與合作關系中的對策互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本文就是運用這一新理論來重新審視和詮釋17世紀英國憲政革命的一種嘗試。
博弈論(game theory)最初是作為數學的一個分支,由美國數學家約翰·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和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發表的合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當時他們主要探討的是經濟領域中的合作博弈與合作均衡現象。進入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納什(John Nash)連續發表《N人博弈的均衡點》(1950)和《非合作博弈》(1951),將研究重點轉向非合作博弈現象,提出了非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均衡概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博弈理論。1994年,納什和其他兩位博弈理論家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標志著博弈理論得到了科學界最高權威的肯定。此后,博弈論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國際關系學、法學、史學等許多學科研究,成為當今最走紅的方法論之一。
博弈論是在棋弈、橋牌游戲規律的啟發下運用數學方法構造的一種行為科學理論,它研究的重點是各個理性個體在其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及其后果問題,即在某一特定條件下,博弈參與人如何針對其他參與人的策略選擇做出相應的對策選擇問題,所以,博弈論又叫對策論。若從博弈參與者的行為特征來區分,博弈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發生源于博弈主體單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目標,而實現合作博弈的前提則是博弈主體在首先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兼顧到對方的利益。若從博弈的后果特征來區分,可分為正和博弈、負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正和博弈的結果可用“互惠互利”、“皆大歡喜”來形容;負和博弈的結果可用“兩敗俱傷”來形容;零和博弈的結果可用“此消彼長”、“一方受益、一方受損”等術語來形容。從功利主義角度講,負和博弈對雙方來說都是有害無益,是應當盡力避免的。零和博弈的結果具有非均衡性和非穩定性,往往導致“以牙還牙”、循環往復,所以從長遠利益看,對雙方也都是不利的。就博弈參與各方的整體利益來說,正和博弈的結果是最為理想和持久的。
二、17世紀英國博弈立憲的理論根據和現實基礎
列寧曾經指出:“憲法的實質在于: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于選舉代議機關的選舉權及代議機關的權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現了階級斗爭中各種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①]據此可以推斷出,憲政本質上是各種社會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對比結構在國家政治體制上的反映。過去,由于受“階級統治工具論”法律觀的影響,人們未能準確領會列寧上述論斷的真諦,總是把憲法、憲政看作是一個階級剝削壓迫其他階級的統治形式和手段。近年來法學界和政治學界的理論研究和史學界的經驗研究均已證明,大凡真正意義上的憲政,無一不具有妥協性、平衡性,[②]其中包括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權力與責任之間、權利與義務之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中央和地方政府內部不同權力機關之間等各個層面上的相互妥協與平衡。盡管不容否認的是,許多國家(指專制國家)的立憲進程通常是以暴力革命為起點的,但暴力革命的實際意義只是排除舊制度的障礙,為啟動立憲進程開道鋪路。如果暴力革命不能適可而止的話,社會將深陷政治動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憲政大廈將很難建立起的。1789年到1875年法國立憲的曲折歷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在這不足百年的時間內,接連發生了5次暴力革命,使一次又一次的立憲努力在持續的政治動蕩中相繼化為泡影。相反,成熟穩固的憲政都是在承認社會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積極吸納社會主要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共同參與,通過各種不同政治利益和要求間的非暴力式的相互斗爭、協調、融合,最后達致整合性平衡的結果。所以,常態的立憲過程實際上都是一個博弈過程,而且立憲的最終成功總是與正和博弈聯系在一起。因此,將博弈論運用于立憲過程分析剛好是“適得其所”、“用其所長”。
與法國等其他國家的憲政革命相比,17世紀英國憲政革命的博弈特征表現的尤為明顯,這是因為在中世紀后期英國形成的特有的政治制度環境所決定的。博弈論認為,博弈的發生需要一定的博弈情境(game situations),即:各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是相互關聯的,既彼此依存,又互相沖突,同時,既定的制度環境具有某種程度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為參與主體提供必要的行為選擇余地,即策略空間(strategy space)。革命前英國特有的混合君主制基本符合這些情境條件的要求。
英國的混合君主制形成于16世紀都鐸王朝時期,它由國王、上院(貴族)、下院(平民)三部分組成,以國王為主導,英國學者稱其為“國王在議會中”(King in parliament)。這種混合政體結構最初萌芽于13世紀,其標志是議會的產生。不過,在14-15世紀時期,由于組成議會上院的貴族是國內除國王之外最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有足夠的力量與國王分庭抗禮,不時對王權提出挑戰,而當時組成議會下院的平民羽翼未豐,還無力自立于政治斗爭舞臺,所以經常搖擺于國王和貴族的“雙峰”之間,但多數情況下站在貴族一邊。因此,國王在混合君主制中的優勢地位因時常面臨貴族與平民聯盟的強大威脅而始終處于不穩定狀態,有時甚至不得不暫時屈從議會兩院的控制(如15世紀),致使國內政局長期動蕩不寧。經過兩個世紀的反復較量,特別是15世紀后期的玫瑰戰爭之后,許多世家望族人死家滅,貴族勢力銳減,喪失了以往與王權抗衡、左右國家政治的能力。與此同時,以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新貴族為主體的平民階層勢力迅速上升,但受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的時代局限,他們還沒有力量和條件在混合政府結構中充當主角。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關系一度呈現勢均力敵的平衡狀態。在這種平衡造成的社會縫隙中,王權獲得了迅速膨脹的大好時機。從國際環境看,當時正值民族主權國家勃興之時,歐洲各國紛紛告別了中世紀封建分裂狀態,建立起以個人專權為特征的絕對君主專制國家。在國內外形勢均有利于權力集中的時代條件下,都鐸王權空前強化,呈現出明顯的專制主義趨向。然而,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在于,英國的議會制度歷經幾百年的持續發展后,到這時已經根深蒂固,都鐸王權已無法逾越這個障礙,建立大陸式的絕對君主專制。他們只能因勢利導,利用議會,而不能甩開議會。于是,便出現了“國王在議會中”的混合君主制。
在混合君主制下,國王和議會一方面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誰也吃不掉誰,另一方面又彼此沖突,誰都渴望在政治運作中發揮主導作用,甚至企圖控制對方。但就16世紀的整體情況看,國王在混合政府結構中一直穩固地保持著核心地位,用亨利八世的話說就是,國王是“首腦”,議會兩院是“四肢”,“首腦”和“四肢”緊密結合一起,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政治共同體”(a body politic),即國家。[③]
以國王為主導的混合君主制是16世紀英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這意味著它只具有暫時的合理性。當歷史的車輪駛入17世紀時,原有支撐它的那些國內外條件已不復存在,混合君主制特別是王權的主導地位出現嚴重危機。因為到這時,英國的宗教改革已勝利結束,羅馬天主教皇的勢力被逐出國外,以國王為最高首腦的國教教會確立起在全國的統治地位。1588年殲滅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后,建立民族主權國家的歷史任務宣告完成,英國開始躋身于歐洲強國之列。另一方面,工農業資本主義出現長足發展,以手工工場主、商人、鄉紳、農場主為主體的平民力量迅速壯大,政治上日益成熟,他們不愿繼續在混合政府中屈居王權之下,希望調整議會與國王間的權重關系,即限制王權,擴大議會的權力,建立以下院為主導的君主立憲制度。這說明,以國王為主導的混合君主制與新的社會政治力量對比結構的關系已陷入嚴重失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對國家權力配置結構做出相應的調整,才能保持社會政治的穩定發展。然而,這時統治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卻不顧時代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宣揚“君權神授論”和“王權無限論”,試圖進一步強化王權,削弱議會的權力,把混合君主制推向大陸式的絕對君主專制軌道。于是,一場憲政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革命前英國特有的混合君主制表明,英國憲政革命的背景、任務和方式,與長期實行絕對君主專制的法國憲政革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法國,必須動用大手術,首先徹底推翻舊制度,然后另起爐灶,方能建立一套全新的憲政制度。而在英國,無須徹底摧毀舊的機構設施,只要對國家權力的配置結構加以調整,改變國王和議會的權重比例,使之由原來的國王主導型變為議會下院主導型就足以完成憲政革命的歷史使命。這就決定了英國憲政革命是一次特殊類型的憲政革命[④],它不但可以通過博弈形式開其端,而且最后能以博弈形式告其終。參與博弈的主體主要是國王和議會下院,上院貴族作為一個被動力量一分為二,分別站在國王或下院一邊。
三、對英國憲政革命的階段博弈分析
回顧近一個世紀的英國憲政革命過程,我們看到的是一副生動形象的迭演博弈(repeated game)的動畫長卷。其中,既有非合作博弈,又有合作博弈,既有零和博弈,又有正和博弈,而且,除了正常形態的博弈外,還有非常態的畸形博弈。但從總體上看,整個過程呈現出從非合作到合作、從零和到正和、從畸形到常態的發展趨勢,最后以合作的正和博弈而告結束。根據博弈主體及其行為特征的變化,從1603年到1688年間的迭演博弈過程大致可劃分為6個階段。
1603年到1640年是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特點是,盡管偶爾出現合作博弈,但大量和主要的是非合作博弈。博弈首先圍繞宗教問題展開。當時,英國的清教運動正如火如荼,清教徒們一度幻想國王能支持他們的宗教改革主張,組織千名牧師上書請愿,要求國王進一步清除國教教會中的天主教殘余,包括取消主教制。國王認識到“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不但堅決予以拒絕,而且支持以大主教勞德為首的“高教會派”,大力加強主教的權力和宗教儀式主義。于是,清教徒們便轉而尋求議會的支持,所以宗教問題成為議會與王權斗爭的焦點之一。財政稅收問題是另一斗爭焦點。斯圖亞特王朝的財政極度困難,多次召開議會要求征稅。議會因不滿于政府政策,幾乎每次會議都要求“先糾正弊政、再討論撥款”,致使國王政府和議會之間經常陷入僵局。每當出現這種情況,國王總是蠻橫地宣布解散議會,然后強行征稅各種非法稅收,違抗者則被逮捕。1610年,商人議員曾建議簽定一份“大契約”,通過商業交易方式解決財政沖突,由議會每年撥款20萬鎊,換取國王放棄封建捐稅和優先采買權,但由于國王要求再追加10萬鎊,議會難以接受,使這次協商解決財政問題的努力歸于失敗。[⑤]
由于每次討論征稅案時議會總會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由此又引發出言論自由等議員特權問題。國王認為,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國王的專有權力,不屬于議會的討論范圍,所以總是壓制議員的辯論自由,多次將批評政府的議員逮捕入獄。對此,議會堅持自己有權不受限制地議論國事,聲稱這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和自由,不亞于土地和物品財產權”。[⑥]議會還試圖影響和控制政府政策,例如,1621年議會反對與天主教國家西班牙聯姻,要求介入大陸“三十年戰爭”,支持新教集團,在1624年通過《反專賣制度法》,規定除具有鼓勵發明作用的專利項目外,對其他一切專賣行為將根據普通法準則進行審查等。該時期議會還對國王的親信大法官培根、財政大臣克蘭菲爾德和白金漢公爵提出彈劾,顯示出議會希望政府大臣對自己負責的政治訴求。
總的看來,該時期的憲政博弈集中在具體問題上,并以議會抵制國王濫用特權為主要表現形式,但實質是議會與國王爭奪國家最高主權。由于國王依靠強大的優勢地位,態度強硬,極少讓步,結果導致非合作博弈一輪接一輪,反復進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圓滿解決。王權與議會的沖突愈演愈烈,最后,混合君主制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出現了1629-1640年長達11年的“無國會”統治。
從1640年長期國會召開到1642年內戰爆發是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長期遭受壓抑的國民不滿情緒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議會向王權展開積極主動的進攻,而國王則迫于形勢,接連做出了一系列的讓步,所以一度出現了合作博弈的勢頭。如國王批準了對斯特拉福和大主教勞德的彈劾案,將他們處死;簽署了《三年法案》,答應每三年召開一屆議會,未經議會本身的同意不得被解散;同意取消了噸稅、磅稅、船稅、騎士捐、國王優先采買權等未經議會同意的非法稅收;撤銷了星室法庭、高等委任法庭、北方法庭、威爾士邊區法庭等特權法庭。這些合作博弈成果,削弱了國王推行專制的財政來源和法律手段,使議會和普通法的權威得到提升,把英國拖離了君主專制的政治發展趨向。但由于議會還未明確提出主權要求,不打算改變國王在國家權力機構中的主導地位,因此,盡管議會反專制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很少觸及根本制度的結構改造問題。從總體上看,議會和國王的權力關系在這一時期還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這時期國王之所以采取合作策略,主要是蘇格蘭起義帶來的巨大政治軍事壓力,迫使國王不得不通過讓步來換取議會的財政支持。然而,不管國王如何的情不自愿,但只要這種合作博弈能夠持續進行下去,英國有可能避免后來的流血內戰,提前半個世紀就能和平地邁入憲政大門。
到1641年,隨著時局的發展,議會開始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這年2月,議會通過了《大抗議書》。與議會以往通過的文件相比, 《大抗議書》是一個憲法性文件,它列舉了幾十年來國王濫用權力的種種暴政,要求進行立憲改革,包括由議會任命政府官員,建立對議會負責的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商業自由和企業經營自由,以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限制主教權力,停止宗教迫害,取消煩瑣的宗教儀式,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大抗議書》勾畫出了一幅立憲君主制的藍圖,標志著博弈斗爭已深入到國家體制改革的深層領域。羅弗爾曾指出,“假如那時國王接受有限君主制和同意非勞德派教會,他將有可能贏得臣民的忠心,從而阻止激進派提出進一步的要求。”[⑦]但查理一世認為,議會要求官職任命權是對國王固有行政權的侵犯,同時,他從《大抗議書》僅以11票多數險獲通過和隨后討論宗教《根枝法案》時議會內部的嚴重分歧看到了重振王權的希望,斷然拒絕了《大抗議書》,還親率衛兵前往議會大廳,試圖逮捕皮姆等五位反對派領袖,此舉標志著國王開始轉向不合作立場。議員們則從這一事件中察覺到國王可能使用武力鎮壓議會的危險,所以在隨后討論民兵法案時,堅持由議會控制民兵的指揮權。逮捕五位議員的企圖失敗后,查理一世非但未接受教訓懸崖勒馬,反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偷偷地離開倫敦,趕往保王派聚集的北方重鎮約克,打算招兵買馬,用武力壓服議會。這一愚蠢的選擇,使他失去了與議會妥協的最佳時機,也使英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642-1648年即內戰時期是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王權和議會之間的非合作博弈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其根源在于國王死心塌地地選擇了不合作立場。在查理一世前往北方的途中,議會仍然試圖與他談判解決爭端,查理一世表面上假裝準備和談,建議議會以書面形式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便仔細考慮,但其真實目的是借此拖延時間,以便平安到達約克。議會通過了《十九條建議》,作為與國王談判的基礎。其主要要求是:①任命樞密院大臣以及包括大使在內的一切高級官員時必須得到議會的同意,由議會委任的人組成政府;②進一步實行宗教改革;③無條件地批準民兵法案,由議會選拔的人接替要塞的司令,解散國王未經議會同意而募集的軍隊;④司法機關應當獨立,未經議會同意不得撤換法官。
很明顯,這些要求一旦實現,混合君主制中的權力重心將從國王一邊轉到議會一邊,國家政治體制將變為君主立憲制,這是查理所不可能接受的。況且,這時國王已募集到一支保王黨軍隊,王后在國外爭取外援的活動進展也很順利。查理一世有恃無恐,在讀完《十九條建議》后怒斥道:“批準這許多條件之后,我們早已被拒之門外,我們不過空有國王的虛名,不過徒有國王的象征而已。”[⑧]于是,他斷然終止了與議會的一切談判。至此,一切和平解決憲政沖突的道路都堵死了。1642年8月23日,國王宣布“討伐議會”,悍然挑起了內戰。
內戰的爆發意味著博弈的中斷。盡管內戰初期議會陣營中的長老會派沒有放棄和平解決憲政沖突的努力,多次提議與國王談判,但查理一世不但是一個頑固的專制主義者,而且是一個兩面三刀的陰謀家。當他在軍事上處于優勢時,便直截了當地拒絕和談;當他處于軍事劣勢時,便虛與委蛇,麻痹議會,伺機反撲。國王還試圖通過卑鄙的離間手段,挑起議會陣營的內訌,以爭取軍事上的勝利。國王的不合作使長老會派的和談努力全部落空,也為較激進的獨立派奪取革命領導權提供了機會。1644年底,獨立派控制了議會軍,他們采取果斷措施,連續取得兩次內戰的勝利。
1649-1660年即共和國時期是第四階段。內戰結束后,議會于1649年成立特別最高法庭,審判并處死了查理一世,宣布取消君主制,成立一院制共和國。由于共和制的建立只是查理一世的頑固不化所激起的社會反彈力和革命慣性的作用所導致的產物,既缺乏現實基礎,更不符合英國的文化傳統,所以共和國的建立并未解決英國憲政問題。于是,憲政沖突從兩軍對壘的戰場又重新返回博弈軌道,但此時的博弈參與者已經改變,代表軍官集團利益的當權派獨立派和代表士兵和下層人民利益的平等派成為博弈的兩大主體。
平等派在其政治綱領《人民公約》中,提出了許多民主主義性質的憲政要求,如實行普選制,建立一院制國會,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獨立派則提出了《施政文件》,主張建立護國主制。它規定,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護國主和國務會議擁有最高行政權,保持現有軍隊,議會必須保證軍費和每年20萬鎊的行政經費。
兩派綱領的差異是明顯的,《人民公約》勾畫出了一副民主憲政的藍圖,而《施政文件》設計的共和制則只是徒有虛名,因為它缺乏制約護國主權力的有效機制。但是,如果雙方采取合作策略,通過正常的博弈過程即對應互動決策過程,或許能找到共同利益的交匯點。然而,當權的獨立派根本不與平等派平等對話,而是單邊決策,對平等派采取了暴力鎮壓政策,從而把英國推上了一條畸形博弈之路。
畸形博弈導致了畸形的政治后果。《施政文件》被獨立派單方面地強行付諸實施,結果出現了護國主名義下的個人軍事獨裁。此間,也曾幾次召開議會,但它只不過是護國主的掌中玩偶,被克倫威爾任意呼來喚去。英國人民砍掉了一個專制國王的腦袋,卻迎來了一個更為專制的無冕之王。英國人開始反思了,他們發現,廢除君主制并非上策,要達到建立憲政的目標,看來還得從“國王在議會中”的混合體制的基礎上重新開始。于是,流亡國外的舊王朝又被請了回來。
1660-1688年復辟時期是第五階段。復辟重建了“國王在議會中”的混合政府體制,而且,國王查理二世和議會雙方均接受了前20年的教訓,甘愿相互妥協與合作。然而,由于當時議會過分注重眼前的政治需要,渴望盡快結束動蕩,重建“有效統治”和國內秩序,因而不但回避了引發這次革命的那些關鍵性問題,而且在財政問題上過于慷慨大方,一次性給予復辟政府以充足的撥款,使王權迅速實現了財政獨立。可見,復辟初年的博弈實質上也是一種非正常的畸形博弈。其結果是,國王在不久之后便有條件放棄與議會的合作,再次退回到不合作的老路。從1681年起,國王對議會反對派采取高壓政策,輝格黨土崩瓦解,王權迅速膨脹。在查理二世統治的最后4年內,再未召開議會,革命前的無國會統治卷土重來。1685年詹姆士二世繼位后,利用每年200萬鎊的巨額歲入,建立起一支3萬多人的軍隊。他不顧議會的反對,在國內外政策上獨斷專行,對外推行親法政策,以換取法王的財政津貼,對內力圖恢復天主教。英國再次滑向君主專制的邊緣。這一事實證明,無原則的過分妥協和無限制的過分斗爭一樣,都不會收到理想的博弈效果,達到預期的憲政目標。
“光榮革命”構成第六個階段。1688年,荷蘭執政威廉應議會之邀,率軍入主英倫,詹姆士二世倉皇逃亡法國。在隨后的一年內,英國的各派政治力量汲取了前五個階段的經驗教訓,選擇了正確的合作博弈之路,從而取得了憲政革命的巨大成功。這一點集中體現在王位問題的解決中。
當時,圍繞王位問題存在三種要求不同的政治勢力,即威廉、輝格黨和托利黨,其中威廉控制著政局,輝格黨控制著下院,托利黨控制著上院,他們共提出了五種解決方案。下院首先提出一份決議,宣布“詹姆士二世已背棄了國王和人民之間的原始契約,力圖顛覆王國憲法,而且業已離國出走,自行退位,致使王位虛懸。”[⑨]該決議表達了多數輝格黨人的意見,但遭到上院托利黨人的普遍反對。托利黨認為,詹姆士二世出走國外僅僅意味著他放棄了國王權力的行使權,但他的國王資格和頭銜并未因此而喪失,即王位并未“虛懸”;“自行退位”說缺乏法律依據,宣布“王位虛懸”的結果必將是由議會來填補虛空的王位,這將根本背離英國正統的王位世襲制原則。所以,他們要求修改決議,將“王位虛懸”一句話刪掉,將“自行退位”(abdicated)改為“擅離職守”(deserted)。據此,托利黨提出了一個自認為是“最接近(英國)法律的最佳辦法”,即實行攝政制(regent)。為消除分歧,求得一致,兩院中的兩黨分別選派部分代表舉行磋商會,會上爭論十分激烈。輝格黨人援引1399年議會使用“自行退位”一詞廢黜理查德二世的先例,證明“自行退位”說的合法性,同時引用內戰期間的事例,證明“擅離職守”說和攝政制暗示著國家統治方式只是“暫時的和可以隨時解除的”,[⑩]這勢必給詹姆士二世的復辟提供法律依據。托利黨也不愿看到詹姆士卷土重來的可怕后果,最后做出讓步,同意將下院決議原文公布。
接下來博弈集中在由誰繼承王位的問題上。輝格黨多數主張由威廉繼承王位,其理由是,威廉是一個新教徒,又有政治經驗和才能,他雖然沒有斯圖亞特血統,但作為詹姆士二世長女瑪麗的丈夫繼承王位也未嘗不可,況且,正因為威廉缺乏合法的繼位資格,所以更便于議會預先對王權規定某些明確的法律限制,作為擁戴他登基的先決條件。另有極少數激進輝格黨人希望廢除君主制,像1649年那樣建立共和國。[11]但大部分托利黨人主張由瑪麗繼承王位,他們認為,既然詹姆士和享有優先繼位權的小王子都已逃亡國外,那么,瑪麗作為詹姆士的長女,就“自動地”繼承了王位,因為國家不可一日無主。還有少數托利黨極端派主張,只要詹姆士答應做出某些讓步,就邀請他回國繼續當政,其理由是,根據正統主義原則,只有詹姆士是惟一合法的國王。
上述四派各執己見,使議會一度陷入僵局。后來,有人提出一個折中意見,這就是第五種方案:由瑪麗和威廉共同繼承王位。這個方案既符合正統主義原則,又能滿足當時政治需要,所以被多數托利黨和輝格黨人所接受。不過,在威廉和瑪麗應以誰為主的問題上,兩黨和兩院仍然意見不一。下院輝格黨主張以威廉為主。上院托利黨主張以瑪麗為主,威廉只能作為瑪麗的配偶而行使王權。威廉堅決反對上院的主張,他召見了部分貴族,明確告訴他們:“他決不會僅僅充當瑪麗的代理人”,并威脅說,“如果不給予他充分的王權”,他將立即率軍隊回荷蘭去,聽任英國陷入動亂的旋渦。[12]面對威廉的要挾,托利黨人做了讓步,同意瑪麗為女王,威廉為國王,以威廉為主。這樣,一種空前絕后的雙王君主制就在英國出現了。這一結局是三種勢力、五種意見相互斗爭與妥協即合作博弈的結果,它實現了博弈各方集體利益的最大化。
隨后,在調整國王和議會權力關系的“憲法解決”中,議會選派代表有意識地把王冠和早已擬好的《權利宣言》一起呈現給威廉和瑪麗。《權利宣言》明確規定了人民和議會享有的各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實際上相當于西方思想家筆下的“社會契約”。盡管當時議會沒有明確要求新國王正式簽署它,但把它和王冠一起呈獻,并當面向新國王宣讀,暗示著接受這個“契約”文件是接受王冠的先決條件,而威廉同時把二者收下,意味著已心領神會,默許了其中的法律規定。1689年,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將《權利宣言》上升為憲法性法律。1701年,議會又通過《王位繼承法案》,對王權又規定了許多新的限制。對于這兩個至關重要的憲法文件,威廉都一一予以簽署。威廉與議會各派的合作態度使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憲法沖突得以圓滿解決,國王的法律中止權、豁免權被廢除,國王隨意任免法官的權力被取消,司法獨立制度確立起來,軍權被置于議會手中,國王獨立于議會之外的一切財政來源均被剝奪,英王“靠自己生活”的歷史宣告結束,此后,國王離開議會的財政支持將寸步難行。另一方面,“憲法解決”又給國王保留了決策權、行政管理權、大臣任免權等,從而為國王有效治理國家提供了基本保證,但這些保留權力必須在議會和法律的廣泛而明確的限制范圍內行使,因而又能避免專制統治的危險。這樣,通過合作型正和博弈,國家權力的配置結構得到重要而適度的調整,現代憲政在英國從此建立起來。
總之,由于參與“光榮革命”的各派政治力量選擇了合作博弈形式,于是,各種不同的憲法訴求便“構成了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形成“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其中每一種力量都力圖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由于每一種力量無不受到其他力量的牽制,因此它們都不可能達到自己的最佳目標,結果是各種力量和要求在相互沖撞和抵消中“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13]由此導致的最終結局雖然與各種力量的要求都不是完全符合的,但卻兼容了每一種力量的要求,因而也是誰都沒有理由完全反對的。英國學者米勒指出,“革命解決”有一個“偉大的優點”,那就是“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全不能接受它的。”[14]這一優點正是“光榮革命”成功的奧秘和“光榮”稱號的根據所在,而這一切歸根到底都是正和博弈的功勞。
四、結語
17世紀英國憲政博弈過程告訴我們,如何避免零和博弈和負和博弈,努力創造條件,以實現正和博弈,是迅速取得立憲成功的一條便捷之道。這一經驗后來相繼得到其他國家的歷史驗證。美國人在1787年制憲會議上,正確地選擇了合作型正和博弈,結果一舉立憲成功。法國人、德國人因受客觀條件和傳統文化所累,在立憲初期走的是非合作型的負和博弈與零和博弈之路,所以立憲進程崎嶇坎坷,走了許多本可避免的彎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證明了同一個道理:正和博弈是立憲成功之道。
通過對英國憲政革命的博弈分析我們體會到,把博弈論引入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眾所周知,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動物界的根本區別在于,自然界完全受制于客觀規律,動物界則主要聽命于本能的支配,而人類是萬物的靈長,是有自覺意識的智能動物,他(她)們能夠借助理性之光,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局限,做出有目的的自主選擇。所以,馬克思說,“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5]“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6]由于利益需求的不同,人們的歷史選擇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同的歷史選擇必然導致不同的歷史結局,由此才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歷史。當然,從宏觀上講,歷史發展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在微觀層面上,由于存在不同歷史選擇的可能性,所以往往是充滿變數的。過去,由于人們經常把歷史的宏觀規律性機械地套用到微觀歷史的研究中,從而有意無意地抹殺了歷史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歷史選擇性,致使不同的歷史選擇及其對歷史的影響成為歷史研究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弱點”、“虛點”甚至“盲點”。結果是,一部本來充滿了無限變數的活生生的人類歷史,變成了一個自然而然的機械性流程,研究歷史就像解一個數學方程式那樣簡單。引入博弈論思路,有助于彌補傳統方法的不足,因為博弈論所關注的正是人們的不同歷史選擇及其對歷史進程的作用。
從博弈論的視角回顧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將不難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社會就是一個無休止的龐大復雜的博弈局。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人類理性水準的低下,非合作博弈是長期而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小到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集團,大到一個階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總是追求自己眼前的最大利益,致使非合作型負和博弈與零和博弈充斥于世界每一個角落和社會的每一個層面。盡管這種博弈也是歷史進步的客觀動力之一,但在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歷史進步的同時往往也給人類整體和長遠利益帶來巨大損害甚至災難,階級奴役、民族壓迫、戰爭蹂躪都是人類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借助博弈論,我們可以優化自己的思維方式,提高理性度,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從而有可能在以后的行為選擇中以最小的代價甚至零代價來換取最大、最廣泛的福祉和進步。令人欣慰的是,自從冷戰結束后,國際社會中的對立與沖突范圍縮小了,程度上也緩和了,同時對話與合作增多了,特別是世界人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當前人類面臨的一些共同的全球性挑戰,如人口壓力、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核戰威脅等,都不是單獨一個階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能解決得了的世界性難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才有望獲得解決。所以,通過合作博弈以達到“雙贏”、“多贏”、“共贏”,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爭取的目標,而博弈論恰恰能夠給予人們的這種共識以科學的理論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說,博弈論可以為人類正確應對目前的各種世界性挑戰和共同謀劃美好未來提供有益和有效的行動指南。
[①]《列寧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9頁。
[②] 參見:謝維雁:《論憲政的平衡性》,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趙頌平:《憲法的平衡品格》,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第1期。殷嘯虎:《協商精神與憲政建設》,載《法學論壇》,2002年第1期。
[③] G.R.Elton,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70.
[④] 近幾十年來,國內不少學者甚至認為17世紀的英國革命不是一次嚴格意義上的“革命”,如陳樂民指出:“如果不是我們所尊崇的馬克思稱它為‘革命’,似乎就可以把英國革命‘革’出‘革命’的教門了。”見陳樂民、周弘著:《歐洲文明的進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11頁。
[⑤] C.R.Lovell,English Consi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296.
[⑥] G.B.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35,p273.
[⑦] C.R.Lovell,English Consi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319.
[⑧] [法]F.基佐:《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伍黨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83頁。
[⑨] M.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0,p229.
[⑩] M.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0,p231.
[11] G.E.Aylmer,The 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8.p220.
[12] J.Miller,The Glorious Revolution,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22.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頁。
[14] J.Miller,The Glorious Revolution,Longman Group Limited,London,1983,P8.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8-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