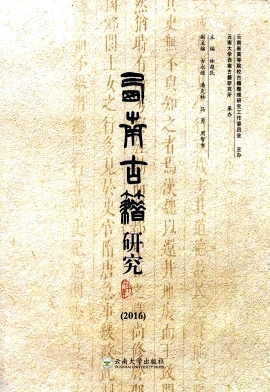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簡析
佚名
[提要]米塞斯學論歷來被作為先驗論的極端表現而不受重視。本文把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區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的具體方法,即先驗性的演繹方法;二是關于什么才能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實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米塞斯經濟學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她揭示了社會中事實性和規范性內容之間的互動。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5]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接下來,我們詳細這兩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目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7]行動是有意識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8]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是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參照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9]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也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定義的理解,即對行動之主觀意義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價值判斷,涉及的是目的的選擇以及借以達成這些目的之手段的選擇,涉及的是對行動結果的評價。"[10]
米塞斯認為人類行動科學有兩個分支:歷史學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praxiology)。歷史學是關于人類行動的理解性的經驗科學,而人類行動學則是關于人類行動的先驗性的演繹科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離開歷史學的研究,但經濟學理論本身則屬于人類行動學。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并不是多少帶有推測性的理解,而是一種嚴格的邏輯演繹。經濟學法則不是經濟歸納的結果,而是從不依賴于具體經驗而不言自明地呈現于人類心智中的公理邏輯演繹的產物。這個公理即"行動范疇"(category of action),它包含了我們賴以理解具體行動經驗的所有結構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無謂、收益和損失等等。它比具體經驗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一樣,在借助附加的、以經驗為根據的,而且可以證實的假設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地從公理演繹和推導出來的經濟法則也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繹方法對于建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是否可行,不是這里所討論的問題。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主張有其獨特的哲學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立場不但是一種"泛物理主義";同時,在有關經濟學知識的意義問題上,它又是一種波普爾式的證偽主義。用薩繆爾遜的話說,經濟學的目的是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對于有意義的原理我只不過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那么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事實上,從操作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的確暗示了對可觀察的量的某種限制,可以想象,通過這樣做它可能遭到反駁。"[11]只有這種知識才能提供對經濟過程的科學預測。而米塞斯則認為,經濟法則事實上不依賴于經濟事實的證實或證偽,它沒有預測性價值,然而卻不能由此說它沒有意義。經濟法則作為人類行動的一般結構,其意義在于提供了我們賴以理解經濟現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學和演繹科學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是演繹性的,但經濟科學的總目標則是理解人類行動及其結果。以上的說明,米塞斯的先驗認識論是服務于一個更為深刻的立場的,即學是旨在理解人類行動的,而不是預測和操縱經濟生活的科學。但為什么說經濟學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預測和操縱呢?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其他科學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預設著一種社會或社會,對社會的存在和運作方式作出理論說明。關于社會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認為一種常見的錯誤是把社會當作一種實體性的存在。在他看來,社會只是個人之間的合作,必須還原為個人的行動。"諸個人行動的特定方面構成了所謂的社會或’大社會’(great society)。但社會本身既不是實體,也非權能(power)或行動者。行動的只有個人。個人的某些行動帶有與他人合作的意圖。而個人間的合作則產生了由社會這個概念所描述的那種事態。社會并不能脫離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而存在。"[12]社會實在的本質在于諸個體的互動,因此,任何科學有效的對社會實在的分析,都必須回過頭來指涉個人的行動,而行動是由行動者主觀預期的意義所塑造的。對社會現象的研究最終必須追溯到對個人行動及其意義的理解,這便是與自由主義互為表里的"論的個體主義"。
米塞斯認為,人類經濟生活中那些明顯的秩序并非人們有意設計的結果,而是諸多并未明確意識到其所做所為會有如此結果的個人的行動之產物。它們是一種"自發性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發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貨幣的使用。貨幣作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是誰也沒打算創造貨幣制度的許多單個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動的結果。[13]各種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從簡單的分工到高度復雜的市場經濟,也同樣如此。經濟學對經濟秩序的解釋,必須追溯到產生這種秩序的有意識的個人行動。經濟學的研究是對個人行動及其結果的理解和理論重述。自凱恩斯以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普遍傾向是通過對宏觀經濟總量的數學分析提供預測和操縱經濟過程的理論依據。用凱恩斯的話說,經濟學家"的最后任務,也許是在我們實際生活其中的經濟體系中找出幾個變數,可以由中央當局來加以統制或管理。"[14]而在米塞斯看來,這完全是建立在錯誤方法論基礎上的錯誤意圖。宏觀經濟總量的分析完全忽視了個人選擇和相互預期的作用;而按照社會的愿望統制或管理經濟生活,則進一步破壞了經濟的自發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經濟學家那樣認為秩序的自發性意味著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經濟秩序的自發性卻意味著必須高度重視個人的選擇、行動和預期在經濟秩序的形成和運作中的作用。這既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性方法(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也是自由主義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和哲學的規范性主張(尊重個人的經濟自主)。
接下來我以諾齊克和羅爾斯關于分配正義的爭論為例,簡略地分析一下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對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關于分配正義,羅爾斯主張"正義即公平",為確保公平必須實行差別原則,即"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而諾齊克則認為正義即維護個人的權利或資格。一種分配結果只要確保每個人獲得了其有權獲得的份額,是不論平等與否的。[16]由于公平著眼于共時態的人際比較,而權利只對個人的財產獲得行為作歷時態的考察,公平與權利之間并沒有共通的基礎。因此,似乎羅爾斯與諾齊克之間的爭論不存在客觀的標準,像麥金太爾所說的那樣是"不可通約的"。然而,從諾齊克的角度看卻并非如此。在諾齊克看來,先不論羅爾斯的答案如何,他把分配問題看作關于何種分配結果正當的問題,這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分配(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之運作方式的錯誤理解上的。它假設了一種按照某一標準集中、統一進行的分配過程。然而,事實上人們之間的財貨分布狀態是各個個人分散的行動(原始獲得和轉讓)的結果。對分配正義的考察必須建立在這個事實基礎上。因而,恰當的問題就不是什么樣的分配結果正當,而是個人在財貨的原始獲得和轉讓行動中應當遵守哪些規范性原則。[17]這種研究方法,與新奧地利學派將"探索修正個人決策的方法"作為重建主流經濟學的方向[18]的主張是內在相通的。它們的直接來源,即是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注釋:
[1] [18] 參見柯茲納爾《"奧地利學派"對危機的看法》,收于丹尼爾·貝爾、歐文·克里斯托爾編《的危機》,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2] 參閱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版),Basic,1974。
[3] 三本書的全名分別為:《國民經濟學的基本--關于經濟學和學的、任務和的》(德文版原名)、《理論與--關于社會和經濟演變的解釋》、《經濟學的最終基礎--一篇關于方法的論文》。
[4] 轉引自《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頁。
[5] 轉引自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頁。
[6] 米塞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頁。
[7] [8] [9] [10] [12] 米塞斯:《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英文版),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2,第34頁、38頁、48頁、78-79頁。
[11] 轉引自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111頁。
[13] 參見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七節。
[14]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08頁。
[15] 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79頁。
[16] 諾齊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七節。
[17] 由于諾齊克認為洛克的財產權限制條款(proviso)"留下足夠多和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是個人(獲取財產)行為的一條基本規則(《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第137-182頁)。而羅爾斯試圖通過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來消除私有財產條件下契約和交易行為的"交易優勢"(見羅爾斯《自由主義》(英文版),第23頁,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兩人思路不同,但在邏輯上卻又是等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