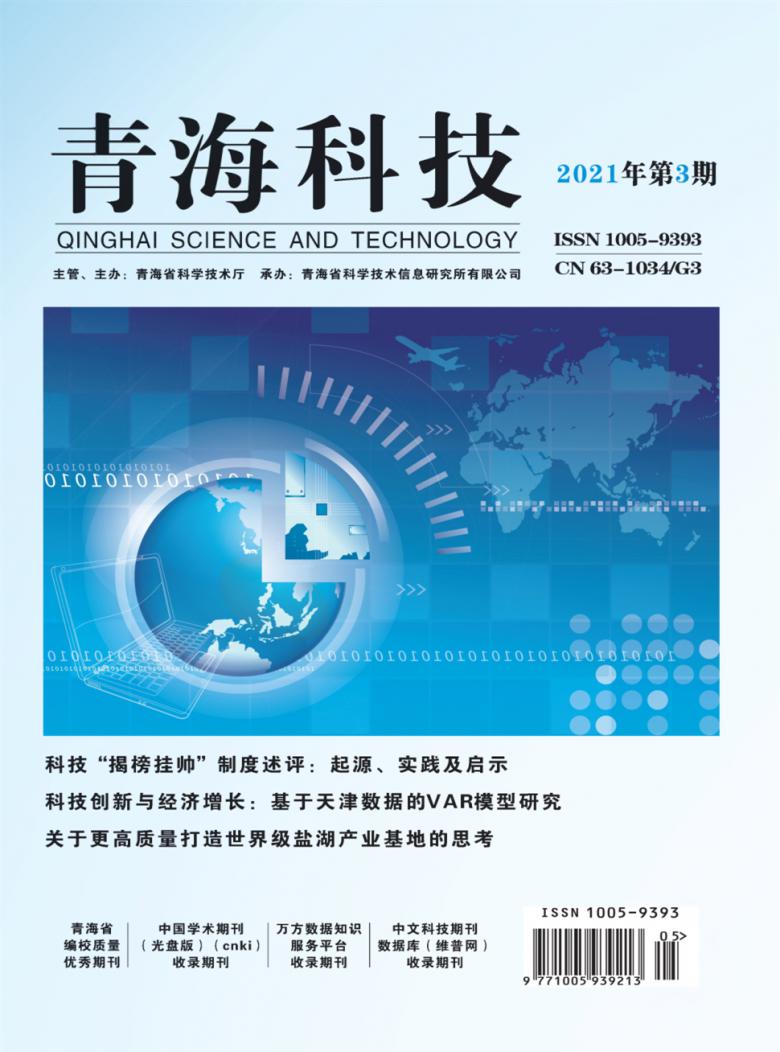關于協商民主的中國空間考察
佚名
基層社會的協商民主之所以能在中國得到回應,超越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爭論而直接進入案例實踐,是因為它符合當下中國政府、政黨和社會在體制內拓展民主的愿望。 因此,對基層民主實踐的表達很容易出現不同的三
個文本:政府的官方宣傳文本、精英的學者研究文本和客觀的民間文本。事實上,雖然這和中國傳統社會的邏輯有著實質區別,但必須警惕這一文本差別造成的誤解。 為什么觀察結果在不同的田野調查個案上存在著一致性?原因就在于基層民主實踐的政府主導性。中國政府的行為邏輯是一致的,所以各地的民主實踐也就很難擺脫這種一致性。即使萌生真正具有草根性的民主,政府的強勢介入和硬性推廣也會使其喪失本來的空間。同時,出版的田野文本應用的理論模式和作者實際觀察的文本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 雖然協商民主在一些個案中體現了巨大的進步,比如浙江溫嶺公共預算的參與式協商,但許多協商民主的實踐都缺乏真正利益的激烈對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個案表達的虛偽性,這在中國缺乏自由主義民主發展階段的情況下,更說明了個案研究的批判性不足。 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民主實踐沒有和國際理論模式接軌的可能性?前面論證的中國當下的社會多重結構本身就為這種接軌提供了可能,問題在于如何定位這種接軌的空間。在應用國際理論時應該首先采取一個批判的態度,這一批判不是批判理論本身,而是用理論去反觀現實和理論在現實載體上的變異。 二、協商民主在中國的個案分析 中國政黨治理社會的領域可分為兩個:一是通過政府體制進行,即從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然后到基層社會治理;另一個就是通過政治協商制度,直接與社會中的階層和黨派進行溝通。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政黨互動,尤其是中華全國工商聯這一組織,我們可以觀察當時協商民主形式與協商民主之間的吻合程度,從而反思協商民主的前提構成。 1、民國時期的商議實踐 如果把時間向前推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也試圖建立類似的機制協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在僅僅存在八個月(1927年3月22日-1927年11月29日)的上海商業聯合會與國民政府的關系中可清晰地看到,它試圖從社會的角度表達上海商業界的利益,協調政府與軍閥以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競爭:“緣本會之所由發起,外應需要,內謀保障。”但由于這一組織是社會自身的組織,和國民政府進行了更多的對抗而不是商議合作,因此中國國民黨取消了工商界自己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然后以自己可以控制的組織進行了代替。 在整個國民政府時期,其所建立的社會協商機制流于失敗,就在于它沒有為社會留下一定空間:“從政治上來講。南京政府完全不理會這些資本家通過上海總商會和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這些組織所表達出來的意見,事實上反而要極力把這些商業團體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從南京政府與上海資本家的交往中的行動說明了它就是這樣一個獨裁的政權。它決心要把這一切獨立的社會力量控制在自己的統治之下。” 2、中國共產黨的協商過程 中國共產黨在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成功地建立了與資本家的協商對話機制。在這一改造過程中,共產黨對待資產階級的態度是比較民主和開放的,許多意見已經充分反映在改造政策中,比如定息、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等,其中的激烈沖突恰恰說明了協商在一定時間內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