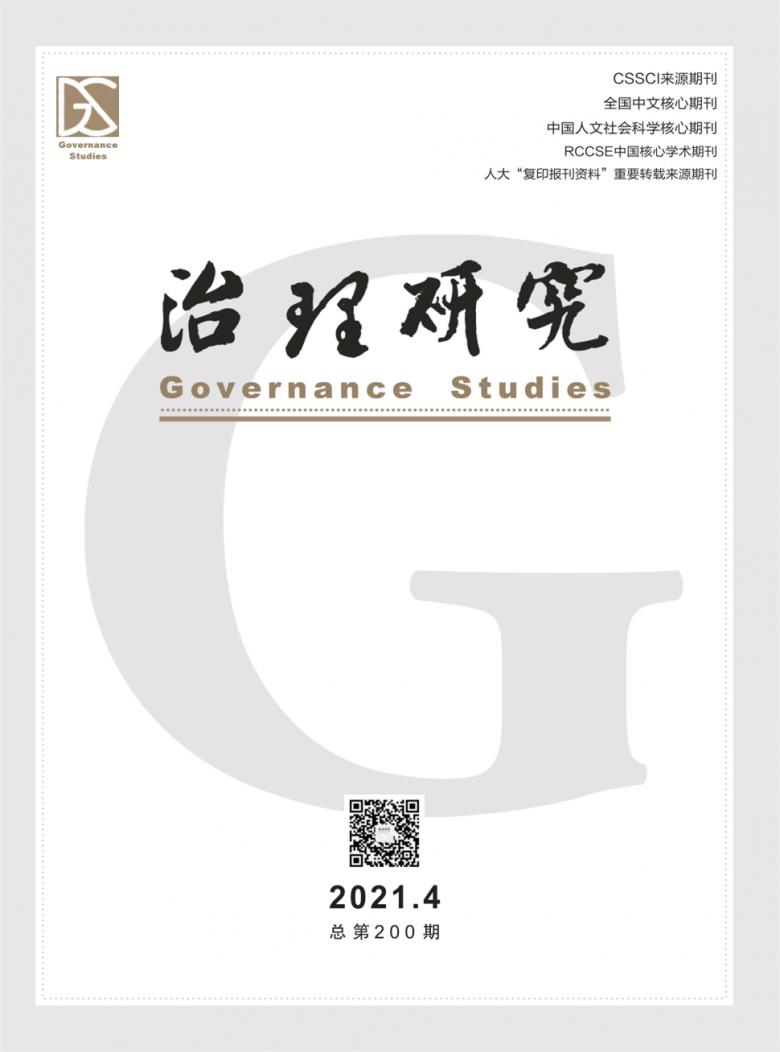20世紀前半期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研究
未知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是近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互作用的產物,它的產生與出現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要影響,對這一群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摘 要 題】中共黨史研究
【關 鍵 詞】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
【正 文】 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個具有統一的理論基礎和共同信念的階級性的政治組織,又是一個由具有不同的經歷、經驗、文化水準、職業、年齡的人群構成的復合文化體。這種復合文化體中具有不同文化意義上的群體間的互動,使得共產黨這一具有生命意義的有機體更具色彩斑斕的性質。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曾對黨內不同的群體進行過分析,并提出正確處理黨內群體之間關系的原則,即“各有長處,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① 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是黨內一個較有特點的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群體。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他們以其固有的特點,在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治組織內,發揮著這樣或那樣的作用,成為共產黨有機體內生動活潑的互動力量。
一、中國共產黨留學生群體代際之劃分
對中國共產黨留學生群體代際之劃分的目的在于對這一群體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和歷史性、總體性的考察。在中國留學生歷史的研究上,一般對一百二十年來留學生群體劃分為六代。本文以廣義留學的概念為基礎,從留學生與中國共產黨這一政治組織的關系出發,對20世紀前半期中國共產黨留學生群體劃分為四代。 第一代:十月革命前留學生群體(1900~1917) 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人的留學生群體應追溯到十月革命前,在世界潮流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碰撞之中,成為后來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弄潮兒已在世界大勢中產生了。從地域上看,中國共產黨人第一代留學生群體是辛亥革命后以留日為中心的,這時期中國共產黨雖然還未產生,但從文化因子上,在留日學生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和決意走“共和”之路的挫折中,已有一批學生以廣闊的眼光觀察世界,接觸和信仰馬克思主義,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出現埋下了伏筆,見表1。 表1第一代: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早期留學生的留學狀況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陳獨秀 1900~1903 日本 1921 在京師范速成科、正則英語學校、早稻田大學 1906~1907 學習 李漢俊 1913~1015 日本 1921 東京法國教會學校、曉星中學、東京帝國大學 1902~1918 學習 成仿俉 1910~1921 日本 1928 東京帝國大學、日本崗山第六高等學堂學習、 1924~1931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 楊匏安 1911~1916 日本 1921 在橫濱半工半讀 李大釗 1913~1916 日本 1921 早稻田大學學習 李 達 1913~1918 日本 1921 自學:先攻讀理科,后學馬列主義 1918~1920 陳望道 1915~1919 日本 1921 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日本中央大學學習, 獲法學學士學位 董必武 1913~1915 日本 1921 東京日本大學學習 1928~1932 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學習 1903~1910 日本 東京成城學校、崗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 吳玉章 1913~1917 法國 1925 巴黎法科大學學習 1927~1938 蘇聯 中山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學習 1910~ 日本 在日本考察小學教育 徐特立 1919~1924 法國 1927 法國欄省公學、巴黎大學學習 1928~1930 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十月革命前在蘇聯 楊明齋 1901~1920 俄國 入黨,1920年8月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轉入中共
第二代: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的留學生群體(1917~1923) 中國共產黨人第二代留學生群體是以留法為中心的。民國初年,留日熱潮漸退,中國留學運動轉向到留學歐洲尤其是法國,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掀起留學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醞釀和發展期,國際國內發生了四件大事:一是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是1917年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三是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四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些事件,不但大大激發了中國留學運動,而且促使留學生探求中國道路的深入思考。留法學生身處第一次大戰主戰場的法國,面臨法國失敗后的經濟蕭條的影響,勤工儉學的遭遇非常艱難,目睹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又受到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后人民當家作主現實的吸引,部分留學生轉向尋求共產主義運動的道路。組建中國共產黨成為留法學生最有影響的事件,見表2。 表2第二代: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的留學生狀況(1917~1923)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1917~1919 日本 在日本自學 周恩來 1921 在法國勤工儉學,在德國作了近一年考察,英國作 1920~1924 法國 了二次近二個月考察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彭 湃 1917~1921 日本 1924 早稻田大學學習 蔡和森 1919~1921 法國 1921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陳 毅 1919~1921 法國 1923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1920~1926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鄧小平 1924 1926~1927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學習 劉少奇 1921~1922 蘇聯 1921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鄧子恢 1917~1918 日本 1926 東京東亞補習學校、日華補習學校學習 1920~1923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趙世炎 1921 1923~1924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何長工 1919~1924 法國 1922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1919~1923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陳喬年 1922 1923~1925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中山大學學習 1919~1923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陳延年 1922 1923~1924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中山大學學習 任弼時 1921~1924 蘇聯 1922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18~1919 日本 東京明治大學學習 王若飛 1919~1923 法國 1922年8月入法 共后轉中共 在法國半工半讀,參加革命活動 1923~1925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1~1924 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學習 蕭勁光 蘇聯 1922 1927~1930 蘇聯紅軍學校、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 羅亦農 1920~1925 蘇聯 1921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彭述之 1921~1924 蘇聯 1922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19~1921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向警予 1922 1925~1927 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2~1925 德國 哥廷根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 朱 德 1922 1925~1926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 1919~1924 法國 蒙達尼女子中學,參加革命活動 蔡 暢 1923 1924~1925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0~1924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 聶榮臻 1922 1924~1925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李維漢 1919~1922 法國 1922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李富春 1919~1925 法國 1922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1919~1921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李立三 1921 1931~1946 蘇聯 在蘇聯列寧學院學習 1920~1921 日本 在東京自修 張聞天 1922~1924 美國 1925 在舊金山勤工儉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1925~1931 蘇聯 學習 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學習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張太雷 1923~1924 法國 1921 在法國勤工儉學 晨報駐蘇記者、莫斯科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 瞿秋白 1921~1923 蘇聯 1921 助教 羅學瓚 1919~1921 法國 1921 巴黎蒙達尼公學學習 1920~1921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蕭 三 1922 1926~1930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0~1921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學習 沈澤民 1921 1926~1930 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19~1922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熊 雄 1922~1923 德國 1922年在德國 加入德共 在柏林參加革命活動 1923~1925 蘇聯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汪壽華 1921~1925 蘇聯 1923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0~1923 法國 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 劉伯堅 1923~1926 蘇聯 1922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1928~1930 蘇聯 莫斯科軍政大學和優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第三代:第一次國共合作至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留學生群體(1924~1930) 中國共產黨人第三代留學群體是以留蘇為中心的。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非常重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積極支持這些國家革命運動的發展。其重要的方法就是為各國培養革命干部以推動世界革命運動的開展。為此,1921年4月21日,蘇聯政府在莫斯科成立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東方大學設有國內部和外國班,其中的外國班主要招收蘇聯境外的地處東方各國的學生,設有中國班、日本班、朝鮮班、伊朗班、土耳其班等。這一時期,大力培養革命干部也是中國共產黨國內革命斗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剛一成立,就投入到革命的斗爭之中,黨十分缺乏有理論、有組織能力的干部。1923年,陳獨秀鑒于國內干部的缺乏,向共產國際建議,將在留法的黨的活動分子派往蘇聯學習,趙世炎等成為第一批由法轉蘇的留學生。此后,從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協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歐支部成員先后有三批赴東方大學學習,包括鄧小平、傅鐘等。到1927年上半年,到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共人員前后達百人以上。 由于中國國內的革命形勢發展非常迅速,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國共兩黨對干部的需求量激增,這樣東方大學中國班及國內由蘇聯援建的黃埔軍官學校所培養的干部已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蘇聯政府決定再單獨創辦一所培養國共兩黨干部學校,1925年這所大學創辦,俄文名稱為“孫逸仙大學”,也即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辦,成為中國共產黨留學生群體的重要來源。 國共合作破裂后,隨著國民黨籍學生分批回國,國民黨中央發布命令,宣布撤銷中山大學,命令稱: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原系孫文大學所改名,假本黨總理之名,吸收本黨同志及吾國青年,并于本黨主義及政策妄加詆毀,是借本黨之名行反叛本黨之實,應速通電國內外,將該校名目取消,同時通令全國,不得再送學生前往。1928年4月,共產國際遵照斯大林關于“國民黨反共,我們要給共產黨培養干部”的指示,將孫逸仙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② 而此時,原來的東方大學中國班也并入了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只接受中國共產黨人入校學習。 從1925年到1930年,中山大學培養了約1000多名畢業生,見表3。 表3第三代:第一次國共合作至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留學狀況(1924~1930)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剪伯贊 1924~1925 美國 1937 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 葉 挺 1924~1925 蘇聯 1924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關向應 1924~1925 蘇聯 1925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張 浩 1924~1925 蘇聯 1922 莫斯科東方大學 (林育南) 1933~1935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王稼祥 1925~1930 蘇聯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 秦邦憲 1925~1930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王 明 1925~1929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俞秀松 1925~1935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 朱 瑞 1925~1935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炮兵學校學習 左 權 1925~1930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優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烏蘭夫 1925~1929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師 哲 1925~1940 蘇聯 1926 烏克蘭基輔導官學校、莫斯科工程兵學校學習 羅世文 1925~1928 蘇聯 1925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孫冶方 1925~1930 蘇聯 1924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張琴秋 1925~1930 蘇聯 1924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楊尚昆 1916~1931 蘇聯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陳 賡 1926~1927 蘇聯 1922 在蘇聯紅軍部隊中學習 伍修權 1925~1931 蘇聯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 張如心 1926~1929 蘇聯 1931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吳亮平 1925~1929 蘇聯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陳昌浩 1927~1930 蘇聯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陳伯達 1927~1930 蘇聯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1928 艾思奇 日本 1935 福岡高等工業學校學習兼自修 1930~1931 甘泗淇 1927~1930 蘇聯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侯外廬 1927~1930 法國 1928 巴黎大學學習 劉伯承 1927~1930 蘇聯 1926 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優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凱 豐 1927~1930 蘇聯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郭化若 1927~1929 蘇聯 1925 莫斯科炮兵學校學習 趙一曼 1927~1928 蘇聯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姓名 出國歸國時間 國別 入黨時間 出國學習狀況 葉劍英 1928~1931 蘇聯 1927 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 李葆華 1928~1931 日本 1928 東亞預備學校、東京高等師范學校 1927~1928 日本 早稻田大學 廖承志 1928 1928~1932 德國 柏林亨德第二大學 帥孟奇 1928~1930 蘇聯 1926 東方大學、中山大學 沈雁冰 1928~1930 日本 1921 在日本自修,從事寫作 艾 青 1929~1930 法國 1945 在法國勤工儉學 1929~1931 日本 東京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 何干之 1934 1935~1936 日本 參加革命文藝活動 何恩敬 1916~1926 日本 1932 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獲學士學位 1926~1926 法國 法國學習音樂 沙可夫 1926 1927~1931 蘇聯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沈志遠 1926~1931 蘇聯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張友漁 1930~1931 日本 1927 東京日本大學社會學部學習 錢 瑛 1929~1931 蘇聯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第四代:土地革命戰爭中期至全國革命勝利時期留學生群體(1931~1949)
二、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群體特點之研究
從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群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在世界各種文化的激蕩中,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之信仰,在外艱苦生活和在俄受到嚴格的黨性鍛煉,成為具有高度覺悟的共產主義戰士。
中國共產黨人的留學生群體大多是在國外留學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當時的中國,危機四伏,任人宰割,強烈的憂患意識使他們走上通過革命來改造與拯救中國的道路。在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條件下,他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瞿秋白在俄考察的兩年,通過親身經歷和深刻思考,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加入了共產黨,他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方向,“共產主義之人間化”,這“偉大而且艱巨的工程”,已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具有實行的把握。瞿秋白在旅俄的短短二年里,完成了其個性的基本定型——一位初步具有革命家、理論家的氣質修養和學識。他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正是此時奠定的。蔡和森到法國后,“搜集許多資料,猛看猛譯”,“對各種社會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③ 從而選擇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鄧小平等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在蘇留學的留學生中,不少人受到了嚴格的黨性鍛煉。劉少奇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期間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共產黨員的,他在東方大學時間不長,學了八個月就被派回國內,對這段歷史的評價,劉少奇講道,學了八個月,“也算取了經,取到的經不多就是了。當時我們學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觀開始確定了。懂得組織上的一些東西,講紀律,分配工作不講價錢、互相批評、一切報從黨,這些東西我腦子里種得很深。”④ 任弼時和劉少奇一樣,對黨的建設思想研究很深,有許多獨到的貢獻,特別是對黨性修養的問題。在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時,研究任弼時的作者指出,任弼時之所以對黨性問題有相當深刻的認識,一個重要原因,是與他早年在蘇聯的經歷有關。他們這一批人在蘇聯學習了兩種東西,一是受到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教育,一是受到嚴格的黨性訓練。從旅莫支部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到:連吃飯時所拿面包的大小、果醬的多少這樣的小事,都要在黨組織會議上升到黨性的高度去檢查。在當年很多留學生填寫的表格和思想匯報中,都說要去掉過去那種個人浪漫主義的東西,“把自己的整個身子交給本階級”。這些研究者指出:正是這種嚴格的黨性訓練培養出一代共產黨的領導人,才能經受住后來殘酷國內戰爭包括黨內斗爭的嚴峻考驗,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⑤
第二,經過系統地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軍事理論學習,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歷經實踐鍛煉,不少留學生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翻譯家、宣傳家、教育家、軍事家。
十月革命后,留學出身的知識分子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力。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李達、李漢俊、蔡和森、周恩來、楊匏安、陳望道等是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宣傳家。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比較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他對唯物史觀的宣傳在中國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第一塊基石。瞿秋白的貢獻在于第一個向中國思想界和中國共產黨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第二塊基石。李達不但是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骨干,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他一直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宣傳、教育工作,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宣傳和研究,直接影響了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提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思想理論來源。陳望道是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家,他是中國第一部《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1920年8月出版,使中國人得以看到這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綱領性文件的全貌。毛澤東等國內知識分子早期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從這幾本書開始的。張如心、吳亮平、陳伯達、艾思奇等人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主要成員,在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理論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沫若、翦伯贊是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開啟了以馬克思主義方法在中國治史的先河。葉劍英、劉伯承、劉亞樓、左權、郭化若等成為中國共產黨著名的軍事家。 中國共產黨人的留學群體不但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其中多數人還注意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一些人較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提出采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差別的觀點。蔡和森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政策的觀點。任弼時提出共產黨人“不應做一個不顧環境的模仿主義者”的觀點,1925年,剛從蘇聯莫斯科大學結束了三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學習的任弼時,一回到國內,就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的命題。⑥ 他指出,有許多同志滿足于做一個“模仿主義者”。他們往往會說,某個國家那樣做,我們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說,馬克思和列寧教導的,不會錯,照做就可以了;在和黨外人士辯論時,別人說到中國的情況,就無辭可答。這些都是只顧原則,不管實際的表現。任弼時指出:“必須按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我們的理論”,⑦ 認為這才是有力量的表現。這一思想成為任弼時后來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思想基礎。長期以來,由于王明教條主義問題,在一般人的觀念中,談到中國共產黨內的留學生,都有一種認識誤區,似乎留學生,特別是留蘇學生,都是教條主義者,其實,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而言,不論是國民黨人的留學生,還是做社會科學研究的留學生,都不能簡單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孫中山這個國民黨內地位最高的留學生,把西方政治理論中國化,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三民主義”理論。在社會科學的學者中,社會學家孫本文把國外學到的社會學理論中國化,是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代表。教育學家陶行知把西方教育學中國化,成為教育學“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各種文化的傳播中,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潮流在20世紀20~30年代以后,逐漸出現融合化的趨勢,正如著名學者戴逸所言,“20世紀的重大特點是中西文化從斗爭走向融合,人們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圍中成長”。⑧ 其中,具有貫通中西的留學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留學的經歷中,留學生以其對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廣闊視野的世界眼光。
在中國共產黨內,長期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革命的歷史潮流有深刻的認識,對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有較為透轍的分析,表現出在革命問題上的博大寬闊的世界眼光。這一眼光的由來,一些來自于列寧、斯大林對世界革命形勢的理論,另一些來自中國政治家自身的實踐,一些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中在諸多國家矛盾中縱橫捭闔的政治智慧。但對科學技術潮流的認識和洞察,卻不能說是那么敏銳。中國是一個現代科學技術極不發達的國家,幾千年來以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條件使人們很難領悟到科學技術的偉大力量。對此的認識,僅僅通過馬恩著作的認識是不行的。而中國革命的實踐又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實踐。這樣的實踐經驗,在觀察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上是有局限性的。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經歷看,曾經留過學和有長期出國經歷的領導者,相對來說,對世界科學技術潮流的認識上較有遠見。建國初期,在建設新中國所采取戰略的選擇上,周恩來較早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構想,他對科學技術有獨到的認識,他以驚人的觀察力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后面很遠”。⑨ 他指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為此他提出要依靠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周恩來這一遠見卓識的戰略眼光,是一種世界眼光的表現。在當初,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并未在高層達成共識,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的經歷、見識、經驗不同造成的。周恩來為什么能提出這一問題,這與周恩來出國經歷有著重要的內在聯系。他早年留學日本、法國,去過英國、德國、蘇聯,這些經歷使他身上具備了一些其他領導人不具備的素質,英國學者《周恩來傳》的作者迪克·威爾遜寫到,“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這一論點的人”。⑩ 應當說,首先提出是最富創意的,而這種創意的來源是什么,這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迪克·威爾遜分析了周恩來思想和經歷的相互關系。他指出:“周恩來一直對外部世界懷有強烈的好奇心,這一點與毛澤東或他那些共產黨同僚們比較起來顯得更為突出。盧西恩·派伊教授曾經評論說:‘他在國外呆的時間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們在國外呆的時間的總和還要多’。”(11) 迪克·威爾遜在分析中國領導人對外開放的思想時指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與那些人(指同僚們)比起來更是不可同日而語。”(12) 外國學者這一研究視角有他的可取之處。鄧小平是具有世界政治眼光和科學技術眼光的領導人。他的科學技術的世界眼光與他出國留學與出國訪問關系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少年出國時的廣闊見識批判目光狹隘、閉關鎖國的“四人幫”,當“四人幫”以風慶輪事件攻擊周恩來、鄧小平引進外國技術的正確觀點時,鄧小平說,他出國時就乘坐法國五萬噸郵輪,其意是指不能自我封閉、自我欣賞,自我吹捧。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多次出訪日本、美國和歐洲國家,20世紀第四次新技術革命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有長足的發展,在親身感受的基礎上,鄧小平對世界科學技術潮流作了充分的揭示,他指出,新技術革命日新月異,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從對世界發展經驗的分析中,他得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留學經歷的重要性也體現在留法學生李富春身上。還在抗日戰爭戰火紛飛的年代,在中共稍有可以歇息的抗日根據地時,1938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建議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中央書記處會議經過研究后,“原則決定開辦”,(13)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成立,一年后,改為自然科學院,李富春兼任院長。這是一所被稱為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這所學校為黨培育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才。當時人們都說,李富春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戰線的火種”,“是我黨有戰略眼光的領導者”。(14) 李富春在建國后長期負責國家的經濟工作,提出過不少重要的正確的建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條是與留學有關的。李富春的傳記作者在傳記中講到了這一問題。作者指出:“李富春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開過火車,當過司機。青年時代在西方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這段生活經歷,使他對現代工業的了解比許多人要深刻得多。”(15) 這一段評論是十分中肯的。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具有知識結構新、視野開闊、開放意識強特點的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對國內共產黨人群體發生著積極的重要的影響,它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國革命歷史條件引起的人們認識視野局限性問題。
第四,在部分留學生中,由于缺乏實踐經驗,又由于在共產國際中,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大環境的影響,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關系上高度集權體制的作用下,部分留學生成為中國20~30年代教條主義的代表。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普遍主義因素,它在中國的傳播不能簡單看作是一種中外文化的碰撞。但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有著一定的共同點。中國共產黨人從接受馬克思主義起,到形成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中有一個“文化本土化”的過程,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初期,不論是有留學經歷的共產黨人,還是沒有留學經歷的共產黨人,都存在一個從接受馬克思主義到學會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這正是文化傳播特點所在。但是,這一傳播過程又有各自特點。從中國革命的過程來看,中國革命受蘇聯影響很大。這種影響除了正確的積極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一定消極影響,這兩種影響混合在一體之中。消極影響主要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在理論上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一個是在體制上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關系的高度集權性。這兩個因素交互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內教條主義的國際因素。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王明路線難以克服的原因有一個是國際原因。由于共產國際是一個高度集中的組織,它對各國共產黨擁有很大的權威,可以直接插手任命各國黨的領導人,批準各支部的綱領政策,它的文件就是最高指示,各支部不得違背和修改。它還對各國黨嚴加監督,稍有越軌,輕者通報批評,重者對領導人撤職查辦。共產國際的核心是蘇聯共產黨,雖然它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其實質上主宰著共產國際,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蘇聯又是列寧的故鄉,是第一個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它有經濟和軍事實力,可以直接為各國黨提供物質援助。因此,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中占有特殊地位,擁有最大的發言權,蘇聯政策的任何變化,蘇聯黨內斗爭的情況,斯大林的任何觀點,都可直接影響到中國及其他國家政策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又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國際間的上下級關系,使中國共產黨獨立制定政策的權力受到限制,這些成為中國出現教條主義的重要背景。而此時,中國共產黨又很年輕,處在幼年時期。從國外回國的一些留學生缺乏實際斗爭經驗,有些留學生則對“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識反應很慢,如王明等。這些人又受蘇聯黨內斗爭的影響。正如劉少奇所指出:“四中全會上王明領導的黨內斗爭搞了許多非法活動,學了莫斯科米夫與支部局斗爭的最壞的東西”。(16) 在中國共產黨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但具有政治的意義,而且具有文化的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在中國傳播成熟和融合理性自覺的表現。這一點對中國共產黨人留學生群體教育是至深的。李富春曾深有感觸地說:“我這個人在思想上真正取得‘國籍’,還是在毛澤東同志幫助下”。(17) 以深諳中國國情和熟悉中國文化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國內共產黨人群體以其之長對黨內留學生群體中存在的不諳國情、厚洋薄中弱點的教育與批評,體現了黨內不同文化意義上群體之間的有益互動,促使共產黨這一復合文化體在新的向度和新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2頁。 ②楊青:《何叔衡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頁。 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頁。 ④《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510頁。 ⑤冷溶:《任弼時研究的新進展》,《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第37頁。 ⑥⑦《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頁。 ⑧戴逸:《二十世紀中華學案》綜合卷,第1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3頁。 ⑨《周恩來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頁。 ⑩(11)(12)[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封長虹譯,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200、298、317頁。 (13)(14)(15)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60、262、381頁。 (16)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98頁。 (17)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