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農(nóng)村計劃生育與養(yǎng)老保障
王嘉彥
論文關(guān)鍵詞:計劃生育養(yǎng)老保障相互關(guān)系
論文摘要:始于上世紀(jì)七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通過幾十年來的嚴(yán)格執(zhí)行,很好的控制了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從根本上保障了我國經(jīng)濟建設(shè)的偉大成果,所以說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隨著第一代計劃生育夫婦在不久的將來就要進人老年,老年保障問題逐漸顯現(xiàn),如何切實保障他們的老年生活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分別從政策角度、經(jīng)濟角度和法律角度分析了我國農(nóng)村計劃生育與養(yǎng)老保障的關(guān)系,并提出相關(guān)法律建議。
與馬爾薩斯的“人口決定論”相反,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chǎn)理論認(rèn)為社會生產(chǎn)不僅包括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人類自身生產(chǎn),二者構(gòu)成了社會生產(chǎn)內(nèi)部的矛盾對立體,社會生產(chǎn)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聯(lián)系、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中發(fā)展的。但兩者不是并列的,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對人類自身的生產(chǎn)有決定作用,人類自身生產(chǎn)對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有反作用。在一定社會生產(chǎn)方式下,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對人類自身生產(chǎn)的決定作用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的性質(zhì)決定人類自身生產(chǎn)的性質(zhì),二是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決定人口發(fā)展的基本趨勢。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人口控制理論的基礎(chǔ)。
計劃生育政策是我國所特有的一項制度,計劃生育工作是一項長期性、持續(xù)性的工作,這項制度得到了全國上下高度貫徹,現(xiàn)在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農(nóng)村,特別是一些老少邊貧地區(qū)。究其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于我國城鄉(xiāng)分離的二元結(jié)構(gòu)所致。在我國城鎮(zhèn)居民有各類社會保障,城鎮(zhèn)居民的養(yǎng)老問題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較小,而就全國整體范圍來看,現(xiàn)在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部分缺失,他們的養(yǎng)老基本上是靠家庭養(yǎng)老,計劃生育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農(nóng)村家庭人口數(shù)和家庭結(jié)構(gòu),由于制度的缺失必然導(dǎo)致農(nóng)民養(yǎng)老問題凸現(xiàn),這也就是為什么老少邊貧地區(qū)陷人“貧困——超生——越貧困”怪圈原因,故本文將探討范圍限定于我國農(nóng)村的計劃生育和農(nóng)村的養(yǎng)老保障。
一、從政策角度分析農(nóng)村計劃生育與養(yǎng)老保障的關(guān)系
(一)計劃生育政策貫徹前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
1.新中國成立至1958年。1956年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示范章程》規(guī)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對于缺乏勞動力或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疾的社員,在生產(chǎn)上和生活上給與適當(dāng)?shù)陌才藕驼疹櫍WC他們的吃、穿和柴火的供應(yīng),保證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們生養(yǎng)死葬都有依靠。此即五保戶政策的由來,但是對于全體農(nóng)民沒有統(tǒng)一的養(yǎng)老保障政策,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仍然延續(xù)幾千年的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
2.1958年至1978年。1958年我國建立人民公社制度,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依靠集體與家庭共擔(dān)來完成,但是由于土地和其他生產(chǎn)資料私有化被消滅,農(nóng)村家庭的收人來源是人民公社按人頭分配的,集體經(jīng)濟的平均性特點無法調(diào)動生產(chǎn)的積極性,人民公社既是經(jīng)濟組織又是政府組織,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保障從源頭上來說是靠集體完成的。
(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1978年以來)
我國的人口控制問題最早應(yīng)追溯到1953年,只不過當(dāng)時未嚴(yán)格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嚴(yán)格執(zhí)行后農(nóng)村家庭子女?dāng)?shù)顯著下降,農(nóng)村家庭結(jié)構(gòu)改變,即成為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父母兩人和獨生子女一人的“四二一”結(jié)構(gòu)。計劃生育政策明顯改變了養(yǎng)老保障模式,目前普遍認(rèn)為“四二一”結(jié)構(gòu)家庭的養(yǎng)老負(fù)擔(dān)嚴(yán)重。其實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1980年發(fā)出的《關(guān)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chǎn)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指出:“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到40年后,一些家庭可能出現(xiàn)老年人身邊缺人照顧的問題。這個問題許多國家都有,我們要注意想辦法解決。”
同一時期我國也開始了從計劃經(jīng)濟體制向市場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變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對于農(nóng)民來說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經(jīng)營責(zé)任制,這一制度再次將土地收益權(quán)賦予農(nóng)民,從而為恢復(fù)農(nóng)村家庭的保障功能奠定了基礎(chǔ)。從1986年開始,農(nóng)村探索性地開展了建立社會養(yǎng)老保險制度試點工作。到1997年底,已有7542萬農(nóng)民投保。但1998年以后,農(nóng)村養(yǎng)老體制改革工作陷人了停頓狀態(tài)。2004年,農(nóng)村勞動力參保數(shù)量為5378萬人,比1997年減少了2164萬人,下降幅度達到28.7%。農(nóng)村勞動力參保數(shù)量占農(nóng)村勞動力總量比例同步下降,由1997年的15.4%下降到2004年11.0%。究其原因,這項試點改革的開展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實施的,農(nóng)民要等10至20年才能獲得實際收益,同時由于政策的不確定風(fēng)險,農(nóng)民不愿意為10至20年后的不確定性的收益埋單。
從計劃生育這一政策執(zhí)行前后兩個時期,我們看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改變了農(nóng)村家庭子女?dāng)?shù)和家庭結(jié)構(gòu),也就事實上改變了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模式,這就迫切需要社會養(yǎng)老制度來保障,但是我們從農(nóng)村養(yǎng)老試點的參保人數(shù)和規(guī)模上來看,試點是不成功的,在農(nóng)村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的大環(huán)境下,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了計劃生育反彈的現(xiàn)象,農(nóng)民重新回到養(yǎng)兒防老的老路上來。所幸的是2004年,中國政府開始對農(nóng)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制度的試點:農(nóng)村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計劃生育夫婦,每人從年滿60周歲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獎勵扶助金,直到亡故為止。獎勵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負(fù)擔(dān)。但是此項政策還未在全國范圍內(nèi)普遍推行。
二、從經(jīng)濟角度分析農(nóng)村計劃生育與養(yǎng)老保障的關(guān)系
農(nóng)村養(yǎng)老需求是指農(nóng)村居民在既定的收人范圍內(nèi)能夠而且具有實際支付能力的養(yǎng)老需求;農(nóng)村養(yǎng)老供給是指通過各種養(yǎng)老保障業(yè)務(wù)活動滿足農(nóng)村居民養(yǎng)老保障需求的行為過程。在我國現(xiàn)存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制度下,養(yǎng)老服務(wù)需求非常強烈,表現(xiàn)為農(nóng)村中農(nóng)業(yè)人口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的養(yǎng)老需求,農(nóng)村中計劃生育戶的養(yǎng)老需求,以及包括農(nóng)村社會在內(nèi)的整個社會的需求。影響農(nóng)村養(yǎng)老需求的因素也很多,這其中又有內(nèi)在因素與外在因素之分。現(xiàn)行農(nóng)村養(yǎng)老供給體系是由家庭保障、社區(qū)保障、市場保障和政府保障共同形成的保障組合,各種保障類型又有其獨立作用性和相互替代性。
1.家庭保障。正如莫迪格里尼亞指出的那樣,根據(jù)生命周期理論,儲蓄隨人口的穩(wěn)定增長率遞增,但兩者并非因果關(guān)系。真正影響儲蓄率的是人口結(jié)構(gòu),特別是工作人口和非工作人口之間的比率是最為重要的。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年輕一代是有義務(wù)照顧家庭中的老年人的,而在實行嚴(yán)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后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即顛覆和破壞了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這迫使人們增加儲蓄以自我養(yǎng)老,生命周期財富的積累作為孩子的替代變得更加重要。但是這里還存在一個問題,用以自我養(yǎng)老的儲蓄如何克服通貨膨脹的危險。
2.社區(qū)保障。所謂社區(qū)就是若干社會群體(家庭和氏族)或社會組織(機關(guān)和團體)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個在生活上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大集體。我國農(nóng)村具有互助的傳統(tǒng),社區(qū)保障就是這種傳統(tǒng)的延續(xù),其經(jīng)濟基礎(chǔ)是社區(qū)經(jīng)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但是社區(qū)養(yǎng)老保障又是一種不穩(wěn)定的養(yǎng)老保障形態(tài),它也具有負(fù)作用。從一個社區(qū)范圍內(nèi)來看,社區(qū)養(yǎng)老保障有助于橫向平等,但是從整個社會看,社區(qū)養(yǎng)老保障有可能加劇社會橫向不平等。可見社區(qū)養(yǎng)老并非長久之計,制度設(shè)計時應(yīng)考慮最終將其納人國民保障體系。 3.市場保障。應(yīng)該肯定商業(yè)保險(市場保障)解決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問題技術(shù)上是可行的。但是從供給方看,其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fēng)險;從需求方看,是否購買商業(yè)養(yǎng)老保險受諸多因素影響,例如社會傳統(tǒng),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以及保險市場價格等。
4.政府保障。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家庭保障的對象是家庭成員、社區(qū)保障的對象是社區(qū)成員,市場保障的對象是具有購買能力且愿意購買商業(yè)保險的農(nóng)民,他們都是針對特定人群的保障,而不是面向整個農(nóng)村社會的。而政府保障是靠法律的強制性來實現(xiàn)的,他們之間是相互補充的關(guān)系。尼古拉斯·巴爾說過,“私營養(yǎng)老金只能提供有限的指數(shù)化,而超出部分的保險最終必須落到政府身上,”“很明顯,如果政府來提供這種防范通貨膨脹的保險,那么它就不是一種真正的保險(因為它不可能成為),而只是一種稅收/轉(zhuǎn)移形式”。
面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嚴(yán)格執(zhí)行,各種保障方式變化表現(xiàn)不一:家庭保障通過增加儲蓄以應(yīng)變;社區(qū)保障和商業(yè)保障總體來說未出現(xiàn)明顯的、有針對性的應(yīng)變,這是供求雙方共同平衡的結(jié)果;而政府保障的應(yīng)變是最具針對性,也最有現(xiàn)實意義。根據(jù)中國人民大學(xué)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的評估,國家在“少生快富”扶貧工程上每投人1分錢,將帶來4元錢的產(chǎn)出,投人產(chǎn)出比是1:40。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方面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所起的引導(dǎo)作用,通過政府供給,以看得見的手的方式直接干預(yù)了農(nóng)村計劃生育戶養(yǎng)老保障市場;從另一方面看,響應(yīng)計劃生育號召的夫婦是農(nóng)村中為國家和長遠(yuǎn)利益而犧牲家庭和眼前利益的先進群體,必須給實行計劃生育的農(nóng)戶必要的補償、獎勵,讓農(nóng)村計劃生育戶在養(yǎng)老上有保障、經(jīng)濟上有實惠。
三、從法律角度分析農(nóng)村計劃生育與養(yǎng)老保障的關(guān)系及制度化建議
在國際上,社會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在英文中稱social vulnerable groupo它主要是一個用來分析現(xiàn)代社會經(jīng)濟利益和社會權(quán)利分配不公平、社會結(jié)構(gòu)不協(xié)調(diào)、不合理的概念。根據(jù)其成因的不同,弱勢群體可分為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兩類。前者主要是基于生理原因,如老弱病殘等;而后者則主要是基于社會原因,如社會改革等。我國當(dāng)前正處于社會改革和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社會性弱勢群體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人群:1.失業(yè)人員;2.進城務(wù)工的農(nóng)村勞動者3.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的農(nóng)村勞動者。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的城市傾斜政策導(dǎo)致農(nóng)村發(fā)展滯后,制度上的藩籬造成社會的進步不能良性互動地帶動農(nóng)村的發(fā)展。
相對于農(nóng)村中其他未嚴(yán)格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農(nóng)戶來說,農(nóng)村計劃生育戶更可以定義為社會弱勢群體,他們還面臨著較他人更多的養(yǎng)老風(fēng)險。農(nóng)村獨生子女家庭一旦出現(xiàn)子女意外致傷、致殘甚至死亡時,計劃生育戶的養(yǎng)老問題即刻便顯現(xiàn)出來,從社會到國家都有責(zé)任去關(guān)心、救助,使其父母有一個較穩(wěn)定的生活來源和老有所養(yǎng)。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生育制度安排在社會發(fā)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發(fā)揮的積極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農(nóng)村計劃生育戶這一弱勢群體的存在與計劃生育的制度安排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他們只是體制轉(zhuǎn)型中社會代價的承擔(dān)者,因此從邏輯上看,政府有責(zé)任保護他們的權(quán)利,保護他們的權(quán)利是政府義不容辭的義務(wù)。
我們應(yīng)該從法律上確立保護農(nóng)村計劃生育戶這一社會弱勢群體權(quán)益的制度,完善農(nóng)村計劃生育養(yǎng)老保障制度:
1.將對農(nóng)村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我們可以從開始于80年代中期的中國農(nóng)村的養(yǎng)老保險試點工作看到前車之鑒,按照官方提供的數(shù)據(jù),養(yǎng)老保險的覆蓋面其實不是在逐年擴大,而是在逐年縮小。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方面是肯定的,試點工作依據(jù)的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時更多的是出于政績的考慮,當(dāng)試點工作不再提到政治高度上的時候,工作績效自然下滑。政策和法律是既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兩個范疇,它們的聯(lián)系表現(xiàn)在對經(jīng)濟活動都有調(diào)節(jié)作用;它們的區(qū)別在于法律調(diào)節(jié)的強制性和政策調(diào)節(jié)的導(dǎo)向性。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才能穩(wěn)定有效的推進這項于國于民皆有利的制度。
2.需要制訂更加細(xì)化的執(zhí)行辦法和實施細(xì)則。有了一項好的制度,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后如何實施到位才是根本。我國地大物博,人口分布不均,經(jīng)濟發(fā)展在各地區(qū)間也不平衡,對于農(nóng)村計劃生育養(yǎng)老保障的要求也不一盡一致,保障應(yīng)從實際出發(fā),因地制宜建立分地區(qū)分類別的保障模式,對于經(jīng)濟相對落后地區(qū),應(yīng)考慮加大財政轉(zhuǎn)移支付力度。
3.建立和健全農(nóng)村計劃生育養(yǎng)老保障運行監(jiān)督機制。據(jù)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潘玉貴在國務(wù)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披露,試點地區(qū)在探索中建立了資格確認(rèn)、資金管理、資金發(fā)放和社會監(jiān)督“四權(quán)分離”的制度運行機制:第一個環(huán)節(jié)資格確認(rèn),由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進行;第二個環(huán)節(jié)資金管理,由財政部門來進行封閉管理;第三個環(huán)節(jié)是資金發(fā)放,現(xiàn)在各個省都是用招標(biāo)形式,從有資金的金融機構(gòu)來確定代理發(fā)放機構(gòu);第四個環(huán)節(jié)是監(jiān)督檢查,這個環(huán)節(jié)一般是由地區(qū)監(jiān)察部門或者紀(jì)律檢察部門牽頭。我們應(yīng)該認(rèn)識到在試點地區(qū)取得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是今后擴大試點乃至將來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農(nóng)村計劃生育養(yǎng)老保障的寶貴財富,政府機制的選擇應(yīng)該遵循追求社會公平這一基本原則。
總之,在我國農(nóng)村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與養(yǎng)老保障是不矛盾的,是相輔相成的,今后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制度的確立應(yīng)考慮有利于計劃生育政策執(zhí)行。
急管理報.jpg)
科大學(xué)學(xué)報.jpg)
代礦工.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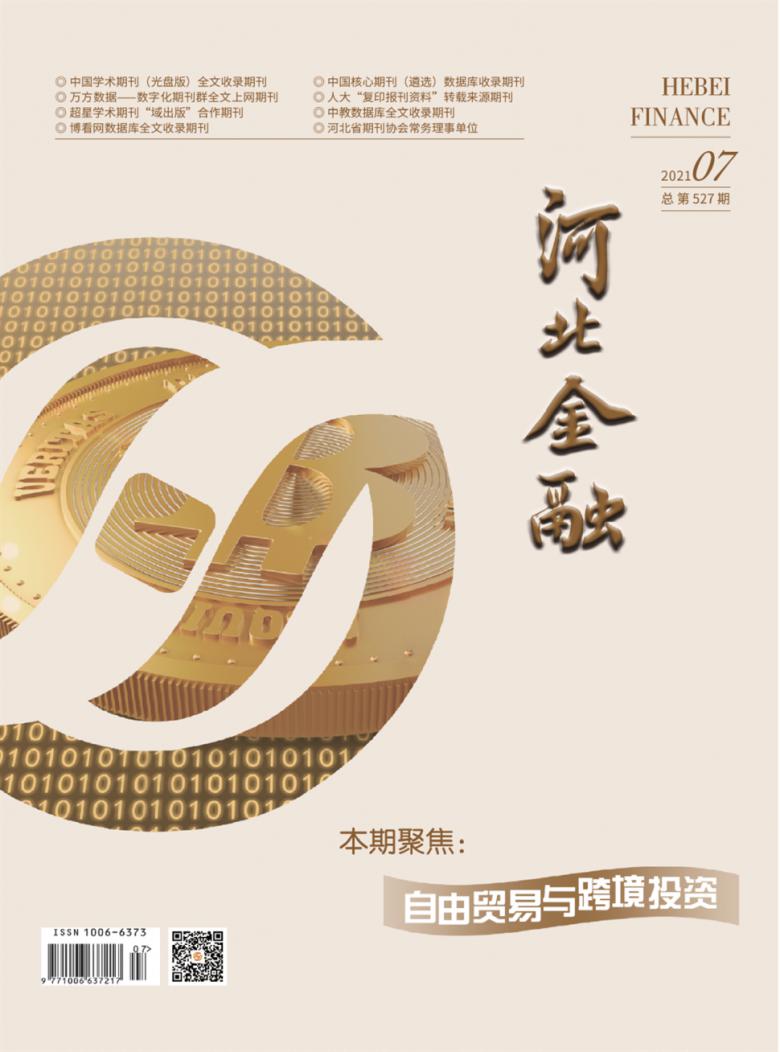
展.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