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未實(shí)際設(shè)立后的案件處理問(wèn)題初探
佚名
「關(guān)鍵詞」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債權(quán)登記確權(quán)訴訟
2003年3月,“穗港信202”輪與“銀虹”輪在廣州港附近水域發(fā)生碰撞,導(dǎo)致“銀虹”輪及其所載的全部集裝箱貨物沉沒(méi),兩船的所有人遂先后向廣州海事法院申請(qǐng)?jiān)O(shè)立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廣州海事法院經(jīng)審理,裁定準(zhǔn)予其申請(qǐng),并依照我國(guó)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規(guī)定進(jìn)行通知和公告;有關(guān)的債權(quán)人分別就與事故有關(guān)的債權(quán)進(jìn)行了登記,并隨之提起確權(quán)訴訟。兩準(zhǔn)予設(shè)立基金的裁定生效后,“穗港信202”輪的所有人按要求提供資金設(shè)立了基金,但“銀虹”輪的所有人卻沒(méi)有提供資金或有效擔(dān)保實(shí)際設(shè)立基金。由于我國(guó)的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及有關(guān)司法解釋缺乏相應(yīng)的規(guī)定,因而出現(xiàn)了一個(gè)程序:海事法院作出準(zhǔn)予設(shè)立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的裁定后,有關(guān)的債權(quán)人進(jìn)行了債權(quán)登記并提起相應(yīng)的確權(quán)訴訟,但申請(qǐng)人沒(méi)有在裁定生效后實(shí)際設(shè)立基金,此時(shí),對(duì)相關(guān)的案件應(yīng)如何處理?本文就此問(wèn)題進(jìn)行初步探討,以尋求解決司法實(shí)踐疑難的途徑。
一、關(guān)于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的設(shè)立及債權(quán)登記、確權(quán)訴訟程序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特有的并區(qū)別于民法一般損害賠償原則的一項(xiàng)特殊制度,是指針對(duì)一次事故所引起的侵權(quán)、合同等各類(lèi)債權(quán),作為責(zé)任人的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經(jīng)營(yíng)人、救助人、保險(xiǎn)人等可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將其賠償責(zé)任綜合性地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nèi),其目的在于降低海運(yùn)風(fēng)險(xiǎn),鼓勵(lì)海上運(yùn)輸業(yè)的,我國(guó)的海商法亦設(shè)此制度。為配合這一制度的運(yùn)作,我國(guó)的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設(shè)置了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及相應(yīng)的債權(quán)登記、確權(quán)訴訟程序。當(dāng)發(fā)生重大海損事故時(shí),責(zé)任人為使其船舶或其他財(cái)產(chǎn)免受司法扣押,有權(quán)向事故發(fā)生地、合同履行地或船舶扣押地的海事法院申請(qǐng)?jiān)O(shè)立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法院受理申請(qǐng)后,向已知的利害關(guān)系人發(fā)出通知,通過(guò)新聞媒體向發(fā)布公告,在此期間,利害關(guān)系人有權(quán)提出異議,異議成立,法院裁定駁回申請(qǐng);異議不成立或利害關(guān)系人沒(méi)有提出異議,法院裁定準(zhǔn)予申請(qǐng)。當(dāng)事人對(duì)裁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間內(nèi)提起上訴。有關(guān)債權(quán)人應(yīng)在公告期內(nèi)申請(qǐng)對(duì)與事故有關(guān)的債權(quán)進(jìn)行登記,若債權(quán)尚未經(jīng)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shū)的確認(rèn),也未經(jīng)法院立案受理的,則需要在辦理債權(quán)登記之后以提起確權(quán)訴訟或申請(qǐng)仲裁等方式確認(rèn)債權(quán)。確權(quán)訴訟案件的審理方式與第一審普通程序案件并無(wú)不同,其特殊只在于程序上實(shí)行“一審終審”,目的是為了盡快明確責(zé)任并對(duì)基金進(jìn)行分配,從而消滅特定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
根據(jù)我國(guó)海商法與海訴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設(shè)立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不是責(zé)任人限制責(zé)任的必經(jīng)程序和前提條件,只是表明限制責(zé)任的意向,主要目的是為使財(cái)產(chǎn)免受扣押。盡管海訴法對(duì)申請(qǐng)登記的債權(quán)只作了“與特定場(chǎng)合發(fā)生的海事事故有關(guān)”的簡(jiǎn)單要求,但結(jié)合有關(guān)實(shí)體法的規(guī)定看,能夠享受責(zé)任限制的只有海商法第 207條所列的限制性債權(quán)。一旦責(zé)任人申請(qǐng)?jiān)O(shè)立基金,限制性債權(quán)的債權(quán)人就必須在公告期間內(nèi)申請(qǐng)債權(quán)登記,逾期未登記的,視為放棄該債權(quán),其不能自基金中受償,也不得在基金分配完畢后就該債權(quán)另行起訴索賠。
二、關(guān)于審理程序處理的如前述案件的情況,裁定準(zhǔn)予設(shè)立海事賠償責(zé)任限制基金后,申請(qǐng)人未提供資金或擔(dān)保實(shí)際設(shè)立基金,與之相關(guān)的案件應(yīng)如何處理?我國(guó)的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釋對(duì)此均未作出規(guī)定。
對(duì)于已經(jīng)受理的確權(quán)訴訟案,傾向性意見(jiàn)認(rèn)為:由于基金沒(méi)有實(shí)際設(shè)立,適用確權(quán)訴訟程序的前提條件沒(méi)有具備,已經(jīng)受理的案件不能繼續(xù)按照確權(quán)訴訟“一審終審”的程序?qū)徖恚菓?yīng)當(dāng)裁定終結(jié);有關(guān)糾紛若要以訴訟方式解決,則應(yīng)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進(jìn)行審理。筆者亦贊同這一觀點(diǎn)。但具體如何操作,因缺乏明確的法條依據(jù),存在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原確權(quán)訴訟裁定終結(jié),直接另立第一審普通程序案號(hào),由原審法院按第一審普通程序繼續(xù)審理。其理由主要是有利于減少當(dāng)事人的訟累,避免造成審判工作的浪費(fèi),以及貫徹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中的“管轄恒定”精神。
第二種方案:原確權(quán)訴訟裁定終結(jié),有關(guān)糾紛如何解決由當(dāng)事人自行選擇 ── 可向原審法院或其他有管轄權(quán)的法院重新提起第一審普通程序訴訟,也可申請(qǐng)仲裁或自行和解。其理由主要是維護(hù)程序的安定和法定,尊重當(dāng)事人對(duì)其處分權(quán)的行使。
筆者認(rèn)為,上述兩種解決方案各有利弊,具體可從以下方面進(jìn)行分析:一方面,從訴權(quán)的保護(hù)和訴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關(guān)系來(lái)看。處分原則是民事訴訟所特有的原則,也是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其核心就是保護(hù)當(dāng)事人的訴權(quán),即尊重和保護(hù)當(dāng)事人對(duì)其實(shí)體權(quán)利和程序權(quán)利所進(jìn)行的合法行使和處分。法律對(duì)訴權(quán)的保護(hù)體現(xiàn)在民事訴訟的各個(gè)階段,如在民事訴訟的第一個(gè)環(huán)節(jié) ── 起訴階段,就實(shí)行“不告不理”,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dòng)和運(yùn)行必須依賴(lài)于當(dāng)事人主動(dòng)行使訴權(quán);而審判權(quán)的啟動(dòng)則是基于當(dāng)事人請(qǐng)求法院對(duì)糾紛進(jìn)行裁判,是被動(dòng)的,法院不得依職權(quán)尋找糾紛、主動(dòng)開(kāi)始訴訟程序。根據(jù)我國(guó)現(xiàn)行民事訴訟法第2條的規(guī)定,民事訴訟法的任務(wù)首先是“保護(hù)當(dāng)事人行使訴訟權(quán)利”,置于此之后的才是保障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二者的先后順序也表明了其間的關(guān)系和各自的地位。可見(jiàn),無(wú)論是遵從立法本意還是適應(yīng)當(dāng)今市場(chǎng)體制的現(xiàn)實(shí)要求,民事訴訟的結(jié)構(gòu)都應(yīng)以當(dāng)事人行使訴權(quán)為本位,訴權(quán)應(yīng)被置于制約審判權(quán)行使的優(yōu)先地位,而審判權(quán)的行使則應(yīng)以保障訴權(quán)的充分實(shí)現(xiàn)為宗旨。① 隨著我國(guó)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全面深入,當(dāng)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日趨形成,其中對(duì)當(dāng)事人訴權(quán)的保護(hù)也得到明顯加強(qiáng),而保護(hù)當(dāng)事人的訴權(quán),首先要保護(hù)的是當(dāng)事人的起訴權(quán)。海事訴訟作為民事訴訟的組成部分,亦應(yīng)與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改革發(fā)展方向保持一致。當(dāng)確權(quán)訴訟因失去存在的前提條件而被裁定終結(jié),即意味著該訴訟程序完全結(jié)束,根據(jù)程序安定的要求,已經(jīng)過(guò)的訴訟程序不應(yīng)被隨意逆轉(zhuǎn),所以如果要重新啟動(dòng)審判程序,仍應(yīng)按照正常的途徑即通過(guò)原告行使訴權(quán)重新提起訴訟來(lái)實(shí)現(xiàn)。由于在設(shè)立基金的通知或公告發(fā)出后,有關(guān)債權(quán)人若不放棄債權(quán),就必須到受理設(shè)立基金申請(qǐng)的法院進(jìn)行債權(quán)登記;辦理登記后,如果需要確認(rèn)債權(quán)的,除訂有訴訟管轄協(xié)議或仲裁協(xié)議外,只能向辦理債權(quán)登記的法院即設(shè)立基金的法院提起確權(quán)訴訟 ── 此時(shí),原告訴權(quán)的行使受到了特定條件下的限制。但當(dāng)沒(méi)有了特定條件的限制,即不屬于確權(quán)訴訟程序時(shí),對(duì)原告行使訴權(quán)的限制應(yīng)予解除。若按第一種方案,由法院直接另立普通第一審案件的案號(hào)繼續(xù)審理,等于由審判權(quán)主動(dòng)啟動(dòng)民事訴訟程序,有強(qiáng)迫起訴、剝奪原告對(duì)受訴法院的選擇權(quán)之嫌,限制了原告對(duì)其訴權(quán)的自主行使,顯然與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和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相反,若適用第二種方案,則能恰當(dāng)?shù)靥幚碓V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對(duì)原告行使訴權(quán)的尊重。

科技術(shù)語(yǔ).jpg)
院學(xué)報(bào).jpg)
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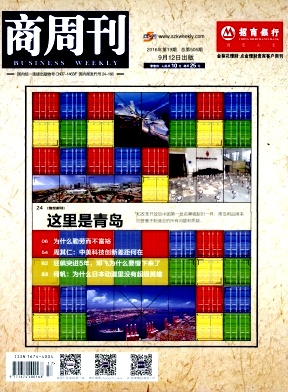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