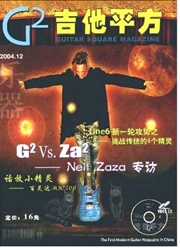關于論張之洞調整中日俄三角關系的外交主張
郝祥滿
[摘要]19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日俄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擴張,清政府如何妥善處理中日俄三國關系,謀求國家安全顯得日益重要起來。張之洞積極參與清政府的外交事務,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間,他提出了“賂目阻俄”的主張,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款前后則主張“聯俄抗日”;在德國搶占青島、俄國強租旅大之時又改弦更張提出了“結日阻俄”的主張。張之洞調整中日俄三角關系的主張經歷了以上三個階段。但始終未能擺脫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關鍵詞]張之洞;賂日阻俄;聯俄抗日;結日阻俄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4799(2010)01—0103—05
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俄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擴張,由于地緣政治關系的作用,如何妥善處理中日俄三國關系,謀求國家安全顯得日益重要起來。由于中國的邊疆危機,尤其是日本問題越來越突出,清流黨出身的張之洞也在有關討論中、工作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外交觀和日本觀,積極言論以展示自己的政見,尤其是在處理中日俄三角關系方面,不斷探索并提出調整的主張,這些主張也反映了他的日本觀經歷了忽視日本、仇視日本、重視日本三個階段。張之洞的主張影響了晚清的外交、政治、軍事、文化政策。一、賂日阻俄:日本侵臺吞并琉球以后張之洞的主張
張之洞最早發表他的外交觀是在1879年(光緒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沙俄強迫中國代表簽訂《伊犁條約》,侵占中國西北,使中國東西兩面同時遭遇“邊疆新危機”之時。當時“海防”與“塞防”的爭議遍及朝野,愛發議論的清流黨人張之洞自然難緘其口,從光緒五年到六年,張之洞就此問題先后11次上書,暢談自己“聯日本以伐交”即賂日阻俄的主張。
從這一時期張之洞的一系列言論看,這一時期他的外交主張是草率的,對俄國與日本的了解都是非常膚淺的。由于教育經歷、任職經歷等條件的限制,此時的張之洞對于經世外務均知之甚淺,不免意氣用事,流于空論,以致缺乏主權觀念。如張之洞在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詳籌邊計折》中提出的阻止俄國向東擴張的以下外交主張:
·
即或我軍不克,我力不支,則我猶出下策,擲孤注,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里海以取土爾
扈特舊牧地,東捐臺灣山后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東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啖日爾曼
以重利使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于外,俄之亂黨起于內,恐比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
此論雖然顯示張之洞拋棄了“守在四夷”的中國傳統外交理念,但對于不同傾向的殖民主義國家不夠了解,簡單化地加以區分,錯誤地認為日本和英國一樣僅是一個重視海權和貿易的國家,擴張土地的胃口沒有重視“陸權”的俄國大,所以認為日本可以通商為利誘,為中國所利用。故張之洞于光緒六年七月初十Et在《謹陳海防事宜折》中繼續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日本宜連和,以伐其交。俄人遠來,專恃日本為后路,宜速與聯絡,彼所議辦商務,可允者早允
之,但得彼國中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
張之洞的這一時期的外交主張(包括他的日本觀)集中反映在他的《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折》中。該折的核心思想是“聯日本以伐交”、“使彼中立,不助俄勢”,其策略是中日商務談判與琉球主權爭論分離,姑且概括為“政經分離”:
所云聯日本者,專指商務。且必可允者方允,與球事無涉也。既允商務,則必與之立約。中俄有
釁,彼不得助俄為寇濟餉屯兵,非無故而曲徇其請也。蓋商務所爭在利,方今秦西諸族腐集,中華加
一貧小之日本,亦復何傷?夫中國不過分西洋諸國之余瀝,以沾丐[溉]東洋,而借此可以聯唇齒之歡,
孤俄人之黨。此所謂不費之惠,因時之宜……。
張之洞提出以上觀點也是基于他塞防重于海防、朝鮮重于琉球的認識。他認為,如果讓“法踞越南,英襲緬廊,俄吞朝鮮,數年之后,屏藩盡失。他國猶緩也,朝鮮一為俄有,則奉、吉兩省患在肘腋之間,登萊一道,永無解甲之日矣”。針對“俄事擾擾,將及一年,廟堂無欲戰之心,將相無決戰之策”的局面,他提出首先應避免國家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故與俄戰,則不得不與倭和;與俄和,則不妨與倭戰,此謀國不易之策也”,又基于他對日本的輕視,認為倭不可畏,但可賄,可以操控。因此他主張先俄后倭,對日本:“以餌貪求,姑懸球案,以觀事變,并與立不得助俄之約。俄事既定,然后與之理論。感之以推廣商務之仁,折之以興滅繼絕之義,斷不敢輕與我絕,設必不復球,則撤回使臣,閉關絕市。日本甚貧,華市一絕,商賈立窘,嚴修海防靜以待之,中國之兵力財力,縱不能勝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窮矣。”Iml卜72
張之洞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一方面輕視日本,故說“夫撫俄猶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另一方面則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場、派系傾向、情感傾向,即支持左宗棠及其塞防派,對抗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所以他批評“海防”派及其海防觀:
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懾日本者以懾外洋各國,計孰有便于此者。徜此舉再誤,則中國安
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師跨海,搗橫濱,奪長崎,掃神戶,臣雅不欲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絕
市以困之,此亦平實而甚易行者矣。
畢竟,張之洞不是一個頑固不化的人,能夠隨著時局的變化、學習的進步而與時俱進,他后來顯然也認識到自己的主張不免“顧此失彼”,于是馬上作了修改。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張之洞在《臺防重要敬舉人才片》中提出的主張就顯得比以前的書生之言務實得多,認識到對日本不可太輕視,“夫日本滅球,乃垂涎臺灣之漸”,于是積極督促朝廷加強臺灣的防務,“為保臺灣計,為保閩省計,此亦不可緩者也。惟望宸斷,早為決計施行”uJ 72用心委任大將加以提防。在光緒七年七月初五日的《疆寄虛懸請早處置折》中,主張啟用彭玉麟等鎮守東南,以期“日本聞之,必且悚懼改圖,就我范圍”。在光緒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集重臣籌議急務折》中則警告朝廷“御侮豫防”:
日本自球案梗議,使臣遽歸,目前相持未定,雖聞其餉絀船敞,人心驚惶,然彼已成騎。
但是在張之洞的眼中,此時的日本乃“海國”且是小國,海國只爭貿易和海權,沒有陸權的抱負,小國也難以威脅大國,且小國日本“與中國在利害上無大沖突”,是可以聯合的。張之洞此時的立意是“聯合弱小對抗強俄”、“以小抗大,以弱敵強”[2J 48。所以在光緒九年中法戰爭爆發時,他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呈的《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折》中提出了“散敵援”的主張,要求朝廷“宜急與英、德、美、澳、日本諸國,開陳曲直,堅立要約,務守公法”
19世紀70、80年代的張之洞之所以忽視日本,主要是受傳統思想和教育的影響,在華夷思想的支配下,他心目中的日本只是一個落后弱小的島國。當然,隨著職務的升遷,涉外事務閱歷的加深,以及參與洋務,張之洞逐漸拋開了書卷氣,其外交觀和日本觀也在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二、聯俄抗日:甲午戰爭前后張之洞的外交對策
1894年春,中日之戰如箭在弦,自認能夠擔當大任、獨擋一面的張之洞更加積極地思考對策并提出自己的主張。他感情上是仇視日本的,因此此時的外交主張和日本觀帶有感情因素,這也是受前一階段作為一個清流健將輕視日本的觀念所影響。
甲午戰爭前張之洞積極主張對日本宣戰,態度鮮明。戰爭爆發后張之洞號召抗戰并且積極備戰,是主戰派的重要代表。戰爭期間,張之洞參與軍務,籌劃后勤補給,切實加強長江沿線的防務,嚴陣以待,隨時準備迎擊溯江而上的日軍。
在此階段,張之洞也非常重視對日“伐謀”、“伐交”,甲午戰爭危機期間,張之洞竭力思考奇謀異策,甚至計劃到海外“募洋兵一萬,令洋將帶之,即乘所買兵船,擇妥便處會齊,中國派大員數人前往,會同督率,許以重賞,包打日本東京,徑赴東洋,直攻橫濱、東京”,張之洞本以為此“實為上策”,可立千古不朽之功,其實乃異想天開,此時的英國找不到第二個戈登和洋槍隊了,彼為一國之內戰,此為二國交戰,外國勢力自然會慎重。
1894年底,中國在海、陸兩個戰場的敗相均露,東北各省危急,俄國出于自身利益,在外交上開始向中國傾斜,張之洞自然不愿意錯過這樣的時機,極力爭取俄國的干涉。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Et,作為地方大員的他在“致俄京許欽差”的電文中指出:
倭患日深,遼沈危,京畿急,非借強援不可。上等借船助戰,次者武斷脅和,如前數年英為俄、土
兩國武斷定和之事。英忌他國奪東方利,俄亦不愿倭強,志在自得,海口似均可商,但必須餌以重利,
恐須商務、礦務、界務等事于彼有利益,方能相助。聞前數年英有在中國開煤礦之請,祈密向駐德、駐
俄、英公使及俄外部委婉探詢,尤望渾淪言之,看其意之所欲何在。
在中日戰爭以及后期的和談期間,張之洞一直力倡“借強援”以“脅和”,反對“講和”。在民族榮譽感、戰爭失敗的恥辱感影響之下,出于對日本正在努力促成的日英同盟的擔心,張之洞基于中國“遠交近攻”的傳統理論,主張遠結歐洲強國英國、俄國對抗小國日本。為了促使這一主張付諸實施,他不斷發電向中國駐外各使節加以解釋,希望他們配合行動。
但由于日本積極和英國妥協,英國難以誘動,從1895年初開始,張之洞不得不把結強援的重點轉向與東亞利益關系至深的俄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張之洞“致俄京許欽差”電:“時局萬分危急。設或京畿有警,關內外隔絕,餉械俱罄,關東二百營將束手且嘩潰矣。鄙意接濟關東軍,惟有商之俄國。”從隨后二十七日“許欽差來電”中“俄主允,如議和時倭索太過,可約英、法勸其退讓”答復看,在張之洞要求下,許景澄和俄皇取得了聯系。
到中日商議停戰,割讓臺灣之論喧囂,在英國不為“借巨款,以臺作押”的利誘所動之時,張之洞更是借重俄國,希望以此利誘俄國。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張之洞繼續“致俄京許欽差”電,要求他與俄外部密商:
將臺灣作押之說能行否,或并許在臺開礦,但須約定必為我保臺方可。然此僅為一臺計,關系尚
小。如再能與商以兵威脅和,令倭人速罷兵,不索割地,不索重費,則中國全局受益。即許以內地他項
利益,如內地開礦與商務、開鐵路諸事,或徑詢俄另有何欲,令其自言。總之,于根本無傷、大局無礙
者,似皆可商。
即使是在割臺議定、大勢已去之后,張之洞依然不死心,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繼續“致俄京許欽差”電,電示許景澄“急速面謁俄皇,瀝懇相助”,并表示自己有“為包胥乞秦之舉,特以中國大員向未聞有與各國之君通電之事,未敢冒昧” 。張之洞等人的運作的結果,雖然促使俄國聯合法國、德國強制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國還為此付出了以三千萬白銀補償給日本的代價,而且中國還不得不對俄、法、德等給予適當的補償以酬勞,此事為以后的危機與爭端埋下了伏筆。
這一時期張之洞的外交主張很大程度上受敵視日本的感情所支配,乃至支持李鴻章與俄國“密約”,聯俄抗日,甚至不惜犧牲國家主權挑起日俄的矛盾,他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致俄京許欽差”的電文中就如此明示:
如能勸俄堅持,不準倭干預韓事,不準倭留一兵在韓,倭必不從,即藉此與倭攻占。一經開仗,倭
船必毀,不惟臺灣之患可解,中國亦可乘機盡翻全約矣,豈非旋乾轉坤轉禍為福乎?如俄肯為此,我
即以界務、商務酬之,有何吝惜?新疆西域及松花行輪、陜漢陸路運茶各節,俄從前要求未允,以此餌
之,斷無不愿。何不商詢外部,指以相助之法,微示以酬謝之意。
與外交策論相映的是張之洞個人在行動上堅決抗日。《馬關條約》簽訂以后,張之洞一再違抗朝廷旨意援助臺灣,并計劃以臺灣為餌結強援以脅和,而在支持臺灣抗日工作失敗之后又積極轉入與日本商戰的籌備工作。這時他依然沒有忘記聯合俄國及其盟國德國。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致俄京許欽”的電文傳達了沈子培部郎致許電文,指明“倭以商約困華,欲其貧而生亂”,要求許景澄“與俄密商,華倭爭商約,兩大國宜有公正語,限制倭人”,這實際上也是張之洞的主張。在國內,張之洞親自指導開展對日的商戰。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張之洞在“致上海葉令大莊”一電中指出:“倭約蘇杭制造、蘇滬行輪,意在奪我絲綢、紗布、小輪之利,我亟宜籌護華商華工之法,以抵倭人。”并且做出了具體的商戰部署,體現了他對于日本的敵視和戒備心理。
《馬關條約》簽訂后不久,張之洞便面臨和Et本的租界交涉事務。在交涉過程中,張之洞及其下屬遭遇了日方代表的惡劣態度,粗暴無禮,甚至蠻橫地侮辱中方代表。張之洞為何在此期間自號“抱冰”,此即表明他仇日的心態,抱冰堂是張之洞湖北新軍指揮所,顯然他在向公眾表明他要學習勾踐臥薪嘗膽、抱冰就火,勵精圖治以報日本,以雪國恥。
張之洞此一時期的外交思想和主張,集中體現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二十七日上書《密陳結援要策片》中,其中他分析了當時的局勢,系統地提出了“立密約以結強援”的“救急要策”,認為與列強之間“若無密約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預”,元以對抗日本的威脅,因此要求朝廷放棄此前的等距離外交政策,“獨加親厚之一二國”,這一國最好選擇俄國,因為“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西洋各國相抗”,不能不依據“遠交近攻之道”。對于選擇與俄國“訂立密約”的理由,張之洞認為英法德美等國“皆難議此”,而俄國“與中國乃二百余年盟聘鄰邦,從未開釁,本與他國之屢次構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案,各國爭哄,而俄國不與其事;伊犁之約,我國家將十八條全行駁改,而俄國慨然允從。此次為我索還遼地,雖自為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已實受其益,倭人兇鋒藉此稍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此論足見張之洞對列強的觀察太表面化,至于他“若有俄相助,將來無論何國尋釁,數旬之內,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游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斷不能為深入內犯之謀矣”…毗一l003的期待,更是一廂情愿的自說白話。而國際局勢的迅猛發展使得張之洞很快不得不改弦更張。三、結日阻俄:德國強租青島以后張之洞的策略
1 897年底,德國人借在“三國干涉還遼”中的功勞要挾中國,強租青島,而此時已經成為中國同盟的俄國卻不加勸阻,實際上德國的行動得到了俄國的諒解,此時的俄國與德國正是“三皇同盟”的軸心,已經約定在國際政治斗爭中共進退。更有甚者,俄
國乘德國侵略之際派軍艦侵入了旅順,此舉正與德國的舉措相呼應。
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還大力鼓吹“黃禍論”,號召歐洲聯合起來對抗黃禍,雖然表面上是針對日本的,自然也包括中國,俄皇在這方面也積極支持德國。
自1898年俄國占領旅順大連以后,張之洞越來越感覺到俄國的不可靠,認識到俄國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強援”,盡管俄國在志得意滿之后示好于中國。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也證明了他這一認識的正確性。而此時的日本,經歷“三國干涉還遼”之后,迫于國際上的孤立,不得不韜光養晦,主動親近、爭取中國實力派人士的認可與接受,尤其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誘導張之洞等人,文化上的Vl號自然是中日“同文同種”。與此同時張之洞隨著與日本方面交涉的深入,他的日本觀也在不知不覺中變化,慢慢由情緒化地敵視日本進入第三階段,即理性化地重視日本,而對于如何處理中日俄三國關系的主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張之洞自己對于日本的認識隨著他的閱歷增加而轉變,畢竟張之洞相對來說是一個很注重實際的人。張之洞對日本態度的改變還和日本人改變與他交涉的方式密切相關。在漢口租借談判、“沙市事件”處理中,張之洞充分感受到日本人的粗暴和淫威,但l897年ll月青島事件以后,前來與張之洞見面的日本人,與以前來中國談判的日本人代表動輒“以違旨大題要挾恫嚇,種種無理”閉,吲5截然不同,表現得相當謙虛、謹慎。這種前倨后恭的改變,使張之洞感受到了日本人所謂的“善意”。
了解中國現實的張之洞,這一時期很重視日本,在文化經濟上主要表現為師日,甚至看似“親日”。張之洞此時的聯絡日本不同于第一階段,著重在種族方面,在結合黃種人對抗白種人,這也是德國“黃禍論”與日本人的“亞細亞主義”宣傳的相互作用的結果。
張之洞從“仇”到“親日”的轉變發生在“戊戌變法”前后。這時他受到了日本有關政治家的重視,也遇到了幾個態度頗為謙虛、和藹的使節,心理上得到安撫。
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時,盡管李鴻章主張請求俄國出頭調解,并和俄國財政大臣聯絡,張之洞堅決反對,認為此時聯俄不利,不僅難以得到俄國的支持,反而會引起英國美國的不滿,主張積極聯絡和英國關系密切的日本,請求日本出面調停,策劃“東南互保”的他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致駐日公使李盛鐸的電文中表明了“中央”的主張:
今亂徒固不辨孰歐孰亞,各國亦莫分為匪為兵,惟日本深知中國情形,有共利。
這多半是出于種族的觀點,而善于投機的日本此時也利用張之洞的這種心理,和他親近,向中國示好。在《辛丑條約》談判的過程中,張之洞密切聯絡日本,也從Et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關的情報,此亦說明張之洞外交方針的調整。
張之洞此時對俄國失望還在于俄國乘義和團運動之機霸占了中國東三省,張之洞對于俄國獨霸東三省的企圖是毫無懷疑的,盡管李鴻章依然迷信俄國。1900年以后張之洞在外交上“親日”有在東北借Et本抵抗俄國的想法。在俄國強迫中國簽訂損害東三省主權的條約前后,張之洞極力活動日本、英國、美國,他在光緒二十七年eLY]二十四日在《俄約要盟貽害,請將東三省開門通商折》中提出的有關主張,顯然是在與日本有關人士協商后的結果,期間他還收到“日本國貴族院議長公爵近衛篤磨書函,并附陳措置東三省條議一冊”,張之洞獨自“詳加察覽”后,認為“其言深切墾至”。近衛篤磨送書函于張的目的就是防止中國權益被俄國獨自侵吞,虛情假意表示日本的好意。近衛在信中稱俄國“其包藏異圖實不可測”,“肆然逞其所欲為而不知厭”,其實日本也同樣“包藏異圖”,即要求日本在東北“一體均沾”,要求清政府“不得厚于甲而薄于己”。
《辛丑條約》簽訂后,關于賠款,張之洞主張在每年上半年籌足后交存上海的日本銀行,他主動將此利益讓與日本,“一則酬其助爭俄約之功,一則作為中日共立銀行,合作經營各項經濟事業之始。顯然在張之洞此時的思想中,已有一中日經濟合作,共拒強俄的想法”。
東北的均勢并未維持多久,l904年“日俄戰爭”爆發,l905年俄日兩國達成和議,平分了中國東北地區的權益,張之洞顯然很關心這一事態的發展,關心中國和日本有關東北各省權益的交涉,關心日本是否及時歸還中國東北權益,就在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張之洞接到“袁宮保來電”,袁世凱曾這樣答復他的詢問:
宥電敬悉。目前有日本大議員平岡浩太郎由京來謁,言“該國民高博士會議,以東三省戰事耗財
傷命,始漸規復。慮華政府力弱,不能保守,或再為俄據,議阻交還,暫代統治。并有議占福建者。
這顯然是讓張之洞傷心的答復,此時的張之洞應該認識了日本人的真實面目,張之洞顯然沒有忘記幾年前和俄國的交涉,以及日本人的慫恿之詞。從張之洞的有關文件看,他此后似乎并未過多關注此事,一心轉向廣九鐵路、練兵等問題上,顯然是對日本絕望,不想自尋煩惱了。
綜觀張之洞以上三個階段提出的處理日俄問題的外交主張,盡管其一變再變,但始終未能擺脫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