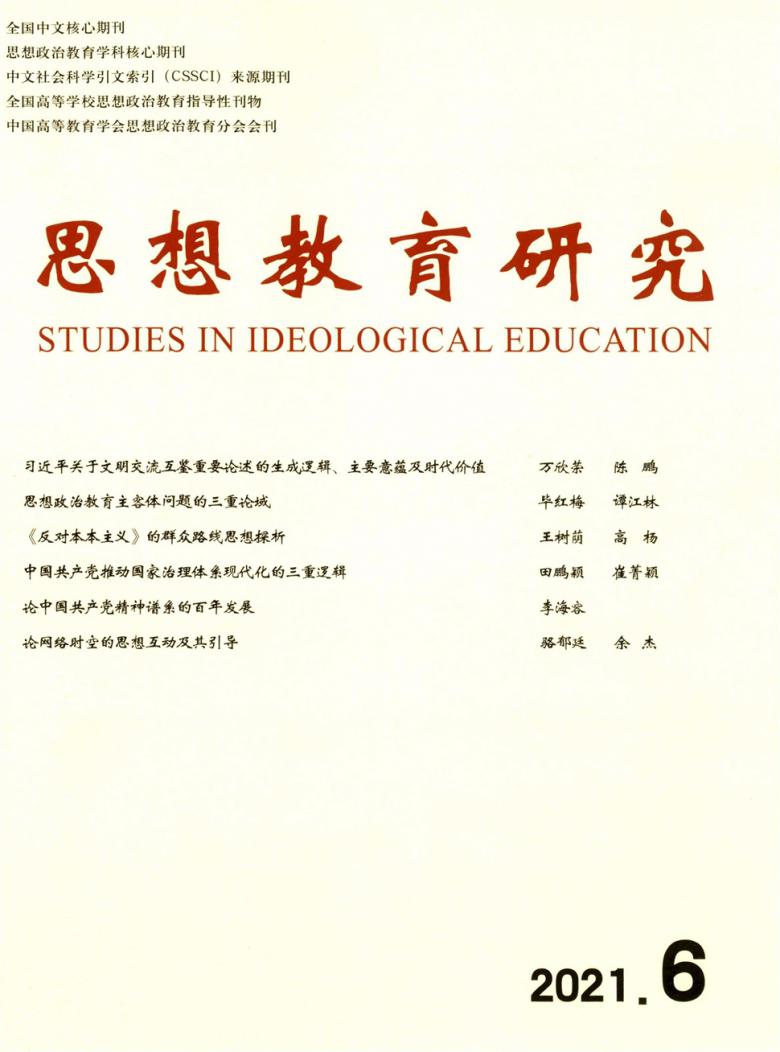從“民政局為遇難流浪漢索賠案”探討我國當事人適格制度
嚴佳維
一、問題的提出2006年4月,江蘇省高淳縣民政局為遇難流浪漢索賠案(以下簡稱“高淳案”)引起了世人廣泛的關注,被法學界和新聞界稱之為政府為流浪漢打官司討說法的 “中國第一案” 。 時隔8個月之久,江蘇省南京市高淳縣人民法院于06年12月18日作出了一審判決:因主體不適格,裁定駁回民政局起訴。盡管該案已暫時告一段落,但這個一審判決并不意味爭議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由該案引發(fā)的對民政局作為原告主體是否適格的爭論,以及倘若民政局不可以作為原告,那么死亡流浪漢是否是撞了白撞,他們的合法權益到底該由誰來維護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仍有待研究解決。適逢我本學期主修民事訴訟法,于是我結合相關案情、立法,針對上述案件原告是否適格問題深入進行了研究思考。 二、案件背景資料的收集因為我只是在課堂上聽老師提起過這個案子,所以我對該案的始末和細節(jié)情況不甚了解,故我首先通過上網及查閱相關報紙報道搞清楚案件的基本情況。1、“高淳案” :2004年12月4日,李某酒后駕車,在南京高淳縣境內將一名躺在馬路上的流浪漢碾軋身亡。多方聯(lián)系后,死亡男子身份仍然無法確定,交警部門在處理這起交通事故中陷入了困境。2005年4月2日,高淳境內再次發(fā)生類似事故。司機王某駕駛車輛,將一流浪漢撞跌在機動車道內,迎面駛來的機動車從流浪漢身上碾軋而過,致使其當場死亡。這個流浪漢的身份同樣無法確定。由于肇事司機多次催促警方來處理事故,高淳交警大隊找到高淳縣檢察院咨詢解決辦法。2006年3月8日,高淳縣檢察院向高淳縣民政局下達了兩份《檢察建議書》,提出建議:由民政局代兩名無名流浪人員提起人身損害賠償訴訟。幾天后,民政局將兩起事故中的肇事方和保險公司訴上法院,要求賠償兩流浪漢的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30多萬元。2006年12月18日,高淳縣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因主體不適格,裁定駁回民政局起訴。在查詢本案相關資料的時候,我驚訝地發(fā)現今年在其他地方也發(fā)生了類似的案件,只是未受到媒體太多的關注而已,并且當地的人民法院也都已經作出了相關的判決,我認為這對研究所要討論的問題有很高的價值。故也摘錄如下:2、“湖南臨湘救助站為遇難流浪漢索賠案”(以下簡稱“臨湘案” ):2005年11月12日晚,一名流浪漢在107國道1419KM界碑羊樓司附近遇車禍身亡,當地交警部門在規(guī)定期限內公布消息尋找死者家屬,至今無人上門認領。2006年4月12日,在當地交警部門和檢察院的支持下,臨湘市民政局救助站以職能部門的身份將肇事車輛所屬的運輸有限公司和投保的財產保險公司告上法院,并提出了25萬元的索賠金。 2006年7月21日,臨湘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兩被告向原告民政局救助站支付賠償款15萬余元。3、“浙江桐廬縣民政局為遇難流浪漢索賠案”(以下簡稱“桐廬案” ):2005年10月31日晚,在桐廬縣境內的省道上,司機姚某駕駛一輛輕型貨車,因疲勞駕駛打瞌睡,車輛失去控制,撞上迎面走來的一男子,造成該男子重傷,經搶救無效死亡。交警部門認定姚某負這起事故的全部責任,但是死亡男子的身份卻一直無法查明。2006年9月,桐廬縣檢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對姚某提起公訴。引人注目的是,桐廬縣民政局作為附帶民事原告人的身份出現在法庭上,為無名氏索賠33萬余元。桐廬縣法院審理后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浙江省實施該法有關規(guī)定,身份不明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傷亡的,損害賠償金由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提存保管。而身份不明之人是有關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三無人員”,屬社會救助對象,民政局是負責處理社會救助事務的部門,由其代為被害人主張權利并無不妥。據此,法院一審判決:姚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同時賠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即桐廬縣民政局)33.8萬余元。 三、背景資料的剖析從上述三個類似案件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各地法院對民政局能否為遇難流浪漢索賠這一問題的立場是不同的。在“高淳案”中,當地人民法院認為民政局作為原告主體不適格;而在“臨湘案” 和“桐廬案”中,當地人民法院顯然認同民政局或其下屬機構救助站具有合法的原告資格。那么為什么類似的案件,人民法院會作出不同的判決呢?進一步深究,我發(fā)現“臨湘案”較之“桐廬案” ,與“高淳案”更具可比性。理由是: 在“桐廬案” 中,由于06年3月底,浙江省人大通過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其中第61條有這樣的表述:“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有權向賠償義務人追償” ,“交通事故死亡人員身份無法確認的,參照城鎮(zhèn)人口賠償標準,其損害賠償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提存保管”。而目前浙江還沒有一個真正的 “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 ,但可以將其廣義理解為政府相關部門。民政局與無名流浪漢之間正好是救濟與被救濟的關系。這樣,法院通過這個地方法規(guī)認定桐廬民政局的維權名正言順。但“臨湘案” 和“高淳案”中,湖南和江蘇并沒有制訂和浙江類似的地方法規(guī)以使民政局的主體資格得到法律法規(guī)上的確認,所以接下來我主要是針對這兩個案子進行比較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桐廬案”對所提問題的解決有著很大的啟發(fā)意義。 四、問題核心的理論介紹“臨湘案” 和“高淳案”所反映的問題核心就是民政局原告主體是否適格,抽象到民事訴訟法學研究上就是有關當事人適格的問題。那究竟民政局是否為適格主體,以下我就帶著這個問題對民事訴訟當事人適格制度進行論述和思考。(一)當事人的概念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是指為保護民事權益,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引起訴訟程序發(fā)生、變更、消滅的人。當事人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當事人只包括原告(起訴的人)和被告(被訴的人),廣義當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還包括共同訴訟人、訴訟代表人和第三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當事人即無民事訴訟。(二)當事人適格1、當事人適格的概念當事人適格,是指當事人在具體的民事訴訟中,能夠作為當事人進行起訴或應訴,具有訴訟實施權的資格。當事人適格和民事訴訟權利能力不同,當事人適格是就具體案件而言的,當事人適格表明該當事人是正當當事人(正當當事人是指對特定的訴訟,有資格以自己的名義成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該案判決拘束的當事人)。而民事訴訟權利能力是針對抽象訴訟而言的一種資格,有民事訴訟權利能力未必是正當當事人。2、判斷當事人適格的標準傳統(tǒng)民事訴訟法理論認為,適格當事人應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具有民事訴訟權利能力(當事人能力);二是對訴訟標的所涉權利義務關系具有訴訟實施權。判斷當事人適格的標準,關鍵就在于有無訴訟實施權。根據當事人對特定的訴訟標的有無訴訟實施權,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學者將當事人分為適格當事人和非適格當事人,我國學者又稱為正當當事人和非正當當事人。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訴訟實施權的基礎是不同的。主要有以下兩種情形:(1)對實體權利有處分權或管理權一般來說,實體法上的民事法律關系或者權利義務主體,即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對訴訟標的具有訴訟實施權,是適格的當事人。這是傳統(tǒng)的利害關系當事人觀念的主要依據,也是我國民訴法規(guī)定的起訴要件之一。爭議的實體法律關系主體如原告對自己的權利有處分權或管理權,他們當然具有訴訟實施權,可以就爭議的法律關系提起訴訟,從而成為正當的當事人。(2)訴訟擔當在某些情況下,法律關系主體之外的某些特定主體雖然不是權利義務主體,但其基于法律規(guī)定或當事人約定對訴訟標的享有管理權或處分權,也是適格當事人。對于上述情形,民訴法理論上稱為訴訟擔當。所謂訴訟擔當,是指實體法上的權利主體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以外的第三人,對他人的權利或法律關系有管理權,以自己的名義,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當當事人的地位就該法律關系所產生的糾紛提起訴訟,法院判決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關系主體 根據訴訟擔當產生的依據不同,訴訟擔當分為法定的訴訟擔當和任意的訴訟擔當。法定的訴訟擔當是指基于法律規(guī)定而對他人的權利或法律關系享有訴訟實施權,如破產管理人、遺囑執(zhí)行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的財產代管人、為保護死者利益提起訴訟人等;任意的訴訟擔當是根據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意思而承認的訴訟實施權,如我國的代表人訴訟中,代表人基于被代表人的授權而擔任訴訟代表人。3、適格當事人的確定學者江偉、孫幫清曾提出了如下思路以確定當事人是否適格:(一)首先判斷是否具備訴訟權利能力。當事人適格必須以有訴訟權利能力為前提,無訴訟權利能力者肯定為當事人不適格,但有訴訟權利能力者不一定適格。(二)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訴訟實施權及訴的利益。對于給付之訴,當事人適格是以訴訟實施權為基礎的。凡屬于原告所主張的實體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主體當然具有訴訟實施權。此外,訴訟擔當人也具有訴訟實施權。對于確認之訴,原告對其請求有確認利益,即為原告適格。對于形成之訴,依照法律規(guī)定可以成為當事人的,即為當事人適格。(三)根據原告起訴時訴的聲明來判斷。對于當事人是否適格,應當以原告起訴時所主張的訴訟標的來判斷,并非以法院調查結果為準,即從形式上認定作為訴訟標的的法律關系應當在何特定當事人間解決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與該法律關系本身是否實際存在是兩回事。五、案例分析結合上面的理論介紹,我來探討下“臨湘案” 和“高淳案”中民政局作為原告究竟是否適格的問題。在“高淳案”中,贊成民政局可作為原告的一方如高淳縣檢察院,它認為,根據國務院《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有關規(guī)定,民政部門承擔對無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職責,這種救助,不僅僅是對流浪乞討人員生活無著的保障,也包括流浪乞討人員人身遭受侵害后提供的法律救助,即損害賠償主張的權利。民政部門以“社會救助部門機關及流浪人員監(jiān)護人的身份” 提起無名流浪人員人身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是符合有關法律法規(guī)的立法本義的。而“臨湘案”中,臨湘法院認為,雖然法規(guī)沒有具體規(guī)定救助站在流浪乞討人員的人身遭受侵害后可提供法律援助,但救助站行使法律維權,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取向,因此救助站以原告身份提起訴訟不違反法律有關禁止性規(guī)定。且由于救助站是代流浪人員的近親屬行使訴訟權,所得的賠償僅是代為保管。除了司法工作人員的意見相左外,學者們對于這個問題的意見也紛紜不同。武漢大學法學院羅英認為民政局作原告為死亡流浪漢索賠不妥,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還有學者則認為民政部門作為職能部門,提起無名流浪人員人身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不僅是其權利同時也是它的義務,符合有關法律和法規(guī)的立法本義。 而我個人認為的臨湘法院的判決還是值得商榷的,問題的主要在于: 一方面,民政局或是其下屬部門救助站是否有為流浪乞討人員在人身遭受侵害的情況下提供法律救助的權利和義務?一般認為,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通過法定程序對處于生存困境的公民所給予的財物接濟和生活照顧,保障其滿足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根據《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第4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負責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工作,并對救助站進行指導、監(jiān)督”,民政局依法負有對流浪乞討人員的社會救助義務。但是,民政局的社會救助似乎僅限于滿足被救助主體最低生活水平即可,索賠訴訟活動顯然不在其列。認為民政局(救助站)為適格主體無疑是賦予了民政局進行索賠訴訟活動的權利,正如臨湘市人民法院認為救助站以原告身份提起訴訟不違反法律有關禁止性規(guī)定。這樣的觀點我認為是站不住腳的,政府權力的運行規(guī)則并非“法無禁止即可為”,而是“法無授權不可為”,即作為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民政局所行使的權力都必須是法律法規(guī)明文規(guī)定的,而不能靠法律推理獲得。《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規(guī)定民政部門僅有提供食物、住宿條件的救助義務,并沒有其他方面的概括授權,因此并不能推理出民政局可以原告身份作為訴訟主體要求賠償的權利。正因為沒有相應的授權,其獲得賠償后的賠償金管理、使用都缺乏相應的管理辦法和監(jiān)管程序,很容易導致權力濫用或隨意處置侵吞賠償金,同樣我們也很難想象民政部門若整天忙于民事訴訟,其本職社會救助工作將怎么來履行。另一方面,在“臨湘案”的判決中,聲明救助站是代流浪人員的近親屬行使訴訟權,所得的賠償僅是代為保管。照此看來,救助站并非該民事法律關系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它的準確身份應該是遇難流浪人員的近親屬的訴訟代理人。我不由地想問,它的代理權從何而來?法定代理?如上所述,我國現行法律法規(guī)中并未有此種規(guī)定 ━━“遇難流浪人員的近親屬不明時,民政局或其下屬部門可以代為訴訟”。委托代理?更不可能!流浪人員的近親屬尚不明了,委托談何說起。綜合以上兩點,我的立場是在現行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下,民政局不可以作為這類案件的原告。 六、對此類案例適格主體的思考這兩例案件引起了法律界的廣泛關注,關于對不知名流浪漢車禍身亡的法律救濟制度,目前國內立法尚屬空白,這也是目前社會救濟體系暴露出的盲點。民政局作為原告為該特殊群體維權,這一嘗試的出發(fā)點毫無疑問是好的,否則人的生命權如何能得到尊重與體現,肇事方、保險公司又是否有不當得利之嫌?如果民政部門有權索賠,獲得的賠償款又如何進行管理?這一系列問題,已超出了案件審理本身,民政局能否勝訴已不重要,如何為這部分弱勢群體維權,由哪個部門行使,這是我們立法、司法實踐亟需解決的問題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具有當事人能力的訴訟主體指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據此,我認為在此類案件中,可以通過法律的授權使政府的職能部門或司法部門成為適格當事人,亦可以依法成立一定的機構組織專門為不知名流浪漢維權。(1)民政局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最合適的行政機關就是政府的民政部門,因為它負責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一切無家可歸者的最終歸宿都應當是民政部門。嚴格來講,正如高淳縣檢察院認為的那樣,民政部門對流浪人員的救助不僅包括生活救助,而且也可以包括法律救助。通過法律的授權,并制定相應的賠償金管理、使用辦法和監(jiān)管程序,無疑是最大程度地維護了流浪漢這類弱勢群體的利益,維護了社會公共利益。落實到現實立法中,我覺得可以由各地區(qū)采取浙江的做法,在地方法規(guī)中作相應的規(guī)定,當然,與其用“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 的名稱,還不如直接按中國目前的國情改用“民政局”為好 。(2)人民檢察院流浪乞討人員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利益作為不特定主體的一類人的利益屬于公共利益的范疇。而自檢察制度產生以來,檢察機關就以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出現,作為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負有監(jiān)督法律統(tǒng)一正確實施的職責,檢察機關能夠有效地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作為為特殊群體維權的公益訴訟的原告,不僅有法理上的依據,而且在實踐中也是可行的。在英國和法國,檢察機關可以代表公眾提起民事訴訟,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正如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上為維護公共利益有追訴權一樣,在民事訴訟上它也同樣可以有追償權。(3)其他組織如消費者協(xié)會、工會、婦聯(lián)等行業(yè)和公益團體組織,對該團體組織領域內發(fā)生的民事公益違法行為可以提起訴訟一樣,可以依法成立一個專門為流浪漢維權的公益性社會團體,根據其自身成立的宗旨、章程,有維護其成員合法權益的職責,當其成員的權益遭到違法行為侵犯時,除了有批評、建議等權利外,應賦予其提起訴訟的權利。“讓某些社會團體作為群體訴訟的適格當事人,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人的實體權益,另一方面可以減少訴訟環(huán)節(jié)和訴訟浪費而有助于減少程序利益的耗費。” 七、總結從情理和法理角度講,應當有人出面及時為遇難流浪漢索賠,以便穩(wěn)定民事法律關系,避免侵權人因此不當得利造成法律不公。盡管民政部門已作為原告提起了訴訟,但從當前的法律規(guī)定來看,民政部門確實沒有此項法定權力,這就暴露了我國救助法律的一個缺陷和漏洞。而這個法律問題,僅靠法院是無法妥善解決的,即便法院最終支持了民政部門的請求,也并不意味著彌補了法律漏洞,它有待于立法解決,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我國的救助制度,創(chuàng)設為特殊群體維權提起訴訟的適格主體。這已是由案例反映出的深層法律問題,值得法學界和司法界更多的思考。 此外,由“臨湘案” 和“高淳案”出現案件類似而判決結果不同的現象,我想到:這種情況基于種種因素在中國屢件不鮮,有法律自身不健全的問題,也有人為認識不同的原因,這就使我不由地想起有學者提出在中國發(fā)展判例法的建議,至于判例法在中國如何發(fā)展,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關于這些問題,留待今后進一步研究。 參考書目:1、 李浩、劉敏:《新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3.7 第一版2、 江偉、孫幫清:《當事人適格的識別》,載中國民商法律網( 2003/10/28)3、 邱聯(lián)恭:《程序制度機能論》 三民書局 1992



藥.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