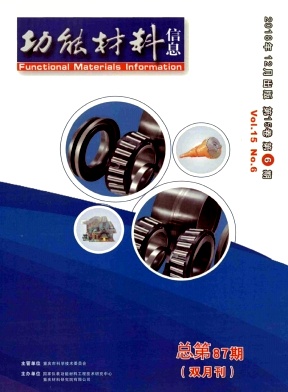苦難敘事、“人民性”與國族認同——對當前“地震詩歌”的一種價值描述
李祖德
【內容提要】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媒體上涌現了眾多的“地震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民眾對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生命價值的追索。從詩與史的關系出發,本文描述的正是當前“地震詩歌”的價值蘊含,即其中表達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
【關鍵詞】 “地震詩歌”;苦難敘事;“人民性”;國族認同:詩史互證
如何重建詩歌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精神關系,這是困擾當代詩歌甚至是整個新詩史的問題。對于當下的詩歌寫作而言,當詩歌(文學)“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之后,我們又如何讓詩歌(文學)“重返”時代和社會,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或理論問題了,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態度和價值訴求的問題。
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媒體上涌現出了許多的相關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詩人及民眾對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中華民族面臨的苦難考驗的哀傷和追索。一方面,有論者認為“大地震震出了一個復蘇的詩歌界”,地震“引發了全民詩歌熱潮”,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詩歌作品具有大眾化、口語化、即時性甚至是“戰時性”的特點,并不具有特別的“藝術水準”。
這些不同評價都涉及到了“地震詩歌”[①]的藝術價值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呈現“地震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訴求。“地震詩歌”也會為時間和歷史(或者某種“文學史”)所選擇和清理。基于這些考慮,本文并不是要從詩歌(內部)藝術的意義上來討論“地震詩歌”這一文學事件,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關系,也即是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描述其價值蘊含。在本文看來,“地震詩歌”中所蘊含的民族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意義指向正是其價值表征。從這一角度來看,盡管作為一種“戰時性”(暫時性)的詩歌現象而且頗多雷同化的傾向,“地震詩歌”仍然為當代新詩寫作如何“重返”時代和社會提供了一種深刻啟示。
一、價值的關聯:地震與詩歌
僅以2008年6月號《詩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災”詩專號為例,關于5·12大地震的詩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民族國家主體性等諸多內容,其他媒體上涌現的詩歌作品也同樣在這些層面上多有表現。諸如李瑛《生命的尊嚴如此美麗》組詩、商澤軍《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國家的眼淚》、蔣同《國哀:那一朵小白花》、白連春《整整一個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證》、葉舟《祖國在上》以及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寶貝啊,不要沉睡》、《媽媽的呼喚》、《孩子,天堂路上別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著淚水》、《開往天堂的火車》、《爸爸媽媽,別為我們難過》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災的“戰時性”狀態下,詩人和民眾對大地震帶來的災難和民族苦難的哀傷和痛惜,同時也傳達出了一個民族在災難和苦難面前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團結。
在這里,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就建立起了一種價值的關聯。也就是說,這些詩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僅僅是一種反映關系,其中還存著在一種意義關系。“地震詩歌”一方面記錄了大地震這一民族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蘊含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戰時性”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苦難敘事、“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價值內涵。
如果說“啟蒙”與“救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變奏[③]的話,那么,從整個現代文學史來看,“地震詩歌”則同時兼具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主題。大地震及其災難,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現實的危難從我們的歷史經驗中獲取了苦難的精神內涵。而“地震詩歌”同樣也從文學史(詩歌史)的經驗中獲取了“民族救亡”的寫作動力。從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④]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⑤]了的歷史形象。“地震詩歌”仿佛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對現實災難和民族生存苦難的觀照中,我們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間、艾青等人歌唱的時代,同時又回到了“中國新詩派”和“七月詩派”等人沉詠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文化事件,在現實的語境(自然災難與民族苦難)中獲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與精神啟蒙的意義。
可以說,在對地震災難、人性磨難和民族悲愴的苦難想象與敘述中,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交織著生命、死亡、苦難、大愛與民族精神的繁復旋律,這些繁復旋律正演繹著“啟蒙”與“救亡”的復調敘事,而非一種聲音壓倒另一種聲音的“雙重變奏”。因此,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看,并在價值和意義的維度上進行考察,“地震詩歌”既體現出了關于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情感和認同。作為自然災難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難和價值重塑的意義和功能,詩歌對苦難的書寫加強了現代新詩“人民性”的文學品質,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族和身份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與詩歌再次確立了“詩”與“史”的關系,并締結了多重的意義關系。“地震詩歌”的出現既是對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大地震的歷史書寫,也是對隱秘的民族心靈史——國族認同的一種情感(文學)呈現。
二、題旨一:災難考驗與“人民性”
當下的“地震詩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大地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考驗,以及國家和人民抗震救災的信心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性”是“地震詩歌”的基本情感和價值意向。在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單純的政治和階級含義,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感、經驗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災——“民族救亡”的歷史時期,“地震詩歌”體現出的這種“人民性”的文學品質,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匯集。
從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詩歌的抒情主體再一次回歸到時代的“大我”。如《這時候——寫在5.12四川汶川震災之后》:“當十三億同胞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淚水打濕了一張張善良的面容/這時候,我們挺直了滄桑的腰板/我們昂起了高貴的頭顱——/為了抵抗這無法避免的天災/我們變成了熱血沸騰的英雄 /這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在這樣的詩歌里,抒情主體“我”和“我們”并不存在什么情感、價值、觀念和意圖的差異,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地震災難和民族精神進行反復的敘說。在詩歌里,“我”是作為一種視點而存在的,而“我們”才真正是詩歌情感擴張的輻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體。因而,作為詩歌敘述者的個人和作為詩歌抒情主人公的集體——“我們”、“十三億人”在這里達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統一性。再如一首《我們的心——獻給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詩歌”中頗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們”進行詩歌的抒情和敘事:
我們的心朝向汶川/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讓我們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淚/夜,很安靜/往日的喧囂也緘默了言語/儼若戰后的城市/荒蕪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滿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樓道里的死亡氣息/埋沒了花草昨日的鮮艷/掩埋了螟蟲昔日的笙歌/飛鳥也遠離了故土/不忍視/汶川流淚/四川流淚/中國流淚
自然災難的考驗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力量在這里匯集了。正如詩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愛這土地》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和民族苦難一樣,國家和民族正面臨著災難的考驗,詩歌抒情主體也轉變成為一個時代的歌手,傳達出了一個集體的聲音。“故土”、“家園”、“戰后的城市”和“災難”等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種精神的意義,而“我們”則成為“地震詩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說,詩歌抒情主體的包容性使“地震詩歌”不僅僅起著一種集體代言的作用,而且還有效地傳達出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詩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顯現,使得詩歌再一次恢復了它應有的功能。
書寫民族的災難和民族的重生是這些“地震詩歌”最基本的意義傾向。其他相關作品如郭文斌《中國,你為什么淚流滿面》、劉繼明《哀悼日》、魯文詠《地泣與國殤》等作品都直接書寫了民族和國家在面臨地震災難時的艱難和信心。這些詩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對災難和苦難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現“人民”和“人民性”的時代主體。因此,重塑一種新的時代主體和主體精神也是“地震詩歌”最普遍的主題之一。作為當代新詩的核心命題,“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詩歌”里被再次激活。
當代詩歌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后,作為一個詩學話題,詩歌的抒情主體從“大我”“回歸”“小我”已經為當代詩歌史所確認,但我們會發現,當下詩歌寫作的思想和審美空間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何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重新恢復“我們”——另一種抒情主體的價值和權利,或者如何在表達個人體驗的同時融入民族國家的情感和命運的內容,這是在當下詩歌寫作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在這次大地震和“地震詩歌”事件中,詩人們及民眾暫時放棄了理論上的成見和分歧,災難、苦難、生命與愛、國家與民族成為當下詩歌的共同話語,這也許正寓示著詩歌寫作應有的一種品質和良知:“我們”如何表達“人民”與“人民性”?
“地震詩歌”作為一種現象,它給我們的啟示恰恰在于:詩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同樣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詩學命題。當“地震詩歌”讓“我們”重新成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時候,一個新的歷史主體也復活了。因此,可以說,作為歷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詩歌,作為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也在激活詩歌的主體——“人民性”。從“地震詩歌”的寫作者來看,眾多“非專業”作者的參與也為當下詩歌寫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正如批評家謝有順在評價“地震詩歌”時所說,“詩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⑥]當“我們”成為當下詩歌的主人公時,詩歌、詩人、民眾與國家民族、時代和社會才再次達成了情感和價值的溝通。因此,“地震詩歌”所展現的“人民性”,給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新的方向。
三、題旨二:苦難敘事與國族認同
對苦難和災難的“歷史化”書寫也是“地震詩歌”的基本題旨之一。對“歷史”(現實)的“歷史化”敘述是建構一個國家和民族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盡管大地震依然是我們當下的現實,作為一種“戰時性”文學表現手段,“地震詩歌”則已經提前將大地震“歷史化”了。在對大地震的“歷史化”書寫中,“地震詩歌”容納了“苦難”敘事的成分,甚至帶有某種民族寓言和神話的特征。在許多“地震詩歌”的敘述里,大地震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正是這種集體的“苦難記憶”成為我們國族身份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苦難是我們共同經歷的苦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已成為建構和強化我們國族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
如在媒體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一詩這樣寫到:“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媽媽怕你碰了頭/快抓緊媽媽的手/讓媽媽陪你走//媽媽/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見你的手 /自從倒塌的墻/把陽光奪走/我再也看不見/你柔情的眸……”在這樣的詩性言說里,個人作為敘述者,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容納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媽媽”和“孩子”穿越時空和生死界限的對白,將苦難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禱告。苦難讓我們反觀和照亮現世的生存。再如《開往天堂的火車》一詩,是將生命與死亡、告別與歸家、苦難與幸福表現得最讓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有一條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們的告別乖得沒有一點聲響/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孩子/變得像大人一樣堅強/他們行將離去的站臺/也不再需要爸爸媽媽與奶奶的/送行//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會穿過一片鮮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們來自神靈的家鄉
這些作品從苦難、人性的角度將災難、生命的罹難和死亡作為生命的歸宿的敘述,對大地震帶來的“苦難”進行“歷史化”的書寫。“火車”、“告別”、“站臺”、“天堂”和“家鄉”等種種意象都無不意味著生命的歸宿和幸福。這樣的苦難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審美化的傾向,災難、苦難和死亡被賦予了一種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某種神話和寓言的意義功能。
在這些充滿“個人化”的苦難敘述中,苦難已不僅僅是個體和生命、死亡的意義關系,而是已經成為我們每一個閱讀者的苦難記憶。“告別”與“歸家”、“離開”與“尋找樂土”的意義結構是詩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話寫作”的基本模式,而這一類“地震詩歌”則在這一向度上體現了生命、人性與苦難的意義關系。應該說,這樣的苦難敘事是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它們所表達的是苦難和對苦難的意義追索。“誰點燃了這燭。并且,讓燭光成了中國鋪滿陽光的午后最痛的傷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寬仁的手指/就著厚厚的黃土與淚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燭光擊中,然后/碎了……”(龔學敏《汶川斷章》)在這樣的苦難敘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燭光”等意象實現了跨越歷史時空的碰撞,地震災難與民族傳說一起呈現了人性、生命、個人和民族國家共同的心理原型,這種“神話寫作”恰恰是有關人性和苦難的,這里面容納的意義和價值正隱藏著一個民族國家潛在的精神結構。
與苦難同時傳達出來的,還有關于愛的內容。苦難與愛作為詩歌(文學)寫作中的一種原型或母題,同樣在大地震這一歷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現的空間。許多“地震詩歌”直接以愛為題,將自然的災難、人性的苦難以及生命救贖等復雜的情感體驗融合到一起。苦難、愛與生命本身結為一體,苦難因此而多了一層悲憫的宗教色彩,愛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為一種“大愛”。地震災難帶來的“恐懼與顫栗”背后是對苦難的擔當和愛的力量。有詩句這樣寫到:“這不是詩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個死難者的聲音/此刻醒來,就要永遠醒來/因為我們還在經受更為嚴重的災難/它來自我們自身,來自陰謀和戰爭/來自掠奪、殺戮、膨脹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還來不及發現/靈魂已離去好多年……”(東蕩子《來不及向你們告別》),還有詩句這樣表達了對苦難和愛的悲憫:“當我寫下/悲傷、眼淚、尸體、血,卻寫不出/巨石、大地、團結和暴怒!/當我寫下語言,卻寫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漁《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在詩人的話語敘述里,有對自然、苦難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卻家園的悲傷,也有對自我的責問,苦難與愛被賦予了懺悔和救贖、生命歸宿與精神家園的意味。
盡管這些詩歌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化”和“神話寫作”寫作的痕跡,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歌作品仍然從“個人化”的苦難記憶里表達了一種集體的苦難歷史。很多“地震詩歌”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或“我們”這一詩歌的抒情主體導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國人”,正如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此刻/我們都是汶川人/我們都是四川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汶川人”與“四川人”作為一種地方性情感、知識和經驗的主體,在“地震詩歌”里則獲得了更高的意義,作為詩歌的抒情主體,它正是一種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個更大的主體性——“中國人”。其他詩歌如《國家的眼淚》、《國哀:那一朵小白花》、《14時28分的祖國》等作品則直接從時代“大我”的角度展開了對民族苦難記憶的“歷史化”書寫。
“歷史化”意味著對記憶的整理,記憶則保存一個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對地震與災難、生命與死亡、苦難與幸福、愛與擔當的“神話寫作”中,詩歌的抒情主體、國家、政府、社會和民眾已經結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的苦難敘事,強化或者凸顯了一直隱藏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心靈深處的身份認同。
四、詩史互證:苦難記憶及其意義
隨著災難的過去,“地震詩歌”的熱潮也會逐漸趨于平淡,“地震詩歌”作品也會經由時間的選擇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與過去的幾次詩歌事件(如“梨花體”等事件)決然不同,這一次的“地震詩歌”事件則激活了“詩”與“史”的互動關系。地震與詩歌發生意義的碰撞,也正是“詩”與“史”實現價值傳遞的歷史契機。在“地震詩歌”熱潮中,凸現出來的是“史”的意義,而“詩”的意義則已經退居其次。對于我們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傷痛,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則讓我們在災難考驗和苦難記憶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質。關于大地震的苦難敘事讓當代詩歌寫作尋找到自我升華的機會,也讓我們從詩歌寫作和歷史敘事中看到一個人、一個民族隱秘的心靈史。這也許正是“詩史互證”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也正如謝有順所評價的那樣,“這(地震詩歌)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示:一是它向我們重申了詩歌和情感之間的永恒關系;二是詩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詩人要重新尋找詩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領域說話的有效方式。國難過后,未必就會出現詩歌繁榮的景象,但這一次的詩歌勃興,為詩歌重返現實敞開了新的可能性。”[⑦]詩歌與時代和現實的意義關系,同時也意味著詩人對時代的態度或價值取向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地震詩歌”既體現了現實對詩歌的情感激發,也體現了在長久的“個人化”寫作之后,詩歌對介入現實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為一種文學事件,“地震詩歌”現象已超越了單純的詩學(詩歌文體)理論的闡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地震詩歌”寫作也是“組織中國‘歷史’的過程,是一種對‘歷史’的寫作”。[⑧]因此,在文學史的視閾中,“地震詩歌”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啟示,即“詩”與“史”的辯證關系及其意義給我們當下詩歌寫作提供的可能性。“詩”與“史”的互證,以及其中容納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價值因素為我們正確認識詩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論的和歷史的依據。
[①] 作為一種描述和概括,“地震詩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的題材和內容而言的,尚未成為一個詩學概念或文學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關作品來源于《詩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網”及其他網絡媒體,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③]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參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頁。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詩作《我愛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詩作《贊美》。
[⑥] 參見《南方日報·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⑦] 參見《南方日報·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⑧] 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