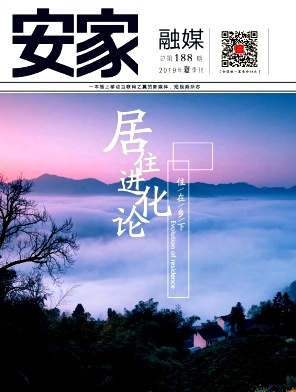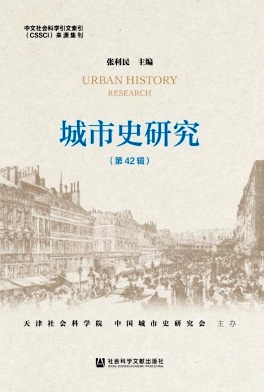對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歷史演變的探討
曾毅
論文關鍵詞: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歷史演變
論文摘要:文章探討了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歷史演變的問題,并對不同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的內容與特點進行了初步分析。
20世紀是一個充滿反思與批判色彩的世紀,一個世紀以來,語文教育的發展始終伴隨著來自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駁詰問難,其先后有文白之爭、課程目標之爭、讀經之爭、大眾語之爭、文道之爭、語文標準化考試之爭,等等。語文教育批評現象成為20世紀語文教育歷史上一道鮮明而獨特的風景線。對這種紛繁蕪雜的語文教育批評現象,它在整個20世紀的發展演變過程是怎樣的?不同階段的語文教育批評有什么樣的特點?語文教育批評與語文教育改革的關系是怎樣的?這些問題至今沒有人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在此,本文首先對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發展歷史演變問題作一些初步研究。
一
要想探討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歷史演變問題,首先應該對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歷史進行分期考察。從現有幾部關于20世紀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的研究著作看,它們對于20世紀語文教育發展歷史分期問題,往往采用社會分期法,即以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基本依據進行分期。如《中國語文教育史綱》一書在闡述現代語文教育分期時就認為:“35年(1949—1985)來,我國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建沒、‘文化大革命’、新的歷史時期的思想建設與‘改造’、‘開放’等幾個大的階段。……從語文教育的角度來看,相應有這樣幾個時期:‘語文’統一期,漢語、文學分科期,‘語文’教育曲折發展期,‘語文’改革實驗期。”[1]這種分期法顯然是將語文教育納入中國社會重大歷史事件前后發生過程的歷史階段來考察的,它雖然比較方便研究,但并不一定能夠如實地體現語文教育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特點。
從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的歷史發展來看,語文教育批評作為對語文教育問題的不滿、議論、閑話、指責和批判等為存在形態的一種教育現象和社會現象,它帶有語文教育批評者鮮明的主觀情感色彩,更多時候是受到社會政治、文化與教育等因素變革的影響,特別是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思潮變化對語文教育批評的影響尤其顯著。因此,對于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發展歷史的分期問題,我們更加注重結合不同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變化對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所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來確立劃分的標準依據,并且依照語文教育批評發展的內在邏輯初步確定其不同歷史階段。從對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的史料分析情況看,參考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政治、文化與教育的變革對語文教育批評的影響,以及語文教育批評自身發展的邏輯特點,我們可以把整個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歷史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語文教育批評的萌芽奠基期、探索發展期、曲折迷失期和興盛繁榮期。這四個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無論是批評的指導思想,還是批評的對象內容,乃至批評的作用效果都各有不同。這樣的劃分法與既有的現代語文教育史在歷史分期問題上采用社會分期法是有所差異的。
二
事物的發展總是存在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過程。20世紀的語文教育批評從產生以來,在近百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由于受到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變革的影響,它也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變化過程,并且,不同時期的發展往往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表現出特定歷史階段語文教育批評的形態與特點。
首先是語文教育批評的萌芽奠基期(1904—1919年)。隨著1904年癸卯學制及其學堂章程的頒布與實施,語文得以獨立設科,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語文教育開始誕生了。在對語文教育問題的反思與批評過程中,現代語文教育批評也開始萌芽。從批評的指導思想上看,這一時期語文教育批評基本上以“實用理性”的思想為主導。這種“實用理性”的思想秉承清末以來的“經世致用”、“中體西用”、“體用一致”等思想中“用”的精神實質,帶有非常強烈的功利色彩,“實用理性并不只是倫理實踐,它也同思辨的思維模式形式對照,……也將有用性懸為真理的標準,認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2]這種以是否“實用”、“有用”作為衡量與判斷事物價值的思想觀念,既反映了近代以來西學的傳播已經逐漸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觀念,表明國人在中西文化的鮮明對比中,開始接受西學崇真尚實的文化價值觀。同時,這種思想觀念與民國初期興起的實用主義思潮也有著相似的本質與價值取向,它們深刻地影響著這個時期的社會實踐活動。從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來看,由于清末以來新式學堂的教育重點是發展高等教育和小學階段的教育,中學階段的教育并沒有得到重視,這點從清末的癸卯學制與民初的壬子癸丑學制的結構就可以理解。因此,語文教育批評更多的是對小學階段語文教育問題的批評。從史料情況來看,人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的語文教科書、識字教學和作文教學三方面。在語文教科書批評上,主要批評其“粗糙龐雜”之弊病。黃守孚、陸費逵、梁啟超、繆文功等人分別對這時期的語文教科書存在編制粗糙,內容龐雜,脫離實際等弊病進行批評。在識字教學批評上,主要是批評識字教學的“繁難低效”,劉師培、沈頤、錢玄同、范祥善、蔡元培等人從文言漢字書寫困難,教學方法不當,教學效果差等方面對識字教學進行批評。在作文教學批評上,主要是批評其“空泛無實”的弊病,蔣維喬、錢基博、張顯光、黃炎培、吳研蘅等人批評了作文教學不切合實用,方法不科學等問題。此外還有對小學語文讀經問題的批評。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與語文教育改革密切聯系,它促進了語文教育的改革,并初步奠定了現代語文教育批評的基礎。
其次是語文教育批評的探索發展期(1920—1952年)。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與民主思想成為這一時期社會文化思潮的主導性思想。人們在思考各種問題時,已經突破了“實用理性”的認識層面,逐漸確立起“科學”與“民主”的思想觀和方法論。這正如當時的教育家王鳳喈先生所說的:“新的教育必須以科學為指導,理論要有科學的依據和證明,實踐要遵循科學的方法,結果要有科學的統計。”[3]表現在語文教育批評上,這一時期語文教育批評的指導思想已經發生變化,人們更加注重以“科學”與“民主”的眼光去審視語文教育的問題。同時,在對1922年新學制醞釀和討論過程中,人們開始比較關注中學階段的教育,特別是美國教育家孟祿對中國中學校教學方法的批評,更加激發人們重視研究中學階段的教育問題。語文教育批評的重心也從小學階段轉移到中學階段,其轉折階段的標志就是1920年發表了幾篇比較有影響的批評文章:《對現在中學國文教授的批評及建議》(種因)、《中學的國文問題》(陳啟天)、《中學國文的教授》(胡適)等。這些文章對中學語文教育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與批評,反映出語文教育批評重心發生了明顯變化。從這一時期語文教育批評的史料分析來看,它們主要涉及中學階段語文課程與教材、語文教學方法、作文教學、語文讀經、語文教師等問題的批評。具體而言,人們批評語文課程與教材“雜糅繁難”,語文教學方法“陳舊教條”,作文教學“敷衍形式”,語文讀經“古奧荒唐”,語文教師“參差散漫”等。對中學語文教育這些問題的批評,實質上就真正深入到語文教育問題最為核心之處。畢竟中學語文教育的問題歷來是語文教育問題最為復雜,最為集中,最為繁難之所在,人們對于語文教育問題的批評,往往是針對中學階段的語文教育而言的。這一時期出現了我國現代語文教育家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包括有王森然、阮真、黎錦熙、葉圣陶、朱自清等著名的語文教育家,他們對語文教育問題的批評往往建立在語文教育實驗的基礎上,因此批評非常精辟,有見地,充滿說服力。無論是從批評的對象內容上,還是從批評的方式方法上,他們都為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期的語文教育改革取得明顯進步,現代語文教育體系在這一時期得以形成。
第四是語文教育批評的興盛繁榮期。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及其文化范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1978年,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當前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的文章,對語文教育存在“少、慢、差、費”的問題進行尖銳地批評,其以科學理性的批評方式,打破了以“政治標準第一”為指導思想的批評窠臼,在語文教育界產生了十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標志著語文教育批評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開始擺脫“政治標準第一”思想的束縛,在8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不斷復興的文化背景下,“人文主義”思想逐漸成為語文教育批評的主要指導思想,陳仲梁、于漪、韓軍等人就積極以這種思想去審視語文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強烈呼喚語文教育人文精神的回歸。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呈現兩種傾向:一是對語文教育中依然存在的極“左”政治思想的批評;一是對語文教育中偽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傾向的反撥。具體而言,人們批評了語文教材的“老套無序”,語文教學方法的“呆板僵化”,文學教育的“蒼白無情”,作文教學的“偽圣乏味”,語文標準化考試的“功利專制”,語文教育理論的“紛亂模糊”,以及語文教師的“淺陋保守”等弊病。作為這一時期語文教育批評高潮的標志,1997年,《北京文學》第11期以“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為題,刊登了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王麗的《中學語文教學手記》、薛毅的《文學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由此引發了20世紀末語文教育問題大討論。期間,人們對語文教育的批評熱烈而活躍,無論就批評的廣度,還是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無法相提并論的。20世紀的語文教育批評達到了自身的興盛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語文教育批評成為推動21世紀初語文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動力之一。
三
對于20世紀中國語文教育批評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們將其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進行考察,這對于我們清楚地認識20世紀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特點與作用無疑非常重要。從不同時期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變化來看,語文教育批評明顯受到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變革的影響。就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言,可以說,每一次社會文化思潮的變革都會對語文教育批評的指導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從清末以來,“實用理性主義”思想,“科學與民主”思想,“政治標準第一”的思想和“人文主義”思想,它們無不對語文教育批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演變,正是隨著不同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革而不斷生成與變化的。此外,社會政治與教育的變革也會對語文教育批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通過結合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的變革來分析語文教育批評的歷史演變過程,既可以使我們對語文教育批評歷史分期更具有科學性與合理性,又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語文教育批評的發展歷程,并對不同歷史時期的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有清楚的認知。
總之,在社會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因素變革的影響下,20世紀中國語文教育批評是處于不斷的發展演變之中的。對其百年的歷史演變過程進行分期考察,進而明了不同時期語文教育批評的特點,探究語文教育批評背后的問題,有助于我們較好地認識20世紀的現代語文教育是怎樣發展變化過來的。這對于我們把握今天的語文教育改革無疑也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
[1]張隆華.中國語文教育史綱[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323.
[2]李澤厚.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M].北京:三聯書店,2005,325.
[3]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