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與奴性的結(jié)合——淺析《西游記》中沙僧形象
伍林光
《西游記》以其特殊的情節(jié),神奇的人物,獨(dú)特的風(fēng)格,長(zhǎng)期以來(lái)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ài)。小說(shuō)以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經(jīng)為線索,以取經(jīng)人物的活動(dòng)為中心,逐步展開(kāi)情節(jié),塑造了眾多的藝術(shù)形象。在取經(jīng)集團(tuán)中最不為人們注意的形象就是沙僧。但沙僧身上既集中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又體現(xiàn)了奴性這一國(guó)民劣根性,是封建時(shí)代普通民眾的人格寫(xiě)照。
《西游記》中,沙僧形象的美德集中表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
一“唯和是貴”
唐僧師徒四人,都是和尚,為什么單單沙僧取“和尚”之名?如張靜二先生所說(shuō):“‘和’字有調(diào)節(jié)、不爭(zhēng)、諧應(yīng)等義。”《西游記》確實(shí)讓沙和尚承擔(dān)了調(diào)和的重任,他的調(diào)和通常是對(duì)人止?fàn)帲诩喉槒摹_@樣做,最需要的是對(duì)別人的體貼、尊重、諒解。取經(jīng)人中最了解也最能體貼唐僧的,是沙僧。這一點(diǎn),第七十二回有集中描寫(xiě):正值春光明媚,前面是小橋,流水,人家。唐僧道:“平日間一望無(wú)邊無(wú)際,你們沒(méi)遠(yuǎn)沒(méi)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yīng),也讓我去化一個(gè)來(lái)。”不言而喻,這是唐僧的豪興,且情出于一種父輩對(duì)子輩的慈愛(ài)和慰撫。可孫悟空卻不同意,說(shuō):“你要吃齋,我自去化。俗語(yǔ)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豈有為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豬八戒也不贊成,說(shuō):“古書(shū)云:‘有事弟子服其勞。’等我老豬去。”唯沙和尚在旁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情如此,不必違拗。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lái),他也不吃。”一個(gè)是“有心栽花花不發(fā)”,一個(gè)是“無(wú)意種柳柳成蔭”。三人跟隨唐僧十四年,行程十萬(wàn)八千里,好我行我素的孫悟空固然常被咒念緊箍,喜賣乖弄巧的豬八戒也常遭厲顏斥責(zé),唯默而侍之的沙和尚卻始終未落一辭,其深層原因恐怕亦在于此吧!取經(jīng)人中最尊重也最愛(ài)護(hù)孫悟空的,也是沙僧。他知道孫悟空的橫掃妖魔是為了保護(hù)唐僧與取得真經(jīng),所以,他總是想方設(shè)法協(xié)調(diào)好孫悟空和唐僧的關(guān)系。比如,路過(guò)號(hào)山,紅孩兒兩次變作紅云,想捉唐僧。孫悟空一會(huì)兒將唐僧推下馬,說(shuō)是妖怪來(lái)了,一會(huì)兒又扶唐僧上馬,說(shuō)是過(guò)路妖怪。唐僧大怒,認(rèn)為孫悟空在捉弄人,“哏哏的,要念“緊箍?jī)褐洹保褪嵌嗵潯吧成鄤瘛狈搅T。他對(duì)孫悟空的智慧和神勇膺服不已,但對(duì)孫悟空的“暴躁”也常施之以柔克剛。比如,“鎮(zhèn)海寺心猿知怪”,孫悟空中了地涌夫人的分身計(jì),回來(lái)不見(jiàn)了唐僧,竟將一腔怒火發(fā)到豬八戒與沙和尚身上: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lái)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沙僧近前跪下道:“兄長(zhǎng),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gè),也不去救師父,徑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gè),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zhǎng)說(shuō)那里話!無(wú)我兩個(gè),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shuí)與看顧?寧學(xué)管鮑分金,休仿孫龐斗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zhǎng)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一席話說(shuō)得孫悟空心悅誠(chéng)服。這哪里是“情求”,分明是“理喻”!句句說(shuō)在點(diǎn)子上,而且又是那么有理,有利,有節(jié)。好一個(gè)柔中有剛、言必中的的沙和尚!取經(jīng)人中最理解也最體諒豬八戒的,還是沙僧。他知道“遠(yuǎn)路沒(méi)輕擔(dān)”,挑擔(dān)是很辛苦的。因而唐僧教他挑一肩,他固然挑一肩,豬八戒讓他挑一肩,他也愉快地接過(guò)擔(dān)子,這就從行動(dòng)上團(tuán)結(jié)了好耍小心眼的豬八戒。他對(duì)豬八戒的動(dòng)輒鬧“散伙”壓根兒是不贊成的,卻不像孫悟空那樣一聽(tīng)就惱火,開(kāi)口便罵,舉棒想打,以至加深兄弟間的不睦。他總是抓住豬八戒愚笨呆直而又自尊心很強(qiáng)這一特點(diǎn),把自己也擺進(jìn)去,予以款款溫存地勸說(shuō)。“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不要惹大哥熱擦。且自換肩磨擔(dān),終須有日成功也。”孫悟空聽(tīng)了固然感到舒服,豬八戒聽(tīng)了也比較容易接受,從而消弭了可能引起的糾葛。
二“唯正是尚”
沙僧是個(gè)真正的老實(shí)人。取經(jīng)路上,他對(duì)自己的工作盡職盡責(zé),踏踏實(shí)實(shí),不計(jì)個(gè)人得失,沒(méi)有非分之想,不象悟空那樣好名,也不象八戒那樣貪心。沙僧最直接的責(zé)任是照顧唐僧的起居生活,如“登山牽馬”之類,這些瑣碎平凡之事,他都處理得有條不紊。遇到妖魔鬼怪時(shí),他一般都是看守行李、馬匹,但一旦直接參加戰(zhàn)斗,就從不象八戒那樣臨陣脫逃。“四圣試禪心”時(shí),唐僧要他留下招贅,他表示“寧死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干此欺心之事”。沙僧是個(gè)十足的善良人。唐僧雖然也十分善良,但他的善良多從佛教的教條出發(fā),難免是非不分,人妖不辨,總給人做作的感覺(jué)。而沙僧的善良,卻是發(fā)自性情的真情實(shí)感。八戒貪色,做了一夜“繃巴吊拷女婿”,“沙僧見(jiàn)了,老大不忍,放了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悟空被三昧真火燒得火氣攻心,是沙僧跳進(jìn)水中救出悟空;見(jiàn)到悟空“渾身上下冷如冰”,他便不由得“滿眼垂淚”,痛哭失聲。唐僧被妖怪變成了猛虎,又受到悟空的“揭挑”,是沙僧“近前跪下”,懇請(qǐng)悟空“萬(wàn)望救他一救”。這種出自內(nèi)心的或者說(shuō)是潛意識(shí)的善良,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總之,無(wú)論老實(shí),還是善良,都是追求正義的結(jié)果。這也說(shuō)明,他的調(diào)和不是無(wú)原則的“和事”。
三“唯法是求”
《西游記》寫(xiě)西行求法,事關(guān)“法輪回輪,皇圖永固”,象征著一項(xiàng)了不起的事業(yè)。一遇重大困難,豬八戒就想回高老莊,“回爐做女婿”。孫悟空也不是沒(méi)有回花果山“稱王道寡,耍子兒去”的念頭,只因頭上戴著緊箍咒,“恐本洞小妖見(jiàn)笑”未走罷了。唐僧雖無(wú)半途而廢之念,但亦常作鄉(xiāng)關(guān)之思。心不旁騖,篤而行之,寧?kù)o淡泊,矢志西行求法者唯沙僧一人而已。孫悟空一路煉魔降怪,圖名不圖利。豬八戒一路所作所為,圖利不圖名。縱然是圣僧唐三藏,其所以矢志西行,亦“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bào)國(guó)耳。既不為名,又不為利,心無(wú)二念,但求正果者唯沙僧一人而已。”沙僧還有個(gè)突出特點(diǎn)就是默默奉獻(xiàn)。在取經(jīng)途中,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都在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兒,像八戒動(dòng)輒在行者已打死的妖怪身上還筑上一鈀,嘴里大叫:“此是老豬之功!”(第70回)這種事兒沙僧是不會(huì)干的。面對(duì)孫悟空的天馬行空,沙和尚雖然也曾有“嫉妒之意”,卻能迅即自我克服,因而不僅始終沒(méi)有去干擾孫悟空的建功立業(yè),反倒在全力助成。沙僧一般在兩個(gè)師兄都去降妖時(shí),默默擔(dān)負(fù)起保護(hù)師父的重任。當(dāng)妖怪來(lái)襲,自己明知本領(lǐng)低微,也要挺身而上。這就使他不失為一個(gè)正派的人、高尚的人、有益于取經(jīng)群體的人。
如果沙僧僅僅只有美德,還談不上一個(gè)成功的形象。《西游記》的可貴,在真實(shí)地展示人物性格中的缺點(diǎn),那就是“奴性”意識(shí)。“和事佬”的身份,使他不能像孫悟空一樣,敢說(shuō)敢干,充分表達(dá)自己的喜怒哀樂(lè);“苦行僧”意識(shí),使他不能同豬八戒一樣,無(wú)所顧忌地追求世俗的七情六欲。總之,是贖罪意識(shí)與奴仆身份決定了他的性格缺陷。
沙僧本來(lái)是在天宮穩(wěn)做卷簾大將的(他的職責(zé)是“扶侍鸞輿”,是玉帝手下的侍臣,實(shí)際上就是奴仆),只因失手打碎玻璃盞這個(gè)偶然性的失誤,便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yùn)。因此,觀音菩薩勸他跟取經(jīng)人當(dāng)個(gè)徒弟,他當(dāng)即表示“愿皈正果”。他一心一意西天取經(jīng),希望以此贖清自己打碎玻璃盞的罪過(guò)。第40回,紅孩兒捉去了唐僧,八戒和悟空提出散伙的話,沙僧一聽(tīng),便“打了一個(gè)失驚,渾身麻木”,說(shuō)道:“師兄,你都說(shuō)的是那里話。我等因?yàn)榍吧凶铮忻捎^世音菩薩勸化,與我們摩頂受戒,改換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護(hù)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jīng),將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說(shuō)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lái),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壞了自己的德行,惹人恥笑,說(shuō)我們有始無(wú)終也!”。可見(jiàn),贖罪意識(shí)已經(jīng)深入到了沙僧的骨髓,也導(dǎo)致他依順隨和,忍辱負(fù)重。悟空說(shuō)他是“好人”,八戒背后譏他“面弱”,實(shí)際上都是說(shuō)他太少“自我”,太少“個(gè)性”。
沙僧的馴順?lè)暮艽蟪潭壬先Q于其奴仆身份。《西游記》中的沙僧名為“卷簾大將”,但那只不過(guò)是皇家為了顯示自己的威風(fēng)。他雖然也曾自我夸耀說(shuō):“南天門里我為尊,靈霄殿前吾稱上”,“往來(lái)護(hù)駕我當(dāng)先,出入隨朝予在上”,但身份卻相當(dāng)?shù)臀ⅲ瑢?shí)際上只是奴仆。比起悟空的大鬧天宮和八戒的調(diào)戲嫦娥,沙僧失手打碎玻璃盞并不算什么罪過(guò),可他受的苦難卻最多。但他卻連一點(diǎn)抗?fàn)幍哪铑^也沒(méi)有,只是默默忍受。在《西游記》中描寫(xiě)悟空,最常用的字眼是“毛臉雷公嘴”;描寫(xiě)八戒,最常用的字眼是“長(zhǎng)嘴大耳朵”,都準(zhǔn)確地揭示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唯有描寫(xiě)沙僧,最常用的字眼卻是“晦氣色臉的和尚(師父)”。當(dāng)我們明白了沙僧的奴仆身份,我們就會(huì)明白作者的這種描寫(xiě),是多么準(zhǔn)確地把握了這個(gè)人物的身份、地位所帶來(lái)的最獨(dú)特的外貌特征。晦氣者,倒霉也。沙僧既是奴仆身份,平時(shí)當(dāng)然飽受窩囊之氣。特別是他的職責(zé)就是侍奉玉皇大帝,常言說(shuō)“伴君如伴虎”,他敢有一絲一毫的松懈嗎?長(zhǎng)此以往,他那張臉便不能不變成“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他的馴順?lè)膫€(gè)性也就在這樣的生活過(guò)程中被體現(xiàn),成為一個(gè)奴性人格的形象。
總之,沙僧形象既體現(xiàn)了奴隸文化的本質(zhì)特征,又代表了農(nóng)耕文明背景下普通民眾的基本性格特征。他的善良老實(shí)、埋頭苦干、任勞任怨、默默奉獻(xiàn),都表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進(jìn)行任何一項(xiàng)偉大的事業(yè),這些美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沙僧身上這些“美德”,又都和他循規(guī)蹈矩、馴順?lè)摹⒚髡鼙I淼呐圆豢煞指睿瑴喨灰惑w,而奴性又是妨礙我們民族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根本大敵,是我們事業(yè)成功的大敵。因此,表現(xiàn)在沙僧身上的“美德”,只有與強(qiáng)健的個(gè)性和富于抗?fàn)幣c進(jìn)取的精神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只有“訴之自身意志”,才有可能煥發(fā)出真正炫目的光輝。
濟(jì)刑法.jpg)
.jpg)


展教育研究.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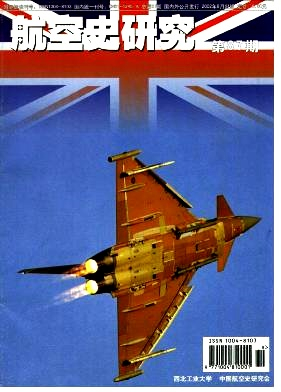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