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語與李贄思想的矛盾
張?zhí)煨?/span>
論文關(guān)鍵詞:《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 評點; 思想矛盾; 評者; 李贄; 葉晝
論文摘要:本文從思想印證入手認為《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評語流露的思想傾向與李贄的思想有明顯的抵牾,卻與葉晝評點的《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北西廂記》中的一些思想風格榫合,所以認為《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是葉晝偽托可信。本文的討論以及運用思想印證的方法對于考察署名李卓吾的小說戲曲評點和推動葉晝的相關(guān)研究都有一定的意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以下簡稱“李本”)是現(xiàn)存較早的《西游記》評點本,關(guān)于它的評點者,學(xué)術(shù)界一般根據(jù)明末清初人盛于斯《休庵影語》和錢希言《戲瑕》的記載認為是葉晝偽托。但由于缺少確切的文獻記載,在具體談到評者問題時,學(xué)術(shù)界多采取較謹慎的態(tài)度,如譚帆先生說:“此書之評點者一般認為是葉晝。”①(P.187)袁世碩先生在為《李卓吾、黃周星評西游記》寫的《前言》中說:“《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是否出自李卓吾筆下,文獻無證,今世學(xué)者多依錢希言《戲瑕》所說,疑為葉晝之的偽托。”②(P.15) 但伍丁先生為該書作的《整理說明》中又說:“李卓吾的批評,有人揭露系葉晝所托。但就整個批評來看,除涉及作品本身的批評外,更多的具有思想史價值,如第一回回后總批所云,可見系出自李卓吾之手。李卓吾的批評目的,主要的是借《西游記》小說宣揚泰州學(xué)派的學(xué)說……”②(P.24) 伍先生的話給筆者很多啟示,既然現(xiàn)存文獻無法直接證明李本的評者,那么能否從李本評語所流露的思想風格入手探討其評者呢?
一、李本評語與李贄思想的矛盾
翻檢李本批語,可以發(fā)現(xiàn),李本評語比同署名為李卓吾的容與堂刊本(以下簡稱“容本《水滸傳》”)和袁無涯刊本《水滸傳》的評語簡單。從文藝理論上看,李本評語除了對小說虛構(gòu)(幻)的揭示頗有價值外,成就與袁本,尤其與容本《水滸傳》的評點有一定差距。但是李本評者用較多的筆墨澆胸中之壘塊,這對我們考察李本評者的意趣神色留下了較豐富的材料。概括起來,可以發(fā)現(xiàn)李本評者與李贄的思想志趣相沖突最明顯處有以下四個方面:
1.蔑視女性總體上講,明代“四大奇書”女性角色的刻畫帶有很多異化成分,并沒能得到較公正的描述。就《西游記》文本而言,除了已剔除人欲的女菩薩、女仙以外,與唐僧師徒糾纏的女性幾乎皆是食欲、情欲或色欲之化身,但這些是從《西游記》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得以體現(xiàn)的。李本評者認為《西游記》中“尚多隱語”,評點之目的是“今特一一拈出,讀者須自領(lǐng)略”(第十四回后總批)。所以他的評點多是就事生發(fā)、不囿文本、傾吐胸中壘塊,對女性的評論尤其如此。如他認為黃袍怪不是什么妖魔,百花羞反倒是妖魔:“那怪尚不是魔王,這百花羞真是個大魔王!”(第二十九回總評)為何認為公主是魔王?推測起來,無非是因為“一個百花羞,便夠斷送此魔矣”(第二十九回總評),因為黃袍怪的失敗尋根求源是女人造成的。這顯然是牽強之辭,明顯有對女性的偏見,大抵他是看不起要強或有主見的女性的。因而該回他又評道:“到底是婦人所制。還是妖魔狠?還是婦人狠?”他還對妒婦進行謾罵:“妖魔是妒婦,妒婦是妖魔。”(第五十九回評語)可以說他對女性的成見早就溢出文本所提供的內(nèi)容,五十九回“大圣長嘆一聲道:‘好厲害婦人!’”他批道:“那婦人不厲害。”不僅如此,他往往借評點直接詈罵女性是妖魔,“既是女人矣,緣何不是怪物妖精?”(第五十四回評語)“非干妖魔癡事,還是女人更妖魔耳”(第七十回評語),“妖精多變婦人,婦人多戀和尚,何也?作者亦自有意。只為妖精就是婦人,婦人就是妖精。妖精婦人,婦人妖精,定偷和尚故也”(第八十二回總評),“人言蝎子毒,我道婦人更毒。或問:何也?曰:若是蝎子毒似婦人,他不來假婦人名色矣。為之絕倒。或問:蝎子毒矣,乃化婦人,何也?答曰:似婦人,尤毒耳。”(第五十五回總評)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看來世上只有婦人毒”(第五十五回評語)。綜上所言,李本評語流露的女性觀比《西游記》文本對女性的異化走得更遠,說李本評者思想中有蔑視女性之傾向并非過分之辭。
李贄的婦女觀學(xué)術(shù)界多有探討,此不贅論,概括起來主要有:李贄主張男女平等,他一生還踐履該主張;在婦女的社會角色上,他認為婦女同樣有參政、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他還認為婦女可以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③李贄的婦女觀雖然有時流露出矛盾,但瑕不掩瑜,他的婦女觀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度。這些與李本評者蔑視女性的思想傾向相比可謂大相徑庭。除了在整體上有鄙視婦女的傾向外,李本評者還認為婦女見識低下,“婦人見識,大足誤事”(第三十回評語)。而李贄認為婦女的見識并不在男子之下,“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④(P.58-59) 另外,在看待女性的情欲問題上,李本評者有明顯的禁欲傾向,如七十一回,紫陽真人送給朱紫國娘娘一件他人觸不得、自我脫不下的霞衣,他評道:“安得張真人棕衣,凡婦人都與她一件也?”顯然他主張要禁錮住婦女的情欲、把持住婦女的貞操,這種主張與李贄的婦女觀是矛盾的。李贄是晚明人情物欲的積極倡導(dǎo)者,認為“蓋聲色之來,發(fā)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④(P.132)因而卓文君主動出擊、追求自由婚姻不是什么“淫奔”,而是與其“徒失佳偶,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⑤(P.626)。總之,李本評語流露的婦女觀與李贄的婦女觀相較,有保守與激進、落后與進步之別。
2.鄙視和尚《西游記》作者對出家人既有贊美也有諷刺,其中諷刺的成份尤令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李本評者能較敏銳地點出《西游記》中對佛界凈土的刺謔成分,如第六十六回“佛祖道:‘鐃破,還我金來。’”他評道:“佛祖也只要金。”該回總評又強調(diào):“笑和尚,只是要金子。不然,便做個哭和尚了。”第九十八回阿儺、伽葉向唐僧索要人事,他評道:“此起(處)也少不(了)錢。”這樣的評點深諳《西游記》諷謔的趣味。但綜合而言,他對和尚尤其是當時的和尚深為鄙視。首先,他認為當時的和尚不學(xué)無術(shù)。第四十回悟空提醒唐僧注意《多心經(jīng)》的要旨,他連用兩處“著眼”提醒讀者留意,該回總評云:“行者說《心經(jīng)》處,大是可思,不若今之講師,記得些子舊講說,便出來做買賣也。今之講經(jīng)和尚,既不及那猴子,又要弄這猴子怎的?”另如,他認為當時的和尚該殺,因為當時“滅法”的都是和尚。可見,李本評者對其時的和尚修為很不滿,因而罵當時和尚皆是無用之輩,連做藥引子都不配。其次,他對當時和尚、道士的行為也頗有微詞。如“原來道士都是畜生”(第四十六回評語),“如今真道士也沒有,假和尚太多”(第四十四回評語),“如今和尚,那個不會弄嘴?”“如今和尚的嘴臉更多”(第七十四回評語),“可見和尚好人少”(第九十六回評語)。正因為他對婦女與和尚成見頗深,所以有時把婦女與和尚放在一起揶揄,如第二十九回,百花羞替唐僧向黃袍怪求情,他評道:“老婆替和尚討分上,可疑!可疑!”第七十回,悟空關(guān)上門與朱紫國娘娘說話,他批道:“一個娘娘,一個和尚,關(guān)在門里,甚是可疑。”這類評點流于低級庸俗,遂墮惡趣。
李贄的確鄙視過出家人,他回憶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曾說:“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xué)先生則尤惡。”⑥(P.1604) 但是李贄四十至五十歲時思想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一是四十歲左右接受了王陽明心學(xué),二是五十歲以后佛家思想日趨濃厚,“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朋友勸誨,翻閱貝經(jīng),幸于生死之原窺見斑點。”佛學(xué)對五十歲以后李贄的影響,他自己歸結(jié)為“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④(P.347) 。李贄晚歲,“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④(P.185) 即尋求身心的自由,遂落發(fā)為僧,遁入空門。李贄五十四歲以前始于寒窗苦讀,既而糊口四方,后又奔波仕途,是不可能有充裕的時間評點《西游記》的。如果李本評點出自李贄之手,也應(yīng)是他五十四歲棄官專事著述之后,他自言:“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自五十六歲以至今年七十四歲,日日如是而已。”④(P.285)這一點還可以從1592年袁中道兄弟去武昌見到他逐字批點《水滸傳》和他同年寫給焦弱侯的信中提到自己正在批點《水滸傳》、《西廂記》和《琵琶記》得到佐證。⑦所以,對于一個釋家思想日趨濃郁、托身佛門之人來說,借小說評點對出家和尚大發(fā)鄙視的言論是難入情理的;再者,李贄五十歲后結(jié)交了許多僧人,包括任姚安知府時與當?shù)孛懻摲鸱ǎ腚u足山閱讀佛教典藏,入住麻城維摩庵、芝佛院,寓居西山極樂寺、南京永慶寺、商城法眼寺等。從李贄的著作中看,不少和尚如定林、心如、真可、深有、無念、黃安二上人等都是他的至交,另外在武昌、龍湖時期與他同吃住為他抄書的常志、懷林也是和尚;復(fù)次,李贄別署甚多,其中不乏禿翁、和尚、李上人之類的佛家稱呼。因而,我們可以說李本評者對和尚蔑視的態(tài)度與李贄的思想及行為若水火之難容。
3.非議王門在李本評語中,有兩處帶有鮮明傾向性的評論很值得我們注意。第一處在第三回:“此時七大圣自作自為,自稱自號,耍樂一日,各散訖”。李本評道:“何圣之多也,極像講道學(xué)先生,人人以圣自居,卻不令人笑殺。”第二處在第四十一回,悟空向紅孩兒解釋曾與牛魔王等七位結(jié)為兄弟,號稱七大圣,李本評云:“何圣人之多也?極像講良知者,一入講堂,便稱大圣人矣!”將這兩條評語聯(lián)系起來可以看出,“講良知者”指王門,“人人以圣自居”就是王門“滿街人都是圣人”⑥(P.116) 、“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⑧的主張。李本評者借評點對王門心學(xué)予以抨擊,可以說這樣的言論與李贄的思想、行徑尤為抵觸。李贄“其學(xué)不守繩墨,出入儒佛之間,而大旨淵于姚江”⑨(P.61),四十歲時接受王陽明心學(xué),“不幸年逋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崛強,不得不信之矣。”⑥(P.1604) 李贄師出王門而自有傳承:“心齋之子?xùn)|崖公,贄之師。”⑤(P.426)東崖公就是王艮之子王襞,所以學(xué)術(shù)界多把李贄看作王門心學(xué)中影響最大學(xué)派泰州學(xué)派的殿軍。而且,李贄還完全繼承“滿街都是圣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主張而又有所發(fā)展,如云:“圣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為圣。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圣人。’佛氏亦曰:‘即心即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即皆圣人也,是以圣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④(P.30),“堯舜與途人一,圣人與凡人一。”⑩(P.361)不僅如此,李贄對王門人物推崇備至,“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心齋之后為徐波石,為顏山農(nóng)。……蓋心齋真英雄,故其門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為趙大洲,大洲之后為鄧豁渠;山農(nóng)之后為羅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后為錢懷蘇,為程后臺:一代高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尸,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④(P.80)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本中這兩處對王門心學(xué)的批判,如果出自李贄,那他就是在非議師門。非議師門即便今天也為人不恥,又怎能是推崇師門、思想又繼承了師門的李贄所為呢!
4.揶揄秀才李本《西游記》評者的思想還有一種傾向,即他認為秀才迂腐無用、見識低下,如“傅奕大是秀才氣”(第十一回評語),“常笑傅奕執(zhí)著道理,以秀才見識,欲判斷天下事理,不太愚癡乎?”(第十一回總評)在第五十六回有評語云:“緣何和尚倒有秀才氣?腐極了!腐極了!”可見他認為秀才有種迂腐之氣。他還認為秀才是無用之輩,“天下只有白衣秀士沒有用了!我道秀士中,竟蛇多龍少”(第十七回評語),“唐僧化虎,白馬變龍,都是文心極靈妙、文筆極奇極幻處。做舉子業(yè)的秀才,如何有此?有此,亦為龍虎矣”(第三十回總評)。所以他揶揄當時的秀才是胸無點墨之輩,如第七十八回,“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他評道:“何異今日秀才解書?” 他還借紅孩兒對老書生進行嘲弄,“修行了三百年,還是一個孩兒。此子最藏年紀,極好去考童生,省得削須曬額”(第四十回總評)。值得一提還有一處,“一部《西游記》,獨此回為第一義矣。此回內(nèi)說斯文肚里空空處,真是活佛出世,方能說此妙語。今日這班做舉子業(yè)的斯文,不識一瞎字,真正可憐!不知是何緣故,卻被豬八戒、沙和尚看出破綻來也。大羞!大羞!”(第九十三回總評)在李本評者看來“斯文,肚里空空”可以看作當時秀才的傳神寫照。李贄七歲隨父讀書,至二十六歲中舉人,其間歷經(jīng)十九年的寒窗苦讀,對于讀書人之甘苦應(yīng)有深刻的體會,所以現(xiàn)存李贄的著述中雖譏諷了較多人物,但鮮有這樣對秀才極盡揶揄譏諷之能事的言論。另外,從事科舉業(yè)在李贄的心目中地位還是較神圣的,他在《童心說》中說:“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為今之舉子業(yè),大賢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④(P.98)所以,雖然“百無一用是書生”之說古今有之,但于情于理上李贄是不會把從事舉子業(yè)的秀才作為一個群體一并罵倒的。
當然,一個人的思想并非一潭止水,不同的人生階段、時勢境遇都會給其思想帶來復(fù)雜的變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上文所稱引李贄的《焚書》、《藏書》、《陽明先生年譜后語》、《道古錄》等書中的言論所代表的是他棄官以后的思想,換言之,正是他專事著述(包括評點小說戲曲)時期的思想。所以綜合起來,我們很自然就能得出一個結(jié)論:《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語不是出于李贄之手。
二、李本評語的評者
據(jù)盛于斯《休庵影語》和錢希言在《戲瑕》中說《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語系葉晝偽托。錢希言說:“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為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11)(P.360) 周亮工也說“跡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后名梁無知,謂梁溪無人知之也”,“后誤納一麗質(zhì),為其夫毆死”(11)(P.377)。這幾位都生活于明末清初,是距離葉晝時間較近的人。這些材料向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葉晝?yōu)槿擞型媸啦还А⒙市远鵀榈奶攸c。申言之,由于率性,即便他評書作偽時,往往也會情不自禁的沖破理智的束縛而流露出自己內(nèi)在的意趣神色來。當前,學(xué)術(shù)界基本同意出自葉晝之手的小說戲曲評點有以下兩部:容本《水滸傳》(12)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13)。另外,黃霖先生論證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也出自葉晝之手。所以,如果我們將《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語與這幾部評點的評語相互印證,如果它們在意趣神色上能多有榫合,則錢希言等記載李本評語系葉晝偽托應(yīng)是可信的。實際上,經(jīng)過比對,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有如下幾方面的明顯相合之處: 1.嘲弄秀才、抨擊官吏李本《西游記》對秀才的揶揄已見上述。該評本也喜好借評點抨擊當時的官吏,如“如今做官的倒要錢”(第十五回評語),第三十九回他借“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就的文官”而感嘆云:“那一國不如此?”“寄語天下太守,也要知他百姓死活方好。”(第八十七回總評)
葉晝在容本《水滸傳》中對秀才頗多微詞,如第十九回林沖欲火并王倫,“林沖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有文學(xué),怎做得山寨之主!’”身為秀才的金圣嘆十分同情王倫,在林沖的罵辭旁批道:“即不落第又奈何?”“即有文學(xué)又奈何?”“秀才可憐,睡在夢里。”但葉晝批云:“知己”、“罵得好。”在該回回末總評又說:“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妒能,安得林教頭一一殺之也。”在第二十回回末總評還說:“嘗思天下無用可厭之物,第一是秀才了。”至于葉晝在容本《水滸傳》中對官吏的抨擊之言尤多,如“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第十八回總評),“你道知縣相公不是強盜么?”(第二十二回總評)“可恨倒埋沒了武松,今之做官的都如此”(第二十七回眉批),“如今戴紗帽的,一失官職,性命一并失了,視阮小七何如?”(第一百回眉批)等等。
葉晝對秀才的成見在評點《三國志通俗演義》也有鮮明體現(xiàn),如第二十八回借趙云訴說尋找劉備的經(jīng)歷批評秀才:“英雄行動如此,你道似世上那一班秀才否?”實則是借趙云有主見、擇主而事來批評秀才們?nèi)鄙僖娮R。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zhàn)張昭:“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夸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yīng)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葉晝認為這是對當時秀才無用的定評:“說盡今日秀才病痛。”但這些都不如第七十三回、第九十五回、第一百九回、第一百十回的總評中說的直接明了,如“妙哉!夏侯存罵滿寵曰:‘汝是秀才之言。’可見天下極無用的是秀才,真正漢子每每恥言之。何今之秀才不自以為恥,乃反沾沾自得也,真秀才乎?真秀才乎?可憐,可憐!”(第七十三回總評)葉晝對當時官吏予以抨擊亦是慣常作風,如“今之上司妝威做勢索取下司者,亦往往有之,安得翼德柳條著實打他二百也”(第二回總評),“孟德雖國賊,猶然知民為邦本,不害禾稼。固知興王定霸者,即假仁仗義,亦須以民為念,方干得些少事業(yè)。何故今之為民父母、代天子稱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也?卒之男盜女娼也,又何尤焉!”(第三十一回總評)
由上言之,同署名李卓吾評點的《西游記》、容本《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對當時秀才、官吏的嘲弄抨擊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而這類看法如果發(fā)生在視舉子業(yè)較神圣、有過較長寒窗生涯、出過仕的李贄的身上是難入情理的,所以黃霖先生在論證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出自葉晝之手時說:“葉晝對秀才、對做官的這類看法給人的印象十分深刻,這與他一生潦倒的生活經(jīng)歷是合拍的,而在中過舉、做過官的李贄的文章中是不易見到這類嬉笑怒罵的。”(14)
2.保守的婦女觀李本《西游記》評語中對婦女的蔑視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葉晝評點容本《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李本《西游記》評語中流露的婦女觀是一致的。葉晝對《水滸傳》中反面女性人物如潘金蓮、潘巧云、盧俊義妻賈氏的評點自另當別論,因為這些女性在文本中反面的傾向性就已十分鮮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感覺出葉晝保守落后的女性觀,如他在第三十四回總評云:“國有國賊、家有賊婦,都貽禍不淺。只如青州府失了秦明、黃信、花榮三個良將,皆劉高一人誤事,而劉高又妻子誤也。真有意為天下者,先從妻子處整頓一番,何如?”顯然葉晝把青州的一番爭斗都歸根在女人身上,有意為天下者也要先從整頓女人著手,這是明顯的女人禍水之論;另如“好女不看燈,如何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都去看燈?”(第六十六回眉批)所謂“好女不看燈”無非是忌看燈時男女混雜,有礙男女之大防,可見葉晝還是希望通過禁錮女子來把持住男女之防的;葉晝多用“婦人之仁”評論見識平庸者,分別見于第五十一回總評、第七十四回夾批、第九十六回眉批,雖不無諧戲成分,但亦有輕視女性之意。
葉晝保守落后的女性觀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評點中比在容本《水滸傳》的評點中體現(xiàn)得更淋漓,除了能全節(jié)而死的女性如徐庶的母親、糜夫人、夏侯令女、王陵的母親等受到他的褒獎外,可以說他對女性極盡詆毀嘲弄之能事。如:“妙哉司徒,用此將軍;妙哉貂蟬,用此兵器;何憂卓賊、布奴不死其手也耶?雖然,這等將軍,這般兵器,人人避不得也,家家有埋伏也”(第八回評語),“今人但知畏十八路諸侯,豈知畏女子哉!真?zhèn)€是:至險伏于至順,至剛伏于至柔也。世上有幾人悟此哉!世上有幾人悟此哉!”(第八回總評)這是在宣稱女性可怖、女色傷人;如“誤天下事者婦人也”(第二回評語),“從來聽婦人之言者,再無不壞事者,不獨呂布也。凡聽婦人之言者,請看呂布這樣子,何如?”(第十九回總評)“天下婦人無不如蔡夫人者,今蔡夫人既得曹操殺之,我心甚快也。安得曹操再出,殺盡今日之所謂蔡夫人者,我心更快也。”(第四十一回總評)這是女人惑人、女人禍根,幾欲殺盡之論;如第二十八回“關(guān)公乃下馬至于前稟問二嫂”,葉晝評道:“此事何必謀之婦人,先生豈講學(xué)人,乃腐氣逼人如此耶?”這是說婦人見識低下,不足與謀,也是蔑視女性之意。
3.厭棄道學(xué)在容本《水滸傳》的評語中,葉晝認為矯模作樣、表里不一的言行都是假道學(xué):“假道學(xué)之所以可惡可恨可殺可剮,正為忒似圣人模樣耳”(第六回回末總評),“若瞻前顧后,算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xué)門風去也?”(第五回回末總評)葉晝對假道學(xué)的抨擊是建立在他對道學(xué)厭棄的基礎(chǔ)上的,如“王矮虎還是個性之的圣人,實是好色,卻不遮掩……若是道學(xué)先生,便有無數(shù)藏頭蓋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第四十八回回末總評),“梁山泊買市十日,我道勝如道學(xué)先生講十年道學(xué),何也?以其實有益于人耳!”(第八十二回總評)可見在他看來,道學(xué)虛假不真、于世沒有實用價值。
對道學(xué)大抒唾棄之辭是葉晝《三國志通俗演義》評點的重要特色之一。與評點《水滸傳》一樣,他認為道學(xué)毋庸、虛偽做作,如“可笑彼曹無用道學(xué),口內(nèi)說得極好聽,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真?zhèn)危唤z不肯放過;一到利害之際,又倉皇失措,如木偶人矣,不知平時許多理學(xué)都往那里去了,真可一大笑也”(第十七回總評),“盜馬反勝似講道學(xué)也,何如何如”(第二十八回評語),“孫郎不信于吉,亦是英雄之見。不比今之道學(xué)先生,口攻異端……即有自立者,老婆做主,不怕他不從也。”(第二十九回總評)葉晝這類對道學(xué)虛假、無用的評論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評語中還有很多,此不贅引。不少論者把容本《水滸傳》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的評語中對道學(xué)的抨擊作為證明它們是出于李贄之手的重要證據(jù)。這是值得分析的,其一,厭棄道學(xué)的虛假、倡絕假存真是晚明思想界的重要特點之一,李贄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其二,葉晝偽托李贄評書,刻畫模仿,幾以假亂真,他受李贄及其思想濃郁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他極可能熟讀過李贄的著述。
李本《西游記》的評語也有較明顯的厭惡道學(xué)的傾向。首先,該本評者認為之乎者也的道理說教都是講道學(xué),“孫行者著實講道學(xué)”(第三十一回評語);其次,他同樣厭棄假道學(xué),如“天下無一事無假,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馬,都是假到矣,又何怪乎道學(xué)之假也?”(第五十七回總評)另外,他還抨擊講道學(xué)者外表堂皇,實則表里不一、內(nèi)心險惡,如“有文殊、普賢、如來,便有青獅、白象、大鵬,即道學(xué)先生人心、道心之說也。勿看遠了”(第七十七回總評)。
當然,以上三個方面只是李本《西游記》與葉晝評點《水滸傳》、《三國志》在思想傾向上最突出的榫合而已,其它如市井細民的口吻風格、苦于懷才不遇、小人撥難、兄弟反目等牢騷也很合拍。另外,這三個評本中一些慣用的評語如“著眼”、“具眼”、“好妝點”等重疊性評語也是特色獨具。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說:錢希言等記載《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語出自葉晝之手是可信的。
三、余論
自明末迄今,對于署名為李贄的小說戲曲評點本孰真孰假一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確切文獻記載的匱乏無疑是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本文從評語流露的思想印證入手,雖然主要探討的是《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的評者問題,但對于進一步認識容本《水滸傳》和《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的評者問題也不無裨益。另外,至今流傳的明代署名李贄的小說戲曲評本有近二十種,也許從評語的思想風格著手是我們探討其評者問題的較好途徑之一。再者,葉晝不但是我國古代一位名副其實的小說批評家,而且就現(xiàn)存的小說戲曲評點本來看,他無疑是金圣嘆之前最有成就的小說戲曲批評家,這恐怕是這位作偽者生前所始料不及的。但他一生窮困潦倒,聲名不彰,用“雪泥鴻爪”來形容其所留下的生平事跡似很貼切,所以至今我們?nèi)鄙賹λ^多的了解。通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對葉晝的思想作風如敵視女性、鄙視秀才、厭棄道學(xué)等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這類思想作風給他的小說戲曲評點烙下了鮮明的印記,這說明關(guān)于葉晝還是有一些值得進一步了解的內(nèi)容的。
①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1。
②李卓吾、黃周星評西游記[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6。
③可參考:陳桂炳.李贄的婦女觀及其實踐[J].南通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哲社版),2001,(3):87-91;林慶.李贄婦女觀述評[J].大理學(xué)院學(xué)報,2003,(2):40-42。
④李贄.焚書·續(xù)焚書[M].長沙:岳麓書社,1990。
⑤李贄.續(xù)藏書[M].臺北:臺灣學(xué)生書局,1974。
⑥王陽明.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⑦袁中道.珂雪齋集·游居柿錄[M].錢伯城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5;李贄.與焦弱侯書[A],焚書·續(xù)焚書[M].長沙:岳麓書社,1990:314。
⑧袁承業(yè).云南左布政使貴溪徐樾撰別傳[A],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卷四)[Z].1912年東臺袁氏鉛印本。
⑨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⑩李贄.李贄文集(卷七)[Z].張建業(yè)、劉幼生主編,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0。
(11)馬蹄疾.水滸資料匯編[C].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重印本。
(12)黃霖在《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中說:“經(jīng)過戴望舒、王利器、葉朗等人的考證,容本《水滸》是葉晝偽托可成定論。”并在該文的注釋中作了較詳細的說明。見《復(fù)旦學(xué)報》社科版,2002年第2期。
(13)參見沈伯俊《論<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的考證部分,《內(nèi)江師專學(xué)報》社科版,1993年第3期。
(14)黃霖.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J].復(fù)旦學(xué)報(社科版),2002,(2):119-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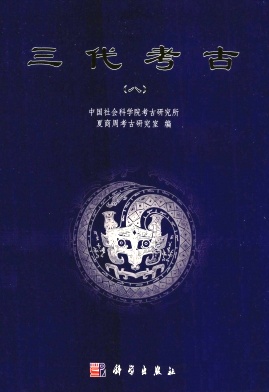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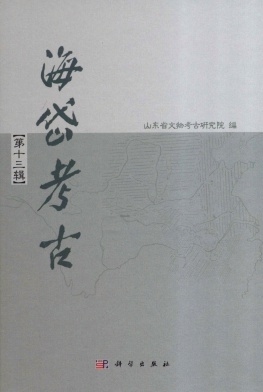
境.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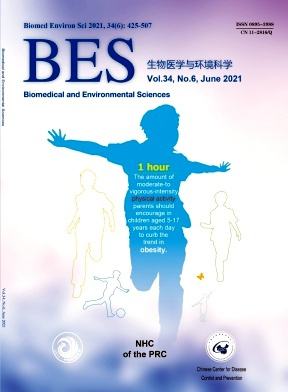
院學(xué)報.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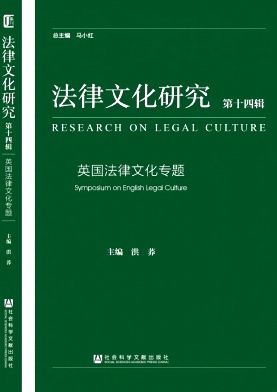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