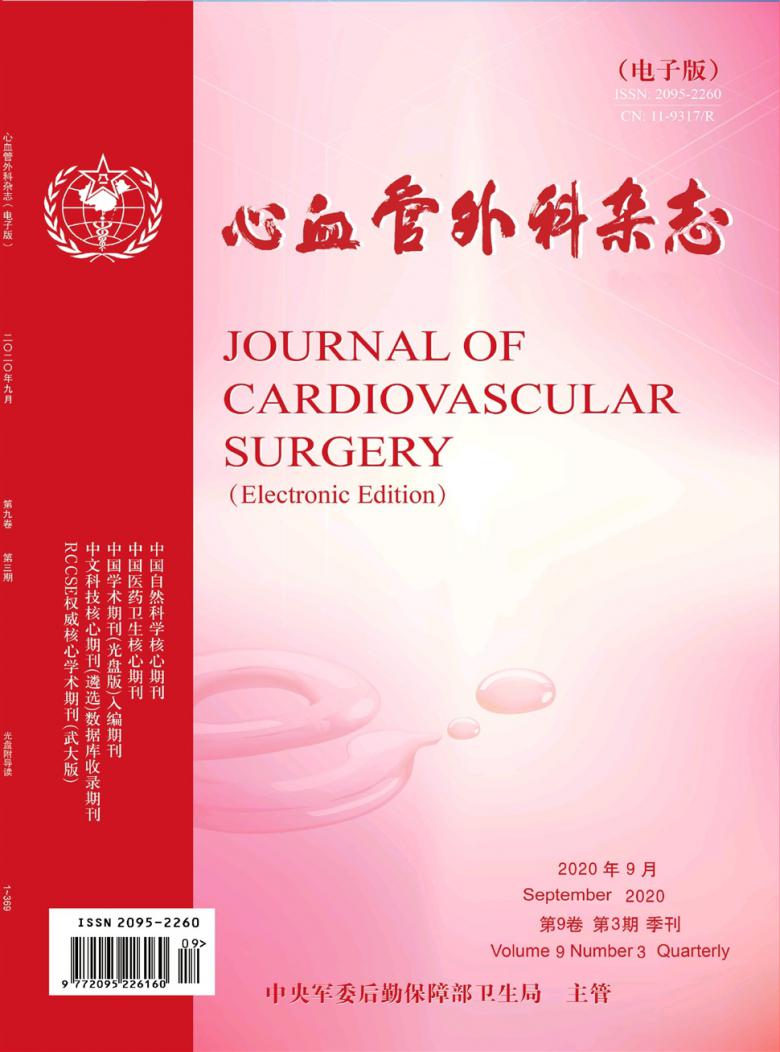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下)
陳才智
三、中晚唐 綜論中晚唐的論文有吳在慶《中晚唐苦吟之風及其成因初探》〔354〕、徐青《中晚唐時期的詩律特點》〔355〕。綜論盛中唐的論文有吳相洲《論盛中唐詩人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356〕。孟二冬《意境與禪玄:中唐詩歌意境論之誕生》〔357〕認為,從理論上明確提出詩歌“意境”的概念,并對之加以探討的是中唐時期的一些作家和詩歌理論家,它標志著中國古代詩歌意境理論的正式誕生,這與前人及同時代的文藝創作、文藝理論、學術思想、哲學理論觀念,尤其是禪玄有密切的關系。吳湘洲《論唐肅宗黜華用實主張對詩風新變的影響》〔358〕研究安史之亂以后,唐肅宗逐步確立黜華用實的用人方針,對士人行為風范主動加以改造,使之由高華走向沉實,詩風亦隨士風發生變化:帝王師式的人物風范不見了;尚言談議論變為勤于吏事了;率性任誕的作用逐漸消失了。 有關晚唐的綜論性文章在兩年間呈上升趨勢,袁文麗《晚唐詩人內向心理探因》〔359〕結合晚唐的衰微國勢、政治生活空間、士大夫文人生活、宗教哲學對晚唐詩人的影響,以及文學思想的轉變,探討晚唐詩人內心幽微心理產生的原因,并進而分析內向心理帶來的詩歌特色:沖淡玄遠、含蓄委曲。趙山林《晚唐詩境與詞境》〔360〕認為,由于時代風氣及詩人審美心理的變化等原因,晚唐詩歌表現出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1.深情與苦調,即濃厚的感傷情緒與悲劇意識。2.艷體與曲筆,即以濃艷之辭寫兒女之情,在很多場合下又借兒女之情寄托身世之感。3.細意與靜境,即描寫對象細小,藝術結構細密,而境界趨于靜謐深邃。晚唐詩歌的這些特色對于處在形成與發展中的詞的特殊風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總《論唐末社會心理與詩風走向》〔361〕認為,宣宗大中末以后四十余年的詩壇,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已形成一定的詩人群,但未能構筑足以前期比配的時代性特征與藝術價值觀念,詩歌主題表現只是前期的余波遺緒:一,承續元白一派政教文學觀而著重描寫民生疾苦并指陳時弊,如皮日休、陸龜蒙、杜荀鶴、聶夷中;二,承續溫李一派唯美傾向而著重描寫艷情聲色,如韋莊、吳融、鄭谷、韓偓;三,承續姚賈一派清淡詩風而著重抒情寫避世心理與淡漠情思,如曹鄴、于濆、方干、司空圖。臧清《論唐末詩派的形成及其特征》〔362〕從“咸通十哲”的形成緣起、創作傾向和審美趣尚,揭示唐末詩派與其社會文化的附生關系、“咸通十哲”的藝術得失。李小榮《略論“咸通十哲”的詩歌意象》〔363〕將所論對象分為三類:一,有關水、孤舟、夕陽的意象,表現生存的孤獨感;二,有關夢、酒的意象,表現生命的空虛感;三,有關僧、的意象,表現宗教的皈依感。相關論文還有王曉祥、劉霞《晚唐詩壇的現實主義流派》〔364〕、方然《晚唐文化背景與晚唐文學的抒情走向》〔365〕、趙藝梅《物物于心的晚唐詩歌》〔366〕、吳在慶《“月鍛季煉”與晚唐詩的奇僻》〔367〕、張學忠《唐末絕句議論化的差異與衍變》〔368〕等。 專攻五代十國的賀中復發表了《五代十國的溫李、姚賈詩風》〔369〕、《五代十國詩壇概說》〔370〕、《論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371〕。末文認為,五代十國時期存在規模可觀的宗白詩風,其勢力和影響遠超溫李、姚賈的學效者,代表了此期詩歌的基本創作傾向。五代十國的宗白詩風以南唐開國、后唐滅亡為界,可分為具有不同特點的前后兩期,從中可以看出其前期承唐、后期啟宋的過渡性質。 有關白居易的論文大約有30篇,其中關于《長恨歌》者仍占主要比例。謝思煒有5篇:《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價值》〔372〕、 《敦煌本白居易詩再考證》〔373〕、《〈新樂府〉版本及序文考證》〔374〕、《白居易詩學思想述評》〔375〕、《白居易與李商隱》〔376〕,均收入其在啟功、鄧魁英門下的博士論文《白居易集綜論》〔377〕,該書上編探討白居易集的版本源流、演變與構成,下編討論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白居易的家世和早年生活、白居易與中唐儒學、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中唐社會變動與白居易的人生思想、白居易的文學思想、白居易的敘事詩創作等,是一部扎實細致的研究專著。有關作品整理方面的書籍有劉明杰點校《白居易全集》〔378〕、褚斌杰主編《白居易詩歌賞析集》〔379〕、時宜之《白居易詩歌精選》〔380〕。 白居易思想創作分期一般以元和五年改官或元和十年遭貶為界,但也有學者有不同意見,如鄧新躍《被貶江州司馬不是白居易前后思想的分界點》〔381〕。張安祖《論白居易的思想創作分期》〔382〕亦認為,一,改官或遭貶并未使白居易放棄對現實的關注,他依然滿懷希望,寫作諷諭詩以干預時政;二,白居易側重現實功利的詩歌理論是在元和十年后成熟,此時他諷諭詩數量減少,同他不在諫官其位的職責密切相關;三,白居易詩閑適心態和好佛趨向與他時運不利又始終關心現實、渴望有所作為的思想意識息息相通。所以分期應以長慶二年白居易自請外任為界。張安祖另有《外容閑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態》〔383〕,剖析白居易在洛陽的18年晚年生活慚愧、悲哀、痛苦與知足、閑適相交織的矛盾心態。鄭敏《人道主義的激情與沉思:白居易諷諭詩與〈策林〉對讀》〔384〕針對謝思煒《白居易的人生意識與文學實踐》所云“白居易撰寫的《策林》和任左拾遺后開展的政治批評……包含了過多有關清明政治的老生常談和道德說教,并非是真正可行、有具體針對性的治國方略。……白居易和中唐其他杰出人士一樣,將自己無條件地交付于封建國家機器,在個人與皇權國家的關系上甘心情愿地處于絕對服從的位置”〔385〕這一觀點,認為即使撇開在“宮市”、“進奉”、元和三年制科案、貶黜元稹案、反對宦官統軍等問題上的眾多重大決策和嚴重斗爭不談,單就《策林》和諷諭詩中,從人道主義出發所觸及的如輕徭薄賦、救濟生民、戒君奢欲、懲治貪官、尊賢納諫、采詩觀風等社會問題而言,上述結論亦顯然與事實有違。 劉維治《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386〕剖析白居易山水之吟與其仕宦沉浮的密切關系,認為除借山水宣泄自己感傷情懷這一主觀因素外,山水自然景觀的特征也使其山水之吟因地域不同而呈現出不同風采:江州忠州之吟充滿哀傷之情,蘇州杭州之吟充滿欣喜之情,洛陽之吟充滿閑適之情,作者還有《白居易詠物詩創作背景、類型及寓意》〔387〕。黃意海、黃井文《白居易〈燕子樓〉詩考辨》〔388〕從燕子樓傳說的由來、唐代法律及社會風氣、白居易對殉葬的態度和婦女觀、作《燕子樓》詩前后的心境及對詩句本意的理解等七個方面,論證所謂關盼盼死節之事并無證據,謂白居易諷關盼盼以身殉張仆射更屬不實。童根羽《白居易“湖上春行”佚詩一首》〔389〕據《永樂大典》卷2264“湖”字韻“輯”得一首佚詩,紀健生《〈永樂大典〉載白居易〈湖上春行〉之二非佚詩》〔390〕隨后乃辨其非。有關白居易的論文還有張文生《白居易詩論新探》〔391〕、嚴杰《入仕求祿與隱退:淺議白居易的出處進退》〔392〕、程紅兵《試論白居易的后期思想》〔393〕、馬永強《白居易前后詩風轉變原因新探》〔394〕、祝德純《白居易閑適詩藝術探微》〔395〕、張浩《試論白居易婦女詩的思想意義》〔396〕、張浩遜《從贈向詩看白居易的婚戀生活》〔397〕、黃果泉《理性的掙扎:白居易諷諭詩說復議》〔398〕等。 綜觀有關《長恨歌》的研究論文,仍舊集中在對主題的探討上,且又多是對舊有諷刺詩、愛情詩、隱喻詩、雙重及多重主題說進行補充或延伸擴展。如荊立民《白居易〈長恨歌〉主題的再思及其他》〔399〕所論,《長恨歌》諷諭的主題是統一的,但作者在表現這個主題時流露的感性和所持的態度,卻是前后有異的。由于作者淡化或回避了起初存在的荒淫情節,加之白居易“自我感受”的寄寓、變文故事的影響、制約、市民審美情趣的影響,使主題呈現引人爭議的模糊狀態。基本上是摭拾舊說而已。它如胡淑娟《歷史鑄就的悲劇: 〈長恨歌〉主題新探》〔400〕、李桂奎《論〈長恨歌〉即對人生苦悶的訴說》〔401〕、張澤暉《論〈長恨歌〉的主題思想》〔402〕、郭世綖《從創作環境和創作意圖深探〈長恨歌〉的主題思想》〔403〕、陳迎平《〈長恨歌〉主題新探》〔404〕、張建東《〈長恨歌〉主題芻議》〔405〕、田原《〈長恨歌〉主題新探》〔406〕等等,亦鮮有突破。鈄東星《〈賦得古原草送別〉之誤解與正解》謂《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取義于《易·離》象曰:“離,麗也”,兩物相附為麗,乃反義相訓,言野草依存古原為生命,獨成一說,不無道理。綜論元白的有許總《論元白文學思想的實現功利及其詩化形態》〔407〕,分析元白的共同趨向:1.等同于政治主張的詩歌認識觀念與價值取向;2.隨著國家政局變動與詩人仕途進退而衍化的表現特征;3.向儒家詩教傳統復歸中的新變性質與內涵。其《論元稹、白居易的文學觀》〔408〕與此大同小異。郭新和《試論元白詩派的五言長篇排律》〔409〕分析了元白二人五言長篇排律內容上對封建士大夫兩重性格的再現、形式上鋪敘手法和以時實入詩的運脾,不無一得之見。惟題目中“詩派”二字,文中未見所指,不妨刪去。 中唐詩人張籍、王建的樂府唱和現象鮮為人知,朱炯遠《論張王樂府中的唱和現象》〔410〕檢索張王同題、異題唱和樂府15組,其中古題、新題兼有。文章從二人的交游以及中唐唱和詩繁榮等因素分樂府唱和詩產生的條件,闡述二人以樂府唱和的時代意義,對文學史上存在著“新樂府詩派”這一觀點有支持提托之力。 韓愈研究仍是熱點,以至有建立“韓學”的倡議。1997年7月,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川師大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對歷代韓集校注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對現存韓詩韓文編年做出了新的考訂,校勘較精審,注釋較準確,解決了不少前人未曾解決的疑難問題,是迄今為止韓集的最佳文本,其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將為韓學研究的深入和“韓學”的確立起到較大的推動。研究專著則有陳勝《論韓愈陽山之貶及其文學評價》〔411〕。曹連觀《尋找陌生:論韓愈的詩藝創新》根據俄國形式主義批評所謂“陌生化”原理,論述韓愈詩擅用獨特生新的詞語、奇拗激越的音節、異乎尋常的形象、以文為詩的手法使其詩擺脫盛唐的羈絆,并為宋詩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不少論文涉及韓孟詩派,如許總《論韓孟詩派主體心性的強化與藝術表現的變異》〔412〕、楊國安《從自然和社會走向自我:韓孟詩派研究》〔413〕、 《心靈創造的世界:韓孟詩派研究》〔414〕和《論韓孟詩派生硬勁峭的內在品質》〔415〕、朱明秋《雕肝嘔肺究為何:尋韓派詩人苦吟的原因》〔416〕等。林伯謙《韓愈文學理論與佛法行持之研究》〔417〕從創作目的和創作方法兩方面比較韓愈文學理論與佛法行持的關系,認為二者盡管有不少共通之處,但也有大相徑庭之處。其相異處可見出韓愈的反佛之心,至于不謀而合處則絕非受禪學啟發所產生的靈感,更不是晚年結交大顛和尚而得到的領悟。相關論文還有閻琦《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系之探討》〔418〕。 有關柳宗元的論文數量仍和前兩年相差不多,較有新意的是朱邦國《論柳宗元的作品與創作心態的關系》〔419〕、周慶義《柳宗元家世與籍貫考》〔420〕。劉禹錫研究在《陋室銘》是否出自劉禹錫之手產生了質疑,吳小如1996年春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首先發難,但未稽考古籍,立論未周,不久即遭駁斥。段麗塔《〈陋室銘〉作者辨析》〔421〕據《新唐書.崔沔傳》,謂《陋室銘》乃崔沔所作。吳小如《〈陋室銘〉作者質疑》〔422〕又據顏真卿《崔孝公陋室銘記》對照今傳《陋室銘》加以考察后認為,說《陋室銘》出自劉禹錫之手固無確據,但說是崔沔傳所作亦不免有人疑竇之處;《陋室銘》實不類唐人作品。而卞孝萱《〈陋室銘〉非劉禹錫作》〔423〕則就自己《劉禹錫年譜》〔424〕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更具說服力的申述。相關論文還有高鈞《劉禹錫〈陋名銘〉作年及陋室所在地考辨》〔425〕。有關劉禹錫的重要論文還有沈文凡《元和詩豪劉禹錫》〔426〕、張鳳芳《簡論劉禹錫的詩歌創作》〔427〕、熊飛《〈劉白唱和集〉編集流散考》〔428〕、張自新《自我心靈的燭照與社會盛衰的思考:論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429〕、林心治《劉禹錫詠史懷古詩新探》〔430〕、任暉《永貞革新與劉禹錫、柳宗元的文學創作》〔431〕、尹楚彬《劉禹錫交游辨正二題》〔432〕、陶敏《曲折微婉寓刺于美:說劉禹錫〈寄李六侍御〉詩》〔43 3〕。書籍方面,蔣維崧、趙蔚芝、陳慧星、劉聿鑫《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是繼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434〕之后又一部劉集整理本,它以民國徐鴻寶影印宋紹興八年本為底本,系年依高國忠《劉禹錫詩文系年》〔435〕。與瞿箋相比,它更側重于語詞。卞孝萱、卞敏《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劉禹錫評傳》〔436〕,洋洋29萬字,分列十章,對劉禹錫的氏族、籍貫、出生地、家世、游學、科名、官職、交游、政治思想、哲學理想、人生觀、文藝思想及對后世的影響一一加以論述,文獻搜求博洽,資料運用精審,考論嚴謹,視野開闊,表述流暢,洵可謂力作。 李賀仍舊是中晚唐研究的熱點,兩年間發表了大約50篇文間。縱觀這些文章,選題以悲劇意蘊、生命意識、獨特之理等較為集中,如郭崇林《李賀詩的悲劇心理特征初探》〔437〕、周尚義《李賀的悲劇情結及其詩歌的悲劇意蘊》〔438〕、阮堂明《李賀的心靈矛盾與詩歌的藝術表現》〔439〕、李寶泰、鄒少雄《超越生命的羈絆:論李賀詩的超我意識兼及其意識構成》〔440〕、王慧《生、死、仙:淺探李賀詩歌中的生命哲學》〔441〕、盧偉、朱繼英《試論李賀詩中的死亡焦慮》〔442〕、李鵬飛《絕望詩人的自我拯救:李賀詩歌與創作心態》〔443〕、王玉民《李賀詩歌中的無意識》〔444〕和《李賀詩歌中的通感、幻覺和高峰體驗》〔445〕、李軍《李賀詩歌意象論》〔446〕、 《論李賀詩歌的荒誕詩風》〔447〕和《論李賀詩歌的藝術變形》〔448〕、王峰秀《淺談李賀的創作心態及詩歌意象》〔449〕、廖明君《生命的有限與無限:李賀詩歌新論》〔450〕、張國榮《淺論李賀詩歌獨特之“理”:兼駁李賀詩歌“少理”論》〔451〕。 李賀詩的章法,歷來受到非議,謂之有句無篇、零碎拼湊、前后矛盾、俱無脈絡,而楊曉靄《略論李賀詭奇詩歌的章法變幻形態》〔452〕則認為,李賀詩結構有內在邏輯性,以心理意識為內在線索,將種種瞬間性印象剪輯成體以達到“陌生化”效果,在詩歌章法表現為“隱合”“復迭”“輻射”“謎語”四種形態。其對西方形式主義文論方法的合理借鑒,可算正切合賀詩之神理。長吉詩善用色彩,前人已多有所悟。陶文鵬《論李賀詩歌的色彩表現藝術》〔453〕則將李賀對色彩的敏感特點融貫到對其詩歌意象和意境的具體分析之中,指出他善于“先聲奪人”和“借色點睛”,擅長表現靈視中夢幻里的廣闊無際虛幻渺遠之色,表現光色的微妙變化,賦予色彩以象征性、情感性和個性,把色彩作為創造冷艷瑰奇意境的重要手段。其論述可謂較全面細致。1983年吳企明曾有《李賀詩歌藝術淵源初探》〔454〕,1997年他又有《長吉詩藝術淵源論》〔455〕一文,結合李賀生活的中唐時代政治情況和自身的坎坷遭際,更加全面系統闡述了這一論題,以求了解其詩歌獨特風貌形成的原因。杜道群亦有《試論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456〕,可同此文相互參看。吳企明另有《論杜甫與李賀》〔457〕。在李賀游蹤研究中,許多年譜、著述皆稱李賀有南游之舉,如朱自清《李賀年譜》、錢仲聯《李賀年譜會箋》、王禮錫《李長吉評傳》、吳企明《李賀》、傅經順《李賀傳論》等均主此說。黨銀平《李賀南游疑證》〔458〕則從諸家新論南游的原因、時間、李賀的生活和身體狀況、歌詩的內容等四個方面一一加以駁論,認為南游之舉并不可信。 同前幾年一樣,無題詩尤其是《錦瑟》,仍是兩年中李商隱研究的特點。王蒙謂之《李商隱的挑戰》〔459〕,形象、豁然。文章認為,李商隱研究熱潮的出現,標識著近年來文學觀念的變遷、發展、開闊深化:“李商隱現象”是對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包括接受美學和文學史的一個挑戰,“我們有可能把李商隱研究作為一個契機,把我們整個國家的理論水平,文學史的水平,詩歌創作的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境地。”孫金榮《潛沉的擴張的隱喻:李商隱“無題”詩意象的主要表現形式》〔460〕認為,李商隱無題詩意象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以特別的文學性(非固式、非直觀化)、內在性《隱喻式思維》、比喻各方面的渾然天成(具旺盛繁殖力的結合)為特征的潛覺的擴張的隱喻則構成其意象表現的主調。相關論文還有彭桂媛《與君共賞“琴瑟”弦外音——試論李商隱無題詩中的“情中情”:兼與先輩諸說商兌》〔451〕、張鳳秋《李商隱“無題”詩探幽》〔462〕、陳建任《言情的藝術:論李商隱無題詩的情感及抒情方式》〔463〕、廖美蓮《言有盡而意無窮:李商隱無題詩意境美淺析》〔464〕、趙忠山、《李商隱無題詩的空白結構及其模糊特征》〔465〕、張明非《李商隱無題詩研究綜述》〔466〕、楊艷梅《〈錦瑟〉是悼亡詩新證》〔467〕、李平《〈錦瑟〉難解:談當代語義學幾種理論在解讀中的運用》〔468〕、王次澄《李義山〈錦瑟〉詩賞析》〔469〕、夏其模《我對〈錦瑟〉詩的理解》〔470〕。 余恕誠《李商隱詩歌的多義性及其對心靈世界的表現:兼談李詩研究的方法問題》〔471〕在論述李詩朦朧、多義及其對心靈世界表現特點的基礎上,提出李詩研究總體上可以著重從反映心靈世界去看李詩,而在深處、細處可以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釋,使詩歌多義性的豐富情感內涵,在解讀和研究中更充分地展開。張明非《論李商隱的比興風騷》〔472〕闡發錢鐘書先生《錦瑟》乃“借比興之絕妙好詞,究風騷之甚深蜜旨”(《談藝錄》補訂本)之意,將之擴展為對整個李詩特征的概括。樊南文研究繼董乃斌《論樊南文》、吳在慶《樊南四六文芻議》之后,劉學鍇《樊南文的詩情詩境》〔473〕從詩語、詩情、詩境、詩心四個方面,剖析玉溪詩對樊南文的滲透與影響,是對錢鐘書先生所云“樊南四六與玉溪詩相通”〔474〕很好的闡發。有關李商隱研究的其它重要論文還有黃世中《李商隱詩版本考》〔475〕、張學松《李商隱詠物詩的悲劇美》〔476〕、張文飛《從新批評的角度論李商隱詩之藝術魅力》〔477〕、黃世中《論李商隱詩的藝術特色:兼評舊箋對李詩的某些曲解》〔478〕、熊國華《論李商隱詩化情境的生成方式》〔479〕和《論李商隱詩歌的隱喻系統》〔480〕、梁佛根《義山桂幕詩作的黃昏情結及其多層底蘊》〔481〕、深澤一幸《蜂與蝶:李商隱詩的性表象》〔482〕。 鐘來茵《李商隱愛情詩解》是一部新人耳目之著,此著分為初戀詩、夫人詩、關于皇帝的愛情放含有性幽默的游戲之作四個部分,對涉及的108首義山詩分別加以注釋、詩解和今譯,其詩結部分注重對義山賦高唐的手法的闡析,注重以詩證詩,注重喻之多邊,喻之二柄,注重詩家創作常規,注重以道藏釋義山詩,作者自謂第一輯初戀詩將最受關注、最會引起爭議,我們拭目以待。楊柳《李商隱評傳》出版了新版〔483〕,增加了錢鐘聯、沈立人的序和其子楊曉東的后記。 自陳尚君、江涌豪發表《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的節要、提出《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以來,學術界給予了充分重視,兩年中又發表了21篇有關文章,其中《中國詩學》第五輯〔484〕專門開辟“《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討論”一欄,收入9篇討論文章。〔485〕 陳尚君、汪涌豪《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486〕全文三萬字,分1.《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生平思想、論詩旨趣及文風取向的比較,顯而易見的悖向;2.明萬歷以前未有人見過《二十四詩品》;3.《二十四詩品》之出世及其疑問;4.《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5.《詩家一指》的初步研究;6.所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為明末人據《詩家一指·二十四品》所偽造;7.余論七大部分。其中《詩家一指》為懷悅所作一說,張健已有訂正。其結論為,明初洪武間人趙撝謙《學苑》中已引錄過《詩家一指》,所以《詩家一指》成書應在此前;其最早版本是成化楊成校刊的《詩法》本,其后百年間的各種版本均不云懷悅作。另,明正間史潛校刊《新編名賢詩法》三卷中,有《虞侍書詩法》,應是較《詩家一指》更接近《二十四詩品》原貌的版本。據“虞侍書”之名稱,及書中“集之《一指》”之“集”的自稱,張健推斷此書作者可能即為虞集。〔487〕 此后,陳尚君《〈二十四詩品〉辨偽追記答疑》〔488〕針對各家反駁詰疑,如司空圖本人或其友人詩文中有無其作《詩品》的證據、如何理解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之文意及“韻”字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唐末至明末七百多年無人稱引這一特殊現象,一一闡述己見,認為目下欲維護司空圖的著作權還看不到有力的證明。汪涌豪《論〈二十四詩品〉與司空圖詩論異趣》〔489〕結合其生平思想,對其所作論詩雜著與《二十四詩品》在哲學觀、文學觀、以及理論形態等方面的不同加以論證,汪涌豪《司空圖論詩主旨新探:兼論其與〈二十四詩品〉的區別》〔490〕則專就其詩學思想的主旨,討論其與《二十四詩品》的區別。 王運熙《〈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我見》認為陳尚君、汪涌豪之論有兩條證據特別有力,一是證明蘇軾沒有提及《詩品》,二是許學夷的論述,他對司空圖十分推崇,不可能把司空圖之著斥為“卑淺”。張伯偉《從元代的詩格偽書說到〈二十四詩品〉》從元代詩格的一般特征入手,對懷悅編本《詩家一指》的各節一一考察,認為它是一部從唐、宋及元代初期的詩論中抄撮編纂而成的書,因而最早出現在《詩家一指》中的《二十四詩品》究竟出于唐、宋,抑或元初,從《詩家一指》本身尚不能得出確實的結論。張健《從懷悅編集本看〈詩家一指〉的版本流傳及篡改》從懷悅編集本《詩家一指》入手,對《詩家一指》的版本流傳加以梳理,得出如下結論:一,懷悅編集本《詩家一指》是一部詩法匯編,懷悅是該書的刊刻者。二,懷悅本《詩家一指》與楊成本《詩法》是同一部詩法匯編的不同傳抄系統。三,《學苑》所引《一指》與懷悅本《詩家一指》是同一傳抄系統的不同抄本。四,《詩家一指》的篡改者是其所依據的《木天禁語》 《詩家一指》合編本的編者。蔣寅《關于〈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為《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補充了一個劉躍進見告的證據,即王應麟《小學紺珠》未收二十四詩品條,說明《二十四詩品》是南宋以后的作品。蔣寅認為陳尚君、汪涌豪《司宏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最有力的理由是明代以前不見收錄與征引及楊慎、胡應麟、胡震亭、許學夷列舉司空圖詩論時不及《二十四詩品》,它使得在明代叢書里將《二十四詩品》寄托于司空圖名下,豁然暴露出極大的疑點。至于張健認為《虞侍書詩法》結構完整,《詩家一指》明顯經過改竄,固然有理;但文章對《二十四詩品》在明末突然橫空出世,自始就沒有引起任何懷疑這一現象也很不理解。〔491〕 李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獻疑》〔492〕、祖保泉、陶禮天《〈詩家一指〉與〈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493〕、祖保泉《再論〈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494〕和《〈二十四詩品〉是明人懷悅所作嗎?》〔495〕、王步高《〈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作質疑》〔496〕、劉倩《〈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駁議》〔497〕則針對陳、汪之論加以質疑。如李文認為,以韻指篇的用法在古代并非鮮見,而以韻指詩之一聯,通常則限于一篇之內,鮮有以之統計不同詩作中的詩聯之例。 張少康《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之我見》〔498〕就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所說“二十四韻”究竟指什么,《二十四詩品》明末以前無人稱引的問題、《二十四詩品》真偽的內證問題和用語問題分別闡述了看法,其結論是《二十四詩品》是否司空圖所作,尚無法下一肯定結論。 討論這一問題的其它論文還有陳良運《司空圖〈詩品〉之美學構架》〔499〕、趙福壇《我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及其體系之點見》〔500〕、汪泓《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辨綜述》〔501〕、張柏青《從〈二十四詩品〉用韻看它的作者》〔502〕、束景南《王晞〈林湖遺稿序〉與〈二十四詩品〉考辨》〔503〕、李祥林《近年來有關〈二十四詩品〉作者之爭》〔504〕。司空圖研究的其它論文還有吳全蘭《靜穆:司空圖推崇的一種審美心態》〔505〕、古風《司空圖的意境形態論》〔506〕、陳登《休姆與司空圖的詩歌理論比較》〔507〕、黃鋼《司空圖與詩味》〔508〕、鐘光貴《司空圖境界說探要》〔509〕、鄭德開《司空圖〈詩品〉 “超詣”美學思想探源》〔510〕、張松輝《道家道教與司空圖》〔511〕。
〔1〕陜西教育出版社,前二書1996年7月版;后二書1996年8月版。 〔2〕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1958年12月版。 〔3〕中華書局1997年11月版。 〔4〕據王友勝《一部唐詩研究的力作:評〈全唐詩人名考證〉》,《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4月版。 〔5〕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版。 〔6〕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考》,考及782首(其中重出9首),又53句,詞34首。《唐代文學叢書》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7〕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版。 〔8〕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版。 〔9〕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 〔10〕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年8月版。 〔1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3〕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 〔14〕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5〕東方出版社1997年7月版;1997年10月版。 〔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17〕臺灣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8〕中華書局1996年11月版。 〔19〕遼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