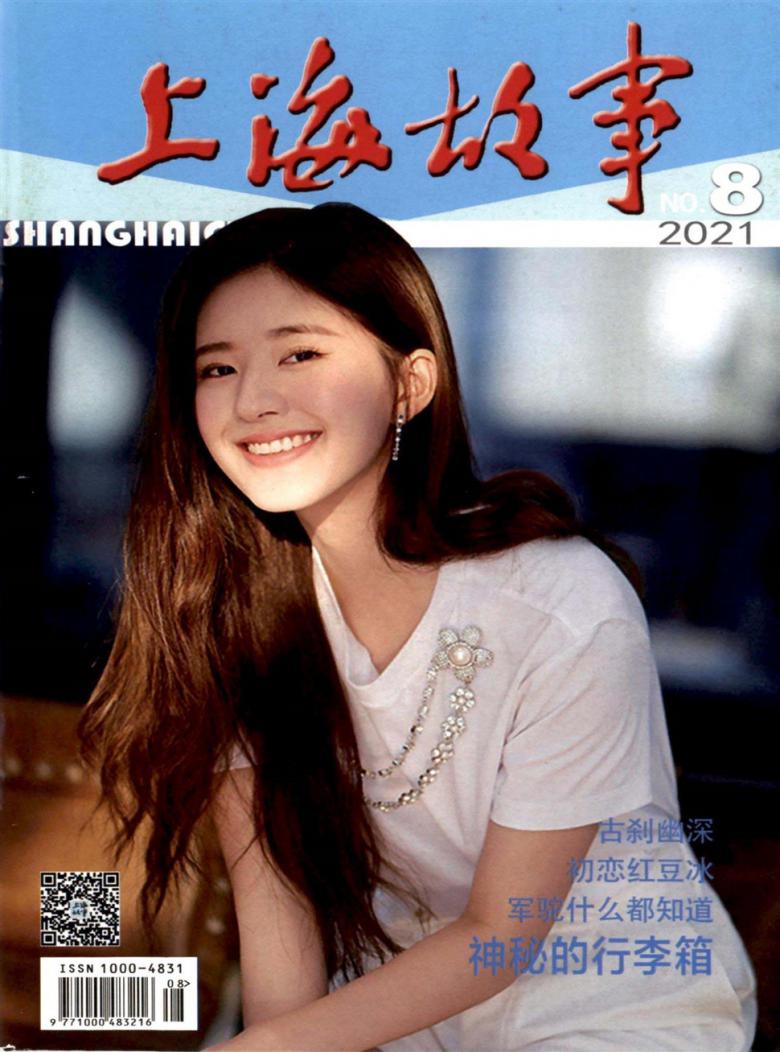二十世紀以來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研究述評
左東嶺
20世紀以來的明代文學研究,一般認為促使明代文學思想發生轉變的外在主要因素有3種:王朝政治的腐敗、心學派別的崛起與經濟領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王朝政治的腐敗是傳統的觀點,已被學者廣為接受。資本主義萌芽是建國后長期討論的問題,并已被許多學者運用于文學研究之中,但由于資本主義之概念、內涵及使用范圍均存有較大爭議,以致令人懷疑該學術命題是否具有真實性。但自上世紀后半期,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的關系卻受到越來越多學人的關注,從而成為明代文學研究的重心之一。認真總結該命題的研究歷史與現狀,將會極大地推動明代文學思想研究的進展。
一、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演進
1、心學研究的5個階段
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的研究一般要牽涉到哲學與文學兩個領域,而文學研究的深度又取決于哲學研究的水準。
第一階段:20世紀上半期。該時期文學研究幾乎很少論及心學與文學思想的關系問題,幾部文學批評史甚至沒有提及王陽明。不過,該時期哲學領域對心學的研究,卻為以后的文學研究定下了一個基本的方向。
當時對心學研究的整體思路,是建立在“五四”所奠定的反儒家禮教基礎之上的,其中嵇文甫出版于1943年的《晚明思想史論》特別值得注意,本書論述心學思潮大致分為王陽明時期、王學分化時期與狂禪派時期三個大的階段。論王陽明的重心是:“處處可以看出一種自由解放的精神,處處是反對八股化道學,打破道學的陳舊格套。” ① 論王學分化則區分為左派與右派,而尤其重視以王畿與王艮為代表的左派王學,認為是他們將“當時思想解放的潮流發展到極端” ② 。而狂禪派則以李贄為核心:“這個運動以李卓吾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顏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 ③ 這就構成了晚明解放思潮的發展演變模式:王陽明發端、左派王學發展、李贄變異并影響到晚明之一班文人。與該書前后出版并對后來影響較大的幾部著作如嵇文甫之《左派王學》(1934)、容肇祖之《李卓吾評傳》(1937)、吳澤之《儒教叛徒李卓吾》(1949)等,大致均遵循此一思路。第二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代表該時期研究特點的是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由于受到哲學研究中唯物與唯心等研究模式的影響,由嵇文甫所設立的心學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更改,即王陽明哲學被定性為唯心主義體系而評價變低,降低晚明解放思潮與王陽明心學的聯系,更突出泰州學派的人民性與平民色彩,更強調李贄反圣教反道學的戰斗精神與平等觀及個性說,當然同時也不忘一分為二地批判其唯心主義“彼岸”的禪學思想。
第三階段:“文革”時期。此為上一時期研究模式的延續,只是更趨于極端而已,其突出特征在于以儒家與法家來區分心學思潮中的各派人物,如將李贄與耿定向的沖突說成是儒法二家的較量等,其政治意義大于學術意義,故不必多言。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本時期的前幾年尚沿襲“文革”習氣,但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與學術的整體進展,心學研究在向著20世紀上半期回歸的同時又有新的進展。在此一階段,李澤厚的哲學與美學研究值得關注。他出版于1981年的《美的歷程》一書,盡管有粗疏簡略的種種不足,但卻影響了中國大陸的整整一代學人,甚至波及港臺學術界。該書將明代文藝分為市民文藝與浪漫思潮兩個側面,并以李贄作為聯結二者的核心,同時突出了兩方面的因素:一是資本主義萌芽。認為李贄所代表的異端思潮“更鮮明地具有市民——資本主義的性質(它在經濟領域是否存在尚可研究,但在意識形態似很明顯)” ④ 。一是重新強調他與王學的關系,認為“作為王陽明哲學的杰出繼承人,他自覺地、創作性地發展了王學” ⑤ 。因限于體例,本書未能對陽明心學本身加以闡述,而在1985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一書則彌補了此一缺憾,作者在“宋明理學片論”一章中認為宋明理學經由張載、 朱熹和王陽明,“是從自然到倫理到心理,是理學的成形、爛熟到瓦解,倒正是趨向近代的一種必然運動” ⑥ 。由于陽明心學“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包含有血肉之心與個體個性,從而使之更重情感欲望,因而“王學在歷史上卻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進步走道。它成為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學基礎” ⑦ 。從中可以看出嵇文甫所設定的從王陽明到王學左派再到李贄的傳統模式,但由于將其與資本主義萌芽與市民文藝結合起來論述,加之作者運用其良好的理論思辨能力,深入分析了“良知”的理論內涵與理論活力,從而在美學史、文學批評史及文學史研究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仍可在不少學者的著作中看到其所提供的思路。另外,該時期還出版了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的《宋明理學史》、蒙培元的《理學的演變》與《理學范疇系統》等著作,均對陽明心學的論述不僅采取了更為中性的態度,同時對于王學的各派理論也論述得更為深入詳細,為文學研究界了解王學提供了更為完整的哲學背景。
第五階段:20世紀至現在。這是心學研究走向深入與多元的時期,出版了許多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如陳來的《有無之境》、楊國榮的《王學通論》、姜廣輝的《理學與中國文化》、張學智的《明代哲學史》、李書增等人的《中國明代哲學》、龔鵬程的《晚明思潮》等。此外,還翻譯出版了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的《王陽明與明末儒學》、溝口雄三的《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曲折與展開》等著作。其中尤其以陳來的《有無之境》最堪注目,本書不僅深入研究了王陽明心學中心與理、心與物、心與性、知與行、誠意與格物、良知與致良知、有與無等理論范疇,更重要的是作者以境界論陽明心學,概括出其求自得之樂的無我之境和與物同體的仁者胸懷,為理解王陽明的內心世界與王學影響下的士人心態提供了有效的詮釋角度,并在某些地方已接近文學的詩意層面。臺灣與日本學者著作的在大陸出版,為文學研究界理解心學增加了不少新的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20年的研究中,文學研究界已不滿足于只依靠哲學研究界提供成果來構成自己的知識背景,而是往往文史哲兼融,依靠自我的能力來進行打通式的研究,從而使理學與文學關系的研究被置于更為圓融的位置。
2、心學家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研究在20世紀上半期,還能偶爾見到對心學家尤其是王陽明文學成就的論述,但在建國后由于學科劃分愈益細密,文學研究界很少再提到心學家的文學貢獻。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正在改變。像陳獻章、王陽明、王畿、王艮、焦竑 等人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均已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現選取對明代文學思想影響最大的二家研究狀況介紹之。
陳獻章的詩學研究:陳獻章至今為止還很少被文學批評史與文學史著作所提及,一些詩歌史與詩歌理論史提到他時也是將其“性理”詩的“陳莊體”作為反面對象而論述的 ⑧ 。但如果從明代學術史的角度和文學思想史的角度,則陳獻章又是非常重要的,黃宗羲曾說過:“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后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似。” ⑨ 可知陳獻章是心學的發端,而其哲學上追求的重自我適意、重主觀情感、重自然真實的傾向,都與中晚明士人的取徑相一致。更何況他還有豐富的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詩學思想逐漸被人所重視,并出版發表了一些著作與論文,如陳少明《白沙的心學與詩學》 ⑩ ,認為其學宗自然與歸于自得
的理論是一種詩意的境界,并在詩作中表達 了其曠達灑落的風韻情懷。張晶《陳獻章:詩與哲學的融通》11 ,認為陳獻章“以自然為宗”的落腳點在于“自得”,而延伸到其詩學思想則是“率情而發”、“發于本真”,并認為“這種觀念由作為理學家的陳獻章提出,更說明了理學內部裂變的必然性與文學解放思潮的密切聯系”。章繼先《陳白沙詩學論稿》一書是對陳獻章詩學思想與詩歌創作的綜合研究,諸如陳獻章“學宗自然要歸于自得”的學術思想與詩歌理論、詩歌創作的關系及白沙詩學在明代文化史上的地位等等。同時也論及了白沙詩學與老莊、禪宗的關系。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一書則從士人心態演變的角度論述白沙心學,認為“它為明代前期士人的心理疲憊提供了有效的緩解途徑,它使那些被理學弄僵硬了心靈的士人尋到了恢復活力的方法,它為那些在官場被磨平了個性的士人提供了重新伸張自我的空間”12 。研究陳獻章的困難在于如何評價由邵雍開創的性理詩的問題,同時還有他與陽明心學的關系也需要認真考慮。
王陽明文學思想研究:明清兩代文人盡管對陽明的學術褒貶不一,但對其事功與詩文創作大都持肯定態度,連持論甚嚴的四庫館臣亦對其贊曰:“守仁勛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亦自足傳世也。”13 受此影響,在20世紀上半期,一般的文學史著作還會提及陽明的詩文創作。20世紀50—80年代,一般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均將陽明思想作為明代文學的哲學背景加以論述。20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有學者對陽明本人的文學思想及審美意識進行探討。黃卓越認為陽明心學的出現是對弘治、正德時期前七子以形式論與情感論為核心的審美主義的“逆動”,并認為心性與良知之學“是為解脫沉重的精神危機所作的不同努力,而審美主義則于此強勁的精神蛻變中反顯得不適時宜”14 。這是就心學對當時文壇之影響而言的,當然合乎實情。左東嶺則結合王陽明的詩文創作及其心學理論,探討了王陽明的審美情趣與文學思想,認為其心學理論的“求樂”與“自得”是通向超越審美境界的關鍵15 。在《論王陽明的審美情趣與文學思想》16 一文中,左東嶺從其創作中歸納出王陽明審美情趣的三種內涵:豐富飽滿的情感、對山水的特殊愛好與瞬間感受美并將其表現出來的能力。此外,文章通過對王陽明心物關系理論的考察與對其詩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主觀心性與情感已在其理論與創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從而在中國古代文學發生論的感物說向性靈說的轉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深刻影響了明代中后期的本色說、童心說、性靈說、言情說等各種性靈文學思想。目前對王陽明心學理論向審美領域轉換的因素與契機研究尚不充分,而這又是研究心學與文學關系的重要問題,應該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關注。
3、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綜合研究
對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之關系做出綜合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潘運告《沖決名教的羈絡——陽明心學與明清文藝思潮》、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許總《理學文藝史綱》、宋克夫與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等。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也列有“陽明心學與明代中后期的文藝新思潮”的專章,亦應算作綜合研究。這些著作水平有高低之別,但均對陽明心學與文學思潮的某個側面做出了較為完整的考察。一般認為陳獻章是明代心學的發端,王陽明是心學體系的完成,嘉靖時的唐宋派是心學實際介入文學思潮的開 始,徐渭是受心學影響而又開始重個性、重情感的作家,李贄的童心說是心學思想向重自適、重自我、重真實、重自然的文學思想轉折的標志,晚明的公安派、湯顯祖、馮夢龍、竟陵派甚至包括金圣嘆,均受到心學尤其是李贄思想的深刻影響。
馬積高是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者,其《宋明理學與文學》一書對明代前期理學對文學的負面影響,明代中期前七子復古運動的反理學傾向,王學的分化與李贄反理學思想及其對文學的影響等,都進行了梳理敘述,可以說這是對理學(包括心學)與明代文學外部關系考察的專門之作,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五章“靈性與靈明:明代心學發展中的文學意識”,主要是在學理層面對心學與文學思想的關系所進行的探討,較之馬著顯然又深入一步。比如書中說:“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滿街都是圣人’,以及何心隱‘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故能鼓動人心’,既是理學之世俗化的表現,也是理學之通俗化的表現。前者是適應新現實,后者是改造新現實。這互相依存的兩面,必須兼顧到,否則,便不能把握理學之新生現實品格的全體。”17 作者將此種現象概括為“人性啟蒙的雙重指向”。這對理解晚明文學思想中既重物欲又重教化的復雜情形是非常重要的,從而顯示了作者良好的思辨能力。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則主要是對陽明心學對士人心態的影響方面所進行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打通心學與文學思想關聯的途徑。書中認為陽明心學本來是一種救世的學說,它由內在超越的個體自適與萬物一體的社會關懷兩方面的內涵構成,目的是要解決自我生命的安頓與挽救時代的危機,然而在現實的歷史運行中,它卻伴隨著環境的擠壓而逐漸向著個體自適傾斜,從而變成了一種士人自我解脫的學說。全書結合歷史具體狀況對此轉化過程進行了描述,并對各時期轉化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對陽明心學如何影響中晚明時期的各種主要性靈文學思想進行了探討。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想》與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想》實際上都是從心學與佛道之關系來論述對晚明文學思想的影響的,因為從陳獻章、王陽明創立心學體系開始,便與佛道結下不解之緣,如果不了解其與佛道的復雜關聯,便很難弄清其真實內涵與特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幾乎很少有獨立論述佛道對晚明文學思想之影響的,而是往往與心學一并討論。如黃著共論七個命題:心源說、童心說、性靈說、主情說、自適說、無法說、白蘇論,它們就全是心學體系影響下的文學理論命題。這些論述深化了對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潮的認識,是很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則是將心學對文學的影響與社會習俗、士人風氣放在一起討論的,這些討論往往涉及心學與城市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的壯大等復雜關系,而要真正理清這些關系,目前的研究深度還是遠遠不夠的。
二、明代性靈文學思想的主要流派及核心理論與心學關系的研究
1、唐宋派本色論與陽明心學
20世紀以來,最早注意到唐宋派與陽明心學關系的是1939年出版的唐順之后人唐鼎元的《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其中對唐順之與王畿、羅洪先等陽明弟子的交游情況進行了考證敘述。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文學研究領域,則主要是將唐宋派置于前七子的反對派地位,很少提到他們與心學的關系。近20年來學術界方開始注意此方面的研究,臺灣學者吳金娥《唐荊川先生研究》一書設荊川“學友”一節,較為詳細地 介紹了王畿、羅洪先、聶豹與徐階的學說主張以及與唐順之的交游情況。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在論述唐宋派時,不僅追溯了其與邵雍、陳獻章、莊昶及王陽明的淵源關系,還考察了心學弟子王畿、季本對其理論的影響。同時本書還認為唐宋派所提出的“言適與稱道”與“直攄胸臆”的合一、法式之工與自然之妙的交融的觀點,都明顯地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18 一文是對此問題的專論,文章被分為三個部分:(一)陽明心學與唐宋派的形成;(二)陽明心學與唐宋派的主導傾向;(三)陽明心學與唐宋派文學創作之得失。可以說是當時論述該問題最為全面的文章。尤其是第二部分,提出唐宋派“直攄胸臆”與法的統一的觀點深受心學影響,并認為正是受心學獨立精神與天理綱常的雙重影響,從而導致了“陽明心學既孕育了唐宋派,又給它帶來了先天不足”的結果。受這些研究的影響,近幾年出版的文學史、詩歌理論史與文學批評史,已經很少有不提及唐宋派與陽明心學關系的了。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唐宋派的形成及理論并非只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其中還存在著更復雜的情形。意與法的平衡的確是唐宋派文論的核心主張,但卻不是心學的主張,只有唐順之的本色論才真正是屬于心學體系的文論。以唐順之為例,“他一生為學有三個階段,追求八股制藝階段、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交雜而又以理學為主階段、悟解陽明心學而形成自我學術思想階段。其文學主張亦可分為三個階段,追隨前七子復古主張階段、崇尚唐宋古文階段、堅持自我見解與自我真精神階段。”19 只有第三個階段才是以心學為核心的文學理論,其由程朱向心學的轉折時間則是唐順之40歲前后時,其標志便是提出本色論的《答茅鹿門主事書》,因為書信中已明顯超越法度之糾纏而只關心“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這才真正是心學的路徑。從此一角度出發,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想》中將唐順之的文學思想概括為“心源說”無疑是抓住了唐順之本色論的核心,但心源說又不是唐宋派文論的全部。因此,要談陽明心學與唐宋派文學理論的關系,就必須首先弄清唐宋派文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與陽明心學的主導傾向有何不同?然后再考慮是將受陽明心學影響時所形成的文學思想作為唐宋派的一個發展階段,還是將其另作為一種文學觀念加以探討。就唐宋派與心學的關系而論,目前還有許多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比如唐宋派的四位主要代表人物接受陽明心學的程度就大不相同,其中唐順之被黃宗羲列入《明儒學案》的南中王門,自然受影響最深,其次是王慎中,而茅坤與歸有光就不甚明顯。這些復雜情況至今尚無人做出具體研究。
2、李贄及其童心說與陽明心學的關系李贄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備受關注的人物,20世紀上半期已有許多學者對其進行過研究,其中黃云眉的《李卓吾事實辨證》20 、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李贄年譜》與容肇祖的《李贄年譜》三種著作,為一般學者提供了研究的基本資料。建國后又出版了林其賢的《李卓吾事跡系年》(1988)、林海權的《李贄年譜考略》(1992),對于李贄的生平材料搜集得更為細密。
20世紀80年代之前,李贄與王陽明的思想淵源關系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建國前更關注他與王學左派尤其是泰州學派的關系,建國后則更強調其從事商業的家庭背景與經濟領域資本主義萌芽因素對他的影響,突出的是他反理學的批判精神與代表市民利益的平民意識。這方面可以張建業的《李贄評傳》(1981)為代表,本書資料頗為豐富,對李贄生平經歷之事實多有細致論述,然其論李贄思想之特點則突出其唯物辯證,強調 其精神主體則頗重其反封建壓迫反傳統思想之戰斗性,闡釋其思想成因則關注資本主義萌芽之影響,從中可以明確感受到五六十年代之思想路向。20世紀80年代后,由于哲學領域之研究已不諱言李贄與陽明心學之淵源關系,文學研究界也多吸收了此種研究成果。馬積高認為:“王學對文學發生較大影響主要是在左派王學形成之后,特別李卓吾的學術活動開始以后。”21 已明確指出王學與李贄的關系。潘運告則強調說:“他(指李贄)吸取并充分發揮王陽明的心學思想,闡發人的主體精神,闡發個體的獨立人格和人生價值。”22 可以看出依然是轉述李澤厚的學術觀點。韓經太則指出:“在李贄這里,王學‘良知’之旨,是被釋學化了的。”23 可以說已經接近于學理性研究了。至20世紀90年代后,已有不少學者在專門從事李贄與心學關系的梳理,臺灣學者林其賢的《李卓吾的佛學與世學》設專章介紹了“影響李卓吾早期學思的幾位思想家”,不僅注意到以前大家共同關注的王畿與羅汝芳,還論及焦竑 與耿定理。臺灣學者劉季倫《李卓吾》一書,則單刀直入地以價值關注作為論述的核心:“卓吾亙續了王學中‘個體性’逐漸增強的趨勢。并藉諸佛道的‘存在的主體’,把這個趨勢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事實上,早在王龍溪,已經以‘良知’可以‘了生死’這樣的命題,突顯了對于個人存在處境之正視,并把此一對于個人存在處境之正視,與‘良知’聯系了起來。其中已經隱含了‘個體性’的增強。卓吾只是向著此一方向,更加向前走進一步而已。”24 左東嶺認為李贄的哲學思想主要由追求解脫的性空理論與講究真誠的童心理論所構成,因而他主要吸取了心學的個體受用、老莊的自我關注與佛教的生命解脫,他所吸取的心學理論,除陽明一系的王畿、王艮思想資源外,還有宋儒周敦頤、楊時、張九成、羅從彥等人的思想25 。關于李贄對心學理論的繼承與改造,左東嶺在《順性、自適與真誠——論李贄對心學理論的改造與超越》26 一文中主要概括為三個方面:(一)從王艮的安身立本論到李贄的順民之性論;(二)從陽明、龍溪的無善無惡境界說到李贄的內外兩忘自我適意說;(三)從心學的倫理之誠到李贄的自然之誠。通過考察最后得出結論說:“李贄在表述其思想時,無論是就其使用的術語還是所談命題,都與陽明心學密切相關,但其內涵卻已發生重大的變化。他的此種思想特征顯示出他乃是一位從明代中期向明代晚期過渡的思想家,向前通向王陽明、王畿、王艮等心學大師,向后則通向袁宏道、湯顯祖、馮夢龍等晚明名士,從而成為明代思想流變史上轉折的標志。”研究界對于李贄與心學思想關系的探討,遵循著如下的一種趨勢,即從早期強調其與陽明心學對立一面的反理學性質逐漸轉向重視對其與心學傳統的內在關聯的發掘與梳理。
童心說是李贄哲學思想與文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對晚明文學界影響最大的理論,所以向來被視為李贄文學思想研究的重點。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者們多從反封建、反理學的角度立論,近20年來則逐漸走向多元。成復旺認為童心即真心,但同時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樣的心只能是市民意識,市民之心,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心。”27 張少康認為:童心“即是天真無瑕的兒童之心”,“它沒有一點虛假的成分,是最純潔最真實的,沒有受過社會上多少帶有某種偏見的流行觀念和傳統觀念的影響”28 。陳洪認為:“‘童心說’所論接近于現代精神分析學派的創作心理動力說”,“指人的基本欲望與不加雕飾的情感狀態”29 。韓經太認為:“李贄‘童心說’之作用于文學思潮者,歸根結蒂,正是一種虛無理念為終極規定的泛真實觀念。”30 周群更重視對童心說學術淵 源的辨析,認為它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主要汲取了陽明的‘良知論’、王畿的求‘真’論及羅汝芳的‘赤子良心’論”,二是“以《心經》證‘童心’”31 。即童心說是心學與佛學的混合物。袁震宇等則注重辨別其與心學之差別:“比較李贄的童心說與王守仁的真己、良知之說,它們的理論在形式上頗為相似。它們都把心看作是一個先天的超然的善的存在,要追求并保護這一存在。但是王守仁認為真己即天理,致良知在去物欲之蔽;李贄則認為童心與后儒所稱的理是相對的,護此童心便當擯除種種聞見、道理。在這點上,二者便有本質的差異了。”32 綜合上述所言,對李贄童心的理解主要表現為空虛潔靜與情感欲望這兩個側面。其實李贄在不同的場合既論述過心性之虛無,也論述過人心之必有私。可以說兩種看法均有一定的材料根據。但李贄在《童心說》中圍繞著自然無偽的宗旨強調了兩種內涵,即人心的本然狀態與表現此本然狀態的真誠無欺。至于人心的本然狀態究竟是什么,李贄并沒有做出嚴格的規定。他在人性論上主張人性不齊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因而其人之初心或曰本然狀態也就不可能有刻板統一的規定。可以說自然真實是李贄童心說的核心。延伸至其文學思想則是以自然為美的理論,這主要包括既承認人性之自然,又主張對其不加限制,同時還強調其文學之自然表現。在與陽明心學的關系上,童心說繼承了心學重主觀心性與真誠自然的傳統,但放棄了早期性靈文學思想重倫理道德的追求,而更加重視個體的價值與個人的受用。
3、公安派及其性靈說與陽明心學之關系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受心學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之一,而其受心學影響的途徑則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受李贄的影響。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狀》中的一段話是經常被學者們所引用的:“先生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批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言語,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3 所以劉大杰早在20世紀50年代即指出,袁宏道“師事李贄,推崇徐渭,在公安派詩文創作和思想上很蒙受他們的影響”34 。但李贄影響公安派的途徑與具體內容如何,仍須做出詳細的考察。公安派開始受李贄影響主要是萬歷十八至二十一年在武昌、麻城對李贄的數次訪學,對此吳兆路《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第四章、鐘林斌《公安派研究》第二章、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第五章、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第六章等均曾論及。只是訪學次數與地點存有爭議,陳書錄認為是三次,第一次是公安郊野;而左東嶺則認為是四次,地點只有麻城與武昌。至于影響的內容,鐘林斌曾概括為四方面:“一、敢于破除思想權威和世俗成見束縛的獨立思考精神;二、反對義理障‘童心’,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文藝觀;三、‘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童心常存,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的文學發展觀;四、以佛補儒的人生觀。”35 其實這些方面的影響不全是前期幾次訪學的結果,而是長期影響的全部。根據實際情形,前幾次他們之間所談內容主要是禪學化的陽明心學,主要目的是為了達到心靈解脫,同時兼及對文藝之看法。宋克夫認為:“李贄之外,袁宏道與泰州學派的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齡、焦竑 等人也有較為密切的交往。”36 然后對其各自的交游情況進行了具體的考察。所以又有人說“公安三袁的思想,顯然受了當時的‘王學左派’的影響”37 。陳書錄則引用宗道與宏道的兩封書信以證明公安派與唐宋派亦有前后的繼承關 系,并認為“公安派在文學批評中,還借鑒了唐宋派所用的某些理論范疇或術語”38 ,并列表以示意。韓經太則從心學與文學思潮演變的過程中來論述公安派與心學之間的關系,認為“袁宏道實質上是在以游戲的快感來闡揚著王守仁的‘良知’和李贄的‘童心’”39 。盡管公安派所受心學影響是多方面的,但就與公安派關系之密切與對其影響內涵之豐富而言,仍以李贄為首選。
性靈說是公安派文學思想的核心,同時也是心學影響的直接產物,因而也成為學者們探討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的重要論題。學術界追溯性靈說源頭時,一般均將其定為南北朝文論,但直接影響則歸于明代心學。成復旺將此一點表述得很明確:“與其說袁宏道的‘性靈’說是前人以‘性靈’論詩的發展,不如說是王學左派自信本心、真性流行、不循格套、不涉安排的思想在文學創作上的貫徹。”40 不過學術界對影響源頭的側重面認識不太一致,有人更重視哲學方面的影響,如蕭華榮說:性靈說“是心學術語‘良知’向詩學的轉化,是哲學概念向審美概念的轉化。它在固有的‘性情’的基礎上,又增添了活潑、飛動、靈明的意味”41 。有人則更關注文學界的影響,如吳兆路認為:“袁宏道‘獨抒性靈’的主張,與唐順之‘直寫胸臆’的‘本色論’有某些相通之處,又與湯顯祖的‘至情’論有著精神上的聯系,更直接受到李贄‘童心說’的影響。”42 有人則強調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影響,如黃清泉說:“袁宏道的‘性靈’說,是以李贄的《童心說》為哲學基礎,在文學思想上又通向湯顯祖的‘情至’說、‘靈氣’說,和馮夢龍的‘情教’說。”43 陳文新說:“從哲學淵源上看,‘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與王學左派和李贄的緣分極深。”“從詩學淵源上看,‘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與徐渭、湯顯祖等人緣分極深。”44 近幾年來,學界對公安派與心學關系的研究已經從外部的交游與文字對比轉向了學理性的內部研究。如周群在《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第八章專設“王學與‘性靈說’”一節,指出:“首先,宏道從陽明及其后學形成的獨特學脈中悟到了隨緣自在的思想氣息,并為其高揚文學革新的旗幟提供了思想基礎。”“其次,袁宏道的‘性靈說’是受到陽明及其后學的心性理論的沾溉而形成的。”45 尤其是指出其受王門后學道德色彩較為淡化后的“昭明靈覺”良知說的影響。隨后,又列“‘童心說’與‘性靈說’”一節以論與李贄之關系,認為二者在“抒寫一己之真情”與“尚趣絀理”兩方面是一致的。黃卓越則結合佛學思想辨析性靈說與心學之關系,認為王陽明稱良知為“虛明靈覺”已近于性靈的特征,在王門后學中又形成了描繪良知的靈知、靈明、靈性等性質相近的一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王畿那里,這一概念家族進而獲得了其神機妙用、盎然天成、生息不止、種種無礙的靈動性和自然性,這也是后來性靈說表達其發用形態時所得以依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說‘靈性’還限于靜態本體,而‘性靈’則明顯偏于動態發用。”46 左東嶺《從良知到性靈——明代性靈文學思想的演變》47 一文認為:“在公安與陽明心學的關系中,其實存在著并不相同的兩個側面:一是順延性的,即從陽明心學原來哲學的良知觀念發展為審美的文學觀念,此可稱之為踵事增華;二是變異性的,即對其原來的儒家倫理內涵進行了揚棄與改造,此可稱之為旁枝異響。”然后文章分三個方面對由良知到性靈說的演變進行了學理性的考察:一是從良知虛明到審美超越;二是從良知靈明到自心靈慧;三是從自然童心到自然表現。應該說這些研究均已達到一定的學術深度,但仍遠沒有達到充分的程度。如陽明心學與性靈說在文學發生論、文學創作論、文學表現論及 文學功能論之間到底存在著何種聯系與不同,從而又造成了什么樣的結果等等,均須進一步做出深入的研究。
三、余論
20世紀以來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關系研究的成就一如上述,當然也存有種種不足,下面擇其要者提出以供參考:
首先是對心學本身的研究需要更加細致深入。以前學術界過于強調晚明進步思潮的叛逆性質,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將其與明代中期的思想界對立起來。其實心學本身便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比如說以前學術界往往批評晚明士人空談心性,從而導致文學上的內容貧乏與缺乏力度,并認為是心學影響的結果。但王陽明當初提出其心學理論時,恰恰是為了挽救政治危機的。只是由于現實政治的黑暗,使這種救世的學說逐漸演變成士人尋求解脫的理論。心學既然有救世的初衷,便不可能完全放棄教化的目的。以前對泰州學派過于強調其物欲色彩與平民意識,卻忽視其在教化上使儒家學說通俗化的一面。而忽視這些,便不能很好地理解諸如“情教說”、“世情說”、小說以補六經說等等文學思想。同時還有心學思潮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以前往往更強調二者的相互支持作用,卻經常忽視其相互間的負面影響。如心學越來越趨向享樂與自適的性質,最后甚至發展到避政治而不談,與城市中日益腐化的風氣有無關聯。這又牽涉到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如果當時果真產生了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具有進取意識與奮斗精神的資本主義,又何以會只對傳統倫理產生破壞作用而缺乏必要的建設性等等。這些問題如不深入研究,勢必會影響對心學性質的認識。
其次是心學與文學思想內在關聯問題。20世紀以來本論題的研究大體呈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是以唯物與唯心看待心學的復雜現象,當學術界將心學定性為主觀唯心體系時,就理所當然地更強調其對文學的負面影響。近20年來對心學的研究深入了,認識到它在明代歷史進程中的廣泛而復雜的影響,自然也就更關注它對文學影響的復雜性。但更多學者還只是停留在外部種種現象的類比,或者說還只是將心學作為文學思想發生的背景因素加以介紹,而缺乏二者之間內在關聯的研究。我以為對本論題的研究應進入第三階段,即對心學與文學思想進行審美方面的關系研究。一方面研究心學在哪些層面擁有審美的品格,并如何具體滲透到文學領域;心學又在哪些層面不具備審美的品格甚至具有與審美對立的性質,這些特性在進入文學領域后又是如何對文學的審美產生負面影響的等等。
其三是要更注意學科間交叉性的立體研究。這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史哲相關領域的交叉。以前的文學研究在涉及相關領域的知識時,往往是借用該領域學者所取得的成果,而較少親身進行這些研究。當然,了解并吸收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是任何學者都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在學科劃分日益細密的現代學術界,更少不了借用其他領域的成果。但由于心學與文學思想關系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從事研究的人員必須擁有廣博的知識背景與文史哲綜合研究的能力。因為其他領域的研究很少去留意其研究對象與文學審美的內在關聯問題,而這種關聯又決非不同領域成果的簡單對比,研究者必須對所牽涉的領域進行深入的研究思考,擁有自己的學術發現與獨立見解,才能得出真正有價值的學術結論。任何借用都不能代替自己的研究,因為這樣可以減少盲從而擁有自身的真實學術判斷。比如以前學者談明代文學的解放思潮必先談資本主義萌芽,仿佛這是個不證自明的真理,所以不假思索就將其作為論 證的前提,可又有誰去認真考察一下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存在,甚至它是否是一個真命題?又如對心學的發展階段的認識,幾乎都遵從嵇文甫、李澤厚等所描繪的既定學術范式:王陽明——左派王學——李卓吾,但有誰認真想過,王畿是左派王學嗎?王學的發展果真如此簡捷明快嗎?另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即使研究的問題大致相近,但所關注的對象與角度卻又是不同的。比如說唐順之是被黃宗羲列入《明儒學案》的心學人物,但幾乎所有的哲學界學者都未將其作為研究對象,文學界要談唐順之的心學思想也就無從借鑒,于是對唐順之“本色論”與唐宋派的關系問題也就是一筆糊涂帳。可以說,文史哲綜合交叉的研究能力是心學與文學思想關系研究的基本前提。二是各文體間的交叉研究,心學對文學的影響應該說在各種文體間是不平衡的,如果只關注一種文體就有可能忽視了很重要一些方面。比如湯顯祖,他在詩歌上近于六朝之華麗,在戲曲上更注重文采,在散文上則更能顯示其心學的意識與政治的關注,在文學觀念上則更強調心之靈氣與才氣,如果只看到湯氏在戲曲方面的特點,就會得出他重愛情自由,反封建禮教的結論,但如果結合其他文體的特征,就會知道他所說的情不僅指男女愛情,也兼指用世熱情,同時還指生生之仁的生命力。又如馮夢龍在“三言”創作中強調通俗與教化,可在民歌與文言小說領域卻又強調“情教”的觀念。只承認任何一方均不是馮氏之全部,而將二者結合起來,尤其是用其“情教”觀念去研究其婚戀小說,那將會是另外一種結果。
上述三點我以為對研究心學與明代文學思想的關系都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更具體的問題,則已在論述各部分時略有涉及,茲不贅述。
注釋
①②③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12頁,第16頁,第50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④⑤李澤厚《美的歷程》第234頁,第2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⑥⑦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46頁,第252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⑧如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第四章及周偉民《明清詩歌史論》第三章均作如是處理。
⑨黃宗羲《明儒學案》第78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見宗志罡編《明代思想與中國文化》第59—71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見張晶《審美之思——理的審美化存在》第418—429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
12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1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49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4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第292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見《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二章第三節。
16《文藝研究》1999年增刊。
17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238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18《文學遺產》1996年第3期。
19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452頁。 20《金陵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21馬積高《宋明理學與文學》第180頁,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2潘運告《沖決名教的羈絡》第79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3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246頁。
24劉季倫《李卓吾》第11頁,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25見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第三章第一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27成復旺、蔡鍾翔、黃保真《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三冊第179頁,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8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下冊第197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29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第68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30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250頁。
31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第117—129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32《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明代卷》第4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3袁中道《珂雪齋集》第7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4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924頁,1982年版。
35鐘林斌《公安派研究》第48頁,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6宋克夫、韓曉《心學與文學論稿》第18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37孟憲明《“王學左派”與公安三袁的反復古主義文學觀》,見張國光、黃清泉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123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38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第366頁。
39韓經太《理學文化與文學思潮》第259頁。
40成復旺、蔡鍾翔、黃保真《中國文學理論史》第256頁。
41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第283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42吳兆路《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第95頁,臺灣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
43黃清泉《略論‘性靈’說與明中后期文化思潮》,見張國光、黃清泉編《晚明文學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7頁。
44陳文新《明代詩學》第183、184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5周群《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第227、228頁。 46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想》第132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47《南開學報》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