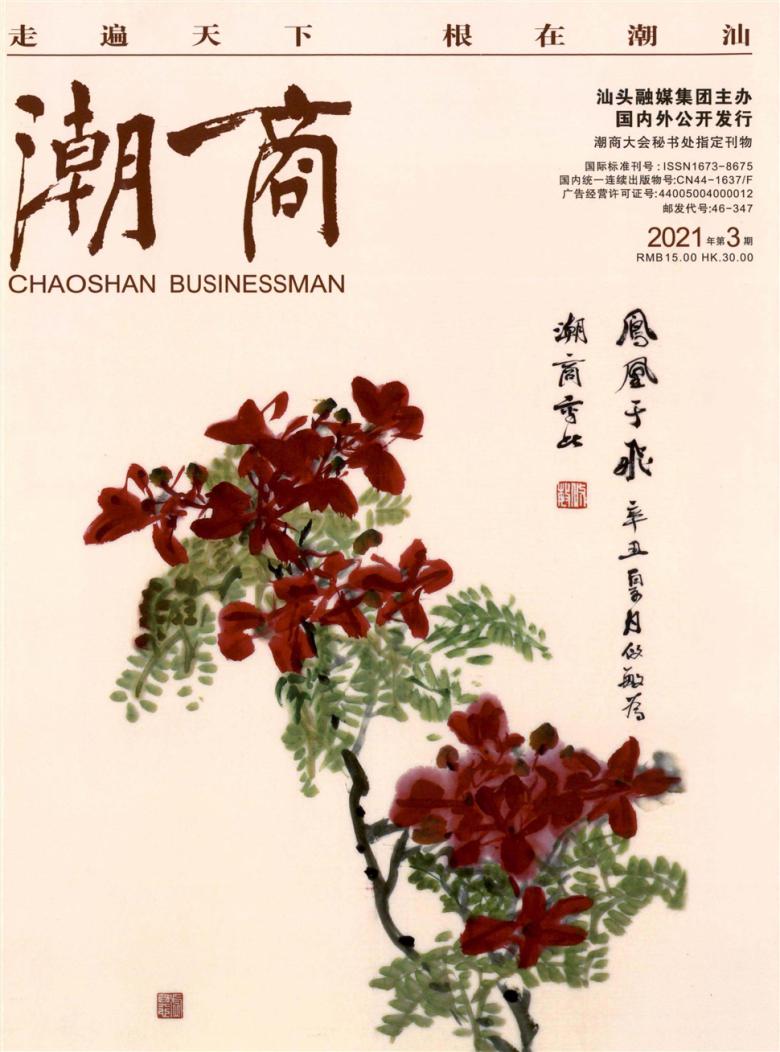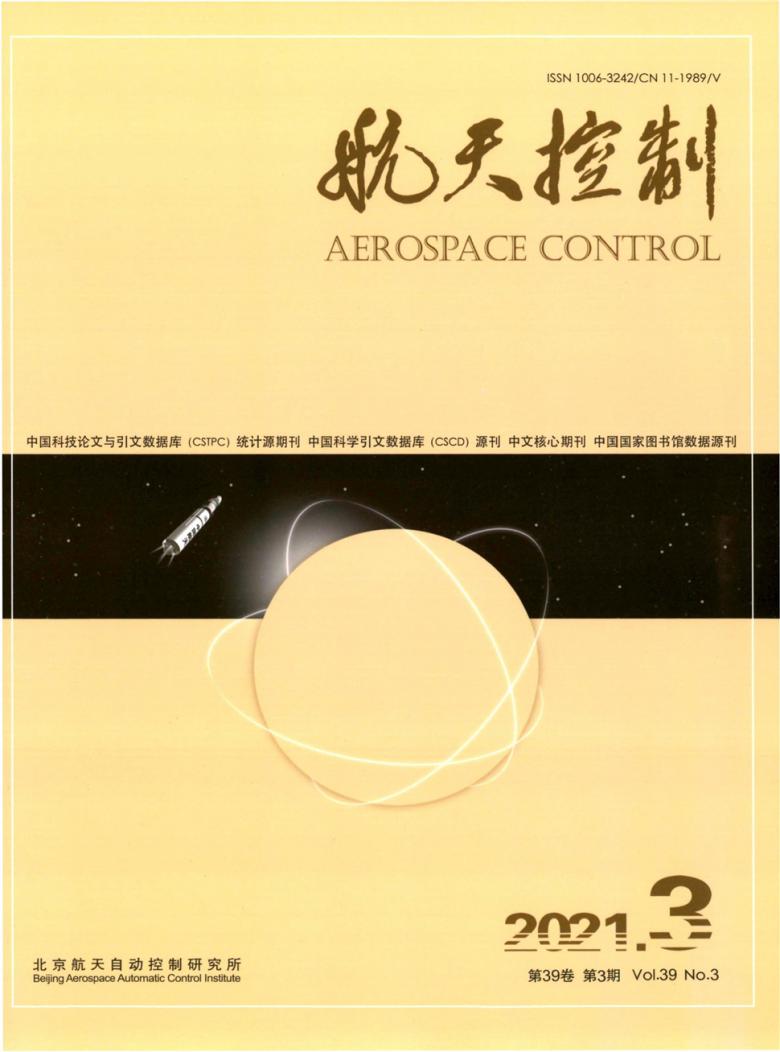論北朝散文之特征
徐中原
[摘要]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探討。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這兩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
[關鍵詞] 北朝散文;質樸剛健;實用性 關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學史家對之雖有概括,但他們的觀點基本上都脫胎于唐代魏征的說法,而且對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現缺乏探討。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討論。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 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 關于北朝散文的文風,最早加以明確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較南北朝文學最繁榮時期的南北文風差異曰:“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并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1]魏征指出了這一時期北朝文學具有“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的特征,也就是質樸剛健的風格特色,這也適用于整個北朝散文。 今天的許多研究者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中得出結論說:“從散文來看,北朝尚質,亦甚明顯,貞剛之氣,時有可觀。”[2]譚家健在《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對比南北散文風格之異時說:“北朝文章以散體為主,求實、尚質,風格剛健清新;與南朝文章崇駢、尚文,風格柔和綺靡有明顯區別。”[3]王鐘陵先生比較南北朝文學的優長說:“文學藝術的發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個落后的民族的許多創作,往往并非一個遠為先進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畫描寫、聲律對偶等方面的精致,無疑是藝術上的進步,北朝文學在這方面遠不及南朝,但它質樸渾厚的氣韻又遠超于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無疑,王先生實際上肯定了北朝質樸渾厚的文風。 在北魏前期的一百年里,散文基本處于沉寂狀態,散文語言總體說來質木少文,甚至談不上文采。直到孝文帝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改革以后,帝王好尚文學,文士們向南朝學習創作技巧,追求審美化,散文發展才獲得轉機,但直到孝明帝時才出現“綜采繁縟”之文。但北朝散文的文采、聲律等形式,與南朝的精美化、雕琢化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西魏時期和隋初的散文,由于西魏宇文泰、隋朝楊堅改革浮華文風,鑿雕為樸,導致這兩個階段的文風重返質樸,藝術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弱。就是在東魏北齊時期,在散文創作技巧上雖與南朝不相上下,但還比不上南朝文的精巧流轉。因此,王鍾陵先生指出:“南朝文風在講究文字之美上是遠超于北朝了。”[5] 質樸剛健也表現在創作構思等技巧上,就拿賦作為例:“抒情言志較少依傍外物,而是直抒胸臆,在十六國和北朝賦中表現尤為顯著……這是北朝文風直質樸實的表現,也反映了北朝賦的總體藝術水平不高。”[6]曹道衡指出:“北朝文人……在作品中往往能直率地表露自己的觀點,很少使用隱晦曲折的手法。”[7]曹氏所論也是再說明北朝散文質樸剛健的文風。 質樸剛健也表現在北朝散文的內容上。整個北朝散文反映的社會生活始終是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的,很難發現像南朝那些純粹“吟風雪,弄花草”,甚至“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8]的作品,更沒有低級的色情成分。即使有人偶爾為之,也會被指責而加以矯正,如北齊的王昕“好詠輕薄之篇”、隋初司馬幼之“文表華艷”都被治罪。遑論那些以治國為宗旨的軍國公文、宮廷詔誥以及大臣章表等應用文字,就是一些抒情文字和山水文字也充滿貞剛之氣。北朝山水文總是突出山水雄奇之壯美,而南方山水文則多表現山明水秀之優美;“南朝作家對山水的描繪沒有停留在微觀上,而是力求形成意境,以意境涵蓋全篇;而北魏山水文由于初起,手法上還顯得嫩稚,于山水的描寫上偏重于客觀描寫,意境構成不足”[9]。就抒情文而言,北朝散文多感情真摯、感蕩心靈之作,特別是那些書信散文如《為閻姬與子宇文護書》、《閻姬母書》,在形式上實無“文”可言,但千載之下讀之,無不為其情真而折服。相反,“終南朝之世,并沒有出現強烈地激動人心或者深刻地感染人心的作品,作家所追求和創造的,大抵是那種精致、華麗和輕柔之美”[10]。相對于北朝散文的質樸剛健,南朝散文顯得浮靡而柔弱。 形成北朝散文特有的文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學、文化上的,也有民族風尚上的,又有地理上的等等。 首先,北朝散文乃至整個北朝文學發展的基礎極差,起點很低,幾乎是在文學的沙漠上開始發展的。由于歷史的原因,西晉末大批中原士人南渡,十六國時期連年干戈擾攘,致使北魏散文和一直向前發展的魏晉文學斷裂開來,致使北朝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積累。而南朝則不同,上承魏晉深厚的文學積累,沿著魏晉以來重形式美的方向,踵事增華,變本加厲。 第二,整個北朝的藏書很少,這使文士失去了豐富學識和借鑒前人創作經驗以提高寫作技巧的機會。《隋書》對整個北朝藏書情況統計說:“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于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后齊遷鄴,頗更搜聚,迄于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后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才至五千。”[11]可見,北朝藏書的總數才達一萬五千卷。而南人私人藏書往往上萬,有的甚至比北朝藏書的總量還多。如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莫比”[12],任昉“于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13],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14]。 第三,北方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以及與此相伴的崇尚樸素節儉的生活風尚也是形成質樸剛健文風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如果她是積極向上日益強盛的,那么她的生活態度一般是勤奮節儉的;如果她是從繁榮走向衰落的,那么她的生活態度一般是享受的奢華的。北朝人大都尚儉節用,體現出積極向上的奮發精神。北朝由于多有戰亂,致使經濟遠落后于南朝,又加之特有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要求北朝士人崇尚節儉又積極進取。《顏氏家訓·治家》:“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5]即使是位居最上層的統治者,他們絕大多數也以節儉為美,身體力行。而且北方的帝王多有勵精圖治、統一天下的宏遠抱負,如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和孝文帝,北齊的高歡、文襄帝以及北周宇文泰、周武帝,還有隋文帝等等,而在南朝卻很難找到這類懷有宏圖大志的帝王,相反,“統治集團很少有宏圖遠略,惟以保持一時的安定承平為治國的根本方針”[16],“士大夫們的奢侈淫逸,大約也不是個別現象”[17]。仔細考察一下北朝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從北魏至隋朝,北朝經歷著一個不斷強大直至統一南北的過程,而南朝則是經歷了一個不斷被削弱被蠶食直至滅亡的過程。南北間不同的生活風尚和民族精神,產生了不同的審美取向,反映在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風。 第四,南北人的民族情愫剛柔不同,也會對文風產生影響。《顏氏家訓·風操》:“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18]“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19]北朝人的性格粗獷、豪放,和長期與少數族融合以及戰亂頻生的社會環境有關。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指出:“南方的情感是柔弱的,偏于個人的享樂,北方的情感是雄壯的。”[20]南人情感脆弱,北人情感則剛強,反映在文風上則南朝文柔弱,北朝文則剛健。 第五,質樸的文風也受北朝的學風和宗教的影響。無論北朝的儒學,還是北朝的佛學和道教都有素樸、重實用的特點,與南朝重義理探尋的學風不同。《隋書·儒林傳序》指出了南北學風的差異:“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21]這種學風的差異和南北朝玄學的發展不無關系。北朝幾乎沒有玄學,只有個別人感興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盧元明、北齊的杜弼、陽烈,終整個北朝都沒能形成風氣。而南朝則不同,南人繼承了魏晉以來對玄理的好尚之風,以致對玄理的追求發展為士人高貴身份的象征,這樣崇尚玄學便成了風靡南朝的社會風尚。許杭生在《魏晉玄學史》中指出:“北方的學風趨向樸實,帶上了漢代經學的遺風。南朝則繼承中朝清談玄風,崇尚玄理之學。與之相應,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業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規模的建寺造像和開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則較多地受玄談的影響,側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22]湯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實用的特點說:“自孝文帝提倡義學以還,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譯經講論之事頗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故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功,為北朝佛法之特征。”[23]南北道教也明顯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論其主張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個人的修煉成仙,長生不死,和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學說似很少直接聯系”;而北朝“寇謙之則要輔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兩者顯然不同”[24]。 第六,北朝散文質樸剛健的風格與北方特有的地理環境也有一定關系。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音辭》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25]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環境,一方面會影響特定的審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風物經過作家審美觀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現出雄壯剛健的文風。 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 北朝散文的另一特征是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北方人對政治盛衰的關心則遠遠超過南方”[26],“北朝文以筆札之文為主,文士創作重視經史之文及軍國實用文體”[27]。嚴可均所輯《全后魏文》共收錄散文一千三百余篇,而純文學的賦作包括存目在內約四十篇,還不到總數的3%(其中還有一部分歌功頌德一類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字),其余絕大多數都是實用性的章表奏議書檄碑志頌啟等文章。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貫穿北朝始終的關于對文章的看法是偏向于文章的實用性,即以表現儒家思想、研究儒家典籍的文章和軍國文翰為文章之首。”[28]這些文章毫無疑問具有極強的實用性,甚至就連表現心性的賦作也不能例外。北魏后期,由于政治混亂、社會黑暗,便產生了一些反映黑暗的社會現實、表達作家不滿情緒的賦作,如李騫的《述身賦》、《釋情賦》、陽固的《演賾賦》,元順的《蠅賦》等。北朝四部散體文著作,代表了北朝散文的最高成就,都具有很強的實用性,正如范文瀾所指出的:“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實用。”[29]如酈道元的《水經注》本是地理著作,由于其描寫山水相當出色,因而又是山水游記散文;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記錄北魏洛陽佛寺興衰歷史的史傳散文;《魏書》本身就是史書,同時也是優秀的史傳散文;顏之推《顏氏家訓》是家誡類文字,是為教育子孫如何“安身立命”而作。北魏初中期、西魏以及隋初是北朝散文表現政治性、實用性最為突出的時期,占據了北朝歷史的一大半的時間。北朝散文雖然隨著南朝文風影響的加深,以及北朝作家審美意識的逐漸自覺,其審美化程度也隨之提升,但始終沒有忽視文章的實用價值。 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北朝以儒學治天下,而儒學的精義在于經世致用,要求文學具有很強的政治功利性和實用性。正如前面在北朝散文發展的動因一節所述,儒學在北朝一直興盛不衰,帝王們大多好尚儒學,士人們也多治經。《隋書·儒林傳》指出了北朝儒學興盛的情狀:“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30]趙翼指出:“六朝人雖以辭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尚多專門名家。”[31]“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學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爭務于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勝,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32] 其次,北朝經濟落后,不允許文士創作不切實際、不關現實的文章。由于北魏經濟落后,以致百官無祿。例如,高允雖在朝廷為官,但“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采自給”[33],至太和八年才準備頒祿。北朝這種艱苦的生存環境,“是不允許北方民族脫離生存的現實,作玄思冥想和浮光蹈世之舉的客觀基礎”[34]。梁啟超頗有見地地指出:“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余裕以馳騖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35] 第三,北朝人在文學觀念上,重視文學的實用性,反對不關實用、浮靡空洞的文風。顏之推對實用性的文字大加肯定,代表了北朝人重實用的文學觀:“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36]相反,他反對尚虛談、重娛樂的文字,曰:“至于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余力,則可習之。”[37]又曰:“士君子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38]隋開皇四年,隋文帝楊堅改革文風,主張“公私文翰,并宜實錄”[39]。接著,李諤又批評那些不關風教之文,說它們是“良由棄大圣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40],顯然他們也是持政治功利性的實用文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