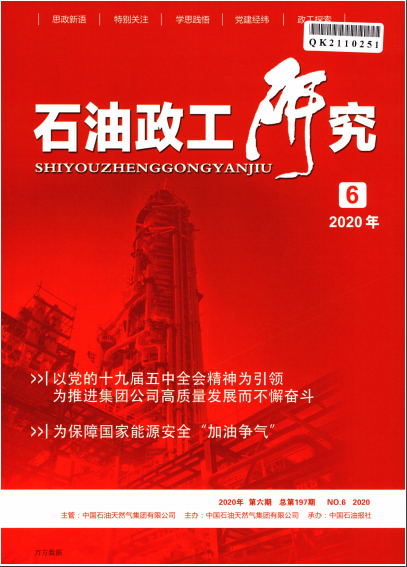關于回歸與超越:論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的雙重特征
涂慕喆
摘 要:現代浪漫主義思潮在三十年代并未消失,而是處于一個轉型期。本文以廢名、沈從文、郁達夫三十年代的小說創作為例,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呈現出在詩性傳統飛揚中的回歸與現代性追求中超越的雙重特征。
關鍵詞:詩性傳統 浪漫主義思潮 回歸 超越
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思潮在五四時期形成高潮,到三十年代在民族解放革命斗爭的時代主題下而逐漸消退,左翼文學成為文壇主流。但浪漫主義并未消失,而是處于流變中的轉型階段。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思潮凸顯傳統文化詩學元素,尤其是以廢名、沈從文、郁達夫的小說創作最為典型,呈現出詩性傳統的飛揚與現代性追求的雙重特征。
一、回歸:詩性傳統的飛揚
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思潮發端于20世紀初,隨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譯介,浪漫主義在五四時期形成一股創作潮流,早期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多受到西方雪萊、濟慈、華滋華斯等西方浪漫主義作家影響,帶有濃郁的傷感與抒情色彩。“中國現代文學田園浪漫主義在承認其受到了西方浪漫主義自然觀念影響的前提下,它更多的是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甚至哲學傳統的回歸——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有著豐厚的關于自然、田園和文學的積淀。”
三十年代,浪漫主義從中心走向邊緣,正如陳國恩所說“五四浪漫主義通過另一條途徑,即由廢名、沈從文和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郁達夫的藝術探索,發展出新的浪漫主義形態,并且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 這種新的浪漫主義形態,實質上正是向中國古典詩學傳統回歸的自覺追求。它表現為含蓄悠揚的詩性語言,空靈澄澈、虛實相生的美學意境,以及道法自然的哲學理想,在三十年代的廢名、沈從文、郁達夫的作品上表現的尤為突出。
無論是抒情小說也好,或者是詩化小說,語言的詩性特征是向傳統詩學回歸的重要標志。中國古典詩歌語言講究含蓄,講究意象,講究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宋代文學理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總結唐代詩歌的特征時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廢名三十年代的小說語言具有鮮明的詩性特征,他自己曾說“我寫小說,乃很像古代陶潛,李商隱寫詩,”“就表現手法說,我分明受到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例如,在他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橋》中,小說語言呈現出鮮明的詩性特征,詩句與小說敘述語言融為一體。“他仿佛是一眼把這一塊大天地吞進去了,一點也不流連——真的,吞進去了,將來多讀幾句書會在古人口中吐出,這正是一些唐詩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邊樹若芥”。又如“老兒鋪東頭一家茶鋪站出了一個女人,琴子心里納罕茶鋪門口一棵大柳樹,樹下池塘生春草。”
詩性傳統回歸的另一重要層面是小說呈現的意境,在這一點深得中國古典詩歌的要旨。在廢名、沈從文、郁達夫的小說中都呈現出優美空靈、晶瑩澄澈的意境,他們筆下的鄉村故土流動著靜謐安詳、單純和諧的自然韻律,猶如一幅幅空靈淡遠的寫意畫,天光云影,水流花開,遠山含翠,竹韻清響。他們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如嬰兒般純真無暇。這里洗滌了現代工業文明的繁蕪與喧囂,回歸自然的淳樸與寧靜,在詩意盎然的文字里將讀者帶入遠離世俗的世外桃源。無論是廢名的黃花翠竹的史家莊,還是沈從文翠色逼人的邊城,郁達夫的桂花飄香的翁家山,其間的意境足以美的讓人流連往返,不知歸路。
小說中自然景色與人物心境的相交相融,呈現出物我相融,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美的意境。正如宗白華所說“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即美學上所謂的‘靜照’,靜照的起點在于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呈現著它們各自的充實的、內在的、自由的生命。”空靈的意境來源于藝術心靈的靜穆觀照,如莊子所言“致虛極,守靜篤”。廢明筆下的鄉村景色,淡雅宜人,清新自然,“春天來了,林里的竹子,園里的菜,都一天天綠得可愛。”郁達夫寫月光下的翁則山,“從樹枝里篩下來的千條萬條的銀線,像是電影里白天的外景。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許多秋蟲的鳴唱,驟聽之下,滿以為在下急雨……一種空山秋夜的沉默的感覺,處處在高壓著人”寫清晨,“早晨的空氣,實在澄鮮的可愛。太陽已經升高了,但它的領域,還只限于屋檐、樹梢、山頂等突出的地方。山路兩旁的細草上,露水還沒有干,而一味清涼觸鼻的綠色草氣,和在桂花香味之中,聞了好象是宿夢之中也能搖醒的樣子。”沈從文寫黃昏“黃昏來時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陽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寫鄉村的氣息,“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飄揚的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的山果香味,有甲蟲類的氣味,有泥土氣味。”鄉村田園,山川草木,在他們的筆下充盈著生命的鮮活,跳躍著自然的韻律,人與自然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匯中綻放出神韻的光輝,剎那間讓人領悟到生命的美好,自然的偉岸。
詩性傳統第三個層面,在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上表現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儒道釋的回歸,尤其是禪宗思想和老莊道家精神,在廢名、沈從文、郁達夫三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們在題材上避開社會革命,關注鄉村田園里那些平凡的小人物,關注他們的生命自在自為的存在,或徜徉在黃花翠竹的禪宗世界,或試圖建立希臘的人性小廟,或留戀于道家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的虛靜境界。
在向傳統文化回歸的道路中,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思潮中,廢名無疑是走的最遠的一個。他的小說《橋》中充滿了禪的意味。《橋》并不在意故事的情節,而主要通過小林、琴子、細竹三人青梅竹馬的生活,在騎馬折柳、對詩論禪,拈花微笑中傳達出禪宗的無相無我,見性成佛,因緣合和。比如他在《橋》中一處寫細竹,“細竹一回頭,非常之驚異于這一面了,‘橋下水流嗚咽’,仿佛立刻聽見水響,望她而一笑,從此這個橋就以中間為彼岸,細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風采,一空倚傍。”
如果說廢名是沉浸在禪宗的世界中探詢悟道,那么在郁達夫和沈從文那里,更多是傾向于老莊道家精神。在郁達夫三十年代的重要代表作《遲桂花》中,我們能體會到一種洗滌塵埃的清澈明朗,自然率真,復歸于嬰兒。情欲在女主人公的純真中凈化為純潔的友誼,人性的美好如遲開的桂花香沁人心脾。而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里,更體現了老莊道家所追尋的“道法自然”,生命的愛與恨,美麗與憂愁都是自在自為的呈現出來,人的原始天性和生命強力在湘西淳樸的民俗風情和美麗的山水間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與自由,人與自然在兩相望中兩相忘,進入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總之,在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中,詩性傳統的飛揚使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呈現出與五四時期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向中國傳統文化回歸的凝望中,中國古典詩學傳統在新的時代和新的體裁中散發出新的活力與光彩,含蓄悠揚的語言、空靈澄澈的意境與儒道釋的再現,使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詩意盎然、余味無窮的一章。
二、超越:現代性的追求
如果說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在詩性傳統的飛揚中完成了一次對古典詩學的回歸,那么在五四以來啟蒙和救亡的雙重時代主題下,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思潮則又在現代性的追求中努力追尋對詩性傳統的超越。在廢名、沈從文、郁達夫三十年代的小說中,在充滿詩意的表層敘述中,在遠離都市現代文明的古樸鄉村大地上,在看似和諧寧靜的田園牧歌里,依然涌動著生命最初的傷痛和揮之不去的哀愁。悲劇精神的彰顯、人性深度的叩問以及對終極價值的探詢成為這一時期浪漫主義思潮中現代性的重要表征。
中國古典文學中幾乎沒有純粹的悲劇,在禮樂互補、天人合一的靜穆安詳氛圍中消退了個體的真實性情和悲劇精神。正如宗白華所說“中國人感到了宇宙全體是大生命流動,其本身就是節奏與和諧。人類社會生活里的禮和樂是反射著天地的節奏與和諧,一切藝術境界都基于此。但西洋文藝自希臘以來所富有的悲劇精神,在中國藝術里卻得不到充分的發揮,又往往被拒絕和閃躲。人性由劇烈的內心矛盾才能發掘出的深度,又往往被濃摯的和諧愿望所淹沒。”
中國現代文學從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始,打破了傳統禮樂的和諧,時代激情的統領和悲劇意識的加強,使現代文學中的悲劇精神大大彰顯,即使在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的溫情敘事下,也依然涌動著悲劇的暗流。這里的悲劇不是西方那種尖銳的矛盾沖突,或是英雄的悲壯行為所引發的流血犧牲,而是平凡人物在時空流轉的平凡生活里所遭遇的無可奈何的蒼涼和痛楚,是個體生命在強大的自然和無法預料的命運前的弱小和無力,是個體生命意識覺醒后要求個性解放思想解放所帶來的兩難困境。在廢名的《橋》里,小林和琴子、細竹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朦朧情感,攙雜著時間和空間阻隔所帶來的最熟悉的陌生感,橫在他們之間的不僅僅只是一座橋,在此岸和彼岸之間,是時光無法流轉、再也回不去了的悲涼,無法渡過的正是這樣一座橋。而在沈從文的《邊城》里則更籠罩著一種美麗的哀愁,正如李健吾所說“自然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罩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久的原則:悲哀。深切的悲哀感里彌漫著人性的善良與命運的殘忍。郁達夫的《遲桂花》中,小說女主人公的不幸婚姻正是那個時代女性命運的縮影,醒來后的無路可走,在含淚的微笑里卻隱藏著最深的傷痛,可以逃離婚姻的枷鎖但卻難以走出一條女性自己的道路,正如一個多余的人,世界如此廣大,卻找不到可以從容安放心靈的地方。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思潮在詩意敘事下貫穿著強烈的悲劇精神,即伴隨著人的主體性的確立、生命個體意識覺醒所帶來的張揚生命與壓制生命的外在矛盾,悲劇主人公對個人加之于生命意義的堅守。當生命的過程被偶然的事故、兇狠殘暴的手段、或某種專制所切斷,悲劇的延續性卻依然滾滾向前,永不停息,正如《邊城》的結局,那個人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 悲劇精神的彰顯打破了古典詩學傳統的追求靜穆和諧的審美風格,而五四以來呼喚人的個性解放,呼喚自由、平等的現代意識的注入,則使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思潮閃現著人性的內在深度,對人的關注、對人的存在及生命意義的追問與探詢成為作品關注的所在。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鮮明的地舉起人文理想的旗幟,“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地說一句,是‘人的文學’”“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人成為新文學關注的中心,敢于正視人性靈與肉的沖突,表現人性的復雜,挖掘人性的內在深度,這一新文學的主旨仍貫穿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思潮之中,尤其以沈從文湘西小說中表現的最為突出,表現了他對“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向往與呼喚。他試圖構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廟宇,用生命最原始、最淳樸的善與美譜寫一曲悠揚婉轉的性靈之歌。在《柏子》里感受到的是充滿陽剛之氣的男子力量,在最本能的欲望滿足中揮灑著生命的激情,用最純粹的情欲照亮黑暗艱辛的生存之路,沒有掩飾、沒有虛偽,一切在自然的狀態下呈現出生命最本真的欲求。在《丈夫》里,生存的困境迫使妻子出賣肉體以養活家人,而丈夫則默默的承受著屈辱,終于那僅存的一點丈夫的尊嚴喚醒了他,“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去,兩只大而粗的手掌捂著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丈夫的委屈、自責、懊悔、辛酸都在這孩子般的痛哭中釋放出來,長久的壓抑下乃是人性的扭曲與變形。最終的結局丈夫和妻子回到了鄉下,這也正揭示了對于人性常態回歸的渴盼。在向內在人性深度的探詢中,沈從文始終堅守營造人性希臘小廟的人文理想,追尋生命的自為自在,生命的伸展自如,釋放外在強加的壓力,做最純粹的自然之子。他筆下的一系列人物,無論是掙扎在生存土壤上的士兵、水手、妓女,或者純真如三三、翠翠、蕭蕭的少女,都閃耀著一種健康、優美、率真的人性之光。
對人性深度的叩問是現代文學永恒的主題,而對終極價值精神家園的追尋則是文學在哲學價值層面的體現。三十年代浪漫主義的詩性言說里,作家們一次次返回鄉村故園,在故鄉的自然風景與人事滄桑中,尋找慰藉心靈的精神家園。海德格爾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對這種本源的接近,決非其他。所以,惟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這乃是命中注定的。”由此,海德格爾提出“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在鄉村故土的大地上,尋找靈魂安居的所在,而無家可歸恰是安居的真正困境。在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創作中,彌漫著這種尋找精神家園的焦慮、迷茫乃至憂傷。“浪漫故事所循環呈現的童性,表現為持續不斷地懷舊情緒,以及對時間空間里某種想象中的黃金時代的執著追求”一方面,作家筆下的鄉村仍流淌著田園牧歌的悠揚情調,展現鄉村的寧靜,人情的淳樸,寄托了對理想家園的緬懷和依戀,乃至一種不能自已的深情。另一方面,這種深情里也包含著失落和惆悵,傳統宗法制的鄉村不可避免地受到現代文明的浸染,人與人、人與自然在表面的和諧中正暗藏著金錢、權利、地位所帶來的矛盾與沖突。即使在廢名的黃花翠竹、遠離塵埃的鄉土世界里,依然隱現著現代都市浸染下鄉村道德的某種淪落。《菱蕩》中擺渡不再是一種方便村民的善舉,而成為一種謀生賺錢的手段,所以陳聾子認為張老漢無法升天。同樣,在沈從文的《邊城》里,圍繞一座碾坊的展開的故事,猜測或謠言,也正說明金錢利益正一點點吞噬了古樸的民風。盡管鄉村田園已不再如理想中的完美,但鄉村仍然是作家們找尋精神家園的終極所在,在鄉村的大地上可以找尋到生命誕生時最初的力量與純凈,人性的真善美,一切美好事物的本源。
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在對現代性的追求中呈現著對詩學傳統的超越,在悲劇精神的彰顯、人性深度的叩問及精神家園的追尋中,將浪漫主 義從飛揚的天空帶回現實的大地,從而完成了浪漫主義思潮從中心到邊緣的轉型。
三、結語
從回歸與超越兩個維度來考察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復雜性和流變性。一方面,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繼承了中國古典詩學的藝術傳統,表現為含蓄而意味無窮的詩意語言,追求空靈悠遠的意境,以及對傳統文化儒釋道的回歸,使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淡化了五四時期過于西化的印記,帶有濃郁的中國民族特色,在西方文學思潮與中國本土民族文學中找到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另一方面,這種回歸不是淺層面的復古或模仿,詩性言說中仍帶有超越的一面,融入現代意識和現代性的追求,在鄉土田園中挖掘人性的深度、展現鄉土人生的社會廣度,作家對恬靜淡泊的田園風光和鄉村淳樸風情的留戀向往,對精神家園的執著追尋,賦予浪漫主義以歷史的厚重和生命的力度。由此,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思潮在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思潮統領文壇的局面中得以頑強的生存,在退居邊緣的時代里依然能讓人聆聽到來自鄉村大地的一首首悠揚的田園牧歌。
[1]朱壽桐.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史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
[2]陳國恩.浪漫主義與20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嚴羽.滄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4]廢名.廢名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5]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郁達夫.郁達夫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7]沈從文.沈從文作品精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8]李澤厚.美學三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3,第288—289頁
[9]中華文學評論百年精華[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0]【德】海德格爾,郜元寶譯.人,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語要.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1]【加】弗萊.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