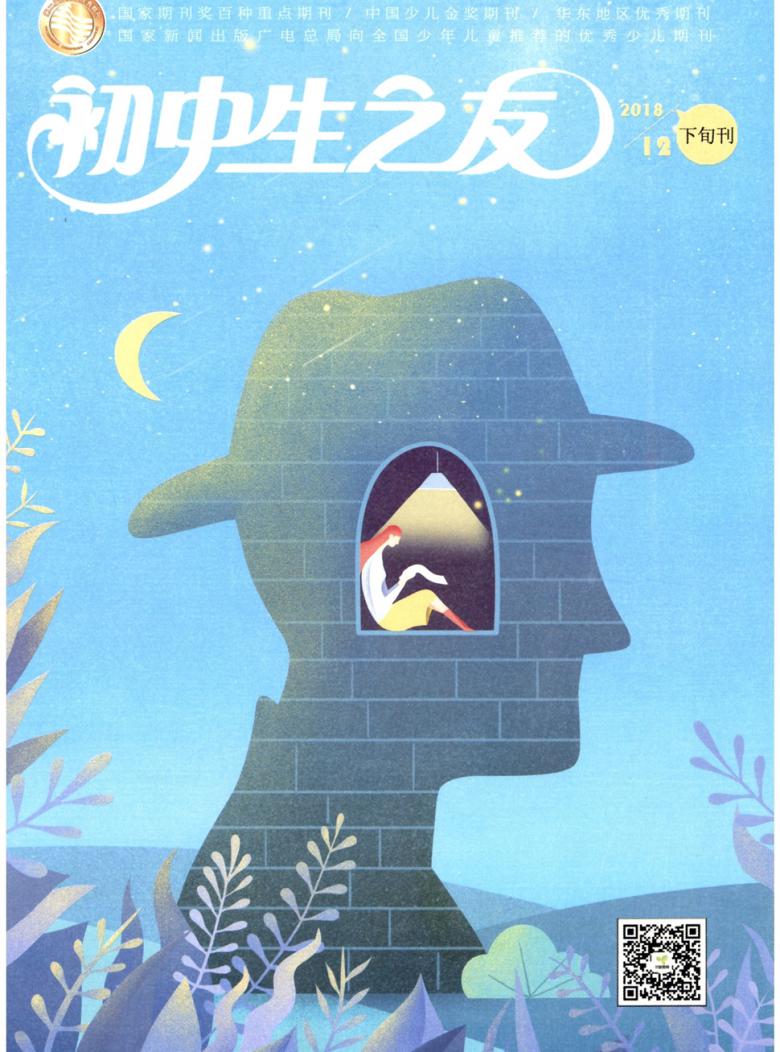論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色
陸永品
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研究莊子的學者,無不認為莊子的散文寫得最生動、最優美、最有個性化特征,因而歷來也最深受人們的喜聞樂見。莊子散文之所以特別受到人們的青睞,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這與莊子其人具有“洸洋自恣”1的氣質及其散文富有濃厚浪漫主義的特色,是密切相關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是中國文學的兩種比較突出的不同的藝術流派。莊子散文可當之無愧地是中國最早浪漫主義文學的杰作,哺育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成長和發展。郭沫若認為,大半個中國文學史都受到莊子的影響,此話并非言過其實。值得在這里說明的是,過去我在研究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時,曾根據高爾基對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的看法,認為莊子散文是消極浪漫主義。現在看來,這種看法未必是正確的。基于此種考慮,本文擬從下面四個方面,對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問題,予以新的研究和探討,即: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新人耳目的寓言故事;熾熱動人的詩人氣質;出乎尋常的夸張比喻手法。
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
先秦諸子散文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一般說來,它的文字大都寫得古樸篤實、簡潔省凈,其中也不乏驚人的奇妙的結構。但是,它的驚人奇妙之處,若與莊子散文相比,卻顯得大為遜色。就莊子散文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而言,不僅在先秦文學中獨樹一幟,即使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顯著的地位。
對于莊子散文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我們為了論述的方便,姑且從其雄奇、險辟、怪誕三點來分析。
《莊子》雄奇宏偉,氣勢磅礴,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莊子》開篇《逍遙游》寫鯤鵬展翅九萬里的寓言,古往今來,曾博得不少評論家的高度贊賞。晉代阮修,曾作《大鵬贊》日:“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鴛鳩仰笑,尺鷃所輕。超然高逝,莫知其情。”2把莊子描寫鯤鵬其大無比,擊水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志存天地,不屑雷霆”,氣勢磅礴,勢不可當,逼真地再現出來。這種雄奇壯闊的意境、宏偉浩瀚的景象,是南華老仙匠心獨運的卓然建樹,為后人留下難得的藝術享受。盡管莊子用此寓言,旨在表現鯤鵬逍遙無為的思想,但在客觀上,卻能“令人拓展胸次”,給人一種“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3的感受。
所以,取師于莊子的唐代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他曾情不自禁地贊嘆說:“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征至(志)怪于齊諧,談北溟之有魚……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吾亦不測其神怪之若比,蓋乃造化之所為。”4所謂“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即高度評價這篇雄文所取得的浪漫主義成就。莊子在戰國時代,竟能以非凡的才智和氣魄,創作出如此高不可攀的藝術佳作,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難怪李白對南華老仙贊嘆不已,驚怪其不知為何,竟然能創作出此等崢嶸、浩蕩之奇言。
清代評論家劉熙載,又用“能飛”來評論莊子崢嶸浩蕩的“神妙”之筆。劉氏說:“文之神妙,莫過于能飛。莊子之言鵬,日‘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5莊子筆法,變化莫測,“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神奇雄偉,豪放灑脫。李白、蘇軾、辛棄疾等豪放派詩人,大多得力于莊子,從莊子那里汲取豐富的營養,才使他們在詩詞文賦方面取得偉大的藝術成就。蘇軾對于莊子,佩服得五體投地。據史書記載,當蘇軾讀《莊子》書時,曾贊嘆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6辛棄疾也深受莊子的影響,他在詩詞中常常征引莊子的語言。他說:“案上數編書,非《莊子》即《老》。”(《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菴即世》)7從這些事實,亦可間接地透露出莊子對后代浪漫主義文學起了積極的哺育作用。
在莊子筆下,出現許多雄奇壯觀的景象,的確令人大飽眼福。雄奇壯觀的景象,在自然界是多有所見的,不足為奇。然而,在莊子筆下出現的雄奇壯觀景象,又不同于自然界所呈現的,它純屬作者豐富的奇特想像,是憑空虛構的奇人奇事奇怪之物。因而《莊子》也就成為天下罕見的奇書。如《人間世》篇,寫齊地有一棵櫟社樹,其大能遮數千條牛,徑寬百圍,臨山十仞而后有枝,枝大能為舟十數。此等奇樹怪木,的確,世上絕無僅有。《外物》篇寫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以五十條牛為釣餌,蹲在會稽山上,投竿東海,旦旦而釣。一年之內,并未得魚。后來。大魚上釣,牽動巨緇,潛人海水,驚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焯赫千里。任公子得此大魚,離而臘之,大半個中國,都飽食此魚。此等雄奇壯觀景象,又是世上罕見。讀者看到此等波瀾壯闊的宏偉氣象,真是大開眼界,嘆為觀止。如若不是作者具有如此博大氣度、廣闊胸襟,是難能孕育出這等氣勢宏偉的篇章的。相比之下,這對于先秦儒家學派的作家來說,只能是望洋興嘆、望塵莫及。莊子寫出此則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寓言,究竟有何意義呢?難道他純屬是胡言亂語、云山霧罩的“侃大山”8嗎?否!劉熙載對莊子的寓言,曾有過精辟的見解。他說:“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里卻盡有分數。”(《藝概·文概))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古代有人認為,莊子此則寓言意義遙深,說:“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9
莊子性格開朗,愛好廣泛,有很高的藝術鑒賞能力。他不僅欣賞宏偉壯觀的大自然景象,同時,他對“警辟奇險”的絕技表演,也有深刻的藝術感受。《達生》篇,寫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不能游。看見一丈人,跳進懸水急流。孔子以為此人,有苦欲死,便讓其弟子,并流拯救。弟子浮游三百步,只見那人,被發行歌,游到水塘之下。看到此情,孔子一場虛驚,方才釋去。如果給予評分,那“丈人”跳水潛游的技能,即使與當今世界體壇跳水名將相比,恐怕也不遜色吧?《田子方》篇,寫列御寇為伯昏無人表演射箭,他引弓搭箭,置杯水在其肘上,箭射出后,肘上杯水點滴不覆。列氏此等高超射技,亦可謂出類拔萃。但伯昏無人卻認為,列氏射箭時,神情猶如“象人”(木偶),“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意謂是有心之射,并非無心之射)。為考驗列氏射箭技術,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讓列氏射他。然而,列氏看到此等驚險境況,已經驚恐萬狀,嚇得伏臥在地,汗流至踵,哪里還有心射箭呢?我們看到伯昏無人此種峻極驚險的鏡頭,就好像身臨其境,觀看一場精彩的雜技表演,獲得一次驚心動魄的審美享受。所以,劉鳳苞評論此則寓言說:“警辟奇險,絕跡飛行,妙有真氣貫注其間,故能使正義分外醒透,非故作可驚可喜之筆,逞其筆鋒舌巧也。”10
莊子筆下,描寫了社會上許多大小人物,各色人等,尤其奇人怪人的形象,更能使人銘記在心,歷歷在目。但是,他筆下的奇人怪人,雖然形象令人可怖,而他們都是得道之人,才智德行超過常人,是道家所謂“至人”的化身。如《人間世》篇,寫一個名叫支離疏的殘疾丑人,其頤頰隱于臍間,肩高于頂,髻高指天,兩腿攣縮幾乎為臂,五臟在上。此人依靠縫衣洗浣餬口;鼓莢播精,可養活十人。國家征召武士,支離疏充數應征。可是,國家發給病員的糧餉,支離疏只領受三鐘,十束薪。作者認為他是個有德行的殘疾丑人,字里行間,都流出贊美之情。《德充符》篇,則好像是一篇怪人奇人列傳,竟然虛構六個殘丑奇怪之人。其一,是魯國的兀者(受刑斷足之人)王駘,弟子甚多,與孔子相等。其奇怪之處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生死不能與之變;天地覆墜,不能與之遺。孔子稱其為“圣人”,拜他為師。其二,是申屠嘉兀者,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此人雖受刑斷足,卻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者認為“惟有德者能之”。其三,是魯國兀者叔山無趾,此人藐視孔子,認為孔子只知追求諔詭幻怪而大出風頭,不知“至人”(得道之人)卻把他當作桎梏。老聃讓叔山無趾勸說孔子,“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解其桎梏。叔山無趾認為孔子是“天形之”,無法解其“桎梏”。其四,是衛國奇丑之人哀駘它,其人雖奇丑無比,以丑惡駭天下,卻能惹人愛戴:“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日:‘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魯國無宰,魯哀公竟以國授之。他雖無君人之位,能救人于死地;雖無聚祿,卻能飽人之腹。其五,是汗跤離無□,無嘴唇,曲體跤行,其脰(頸)肩肩(細竦貌),丑陋不堪。說衛靈君,衛靈君悅之,視若全人。其六,是饔瓷大癭,頸瘤之大,猶如甕盎,其脰肩肩,說齊桓公,齊桓公喜愛非常,視若全人。莊子筆下這六個“以丑駭天下”的丑人奇人,卻都是得道的超人,都有非凡的才能,受到社會的特殊敬重和愛戴。顯而易見,莊子在這些奇人丑人身上,寄寓了道家的理想,他們都是道家的化身。我們看了這些奇人怪人,真能新人耳目,長人識見。對于莊子塑造的這些奇人怪人。其旨意所在,古人早就有評價。宣穎說:“莊子雅尚德充,而特敘列殘丑,以破夫規規者與!”11說明莊子塑造殘丑怪人,其目的是在破除陳腐的道德規范。其實,從藝術思想而言,莊子“意出塵外,怪生筆端”,12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思想特色,在其塑造殘丑怪人形象上,即生動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劉鳳苞在評論《德充符》時說:“憑空撰出幾個形體不全之人,如傀儡登場,怪狀錯落,幾于以文為戲,卻都說得高不可攀,見解全超乎形骸之外。”13高度評價了莊子散文在塑造奇人怪人方面所取得的偉大藝術成就。
新人耳目的寓言故事
《莊子》之書,大都是寓言故事,虛構成分居多。寓言故事,一般都具有寓意深刻,含蓄蘊藉,生動形象,娓娓動聽的特點。莊子的寓言故事,還有其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個性特征,即具有新人耳目的特點。莊子把它的書,分為寓言,重言、卮言三類,其實這三類是一類。胡遠溶就曾經說:“莊子自別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實重言皆卮言也,亦即寓言也。”14此話頗有道理。莊子的寓言故事,究竟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應當從哪幾方面去探討呢?我認為,應當從以下三方面去研究。(一)辛辣冷峭的諷刺藝術;(二)幽默詼諧的人生態度;(三)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
文如其人。莊子為人正直不阿,不媚權貴,不屈于勢利。他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丑惡現象,都能夠使用辛辣冷峭的文字,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前人說莊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把它視為莊子散文的一種鮮明的藝術特色,這樣的評價是比較公允的。,在《莊子》中,說莊子寧愿過貧困生活,也不愿做官,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秋水》篇說:“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日“‘愿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日:‘吾聞楚有神龜,死亦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日:‘寧生而曳尾涂中。’莊子日:‘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這雖然是以寓言形式表達出來的,但卻生動地說明,莊子寧愿過著貧困生活,也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態度。《至樂》篇有則寓言,寫莊子夢見髑髏,髑髏說:“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它生動形象地說明,莊子追求自由、渴望無拘無柬的生活。然而,他的朋友惠施,做了梁惠王的相,由于小人從中作梗,說莊子要去奪取惠施的相位,惠施便在大梁都城搜查三天三夜,表現出非常不友好的態度。莊子得知此事,頗為氣憤,在他會見惠施時,便向惠施講述一則寓言說:“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鶵過之,仰而視之日:‘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秋水》篇)惠施是否會有此等舉動,這是不必深究的。莊子只不過是借用此則寓言,發泄自己的牢愁而已。對此,劉鳳苞曾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實質。他說:“惠子非真有此事,特莊子寓言以醒世耳。”“腐鼠一喻,極雋極毒,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15的確,莊子通過此則寓言,把世間那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鄙夫”的陰暗心理,揭露得淋漓盡致,諷刺何其辛辣!陸西星評論說:“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長笑。莊生直為千古寫出鄙夫鄙怯之態”。16這則寓言的主旨,正在于此。
基于不逐勢利,不愿做官,甘愿過貧困生活的思想,莊子對那種不擇手段,阿諛奉承,而取得高官厚祿、榮華富貴的小人,是深惡痛絕的。《列御寇》篇,寫宋國曹商,出使秦國,阿諛逢迎,大悅秦王之心,得車百乘。他以此夸口于莊子說:“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百乘者,商之所長也。”他這番話,一則諷刺莊子無能,只能身居窮聞阨巷,困窘織屨為生;二則自我吹噓,說自己有一悟萬乘之主,取得榮華富貴的才能。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拙劣表演,真堪稱古今“鄙夫”的典型。對待此等小人,莊子并未施以仁慈,他以牙還牙,給以有力的還擊。他說:“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砥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莊子以辛辣冷峭的深刻語言,諷刺曹商給秦王舐痔,所以才竊得榮華富貴。莊子借用此類小人,“以比今之阿諛茍容、竊取權勢者”17,顯然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家學說與儒家學說,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相互牴牾的。司馬遷曾經指出,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18蘇軾以來,明清學者,出于維護孔子的地位,強說莊子是尊孔的,這除了制造混亂,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莊子對儒家標榜仁義,欺世盜名,是極為憎惡的。《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的寓言,對那些以詩禮為名,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的偽儒,給予了尖刻辛辣的批判。陸西星說:“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余緒,斯不謂之盜儒乎?”(見《南華經副墨》)劉鳳苞說:“詩禮是儒者之所務,發冢乃盜賊之所為。托名詩禮,而濟其盜賊之行,奇事奇文,讀之使人失笑。”陸、劉的評論可謂是頗有見地的,道出了這則寓言的真諦所在。《盜跖》篇,寫莊子痛斥孔子搖唇鼓舌,欺世盜名,蠱惑人心,竟使孔子無地自容,連連下拜。真是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堪稱諷刺文學一絕!縱觀中國文學史,可以說莊子對后代諷刺文學的成長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莊子》中,我們通過類似這樣的寓言故事,不難看到,南華老人不僅沒有脫離現實社會,他對現實社會還是十分關注的。胡文英對莊子的研究有獨到見解,他說:“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心腸熱,故感慨萬端。”19說明莊子雖有消極遁世思想,事實上,他并沒有完全脫離現實社會,過著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生活。相反,他對社會上許多丑惡現象,往往都是憤憤不平,嫉惡如仇的。莊子這種對待政治的態度,恰恰又促進他散文風格的形成。所以說思想和文風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能截然分開。另一方面,通過一些生活和生死問題,我們也能看到莊子的人生態度極其鮮明的藝術特點。人世社會,五花八門,三教九流,紛紛揚揚,熱鬧非常;冷暖炎熱,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真善美丑,應有盡有。人們究竟怎樣才能應付這種繁復雜亂的社會現實,渡過艱難的人生呢?的確,這是一門頗深的學問。莊子對待人生和社會問題,與眾不同,他應對如流,總是以談笑風生,幽默詼諧的態度,輕松愉快地予以對待。在莊子寓言故事中,表現這方面主題的作品并不在個別篇章。《外物》篇寫莊周家貧,去向監河侯貸粟,監河侯是個吝嗇鬼,不愿借給,還戲弄莊周說:“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頗為生氣,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以談笑風生講故事的方式,來諷刺監河侯其為人。莊子忿然作色說:“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日:‘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日:‘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日:‘喏!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鰣魚忿然作色日:‘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寫得很生動,饒有情趣。揭示出朋友之間,平日侃侃而談,似乎親如手足,而一旦遇到危難,卻冷若冰霜。陸西星對此則寓言故事,曾經評論說:“生事蕭疏,窮途仗友,仁者當亟恤之。乃為此紆緩不急之淡,友道之薄,為甚于此。”這對于勢利之交,不講情誼之徒,無疑將是有力的諷刺。
南華老人稟性曠達,所以能視生死如春秋代謝,瀟灑超脫。《莊子》中的許多寓言和議論文字,即足以表現莊子曠達超脫的個性及其幽默詼諧的藝術風格。《至樂》篇寫莊子妻死,莊子不哭。惠子去吊喪,看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感到異常奇怪,于是就問莊子說:“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其實則不然。莊子妻剛死,他本來也很悲傷。后來,他悟出生生死死的道理,就變悲傷為快樂了。所以,他答惠子說:“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元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所謂“不通乎命”,即不懂得人的生死規律。莊子所謂人生的規律,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番道理。在一般人看來,南華老人此等言行舉止,似乎近于滑稽,不近人情。晉代的孫楚就曾經指責莊子說:“妻死不哭,亦何而歡?慢吊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20明代陳榮選表示不同意孫楚的看法。他說:“莊子鼓盆,似不近人情,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于此。”21“應當說,陳榮選別具慧眼,識破了南華老人的天機,真正體會到“莊子妻死”寓言的旨趣所在。徐文長說:“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22則更是撥開千占迷障,還原莊子超脫曠達的人生態度。
即使莊子自己將要死去,他也仍然是談笑風生,置生死于度外,表現出幽默詼諧的態度。《列御寇》篇寫莊子將死,弟子想為他舉行厚葬之禮。莊子反對弟子這種想法。他說:“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吾葬具,豈不備乎?何以加此?”弟子說:“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說:“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在這里,莊子在臨死之前,沒有絲毫貪生怕死的念頭,能夠這樣談笑自如,口出奇言,幽默非常,這種豪放曠達的浪漫精神,真是“天地萬物中,赫赫然有此一人在!”23不愧為是中國文學豪放派的鼻祖。
談到莊子其人,人們總感到他是個神秘而難于捉摸的人物;談到莊子其書,人們總感到太復雜,比較費解。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認為《莊子》書中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也是人們產生這種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莊子》書中這種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又構成莊文比較突出的浪漫主義風格。正因為如此,人們一方面感到《莊子》之書神秘玄虛,一方面又愛不釋手,感到其中有令人咀嚼的濃郁芳香。要深究這個問題,必然就要涉及老子和莊子尊崇的“大道”。他們尊崇的“大道”究竟是何物?說來,這也是個難以論述而帶有嚴重神秘色彩的問題。從本質上而言,老子和莊子都認為“道”是物質的東西。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不僅是物質的東西,老子還認為“道”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不可名狀的東西。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大“道”觀念,認為“道”無所不在,在螻蟻、梯稗、瓦甓、屎溺等一切物質中。而且,認為此“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老、莊所謂的“道”,其神秘玄虛性,由此亦昭然若揭了。在莊文中,就浸透了這種神秘玄虛色彩,因此,它也就孕育了莊子文學的浪漫主義風格。
《天道》篇輪扁斫輪的寓言故事,是眾所周知的。輪扁斫輪,技藝雖然高超,但不能傳授。輪扁聲稱其斫輪技藝:“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其妙就妙在,只能體會,不能言傳。宣穎說此則寓言,正說明“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為也”24。林云銘說:“說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求道者,當于不傳處通之,則幾矣。”25宣、林二氏,皆說明莊文的神秘玄虛色彩。“庖丁解牛”(《養生主》篇)、“呂梁丈夫蹈水”(《達生》篇)、“梓莊削木為鐻”(同上)和“捶鉤者”(《知北游》篇)、“匠石運斤成風”(《徐無鬼》篇)等等所表現出來的出眾技藝,表面上看,在具體操作上與輪扁斫輪不同,實際上它們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旨趣基本是相同的。
莊子散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物化”觀念,實際上又是其“大道”觀念的另一種表現。可以說,莊子的“物化”觀念,從不同的角度,又給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征,增添了許多“弦外之音”和光怪陸離的異彩。《齊物論》中莊周夢蝶寓言,古來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并成為不少文人騷客創作的題材。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此時,莊子已經進入“物化”境界。他感到舒適愉快,竟然忘記自己是現實存在著的莊周。可是,當他忽然覺醒時,又感到自己還是莊周,因此,便驚疑萬狀,不得其解,發出“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的感嘆。事實上,“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所謂“物化”,按照莊子的觀點,這就叫“大道”時而化莊周,時而化為胡蝶,萬物齊一的“物化”現象。《至樂》篇寫滑介叔左肘生柳(瘤)的寓言故事,與莊周化為蝴蝶,同樣都是“物化”現象。死生同狀,萬物為一,即莊子《齊物論》的基本思想。宣穎說:“周可為蝶。蝶可為周,可見天下無復彼物此物之跡,歸于化而已。”26林云銘驚嘆,莊生老人想象奇特,認為“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此,”“意愈超脫,文愈縹緲”27,洋溢著浪漫主義的濃厚感情。直至當代,莊周夢蝶的“物化”現象,為今天作家創作時傳神人化,又提供了借鑒。
熾熱動人的詩人氣質
一般說來,浪漫主義文學家對人生大都充滿幻想,對生活具有執著追求的欲望,對黑暗腐朽社會嫉惡如仇,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大膽揭露的批判精神。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莊子是最典型最富有個性特征的浪漫主義文學家,說他最典型,就是因為他既具有一般浪漫主義文學家的共性,也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個性。他的與眾不同的特殊個性主要表現之一,就在于他具有熾熱動人的詩人氣質。莊子的這個特點,可以從這樣三方面來論述:(一)熾熱動人的詩人感情和豐富奇特的想像力;(二)執著的追求精神;(三)強烈的詩的語言節奏和韻味。
盡管,莊子有時對人生有些冷漠,他似乎看破了紅塵,失去生活的信心,往往表現出消極遁世的思想。正如上面所說,從莊子一生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并沒有真正消極遁世。他對黑暗社會,是大膽揭露和批判的;對邪惡勢力,是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對美好事物,是熱情贊美和歌頌的。莊子懷有一顆熾熱激動的心,在為正義不遺余力地呼喚著、奮斗著。當他看到封建統治階級標榜“仁義”,進行罪惡活動的時候,他竟是那樣無比憤怒,揭露他們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肱篋》篇)他認為,世上之所以會出現“盜賊”,就是那些自稱為“圣人”、“圣智”的統治者自己造成的。莊子曾氣憤地說:“圣人生而大盜起”,“圣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同上)。莊子是在“痛駁仁義圣知,不足以防患止亂”,28適足成為“巨盜”的行竊之資。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不斷發動掠奪戰爭,弱肉強食,殘害人民。莊子譴責他們“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則陽》篇),屠殺無辜的罪行。莊子對那些邪惡勢力,也是大加鞭撻的,正如上面所說那樣,這里不再贅述。同時,我們也看到,莊子對美好事物,總是給予滿腔熱情的頌揚。他不僅歌頌殘疾怪人的高尚情操,他對所有有德之人,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贊美“德人”說:“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天地》篇)至于世上有無此等“德人”,這里姑且不論。莊生老人,有一顆善良的心,他懲惡勸善,苦口婆心。他一方面批評邪惡,另一方面又在規勸“驕矜”,改舊圖新。《山木》篇有則寓言,說宋地某旅店主有妾二人,一人美,一人丑,丑者貴而美者賤。所以會如此,原因即在于。“其美者自美”,店主卻不以為美;“其惡者自惡”,店主卻不以為丑。此作的主旨告訴人們: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莊子對那些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人,“痛下針砭,而示以處世免患之道”(同上),用心可謂良苦。宣穎對莊叟之用心,評論則更為清楚,他說:“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復致警,蓋為普天下最深病根只在于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禍機踏動矣。”29南華老人勸誡世人的一片赤誠之心,真是熾熱動人,沁人肺腑。
南華老人飽經滄桑,對社會生活和自然變化都有著深刻的體驗,因而他具有超出常人的豐富奇特的想像力。《莊子》之書之所以會被譽為奇書,自然也就不奇怪了。莊子自謂其著書:“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筋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下》篇)也就是說,他認為天下溷濁,不能用莊重的語言來論說,只能用悠遠、廣大、不著邊際的言詞和話語,無拘無束,自由地抒發感情。他的寓言故事的取材范疇,是相當廣泛的。有的是獵取平常生活中的素材、有的則純屬杜撰而成、有的是借助史料而改寫、賦予新的血液和生命、有的是利用神話作為題材而寫。這就使《莊子》之書,成為想像奇特,富麗堂煌、豐富多彩的杰作。猶如萬紫千紅的花苑,奇花異草,爭奇斗妍,經久不衰。所以,我們閱讀《莊子》之書,就好像游覽大干世界,令人目不暇接,獲益甚夥。
談到莊子的平生理想,如若不仔細研討,就很難找到答案。只要經過反復研究,就會發現,莊子一生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的理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他們追求的理想是實行“仁政”。道家學派的老子和莊子,他們追求的理想,是“以自然為宗”、恬淡無為。近入李大防曾經說,莊子之道“至博,至大、至深、至玄,而其指歸則至約也”。30所謂“約”者,指“虛”而言,認為“惟虛而后無為,亦為虛而能自然”。(同上)林云銘說:“三十三篇之中,反復十余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31他們的看法,有一個共同點,即莊子追求的最終理想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安時處順,復歸自然。這種“以自然為宗”的理想境界,莊子鍥而不舍,夢寐以求,至死不悔。
莊子執著追求“以自然為宗”的理想境界,包括下面三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恬淡無為,順應自然。《田子方》篇說:“夫水之于溝也,無為而才自然矣。”意謂水自然涌出,不受任何約束,言外之意,說明人亦應如此。《天地》篇說:“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者……”成玄英詮釋說:“夫心智明白,會于質素之本;無為虛淡,復于淳樸之原。”32陸西星比成氏詮釋得更加清晰,他說《莊子》“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于樸為主。”33莊子所謂“入素”, “復樸”,是在宣揚“無為虛淡”、復歸自然的思想,并非今天學術界有人所說是莊子“崇尚自然美”。莊子宣揚“無為虛淡”、復歸自然的思想,具體表現,即在其主張順應自然,反對有為,認為有為即有害。這種思想,在《莊子》中,比比皆是。如《大宗師》篇說:“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成玄英說:“夫旦明夜暗,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于何系哉?……而流俗之徒,逆于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劉鳳苞說:“究之天,亦純任自然,而非有造作安排之跡。”34他們所謂“任變隨流”、“安時處順”、“純任自然”云云,都是詮釋莊子“以自然為宗”的思想。莊子經常還談到“能天”。所謂“能天”,亦是“以自然為宗”的意思。《庚桑楚》篇說:“惟蟲能蟲,惟蟲能天。”這里所謂的“天”,亦是無為虛淡,順應自然的意思。何謂“天”?莊子自己曾經明確地說“無為為之謂之天”(《天地》篇)。對于這個問題,錢澄之曾經指出:“莊子以自然為宗……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35錢氏之見,不同凡響,把一般學者難以解決的問題,竟寥寥數語,就講得非常明白。
第二,反對約束,恢復本性。莊子主張純任自然,自由地發展和生存,反對人為地約束性靈的一切桎梏。莊子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天運》篇)又說: “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秋水》篇)鴿白烏黑,出自本性,天生而成。牛與馬天生四足,是其本性;落馬首,穿牛鼻,是人為之,失其自然,損其本性,妨礙自然發展。顯而易見,莊子是以禽鳥和動物比喻人類。反對用人為的桎梏,約束人的本性,妨礙人類自由發展。《駢拇》篇就對用禮樂仁義等削性害生的罪過,大加鞭撻。《漁父》篇,更加明確諷刺孔子提倡“仁義”,是對人的“真性”的危害。說孔子“仁則仁矣……苦心勞形,以危其真”。所謂“真者”,莊子自己曾解釋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同上)《天地》篇繼承和發展老子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以及“趣舍”使人“失性”的思想,認為此五者“皆生之害也”,“為天性之桎梏”36。從莊子有關這方面的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到,莊子的目的是在猛烈地抨擊儒、墨之徒、設置禮樂仁義等陳腐教條,窒息人們的思想,損害性靈,妨礙人們個性自然發展。
第三,向往原始社會和“混茫”世界。所謂“建德之國”,即是莊子向往的理想王國。按照莊子的描述,這個國度,“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山木》篇)不言而喻,此等社會,是不知禮義的愚昧無知的原始社會。對這種古老的原始“混茫”世界的狀況,除上面描述的情景外,在《莊子》里,還有幾處具體的描寫,如《繕性》篇說:“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知為而常自然。”宣穎說“混茫之中”,是謂“元氣未離”;“至一”是說“無知無欲”37。這種淡漠無為,與萬物群生,不傷不夭,同生同長,無知無欲的社會,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論述,還是處在人類沒有開化的最低級的蒙昧時代。《馬蹄》篇,所謂的“至德之世”,與“建德之國”是同樣的蒙昧社會,只是描繪的具體境況有所不同罷了。莊子所說的“至德之世”的情景是:“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是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可想而知,莊子崇尚的這種“民性素樸”的原始社會,是愚昧無知的人類個性絕對自由的社會。我們必須看到,莊子所追求的個性自由發展,反對人為的約束,有其正確的方面;但其中也有其消極頹廢的落后性。社會在發展,歷史在前進,不管莊子出于什么目的,他主張社會倒退,挽回已經前進了的人們的耳目,只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退行為。司馬遷針對老子和莊子的這種倒退思想,曾經提出這樣的批評。如果莊子企圖以此來表現對當時黑暗社會的否定,這也是非常消極的。這即暴露出莊子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詩人氣質的明顯弱點。
其三,莊子散文具有強烈的詩的語言節奏和韻味。在先秦諸種,《老子》是具有哲理性的散文詩,文句簡短,頗有韻味。《論語》只是一種語錄體文字,文字呆板,缺乏詩意。《孟子》篇幅較長,長于敘事,善于雄辯,言辭豐富,筆鋒犀利,作為先秦散文,已經蔚為大觀。莊周與孟軻,同為戰國早期人,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莊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莊子無論在氣質和個性方面,都與孟子迥然不同。嚴格地說,孟子書生氣很重,只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莊子富于幻想.胸懷坦蕩,直言不諱,具有熾熱的詩人氣質,是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典型的知識分子。因此,莊子的散文,并非是一般的散文。而具有詩歌的節奏和韻律,生動抒情,輕快、活潑,令人喜愛,富有無窮的韻味。如《逍遙游》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在宥》篇寫廣成子斥責黃帝說:“自而治天下,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天地》篇:“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凡此等等,真是如詩如畫。作者經常以詩人的筆觸,用高度概括和凝練的語言,用長短句對稱的筆法,用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抒發其熾熱的情懷,唱出悅耳動人的歌聲。其中,意蘊深邃,飽含著富贍的哲理性,又令人索解不盡。
出乎尋常的夸張比喻手法
夸張和比喻,是文學作品常見的手法。先秦文學作品都具有這個特色,所以人們對夸張比喻手法,并不感到有什么新奇。但是,莊子散文所使用的夸張比喻手法,出人意料,新穎奇特,與眾不同。如《逍遙游》寫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其廣數千里,不知究竟有多長。又說有鳥名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扶搖直上九萬里。說楚國的南方有冥靈之樹,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棵大椿樹,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達生》篇寫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浪花)四十里。《外物》篇寫任公子釣魚,為大鉤巨緇,以五十條牛為餌,蹲在會稽山,投竿于東海。《列御寇》篇寫莊子將死,說莊子以天地為棺遊,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等等,這種新奇怪誕的夸張手法,往往都注入神話和傳奇的色彩,令人驚嘆,令人傾倒。
莊子散文善于比喻,富于變化,含蓄蘊藉,生動活潑,比其他先秦諸子散文,又具有突出的特色。如《大宗師》篇寫“子來有病”一段,使用了三個比喻:“父母于子”一喻,“鑄金”一喻,“寐覺”一喻。前兩喻中間夾一段證議,如層峰起伏。后一喻兩句陡住,如峭壁斬然。《天運》篇寫“孔子西游于衛”一段,接連使用“古今非水陸”、“周公非舟車”、“桔槔俯仰”,“相梨橘柚可口”、“猨狙衣周公之服”、“西施病心而臏其里”六個比喻,作六層轉換,愈轉愈活。此段由于運用六個比喻,便更加生動地說明“禮義法度”,必須“應時而變”的道理。《馬蹄》篇開篇陡用伯樂“善治馬”,陶者“善治埴”,匠人“善治木”三個比喻,就使此段文字如“風騎雨驟,飄忽非常”38。以上是說,莊子善于使用比喻的特點。
同時,還應看到,莊子使用比喻,還有千姿百態,變化莫測的特點。如《在宥》篇說:“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水,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這里使用了一連串的排喻,“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俯仰四海”喻其速,“淵靜懸天”喻其動靜各殊,皆用來比喻人心不可攖。還有明喻、暗喻,“駭喻切喻,微妙警策,毛寒骨竦”。39對于莊子比喻這種變化莫測、層出不窮的特點,宣穎曾評論說:“莊子之文,長子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云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同上)所以,莊子散文言有盡而意無窮,給人留下咀嚼不盡的余味。
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色,古人曾有高度評價,宋代高似孫說:“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涌,聲沉影滅,不可控搏。”40但是,莊子散文固然對后代有積極的影響,同時也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對待這個問題,長期以來都沒有能夠給予正確的評價,曾經產生過忽左忽右的現象。必須看到,中國古典文學遺產,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其中必然會存在民主性的精華和封建性的糟粕。我們對待古代文化遺產,必須堅持批判繼承、古為今用的原則,不能兼蓄并收。這才是惟一正確的態度。并不能因為歷史的發展,時代的前進,意識形態的變化,而拋棄這個基本原則。對于莊子散文的思想內容及其藝術風格,我們也必須本著這樣的原則,吸收其有益的精華,剔除其消極頹廢的糟粕,為弘揚祖國文化優良傳統、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作出積極的貢獻。
注 釋
1 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2 《晉書·阮修傳》。
3 《南華經副墨》。
4 《大鵬賦》。李白還有(古詩第三十三首)描寫“北溟有巨魚,身長數
千里”的贊美詩。
5 《藝概·文概》。
6 《宋史·蘇軾傳》。
7 《稼軒詞編年箋注》。
8 “侃大山”:北京方言,意謂神聊。
9 《南華雪心編》《外物》篇夾注引語。
10 《南華雪心編》。
11 《南華經解》。
12 劉熙載:《藝概·文概》。
13 《南華雪心編》。
14 《莊子詮詁·序》。
15 《南華雪心編》。
16 《南華經副墨》。
17 《南華經副墨》。
18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19 《莊子獨見·莊子論略》。
20 《莊子贊》。
21 《南華經句解·至樂篇》眉批。
22 《讀(莊子)》。
23 胡文英:《莊子獨見》。
24 《南華經解·天道》。
25 《莊子因·天道》。
26 《南華經解》。
27 《莊子因》。
28 《南華雪心編》。
29 《南華經解》。
30 《莊子王本集注》內篇總論。
31 《莊于因》總論。
32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下引同,不再注明出處。
33 《南華經副墨》。
34 《南華雪心編》。
35 《莊·屈合詁自序》。
36 宣穎:《南華經解》。
37 《南華經解》。
38 林云銘:《莊子因》。
39 宣穎:《南華經解》。
40 《子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