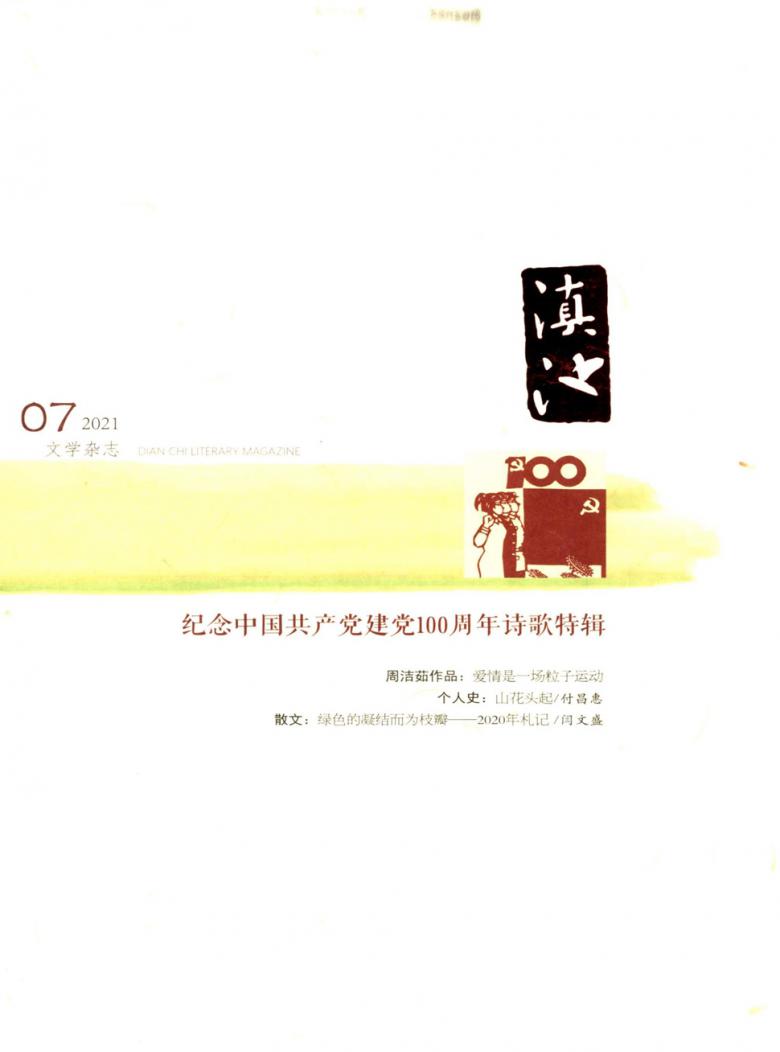“新寫實”小說與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嬗變
王忠信
池莉的《煩惱人生》以反典型化的創作方法,用生活“流水帳”來敘述青年工人印家厚從早晨起床到夜晚上床這一整天瑣碎、平淡的勞碌,無論是生活層面,還是精神層面,煩惱都如影相隨。小說看似平淡、乏味,卻揭示了真實的世俗人生,人們的生活常態就是充滿了令人尷尬而又無可奈何的生存煩惱。方方的小說則以平民化的視角,表現市民階層的價值立場。在小說《風景》中,漢口“河南棚子”那住在“十三平米板壁屋子里”的一對夫妻和他們的“七男二女”,令人怵目驚心地看到了“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黑暗的深淵所在,這里是文化的荒漠,這里是物質的寒窯,生存的貧窮和人性的丑陋一覽無余,充滿了粗俗和卑賤,方方以冷峻旁觀的敘述徹底顛覆了“物質貧窮,精神高尚”的經典命題。 現實主義文學從典型化到世俗化的變化,也使文學真正擺脫了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去除了籠罩在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和虛幻的浪漫主義,暴露出赤裸裸的世俗性。劉震云的小說《塔鋪》,講述了當年高考補習班的那段生活,人們忍受著惡劣的學習環境和生活條件參加高考補習,并沒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情,而是各為前程,“將來一旦考中,放個州府縣官啥的”。《新兵連》中的那群來自河南農村的子弟,為了集訓后能分到好一點的崗位,個個挖空心思表現自己,討好、巴結連排干部,甚至出賣老鄉。“三個月下來,個個跟仇人似的”,這些“穿著軍裝的農民”,使軍營生活也變成了世俗化,沒有了以往的崇高與神圣。 三、從“主觀介入”到“情感隱匿” “新寫實”小說產生于2O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文學的終極理想消失、作家的政治熱情降溫、個體生存更加艱難等復雜的現實背景中,它放棄了思想啟蒙和人性批判的功利性,放棄了文學的社會干預以及對人生意義的探索,以冷峻旁觀的敘述姿態描寫生活在社會底層人們的生存狀態,表現他們世俗而瑣屑的生活,既不評價生活,也不干預生活,當然更不想去改造生活。“新寫實”小說作家在表現世俗人生中集體選擇了主觀情感退隱的敘事策略,不再介入現實,即“壓制到‘零度狀態’的敘述情感,隱匿式的缺席式的敘述”。 現實主義文學強調文學與人生的密切關系,它不是自然主義地描寫現實社會和人生,而是要表現人生,探索人生,改造人生,必然要在作品中傾注作家的主觀感情和人生理想。無論是思想啟蒙,還是社會批判,都離不開作家的主觀情感和價值判斷,顯示出作家的思想傾向,表現作家的審美意識。“新寫實”小說這種平面化的描寫,保存了自然、客觀的“生活本色”,突出了人的食、色本性以及由此產生的生存困境,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政治化描寫及虛幻的理想主義。同時“新寫實”小說也放棄了文學的審美追求,不忌諱人性的惡俗、丑陋,更不會忌諱環境的臟亂和世俗生活的庸俗。其實,“新寫實”小說在對表現生活不避其丑的同時,也拋棄了作家的審美意識。 “新寫實”小說的出現,使現實主義文學觀念在社會轉型期發生了嬗變,它“切人過去現實主義小說的盲區,呈現了為革命現實主義所有意擯棄或遮蔽的生活經驗,開拓了對現實的新的表現空間”[9],并在對個體生存狀念的關注中探索生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