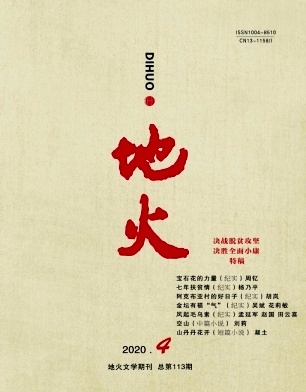現代民族國家與中國新古典主義
楊春時
關于革命文學(包括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和建國以后至“文革”時期的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性質問題,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敏感而又不清楚的問題。顯然,把革命文學定性為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看作現實主義的高級形式)的傳統說法并不合適,已經不為學術界所認同。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新古典主義的觀點[1],但是,當時對新古典主義的理論闡釋還不到位,對這個觀點的論證也有所欠缺。今天,我將運用現代性理論,從現代民族國家與新古典主義的關系的角度對此加以闡釋和論證,以期深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這個重要文學思潮的認識。
文學思潮是文學對現代性的反應。什么是現代性呢?簡言之,就是使現代社會成為可能的東西。現代性的核心是現代理性精神,包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正是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使文學具有了自覺性,產生了不同的文學思潮,如回應現代性、呼吁理性精神的啟蒙主義、反抗理性桎梏和城市文明束縛的浪漫主義、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黑暗、墮落的現實主義以及全面抗議現代性導致的異化的現代主義等。那么,古典主義是什么?古典主義是對現代性的政治形式——現代民族國家的回應。那么什么是現代民族國家呢?吉登斯的定義是:“民族-國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之中,它是統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對業已劃定邊界(國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它的統治靠法律以及對內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維護。”[2]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性催生的和賴以存在的政治實體,它相對于朝代國家而言。傳統國家是朝代國家,其合法性在于神意,君主不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而是以神的名義進行統治。現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在于民意,國家是以民族利益代表的身份進行統治,這是理性精神在政治領域的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充分形式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其前身或初級形式是被吉登斯稱為“絕對主義國家”的中央集權的王朝國家。吉登斯認為:“在絕對主義(absolutist)國家中,我們發現了與傳統國家這一形態的斷裂,這預示著繼之而來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自絕對主義(absolutism)時代始,與非個人的行政權力觀念相聯系的主權觀念以及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政治理念,就已逐步成為現代國家的組成部分。”[3]法國路易十四王朝就是典型的“絕對主義時期”的現代民族國家,它一方面聯合新興的市民階級壓制封建貴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利益;另一方面它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是封建王朝,因此只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初級形式。馬克思指出,在法國,君主****是“作為文明的中心、作為民族統一的奠基者”[4]而出現的。新古典主義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歐洲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運動是與爭取實現現代性的運動相始終的,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成為實現現代性的任務之一。
中國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是在鴉片戰爭之后被歷史地提出來的。中國傳統國家也是朝代國家,是一家一姓的“朝代”,“朕即國家”,家天下;皇權的合法性在于天意,而不是民族的代表。同時,由于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國”,不承認還有其他平等的國家,因此也不把自己看作是“國家”,而是看作“天下”。只是在鴉片戰爭以后,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沖擊之下,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才被提出來,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就表現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從根本上說,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與實現現代性的任務應當是一致的。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建設現代性的任務也得到推進;同時,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也成為建設現代性的一個方面。但是在中國卻與歐洲不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與實現現代性的任務產生了沖突。中國本土沒有自發地產生現代性的條件,只能從西方引進。這就是說,中國的現代性是外發型的,是由西方引進而非從自身產生的,因此具有外源性;是由于落后挨打不得不進行的選擇,而非由于自身發展的要求而產生的訴求,因此具有外迫性。外源性導致中國現代性缺乏傳統的“支援意識”;外迫性導致中國現代性訴求不堅定。因此,中國現代性先天不足,容易夭折。而由于中國處于西方列強的壓迫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意味著首先爭取民族獨立,反抗西方列強。這樣,實現現代性要求向西方學習,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則要求反抗西方。這樣,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必然發生沖突:要實現現代性就必須學習西方,走西方的道路,從而導致反傳統;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又必須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走反西方的道路,從而導致認同傳統,從傳統中獲取“支援意識”。中國必須進行兩難的選擇。由于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壓倒了實現現代性的任務,為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不得不犧牲現代性,甚至反現代性。這就是說,20世紀中國面臨的任務首先不是實現現代性,而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又必須采取反(西方)現代性的立場。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的歷史階段,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與實現現代性的任務還大體上一致,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與引進科學、民主并行不悖,因此啟蒙主義(包括文學啟蒙主義)是主潮。但由于民族危機的加深,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壓倒了實現現代性的任務。五四新文化運動剛開展數年,啟蒙任務遠沒有完成,社會革命風暴突起,啟蒙運動中止。這時,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矛盾突現。由于辛亥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嘗試失敗,于是選擇以反(西方)現代性的方式完成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都是采用了非西方的革命道路,都接受了蘇聯的政治革命模式,其歷史任務都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而實現科學、民主的現代性任務被擱置,甚至成為批判的對象。這就是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真正涵義。這種歷史要求使五四啟蒙主義中斷,新古典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
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新古典主義都是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回應,這是新古典主義的根本性質。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動員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力量。特別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階段——“絕對主義國家”時期,更需要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的支持,以造就民族國家這個“想象的共同體”。支持絕對主義國家的文化力量是政治理性。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適應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宰相黎塞留大力提倡新古典主義,推動了新古典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在英國的王政復辟時期也產生了新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有幾個基本特征:第一,高揚理性,認為理性是人的本質,也是文學的本質。認為理性就是真實,就是自然。法國新古典主義理論家布瓦洛提出:
“首先須愛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遠只憑理性獲得價值和光芒。”1
這個理性是群體理性。新古典主義的群體理性是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正面回應。它強調個體情感、欲望必須服從國家、社會的責任。新古典主義悲劇就突現了個體對社會責任的犧牲而顯示的崇高。第二,尊崇古代文學典范,強調服從權威,認為“摹仿自然就是摹仿古代準則”(蒲泊)。第三,認為文學形象應當體現某種普遍人性,形成人物形象的“類型”說。蒲泊就提出“詩人的任務是細查類型,而非細查個別”。第四,“高級的題材”和崇高的風格。新古典主義具有貴族文學的精神氣質,它認為悲劇反映上層社會生活,是高級題材;而喜劇反映下層社會生活,是低級題材(布瓦洛)。古典主義往往選取古希臘、羅馬的題材,描寫宮廷貴族的生活。它的語言典雅、氣質高貴、風格崇高,表現人性的偉大。第五,講求藝術規范,認為共同規范比個性創造更為重要。尤其是新古典主義的“三一律”,給戲劇制定了不容違反的形式規則。這是理性主義在文學形式上的表現。
新古典主義產生于法國,也流傳于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洲諸國。但對中國產生直接影響的是蘇聯的新古典主義即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十月革命后蘇聯建立了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這是吉登斯說的“絕對主義”國家的基本特征。這種“絕對主義”國家要求政治理性的支持,而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斯大林主義就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文學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于是,按照國家意志,就造就了蘇聯的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這個文學思潮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名稱出現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現實主義,而是新古典主義,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二者的歷史定位不同。現實主義不認同現代性,不順應國家意識形態,它是對資本主義的揭露和批判,是對現代性的陰暗面的抨擊,因此具有了文學現代性;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絕對主義國家”的認同,順應國家意識形態,以肯定現實為主要傾向,因此是前現代性的文學。
第二,二者的意識形態基礎不同。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人道主義,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政治理性即國家意識形態。現實主義關注小人物的個體的命運,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關注階級的命運和國家的責任。
第三,現實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實證主義,主張客觀性,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反映論和意識形態論。所謂“反映現實的本質”是被意識形態立場所規定的,因此更強調文學的理想性和意識形態性。
第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雖然自稱繼承了現實主義精神,但實質上對19世紀現實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是資產階級文學形式,缺乏理想性,只批判不肯定,不能反映現實的本質和歷史的發展趨勢等等,這樣就離開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品質。
第五,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性質除了上述表現以外,還體現為諸如“典型化”等形式規范以及崇高的風格。總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符合了新古典主義的尊崇理性、講求規范的基本特征。
中國的歷史條件為新古典主義鋪就了豐厚的土壤,造就了中國新古典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處于啟蒙時代,啟蒙理性成為時代精神。五四文學思潮一直被錯誤地稱為五四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實際上屬于啟蒙主義,這是由其與現代性的關系決定的:它呼吁和謳歌現科學、民主,批判封建主義,是對現代性的正面回應。1但是,啟蒙運動行之未久,由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壓倒了實現現代性的任務,革命取代了啟蒙。社會革命需要新古典主義,也產生和延續了新古典主義,法國大革命如此,蘇聯革命如此,中國革命也如此。作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手段的中國革命,需要政治理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的支持。因此,五四以后,蘇聯的新古典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引進,啟蒙主義退出歷史舞臺。新古典主義的歷史定位在于適應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而在中國,這個歷史任務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的。革命勝利以后,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采用了蘇聯模式。蘇聯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因此作為國家意志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文學的主導思想,新古典主義不僅被延續,而且更為徹底,也走向僵化。從“革命文學”論爭到左翼文學運動、抗戰文學和延安整風,以及解放以后的社會主義文學時期的“革命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新古典主義形成、發展,直到“文革”推出“樣板戲”和“三突出”原則而走向終結,新古典主義主導了中國文壇達半個多世紀。
此外,新古典主義的產生也有中國文學的理性主義傳統的基礎。正如歐洲新古典主義繼承了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理性精神一樣,中國文學的新古典主義也繼承了古典文學的理性傳統。中國文學本身具有強大的理性傳統,只不過這個理性不是現代理性,而是前現代的道德理性。五四文學雖然沖擊了傳統理性,但并沒有使之壽終正寢。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傳統的道德理性轉化為新的政治理性,而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新古典主義文學。五四文學的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沒有來自傳統的“支援意識”,因此中途夭折。而中國順利地接受了蘇聯的新古典主義,且根基深固、持續長久,則有賴于理性主義文學傳統的“支援意識”。
無論是“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還是“兩結合”,都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變體,都是新古典主義的中國形式。中國的新古典主義是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從“革命文學”論爭到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一直都在理論上批判現實主義,自認為是對“資產階級現實主義”的革命。五四啟蒙主義被誤解為現實主義,并被歸結為資產階級批判現實主義一類。它的科學、民主精神和人道主義被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啟蒙任務和對“國民性”的批判被認為是過時的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引進中國之初,就鮮明地針對現實主義和五四啟蒙主義(被當作現實主義)。周揚認為:“現實主義者攻擊了現實的丑惡,暴露了缺點,但是他們止于批評,并沒有積極的建樹。”“由于作家世界觀的桎梏和缺陷,它并沒有達到生活的真實的全面的反映。”2周揚還認為,舊現實主義的批判性已經過時了,革命現實主義應當變批判為歌頌,因為“現在,阿Q們抬起頭來了。關于覺醒了的阿Q值得寫一部更大的作品”。3《講話》發表以后,特別是建國以后,對“資產階級現實主義”的批判進一步加強,而粉飾現實的傾向日益加強。這樣。革命文學就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批判性。革命文學自稱為“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方面自認為克服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缺陷,同時也認為繼承和發揚了現實主義精神。實際上,革命文學對現實主義的接受是一種“誤讀”。它把現實主義理解為“真實地反映現實”而抹殺了現實主義的本質——對現代性帶來的社會災難的揭露、批判。這樣,就可以推導出“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對現實的肯定,因為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本身是光明的,反映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的現實就意味著歌頌現實。前面已經說過,現實主義是對現代性帶來的社會災難的揭露、批判,它不會肯定現實,更不是歌頌現實。否定了這一點,就離開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精神。而革命現實主義就在這方面離開了現實主義,成為新古典主義。
革命文學也是對五四啟蒙主義的反撥。“革命文學”論爭是接受蘇聯文學思想,批判五四啟蒙主義的開端。30年代正式引進和接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原則上與五四啟蒙主義劃清了界限,形成了中國“革命現實主義”思潮。五四啟蒙主義被誤認為“資產階級現實主義”,它的人道主義、個性解放思想被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被批判。這種批判在〈〈講話〉〉發表以后和建國以后進一步得到加強。
中國新古典主義具有一般新古典主義的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中國新古典主義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尤其是強烈的政治理性主義。蘇聯的新古典主義在主張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的同時,還注重文學的客觀性(反映論),而中國新古典主義卻更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性,不那么強調文學的認識論意義。這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得到明確地表述。《講話》沒有從文學是什么的科學角度談起,而是從“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意識形態角度談起;它沒有運用反映論確定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認識,而是大談文學的階級性以及從屬于政治,為政治服務。蘇聯的新古典主義主張文學的意識形態性,但還沒有局限于政治性,還包括道德等方面。中國新古典主義不僅明確主張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鮮明地宣稱“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中國新古典主義作家不是采用私人視角,而是采用階級視角;不是采用多方面的生活視角,而是采用單一的政治視角。新古典主義文學作品也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如《子夜》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描寫形象地表達了作者對中國革命的信念;至于“革命樣板戲”更極端地突出了(而且是偏執化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中國新古典主義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尤其是強烈的政治性既出自中國文化的實用理性傳統,也是由中國革命的嚴酷性造成的,它需要文學參與革命斗爭,需要突出文學的階級意識。當然,建國以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思潮助長了新古典主義的政治理性主義,但這仍然要從“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本身尋找根源。
其次,中國新古典主義注重選取重大社會政治題材,突出了崇高的風格。它不是選取關注個體命運的立場,而是選取關注階級、民族的命運的立場。這是政治理性主義在文學題材方面的表現。同時,中國新古典主義也突出了崇高的風格,它謳歌社會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展示無產階級性的偉大和崇高。不僅在“革命現實主義”時期是如此,而且在解放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兩結合”時期也是如此;以后竟至完全排除了非社會政治題材和其他美學風格,如“文革”前和“文革”中階級斗爭題材的絕對化、對“反題材決定論”和“時代精神會合論”的批判;“革命樣板戲”更是把這種傾向推倒極致, “塑造高大完美的無產階級英雄形象” 成為文藝的“根本任務”。
還有,中國新古典主義表現了強烈的理想主義和樂觀精神。它突出了理想主義,并認為這是區別于“批判現實主義”的特征。《講話》提出文藝“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在“兩結合”中,更強調和突出了理想主義。所謂“兩結合”實際上是強調政治理想主義,因為這里的“浪漫主義”被理解為理想主義。這是中國新古典主義區別于歐洲新古典主義和蘇聯新古典主義之處。新古典主義不是客觀地描寫現實,而是按照理想主義原則描寫現實中還沒有發生或還沒有成為普遍事實的東西;不是展示人性和社會生活的黑暗面,而是展示光明的未來。這就是所謂“反映現實的本質”。在《講話》中就已經批判了“寫黑暗”和“寫黑暗與光明并重”的主張,指出“以寫光明為主”;在解放以后更強調頌揚社會主義的光明面。在“革命樣板戲”中,這種理想主義更發揮到極致。同樣,與歐洲新古典主義不同,中國新古典主義沒有形成悲劇意識,它不是表達個體對社會責任作出犧牲的悲痛,而是展現個體犧牲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因此,中國新古典主義充滿了樂觀精神,堅信個體的犧牲是完全值得的,革命必將勝利,。這種理想主義和樂觀精神既來源于中國的集體理性和“樂感文化”(李澤厚),也出自鼓舞革命斗爭意志的需要。
最后,中國新古典主義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規范。中國新古典主義也遵循了一般新古典主義的人物類型化原則,蘇聯新古典主義的形式規范如“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得到繼承,這種“典型”被確定為“共性與個性的統一”,而共性即階級性是個性的本質。而且不僅如此,中國新古典主義還創造了更為特殊的形式規范,最明顯的是“樣板戲創作經驗”如“三突出”原則等。
需要指明的是,中國的新古典主義與歐洲新古典主義不同,它不具有貴族氣質和高雅風格,相反,它具有平民氣質和通俗化風格。這是由中國“新式農民革命”的性質決定的。它要求革命文學貼近工農大眾,為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學的平民化和通俗性也有中國文學的平民性傳統的影響。歐洲“絕對主義國家”是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文學以宮廷趣味為中心,因此歐洲新古典主義繼承了貴族文學傳統。中國革命致力于建立工農政權,工農成為文學的主要對象,而且中國貴族文學傳統薄弱,平民文學傳統強大。因此,革命文學具有平民氣質和通俗化風格。革命文學反映工人、農民的革命斗爭生活,形式通俗。它提倡大眾化,認為普及先于提高。但是,這種通俗化也不等于通俗文學,它對以消遣娛樂為特征的現代通俗文學是排斥的;它是革命的政治內容與通俗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因此屬于嚴肅文學范圍。
歷史在五四以后拐了個彎,由實現現代性轉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現代性思潮退潮。與此相應,文學思潮也跟著拐了個彎,由啟蒙主義轉回到新古典主義。從直線進化論的角度上看,這似乎是倒退,而從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看,這正是一種必要的迂回,因為只有完成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才能進一步完成實現現代性的任務。只有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才能接續未完成的啟蒙主義任務,并進而建設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學。中國新古典主義的歷史作用是適應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發揮了推進革命的功能。但是,對文學而言,不可避免地出現這種情況,即文學為歷史作出了犧牲。中國的新古典主義對五四啟蒙主義而言,在審美價值上有所退步,從五四文學的高度上跌落下來。而對于五四以后的非主流的文學思潮(如對于老舍代表的現實主義和沈從文代表的浪漫主義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流派)而言,這種落差就更為明顯。至于建國以后到“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兩結合”文學的負面教訓恐怕要大于正面經驗。由于新古典主義是五四啟蒙主義的逆轉,它雖然具有歷史的依據,但并沒有達到時代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后期加劇的的公式化、概念化以及僵化的政治理性主義違背了文學自身的規律,所以從總體上說,革命文學的藝術成就不高。文學對歷史的犧牲是歷史需要與精神自由之間的矛盾造成的。歷史進步并不一定意味著人的價值的提高,而往往是以對人的價值特別是精神自由的犧牲為代價的。這就是所謂“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文學作為“自由的精神生產”,往往要為歷史作出更大的犧牲。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最大秘密。
隨著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任務的基本完成,建設現代性的任務又提到日程上來。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接續了五四啟蒙傳統,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建設現代性的任務。與此相應,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也退出歷史舞臺,新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崛起。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特別是在90年代興起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啟蒙主義退潮,多元的現代文學思潮形成,如以“新寫實主義”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各種先鋒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等。當然,新古典主義并沒有完全消失,它的影響依然存在。這是由于中國現代性建設還沒有完成,還保留著傳統社會主義的痕跡。但是,新古典主義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它的生命力已經枯竭,不可能主導當代文學了。新古典主義退出歷史舞臺,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文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它留下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1] 參閱楊春時《古典主義傳統與當代文藝思潮》,《北方論叢》1988年第3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文藝評論》1989年第2期。
[2] 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7頁。
[3] 同上書,第4——5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2頁。
1 伍蠡甫編《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1頁。
1 參閱楊春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是啟蒙主義——現代性視野中的五四文學思潮》,載《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2 周楊《現實主義試論》載1936年1月1日《文學》第6卷第1號。
3 周楊《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任務》,轉引自《文學運動史料選》第4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