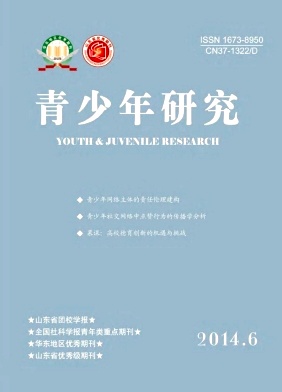“入乎其內” “出乎其外”——兼談戲曲意象創作問題
肖旭
我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六十)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六十一)又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這是說,詩人要深入生活之內,才能獲得豐富的創作材料,作品才會有生氣;詩人又要從一定的高度來觀察生活,縱觀生活的總體,作品才能有深刻的內容,才能有獨到之處。可以這樣說,王國維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領悟到了藝術與生活的辯證關系,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文藝創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意思。從藝術是心物交融(我國古文論)、是審美主體與客體互逆交流的結果(西方哲學)來看,“所謂入,是說我入物內,以物為主,我為被動;所謂出,是說我出物外,以我為主,故我為主動,這正申明情物交融,物我雙會之旨。”(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王先生的“出入說”是針對詩歌創作中“物我”關系說的,即我們常說的“意象”。所謂“意”,就作品而言,是指一篇作品中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類似我們所說的“主題”;從主客體、物我關系來看,“意”當指詩人及其思想感情。所謂“象”,就是詩歌作品了,是詩人所描寫的客觀事物了。從美學高度來看,只有意與象,我與物,主體與客體、情與景融交在一起,才能創作出美的藝術境界。此時的“象”(或“境”)已不是純客觀的物了,已是經過心靈化了的,它已浸染上了作家的主體情志,它是情志的“感性顯現”,一般稱之為“意象”,即含主體情志的客體物象。在文學藝術創作領域,不論是詩歌、小說、戲劇的創作都會涉及到物我關系,只是他們所走的途徑,所堅持的法則不同而已。詩歌創作是強調“物化”境界,即物我合一的境界,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意境,這是一種詩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與所表現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所形成的一種藝術境界。在繪畫藝術中,鄭板橋將物我關系歸納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竹象三意說”。王先生的“出入說”同樣適用于戲曲意象創作。他在“出入說”中所說的“入乎其內”,可以理解為劇作家要深入生活,搞創作必須要深入了解、觀察、體驗生活,并達到“與花鳥共憂樂”的程度。這樣塑造出來的藝術形象才會有生命,有生氣。而且還指出,深入生活不能是純客觀的、不動腦筋的,要發揮劇作家主體情志的作用,要動感情,要以全部熱情甚至生命來對待它。
“出入說”的另一方面,強調了主觀“我”的作用,既要深入生活,但又不能陷入生活,要站的比生活更高,“以奴仆命風月”,做生活的主人,不當生活的俘虜。“我”這顆種籽植入“物”的泥土中,主體情志熔鑄于客體物象之中,才能開出燦爛之花,藝術形象才能有個性,才能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出入說”中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不能截然分開,“我入物內”,“我出物外”是緊密連在一起的。因為藝術形象是“物”與“我”結合的產物。蘇拭在《琴詩》中曾作過一個比喻,他說:“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里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他是說若把琴和手指分開,那琴就不會出聲了,指頭上也聽不到聲音了,只有手與琴很好結合才能發出悅耳的聲音,這里強調的是物、我統一問題,王國維先生的“出入說”也談的是物我結合、生活與藝術統一的問題。我們用這種思想來解釋戲曲意象創作,那舞臺藝術形象便是劇作家主體情志與客體物象相結合的產物。詩人鄭敏曾將這一創作過程歸納為“我——物——我——物”,這最后一個“物”當為劇本中的人物形象了,但此時的人物形象中已有了“我”,而“我”中已有了“人物形象”,他成了物我的有機結合體。
運用王國維的意象創作“出入說”,來檢驗戲曲藝術,無論在劇本創作、舞臺藝術創作等方面,都可以讓我們恰當地探尋出藝術的規律。如關漢卿的著名悲劇《竇娥冤》中的竇娥形象,就是意象交融的。竇娥形象是有原型可尋的。
古代傳說《淮南子·覽冥》中“庶女叫天,雷電下擊”的故事,說齊有寡婦是貧賤人家之女,她沒有兒女但不改嫁,一心侍奉婆婆,對婆婆孝順恭敬。她婆婆有個女兒,總想貪占她母親的錢財,為此而叫她嫂嫂改嫁,這個寡婦堅決不從。后來小姑殺了自己的母親,反誣嫂嫂。寡婦無處說理而遭到冤殺,寡婦叫天,感天通地,而雷電下擊,洗刷其冤情。
《漢書》卷71《于定國傳》也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后姑自以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余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致其故,于公日‘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倘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還有劉向的《說苑》也記載了這段故事,基本與《于定國傳》同)。
晉·干寶《搜神記》卷11也有《東海孝婦》條,內容基本同《漢書》的記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于眾日:‘青若有罪,愿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上標,又緣幡而下。”
“東海孝婦”這個故事的思想,不外:一是表彰孝婦的孝順,二是歌頌于公的陰德。不過《搜神記》中已進一步增入了周青的誓愿以及誓愿的實現,同時也強調了周青之冤,表現了一定的反抗性。我們可以把“庶女叫天”、“東海孝婦”看作是竇娥的原型。庶女、孝婦和竇娥都有類似的經歷,后來她們都負屈銜冤。兩個原型與竇娥還有其共性——即比較善良。可以說庶女、孝婦是類似的,一個是靠老天作主,一個是屈打成招。但跟竇娥是不一樣的。
關漢卿創作竇娥形象還有什么依據,不得而知,但吸收了庶女、孝婦的素材是沒有問題的,關漢卿對東海孝婦的故事熟知也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一再把這故事引到自己劇作之中,如第三折竇娥唱:“做甚么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第四折竇天章云:“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為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又云:“昔于公曾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感召得靈雨如泉。”關漢卿還注意到歷史上其它的冤獄,如“六月飛雪因鄒衍”等。但關漢卿并沒有照搬東海孝婦等冤案,而是聯想到歷史上的不平倍感悲憤,把目光更注視著在滿布瘡痍的現實,揮動他那如椽的大筆,“自鑄偉詞”,加強了竇娥的反抗精神,這突出表現在法場(第三折),竇娥不僅痛斥人間的勢力,連天地也懷疑否定了,認為“天地也怕硬欺軟”,“不分好歹何為地,錯勘賢愚枉做天。”關漢卿沒有讓竇娥的反抗精神僅僅停留在痛斥天地的境界,而是進一步把全劇推向感天動地的高潮,成為支配天地的力量。竇娥臨刑前發下三樁誓愿,“血濺白練”、“六月飛雪”、“亢旱三年”不僅吸收和點染了東海孝婦故事的一二節情節,而且豐富了六月飛雪的情節,它熾烈的展現了遭受迫害的無辜者的反抗精神,充分地表達丁關漢卿對冤死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更強烈地表現了廣大群眾對黑暗統治造成的無比罪惡的憤愾。這三樁誓愿揭示出了造成冤獄的根本原因是“官吏每無心正法”,是腐朽的政治。“將濫官污吏都殺壞”,分明把這件冤獄的造成原因歸咎于濫官污吏。到此會讓我們感到,這是竇娥的聲音,還是關漢卿的聲音?這正如郭沫若在《蔡文姬·序》中所說:“蔡文姬就是我。”我們完全可以說,竇娥就是關漢卿。竇娥的控訴,飽含著關漢卿的憤懣不平。
我們還應看到,關漢卿的《竇娥冤》吸收了東海孝女的故事,但只是受到了這一故事的啟發,用了它的框架架,其內容是作了徹底改造的,故事情節是來源于當時的社會現實的。關漢卿對發生在元代類似竇娥的冤獄,是深有體驗和了解的,所以他大量寫進了元代社會現實,諸如賽蘆醫、張驢兒那樣的惡棍潑皮,桃機那樣的贓官污吏,全國到處都有的高利貸剝削等,把廣闊的社會生活作為背景。關漢卿一方面通過竇娥的冤獄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另一方面又通過竇娥這個形象歌頌了人民反抗壓迫斗爭的精神。兩方面合起來構成這個劇本的主題思想,以此來表現新的時代特色和深刻的社會意義。
從《東海孝婦》的傳說到《竇娥冤》,已經帶上了元代社會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關漢卿不僅能“入乎其內”,還能“出乎其外”,站在那個時代的高度,對類似竇娥的冤獄重新審識,重新評價,得出與庶女、孝婦不一樣的結論,使竇娥這一形象從生活原型到舞臺形象發生了很大變化,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態度。可以說,關漢卿的主體情志滲入到了竇娥形象里,他站在當時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方面,代表著人民對元代黑暗現實進行控訴,對吏治腐敗、貪官污吏進行揭露和鞭撻。竇娥形象之所以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及不朽的審美價值,是跟意象創作、主體情志的發揮,用主體情志統帥塑造形象是分不開的。
庶女、孝婦、竇娥的藝術形象之所以不同,在于竇娥形象是藝術典型。她們之間的最根本區別,就在于物我兩方面的組合方式不同。戲劇藝術跟一切藝術一樣。由于藝術家對主體情志、客體物象有不同的處理,所以就存在著不同舞臺形象的創造方法和不同的舞臺形象類型。按戲劇舞臺的實際狀況,可以分為三種:摹象、喻象、意象,因此世界上的戲劇也有三種,即摹象戲劇,就是寫實話劇,在西方舞臺上雄踞二千多年,到現在還有不可抹煞的影響;意象戲劇,就是中國的戲曲,統帥東方戲劇舞臺八百多年;喻象戲劇,有近百年的歷史,有人亦稱現代派戲劇。
戲曲意象創作同摹象、喻象戲劇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們說,主體情志與客體物象最后都要達到統一,這一點是相同的,只不過達到的途徑、采取的方法、位置的擺放不同而已。
摹象戲劇是突出物、隱蔽我;喻象戲劇是背離物,突出我。而我國的戲曲既不純粹采用摹象方法,也不純粹采取喻象方法,而是要創造出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交融的場面。它既不特別強調意象的認知作用,也不特別強化形象的評價作用,重在強調二者的有機辯證結合。為了認清這一點,不妨簡述一下摹象戲劇與意象戲劇,看它們在物我兩方面是如何處理的。應該說,物我是對立統一的,而對立統一有兩個方面,但總有一方面是主導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摹象戲劇,是把“象”(客體物象)放在制約方面、主導方面,最后達到意象統一;意象和喻象戲劇是把“意”(主體情志)的發揮作為矛盾的主導方面,最后達到意象統一交融。如果從藝術的再現與藝術的表現角度來看,我認為摹象戲劇是再現藝術,喻象戲劇是表現藝術,中國戲曲的意象創作則是在再現基礎上的表現藝術。這一特性是由藝術的本質——戲劇行動和戲劇動作所決定了的。中國戲曲可以通過戲劇行動通向再現,走向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深化;也可以通過戲劇動作通向表現,走向駕馭生活的自由空間,達到時空自由,虛擬抒情。
戲曲意象的出現,大致經過一個藝術意象到戲曲意象的過程,而在這諸多意象里,重要的是詩歌意象的產生。詩歌,這里指抒情詩的發展過程,大體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比興體的詩歌;二是意象體的詩歌。在比興體詩歌中,詩歌形象中的物我,處于游離狀態,不是一蹴而就。如“關關雎鳩”是興體詩,詩人先聽到鳥的叫聲由此觸發而想起美女是君子的伴侶。學者葉嘉瑩說:“興則是先對一種物象有所感受,然后引起內心之情意,其意識之活動乃是由物及心的關系。”這是物在興先,先聽鳥叫聲,轉而啟發想人之事。《碩鼠》是心里先有所慮,對剝削很有意見,要批評,要揭露,以田鼠作引子,從物我關系看,興在物先。那么到意象體詩歌時,就達到物我交融、情景交融。唐詩、宋詞、元曲就是代表。
從生活的物象到藝術的意象統一交融,作為審美意識的發展,在藝術實踐里是逐漸產生的。意象美學作為理論形態來說,到晚清才成熟,到王夫之時達到了高峰,由他作了總結。他在《昌齋詩話》里說,詩歌創作要“以意為主”,“意猶帥也”“寓意則靈”。這是說,“意”跟統帥一樣,沒有統帥就成了烏合之眾。而客體物象“煙云泉石”、“花烏苔林”,“寓意則靈”,一定要把藝術家的主體情志溶進去,而且在藝術形象的創造里,以主體情志為統帥,這樣創作出的形象才有生命力,才有靈氣。前面我們舉的關漢卿與他所創作的竇娥形象例證即是這樣的。我們將古代人所提出的意象創作規律、原理歸納一下,即“意”起著主導作用,“象”決定著“我”但不決定藝術形象,它是基礎,只有意象交融,兩方面都不偏廢,其藝術形象才能飽滿、豐富。請注意,詩文“以意為主”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古老問題,船山先生的所謂“意”,籠統一點說就是作者賦予作品的思想內容,而這思想內容必須是具體形式的活的思想。這一具體思想與“情”相近,相當于我們常說的“情意”一詞,情中之意,意中之情,密不可分。還應看到,在作出理論總結之前,意和象的統一早就存在了,只不過有個發展過程而已。意和象要求交融,到宋金元時期,已成為美學的主要思想了,全面作用于文藝領域。這時在山水畫表現的特別突出。如北宋有一山水畫家曾說過,山水畫要使欣賞畫的人產生一種愿望,要到畫中山水里去玩,去居住。達到這種程度,若不是意象交融是不可能的,不是主體情志作用于客體物象,二者交融了,也是不可能的。總之,宋金元時期意象美學已成為一種主要思潮,作用于整個文學領域了。在這一時期,戲曲一經成熟,戲曲意象就產生了。
總之,我國戲曲意象理論的發展,受到我國文藝理論中意象學說的影響與制約。由于戲劇藝術有其自己的表現方法,因而在戲劇的表現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意象表現形態。這是我們今天發展戲曲創作的一筆重要理論遺產值得借鑒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