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國歌劇《原野》的整體特點(diǎn)與創(chuàng)作構(gòu)思
胡波 黃瑾
內(nèi)容摘要:根據(jù)曹禺原著改編,由金湘教授創(chuàng)作的歌劇《原野》是中國當(dāng)代歌劇創(chuàng)作領(lǐng)域較為成功的一部作品。文章擬從音樂與戲劇的整體融合、聲樂與器樂部分的立體構(gòu)思及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的關(guān)系處理三方面分析該劇作的整體創(chuàng)作與音樂特點(diǎn),以期深入剖析該作品的成功之所在。
關(guān) 鍵 詞:《原野》 歌劇 金湘 音樂 戲劇
建國后,新中國歌劇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較熟悉的民族民間音樂為基礎(chǔ);另一種側(cè)重于借鑒西方歌劇的結(jié)構(gòu)模式與作曲技法。筆者認(rèn)為,兩種風(fēng)格各有所長,中國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的進(jìn)一步提高以及能否成功登陸國際舞臺將取決于它們的相互融合、升華及創(chuàng)新。歌劇《原野》即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其整體創(chuàng)作與音樂特點(diǎn)總體呈現(xiàn)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音樂與戲劇的整體融合
1.“音樂應(yīng)當(dāng)是戲劇的音樂,戲劇應(yīng)當(dāng)是音樂的戲劇。”歌劇藝術(shù)的理想境界就是音樂與戲劇的完美融合。在談到歌劇《原野》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時(shí),金湘教授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首先處理好“音樂與戲劇的關(guān)系”,音樂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準(zhǔn)確定位是決定歌劇作品能否具有長久生命力的關(guān)鍵起點(diǎn)。在他看來,歌劇創(chuàng)作中,音樂的進(jìn)行要充滿戲劇性,而戲劇要在音樂的總體布局下展開發(fā)展,以戲劇為基礎(chǔ),以音樂為主導(dǎo),只有把握住這點(diǎn),才算奠定了一部歌劇的基礎(chǔ)。作曲家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在歌劇《原野》的音樂創(chuàng)作中,他改變了音樂的從屬地位,摒棄了戲劇與音樂的舊有組合模式,也對劇本編寫與音樂創(chuàng)作各負(fù)其責(zé)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方法進(jìn)行了改革。作曲家、編劇、導(dǎo)演三方自一度創(chuàng)作開始,從制訂整體的音樂布局方案到具體的場景設(shè)計(jì)、人物沖突、劇情發(fā)展等方面都相互緊密合作,致使各音樂表現(xiàn)手段不再分散孤立。隨著劇情的發(fā)展,每個(gè)聲部的各種聲樂形式的運(yùn)用、管弦樂的鋪墊融合及各類色彩打擊樂的運(yùn)用,均在觀眾面前呈現(xiàn)出立體的交響性藝術(shù)效果。
2.具體人物塑造上音樂與戲劇的關(guān)系。一個(gè)成功歌劇角色的塑造,也應(yīng)是音樂形象與戲劇形象的有機(jī)融合與高度統(tǒng)一。以往有些歌劇常常放棄音樂表現(xiàn)戲劇沖突的功能,遇到尖銳的戲劇沖突時(shí),音樂形象就會(huì)出現(xiàn)“空白”,而戲劇形象逐漸放大“突現(xiàn)”,變成了“話劇+歌唱”。做這樣的處理,勢必大大降低音樂形象表現(xiàn)戲劇沖突的藝術(shù)魅力,而且也背離了歌劇藝術(shù)的原則。歌劇《原野》的編劇萬方(曹禺之女)具備得天獨(dú)厚的條件,深刻領(lǐng)悟了原作的精髓。在音樂與戲劇的結(jié)合上,她力求簡練準(zhǔn)確,避免音樂行進(jìn)中出現(xiàn)人物間的唇槍舌劍,還音樂于主導(dǎo)地位;劇中人物之間的沖突性戲劇場面的完成,幾乎全靠演員的獨(dú)唱、對唱、重唱及樂隊(duì)來完成。例如仇虎的詠嘆調(diào)《焦閻王,你怎么死了?》,一開始即強(qiáng)化了仇虎的角色特征。隨著劇情不斷深入,斗爭不斷激化,感情爆發(fā)也愈加熾烈。使觀眾與演員共同隨著音樂的不斷進(jìn)行,劇情的不斷深入,矛盾斗爭的不斷激化,感情也愈加高漲。
二、聲樂與器樂部分的立體構(gòu)思
“以聲樂為主導(dǎo),器樂為基礎(chǔ),追求交響性、立體性、整體性的統(tǒng)一構(gòu)思。”聲樂和器樂是歌劇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兩大表現(xiàn)手段。一般情況下易忽視器樂部分,甚至將其降為伴奏位置。金湘主張?jiān)谠亣@調(diào)中以聲樂為主導(dǎo);在宣敘調(diào)中兼顧器樂部分的表現(xiàn)力,對兩者應(yīng)整體構(gòu)思,統(tǒng)一規(guī)劃,二者互為主導(dǎo),適時(shí)可將聲樂、器樂的主導(dǎo)地位予以轉(zhuǎn)換。例如在歌劇第二幕之八《大星、金子與焦母三重唱》的尾聲部分,交響樂隊(duì)就在表現(xiàn)人物戲劇沖突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dāng)金子被逼問說出誰是她的情人時(shí),器樂部分隨即逐漸展開,先是弦樂組和木管組奏出固定音型,緊接著銅管組圓號、小號、長號依次而入,奏出呼喊般的音調(diào),打擊樂組也緊鑼密鼓,使氣氛愈加緊張。爾后,樂隊(duì)全奏,弦樂、木管組的固定音型不斷發(fā)展變化,向上沖擊,銅管組奏出平行小二度的下行音調(diào),整個(gè)樂隊(duì)以其宏大的音響,將戲劇沖突白熱化。此時(shí)此刻三人的激烈沖突及內(nèi)心的復(fù)雜感情都通過樂隊(duì)的交響有力地揭示出來,強(qiáng)烈地震撼了觀眾。
此外,為了使對白音樂化,作曲家還根據(jù)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dòng)與劇情發(fā)展,使用了樂隊(duì)手法。使對白成為歌劇音樂結(jié)構(gòu)整體中的一部分,如此,音樂既服從于對白,又積極作用于戲劇情節(jié),彌補(bǔ)了單純只聽臺詞的音樂空白。例如第二幕之一《仇虎與金子的對唱》中金子的臺詞中較有特點(diǎn)的“緊拉慢唱”。
金子咒罵道:“討——厭!”
“丑—八—怪!”
“還不快,滾——出來!”
透過上面幾句簡單的話語,觀眾似乎覺得金子十分討厭仇虎,并對仇虎的到來表現(xiàn)出愛理不理的狀態(tài),而器樂部分卻緊湊活潑,充滿生氣,實(shí)際上是暗示金子的內(nèi)心充滿著期待已久的喜悅心情,從而達(dá)到了器樂與聲樂部分的立體性整體構(gòu)思。
三、“詠嘆調(diào)”與“宣敘調(diào)”的鏈狀關(guān)系
“支點(diǎn)與鏈環(huán)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詠嘆調(diào)”往往是全劇的框架,是支點(diǎn)。主要用于抒發(fā)人物情感,揭示人物內(nèi)心活動(dòng),并且易于情感的升華。因此,作曲家通常都會(huì)較為重視。“宣敘調(diào)”則是全劇各個(gè)“詠嘆調(diào)”框架之間的鏈環(huán),是線條。主要用于交代故事情節(jié)、描述沖突背景、激化人物矛盾、展現(xiàn)戲劇沖突。通讀《原野》歌劇總譜會(huì)發(fā)現(xiàn),隨著戲劇化音樂劇情的發(fā)展需要,作曲家除了同樣注重“詠嘆調(diào)”外,還較多地運(yùn)用了“宣敘調(diào)”。這類“宣敘調(diào)”大多由相同或相近的音樂素材發(fā)展變形而成,從而達(dá)到全劇的對比與統(tǒng)一。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能簡單將金湘所運(yùn)用的“宣敘調(diào)”理解成對過去傳統(tǒng)西洋古典歌劇中“帶音高說話”演唱形式的一種“復(fù)制”。筆者認(rèn)為,這是一種包含了“演唱、對唱、對白、吟誦”等多種說唱形式的“綜合體”。作曲家力求在樂隊(duì)的伴奏行進(jìn)中,使音樂同劇中人物的“道白、對唱、吟誦”等細(xì)小部分緊密結(jié)合,而音樂本身又可單獨(dú)游離出來。同時(shí)在音樂與語言的關(guān)系方面還大膽借鑒了中國戲曲韻白的神韻、古典詩詞吟誦的方法以及說唱音樂中的形式,從而賦予“宣敘調(diào)”以各式中國特色。如第三幕之二《焦母與仇虎的對唱之一》中焦母的一段臺詞:“霧騰騰天陰沉,我看見你人頭落了地,鮮血四處噴,閻王要來收你的尸,招你的魂!”作曲家讓焦母使用了一種似唱非唱、似說非說的“吟誦式”演唱,伴以樂隊(duì)中低沉詭異的大提琴和奏以固定節(jié)奏的木魚聲,三者之間緊密融合,立刻獲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樂戲劇化效果。
客觀來看,這種手法的運(yùn)用不能簡單等同于話劇舞臺上的“對白”“朗誦”或傳統(tǒng)西洋歌劇意義上的任何一種歌唱類型,其藝術(shù)處理方式所獲得的音樂戲劇化效果更具東方性、民族性色彩。這反映出金湘先生在實(shí)際創(chuàng)作中注重發(fā)揮各種表現(xiàn)要素的舞臺戲劇作用,在整體構(gòu)思下使之形成了一個(gè)含有“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詠敘調(diào)”、臺詞道白、吟誦、樂隊(duì)背景及舞臺感等多層次的大系統(tǒng),其中每個(gè)要素既獨(dú)立又綜合,缺一不可。
結(jié)語
綜上所述,歌劇《原野》作為中國當(dāng)代歌劇中的一部成功作品,與過去傳統(tǒng)歌劇創(chuàng)作模式、寫作方法、指導(dǎo)思想、立意構(gòu)思上有著較為明顯的不同,特別是反映在“音樂與戲劇的整體融合”“聲樂與器樂部分的立體構(gòu)思”“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的關(guān)系處理上,值得我們認(rèn)真思考與積極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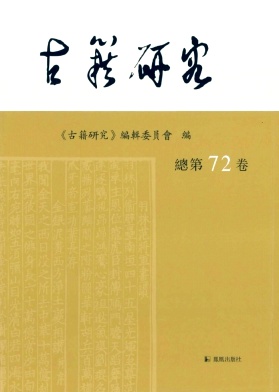
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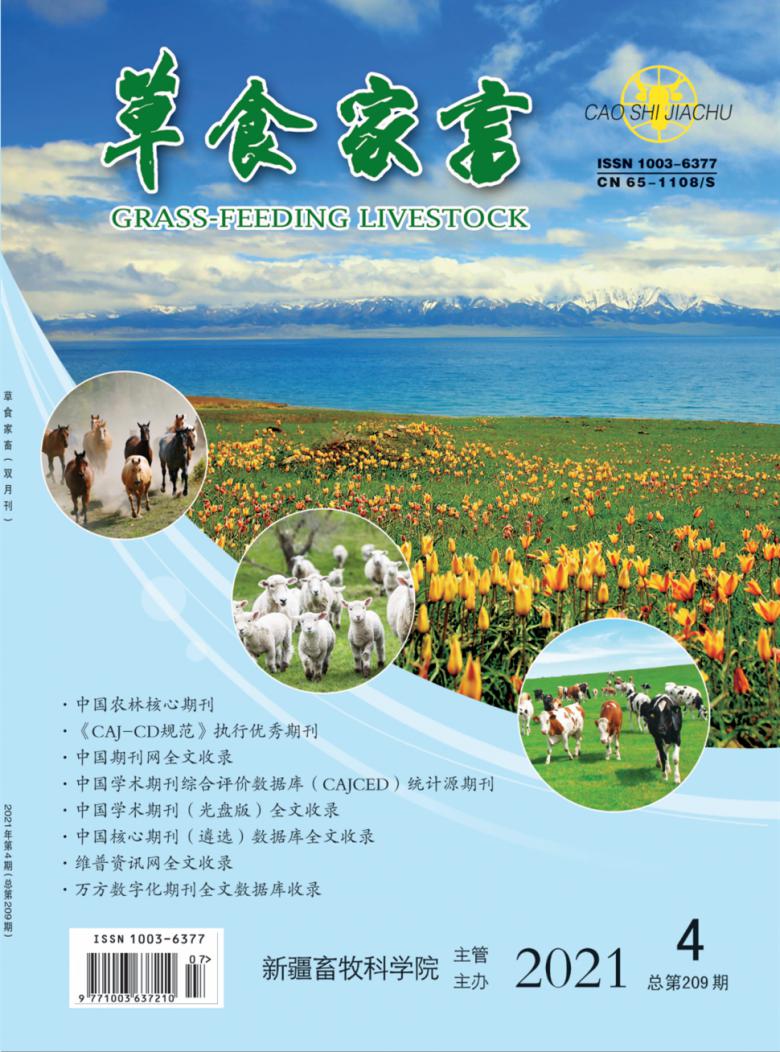
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