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xué)如何向我們敞開(kāi)?——評(píng)《儒家倫理爭(zhēng)鳴集》
鄧曦澤
當(dāng)儒家“倫理”被我們以目前的方式做喋喋不休的爭(zhēng)論時(shí),透顯的卻是儒學(xué)和中國(guó)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近代境遇。由于列強(qiáng)入侵,振興失敗,國(guó)勢(shì)日衰,到甲午五四之際,部分精英喪失了民族自信,從而掀起反古思潮和運(yùn)動(dòng),到五四時(shí)期發(fā)展到極致,到文革時(shí)期走向極端,至今未絕。中華民族幾乎被連根拔起,至今未著地。
隨著國(guó)際大氣候的變化,反古思潮時(shí)時(shí)翻新。西方學(xué)界正在熱切追蹤全球普遍倫理,國(guó)內(nèi)雖然總是晚幾步,卻也有人聞風(fēng)而動(dòng),起來(lái)指責(zé)儒家倫理,從而引發(fā)了有關(guān)儒家倫理的爭(zhēng)論。這場(chǎng)爭(zhēng)論,首先由儒家的反對(duì)者挑起,本文稱(chēng)之為正方。為儒家不平則鳴的回?fù)粽撸疚姆Q(chēng)之為反方(另外還有中立方),雙方以“親親互隱”為中心,展開(kāi)爭(zhēng)論。這場(chǎng)爭(zhēng)論中的主要文章,被收入郭齊勇主編的《儒家倫理爭(zhēng)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本文凡引該書(shū),隨文注明作者姓名,再加“文”字表示該作者的文章,如果需要,則加注該書(shū)頁(yè)碼)。本文就該書(shū)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問(wèn)題,尤其是我們?nèi)绾螌?duì)待儒學(xué),如何讓儒學(xué)向我們敞開(kāi)作一評(píng)論。
正方的目的是回到生活,以自己的理論解釋生活問(wèn)題。那么,正方一定有這樣的生活出發(fā)點(diǎn):現(xiàn)實(shí)生活出了困境,所以才討論某些問(wèn)題,尋求理論的解釋和解答。那么,是生活的哪些方面還是全面地出了問(wèn)題?因此必須找出問(wèn)題之所在。從正方的文章看來(lái),正方的目的主要不在倫理上,而在政治上,認(rèn)為今天的社會(huì)徇情枉法、任人唯親、貪污腐敗。但是,正方認(rèn)為,癥結(jié)表現(xiàn)在政治上,病灶卻在倫理上。因此,把不良政治之原因歸咎于儒家倫理。正方認(rèn)為,儒家倫理是血親倫理,它的出發(fā)點(diǎn)是具體的關(guān)系,沒(méi)有普遍性,會(huì)導(dǎo)致政治腐敗(劉清平文、黃裕生文),因此,正方的基本問(wèn)題是:儒家倫理是否具有普遍性?
不管問(wèn)題的答案是什么,這種發(fā)問(wèn)已經(jīng)作了太多的立場(chǎng)、價(jià)值和邏輯的預(yù)設(shè),概言之,唯西方馬首是瞻,立場(chǎng)壓倒一切。因此,反方對(duì)正方這種問(wèn)題方式作了回應(yīng)和批評(píng)。反方認(rèn)為,正方乃是照搬西方的倫理,以之裁剪中國(guó)文化,導(dǎo)致正方在討論時(shí)已經(jīng)犯了“失語(yǔ)癥”,“只會(huì)轉(zhuǎn)述、重復(fù)人家的話(huà),匍伏在西方強(qiáng)勢(shì)的話(huà)語(yǔ)霸權(quán)之下,而對(duì)于自家的、人家的論說(shuō),卻缺乏深度的全面的理解”(郭齊勇文,p8、10)。反方還認(rèn)為,正方的問(wèn)題與甲午五四以后的許多問(wèn)題相比,不過(guò)換了一種源理論,投射到傳統(tǒng)的領(lǐng)域也有變化,但是,它跟中國(guó)有沒(méi)有哲學(xué)、儒家是不是宗教等等這樣的問(wèn)題的發(fā)問(wèn)邏輯完全沒(méi)有區(qū)別。這種發(fā)問(wèn)方式已經(jīng)設(shè)定了外在的標(biāo)準(zhǔn),是追問(wèn)一個(gè)儒學(xué)(對(duì)象)符不符合某個(gè)現(xiàn)成標(biāo)準(zhǔn),而不是就儒學(xué)自身進(jìn)行發(fā)問(wèn)。這種發(fā)問(wèn)總是把儒學(xué)籠罩在西方的陰影下,而無(wú)法凸現(xiàn)儒學(xué)自身的問(wèn)題(鄧曦澤文)。
因此,如何發(fā)問(wèn)就至關(guān)重要。而問(wèn)題不是憑空而發(fā),它當(dāng)然導(dǎo)源于生活困境。如果把生活與歷史(如儒學(xué))相關(guān)聯(lián),在歷史中尋找問(wèn)題及其原因時(shí),對(duì)文本本身的解讀就是正當(dāng)發(fā)問(wèn)的基礎(chǔ),也才可能建構(gòu)我們與歷史,我們之間的基本的對(duì)話(huà)平臺(tái)。
要想發(fā)問(wèn),要想質(zhì)疑儒家倫理,首先得認(rèn)真閱讀并比較準(zhǔn)確地理解儒家文獻(xiàn)。正方立論的主要文獻(xiàn)依據(jù)是《論語(yǔ)》和《孟子》中的與“親親互隱”相關(guān)的三個(gè)案例:父子相隱、舜棄天下和舜封象。正方通過(guò)對(duì)三個(gè)案例的解讀,得出幾個(gè)結(jié)論,認(rèn)為儒家倫理基于血親關(guān)系,沒(méi)有普遍性,容易孳生不良政治。
正是在解讀文獻(xiàn)這個(gè)基礎(chǔ)工作上,雙方產(chǎn)生了極大的分歧。反方幾乎無(wú)一例外地指責(zé)正方誤讀文獻(xiàn)。《<孟子>的誤讀》(楊澤波文)直截了當(dāng)?shù)刂赋龇捶秸`讀文獻(xiàn)。《也談“子為父隱”與孟子論舜》指出“不能脫離整個(gè)《孟子》文本去討論……必須領(lǐng)悟、通曉孟子的機(jī)巧,孟子的深刻及孟學(xué)的整個(gè)預(yù)設(shè),尤其是仁義內(nèi)在、性由心顯的思想內(nèi)核和天道性命的觀(guān)念”(郭齊勇文,p17)。
反方指出,我們今天對(duì)古文獻(xiàn)的閱讀和理解,“一般都有兩個(gè)缺陷,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受西化影響太深”(楊澤波文,p89)。反方也基本一致認(rèn)為,儒學(xué)不是不能批評(píng)。恰恰是儒學(xué)自其誕生之日起,對(duì)它的批評(píng)沒(méi)有中斷。葉公、桃應(yīng)、萬(wàn)章,就已經(jīng)對(duì)儒學(xué)的主張產(chǎn)生了質(zhì)疑,至于諸子百家之間的爭(zhēng)鳴則綿綿不斷。而正方的問(wèn)題,其實(shí)與萬(wàn)章的問(wèn)題差不多,都是在質(zhì)疑舜這樣使用權(quán)力是否合理,是否能夠普遍化地執(zhí)行。“居今之世,人們不是對(duì)儒家相當(dāng)隔膜,就是動(dòng)輒即批判”(文碧方文,p358),這正是今人對(duì)儒學(xué)的不同情不了解之表征。如果說(shuō),我們今天再去質(zhì)疑古人,應(yīng)該追求比古人的質(zhì)疑更高明。怎么樣才能更深刻、準(zhǔn)確地發(fā)問(wèn)呢?首先要有“文獻(xiàn)學(xué)功底”,同時(shí)要有“人文學(xué)關(guān)懷”。在此基礎(chǔ)上,才有可能比較準(zhǔn)確地解釋文獻(xiàn)、評(píng)價(jià)文獻(xiàn)(楊海文文)。
怎樣才能比較準(zhǔn)確地解讀文獻(xiàn)?反方指出,“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詮釋方面,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兩種立場(chǎng)之間的沖突始終存在,而從80年代以來(lái)國(guó)際學(xué)壇的走向來(lái)看,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普遍主義的詮釋方法和立場(chǎng),明顯占了上風(fēng)……就方法論而言,此種詮釋有可能導(dǎo)致兩方面的問(wèn)題:一是以哲學(xué)詮釋取代歷史詮釋……二是‘偽普遍主義’盛行”(鄭家棟文,p473-474)。“劉教授(引者案:指劉清平)采用一種普遍主義立場(chǎng),將儒家重視‘血緣親情’的歷史問(wèn)題普泛化”(吳根友文,p549。此文對(duì)爭(zhēng)論雙方比較中立)。反方認(rèn)為正方把特殊當(dāng)普遍,再把被普遍化了的特殊作為標(biāo)準(zhǔn),裁判其他;認(rèn)為正方斷然地以二元對(duì)立來(lái)處理倫理問(wèn)題,不過(guò)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學(xué)的某些觀(guān)念的拼湊和堆砌,向壁虛構(gòu)本相和普遍(胡治洪文)。
反方比較一致地認(rèn)為,要?dú)v史地解讀文獻(xiàn)。如何才能歷史地解讀?反方認(rèn)為應(yīng)該象陳寅恪說(shuō)的那樣具有“了解之同情”(歐陽(yáng)禎人文,p250),認(rèn)為由于正方缺乏了解之同情,致使正方由于沒(méi)有吃透原典,而與反方有太大的差距(歐陽(yáng)禎人文,p265)。
不僅對(duì)于儒學(xué),更廣泛地說(shuō),對(duì)于歷史,都應(yīng)該了解地同情并同情地了解。盡管儒學(xué)在近代以來(lái)已經(jīng)遭到了極大的摧殘,但是,同情決不是強(qiáng)者對(duì)弱者的憐憫,而是設(shè)身處地、情同手足。因?yàn)榫唧w的寫(xiě)作場(chǎng)景、寫(xiě)作方式,尤其是寫(xiě)作技術(shù)的限制,加之流傳中產(chǎn)生的亡佚訛誤等等原因,導(dǎo)致古書(shū)難讀,并不是今人的發(fā)現(xiàn)。陸九淵就說(shuō)“《論語(yǔ)》中多有無(wú)頭柄的說(shuō)話(huà)”(《象山語(yǔ)錄》)當(dāng)我們考慮這些限制因素,就是在替古人考慮了,在同情在了解中了。正是考慮到這些,我們才可能努力認(rèn)真地閱讀古書(shū),查閱文獻(xiàn),相信古人如此說(shuō)話(huà)不會(huì)沒(méi)頭沒(méi)腦,總有具體的緣由(對(duì)外國(guó)文獻(xiàn)也應(yīng)這樣),力求弄清楚以后再下意見(jiàn),而不是拿一本古書(shū)翻翻:“哦,原來(lái)不過(guò)如此!”
以前,人們批判儒學(xué)“以理殺人”、“以公滅私”,強(qiáng)調(diào)公(德)而忽視甚至閹割了私(德),因?yàn)槿藗冋J(rèn)為凸出個(gè)人(甚至單子式的個(gè)人)是建立民主社會(huì)的理論前提。因此,有些人為了證明儒學(xué)的現(xiàn)代價(jià)值,則努力闡發(fā)儒學(xué)的功利主義、個(gè)人主義、重視私人或者個(gè)人私欲的思想(如對(duì)宋明理學(xué)的事功派進(jìn)行功利主義闡發(fā))。但在這場(chǎng)爭(zhēng)論中,正方對(duì)傳統(tǒng)觀(guān)點(diǎn)進(jìn)行翻案(劉清平文,p853),對(duì)儒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倒轉(zhuǎn)過(guò)來(lái)。正方抓著一些儒家重視親情的文獻(xiàn),把血緣親情當(dāng)作儒家倫理的根本特征,認(rèn)為儒學(xué)倫理講私德不講公德,或者說(shuō)私德壓倒公德。真是歷史在諷刺——正方的解讀和批判似乎在對(duì)我們說(shuō):“風(fēng)水輪流轉(zhuǎn)”。
正方認(rèn)為“孔子和孟子把本根至上的‘血親情理’視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把“血親情感看成是人們從事各種行為活動(dòng)的本原根據(jù)”(劉清平文,p855),導(dǎo)致以私德壓倒公德。從文獻(xiàn)看,《論語(yǔ)集釋·子路》“吾黨之直躬者異于是”下引程瑤田說(shuō)“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wú)私。此非過(guò)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ài)物。”不管程瑤田的批評(píng)對(duì)不對(duì),但可以肯定的是,當(dāng)時(shí)非但不缺乏對(duì)大公無(wú)私的強(qiáng)調(diào),而且有可能強(qiáng)調(diào)過(guò)甚。雖然僅此一例足以證明正方對(duì)問(wèn)題所涉及的基本文獻(xiàn)的誤讀(甚至根本就沒(méi)有讀),但還有幾則文獻(xiàn)需略加指出。《尚書(shū)·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孔安國(guó)傳曰:“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禮記·禮運(yùn)》:“天下為公。”鄭玄注:“公,猶共也。”“公共”一語(yǔ),大約首見(jiàn)于《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這不僅說(shuō)明儒學(xué)重公,而且尖銳地提出了一個(gè)文獻(xiàn)解讀問(wèn)題:如何讓儒學(xué)乃至任一理論本真地向我們敞開(kāi)?
反方對(duì)正方的回?fù)簦C合如下。第一,正方的立論前提有雙重錯(cuò)誤。(一)、正方嚴(yán)重誤讀儒學(xué),對(duì)儒學(xué)的本質(zhì)的認(rèn)定是虛假的,導(dǎo)致其“事實(shí)前提”虛假。就三綱五常而言(三綱五常并非古代倫常的全部,而是其最主要的),君臣、朋友關(guān)系都不是基于血緣的,而且夫婦關(guān)系本身也不是基于血緣的,而是盡可能地遠(yuǎn)離血緣(避免近親結(jié)婚),所以,去掉君臣、夫婦、朋友三倫來(lái)概括儒家倫理之本質(zhì),如何可能不以偏概全,導(dǎo)致前提虛假?(二)、三綱五常之“三”和“五”已經(jīng)是多,已經(jīng)是在具體上講的(同時(shí)又是天人一貫的),沒(méi)有誰(shuí)說(shuō)某種關(guān)系是普遍的,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其中之一作為倫理的根據(jù)。(反方不少論者指出,儒家倫常的根據(jù)在于天道,天道下貫顯現(xiàn)為心性。)所以,正方說(shuō)血親關(guān)系沒(méi)有普遍性,就跟說(shuō)鹿不是馬,圓規(guī)不能測(cè)量長(zhǎng)度一樣正確而無(wú)聊。基于這兩點(diǎn),反方揭露了正方完全是制造“假想敵”,認(rèn)為其立論根本沒(méi)有有效的事實(shí)基礎(chǔ),其所謂的事實(shí)和根據(jù)不過(guò)是盲人摸象,是對(duì)儒學(xué)的整體性誤讀——執(zhí)于一偏,以偏概全,并通過(guò)誤讀對(duì)儒學(xué)進(jìn)行封殺。
第二,倫常關(guān)系極為重要,如果在功用上考察,制度本身的倫理原則就體現(xiàn)了由個(gè)人之利到公共(國(guó)家、天下)之利的推擴(kuò)(陳明文)。但是,基于血緣的倫常只是倫常之部分,它的功用也只是有限的而不是任意泛化的,泛化會(huì)把它逼迫到理論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困境,反而導(dǎo)致對(duì)倫常的批判和瓦解。
即使按照正方的觀(guān)點(diǎn),我們要建構(gòu)現(xiàn)代的公民社會(huì),也要注意,公民社會(huì)主要是在政治角度談的,是指如何建構(gòu)政治性的公共領(lǐng)域,它的運(yùn)作主要依靠公共權(quán)力而不是依靠道德或者親情倫常關(guān)系。但公民社會(huì)完全沒(méi)有否定親情倫常的作用,因?yàn)檎喂差I(lǐng)域或者政治公共生活不是社會(huì)生活的全部,更不是個(gè)人生活的全部。在公共權(quán)力不能涉及和不應(yīng)涉及的生活領(lǐng)域,非權(quán)力的運(yùn)作就至為重要。譬如,現(xiàn)代社會(huì)無(wú)論與傳統(tǒng)社會(huì)有多大不同,個(gè)人基本上都還生活在家庭中。家庭(生活)無(wú)論如何都還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的重要構(gòu)成,并且還有圍繞家庭產(chǎn)生的親屬,從而構(gòu)成個(gè)人-家庭-親屬這樣的由己及人,由近及遠(yuǎn)的推擴(kuò)的三重關(guān)系的倫常結(jié)構(gòu)——它是個(gè)推擴(kuò)結(jié)構(gòu),而不是現(xiàn)成的固定的結(jié)構(gòu)。在這個(gè)倫常結(jié)構(gòu)中的生活,就是倫常生活。個(gè)人-家庭-親屬這個(gè)倫常結(jié)構(gòu)和倫常生活主要是基于血緣的(朋友關(guān)系不在此),并且既有非政治性的公共生活領(lǐng)域,也有私人的生活領(lǐng)域。譬如,結(jié)婚既不只是個(gè)人也不只是夫婦雙方的事情,它連接了父母(家庭),還連接了親屬,因此結(jié)婚這種倫常生活就關(guān)涉許多人,呈現(xiàn)為由己及人、由近及遠(yuǎn)的推擴(kuò)(結(jié)構(gòu))。只要個(gè)人的倫常生活不越出已經(jīng)被公共權(quán)力規(guī)定的界限,公共權(quán)力就不能也不應(yīng)介入。當(dāng)我們?cè)趥惓I钪杏懻搯?wèn)題的時(shí)候,情或者人情——不管是親情還是友情,也不管是否基于血緣——就極端重要。正常的親情關(guān)系和生活(關(guān)系是在生活中構(gòu)成的)非常顯著地幫助個(gè)人安頓身心。反之,當(dāng)倫常生活打破常態(tài),如夫婦不和、父子不和,不但影響當(dāng)事人,而且由近及遠(yuǎn)地影響家庭和親屬(如影響孩子的正常成長(zhǎng)),從而影響社會(huì)的穩(wěn)定、協(xié)調(diào)與和諧。因此,如果在功用上看,格物致知、親親尊尊、推己及人,就具有巨大的維系社會(huì)穩(wěn)定的作用。古代重視倫常生活,并形成了一套倫常規(guī)范和理論。今天,我們建構(gòu)現(xiàn)代生活,非但不應(yīng)去瓦解中華民族的倫常生活,相反,應(yīng)該積極維護(hù)它,幫助人們安頓身心,維系社會(huì)穩(wěn)定。為什么要批判、瓦解它呢?[①]統(tǒng)觀(guān)世界,無(wú)論中國(guó)、西方還是其他地方,無(wú)論不同的國(guó)族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有多么不同,倫常生活都非常重要。
在具體的解釋細(xì)節(jié)上,譬如,正方從攘養(yǎng)這件事中推論出“不管父親干什么罪惡勾當(dāng)(比如父親殺爺爺),兒子又有何理由不隱而蓋之呢?……”(黃裕生文,p960)反方則駁斥了這種“深度邏輯學(xué)”的荒謬,認(rèn)為正方“犯了以不完全歸納方法得出一個(gè)大前提,并按照大前提進(jìn)行無(wú)限推理的邏輯錯(cuò)誤”(鄧曦澤文,p417)。《論語(yǔ)集釋·子路》“吾黨之直躬者異于是”下對(duì)父子相隱也說(shuō)得非常明白:“何故隱?正謂其事于理有未安耳。則就其隱時(shí),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惻隱羞惡之中,并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wú)所枉也。茍有過(guò),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就在隱之際,說(shuō)明隱之人已明天理人欲、公私之是非。“情與理必相準(zhǔn),天理內(nèi)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內(nèi)之天理,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這就說(shuō)明隱不是可以隨意泛化、推演的。這些解讀,似乎僅僅是細(xì)節(jié),其實(shí)非常緊要,因?yàn)檎秸墙柚鷮?duì)文獻(xiàn)細(xì)節(jié)的解讀鋪墊立論的事實(shí)基礎(chǔ),然后從這些無(wú)可置疑的“事實(shí)”出發(fā),進(jìn)行推理、批判,而實(shí)際上,這是結(jié)論蘊(yùn)含在前提中的暗渡陳倉(cāng)手法,其推理和批判早已蘊(yùn)含在對(duì)細(xì)節(jié)的解讀中了,故不可不察。
在文獻(xiàn)解讀中,正反雙方有一個(gè)重大差異,就是如何對(duì)待五四之際以來(lái)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和中國(guó)人的失語(yǔ)。首先需要明白的是,用西學(xué)解釋中學(xué)而導(dǎo)致的失語(yǔ)是對(duì)文獻(xiàn)(歷史)的遮蔽。我們處身五四以后的歷史-現(xiàn)實(shí)語(yǔ)境,誰(shuí)也很難說(shuō)他完全沒(méi)有受用西學(xué)解釋中學(xué)的影響,誰(shuí)也很難說(shuō)他完全沒(méi)有失語(yǔ)。但目前的首要的問(wèn)題是,如何對(duì)待失語(yǔ)?這“如何”有兩層含義,一是持什么態(tài)度,二是如何實(shí)際地貫徹這種態(tài)度。反方大致認(rèn)為,失語(yǔ)是我們不可否認(rèn)的當(dāng)下的實(shí)然,但絕不是應(yīng)然。我們承認(rèn)我們的當(dāng)下處境難以擺脫,但是我們決不能自認(rèn)為我們目前的失語(yǔ)也就是處處依傍西方是合理的——否則就是奴才!我們的使命是突出重圍!我們應(yīng)該做的是:如何擺脫失語(yǔ)?這不僅僅是學(xué)術(shù)獨(dú)立的訴求,更是歷史-傳統(tǒng)-文化自己言說(shuō)自己重新扎根和滋長(zhǎng)的訴求。反方飽含憂(yōu)患和焦慮,并努力試圖自己言說(shuō)自己。譬如,《論劉鑒泉先生的<<大學(xué)>、<孝經(jīng)>貫義>》(歐陽(yáng)禎人文)就是一篇較少使用西方概念的文章。既然我們今天解讀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都首先要求在它自身的概念、話(huà)語(yǔ)、思維系統(tǒng)中進(jìn)行自我解釋?zhuān)瑸槭裁次覀兘庾x儒學(xué)、解讀自己的歷史文獻(xiàn)不應(yīng)該這樣呢?而進(jìn)入文獻(xiàn)自身的概念、話(huà)語(yǔ)、思維系統(tǒng),進(jìn)行自我解釋?zhuān)苍S才是最本真、最有效的解蔽。
由于失語(yǔ),導(dǎo)致正方把父子相隱、舜棄天下和舜封象這三個(gè)案例納入儒家“倫理”去做“倫理學(xué)”考察。如果一定要用西方話(huà)語(yǔ)來(lái)說(shuō),并承認(rèn)倫理或道德與法律、政治是有區(qū)別的,那么,對(duì)三個(gè)案例就不能作、至少不能主要作倫理學(xué)的分析,而更應(yīng)該作法理學(xué)或者政治學(xué)的分析。案例1的“其子證之”之“證”,是法律上的告發(fā)的意思(《論語(yǔ)集釋》的不少相關(guān)解釋都是在法律上層面上講的)。如果當(dāng)時(shí)的法律允許這樣做,父子相隱就是合法的。具體的法律規(guī)定并不以抽象的普遍性為前提,也不追求什么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因時(shí)宜而制定,處理有限范圍內(nèi)的事情。案例2和3更是舜作為天子的政治行為,直接涉及權(quán)力之使用。所以,正方在運(yùn)用西方理論時(shí),搞錯(cuò)了對(duì)象,用圓規(guī)來(lái)量速度,用天平來(lái)稱(chēng)顏色。這說(shuō)明正方既誤讀了儒學(xué),也誤讀了西學(xué),然后在雙重誤讀之上大談儒家“倫理”。
至于誰(shuí)在努力解蔽已經(jīng)被五四之際以來(lái)的解讀遮蔽了的儒學(xué)和歷史,誰(shuí)在繼續(xù)遮蔽滿(mǎn)面塵灰的儒學(xué)和歷史,讀者可以在閱讀中自行分辨。
正方認(rèn)為儒學(xué)阻礙了我們的生活、阻礙了我們向以西方為標(biāo)準(zhǔn)的現(xiàn)代化前進(jìn)。雖然正方也說(shuō)不能把造成腐敗的一切原因都?xì)w咎于儒家思想,但是儒家的血親情理精神會(huì)在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深度層面上,為腐敗的產(chǎn)生“提供適宜的溫床”,儒家思想在造成腐敗中“難辭其咎,無(wú)法推卸它所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的那一部分責(zé)任”(劉清平文,p895-896)。[②]
針對(duì)之,反方指出:“今天,徇情枉法、任人唯親、貪污腐敗所以公行,有今天的經(jīng)濟(jì)、政治、社會(huì)、法律、思想、制度、道德?tīng)顩r、文化氛圍、個(gè)人修養(yǎng)、價(jià)值觀(guān)念等等方面的多重原因,不能由歷史上的孔孟儒學(xué)來(lái)承擔(dān)責(zé)任,更不能把帳算到親情倫常上,那時(shí)推卸今人的責(zé)任”(郭齊勇文,p19)。
這里的爭(zhēng)論逼顯出如下問(wèn)題:儒學(xué)阻礙了誰(shuí)?如何阻礙?這兩個(gè)問(wèn)題都蘊(yùn)含了一個(gè)前提:儒學(xué)能自行阻礙(人的活動(dòng))。是這樣的嗎?當(dāng)批判儒學(xué)時(shí),儒學(xué)就成為在批判者之外的對(duì)象。因此,問(wèn)題立馬前進(jìn)到:對(duì)象或者作為對(duì)象的儒學(xué)何以可能阻礙我們?
作為對(duì)象的儒學(xué)一定不可能象主體(人)一樣地能自行活動(dòng),能自行作用。它不能自行影響人。只有人讀它,儒學(xué)才可能而不是必然影響人。如果人不讀它,則它就是死物。我們當(dāng)然承認(rèn)儒學(xué)有自身的含義,但這個(gè)含義未經(jīng)閱讀,則無(wú)法呈現(xiàn)。是讀者使儒學(xué)(或者任一理論)成為活物,是讀者這個(gè)主體使儒學(xué)對(duì)讀者發(fā)生作用,而不是儒學(xué)這個(gè)對(duì)象(客體)自行對(duì)讀者發(fā)生作用。儒學(xué)如何對(duì)讀者發(fā)生作用呢?只有通過(guò)理解、判斷和選擇。如果說(shuō)文本的含義在閱讀中呈現(xiàn)出來(lái),那么大體可以說(shuō),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會(huì)教人貪贓枉法,胡作非為。儒學(xué)講的道理對(duì)不對(duì),每個(gè)讀者都有自己的判斷。如果說(shuō)儒學(xué)中有什么不良的東西,讀者拒絕它不就行了嗎?讀者是自由的。儒學(xué)有什么思想是一回事,它能對(duì)讀者產(chǎn)生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如果說(shuō)讀者無(wú)法改變?nèi)鍖W(xué)本身的思想或含義,那么,他卻一定有權(quán)利、有責(zé)任,更重要的是有自由理解、分析、裁判和選擇它的思想,有自由決定其思想對(duì)自己產(chǎn)不產(chǎn)生作用,產(chǎn)生什么樣的作用。如果不這樣,這是讀者的自我放棄,而不是儒學(xué)的責(zé)任。孔子說(shuō)“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就已經(jīng)告訴了我們?nèi)绾紊髦貙?duì)待儒學(xué)嗎?為什么要把責(zé)任推卸給儒學(xué)呢?所以,批判對(duì)象化了的儒學(xué)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但是,經(jīng)過(guò)閱讀,儒學(xué)的某些思想被接受,成為行動(dòng)的思想資源,發(fā)用為生活,它就不再是對(duì)象,因此,我們的討論就轉(zhuǎn)入下一步。那么,如何對(duì)待已經(jīng)成為思想、生活的儒學(xué)呢?可以肯定的是,當(dāng)發(fā)現(xiàn)思想和生活出現(xiàn)問(wèn)題的時(shí)候,批判是必要的。但問(wèn)題是:批判指向誰(shuí)呢?是儒學(xué)還是我們的思想?(當(dāng)進(jìn)行批判時(shí),儒學(xué)和思想都被推出批判者而成為對(duì)象,即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對(duì)象。)答曰:自我批判——接受批判的應(yīng)該是我們的思想,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并用以指導(dǎo)生活的儒學(xué),也就是我們的內(nèi)心世界。如果說(shuō)儒學(xué)的某些東西錯(cuò)了,從而錯(cuò)誤地影響了我們(的思想),那么,即使批判了儒學(xué)這個(gè)對(duì)象,仍然不能解決我們自身的業(yè)已存在的思想問(wèn)題,我們?nèi)匀槐仨毞祷刈陨恚辞笾T己,進(jìn)行自我批判,才能解決思想問(wèn)題,從而解決生活問(wèn)題。這正是儒學(xué)所說(shuō)的“反求諸己”,“克己復(fù)禮”。把造成思想問(wèn)題和生活問(wèn)題的責(zé)任推卸給儒學(xué),難道不是怨天尤人,難道不是歸咎歷史,逃避責(zé)任?!
最后想說(shuō)的是,不知這場(chǎng)爭(zhēng)論是殊途同歸,還是道術(shù)之為天下裂,有人往而不返?在這場(chǎng)討論中,無(wú)論就立場(chǎng)、方法,還是言說(shuō)方式,雙方的差異都很大。雙方并沒(méi)有一個(gè)基本的對(duì)話(huà)平臺(tái),恐怕只有各種各樣的公共的說(shuō)話(huà)場(chǎng)所。《儒家倫理爭(zhēng)鳴集》就是這樣的說(shuō)話(huà)場(chǎng)所。作為反方的先鋒和主力,也作為《儒家倫理爭(zhēng)鳴集》的籌建者,郭齊勇先生能夠主動(dòng)地營(yíng)建公共的說(shuō)話(huà)場(chǎng)所,讓雙方的爭(zhēng)論在這個(gè)場(chǎng)所中集中展開(kāi),讓讀者在這個(gè)場(chǎng)所中全面地統(tǒng)觀(guān)這場(chǎng)爭(zhēng)論。此書(shū)基本上收集了正反雙方的主要文章,并收集了一些相關(guān)的但沒(méi)有直接介入爭(zhēng)論的文章,匯集成這本五顏六色的《儒家倫理爭(zhēng)鳴集》。也許正因?yàn)槲孱伭攀菭?zhēng)鳴,也才具有公共性,也才是群而不黨。盡管雙方?jīng)]達(dá)成基本的一致,但雙方的主要觀(guān)點(diǎn)、方法等等,基本上都已說(shuō)完,故這個(gè)話(huà)題或許可以暫且擱下。“述往事,思來(lái)者”,后人可能重提舊事,但希望也相信,后人能夠了解地同情并同情地了解他們的歷史,與為儒學(xué)復(fù)興、為民族復(fù)興的奮斗者情同手足,感受儒學(xué)復(fù)興和民族復(fù)興的歷史涌動(dòng)!
--------------------------------------------------------------------------------
[①] 至于那些依托倫常關(guān)系建立的權(quán)力紐帶(即通常說(shuō)的裙帶關(guān)系),問(wèn)題不在于倫常關(guān)系本身,而在于權(quán)力者濫用權(quán)力。倫常關(guān)系跟權(quán)力裙帶關(guān)系之間沒(méi)有因果關(guān)系,不能胡亂追究責(zé)任,傷及無(wú)辜,把濫用公共權(quán)力造成的政治腐敗歸咎于親情倫常,破壞正常的倫常生活。
[②] 正方的邏輯,基于兩個(gè)前提:前提1:對(duì)社會(huì)作經(jīng)濟(jì)、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關(guān)系。其中,儒學(xué)屬于文化領(lǐng)域,腐敗屬于政治領(lǐng)域,另外還有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由此而影響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發(fā)展。(筆者已作文《近代以來(lái)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邏輯”批判》,對(duì)反古邏輯作了詳細(xì)分析。)
計(jì)師.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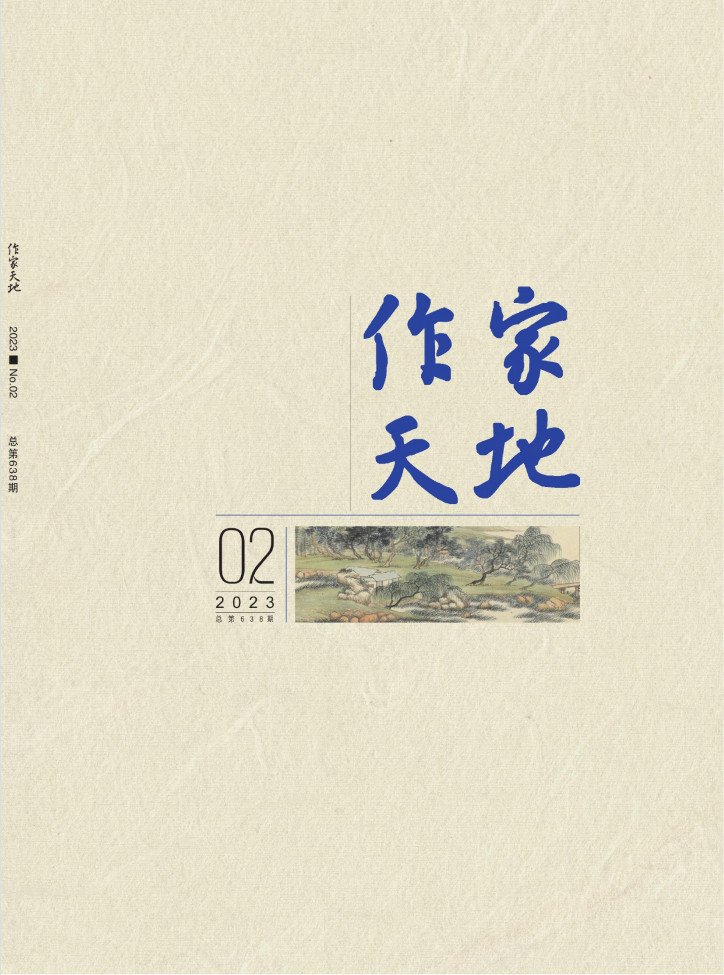
代英語(yǔ).jpg)
.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