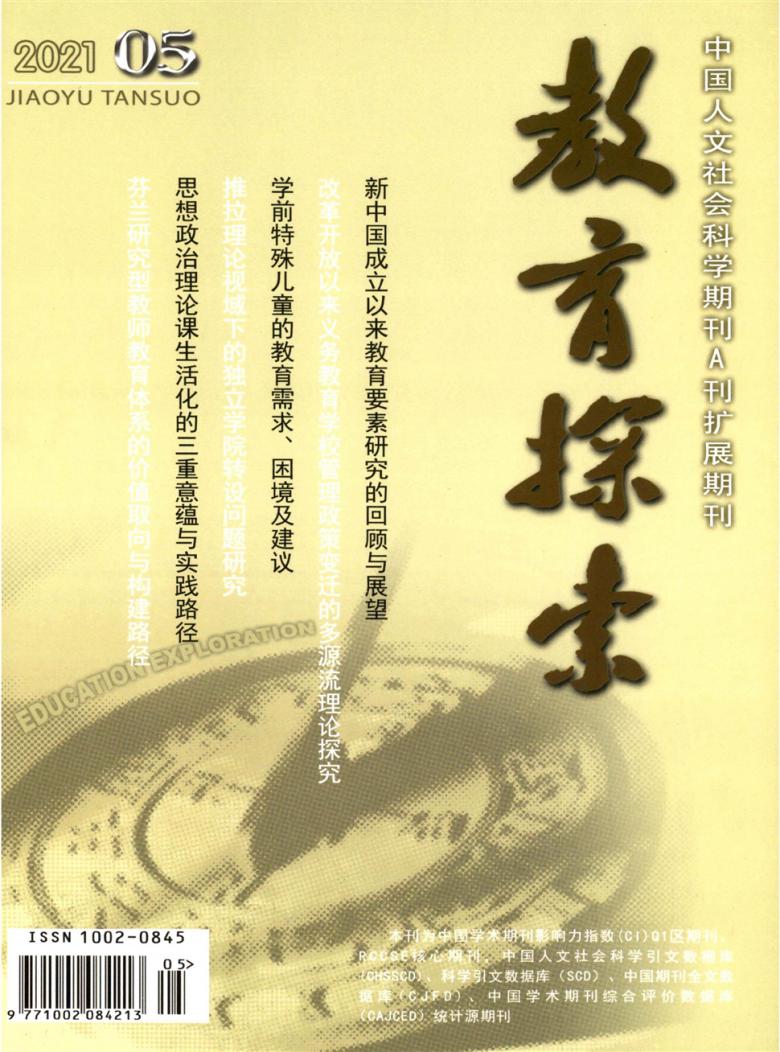傳統·普遍性·現代化——讀《儒家倫理爭鳴集》并對雙方分歧的再反思
丁為祥
內容摘要:學界關于儒家親情倫理的爭論主要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對儒家倫理的評價問題,分歧主要表現在對傳統的不同心態上;第二層次則是儒家倫理有無普遍性蘊涵與現實意義的問題,其分歧主要在于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不同的智慧形態與研究進路上。此外,對中西文化的不同取資、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不同選擇,則既構成了這一爭論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這一爭論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新世紀之初,學界發生了一場關于儒家倫理的大爭論,其起因主要源于劉清平對儒家親情倫理的批評。批評儒家倫理是劉清平先生的一貫立場 ,但此次批評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腐敗日益成為國人關注焦點的條件下,將其與儒家的經典相聯系,認為儒學自形成起便包含著腐敗的基因。劉清平的這一批評實際上是20世紀反傳統思潮的繼續,但其批評的具體內容則具有“與時偕行“的特點。比如說,當現實需要反復辟的時候,儒家(孔子)就是”復辟狂“,當需要反保守的時候,儒家又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當需要反腐敗時,儒家理所當然地就是腐敗的“始作俑者”。劉文的這一批評馬上激起了郭齊勇先生的反對,所以,他也在同一刊物(《哲學研究》)上撰文對儒家倫理進行辯解,并批評劉對儒家經典的簡單化理解。倆月之后,《哲學研究》又刊發了署名穆南珂的文章,對郭文進行反批評。由此之后,《中國哲學史》、《哲學動態》、《復旦學報》、《中山大學學報》、《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等一系列刊物相繼介入爭論,數十名學者參與論戰,一場關于儒家親情倫理的爭論就這樣展開了。2004年,當雙方的觀點都得到基本的表達時,作為論戰方之一的郭齊勇先生,為了總結這一爭論的理論成果,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爭論雙方的論文進行了系統的收集,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結集出版,這就是《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一書的由來(以下凡引爭論文章,均只注該書頁碼,而不再注明原發表刊物)。
對于這場爭論,筆者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與批評儒家倫理的幾位學者也都有過文字的交流甚或當面的磋商。現在,當爭論的塵埃落定,——全部爭論文章集結為書呈現于世人面前時,作為曾經參與爭論的筆者本人,能否對雙方的分歧作出某些反思呢?本著溝通、交流,“不有益于人,必有益于己”的想法,特撰這一“反思性“的文章,以表達自己對雙方分歧的再把握。
如上所言,這場爭論既然是20世紀反傳統思潮的繼續,并且也是由一貫堅持批評傳統的劉清平先生所挑起的,因而其相互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對傳統的不同態度,或者說就集中在是積極地繼承傳統還是消極地拋棄傳統這一基本的價值取向上。
比如說,當劉清平以《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第888——896頁)挑起這一爭論時,其目的本來就是為現實生活中的腐敗現象探尋歷史或文化的根源,所以他寫道:“在現實生活中,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不正之風或是腐敗行為,諸如走后門、拉關系、裙帶網、行賄受賄、以權謀私等等,往往也是利用某些特殊性的團體私情(除親情外還有愛情、友情、鄉情、恩情等等)作為突破點或是潤滑劑,憑借‘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概念(即認為特殊性的團體私情可以高于普遍性的法則原理)大行其道。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度層面上,孔子和孟子自覺確立的主張血緣親情至高無上的儒家根本精神,正是這種‘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觀念的始作俑者”(第895—896頁)。這一追根溯源性的類比(推理),說明劉清平本來就是為了現實的問題而深入歷史的。而這,正構成了他對儒家倫理大加討伐的基本出發點。
本來,由探尋現實現象的根源而深入歷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并沒有什么不可。問題在于,劉先生深入歷史的目的既不是為了澄清歷史的真相,也不是為了照歷史的鏡子,而是因為要給現實問題以歷史的說明或追溯現實問題的歷史根源而不得不涉及歷史,并要以現實的視角給歷史以新的裁定。這樣,雖然其資料的爬梳、征引已經進入了歷史,但對資料進行分析與解釋的主體卻全然停留于現實的此岸。如此以來,與其說是劉先生進入了歷史,沉入于歷史的情境之中,不如說他是高坐現代的審判臺,而歷史的案例、資料則隨著劉先生視角的需要而不斷地呈現。果然,在《論孔孟儒學的血親團體性特征》(第853——887頁)一文中,孔孟儒學就不得不隨著劉先生的視角與標準進行自我呈現:
在血親團體性與個體性和社會性之間不存在對立沖突的情況下,他們(孔孟儒家——引者)的有關主張必然會迫使個體性和社會性依附并從屬于血親團體性,甚至導致個 體性和社會性受到后者的約束限制而無法獲得充分的發展;而在血親團體性與個體性和社會性之間出現了對立沖突的情況下,為了確保血緣親情的本根至上地位,他們的有關主張更是會迫使個體性和社會性否定甚至消解自身,以致人的整體性存在僅僅被歸結為血親團體性存在(第862頁)。
在這里,“個體性”、“團體性”與“社會性”自然都代表著劉先生的現代視角,而孔孟的“孝弟”、“仁愛”包括“泛愛眾”則代表著歷史的舊案。劉清平的“簡捷”之處在于:他全然不管孔孟思想中是否包含這種“個體性”、“團體性”與“社會性”的劃分,卻一定要以之作為裁定孔孟思想的標準,所以后者就不得不在劉先生的現代剪裁下一一呈現:既然“他們”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要維護其“血親團體性”,那么,這不導致腐敗又會導致什么呢?
為了將儒家的這一特征徹底證實,劉先生還找來了歷史的“旁證”,并通過儒家對它們的批判反證儒家的“血親團體性”特征:
盡管楊朱主張的“為我”要比儒家更為重視人的個體性,墨子主張的“兼愛”要比儒家更為重視人的社會性,但孟子卻明確認為:由于他們并沒有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的團體性“人之大倫”視為本根至上的最高原則,因而只能是“無君無父”的“禽獸”(第873頁)。
楊朱的“為我”與墨翟的“兼愛”都曾遭到過孟子的批判,但孟子的批判是有儒家學理——萬物一體之仁的依據的。今劉先生既不需要弄清儒家本身的學理依據,也不需要弄清孟子要求在楊墨二者之間“執中有權”的具體指謂,更不需要澄清楊朱與墨翟的主張究竟是什么樣的個體性和社會性,只要他們都反對儒家并且遭到儒家的批評,自然對劉先生有用;而只要劉先生將其“個體性”、“團體性”與“社會性”的“明鏡”一經高懸,儒道墨三家馬上就一個蘿卜一個坑地顯現出自己的本真面目。而對儒家來說,由于其既反對楊朱的“為我”——個體性,又反對墨翟的“兼愛”——社會性,那么,除了導致腐敗的“血緣團體性”這條死胡同,儒家還有什么路可逃呢?
既然儒家已經被釘死在“血親團體性”這張“腐敗溫床”上,那么從廣泛的社會效應的角度看,它又會起什么作用呢?自然,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壓抑”社會公德的作用:
儒家倫理處理公德與私德關系的這種方式,已經蘊含著憑借血親私德壓抑社會公德的負面效應。這一點集中表現在:由于儒家倫理賦予孝悌私德以遠遠高于仁愛公德的終極意義,結果,在它倡導的道德規范體系中,只有血親私德才能夠成占據主導地位的核心內容,而處于依附地位的社會公德則必然受到前者的束縛限制,以致喪失自己的自律意義,難以獲得充分發展(第898頁)。
這就是說,由于儒家把“血緣團體性”看得至高無上,因而它不僅在社會層面上壓抑公德,而且由于其對社會公德的“束縛限制”,最后也必然喪失公德本身所具有的“自律意義”,——這就連私德也“難以獲得充分發展”了。既然儒學既是現代腐敗現象的精神根源,同時又“壓抑”公德、消解私德,那么,在這種條件下,儒學這種傳統社會的主流精神,還能對現代社會起什么作用呢?所以劉先生的結論自然是:“顛覆儒家傳統,摧毀儒家精神”。其所謂的“后儒家”論說,正是在“顛覆儒家傳統”基礎上——將儒學剪成碎片之后對儒學的再塑。
劉先生這種完全按現實需要來裁定歷史的方式遭到了郭齊勇先生的批評。按照歷史的還原原則,郭先生首先將這幾個“腐敗”案例還原于當時的歷史情境之中,認為在傳統的宗法社會,舜、孔子的做法有其深度倫理學的依據。簡而言之,其依據就在于:父子親情是最基本的人倫關系,而父子關系又是不能簡單地等同或直接化約為現代社會中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法律關系的;一旦父子關系完全化約為法律關系,那就成為“問題父子”(第13頁)了,——文革中“父子、夫婦間相互揭發,人人自危,那正是整個社會政治、倫理和家庭倫理出現大問題大危機的時候”(第13頁)。所以,在郭先生看來,所謂的“腐敗”,實際上是孟子依據儒家經、權統一的思想對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張力的一種“巧妙“化解,也是儒家的仁愛情懷與權衡分辨智慧高度統一的表現。至于當今的腐敗問題,那是有著復雜的現實成因的,完全將腐敗歸結為儒家對親情倫理的重視,“那是推卸今人的責任”(第19頁)。
由于郭先生堅持孟子的經、權統一思想并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來詮釋二者的關系,因而又遭到了穆南珂先生“雙重標準”的反批評。在穆先生看來,“在需要為這一原則的原始意義作辯護時,郭文用了‘特殊意義’的文獻考古;當需要闡發這一原則的當代意義時,郭文用了‘普遍主義’的詮釋”(第966頁)。穆先生批評郭文是“雙重標準”,按照反向推理的原則,他自然是堅持一元標準的,那么,其一元標準是什么呢?穆文一開篇就明確斷定:“‘父子互隱’的命題,既不為法律所容,又有違于倫理公德,其間的是非、道德明若涇渭,對任何一個奉公守法的正直公民都幾近常識……”(第964頁)顯然,穆文不僅在繼續著劉清平的論說,而且還將劉文以現實裁定歷史的方法推向極端,推到了絕對化的地步,即:當今的法律完全可以裁斷千古,任何以特殊主義為歷史舊案辯護的觀點,都必然會陷入穆先生所設計的“雙重標準”的泥潭。所以,對于劉清平與郭齊勇爭論的那幾個“腐敗”案例,穆先生不無“欣喜”地評論道:
無論把這種“舜之德”牽強附會到何種程度,都難以克服“孟子論舜”之理論上的兩難,即:要么認同雙重道德標準,要么放棄這種道德。無論那種選擇,都會把這種“親情”之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引者注)銷蝕殆盡(第969頁)。
到這里,對儒家親情倫理進行批評的觀點已經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這就是通過揭示儒家的親情倫理與“腐敗”之間的內在關聯再進一步打到儒家或“顛覆儒家”。所以,穆先生在宣布“這種‘親情’之德的普遍性和永恒性銷蝕殆盡”之后,馬上就以“大批判”的目光掃視整個學界,并對南懷謹、李澤厚(第965頁)以及以存在主義研究王陽明的“某著名教授”和某“泰斗級國學大師”一一進行批評,并斷定其對傳統的論說不過是一種“嘩眾取寵”與“信口開河”(第970頁)之論。
顯然,爭論雖然發生在如何理解儒家的親情倫理上,實際上則是整個20世紀繼承傳統與反傳統思潮的繼續。批評傳統的一方雖然是從儒家的親情倫理上提出問題的,其目的則在于對整個傳統的“顛覆”和“摧毀”。因為這種完全以現實裁斷傳統的心態與方法,在古與今、傳統與現代天然有別的前提下,必然會將整個傳統視為“歷史的陳跡”,也必然會以把傳統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視為自己的職志。至于所謂血緣親情及其與腐敗的關聯、對公德的壓抑等等,實際上不過是一個“與時偕行”的“靶子”而已。
正由于對儒家親情倫理的批判不過是一個暫時的“靶子”,所以隨著爭論的深入,雙方的分歧也就越來越明晰,越來越接近各自思想的內核。而這一點,又是隨著黃裕生先生的介入而成為現實的。在此前后,楊澤波、筆者包括一大批參與者也都從經、權兩層——普遍與特殊相統一的角度對儒家的親情倫理進行了辯解性的論證,——既論證儒家的親情倫理所曾經具有的歷史意義,同時也論證了儒家倫理所具有的超越于歷史條件——人之為人的普遍意義(還在此爭論之前,法學界就已經從中西法學比較的角度探討過中國倫理法的現代合理性問題了,參見范忠信先生的三篇論文:第601——713頁)。但是,隨著黃裕生的介入,這一爭論卻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轉向,即由儒家倫理是否必然導致腐敗的問題轉化為儒家倫理是否具有人倫普遍性的問題。所以,對于原來的爭論,這既是一個轉向,同時也是一種深化,深化到從現代的角度看,儒家的親情倫理是否還有其存在必要、還有其現實意義的問題。黃裕生先生正是從這一角度介入爭論的。
黃裕生從其所研究的西方哲學(康德)出發,先將所有的倫理學進行了一番普遍(本相)與特殊(角色)的二分與清理,并認為“只有在存在論層面澄清了本相與角色的區分,普遍倫理學才可能自覺地把本相當作自己的出發點;也只有這種存在論區分才能提供出一個人們可據以檢視一切傳統倫理學是否是一種普遍倫理學的普遍性視野”(第938——939頁)。顯然,黃裕生首先是要依據其所研習的西方哲學,提出一個可以裁決一切傳統倫理學的絕對標準;然后以此來權衡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有無存在的必要及其存在的現實意義問題。而從其《普遍倫理學的出發點:自由個體還是關系角色?》(第938——963頁)這一標題來看,他也是明確地以二者必居其一的方式,將儒家倫理押到了“活著,還是死去”的十字路口。
那么,作為黃裕生裁決一切倫理學之絕對標準的本相倫理學,其“本相”的涵義又是什么呢?在黃先生看來,每個人生來就具有自由意識,而對這種自由意識的自覺也就構成了其人之為人的本相;人只有先自覺其本相,然后才能擔當起各種功能性、關系相關性與歷史性的角色。倫理學也同樣,只有先建立起所謂本相倫理學,然后才有可能建立各種歷史性、功能性的角色倫理學。從這一標準出發,黃先生對儒家倫理評論說:“愛有等差,這是儒家倫理學中最荒誕、最黑暗的思想,它在理論上導致整個儒家倫理學陷于相對主義和特殊主義,從而否定一切絕對的普適性的倫理法則;在實踐上,則給實踐—踐履原則的過程留下了可以靈活的巨大空間,直至一切保證正義的絕對原則都喪失掉規范作用”(第952頁)。言下之意,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儒家倫理都非但不起正面作用,而且只能起極大的破壞作用;至于儒家倫理有無存在必要的問題,在黃先生看來,顯然已經無須再費口舌了。
為什么儒家倫理只能起負面作用呢?這是由黃裕生獨特的理論標準決定的。在黃裕生看來,“一種倫理學是否是普遍倫理學,從而是否承擔起確立與維護人間正義法則這一使命,在根本上取決于它是把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個體作為確立倫理法則的出發點,還是把人的關系存在即關系角色作為出發點”(第938頁)。由于作為儒家倫理之根本原則的“仁”實際上也只停留于父子兄弟等各種角色之間,所以它根本不是本相倫理學,只能是一種角色或關系倫理學,所以黃裕生又說:“儒家倫理學包含著大量違背本相倫理法則的角色倫理規則,它們實際上是在完全忽視甚至否定個體的自由存在的情況下被確立起來的”(第950頁)。“甚至連‘仁’這個最高原則本身都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因為它沒有非經驗的絕對根據),因此,它所倡導和維護的那種‘親愛’只是一種特殊之愛,而不是一種普遍之愛”(第953頁)。顯然,黃文之所以要否定儒家倫理,關鍵在于它缺乏本相法則、缺乏普遍性的根據。
那么,黃裕生所謂的普遍性又指什么呢?實際上,其所謂普遍性主要是一種抽象的或形式的普遍性,而其根源與依據也主要在于西方的一神教(基督教)傳統,所以,對于他的本相論說,他明確申明必須以基督教信仰為后援保證。如他說:“如果我們從一神教信仰,特別是基督教信仰來看,我們上面的觀點就更容易得到理解。……每個人首先是與唯一的神發生關系,才與他人發生關系,而且人與神的關系是人與人的關系的前提”(第948頁)。這就是說,構成黃裕生裁決一切傳統倫理學的絕對標準,完全是從西方的一神教中借來的;即使從哲學的角度看,黃文那種惟我獨尊、“物物(角色)而不物于物”的強悍邏輯說到底也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本質主義。但問題在于,經過20世紀的全球回歸思潮,到了新世紀的今天,無論是西方的一神教傳統還是抽象的本質主義,有沒有裁決一切民族傳統的資格?而對于中國的傳統倫理而言,它有沒有不需要論證——先天就具有裁決一切倫理的絕對地位?這就涉及到對普遍性含義的理解及其不同表現形態的把握問題了。
如所周知,中國人根本沒有一神教傳統;如果以基督教為宗教的標準,中國人甚至不信宗教,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那么,在這種條件下,以源于基督教的本相言說作為裁決中國傳統倫理的絕對標準,是否會陷于圓鑿方枘不相入的地步?從哲學的角度看,以西方抽象的本質主義作為裁決中國具體型智慧的標準,是否又會成為一種典型的橫截與偏取?進一步看,中國具體型的智慧是否就根本缺乏普遍性的關懷,從而也只能津津于各種功能性的角色言說呢?正是基于上述幾個方面的考慮,郭齊勇與筆者以《也談本相與角色》(第21——44頁)為題聯合撰文,既論儒家道德倫理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同時也兼答黃裕生先生。這就進入了爭論的第二個層次或第二階段。
在“也談”一文中,我們除了先“對黃文思路、觀點”提出幾點質疑外,專門分析被黃文定性為純角色性言說的儒家之“禮”與“仁”,以掘發其中的普遍性蘊涵。比如在“禮:蘊涵在角色中的本相意識”一節中,我們首先從禮的角色性特征出發,通過孔孟荀對禮的大量論證,說明“禮正是以其具體的‘節文’,表現著人的普遍而又共同的需要和規范。這種共同、普遍的需要與規范,就是貫穿在禮這種具體形式的‘變’中之‘常’(不變)的因素,亦即普遍性與絕對性”(第32頁)。至于被視為典型的禮之角色性表現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我們看來,也“蘊涵著人都不能脫離其具體角色這樣一種共同性與普遍性;而正是這種豐富多樣、繁復多變的角色,才蘊涵并表現出了人之為人這一人的本相含義及其共同性與普遍性”(第33頁)。所以,我們總結說:“人的本相究竟存在于哪里呢?從現實人生來看,它也就首先存在于各種具體的角色之中,因為人首先只有獲得各種角色的存在,然后才能通過具體的角色去體認、提煉并概括出自己的本相”(第34頁)。相反,“那種完全先于角色并獨立于角色的所謂‘本相存在’,實際上只是思辨哲學的邏輯虛構,其關系也只是思辨邏輯的關系而不是現實人生中本相與角色的實際關系”(第34頁)。
由角色性的“禮”到作為根本原則的“仁”,儒家倫理表現出了更多且也更強的普遍性色彩:“一方面,‘孝弟’、‘忠恕’、‘愛人’等等固然已經是為仁,但對整體的作為本相的‘仁’來說,卻不過是其具體而又相對的節目時序,——所謂角色性的表現而已;另一方面,作為與圣并立的仁——即整體上體現‘仁’的仁人,則是一種理想性的境界或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第37頁)。這就是從孔子、子思(《中庸》)到孟子一直堅持“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以“仁”為人之為人之本相的根本原因。正由于儒家論仁的這一特點以及“仁”本身含義的多重性、復雜性與有機性,所以儒家的“仁”既不是孤絕的信仰,也不是干枯而又抽象的純形式(本質),它始終存在且也表現于各種具體的角色之中,而“它所蘊涵的絕對與相對、普遍與特殊不僅不是二元對立、互相排斥的關系,反而是互滲互證、并且是始終融為一體的”(第40頁)。孔子的“禮”、“仁”如此,孟子的“心”、“性”亦是如此,直到宋明,朱子的天理論、陽明的良知說概莫不如此,有誰能夠否定其中的普遍性蘊涵呢!問題在于,由于儒家倫理中的普遍性與絕對性始終是內在且也表現于特殊而又具體的角色之中的,是二者統一的表現,因而只有從孤絕的信仰主義或抽象的本質主義出發,才會對其中的普遍性與絕對性視而不見,從而試圖將其逼向特殊主義與相對主義的死角。
這樣,關于儒家倫理有無普遍性蘊涵之爭,實際上也就成為一種中西文化之爭了,——是以西方文化來裁決中國文化還是以中國傳統來理解儒家倫理之爭。黃文之所以堅決否定儒家倫理的普遍性蘊涵,關鍵在于他的標準是完全來自西方的,是以西方的抽象智慧(信仰主義與本質主義)來裁決中國的具體智慧,所以得出了否定性的結論。而我們之所以與黃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也主要因為我們是以具體來詮釋特殊和相對,因而所謂特殊就不僅僅是特殊,——與普遍彼此外在;所謂相對也不僅僅是相對,——與絕對彼此對立,而是同時蘊涵普遍性與絕對性于其中的具體,是二者的同時并在與當下統一的表現。這可能就是我們與黃裕生的主要分歧所在。
作為理論“爭鳴”,隨著《文集》的編定,同時就已經截至了,但作為思想的分歧則仍然在繼續。那么,這一由數十位學者參與、長達數年的論爭,其發本要歸性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筆者以為,這無非是兩個問題:其一即不同的思想取資問題;其二則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不同選擇問題。
首先,從思想取資來看,從劉清平到穆南珂再到黃裕生,雖然其具體觀點不無差別,但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模式,這就是以現實裁定歷史、以西方裁定中國。比如說,劉清平是直接從現實的腐敗問題而追根于儒家的親情倫理的,穆南珂斷定儒家親情之德的普遍性會“銷蝕殆盡”也是同樣的邏輯;而黃裕生以盜賊之子為“法院院長”的假設尤其表現了這一特征。這說明,在對儒家倫理的評價中,批評的一方確實存在著從現實需要出發來裁定歷史的問題。相反,對儒家倫理進行辯解與詮釋的一方,雖然其具體觀點也不盡相同,但卻都能堅持一種還原歷史情境的方法,——穆南珂對郭齊勇“雙重標準”的批評,正是后者堅持歷史的還原原則的表現。這自然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與方法。那么,為什么會形成這種差別呢?這就與其不同的思想取資與出發坐標有著割不斷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就是其不同的思想取資與參照坐標的直接表現。比如說,對儒家倫理進行批評性研究的一方,其思想資源無疑都直接或間接地源自西方,也是在中西橫向比較的大背景下展開其對歷史與傳統的裁定的。而相反的一方,無論是對儒家倫理進行歷史性的疏解還是現代性的詮釋,其思想則都存在著一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立場與主體性背景;其之所以能對儒家倫理堅持疏解與詮釋的態度,也與其自覺的主體繼承性立場分不開。這樣,就思想取資而言,我們完全可以說這一爭論實際上是中西文化在對儒家倫理評價問題上的分歧表現。
那么,從西方文化、哲學的背景出發是否就無法與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進行順暢的溝通呢?其實也不盡然,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與把握甚至并不亞于中國學者(參見本文集中美國與德國學者的一組論文,第762——828頁)。實際上,這里的不同文化不過構成了其研究的一種較為遙遠的背景而已,而在具體的研究中,直接起制約作用的往往是研究者對傳統的不同心態,正是這種不同的心態,既決定著其不同的思想取資,同時也直接決定著其研究的視角與結論。之所以說這一爭論是20世紀反傳統思潮的繼續,主要是因為,經過近一個世紀反傳統思潮的熏陶,批判傳統已經成為國人的一種重要的心理積習了:只要現實不如人愿,只要現實出現了什么問題,國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訴之于對傳統的批判,并試圖通過對傳統的批判來說明現實、改進現實。劉清平從現實的腐敗問題追根于儒家的親情倫理,又由親情倫理(所謂團體性私德)說明儒家對社會公德的壓抑作用,就典型地表現著處處以傳統來說明現實,并處處以傳統為現實承當責任的心態。當然,這同時也可以說是一種通過批判傳統以改進現實、推進現實的嘗試與努力。
但最為重要的是,為什么對儒家親情倫理的批判激起了人們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實際上,這才是這一原本單方面的批判最后能夠演變為爭論的根本原因,也是這一爭論的根本意義之所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國人的現代化追求,主要表現為向西方學習;所謂現代化也就意味著西方化。而中國傳統,則代表著現代化追求的主要阻力;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就要唾棄這種傳統。在整個20世紀,這幾乎是國人的常識,穆南珂之所以對“國學”或“東方文化”深表反感,正是這種“常識”的表現;而黃裕生之所以能夠以唯我獨尊的心態面對除西方外所有的民族傳統,則是這種“常識”的信仰化或積淀為“信仰”的表現。但是,經過一個世紀的追求與實踐,現代化已經不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明顯地呈現出多元的色彩。各個民族也完全可以根據自己不同的民族傳統,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不必一味地效法西方、惟西方馬首是瞻。因此,這一爭論雖然只表現為對儒家倫理的評價問題,實際上則是我們以何種精神為思想資源、從而又以何種精神走向現代化的表現。所謂不同的思想取資,實際上也就首先決定于人們對現代化道路的不同選擇,而傳統則正為我們的選擇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當然,數十名學者對儒家倫理的捍衛、疏解與詮釋,并非說儒家倫理就完美無缺、不可批評,也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借鑒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成功經驗,而是說,我們只有先確立民族精神的主體性,才能談得到真正的借鑒與吸取。所以,作為前提的前提,我們也只有首先對自己的民族傳統保持足夠的敬意,保持積極理解與開放詮釋的心態,才能在經歷一個多世紀的反傳統思潮之后,贏得民族精神的真正復蘇,從而也才能以我們的傳統、我們的精神,走出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