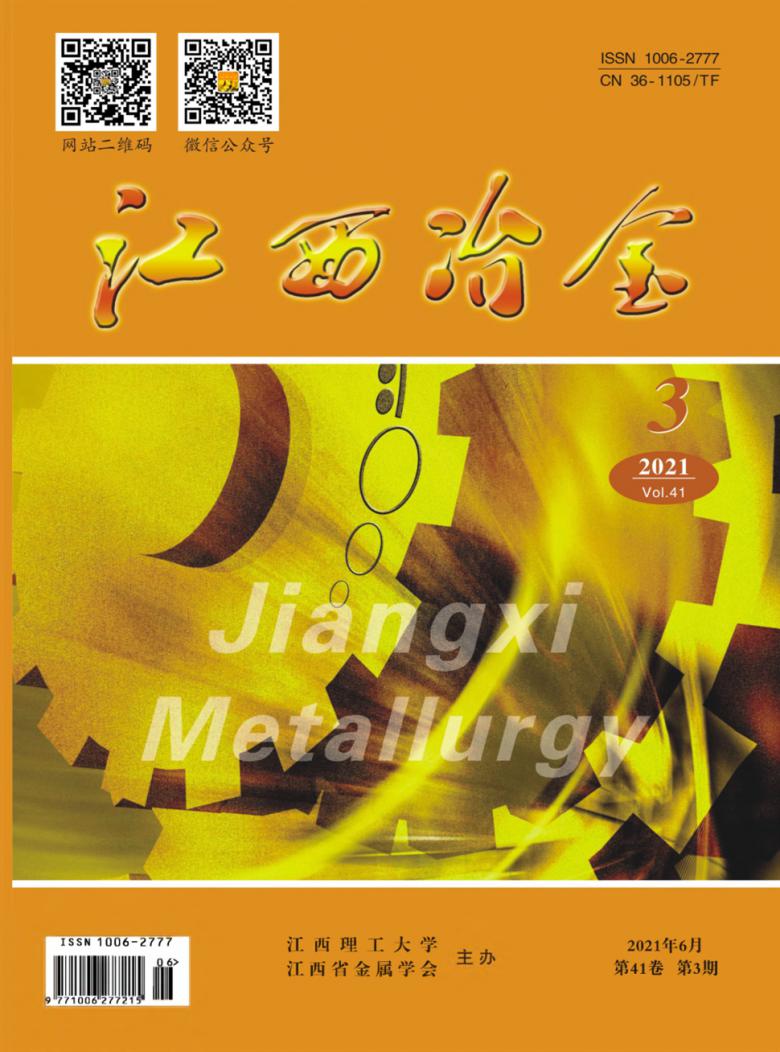關于大眾傳媒的符號救濟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基于符號資本的視角[1]
袁靖華
關鍵詞: 大眾傳媒 符號資本 農民工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關轉型期中國城市化成敗的核心問題之一。單純依靠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政策法規,僅能推動表層的社會融入;而要實現深層理念意識層面的社會融入,則離不開符號生產者和傳播者——大眾傳媒發揮的社會整合功能。基于符號資本理論,通過對代表性城市媒體報道的文本解析,對大眾傳媒的話語符號生產及新生代農民工擁有符號資本的實際狀況展開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大眾傳媒的符號生產機制與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號資本之間存在緊密聯系:新生代農民工符號資本的赤貧是其城市融入過程中遇到的重大“符號障礙”;大眾傳媒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符號生產者,有必要通過提供信息平臺、正名和擴大話語權等具體的符號救濟途徑,幫助新生代農民工提升符號資本,消除“符號障礙”,進而促進其融入城市社會。
一、問題的提出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融入問題已成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目前相關社會學研究主要有四個研究視角:一是以社會排斥與社會距離為視角,強調農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礙。二是以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為視角,注重揭示農民工是否具備融入的社會關系資源。三是以人力資本為視角,關注農民工文化教育水平與融入的關系。四是以社會認同為視角,深入農民工文化心理歸屬與身份認知,探討融入的標志和衡量標準,研究圍繞身份認同、社區歸屬感等展開。社會學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們在融入城市過程中的現實困境,尤其是身份認同的心理危機,試圖從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層面找到原因。但是,相關研究卻忽略了推動身份認同得以實現的象征符號體系在社會權力運作當中的動力機制。不少社會學者籠統地認為大眾傳媒在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現代人格確立、心理健康、身份認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遠春,2005;許傳新,2007),但未就此展開研究,也沒有從社會象征符號生產的視角,研究大眾傳媒發揮上述促進作用的具體路徑。
傳播學界相關研究主要在籠統、寬泛的弱勢/邊緣群體(含農民工)范疇內進行。可歸納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論視角,研究農民工媒介形象及媒體報道,注意到都市媒體的農民工新聞報道對該群體社會身份建構有影響(馮恩大,2004;張慧瑜,2007;李艷紅,2006;許向東,2009)。二,農民工媒介話語權和利益表達研究(衛夙瑾,2004;楊敦顯,2005;時艷釵,2007),查找農民工失語喪權的原因,側重媒體應如何維護農民工話語權。上述研究都強調大眾傳媒對農民工的影響與責任,但對大眾傳媒如何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未有進一步探討。三,農民工的媒介接觸/使用/消費的調查(陶建杰,2003;段京肅,2004),有學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對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絡建構的影響(曹晉,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數學者論及農民工媒介素養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馮恩大,2005),但未對該理論假設可行性作進一步深入探討。總之,傳播學界已從媒介形象、話語表達、媒介使用及素養等層面關注到農民工與傳媒的關系,并揭示了農民工在現有傳媒資源分配中的弱勢地位。然而,現有研究沒有結合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機制,進一步深入探討傳媒的“符號生產”是否可能及如何來推動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問題。
概言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關轉型期中國城市化成敗的核心問題。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農民工主體,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職業期望值、對物質/精神享受要求較高,“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較強。他們既不能適應農村,也無法融入城市,處于社會認同和身份認同雙重危機之中,從而易導致社會仇視心態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傾向,因此,其社會融入與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十分緊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楊建華,2008)。傳播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定群體的研究關注有待深入,尤其是關于傳媒如何推動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這一具強烈現實意義的課題未得到應有重視。鑒于此,本文立足符號資本理論,試探討大眾傳媒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符號生產及其作用機制。
二、研究視角與理論框架
(一)符號資本理論
“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這一概念由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號資本理論建構在“場域”概念基礎上。他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而決定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各種位置實際和潛在的處境;二是這些位置彼此之間的客觀關系。在場域中,位置與資本密切聯系,資本的多寡決定著行為者的處境。
布迪厄進而提出了四種資本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其中,經濟資本產生于經濟領域,可直接兌換成貨幣;文化資本涉及通過教育傳遞的各種正統知識;社會資本由與人們有價值的社會關系構成;符號資本則代表個人的榮譽和聲望,“是前述任一種資本都可體現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邏輯可以通過各種類別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認識到它的特殊邏輯”(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擁有符號資本,意味著其他資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認可。概括起來,符號資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號資本具備資本的再生產與轉換功能。一個人的符號資本來自其他個體/組織機構/群體的主觀認可和主觀感知。無論是身體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還是社會的資本,當“我們通過感知范疇把握這幾種資本時,這幾種資本呈現的就是符號資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資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轉化為符號資本,依賴于個體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資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歷史性場域中的其他個體/組織機構/群體“感知并認可為是合法的”(王異虹,2009:68-69)。個體擁有的其他資本形式一旦被社會認可,這些資本就能生成為符號資本,“符號資本以將聲望和名譽附加在一個家庭和一個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轉換回經濟資本,或許這是在一個社會中最有價值的積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號資本和其他資本之間相互轉換,并進一步實現各類資本互動式的增值循環,其生產與轉換關系如圖1所示:
第二,符號資本具有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即通過占有符號資本而取得支配社會資源和他人行為的象征權力。擁有符號資本可以獲得社會和他人的欣賞、尊重、敬意等,并進而獲得其它服務等(Bourdieu,1990:112-121)。符號資本的運作,是由社會場域建筑的制度和社會行動者共同參與的,并以對符號的信息認知方式存在。借助具體的符號,符號資本的象征權力將世界的區分原則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觀輸入給行動者,并作為交流和認知的結構被內嵌入行動者的身體,成為內在的感知體系,指導人們的價值判斷標準(Bourdieu,1989)。布迪厄認為,符號權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體的權力,包括“已經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體,或等待被建構的群體”(布迪厄,2001:306)。“符號資本是一種信譽……是一種建構的權力,一種通過社會動員造成新群體的力量,換言之,符號資本是社會群體權威代言人的權力,它只能作為一種長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終結果而獲得,即從該群體獲得造就群體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來指稱或描述個人、群體與制度的符號,能夠保全或改變社會中人們之間的聯合與區分、結合與離異、聚合與游離。
第三,符號資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賦予被認可者以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符號資本涉及到對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積累”(Bourdieu,1998:7),從而賦予資本的擁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來,權力的成功實施需要以合法化為基礎,而合法化則依賴于符號資本的獲取,符號資本是特定場域個體或群體被認可并獲取合法性的特殊資本形式。體現符號資本的符號表征體系則是行動者和社會之間的中介,具備認知、交流和社會區分等相關功能,既是行動者實踐的產物,同時也塑造和雕刻行動者的社會身份。
據符號資本理論來推論,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過程中,資本的多寡決定了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的權力分配和具體處境。而該群體符號資本的多寡則不僅直接反映其他各類資本的狀況,而且直接影響了他們能否具有符號權力、獲得社會合法性。
(二)大眾傳媒的符號生產
符號(symbol)是對客觀實體的表征,具有表達性和象征性。人類生存的世界不僅是一個自然的物質世界,而且是一個人造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的創造與維系依賴于人類通過符號進行傳播的能力。人的互動是以使用符號,通過理解或確定彼此行動的意義來實現的 (米德,1992:20)。在傳播活動中,媒介所運載的其實是各種符號,受眾所接受的也是各種符號。“傳播是人類通過符號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發生相應變化的活動”(邵培仁,2007:59),符號是傳播的核心要素,大眾傳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號生產意義、“命名”并書寫合法性——“在當代社會中,大眾傳播最可能成為完成這些過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會機制”,“(這種符號權力)在普遍公認的大眾傳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現得尤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當代大眾傳媒制造的符號,“處處以媒介為中介……帶進我們所有的生活空間和時間里”(胡春陽,2005),借助各類符號發布的“信息……是充滿象征標記和身份領地爭奪的‘權力場域’”(王建民,2008)。當代傳媒對現實生活強大的符號表述力,體現了其進行話語制造和意義再造的“社會建構”能力(斯蒂芬?李特約翰,2004:180,194)。麥奎爾總結道:大眾傳媒是一種權力資源,是獲取聲望與地位,并對現實生活擁有重要影響力的關鍵途徑;它提供經驗性、評價性的標準來幫助構建規范性的公共意義體系;并對偏離此體系的行為進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眾傳媒業作為話語權力的增效器以及話語生產場域的一種……以其自身的場域邏輯進行著這樣一種資本轉換的活動”(劉文瑾,1999)。因而,傳媒的話語符號生產同時是社會各方生產并爭奪符號資本的過程。
大眾傳媒正是借助符號生產機制,“形塑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幫助構建規范性的公共意義體系”,“有力地影響、操縱并變革社會”(Denis Mcquail,1994:1),“喚起和提高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認同程度”(斯蒂文?小約翰,1999:297),實現了它的社會整合功能。而且這種社會整合具有更強的持久性和穩固性,它可以進入社會個體的內心世界和意識深處,并且一旦進入就很難更改。正因為大眾傳媒通過話語符號的生產和傳播,具有推動社會整合、促進人的社會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為“社會水泥”。
據此推論,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和政策法規僅能夠推動表層的社會融入,而要實現深層理念層面的社會融入,則需要依靠話語、身份、儀式等表征符號的整合力量才能潛入意識深處。大眾傳媒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符號生產者,由此,以大眾傳媒的符號表達為切入口,研究大眾傳媒的話語符號乃至其中符號資本的生產,在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的影響與作用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與調查分析
以杭州為例,新生代農民工現已成為在杭農民工的主體。“杭州市外來求職民工中,34歲以下的占87.31%,而16—24歲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選擇在杭新生代農民工及其相關媒體報道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體資料來源于浙江日報集團旗下的網絡媒體“浙江在線”和杭州日報集團旗下的網絡媒體“杭州網”的相關新聞報道。這兩份網絡媒體集合了浙江日報集團、杭州日報集團旗下主要報刊媒體的所有新聞資訊內容,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報刊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關注情況。在“浙江在線”和“杭州網”上,以“新生代農民工”為關鍵詞檢索相關新聞報道,剔除不相關內容后,共檢索到相關報道114篇。詳細如下:在“浙江在線”上,檢索到相關報道62篇,時間跨度為2006-2010年;在“杭州網”上,檢索到相關報道52篇,時間跨度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運用傳播學研究常用的內容分析法,同時結合訪談和調查,解析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符號表達,進而探討這一群體在城市社會融入過程中的符號資本問題。
(一)媒體呈現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客觀資本匱乏——阻礙符號資本的積累與轉化
為便于分析,根據研究需要將報道內容歸為政府舉措、犯罪、心理問題、婚戀家庭、理想期望、教育問題、工作求職、經濟收入和維權等9大類。據統計,在114篇報道中,九大類內容的出現頻次如圖2所示:
媒體報道最多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求職問題,其次是經濟收入狀況。通過媒體報道,社會大眾可以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求職困難、多數從事低端工作、工資報酬低、收入來源有限。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地位上處于社會底層,其經濟資本的積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資本積累不足,則是影響他們經濟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原因:新生代農民工掌握的知識技能有限,主要為初中畢業,其次是高中和中專教育,很少獲得更高學歷。
媒體報道還較為集中地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問題。這兩個方面經常聯系在一起。新生代農民工多數抱有更高的職業期望和社會地位期望,他們以城市居民為參照對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僅僅滿足溫飽。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報道往往將這一對照引發的極端情緒和行為歸為犯罪的基本誘因。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情感孤獨問題,婚戀對象難找,社會人際關系網絡封閉單一,社會資本嚴重匱乏,但這方面的報道出現頻次最低。
綜上,媒體報道呈現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說明:這一群體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客觀資本較匱乏,處于社會弱勢地位,難以讓城市主流社會認可或承認,這直接影響了其符號資本的轉換與積累;新生代農民工對資本積累的高期望與實際資本的匱乏造成巨大落差,誘發了其一系列心理問題,成為一個“問題群體”,這進一步增加其“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積累”難度,嚴重阻礙其符號資本的獲取。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客觀資本分配中處于城市社會的底層,其身份地位處于城市社會邊緣,無法獲得爭取社會合法性權利賦予所必須的資本博弈力量。換言之,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客觀資本匱乏,缺少積累“聲望、名聲、奉獻或者榮譽”的基礎,難以達到城市主流認可的資本累積高度,很難獲得融入城市必須的符號資本。
(二)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稱謂:身份污名化——直接減損符號資本
稱謂是社會主流對一個群體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可的符號表征,其歷史變遷可以集中體現這一群體在社會場域當中所獲符號資本的微妙變化。大眾傳媒如何稱呼和命名一個群體,表面上體現了主流社會的話語表達對該群體的身份指稱,背后卻體現著該群體符號資本和符號權力的大小。
對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的稱呼,有一個歷史變遷過程。上個世紀對農民工普遍帶有強烈歧視性質的“盲流”等稱謂,自新世紀以來已較鮮見。在當下,國家越來越重視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對這一群體的稱呼除了“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務工人員”、“外來務工人員”等,甚至出現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鮮稱呼。筆者對這一群體的不同稱謂在“浙江在線”和 “杭州網”上出現的頻次分別進行了檢索、統計,結果如下:
比較發現,在“浙江在線”和“杭州網”上,每個具體稱謂出現頻次不一,但各個不同稱謂出現頻次的差異比例大致相同。媒體對該群體的稱謂,出現頻次最高的是“農民工”,其次是“外來務工人員”和“新生代農民工”。 而近年來為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鮮稱謂“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現了一定頻次,不過這些新鮮稱謂出現頻次遠遠低于“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和“外來務工人員”等稱謂。
那么,現實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是否認可那些高頻次出現的稱謂呢?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專項課題研究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民工”的稱呼并不認同,他們對市民身份的認同遠遠大于對農民角色的認同。全國總工會的調查也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中,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只有32.3%,認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傳統農民工10.3個百分點”。搜狐網在線調查則發現,在3920名網友投票中,83.05%的網友認為“農民工”這一稱謂帶有歧視性,80.42%的網友投票贊成取消“農民工”這一稱謂,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體現在稱謂的平等。筆者對部分在杭新生代農民工及用人單位作過深度訪談,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將“農民工”這一稱謂普遍視為一種身份歧視,并對此抱有比較強烈的排斥感。
個案1 秦某,女,22歲,高中文化,安徽潁上縣人,下沙高教園區服裝店營業員:“我高中畢業就出來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們很多老鄉都是這樣,我們戶口還在老家農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們和城里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受國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憑,為什么我們就非得被叫做農民工?”
個案2 王某,男,21歲,職高文化,河南信陽人,濱江高新技術開發區某工廠技術工人:“我爸、我叔他們都是農民工,他們那一輩人很多都是,他們沒讀什么書,長年在外拼老命賺錢,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們這一代能夠成才,不再像他們一樣做農民工。我讀了12年書,在職業高中學了電工技術,憑技術吃飯,這是靠自己讀書讀出來的。我現在還在準備自學考試。我是技術工人,還是個讀書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輩一樣繼續當農民工。也不要叫我們什么新生代農民工!”
個案3 靳某,女,34歲,大學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經濟開發區某企業人力資源部職員:“我們廠里招的工人大多數是外地來的年輕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農村戶口占了大多數。不過我們一般都稱他們工人了,沒有什么農民工不農民工的這樣叫他們的,他們也不喜歡這樣被人叫的。反正來廠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實際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并不認同“農民工”這一強加的命名。污名現象的出現是社會現實與大眾傳媒互動的結果。人們廣泛持有的共識或常識和意識形態一起決定了傳媒的話語選擇,傳媒話語又對其具有推廣、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樂國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會學家戈夫曼(E. Goffman)認為,污名是導致社會歧視的起點,作為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必然導致社會對他們的貶低、疏遠和敵視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這些污名標簽,令該群體游移于明確的合法身份范疇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識形態話語之下的“工人”/“農民”話語體系的包容,也無法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市民”、“公民”等話語體系,成為新舊話語體系共同拋棄的對象。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符號帶有歧視意義的原因不在于詞語本身,而在于農民工群體的符號資本匱乏和符號權力不足。“農民工”這一污名標簽,已經直接減損其符號資本,剝奪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會資源的符號權力,從而進一步阻礙了他們各類客觀資本的順利獲取和各類資本的增值轉化。由此,他們在就業、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許多方面遭受歧視和區別對待是必然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體現了這一群體的身份意識覺醒以及對符號資本的渴求。
(三)媒體報道新生代農民工的敘述方式:自我表達匱乏——限制了符號資本的積極獲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這一西方諺語,形象地說明人的自我表達與其身份的社會認同緊密相連。個體的自我由三個層面組成:自我展示、自我實現和自我的主動表達(斯蒂芬?李特約翰,2004:197),因此,“人們為了維護自身的自主權,不僅需要對自身的行動進行解釋,而且還需要對自身作出解釋”(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在大眾傳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達,有助于了解作為個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公眾當中得到自我呈現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筆者從敘述方式和信息來源兩個層面,對“浙江在線”和“杭州網”的114篇報道進行了文本敘事分析,結果如下:[2]
在“浙江在線”的62篇新聞報道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敘述主體,通過自我陳述方式表達自身話語的文獻有8篇,新生代農民工主要作為客體被他者呈現的有54篇。兩種敘述方式按年份比較對照如圖4所示:
在“杭州網”的52篇新聞報道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敘述主體,通過自我陳述方式表達自身話語的文獻有10篇,新生代農民工主要作為客體被他者呈現的有42篇。兩種敘述方式按年份比較對照如圖5所示: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媒體近年來的報道已開始逐漸重視引述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話語表達,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話語表述遠遠弱于被他者陳述的主流敘述方式。
進一步考察媒體報道的信息來源是分析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表達情況的另一路徑。在114篇文獻中,媒體報道的信息引述來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門,其次是權威專家、企業主和用人單位,最后才是農民工。按照信息源對新聞報道進行的分類,如圖6所示:
媒體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報道,其主要信源本應是作為故事“主人公”的農民工自身,但實際上媒體卻更傾向于政府、專家和用人單位。顯然,這種現象不能簡單地以新生代農民工主動運用媒體的媒介素養有待提高來解釋。媒體對主流話語的遵從,決定了它的敘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傾向于政府、專家和用人單位等擁有更多符號資本的社會精英群體。
然而,由于媒體的新生代農民工敘事更多采用他者陳述并以他者信源為主,削弱了新生代農民工向公眾進行自我解釋的自主權。新生代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自我呈現相當不足,其真實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話語所遮蔽。匱乏表達的自主性,結果就是“失聲”或被動的客體化呈現——作為一個被他者呈現的客體對象出現。
福柯認為“話語生產總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選、組織和分配的”,體現的是社會權力網絡的整體運作(福柯,2003: 406,417)。大眾傳媒是不同群體角逐符號權力最重要的話語平臺,“擁有信息和話語權力的人可以單方面地生產‘普適性’意義框架,進而將其灌輸給其他群體,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統的生產與傳播為機制的身份區分邏輯”(王建民,2008)。在大眾傳媒的話語平臺上,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呈現受到現有媒體敘事的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達權。由于經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陳述,其身份符號必然被他者的話語所塑造,從而難以成為自我身份建構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已然喪失了謀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號權力。這無疑成為阻礙其獲取符號資本的另一重障礙。
四、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媒體報道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客觀資本嚴重匱乏、身份稱謂污名化和自主表達權缺失等,充分說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號資本嚴重不足,符號權力明顯缺失。換言之,在當前大眾傳媒的話語生產機制中,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取融入城市必須的符號資本與符號權力。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僅僅是物質和制度層面的障礙,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符號障礙”(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勢地位、污名稱謂、非法身份、主體缺失等等都是“符號障礙”的集中體現。
較之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會的更好基礎。如何抓住這一群體的資質機遇,阻斷“符號資本貧困”的代際傳遞,消除“符號障礙”帶來的社會心理游離現象,進而幫助這一群體盡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會和農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眾傳媒可以作出獨特貢獻。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符號最重要的生產、傳播和賦予者,應當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符號救濟”,消除其融入城市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符號障礙”,改變其符號資本的赤貧狀態和符號權力的缺失現象。
(一)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臺
新生代農民工要融入城市社會,需要其自身經濟、社會、文化等客觀資本的不斷積累。各類客觀資本的提升有助于轉化為符號資本并實現各類資本增值。大眾傳媒首先需要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客觀資本的獲取提供信息支持。大眾傳媒作為信息提供者、傳播者,應當盡可能及時、有效地為新生代農民工免費提供求職、就業、培訓、維權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類信息,從而為新生代農民工提升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提供直接幫助。
同時,大眾傳媒應進一步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正面宣傳力度,著力發揮輿論引導職能,以公眾信息和社會共同認知的話語形式為該群體贏得社會公眾的積極關注和認可,提升其符號資本,融洽城市與新生代農民工的關系,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歸屬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動其成為具有現代特質的城市公民。如媒體對富士康系列跳樓事件的追蹤報道引發的社會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深切關愛,直接推動農民工獲得“加薪”、“減壓”等相關待遇。
(二)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過程,不單純是改變稱謂的文字修辭策略,更是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符號資本、被社會賦予合法性的過程。“除非一個社會群體具有足夠的資源和影響來左右公眾對另一群體行動的態度,否則污名就很難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匱乏客觀資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影響去除污名,這就需要大力依賴符號生產者和傳播者——大眾傳媒的符號選擇,賦予被污名對象“足夠的資源和影響”,“改造”社會公眾對該群體的“感知與認可”。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項名為“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運動,就是在社會與新聞共同推動下,去除語言中因傳統承繼下來的偏見,以創造一個對特定種族、宗教、性別、年齡群等社會弱勢群體的中性、無歧視的傳播與溝通環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稱有助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符號資本。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新一代城市產業勞動者的主體,他們是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主力軍。大眾傳媒有責任為他們消除“農民工”這一緊箍咒的符號魔力,確立起新生代產業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為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符號資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眾傳媒應該承擔起這一“去污名”的職責,主動對新生代農民工改用新生代產業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稱呼。“媒體心態與城市主流社會心態之間存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系”(劉力、程千,2010),因此,大眾傳媒主動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符號救濟”和去污名行為,對城市主流人群接納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進作用。
(三)大眾傳媒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賦予話語權
符號資本的獲取離不開話語權的獲取。新生代農民工要改變自身在傳媒話語權角逐中的缺席狀態,為自身塑造有尊嚴的形象與積極正面的社會聲譽,必須從被動接受他者的標簽轉變成為主動的發言人。新生代農民工提升自身符號資本,需要借助媒體的話語賦權,站出來為自己說話,說自己的話,而不是被動的、沉默的接受社會、城市和媒體強加的符號和標簽。農民工積極的自我表達(言語和行為)展現在大眾傳媒中,已經對這一群體的形象塑造產生了積極正面的影響。農民工周述恒撰寫網絡小說講述《中國式民工》,網上點擊率超過50萬次,就是新一代農民工積極自我表達并向主流媒體爭取話語空間的一種努力。
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僅需要自身積極主動的話語表達,更需要媒體的積極幫助。媒體應該在相關報道中更多地讓新生代農民工自己說話,而不是過多依靠對政府部門、用人單位或專家的采訪等各類他者陳述的敘事模式。媒體改變敘述方式,不僅僅是提高新聞可看性的一種敘事策略,對全面展現新生代農民工形象更有幫助。近兩年來,媒體上開始出現一些深度報道,在敘事角度、敘述方式上更多從農民工自我陳述出發,農民工在報道中不僅僅作為一個記者描述下的客體,更是記者采訪話筒前進行積極自我表達的主體。盡管這樣的表達和報道還不夠多,但這種生動的敘事形式,給讀者呈現出了更為形象、鮮活、可信的新生代農民工形象。身為社會之公器的大眾傳媒,應該走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工作和生活,專辟欄目、版面等為其提供更多更廣闊的話語空間,有意識地塑造有尊嚴、有追求、勞動光榮的新生代農民工媒體形象。像《農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國農民工》、《狀元360》等節目,就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個案1 貴州衛視自2007年開播的《農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國農民工》電視欄目,以農民工自我講述的第一人稱敘事,展示了一個個積極向上、健康勵志的農民工形象,同時還成功地推出了新時代的中國農民工群像,贏得了不俗的收視表現和社會效益。
個案2 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狀元360》欄目,以弘揚“勞動最光榮”為主旨,在一期“挖掘機騰空行走比賽”節目中,來自建筑工地一線的青年農民工憑借自己高超的專業技能,在全國電視觀眾面前展示了平凡勞動者不平凡的一面。節目將農民工打造為一個個知識技能型的電視勞動明星,塑造了農民工身為勞動者的光榮形象。
當然,大眾傳媒上述作用的發揮離不開政府、社會的支持和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積極參與。比如,在政府主導下開辟專門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服務的媒介渠道,為新生代農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溝通的平臺;建立起新生代農民工權益訴求與政府決策反饋的有效鏈接機制;開展新生代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提高他們的媒介使用素養和媒介表達素養,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開。
[注釋]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傳媒助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入的對策研究——以杭州為例”的成果之一,課題編號:B10XW03Q。 [2]此處以是否引述農民工的話語作為主要報道依據來作為分類標準。對所檢索到的新聞報道逐篇進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農民工自我陳述并作為其報道主要依據的文獻,均列入“自我陳述”式的報道中。而主要由記者、政府部門、企業主、專家、市民等非農民工為表述主體的文獻均列入“他者陳述”式的報道中。盡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類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觀性,但文本的細致分析還是能夠相對客觀的看出農民工自我的話語表述在主流媒體中的總體呈現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