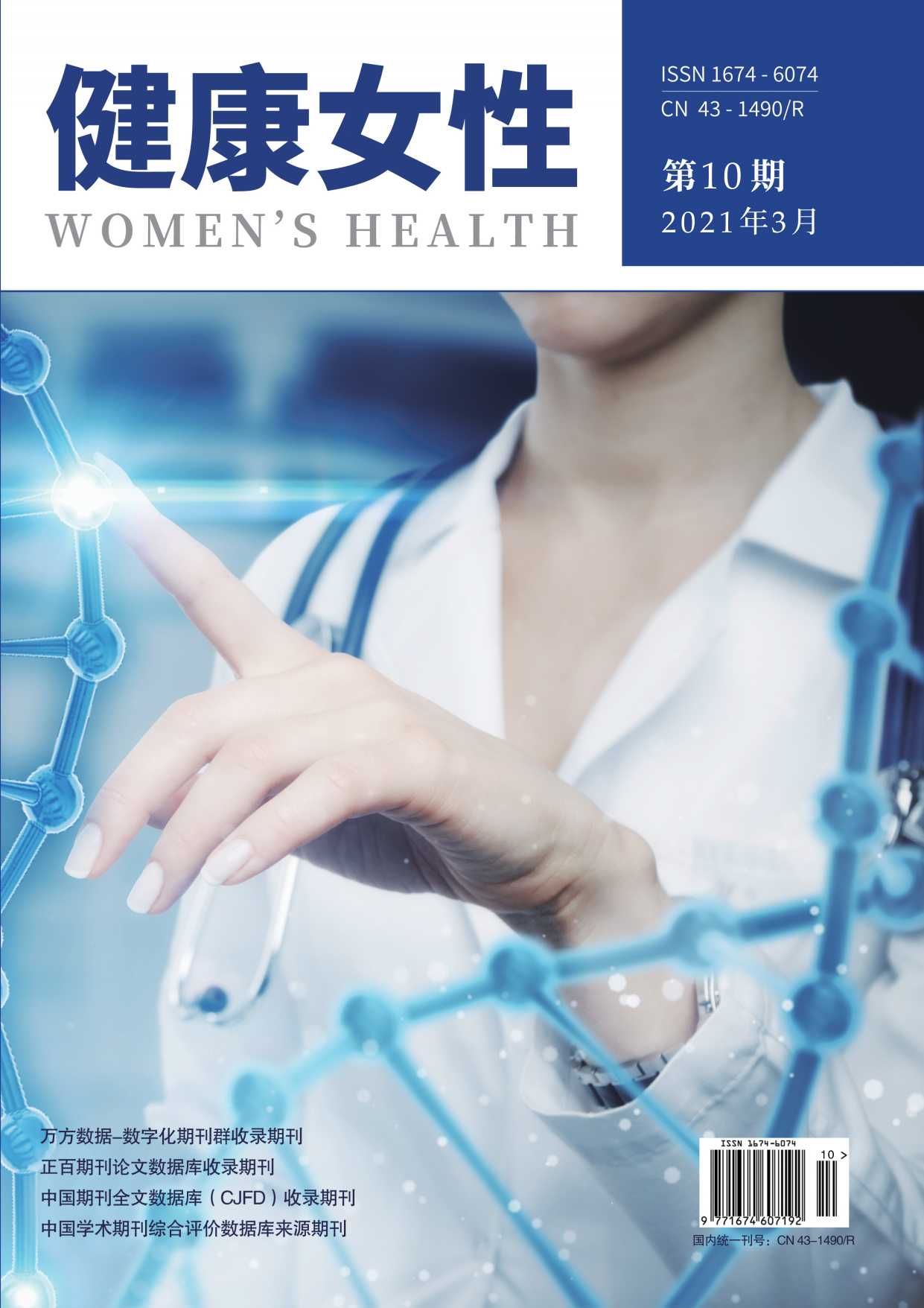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視野下的“命學”
李帆 朗宓榭
在中國,關于命運的思考自古有之,與此相關的學問也一直存在,所謂“命學”(命理、命相之學)不絕如縷。廣義上講,這一學問是有“學”有“術”或有“道”有“器”的。“學”或“道”是關于命運的各種思考與解說,在儒家、道家、佛家學說中,特別是在儒學第二期的理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術”或“器”是它的操作層面,其文獻大多存在于子部的術數類書中,大致以預測為主,主要體現在占卜、算卦等具體行為上。狹義而言,“命學”僅指體現在術數類書中,以預測為主的“學問”。到了清末民初知識轉型時代,有關命運的“學”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間,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學科的不同領域中;而“術”在新的時代環境和近代分科體系下幾無生存空間。這樣一種狀態,無疑使得“命學”被邊緣化。由此所帶來的變化,不僅是部分讀書人生存軌跡的改變,而且關聯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思考和與此相關的個體行為的轉變。所以,研究知識轉型視野下“命學”的邊緣化問題,學術意義頗大。
一、知識轉型的時代語境
總體而言,在古代中國,讀書人的精神狀態是身心家國一體,講求為學和為人的統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體,最高境界為立德。這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讀書為學融為一體,并無明顯的矛盾沖突。因此,讀書人對命運問題的思考和舉措也融入為學與為人的統一中,“命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是很自然的存在的。無論是作為形而上的儒、道、釋各家命運學說,還是作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運預測行為,都在讀書人的生活視野中常態存在,甚至成為他們日常修養的一部分。而且“命學”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在他們那里是協調一致的,理學家可以在探究命、運、性、情等觀念的同時,在生活實踐中進行著占卜、算卦等預測活動。
這樣的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識轉型時期發生了巨變。隨著讀書人在身份上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其所認同和服膺的價值標準發生變化,“命學”也就無法保持過去的那種地位,而不得不邊緣化了。當然,這樣的變化離不開知識轉型的時代語境。
所謂知識轉型,是指知識體系發生變化,即知識內容的更新和表現形態的改變。在中國,應指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發生變化,即向西方近代知識體系接近和轉變,其核心是學術體系的變化,也有學者稱之為學術轉型。一般說來,清末民初是中國的知識轉型時期,其核心是中國古典學術形態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態的轉換,即由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向文、理、法、商、農、工、醫七科之學的轉換。這一轉換大體經過20年左右的時間,即從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變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經清末、民初兩代人的努力而完成。這樣,中國學術從古典形態走出,進入到近代形態,直到今天,已形成新的學術傳統。
知識轉型之所以出現,時代的劇變當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國,內憂外患不絕,尤其是外來勢力的沖擊,李鴻章所謂的“三千年一大變局”,曾紀澤所謂的“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無疑都反映了外來沖擊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震動。震動之下,各方面都在發生或隱或顯的變化,知識體系也不例外。在知識體系的變化中,西學成為觸媒。
盡管在明末清初時,西學在中國就有一定程度的傳播,但傳播的范圍和內容十分有限,未能改變中國絕大多數讀書人原有的知識結構。不過鴉片戰爭后,這種情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方面西學的傳播力度急劇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國讀書人開始認真審視中西兩種文化,探尋西方文化的進步意義,學習西學以自強。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后和戊戌變法期間,讀書人對西學有了普遍性的反應,開始自覺接受和引進西學。作為一種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的異質文化,西學的大規模引入和被適度接納,使得傳統中學的知識結構體系和發展趨向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導致新的知識體系和學科分類的出現。
所謂新的知識體系和學科分類,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知識體系和學科分類。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時期,學術分科觀念已開始為一些中國讀書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鄭觀應在1884年所作的《考試》一文中開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設有數科,無不先通文理算學,而后聽其所好,各專一藝。武重于文,水師又重于陸路”①。這顯示鄭氏不僅對西方學術分科觀念深有了解,而且還接受了西方“各專一藝”的分科觀念及其分科立學的原則,所以他在提出改革科舉考試的方案時,即主張專考西學。甲午戰爭之后,隨著西書翻譯的增多和西學傳播規模的擴大,西方近代學術分科觀念為越來越多的中國讀書人所了解和接受。他們開始突破中國固有的“經、史、子、集”分類法,用西方知識觀念解析中國傳統學問,如嚴復在將《天演論》、《群學肄言》、《社會通詮》、《穆勒名學》等西方社會科學著作譯介給國人時,常通過序文、凡例、按語、夾注等形式不斷援引中學內容,與所述西學比較、對照、印證,在《天演論·自序》中,他便有這樣的論斷:“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②。嚴復的這類論述,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反響,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王國維等學術大家皆循此路徑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學術的工作,用西方近代學科分類標準來匯通中西學術,嘗試構建中國自己的、新的知識系統,如劉師培在《周末學術史序》中,即借用已接受的近代西方分科觀念來反觀中國傳統學術,將周末學術分為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計學、兵學、教育學、理科學、哲理學、術數學、文字學、工藝學、法律學、文章學等十六類③。這樣,中國固有的經史之學便被配置到了西方近代學科體系及知識系統中。
當然,新的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僅靠部分學者的呼吁是建立不起來的,還需要充分的制度保障來為其開辟通路。在這方面,新式學堂的設立和新學制的實施,起到關鍵作用。出于自強和變革的需要,洋務運動時期已有一些新學堂陸續設立,戊戌變法期間又開始設立中國第一所大學堂——京師大學堂。顯然,傳統的經學、史學、諸子學、詞章學等已不適用于這些新式學堂,于是這些學堂紛紛按照西方的分科立學原則和分科治學觀念設置課程。漸漸地,不僅新式學堂如此,傳統的書院也開始分齋設學、分齋治學,變革舊課程,開辟新科目。這種形勢的發展,最終促成了新學制的誕生。新學制以效法歐美的日本學校課程設置為藍本,把中國固有的以“經、史、子、集”為代表的“四部之學”,最終轉向包括“文、理、法、商、農、工、醫”在內的“七科之學”。從此,中國學術按照這一分科體系走上新的發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體制建立、各類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國故”方式研究傳統學問成為共識,中國近代學術才算真正建立起來。
在知識體系轉型的同時,讀書人的身份也在發生著變化,即從“士”轉換為“知識分子”。在傳統中國社會里,讀書人處在士、農、工、商社會序列的首位,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會變革中,伴隨著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則為古老的科舉制的廢除,而科舉制廢除的直接后果就是作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極大沖擊,并造成士、農、工、商四大社會群體為基本要素的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因為“廢科舉興學堂的直接社會意義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切斷了‘士’的社會來源”,于是“士”逐漸成了一個歷史范疇,代替它的是近代教育制度培養出的知識分子,“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社群的出現是中國近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最主要特征之一”⑤。作為能在社會上自由流動的群體,知識分子的構成和社會功能自然與士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再是官吏基本來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承擔著廣泛的社會教化功能以及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責任,而是成為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專業人才,以一己之專業素養貢獻于社會,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變化,他們大多不再是知識系統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領域的“專家”。士之“通人”之學所講求的修身與治學融為一體,在知識分子的“專家”之學里越來越沒有市場,中國固有的修身與治學一體的觀念逐漸轉換為二者分離。
也就是說,清末民初知識轉型時代,新興的知識分子大都由“通人”轉換為“專家”,求學和治學成為一種職業行為,不僅與修身養性關聯不大,甚至與治國平天下也漸趨分離。這當然與近代西方知識形態和價值標準漸趨主導密不可分。于是理性上傾向西方成為較普遍的現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實踐中,并非可以徹底理性化,中國傳統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認識和感性實踐的矛盾,使得一些知識分子對命運的理性思考和具體實踐產生分離,“命學”因此也無法保持過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邊緣。
二、知識分類和“命學”的邊緣化
在古代中國,有關“命運”的思考和論爭從未停止過。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歷朝歷代的讀書人無不留下思索和實踐的記錄,并以各種面貌呈現出來,進入中國固有的知識系統中。
中國固有的知識系統形成甚早,應是在雅斯貝斯所言的“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之際,而對此系統予以分類或分科亦應是同步進行的事情,至少在漢代已趨完善,具體體現在作為知識之總括的典籍分類上。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所編之《七略》,已然是頗為專門的典籍分類目錄。《七略》由《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組成,其中與廣義“命學”相關的思想和知識分布在《六藝略》所包含的《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等典籍里和《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等諸子學說中,甚至在《詩賦略》中的“屈原賦之屬”等詩賦中也有鮮明體現。而與狹義“命學”相關的知識集中在《術數略》的五行、蓍龜、雜占等類別中,這幾類是《術數略》的核心內容。所以,研究中國“命學”的流變,術數類知識的變化和走向是考察的關鍵。應該說,秦漢時期中國的知識系統已大致區分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這體現在《七略》的六部分科中⑤,六藝(即六經)和諸子的地位最高,顯示作為中國學術之源的六經和六經之支流的諸子,構成了知識系統中的“道”,而術數、方技等類則為“器”,地位相對低下⑥。不過盡管如此,《術數略》畢竟為《七略》之一,相較后世,這已是術數類知識地位最高的時期了。相應地,也可視作是“命學”地位最高的時期。
唐初修撰的《隋書·經籍志》對先秦到唐初的典籍加以整理分類,建立起隋唐時期的學術分科體系和知識分類系統。在這一系統里,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取代了漢代的《七略》分類,而且直到清代,四部分類始終被沿用。從“命學”的角度看,與廣義“命學”相關的知識和思想在經、史、子、集四部中都有分布,而與狹義“命學”相關的歷數、五行之學則列于子部之下,即術數類知識從《七略》中的一大類,降為子部下的一小類。從“道”和“器”的角度看,有關形而上之“道”的知識在數量上急劇增長,反映在四部目錄中此類書籍的比重上升很快;與此相反,有關形而下之“器”的知識在數量上增長不快,成為目錄中的小類,地位自然也就降低了。這與重“道”不重“器”的觀念愈益強化密不可分,特別是在科舉取士的大背景下。在清代修纂《四庫全書》所形成的《四庫全書總目》中,四部分類得到極大完善,達到中國古代典籍分類的最高水平。《四庫全書總目》里,與廣義“命學”相關的知識和思想仍分散在經、史、子、集四部當中,而與狹義“命學”相關的知識則集中在子部的“術數類”中,包含“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等子目。這一分法與《隋書·經籍志》一脈相承,表明狹義命學”知識在典籍分類中的地位自唐以來沒有改變。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中對子部知識體系的邏輯關系有所闡發,認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這六類“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在子部知識系統中最為重要,而“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在他看來,這兩類知識,“皆小道之可觀者也”⑦。這番話透露出時人根深蒂固的道、器觀念,而且視術數類知識為“或有益或無益”,難下結論,僅以“其說久行,理難竟廢”為理由而列入子部。由此可見此類知識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見狹義“命學”的地位。
盡管《隋書·經籍志》和《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排序已說明了狹義“命學”頗為邊緣的地位,但畢竟“其說久行,理難竟廢”,還是在子部知識中堂皇存在。而到清末民初知識轉型之際,這種存在成了問題,成為被忽略或革除的對象。
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是個復雜的過程,晚清時期知識界關于引入西學改良中學甚至改造中學的各種言說始終不絕,但真正落實到制度層面則是到了清末新政之時,體現在新學制的制定與實施上。1901年,清廷決定推行新政,并將廢科舉、興學堂作為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制定和實施新式學堂章程,提到日程上來。經張之洞等人的努力,在1903年終于制定出一系列新式學堂章程,并奏請清廷,以《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等為名公布實施,建構了一套新式學制。這套學制規定大學堂分八科設學,即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從這八科下所分的具體學科門類來看,中國固有學術中的經學、史學、文學等在經學科和文學科中得到保存,引進的各類西學在政法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中確定下來。于是,“中國以經、史、子、集為骨架的‘四部之學’知識系統,被包容到以西方學科分類為主干之‘八科之學’的新知識系統之中”⑧。在這一新知識系統中,與“命學”相關的形而上層面的知識,因分散在固有的經學、史學、文學中,故仍能在經學科和文學科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子學遭到排斥,未作為一科列入,子學下的術數類知識也就無法進入這一系統,從而導致狹義“命學”與新知識系統無緣。
張之洞的“八科分學”方案在中華民國建立后被修正。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學令》、《大學規程》,對大學所設置的學科及其門類作了原則性規定,決定大學取消經學科,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農科、工科、醫科等七科。從此,中國學術開始擺脫經學束縛,創建起類似近代西方的學科門類和知識系統。在這七科中,文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中國固有學術體系中的經學、史學、子學和集部之學大體被“文科”消融進去,表明“四部之學”已被納入到“七科之學”知識系統,即從中國傳統知識系統轉向西方近代知識系統的軌道。就“命學”而言,形而上層面的知識和思想繼續存在于包容了經、史、子、集的哲學、文學、歷史學之中,特別是對“命運”、“命理”問題思考最多的儒、釋、道,基本被納入哲學范疇。在哲學思維籠罩下,形而上的“命學”開始進入一片新天地。至于以術數類知識和實踐為代表的狹義“命學”,仍無法實現近代轉換,未能進入新知識系統。在被主流知識系統完全排斥的境況下,這樣的“命學”徹底邊緣化了。
西方近代知識系統真正在中國的學術研究中發揮實際效用,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北京大學。由京師大學堂發展而來的北京大學,在民國之初的幾年里,仍為一“官僚養成所”,直到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本著“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宗旨改造北大,才使北大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中心。在這里,教育部所公布的分科原則得到真正貫徹,各類西式學科基本固化,教學、科研一本于此,現代大學體制建立起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倡“民主”與“科學”、反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氛圍下,以北大為代表的西式學科分類和研究取向在中國愈益穩固。與此相對,作為舊文化的代表之一,傳統“命學”只能越發式微了,不僅狹義“命學”難有空間,就是形而上的“命運”、“命理”思考,也因與西方哲學重本體、重認識、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謂“人生哲學”,而在哲學講堂上難以居于主導地位。可以說,邊緣化是“命學”在近代中國知識轉型完結之際不可避免的命運。 三、讀書人身份、態度的變化和“命學”的衰微
與知識轉型進程相伴隨,讀書人的身份也在發生著變化,由傳統的士轉向近代知識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識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體,而是主客相融的產物,因讀書治學并非單純為了求知和獲得學術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需要。這種治學與修身一體的狀況,使得士人講求的學問是以博通為基礎的,“道”與“器”在他們心目中雖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內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學”的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他們往往能夠協調起來,并不發生沖突,或至少不發生大的沖突。不過到了清末民初知識轉型時代,隨著近代知識分子的出現,這種局面發生了根本變化。
知識轉型是以學術分科為表征的知識體系的變化,即西方近代知識體系逐漸取代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西方近代知識體系大體形成于18世紀啟蒙時代,它有兩個根本特點:一是源于古希臘的對知識與真理的獲取與客觀把握,而非將知識、真理和修身之類的德行培養聯系在一起;二是科學化,以科學的名義界定所有事物,分門別類,此前在西方知識系統中存在的星相學之類由此被打上“迷信”標簽,逐出學術之門。對中國而言,接受這種特點的知識體系只是晚了一個多世紀而已,所引發的讀書人知識結構和價值體系的變化,無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隨著讀書人社會身份的變化和近代知識分子的產生,讀書治學漸成職業行為,知識成為客觀對象,不再與人的德行緊密相連;另一方面,分類之學取代博通之學,使得讀書人的知識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由“通人”變為“專家”,而且是科學思維下的“專家”。當然,這樣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清末民初兩代學者的進程。不過對“命學”而言,轉變的發生和轉變程度的深化,是個越來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學者熱衷西學,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圖存的需要,是理性層面思考的結果。但是,傳統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環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響等因素,使得他們在感性生活實踐上還是更多地認同過往的一切,這在清末讀書人對待“命學”的態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傾向西學的知識分子在涉及“命運”的理性思考和解說時,已開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觀念和思想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但在日常生活層面,還是時有占卜、算卦等行為,形而下“命學”的強大魅力仍在。這方面嚴復之所為便是典型。在廣泛傳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進化學說為民族、國家命運把脈,大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同時,日常生活中的嚴復頗多占卜算卦之舉,如在其宣統三年(1911)的日記中,時有這樣的記載:“占財,大有。寅木財爻極旺,雖空不空。世爻暗動,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貴逼人之卦也,斷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實空之日得之(注:末句當系事后補記)”;“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進酉逢月破,應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癥業已臨危,得未濟之革。申己合而長生,亥水雖為月建所尅,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獨發,以得氣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為月破,此癥當活也。后于酉時得醫,己亥日愈(注:末句當系事后補記)”;“卯月甲寅日占風水,困之節。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財持世,而化回頭,生之應爻,生之自身。可謂美滿矣”;“占弟被論吉兇,得困變恒、金。午鬼極旺而動,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無生扶,其兇必矣。雖得生于日辰,恐不敵也。后于申年,遂被極刑(注:末句當系事后補記)”;“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沖而變六合。父爻發動生世,應為忌神,與卯木同動,化剋為生,當主離而復合”;“占出行,得明夷變小過,水。世臨官動,化回頭生,應臨子孫,動而尅世,是宜成行。但為子日所合,須俟午日沖子,然后成行”⑩。這里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證嚴復日記中的卜卦釋詞,是為說明卜卦是嚴復生活中的常態。其所卜算的內容很廣泛,包含發財、升官、疾病、生死吉兇、風水、婚姻、出行等,是人們俗世生活中最為關切的東西。其中不少是應他人之求而代為占卜的卦,說明卜卦也非完全是個體的私密性行為。甚至在一些釋詞后面嚴復還記下事件的結果,以示所卜之卦的靈驗。
應該說,對嚴復這代讀書人而言,日常生活與占卜算卦相連,并非是多么奇異的事情。盡管知識轉型開始在他們身上發生,但他們畢竟屬于過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國傳統教育,即以博通為根基的治學修身一體的教育,后來所接受的外在于他們的西學,只不過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并未能對他們的生活態度發生根本影響。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層面,他們仍能像古代讀書人那樣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學”兼容并蓄。實際上,以“科學”面目出現的西學和中國形而下的“命學”是難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與占卜算卦的生活行為之間有巨大落差,如果一個人將西方理性完全內化于身心,而不僅僅是把它作為外在于己的知識與思想,那么他是很難認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為的。只是在嚴復這代人那里,對西學的認知還未達及此等程度,“科學”認同的社會環境也未形成,所以他們并未自覺體認到其行為所具有的內在矛盾性。
進入民國之后,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科學”認同的社會環境基本形成,新興知識分子對待“命學”的態度就與他們的前輩有了較大不同。已有學者作過研判,新文化運動時樹起的“科學”旗幟,其內涵不僅是指科學知識、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種價值觀,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信條體系,一種規范性的評價尺度,即所謂的“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一詞……其意義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這種信仰認為只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和由現代科學家描述的科學方法,才是獲得那種能應用于任何現實的知識的唯一手段。”(11)在這種信仰的籠罩下,新文化運動期間甚至出現這樣的情形,“只要與科學、理性相違的一切傳統文化及行為皆為迷信,包括儒家倫理、宗教、帝制、民間信仰以及風俗等等”(12)。陳獨秀就曾明確指出:“若相信科學是發明真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學相反的鬼神、靈魂、煉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風水、陰陽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萬萬不足相信的。”(13)如此的氛圍和時代環境,自然對“命學”特別是狹義“命學”的發展極為不利,以至于民國年間從事“命學”者也要極力向“科學”或“哲學”靠攏,如袁樹珊《命譜》前有《序》言:“科學名詞,吾國古所未有,由轉輾迻譯而來。解之者曰:‘凡為有系統之研究者,是之謂科學。’然則吾國專門技術,何一而非科學耶?潤州袁樹珊先生,以所輯《命譜》見示。余曰:‘是亦科學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學》,推演而貫通之,科學之精義,昭然予世以共見。或疑為秘聞,陋已”(14)。“星命學為吾國哲學專科。……竊謂是書(指《命譜》)果能流傳區宇,使之人手一編,久必改進國風,消弭世變,同登于人類進化之盛運,然后見哲學之明效大驗也。”(15)將袁氏“命學”比附為“科學”或“哲學”,顯然是時代大潮的產物,亦有為“命學”在近代學科體系和學科分類中爭正統、爭地位的考量。這種考量恰恰說明“命學”已處在極為邊緣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學”話語力爭一席之地。
盡管作了種種努力,但“命學”仍為民國主流知識界所排斥,特別是形而下的狹義“命學”,始終難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證很能說明問題。在為袁樹珊《述卜筮星相學》作序的人當中,有一位號稱信奉唯物史觀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幾年我對于卜筮星相,覺著有點好玩,所以閑空的時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為了一時的興致,寫了一部《人鑒》,很風行一時。當下我的朋友,有許多不以為然,他們說:‘你是相信唯物史觀之一人,為甚么提倡這些,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后來看見《語絲周刊》,錢玄同居然罵我渾蛋”(16)。林的朋友和錢玄同的態度,恰能代表當時知識界較為普遍的看法。畢竟在經歷知識轉型和五四洗禮之后,已成型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在知識結構和價值體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學術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學思維的“專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學觀念使他們無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學”的“命學”存在。當然,也有一些被視為“保守”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給“命學”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學者吳宓在其日記中就不時有卜卦記載,這里略舉幾例:1937年7月28日,“寢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兇”(17);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憂父在西安遇難。今晚尤惶擾不寧。乃用閉目開書,手指某頁一句之法占卜”(18);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樓詩》禱卜宓本年應在清華抑往武大,得句云‘義方教子恩及侄’。宓以為子指淑,侄指克強,此句似命宓回清華之意”(19)。從這些記載來看,吳宓之卜卦,有其特點,一是此舉非生活常態,往往是在時代劇變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時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即將進北平的關鍵時刻卜吉兇;1939年憂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軍轟炸、軍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則是面臨關鍵選擇,為定行止而卜。二是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強。從日記看,基本未見吳宓為他人卜卦的記載,這和嚴復大量為他人卜卦,形成鮮明對照。無論如何,在“科學主義”盛行的大環境下,盡管吳宓對“科學主義”頗有微詞,但也不能不顧及整體的社會環境,無法公開從事主流知識界所界定為“迷信”的卜卦活動。實際上,在吳宓這代知識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個人中國式感性生活實際的分離,較之清末嚴復那一代更為明顯,內在矛盾沖突也更大,在各種有形無形因素的制約下,一些生活實踐只能越來越個人化、私密化。這樣的事實本身,就已表明中國式的“命學”不能不走下坡路。
總之,在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總體格局下,不論就知識分類而言,還是就讀書人社會身份和態度的轉變而言,都對傳統“命學”頗為不利。“命學”中的“學”或“道”,被分離在近代不同學科中,主要是在哲學層面講求,但因與西學主流不符,在哲學中也難以占據主導地位,日趨邊緣化;“命學”中的“術”或“器”,命運更是不佳,在愈益強大的科學主義潮流面前敗下陣來,從文化“大傳統”的一部分淪落為“小傳統”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學”的這一歷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極多,本文只是大體描述一個框架,一系列相關課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注釋:
①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上》,載《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頁。
②嚴復:《天演論·自序》,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19、1320頁。
③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載《劉申叔先生遺書》,1936年寧武南氏排印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503頁。
④羅志田:《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載《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頁。
⑤在《七略》中,《輯略》是“諸書之總要”,因此《七略》分類實為六分法,即將典籍分為六大部類。
⑥《論語·述而》載:“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孔子對“道”和“藝”(或曰“器”)之先后、高下進行區分的觀念,顯然對秦漢時期及其后中國知識系統的構建有深遠影響,《七略》僅為一例。
⑦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69頁。
⑧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⑩《嚴復日記》,載《嚴復集》第五冊,第1506-1510頁。
(11)J·韋莫斯:《唯科學主義的本質與起源》,轉引自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頁。
(12)宋紅娟:《“迷信”概念在中國現代早期的發生學研究》,《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8年第4期。
(13)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70頁。
(14)王清穆:《序》,載袁樹珊《命譜》,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15)董伯骙:《序》,載袁樹珊《命譜》,第2頁。
(16)林庚白:《序》,載袁樹珊《述卜筮星相學》,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頁。
(17)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六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80頁。
(18)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七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