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天府之國”
王雙懷
摘 要: “天府之國”是最適宜于人類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勢險固、土地肥沃、物產(chǎn)豐富的地方稱為“天府”或“天府之國”。在中國歷史上,曾先后出現(xiàn)過9個“天府之國”。它們是關(guān)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區(qū)、太原附近、閩中地區(qū)、沈陽一帶、武威地區(qū)和臺東地區(qū)。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看,這些“天府之國”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則與人為因素息息相關(guān)。由于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的差異,有的“天府之國”長期存在,影響很大,有的則曇花一現(xiàn),轉(zhuǎn)瞬即失。歷史時期“天府之國”的形成與演變,對于我國當(dāng)前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guān)鍵詞: 歷史地理; 天府之國; 環(huán)境變遷
Abstract: Historically, the “Nature's Storehouse” referred to the fittest locality for human life.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usually regarded a locality with hazardous terrace, fertile land and abundant produce as the “Nature's Storehouse”. Thus, there were 9 localities respectively named “Nature's Storehouses” in Chinese history, namely, the Guanzhong Basin, the Beijing Valley, the Chengdu Plains, the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the areas adjacent to Taiyuan, the Central Fujian, the areas adjacent to Shenyang, the Wuwei region and the Eastern Taiwan. Owing to respective distinctions in geographic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some of these “Nature's Storehouses” have endured history and remain influential, but others lasted only momentarily and faded soon. Thus, the shaping and evolution of these historical “Nature's Storehouses” are of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urr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histogeography; “Nature's Storehouse”; environmental change 據(jù)史書記載[1],戰(zhàn)國后期,關(guān)中盆地和北京一帶就先后獲得“天府”的美譽。秦漢之際,關(guān)中成為著名的“天府之國”,成都平原開始躋身于“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稱為“天府之國”。隋唐兩代,關(guān)中盆地高度發(fā)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國”的美名。宋遼夏金時期,北方地區(qū)戰(zhàn)爭頻繁,社會動蕩,而江南地區(qū)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成為新的“天府之國”。到元明清時期,北京作為首善之區(qū)受到統(tǒng)治者的高度重視,成為文人墨客津津樂道的“天府之國”,而閩中、盛京(沈陽)、涼州(武威)、臺東等地也有了“天府之國”的美稱。近代以來,關(guān)中等老天府或趨于衰落,或有了新的稱謂,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國”的稱號。如此算來,在中國歷史上,共有9個“天府之國”。這些“天府之國”分布在西北、西南、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不同的地理單元。其中關(guān)中盆地、北京一帶和成都平原影響較大,其他幾個地區(qū)知名度則相對較小。本文擬對這些“天府之國”的具體情況加以探討,希望有助于大家對“天府之國”的認識。 一、 關(guān)中盆地 關(guān)中盆地位于陜西中部,被山帶河,金城千里,土地肥沃,物產(chǎn)豐富,古稱“陸海”,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國”。從文獻記載來看,關(guān)中作為“天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后期,作為“天府之國”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秦漢之際。歷史上最早把關(guān)中稱為“天府”的人是蘇秦,最先將關(guān)中稱為“天府之國”的是張良。自戰(zhàn)國至于明代,關(guān)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國”的美譽。 關(guān)中盆地的基本特點是山環(huán)水繞、沃野千里。秦嶺山脈、渭北山系與黃河形成天然屏障,涇、渭、、灞諸水從八百里秦川上流過,非常適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人類生活。早在舊石器時代,這里就有人類繁衍。夏商周三代,這里曾是西周王朝的統(tǒng)治中心。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過秦人的開發(fā),這里已變得相當(dāng)富庶。故蘇秦在公元前338年對秦惠王說:“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guān)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1]卷69《蘇秦列傳》戰(zhàn)國末年,秦國在渭北地區(qū)修建了著名的鄭國渠,進一步優(yōu)化了關(guān)中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促進了這里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高了秦的綜合國力,從而很快完成了統(tǒng)一全國的大業(yè)。雖然秦朝二世而亡,但關(guān)中的統(tǒng)治基礎(chǔ)依然很好。正因為如此,楚漢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劉敬建議漢高祖定都關(guān)中。他認為:“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guān)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1]卷99《劉敬叔孫通列傳》漢高祖身邊的大臣多勸他建都洛陽。認為“洛陽東有城皋,西有肴殳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漢高祖猶豫不決。張良對他說:“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shù)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guān)中左肴殳、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1]卷55《留侯世家》于是漢高祖決定奠都關(guān)中。自從張良給關(guān)中戴上“天府之國”的桂冠之后,人們便開始將關(guān)中稱為“天府之國”了。 秦漢兩代十分重視對關(guān)中地區(qū)的開發(fā)與經(jīng)營。秦統(tǒng)一全國后,徙各地富豪12萬戶于咸陽。漢初徙齊、楚大姓及韓、趙、魏王室成員10余萬口到關(guān)中,又徙諸郡豪民于關(guān)中陵邑。另一方面,在關(guān)中大力興修水利,不僅擴大了舊有的灌溉渠系,而且興建了白渠、成國渠、漕渠和龍首渠等規(guī)模較大的工程。班固《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成云。五谷垂穎,桑麻鋪。”[2]卷24班固《西都賦》民謠中也有“涇水一石,其泥數(shù)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的說法。[3]卷5《鄭白渠歌》渠道兩岸萬頃農(nóng)田得到灌溉,呈現(xiàn)出一派富庶繁榮的景象。此外,這一時期還在關(guān)中推廣冬麥,又采用先進的犁、耬等生產(chǎn)工具,推廣代田法和區(qū)田法,通過集約使用水肥,實現(xiàn)精耕細作,奪取高額豐產(chǎn)。隨著中外農(nóng)業(yè)文化的交流,黃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經(jīng)濟作物也開始在關(guān)中種植。于是關(guān)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農(nóng)業(yè)區(qū)。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關(guān)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卷129《貨殖列傳》由此可見關(guān)中盆地的富庶程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關(guān)中地區(qū)多次遭受戰(zhàn)爭的摧殘,但不少人在談到關(guān)中時仍不約而同地稱之為“天府之國”。如西晉時,東海王司馬越表征鎮(zhèn)守關(guān)中的王模為司空。王模的謀士淳于定對他說“關(guān)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4]卷37《南陽王模》,建議他繼續(xù)鎮(zhèn)撫關(guān)中,不到朝廷任職。十六國時,苻登等人與姚萇爭奪關(guān)中地區(qū)的統(tǒng)治權(quán)。古成詵對姚萇說:“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余瑣瑣焉足論哉。”[4]卷116《姚萇傳》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為高歡所迫,欲逃往荊州。柳慶對他說:“關(guān)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宇文泰忠誠奮發(fā),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閉關(guān)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5]卷22《柳慶傳》建議他前往關(guān)中投靠宇文泰。北周時,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于謹對北周太祖說:“關(guān)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jù)其要害,招集英雄,養(yǎng)卒勸農(nóng),足觀時變。”[5]卷15《于謹傳》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在這個大分裂的時代,關(guān)中地區(qū)雖受到破壞,但在全國仍處于領(lǐng)先的地位,還是當(dāng)時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國”。 隋唐時期,關(guān)中作為帝都長安的所在地,受到世人的高度關(guān)注。隋朝末年,李密對楊玄感說: “關(guān)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wèi)文升不足為意。若經(jīng)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jù)險臨之,固當(dāng)必克,萬全之勢。”[6]卷53《李密傳》建議他西入關(guān)中,奪取天下。楊玄感未予采納。劉文靜和裴寂對李淵說:“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jiān)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guān)中天府,代王沖幼,權(quán)豪并起,未有適從。愿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6]卷57《劉文靜》李淵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起兵晉陽,奪取關(guān)中,建立了唐朝。為了解決長安城的物資需求,唐王朝大力發(fā)展漕運,同時加大了關(guān)中的開發(fā)力度。到唐玄宗統(tǒng)治的開元天寶年間,關(guān)中達到了繁華的頂點。但安史之亂使關(guān)中地區(qū)遭受了一場浩劫。程元振勸唐肅宗遷都洛陽。但郭子儀委托兵部侍郎張重光上奏說:“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后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shù)千里,帶甲十余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yè)。”[6]卷120《郭子儀傳》顯然,盡管安史之亂對關(guān)中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關(guān)中在唐人的心目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長安城為朱全忠所毀,關(guān)中的地位隨之大幅度下降。 五代以后,關(guān)中地區(qū)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經(jīng)濟形勢每況愈下。不過,仍有人將關(guān)中稱為天府之國。如宋“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鄭]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7]卷448《鄭驤傳》《三朝北盟會編》的作者說,關(guān)中“據(jù)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guān)中所以衛(wèi)京師。脫若關(guān)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也。經(jīng)略左丞忠義一節(jié),勤勞百倍,所以為國家計者,至矣盡矣”[8]卷77。張闡也有類似的說法:“金歸我關(guān)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fù)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矣。”[9]卷28這說明,到兩宋時期,關(guān)中地區(qū)已經(jīng)衰落,但它的影響依然存在。 元明之際,關(guān)中的地位繼續(xù)下降,但人們還對它保持著“天府之國”的歷史記憶。如在蒙古國晚期,憲宗蒙哥大封同姓,讓忽必烈在南京和關(guān)中之間選擇封地。忽必烈的謀士姚樞對他說“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guān)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10]卷158《姚樞》,建議他選擇關(guān)中。于是忽必烈據(jù)有關(guān)中,成為關(guān)中的統(tǒng)治者。明初朱元璋與群臣討論建都之地, “或言關(guān)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11]卷45朱元璋對此表示認可,但他最后還是選擇了南京。《大明一統(tǒng)志》在講到關(guān)中形勢時仍沿用關(guān)中是“天府之國”的說法[12]卷32。此外,明代的不少學(xué)者在論及建都形勢時,也都對關(guān)中的形勝表示贊賞。如邱氵睿在其《大學(xué)衍義補》中說:“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guān)中比也。”[13]卷86武夷熊氏說:“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故言定都必先焉。”[14]卷33有人甚至從風(fēng)水的角度,說關(guān)中是“中龍”所在[14]卷33,認為“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肴殳右蜀,太華涇渭,表里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zhèn)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15]卷11《漢南北軍記》。 但到了清代,關(guān)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國”的美譽。“天府之國”僅見于方志的記載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懸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三輔南有江漢,北有河渭,隴以東,商雒以西,厥田肥饒,所謂陸海。東有函谷、蒲津,西有散關(guān)、隴山,南有山、武關(guān),北有蕭關(guān)、黃河,踐華為城,因河為池。”[16]卷7清朝滅亡后,再也沒有人把關(guān)中地區(qū)稱作“天府之國”了,甚至就連生活在關(guān)中地區(qū)的一些人,都不知道關(guān)中曾經(jīng)是“天府之國”,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了。這是多么令人傷感的事。 二、 北京一帶 北京小平原東臨渤海,西靠太行,南環(huán)河濟,北枕燕山,水深土厚,自然條件相對較好。這一帶被稱為“天府”的歷史,也可追溯到戰(zhàn)國末年,但它真正受到重視,被稱為“天府之國”則是明代以后的事。 北京小平原在戰(zhàn)國時代是燕國的領(lǐng)地,燕國的都城薊就座落在這里。蘇秦在離開秦國后,奔走于齊、趙、魏、秦諸國之間,設(shè)計防止齊國攻燕,并發(fā)動五國攻秦,成為燕國的重要謀士。為了鼓勵燕文侯爭霸的決心,他對燕文侯說:“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shù)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shù)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于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1]卷69《蘇秦列傳》因此,北京小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稱。但由于當(dāng)時燕國自然環(huán)境不如關(guān)中,經(jīng)濟相對落后,知名度相對較低,蘇秦提出的這個“天府”,并沒有引起其他人士的共鳴。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京小平原陸續(xù)得到開發(fā)。秦統(tǒng)一全國后,在燕地設(shè)廣陽等6郡進行管理,薊成了秦在東北地區(qū)的重要城市。故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1]卷129《貨殖列傳》西漢時北京一帶分屬廣陽國及涿、漁陽諸郡,屬幽州刺史部。東漢設(shè)廣陽、漁陽、涿郡,屬冀州。秦漢兩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所發(fā)展,手工業(yè)也有所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京小平原曾是“前燕”的中心區(qū)域。由于社會動蕩,戰(zhàn)亂不已,北京一帶也受到戰(zhàn)火的摧殘。但當(dāng)?shù)厝嗣袢耘氖律鐣a(chǎn)。如三國時代在北京近郊的永定河流域,修建了攔水壩戾陵遏,開鑿了車箱渠等規(guī)模較大的水利工程,為北京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由于遠離全國的政治中心,加之經(jīng)濟相對比較落后,北京小平原一直處于默默無聞的狀態(tài)。 隋唐時期,薊城在北方地區(qū)的軍事地位重要起來。隋以薊為涿郡治所,并開通了南迄余杭,北到涿郡的南北大運河。唐代改涿郡為幽州,改薊城為“幽州城”。唐太宗征高麗,即以幽州城為大本營。唐玄宗時實行重外輕內(nèi)的軍事部署,在北方設(shè)置8個節(jié)度使,幽州是范陽節(jié)度使的駐地。天寶十四載(755),身兼范陽、平盧、河?xùn)|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發(fā)動了叛亂,給中原地區(qū)造成了深重的災(zāi)難,同時也給北京小平原造成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安史之亂以后,北京小平原在全國的地位有所下降。 五代宋遼夏金元時期,北京由遼南京、金中都發(fā)展為元大都,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公元936年,石敬瑭為了當(dāng)皇帝,將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遼太宗派兵占據(jù)幽州城,并將它變成遼的陪都,稱之為“南京”、“燕京”。在遼代,北京一帶雖然與內(nèi)地缺乏聯(lián)系,但仍不失為一個人口稠密、市井繁華的大城市。北宋前期曾多次打算收復(fù)燕云十六州,結(jié)果均以失敗而告終。12世紀初葉,金人崛起,滅遼、滅宋,將都城從松花江邊的會寧遷至燕京。1151年,金主完顏亮改建燕城,兩年后正式遷都于此,改名“中都”,使之成為金王朝的統(tǒng)治中心。金朝末年,中都毀于戰(zhàn)火。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的東北郊外修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大都”城。從此,北京一帶迅速發(fā)展起來,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明代遷都北京,有人出于維護統(tǒng)治的目的,對北京的地理形勢進行重新審視,認為北京是“天府之國”。史載明成祖即位后,“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chǎn)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11]卷182《大明一統(tǒng)志》的作者說:“京師古幽薊之地,左環(huán)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我太宗文皇帝龍潛于此,及纘承大統(tǒng),遂建為北京而遷都焉。于以統(tǒng)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dāng)形勢之勝而為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邑之盛未有過焉者也。”[12]卷1明人章潢在《圖書編》中也說:“古幽薊之地,左環(huán)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自唐虞三代以來都邑之盛未有過焉者也。”[14]卷35 清代的統(tǒng)治者認定北京是“天府之國”,并有意識地進行宣傳。如乾隆十二年敕撰之《皇朝文獻通考》云:“京師為古燕薊之域,地勢雄厚,滄海環(huán)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諸關(guān)口衛(wèi)其后,據(jù)九州之上游,南面而臨天下。自古天府之國無過于此。”[17]卷269乾隆三十九年敕撰《欽定日下舊聞考》云:“幽州之地,左環(huán)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天府之國。而太行之山,自平陽之絳西來,北為居庸,東入于海,龍飛鳳舞,綿亙千里,重關(guān)峻口,一可當(dāng)萬,獨開南面以朝萬國,非天造此形勝也哉!”[18]卷5吳元萊在《畿輔通志》原序中說:“京師故燕冀地,抱衛(wèi)齊,連晉趙,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長城為屏障,憑太行為股肱。潞水南趨,直沽東下,達濟汶以通漕運,所謂金湯千里,天府之國也。故自遼、金、元、明皆都此而莫之易。”[19]《原序》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中也說:“建都之地,自古為關(guān)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余如汴、如金陵,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議者以關(guān)中為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為下。愚竊謂不然。”[20]卷15在他看來還是北京最好。 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北京作為“天府之國”存在一定的缺陷。《五雜俎》的作者說:“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wèi),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運,然當(dāng)群雄奸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dāng)慮者也。”[21]卷3《地部一》 三、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氣候溫潤,“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22]卷28下《地理志》下,是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具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在中國古代,最早把成都平原稱作“天府”的人是東漢末年的諸葛亮,而最早把它稱為“天府之國”的則是唐代的陳子昂。從東漢末年到現(xiàn)在,成都平原一直保有“天府”和“天府之國”的美名。 成都平原的特點與關(guān)中相似,具有“沃野”和“險塞”[23]89。先秦時代,成都平原在開明氏的統(tǒng)治之下,時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頗為艱難。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將司馬錯入川,設(shè)置蜀郡,修筑棧道,加強了蜀地與關(guān)中的聯(lián)系,使蜀成為秦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數(shù)十年后,秦昭王使李冰修都江堰,“蜀守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1]卷29《河渠書》。都江堰修成后,灌溉蜀、廣漢、犍為三郡,既除水害,又利農(nóng)業(yè),不僅便利了交通,而且使蜀中生態(tài)環(huán)境得到優(yōu)化,逐漸成了最適宜人類生活的地區(qū)之一[24]。故清代學(xué)者朱鶴齡說:“史稱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蓋成于李冰,而肇于神禹也。”[25]卷8
子.jpg)
院學(xué)報.jpg)
蒙古水利.jpg)
代防御技術(shù).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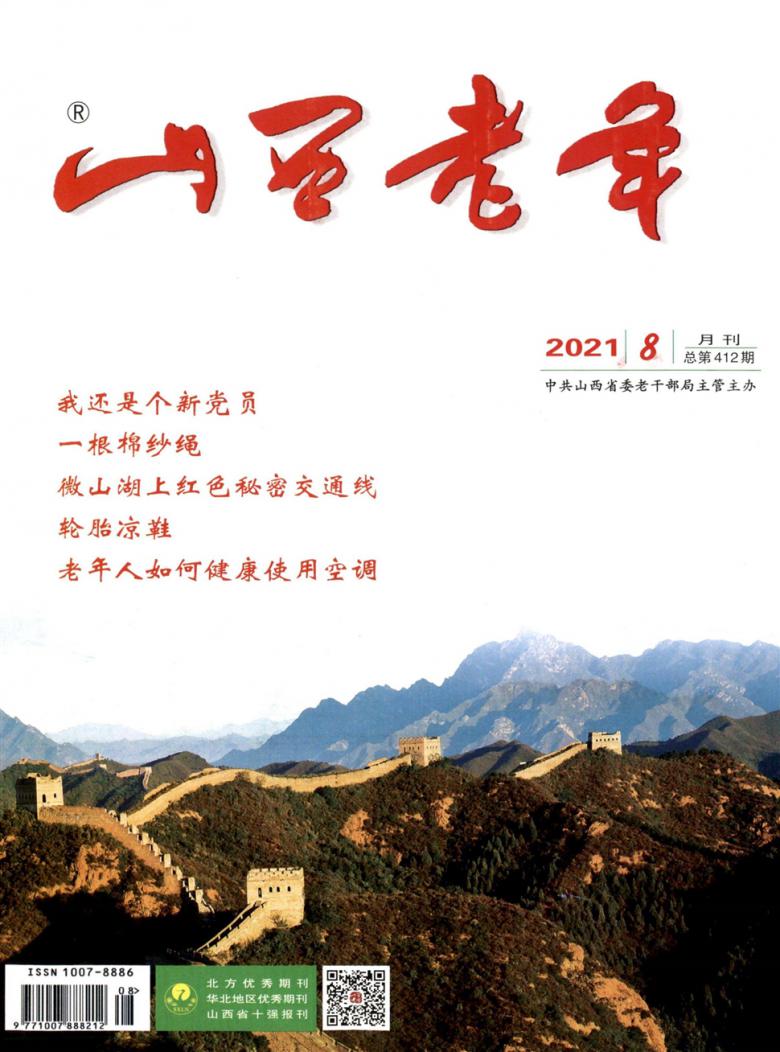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