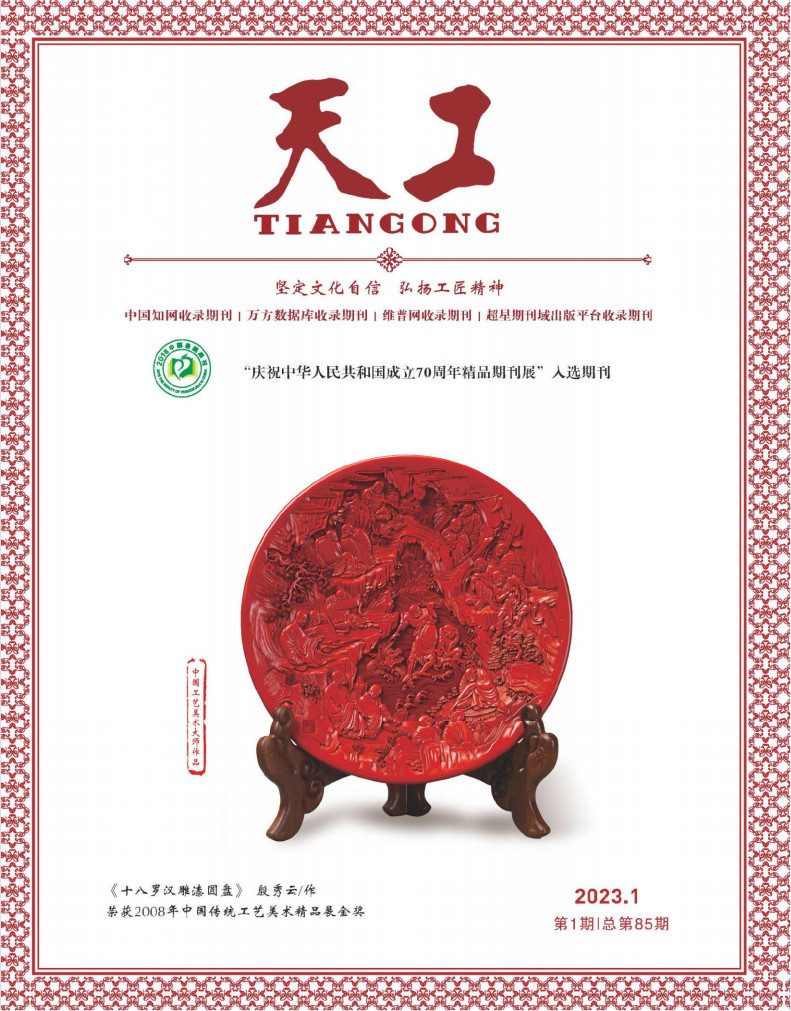關于儒家民族主義與混合政體
佚名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在當今世界興盛不衰,既有積極后果,也有消極后果。貝淡寧《儒家與民族主義能否相容?》一文的核心論辯是,儒家民族主義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欲的;我們確實應該“希望儒家民族主義贏得中國人民的心靈”。貝淡寧認為,儒家民族主義優于他所稱的“法家”民族主義或“怨恨式”民族主義,他還認為,信奉儒家的人選擇儒家民族主義而不是自由派民族主義,是可以據理辯護的。我大體上支持他的立場,但在本文中,我將對他的論辯提出三點修正。首先,對家、國和天下的各自承諾之間存在著關聯,但我相信,此種關系類型最好根據“平衡”與“和諧”來理解,而不是根據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先性。第二,貝淡寧重要的,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家有著激烈批評,但貝淡寧對于這個問題的回應,以及對于儒家民族主義可能被濫用的擔憂所做的反駁,都顯得單薄。如果儒家民族主義要有吸引力,它必須要么被放在混合型政體,該政體納入了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強有力保護,而這些權利不是從儒家引申出來的;要么,我們需要為這些權利找到比貝淡寧已經識別的理據都更為強健的儒家基礎。 讓我們從貝淡寧一段看起來不會引起爭議的陳述開始。他說,對于儒家,“隨著從家庭延伸到國族,義務也就減弱,倘若家庭義務和國族義務之間沖突,前者優先”。貝淡寧的意思可能不止一個,或許,他會同意我在這里不得不說的事情。對貝教授關于“優先性”的談論,會有一種自然的解讀方式,但這種方式會導致對儒家的錯誤解釋。在這句話后面幾行,貝淡寧注意到“甚至一些西方國家也承認家庭的神圣性而不論公共之善的代價有多高”。尚不完全清楚他是否認為儒家相信此強意義上的“家庭之神圣性”,但是,倘若這是家庭對其他考量具有優先性的假定內涵,那無疑是對儒家的錯誤解釋。問題在于,家庭的價值是勝過其他所有價值呢——更技術些,我們可以說家庭的考量是對我們的選擇的義務論約束——還是說,家庭是我們力圖與其他重要程度較低的價值保持和諧的重量級考量。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好的儒家行動者將受家庭關系的強烈影響。但貝淡寧卻讓人覺得,就像是在明顯的沖突情形下,儒家的行動者視自己面臨著非此即彼的選擇:要么以家庭為重,要么以國為重。“父為子隱”看起來像是支持這樣一種道德選擇兩分法的,因為似乎是孔子告訴我們選擇家庭勝過選擇法律。但該段落對父如何為子隱保持沉默。他只是簡單地置兒子優先于法律并忽視法律嗎?抑或是他找到了一種方法,既能隱子,但又承認他的兒子犯法并傷害了失去羊的家庭,并能容納其他考慮?在《孟子》中,對假定的價值沖突的更細致入微的討論強烈地暗示是后者。 家庭固然十分重要,但要說它對國及其法或民族主義關懷具有“優先性”,顯然過于簡單。相反,面對社會世界和物質世界提出的多樣要求,好的儒家行動者是尋找平衡的方法。 我們應當讓諸般價值處于和諧之境而不是簡單地排列優先性,這一思想至少和貝淡寧的方法一樣為儒家民族主義開啟了很大的空間,并與他論辯中的其余部分相當一致。貝淡寧的思路似乎認為,民族主義只在家庭不具有優先性的環境下才是問題,而我的思路側重“和諧”,以此我得以強調,對國或天下等的關切本身能以更為通俗的方式被感受到。貝淡寧對民族主義的最低定義有兩點要求:“服務于一個有著領地邊界的國家的志向”,和“對生活在該國的人民的特殊承諾”(一個提醒:界限對民族主義確實很關鍵,但至少從理論上講,這些界限是否對應于國界并不重要。貝淡寧的定義似乎把民族主義局限于民族國家,盡管民族國家確然是重要類型,但并不能窮盡此范疇。)我們談論的是什么樣的“特殊承諾”?它如何表現?我的回答是:一個人的承諾通過他參與到民族集團的特殊價值觀和實踐來表明,或通過認同該集團興起(或經歷的辛勞)的故事來表明。換句話說:通過參與民族文化,特殊承諾得以顯明。 這或許是令人驚訝的,因為貝淡寧已經告訴我們,一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轉型,即“從對文化觀念的認同(文化論)轉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事實上,這與我的建議相容,即民族主義可以通過參與民族文化來表明,因為文化論的“文化”和民族主義的“文化”是不同的。前者是指被文所化的狀態,與缺乏文化(或文明)相對:一定程度上,人民都被文所化。因此,舉例來說,韓國人或日本人可以被認為是相對開化的,只要他們承認天子之命(即中國皇帝)和儒家的規矩及其實踐。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把一個既定民族的文化視為諸般文化之一。因為“我們”贊同“我們的文化”之獨特的價值觀,我們可以置我們的文化于高處,其他不贊同同樣的一套價值觀的文化就比我們的要低等,但我們并不認為所有其他文化是我們自身文化的退化形式。民族文化可以是多樣化的并互相競爭,但我主張,在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中,族民展現他們對國族的特殊承諾是在于對民族文化的參與。貝淡寧提到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個特例,他將之定義為這樣的“確信”:“與國族聯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化構成國民身份認同的基礎”。(同上,115頁)這部分正確:文化民族主義的一個關鍵是,文化是“基礎”,而不僅僅是國族身份的表達手段。但對于文化民族主義同樣是核心的一點是,文化之特定支流是權威性的,比如,在中國是儒家,在印度是印度教(而且常常是其中的某種特定解釋)。文化民族主義之所以獲得力量并引來爭議,并不因為它贊同現代國家的文化之所有側面,而是在于它讓一個傳統處于優勢地位。 考慮到所有這些,我們最后可以回到本文的第二點,即貝淡寧有時不太理解文化和國族會對儒家實踐的具體內容產生影響。因循“文化民族主義”的觀念,貝淡寧說,“被納入‘儒家之國’的唯一相關準則是承諾儒家價值觀”。但是,這個意義上的“儒家之國”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容納不了邊界確定的獨特共同體的觀念,而那(按貝淡寧的想法)對于民族主義來說是很關鍵的。相反,我們需要思考“諸般儒家民族主義”,每一種是特定民族共同體所獨有的。韓國的儒家不同于中國的儒家,而中國的又不同于印尼的。在筆者最近一篇論及美國儒家之前景的文章中,我較多援用中國佛教和美國佛教的比喻。當佛教經師在公元紀元初來到中國,他們啟動了雙向適應的過程:中國和中國人適應印度和中亞佛教的語言、概念和踐習,但這些東西又反過來被中國語言的、概念的和踐習的癖性所適應。在這一適應過程的早期,中國佛教的可能性本身(暫且不論任何中國特色的佛教教義之正當性)是被質疑的。但最終,中國成為世界佛教的主要中心。美國佛教在近幾十年的飛速成長(現在是美國第三大宗教)展現出許多類似的特點。和佛教一樣,儒家是有著普世抱負的哲學—宗教傳統:它自稱適用每個人,而不是僅限于中國人。但和佛教一樣,當儒家到了它的出生地之外的地方,它被改變了。任何對儒家與民族主義之互動的討論,都必須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一動力機制。 貝淡寧對儒家民族主義在中國未來可能擔當的角色抱樂觀態度。他承認,有些人對儒家和民族主義都擔憂——儒家可能會允許對家庭的關切而擾亂政治共同體,而民族主義可能被國家濫用——但他對此的回應是,兩種操心都夸大其詞了。他說,儒家的家庭觀畢竟是傾向于支持關心他者的德行之發展的,而儒家在歷史上也經常對國家的錯誤治理提出批評。此外,許多當代儒學理論家已經呼吁保護某些公民權利。這都不錯,但還太弱。在全球范圍內的許多社會,人們已經認識到,民族主義有可能被用作萬金油,為任何種類的錯誤治理辯護,因此,假如民族主義的建設性一面要得到揭示,就必須面對強大的抵制。眾所周知,儒家作為限制國家權力的源泉在歷史上短處多多,這不僅被儒家的批評者所強調,甚至也被著名的儒家思想家所強調(比如新儒家牟宗三)。貝淡寧注意到,像蔣慶和康曉光這樣的當代儒家呼吁公民權利,但這只是一方面,要他們據理為這樣的自由提供恰當的辯護,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同意牟宗三的一個看法,即在歷史上的儒家傳統中根本找不到據理對公民或政治權利的直接辯護。我不嘗試在此處捍衛這個主張。但是,如果這一結論被接受,那么,就只有兩個途徑:要么,任何可接受的儒家民族主義必須被放置于混合型政體,該政體納入了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強有力保護,而這些權利并非從儒家引申出來;要么,我們需要為這些權利找到比貝淡寧已經識別的都更為強健的儒家基礎。這兩種取徑的任一種都將解決我所說的問題。一個綜合了儒家思想的強健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體系將免于極端家庭論和民族主義的濫用。 就我對貝淡寧更大議程的理解而言,我相信他更偏愛上述兩種選擇中的第一種,即混合政體。對當代中國來說,這是可理解的取徑,即這是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對建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有正式的承諾,其中包括對個人權利的諸多保護。我相信,也有可能嚴格根據儒家義理為個人權利的強有力保護體系提供辯護:我在將要出版的《當代儒家政治哲學》一書中認為,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辯更值得提倡,而且比通常所認為的還要成功。該論點的核心是,為了有可能實現儒家對德的承諾,我們中的每個人(包括圣賢)必須接受被獨立的法律和權利所制約的狀態,即使那不是20世紀之前的儒者所做出的證明。只要我們承認儒家是個活著的傳統,我們就應當承認,儒家能繼續發展,就必須回應新的洞見和新的處境。只有一個活著的儒家,才能足夠靈活,以找到擁抱民族主義之價值側面但又能避免其缺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