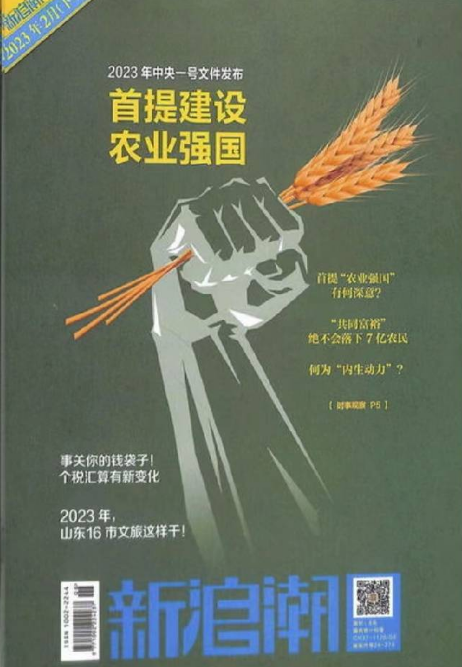元代稅糧制度初探
陳高華
元代賦稅,主要有二項,一是稅糧,一是科差。
在我國封建社會,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因此,糧食是封建國家用賦稅形式向編戶齊民征收的主要物資。元代的稅糧,就是指以征集糧食為主的稅收;其項目在南北有所不同,北方是丁稅和地稅,南方則是夏、秋二稅。
元代稅糧制度是很復雜的,不僅南北異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此外,有關的一些文獻資料的記載存在不少錯誤,也增加了了解這項制度的困難。本文對這個問題作初步的探索,特別著重于對《元史·食貨志·稅糧》(這是關于元代稅糧制度最基本的史料)的記載作必要的考辨和補充。目的是想通過對這一制度的解剖,從一個側面來說明元代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狀況。
一 北方的稅糧制度
元代北方的稅糧制度,分為丁、地稅兩種。《元史·食貨志》敘述北方稅糧之法,大體如下:
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
[中統]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余悉征之。……
[至元]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
上面幾段記載,帶給我們一連串問題。歸結起來,集中到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民戶到底負擔什么稅?另一個是,丁、地稅的稅額到底是多少?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民戶負擔什么稅?
元代戶籍問題十分復雜。封建國家按不同的職業以及其他某些條件,將全體居民劃分為若干種戶,統稱諸色戶計。各種戶對封建國家承擔的封建義務各有不同,例如,軍、站戶主要服軍、站役,鹽戶主要繳納額鹽,其他賦役就可以得到寬免或優待。儒戶宣揚孔、孟之道,各種宗教職業戶宣揚天命論,對維護統治秩序有用,在賦役方面也得到優待。因此,戶、地稅對各種戶來說是很不相同的。從《元史·食貨志》的敘述來看,有幾種情況:
(1)工匠、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等,都是“驗地”,也就是按占有的地畝數,繳納地稅。
(2)軍、站戶占有土地在四頃以內可以免稅,四頃以上要按超出的數額繳納地稅。
(3)官吏、商賈“驗丁”,即按每戶成丁人數繳納丁稅。元代法定的成丁年齡沒有明確記載,估計可能是十五歲①。
以上幾種情況,交代的比較清楚。但是,對于占居民大多數的民戶應該繳納什么稅,記載卻是含糊不清的。太宗丙申年(1236)的規定,既說“驗民戶成丁之數”收稅,則應是民戶負擔丁稅。可是接著又說:“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征焉。”則民戶納的應為地稅(以牛具計數,是按地征稅的變種)。上面兩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下文還有一段:“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這兩句話常被人們引用作為元代北方稅糧的原則。但只要認真一想,就會產生許多問題:“少”和“多”的標準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又怎么辦?像這樣奇怪的沒有統一標準的稅制,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且事實上也絕不可能行得通。
《元史·食貨志》是根據元代政書《經世大典》節錄而成的。《經世大典》早已散佚②,無法窺見原文。我們只能根據元代其他記載,對北方民戶的稅糧負擔問題,作一些探索。
元末,危素曾不止一次談到南、北賦役原則的差別。他說:“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田(南)則取諸土田。”又說:“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③南方賦役是按土田征收攤派的,北方賦役則是按戶口征收攤派的。這是元代南、北賦役根本差異之所在(當然,這里是指占人口大多數的民戶說的)。
元秦定帝泰定元年張珪等人的奏議,說的也是一樣:
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征丁稅,其括勘重并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④。
北方原來只征丁稅(前面危素所說的“取諸戶口”,實際上就是指的丁稅),中期以后,雖有變化,亦僅限于兩淮、河南括勘所得田土。正因為民戶已征丁稅,而括勘田土又征地稅,故張珪等稱之為“重并稅糧”,主張“除之”。
除了上面幾條材料外,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有力的旁證。太宗丙申年詔令全文已不可見,但保留下來的文字中有一句話,說是“依仿唐租庸調之法”⑤。唐代租庸調,正是按丁征收的。
既然北方民戶負擔的是丁稅,那末,為什么《元史·食貨志》的記載,會如此混亂呢?原來,元代北方各種戶的丁地稅負擔各不相同,早已造成了很大混亂,以致當時有很多人已不很了然了。請看元代前期的官僚胡祗通的敘述:
近為民戶張忠買到軍戶王贊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重納重稅事。……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稅糧一也,而曰丁糧、地糧;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推取,義例甚明。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并當重當者也。
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既納丁糧,囚買得稅之地,而并當地稅。或地稅之家,買得丁糧之地,而并納丁糧。如此重并,府、司屢申,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繁亂,名實混淆,軍民重并,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后失信。……
所以名曰丁糧、地糧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日隨地推收,先自先(當作食)言。合曰丁糧、地糧,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賣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稅;軍賣與民地,不問多寡,止納丁糧。豈不簡易⑥。
胡祗通是一個精明強干的地方官,他這篇文字很重要,幫助我們弄清了如下問題:(1)根據元朝政府規定的格例,當丁稅者不納地稅,當地稅者不納丁稅;軍戶地在四頃以上納地稅,四頃之內免,民戶只納丁糧。這和上面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說明所謂“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是不正確的。(2)由于只納丁糧的民戶和只納地稅的軍戶(還有其他戶)之間相互買賣土地,因而在征收稅糧時出現了混亂和糾紛,往往同一戶并納二者。元世祖忽必烈時如此,到了后來,一定更加混亂。(3)由于格例遭到破壞,“案牘紊亂,名實混淆”,以登錄案牘為主要內容的《經世大典》,肯定也是混亂的。明初《元史》的編者,都是一些南方的文人,還有一些理學家,他們對元代制度(特別是北方)本來就不很清楚,對《經世大典》的文字任意刪削,于是就在《元史·食貨志》中留下了許多矛盾牴牾之處。
為什么元代北方民戶稅糧采取按丁征取的辦法?原因很簡單。在連年戰亂以后,北方農業勞動人手大大減少了,地廣人稀。農業生產普遍采取廣種薄收的辦法,每個勞動力耕地往往達百畝之多⑦。在這種情況下,控制勞動力的意義更為突出。所以統治者采取按丁的辦法。
第二個問題:丁、地稅的稅額是多少?
先說地稅。《元史·食貨志》沒有說太宗丙申年(1236)的地稅數額是多少。據有的記載說,丙申年規定,“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⑧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改為白田每畝三升,水田每畝五升。到了至元十七年(1280),干脆連水田和旱地的區別也取消了,地稅每畝三升。元朝政府逐步取消了地稅的等級差別,主要是因為在地廣人稀、廣種薄收的情況下,劃分土地等級,意義不大,不如采取一個平均數,較為簡便易行。
再說丁稅。丁稅在北方稅糧中所占比重較地稅大得多。《元史·食貨志》的有關記載好些是不清楚或過于簡略的,需要加以說明,有的還要訂正。
《元史·食貨志》說:“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但均未言具體時間。據《元史·太宗紀》:“(元年)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則確立以戶征稅原則,在太宗元年(1229)⑨。戶科二石,亦應在此時.又太宗五年(1233)詔令,沿河置立河倉,“其立倉處,差去人取。辛卯(三年)、壬辰(四年)年元科州府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并附余者撥燕京”⑩。“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即增一倍。可知戶稅由二石增為四石,應即太宗五年之事。當時南宋派到北方的使節,也提道:“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⑾
太宗六年(1234),蒙古政權在北方括戶口。太宗八年(1236),在括戶基礎上,“始定天下賦稅”⑿。《元史·食貨志》說,這一年“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可見,從這一年起,按戶征稅糧變成了按丁征取。
但是,《元史·食貨志》這一段記載,卻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原來每戶粟四石,現在改成每丁粟一石。如果每戶平均四丁,那末丙申年前后稅額相當。但是,每戶平均四丁的現象,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而根據這次括戶的統計,平均每戶五口強⒀,除去老幼和婦女,絕不可能每戶平均四丁,只可能有兩丁左右。這樣,只有兩種解釋,一是蒙古統治者減輕了剝削,另一是記載有錯誤。前一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蒙古統治者在控制中原后,千方百計進行搜刮,哪里有自動減輕剝削之理.因此,只可能是《元史·食貨志》的記載有問題。估計,“每丁歲科粟一石”應是“粟二石”之誤。因為:后來忽必烈時代丁稅就是粟二石[詳見下文];再者,以每戶二丁計,一丁二石,正好與原來一戶四石相當。
又,“驅丁五升”,亦疑有誤。元代賦稅通常以驅口為良人的一半。丙申年的規定不應相去如此之遠。此外,當時北方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奴隸,如果對驅丁(奴隸)征稅如此之低,勢必大大影響蒙古政權的財政收入。估計,“五升”應為“五斗”。
丙申年規定中的“新戶”,系指蒙古滅金后由河南遷到河北各地的民戶而言。他們顛沛流離,生活很不安定。蒙古政權為了誘使他們定居下來,所以在賦役方面暫時有所放寬。太宗十年(1238)六月二日的“圣旨”中提到的民戶,也有新戶、舊戶之分。建立站赤時,“舊戶二百一十七戶四分著馬一匹,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著馬一匹;舊戶一百九十六戶二分著牛一頭,新戶三百三十八戶四分著牛一頭。”⒁新戶的負擔為舊戶的一半。由承擔站赤牛馬的情況,可以推知“新戶丁驅半之”的記載是正確的。
《元史·食貨志》中關于至元十七年戶部諸例的敘述中,提到“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也是有問題的。估計亦應為二石之誤。我們的根據是:
(1)文中說:“減半科戶每丁粟一石。”既云減半科戶,則其丁稅自應為全科戶之半。由減半科戶的稅額可以推知全科戶丁稅應為二石。
(2)文中列舉新收交參戶每年遞增丁稅數,除第二年脫漏(疑應作一石),自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遞增二斗五升。據此數推算,則第六年人丁稅時,應為二石。
(3)文中云:“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而據《元史·桑哥傳》:“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協濟戶“半賦”為一石,則全賦為二石無疑。
(4)延祐七年(1320)的中書省咨文,其中說:“腹里漢兒百姓無田地的每一丁納兩石糧,更納包銀、絲線有。”⒂包銀、絲線屬于科差。這篇咨文明確指出了丁稅為兩石,和上面的分析完全一致。
總之,我們的結論是,蒙古政權先以戶定稅,每戶稅糧開始為二石,不久增為四石。太宗丙申年起,改為以丁定稅,稅額為每丁粟二石,驅丁、新戶一半。
在討論北方稅糧制度時,還必須討論一下窎戶的問題。《元史·食貨志》載:“至元三年,詔窎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于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政府專門為之頒布詔令,說明窎戶的數量是不少的。
窎戶的涵義是什么?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討論過。窎戶亦稱窎居人戶,指的是離家到他鄉生活的民戶。上引至元三年詔書中所謂“附籍之郡”,指窎戶的本貫,即戶籍所在地;“種田之所”,即窎戶現在生活勞動的地方。在當時,這種情況有時也稱之為僑寓、客戶等。山東益都元代《駞山重建昊天宮碑》的碑陰,有“管寧海州窎戶崔千戶”一名⒃。這個崔千戶管理的就是本貫寧海州、現窎居益都的人戶。
武宗至大三年(1301)的一個賑濟災民的文書中說:“亦有窎居人戶正名下曾申告災傷賑濟,其各管頭目人等,代替申報,各州縣并不照勘取問,便行移文元籍官司倚除。”元朝政府認為這樣不妥,決定“今后……窎居者亦依上例,令各戶親赴見住地面官司陳告,體復保勘是實,各用勘合關牒,行移原籍官司,以憑查勘移除”⒄。以這份文書和《元史·食貨志》中有關窎戶的記載相對照,就很容易理解。“見住地面”即《元史·食貨志》中的“種田之所”,“原籍官司”即“附籍之郡”。而“各管頭目人等”即上述《昊天宮碑》中的崔千戶之類.這份文書說明,一直到元代中期,仍有窎戶之稱,而且繼續采取另行設官管理的辦法。
《元史·食貨志·稅糧》中說,“其(窎戶)丁稅于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這樣的說法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誤會窎戶既納丁稅又納地稅。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窎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戶計,規定應納丁稅的戶計(如民戶),因為戶籍在本貫,所以丁稅在原籍交納;規定納地稅的戶計(如軍、站戶等)所種土地在見住地面,所以地稅要“于種田之所驗地而取”。上舉賑濟災民的文書規定窎戶受災,由見住地面官府行移原籍官府倚除,正好說明窎戶一般均是納丁稅的民戶,他們要在原籍繳納稅糧。
上面我們討論的是元代北方的正額稅糧,實際上百姓的負擔決不以定額為止。《元史·食貨志·稅糧》說:“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則每石稅糧須加納七升。這也是官方的法定數。據胡祗通說:“鼠耗、分例之外,計石二、三可納一石谷”,而且都要“精細干圓”;到倉庫交糧時,“人功車牛,往反月余,所費不淺”。不僅如此,許多倉庫“并無厫房”,于是又強行“借之與民”,“秋成征還加倍”。經過這樣層層剝削的結果,“是國家常稅本該一石,新舊并征,計以加耗,而并納三石矣”⒅。忽必烈的親信謀士劉秉忠也曾提出“倉庫加耗甚重”,要求統一度量衡,以免上下其手⒆。正額之外的附加名目往往超過正額,這是封建賦稅制度的一種普遍現象。我們在研究封建賦稅制度以及勞動人民負擔時必須注意這個問題。
二 江南稅糧制度
元代江南稅糧之法,與北方大不相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日夏稅,此仿唐之兩稅也。”北方的稅糧,包括丁稅和地稅;南方的稅糧,則專指土地稅而言。
江南兩稅之中,以秋稅為主。秋稅征糧,夏稅一般是按秋稅所征糧額分攤實物或錢。所以我們的討論就從秋稅開始。
秋稅每畝土地征收多少?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元史·食貨志》對此沒有記載。有的同志以為“江南田賦,也是每畝三升,與中原同”。并進一步推論:“宋代田賦,每畝遠在三升以上,今元代改為每畝三升,總是要比宋代輕得多。”⒇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
我們試舉數例:
徽州路共一州五縣。其中歙縣田分四色,上田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休寧縣上田秋苗米二斗四升七合四勺八抄。祁門縣地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上田秋苗米二斗一升六合一勺。黟縣田分五色,與祁門同,上田秋苗米九升七合二勺九抄。績溪上田秋苗米三斗五合六勺二抄。婺源地分六色,上田秋苗米一斗八升九合五勺八抄[21]。
鎮江田分四等:上、中、下、不及等。上等秋苗米每畝四升五合或五升,不及等秋苗米一升[22]。
婺州蘭溪“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23]。
常熟田土“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起科”[24]。
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1)元代江南并不存在統一的田賦稅額。地區之間,差別很大。同一地區內也有若干土地等級,承擔數量不等的秋糧。(2)有的地區秋糧稅額在三升之下,但也有不少地區,遠在三升之上,甚至有高達十倍者。因此,所謂江南每畝三升之說,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元代官方文書中說,江南“田地有高低,納糧底則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勻一般”[25]。這是符合江南實際情況的。宋代江南各地田土稅就很復雜,“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26],也就是說,元沿襲了南宋的制度,并沒有制定新的辦法。各地稅糧和宋代一樣,是很不一致的,有的低到一、二升,有的高至二、三斗。
其次,關于江南夏稅的問題。
《元史·食貨志·稅糧》云:“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余獨征秋稅而已。……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稅之制,于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
按,成宗元貞二年征科江南夏稅的決定,見于《元典章》卷二十四《戶部十·租稅》。為了討論方便,抄錄如下:
元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過事一件節該:江南百姓每的差稅,亡宋時秋、夏稅兩遍納有。夏稅木綿、布、絹、絲綿等各處城子里出產的物折做差發斟酌教送有來,秋稅止納糧。如今江浙省所管江東、浙西這兩處城子里,依著亡宋例納有,除那的外,別個城子里依例納秋稅,不曾納夏稅。江西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時分納的如今納稅重有,謂如今收糧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糧的斛抵一個半大有,若再科夏稅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復么!兩廣這幾年被蘋賊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東、福建、湖廣百姓每夏稅依亡宋體例交納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欽此。
關于夏稅,有三點需要考辨。
(1)江西有無夏稅?據陳垣先生校改,上面所引《元典章》文書中,“江西”系“江南”之誤。有的同志由此立論道:“不征夏稅者應指所有用現行斗斛納糧之處,并不專指江西各地。”[27]其實,陳垣同志這條校改是否可信,很值得懷疑。第一,《元典章》文書中明言元貞二年起浙東、湖廣、福建三地起征夏稅;《元史·成宗紀二》亦云:“征浙東、福建、湖廣夏稅。”兩者完全一致。江西并不在起征之列。如將“江西”改成“江南”,那末,“浙東、湖廣、福建”都應包括在“江南”之內,這樣,全文前后顯然是講不通的。第二,有一份材料可以和《元典章》文書相印證,那便是方回的《紹興路嵊縣尹佘公遺愛碑》[28]。碑文說:“元貞二年丙申秋下車。越歸職方二十一年矣,未科夏稅。上司科夏稅,自明年丁酉春始。公建言:□(都)省咨,元行初江西以省斛,較文思院斛,民多納米叁斗奇,故免夏稅。”都省即中書省,“都省咨”應即《元典章》所載奏章。據此可知確為江西無疑。也就是說,江西在元貞二年增加夏稅的命令中,仍屬于免征之列.此外,兩廣也免征。除了原來已納夏稅的江東、浙西外,這一次在浙東、福建、湖廣三地增征夏稅。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省斛和文思院斛的比例大小問題。《元史·食貨志·稅糧》說:“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所謂“宋斗斛”就是文思院斛,它的一石相當于省斛七斗。元代江南多數地區都是用文思院斛征收稅糧的,例如,《大德昌國州志·田賦志》所載秋糧額,有文思院斛數,有省斛數,其折合就是這個比例計算的。《至正金陵新志·賦稅》也說:“米用文思院斛,當今七斗。”但也有些記載,如《至順鎮江志》說,文思院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一石折合省斛六斗多。前面所引元貞二年征收秋糧文書中所說“此亡宋文思院收糧的斛抵一個半大有”,以及方回文中所說“多納米叁斗奇”,顯然是后一種折算比例。看來,這兩種折算比例都是存在的,分別在不同地區使用。從上面所引一些元代方志記載來看,江東(金陵,即南京)、浙西(鎮江)、浙東(昌國州)輸納稅糧都以文思院數折合省斛數,但折合比例略有不同。只有江西多數地區則不加折算,按文思院斛原額用省斛征,這樣,實際上已多征了三分之一,所以才獲免夏稅。
(2)夏稅按什么標準征收?征收哪些東西?
對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類地區進行討論。一類是原來就征收夏稅的地區,即江東、浙西。夏稅大體上是按南宋原有辦法征收的,一般是按土地等級攤派實物,如《至順鎮江志·賦稅》載,鎮江“上等、中等者田則夏有綿,……地則夏有絲、綿、大小麥”。有的地區還征布[29]。也有些地區實物折合成錢,如徽州因為“絲、綿實非土產”,經過批準,“每歲絲、綿折納輕赍寶鈔”[30]。
另一類是元貞二年起征夏稅的地區,即浙東、福建、湖廣。元朝政府規定,也是“依亡宋體例交納”。為了確定各地的夏稅額,元朝政府還下令“追尋亡宋舊有科征夏稅版籍志書一切文憑,除文思院斛抵數準納省斛及已科夏稅外,但有未科去處,自元貞三年為始照依舊例比數定奪科征,務要均平。[31]
但是,在根據宋代記載定奪夏稅時,到處都存在實物與貨幣的折價問題。宋代的物價與元代物價不同,折算起來,到底以什么為據,大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以浙東紹興路為例,方回《嵊縣尹佘公遺愛碑》[32]中說:
上司科夏稅自明季丁酉春始。公建言:……絹壹匹該米叁斗奇,準時價中統鈔可兩貫奇。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內批,以越罕蠶,夏絹壹匹折納十八界會拾貳貫,永遠為例。故碑具存。時十八界會壹貫準銅錢貳伯伍拾文,拾貳貫計銅錢叁貫。向者欽奉先皇帝圣旨:亡宋銅錢叁貫準中統鈔壹貫。今欽奉圣旨浙東等處夏稅依亡宋例交納,則絹每匹合準中統鈔壹貫爾。……省割下,酌公請,越夏絹壹匹準中統鈔兩貫,它郡率三貫。
宋代征夏稅曾以實物(絹)折會子(紙鈔),當時的實物(絹)、會子、銅錢之間有一定的比例關系,即絹一匹=十八界會子十二貫=銅錢三貫。元初,又規定銅錢三貫等于中統鈔一貫,亦即絹一匹等于中統鈔一貫。但是到了元貞二年,這個比例關系隨著物價的上漲遭到了破壞,絹一匹時價中統鈔二貫多。要重征夏稅時,就發生了問題。這個官員主張按元初的比例征收,元朝政府當然不肯吃虧。結果是,對這個官員所在的紹興地區作了點照顧,夏稅絹一匹折合鈔二貫,其他地區折合鈔三貫。這正好說明,在大多數地區,實際上元代所征夏稅比宋代要重。
在有些地區,還實行按秋糧定夏稅的辦法。如浙東慶元路所屬昌國州,“至大德元年(元貞三年改),始以民苗為數,每石征中統鈔三兩,以為夏稅焉”[33]。這種辦法似乎是按秋稅糧額決定夏稅額的,它與宋代夏稅之間的關系,尚不清楚。當時昌國州官價米一升鈔六分半,一斗應為六錢五分。三貫合米四斗六升強。秋糧每石征夏稅錢三貫,則夏稅約相當于秋糧的一半。
(3)關于湖廣門攤和夏稅關系問題。《元史·食貨志·稅糧》說:
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余錠矣。
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
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按,中原所謂“門攤”,系指征稅時按戶攤派之意。如中統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五月中書省奏準宣撫司條款中云[34]:
今年照勘定合科差發總額,府科與州,驗民戶多寡,土產難易,以十分為率,作大門攤均科訖。
《元典章》卷廿二把“門攤”列于“雜課”一門,其中所載至元廿九年(1292)湖廣行省札付中說:“每戶一年滾納門攤課程一兩二錢”,“驗各家實有地畝均科,許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顯然,湖廣門攤也是按戶攤派之意,攤派時按各戶實有地畝數“均科”。征收門攤是作為“許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的代價,換言之,就是一種酒醋稅。因此,它與夏稅之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此后的一些記載也完全證明這一點。大德五年(1301)九月,“江陵、常德、澧州(均屬湖廣)皆旱,并免其門攤酒醋課。”大德六年(1302)三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并蠲免之”[35]。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浙水,民饑。詔賑糧三月,酒醋門攤課程悉免一年。”[36]又,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討論私酒處理辦法時,曾引用湖廣行省常德路的申文:“酒醋課程,散人民間恢辦,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納門攤酒課者,許令造酒食用。”中書戶部同意這種“認納門攤,許令釀造飲用”的辦法[37]。可見,門攤就是酒醋課,這是不成問題的。而且,門攤并不限于湖廣,江浙也有。另外,有一點需要注意,上所引“(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并征之”的說法是不可信的,在此以后,門攤仍然存在。如前所述,湖廣夏稅,應該是元成宗元貞二年決定、次年起征的,此后夏稅與門攤并存。
上面所講的是江南夏稅的一般情況,還需要指出的是:(1)元代江南兩稅不斷加重。元朝政府在延祐七年(1320)下令:“凡科糧一斗上添答二升”,即增加百分之二十[38]。(2)和北方一樣,繳納稅糧時,要加以鼠耗分例,“江南民田稅石,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39],以鎮江為例,“秋租正米十一萬七千余石,鼠耗米為五千三百余石”。實際上,要繳納稅糧的各種額外支出,名目繁多,決不限于鼠耗分例七升。如湖南郴州,“受納秋糧,石加五斗”[40]。(3)繳納兩稅時,豪強地主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他們欠下的份額就由官府強行轉加到農民頭上,如浙西平江(蘇州),交稅糧時,“初限皆細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僅納二、三,卻用細民多輸者足之”[41]。因此,南方一般農民的稅糧負擔,比法定的數額要大得多。“前年鬻大女,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稅迫,非以饑所為。”[42]稅糧“科征之際,枷系滿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饑寒迫身”,殘酷的賦稅剝削,把廣大勞動人民逼得無法再照舊生活下去,或者死亡,或者逃亡,更多的則走上了反抗的道路[43]。 三 官田稅糧
上面所說南、北稅糧制度,都是就民田而言的。現在我們來討論元代官田的稅糧制度。
《元史·食貨志·稅糧》云:
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
凡官田夏稅皆不科。
按,江北、兩淮荒田召募開耕之法,見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詔令,其中規定:“若有前來開耕人戶,先于荒閑地土內驗本人實有人丁,酌量標撥,每丁不過百畝”;“三年外依例收稅”[44]。《元史·世祖紀十》記此事,亦云“免稅三年”,則應是第四年起科。但大德四年(1300)十月詔令:“江北系官荒田,許給人耕種者,原擬第三年收稅;或恐貧民力有不及,并展一年,永為定例。”[45]《元史·成宗紀三》同。則似在至元二十二年后,已將“三年外依例收稅”改為第三年起科,但后來又改了回去。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招募農民開墾耕種江南官府“荒蕪田土”[46]。二十五年(1288)正月規定,耕種江南公田荒閑田地,“第一年不要地稅,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三停內交納二停。種的百姓每根底不交當別個雜泛差役”[47]。其收稅之法比起江北、兩淮來,有所不同。
官田的所有者是封建國家,租佃者便成了國家的佃戶。因此,官田的地稅,不同于民田的地稅,實際上是一種地租。
除了荒閑田土之外,還有另一類官田,在《食貨志·稅糧》中卻被忽略了。那便是兩浙特別是浙西一帶的官田,多數是比較好的土地。它們是宋、元兩代通過沒收罪人的資產和向民間強行收購等方式得來的。例如有宋末年賈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六郡強行收買民田三萬五千余頃,后來雖曾退還民間,但到元代仍被收為官田[48]。元成宗沒收浙西豪門朱清、張碹的田土,每年稅糧即達十余萬石[49]。這一類官田的總額雖不可知,但僅鎮江一地即達九千余頃,為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強[50];而平江、松江等地官田數更遠在鎮江之上。由此也足以推知官田為數之巨了。
兩浙官田,有的由地方官府管理,有的由元朝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如江浙財賦都總管府、江淮財賦都總管府等管理。官田土地有的直接租給農民,有的由官僚豪強承佃,再轉租給農民。例如松江大地主瞿霆發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51],足見其包佃官田達七千余頃之多。
這類官田的稅糧就是地租,通常都照入官前租額起科,為土地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其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52]浙西官田有的每畝“歲納稅額須石半”[53];浙東上虞官田最高“畝歲輸谷二石二斗”[54]。所以當時有人說:“公租視民所輸且二十倍”[55],確非虛語。和民田的情況一樣,官田稅糧交納時,同樣也加上許多額外的費用,例如鎮江官田,“畝納五斗之上,及至秋成,催租勾擾,赴倉送納,又有船腳、加耗、倉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輸納正米五斗”[56]。
還要指出的是,有的官田也要交夏稅,鎮江、湖州等地區江淮財賦總管府所轄官田就收征絲、綿、大麥、小麥等物作夏稅[57]。這也許是根據各類土地的出產物不同而征收不同的東西。這個問題還值得研究,但《元史·食貨志·稅糧》所說:“凡官田夏稅皆不科”,則肯定是不確切的。
官田租額很高,“輸納之重,民所不堪”[58];而且“不問兇荒水旱歲”,都要如額征收[59]。當佃戶“終歲勤苦,盡田內所得籽粒,輸官不敷,拖及無納”時,官府便將其“父子妻女,累累禁系,枷扒拷打,抑逼追征,十戶九空”;使他們只好“將家業變賣無資產者賣子鬻妻。或棄生就死者有之,拋家失業者有之”。因此,浙西農民,“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誰肯耕作!”[60]殘酷的封建剝削,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至于官僚地主包佃的官田,也交納地稅,但性質有所不同。這是他們與封建國家之間瓜分地租收入。在這些包佃人控制下的佃戶,要受雙重剝削,其遭遇之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四 附論:代役田
《元史·食貨志·稅糧》最后談到助役糧問題:
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之上者,于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于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余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按,助役糧又名義役,始自宋代。元代部分地區仍然施行。見于元朝政府法令,則自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始。《元史·英宗紀二》:
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
可見“泰定之初”說法不確。原來民間義役之法,各地有所不同。有的是“分戶九等,各出助田若干,……每歲以三、兩戶應充里正、主首,即收義粟與之”[61]。有的是“眠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62]。助役法頒布后,不少地區都采取按比例抽田入官的辦法,有的地方“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63]。有的地方達到“田畝什抽一以助役”[64]。
原來民間所行義役,無論田產或是錢,都掌握在地主豪強手里,他們可以從義役田的地租或義役錢的利息中得到很大好處。助役法推行之后,助役田由官府掌握,得到好處的主要是官吏。
助役田主要為了解決差役問題。里正、主首是元代差役的重要項目,元朝政府用差役的辦法來建立自己的基層政權組織。助役田就是元朝政府從經濟上加強其基層政權的一項措施。但助役田上的收入除交納二稅之外,按規定應專門用作津貼差役之用,并非封建政府的賦稅收入。因此,將它列入稅糧名下是不恰當的。
注釋:
① 當兵以十五歲為成丁,見《元史·兵志一》。工匠“拾伍歲已上為大口。”見《通制條格》卷一三,《錄令》。
② 部分篇目和各篇序錄保存了下來。
③ 《休寧縣尹唐君竅田記》,《危太樸文集》卷二。《書張承基傳后》,《危太樸文續集》卷九。
④ 《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⑤ 《經世大典序錄·賦典·賦稅》,《國朝文類》卷四○。
⑥ 《丁糧地糧詳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⑦ 《匹夫歲費》,《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⑧⑿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國朝文類》卷五七。
⑨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記太宗六年(1234),蒙古統治集團曾圍繞著是否“以丁為戶”展開激烈爭論,疑應為太宗元年事。
⑩ 《大元倉庫記》。
⑾ 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按,徐霆至燕京,應在太宗七、八年之間。
⒀ “七年乙未,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⒁ 《大元馬政記》,《經世大典·站赤》,《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⒂ 《元典章》卷二一,《戶部七·錢糧》。又見《典章新集·戶部差發》。
⒃ 《益都金石記》卷四。
⒄ 《元典章》卷一七,《戶部三·戶計》。
⒅ 《論倉糧》,《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⒆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⒇[27] 《元代賦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
[21]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貨·元歲征之式》。
[22][48][56][60] 《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
[23] 胡翰:《吳季可墓志銘》,《胡仲子文集》卷九。
[24] 《嘉靖常熟縣志》卷二,《鄉都志》。
[25] 《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租稅》。
[26] 蘇伯衡:《覈田記》,《蘇平仲文集》卷六。
[28] 《越中金石記》卷七。
[29] 《吳興續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門引。
[30]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貨·元歲征之式》。楊翮:《送李復之郡曹調寧國序》,《佩玉齋類稿》卷六。
[31] 元貞二年九月科征夏稅文書,見《元典章》卷二十四,《戶部十》。
[32] 《越中金石記》卷七。
[33] 《大德昌國州志》卷三,《敘賦·田糧》。
[34] 《元典章》卷二五,《戶部十一·差發》。
[35] 《元史》卷二○,《成宗紀三》。
[36]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
[37] 《元典章新集·戶部·酒課》。《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酒課》。
[38] 《元史·英宗紀一》。《元典章》卷二四,《戶部十·租稅》。
[39] 《元典章》卷二一,《戶部七·倉庫》。
[40] 黃溍:《參知政事王公墓志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一。
[41] 鄭元祐:《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僑吳集》卷一一。
[42] 王冕:《悲苦行》,《竹齋詩集》卷二。
[43] 朱德潤:《平江路問弭盜策》,《存復齋續集》。
[44][45][46] 《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荒田》。
[47] 《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種佃》。
[49] 王艮:《議免增科田糧案》,《嘉慶松江府志》卷二○,《田賦志上》。
[50] 《至順鎮江志》卷二,《田土》。
[51] 楊瑀:《山居新話》。
[52] 吳澄:《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吳文正公文集》卷二八。
[53] 朱德潤:《官買田》,《存復齋文集》卷一○。
[54] 貢師泰:《上虞縣竅田記》,《玩齋集》卷七。
[55] 鄧文原:《刑部尚書高公行狀》,《巴西文集》。
[57] 《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吳興續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門》。
[58] 吳師道:《國學策問四十道》,《吳禮部集》卷一九。
[59] 朱德潤:《官買田》。
[61] 陸文圭:《陸莊簡公家傳》,《墻東類稿》卷一四。
[62] 黃溍:《鄞縣義役記》,《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
[63] 黃溍:《禮部尚書干公神道碑》,《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七。
[64] 鄭元祐:《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公遺愛碑》,《僑吳集》卷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