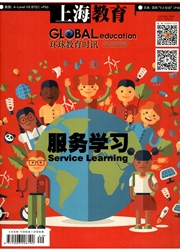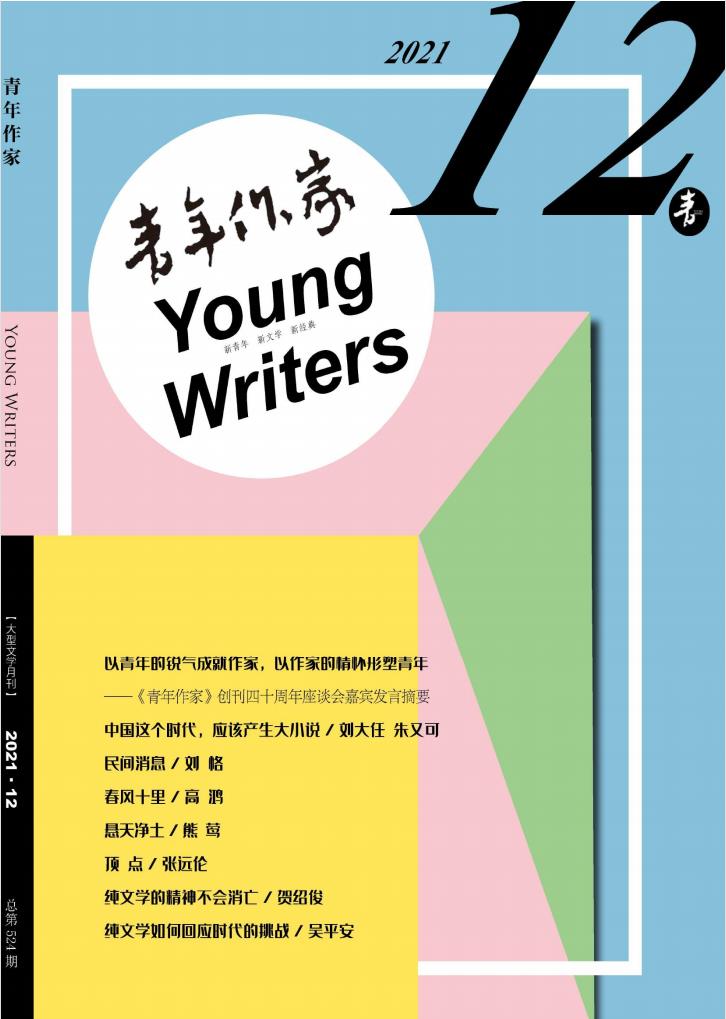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一)
佚名
市場源于分工。但市場一詞,因所論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概念。本文目的在探討十五世紀以來我國國內市場變化對于資本主義發生和的作用。因而可定義為:商品流通形成市場。商品流通的量決定市場的大小,商品交換的決定市場的性質。
馬克思說:“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前提。”[1]①在西歐,由于日耳曼人的征服和城市的破壞,進入封建后,商業大大衰落了,封建領地變成彼此孤立的莊園。到十六世紀以后,民族市場和世界市場形成,才成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重要條件。在我國,由于較早地廢除了領主制割據和實現國家的統一,商業一向比較發達。但是,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不是較早,而是萌芽較遲、發展甚慢。這是什么原因呢?
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遲緩,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的問題。我認為,主要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去尋找原因;另外,也有流通上的原因。在封建社會,不是所有的流通都能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是要看這種流通,能否為擴大再生產準備市場,能否為生產積累貨幣資本,在這樣的非海上貿易國家,還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改變。
一 我國封建社會的各級市場
我國的封建商業,在宋代有了飛躍的發展。它打破了坊市制,形成各級市場。下面就按照各級市場,考察一下流通的作用。
第一,地方小市場,即墟集貿易。這是我國封建社會十分發達的一種交易形式。宋代的墟集、草市已頗具規模,其稅收幾占全部商稅之半。然而,和西歐所稱集市不同①我國的墟集基本上都是地方小市場,范圍不出一日內往返里程。這種市場上的交換,主要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是屬于自然經濟范疇內的交換,它的一定的發展,不是破壞自然經濟,而是鞏固自給自足。這種交換,雖采取商品形式,但是為買而賣,實際是使用價值的直接交換;雖也經商人之手,但除臨近大城市水陸要道的一些草市外[2]②,實際上沒有什么流通的作用。只是在后來,隨著長距離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小地方小市場逐漸有了大宗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以至成為真正的初級市場,其性質才有所不同。這種變化,是在明代在江南某些絲的集中產區開始出現的。
第二,城市市場。這是我國封建社會最為發達的一種市場形式。宋代的汴京和臨安,如《東京夢華錄》《夢梁錄》等所記述,已達高度繁榮景象。然而,和中世紀西歐的城市不同,我國的封建城市,原來都是各級政權統治的中心,或是軍事重鎮,集中了大量的消費人口,城市手的生產也主要是供城市居民的消費。[3]③因此,城市市場上,主要不是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而是一種以政府和私人的貨幣收入為基礎的交換,即貴族、官僚、士紳(以及他們的工匠、隸役、士兵、奴仆)用他們的收入來購買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而他們的收入,基本上不外是封建地租的轉化形態,即農民的剩余產品。[4]①所以,城市市場的繁榮,主要是反映封建經濟的成熟(剩余產品和地租量的擴大),并不代表真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種交換中,農村流入城市的產品,盡管也經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單向流通,而沒有回頭貨與之交換。這種流通大體包括三個內容:(1)政府征收的田賦和雜課;(2)城居地主引入城市的地租;(3)商業高利貸資本取自農村的利潤或利息。這三項,無論采取實物或貨幣形態,家村每年都要把同值的產品輸往城市,而不能從城市取得商品來補償。這種單向流通造成城市繁榮,但由于沒有商品交換,它實際不是商品,不是商品流通。
我國城市市場這種消費性的特點,雙使得它特別發展了零售商業、鋪坊加工業、飲食業和服務業,象宋代《清明上河圖》所表現的,都是這種商業。這種商業自然也積累了一定的貨幣資本,但是,與那些經營長距離販運貿易的大商人(如后來的微商、山陜商、粵商)是不可比擬的,并且,直到消費社會興起以前,城市零售商業并不是執行流通任務的職能商人資本(飲食、服務業當然更不是了),而是一種“不執行職能或半執行職能”的“雜種”[5]②。因而,這種商人資本盡管發達,對于我們的目的來說,作用是不大的。
但是,隨著長距離販運貿易的發展,在沿江、沿海等商路要道上,逐漸會興起一些新的商業城市。這些城市市場,反映真正商品的擴大,其作用就不同了。宋代已有許多商業城市出現,不過,主要是在沿海地區,如廣州、泉州、明州、秀州等,反映海運貿易的發展。經元代大規模修建水陸驛道,到明王朝,國內市場的新興商業城市才有比較顯著的發展。
第三,區域市場。如通常“嶺南”“淮北”這些概念中的市場,以及多數省區范圍內的市場。它們是由同一自然地里條件和共同生活習慣形成的,因此,區域市場內的流通,一般并不反映生產的地域分工或社會分工。這種區域市場,可視為農村自然經濟的延伸。原來所謂自然經濟,并不是指農民一家一戶的自給自足(在我國小農經濟中,那幾種是不可能的),它實際是指社會是由許多的“單一的經濟單位”所組成,而全部或大部分再生產條件,都能在本單位中得到補償。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在古代是指氏族、村社、奴隸主莊園,在中世紀的歐洲是指一個個的封建領地;在我國的地主制經濟中,則應是相當于過去采中邑的鄉里或區縣,并且是包括地主和農民兩上方面,不是單指農戶。[6]①
不過,區域市場范圍內的流通,究竟已不限于單一的經濟單位,而至少是各單位間的商品交換,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了。尤其是一個區域總包括一定的城鎮,區域市場內的城鄉交換,反映一定的工農業產品的交換,這是應予充分注意的。這里,重農學派的“工農業產品的交換形式市場”這一古老概念,對我們研究的目的來說頗有用處。因為這和交換代表真正的社會分工,也是自然經濟瓦解的前兆;并且,市場的由小而大,也常是工業品(這時是手工業品)參加交換的結果[7]①。我國城市手工業者由承接顧客來活的手藝人向小商品生產者的轉化,是在明代才顯著。區域市場的重要性,也自此始。但總的說,我國區域市場內的工農來產品交換并不多,因為農家庭手工業比較發達,而城市手工業又主要是供應城市消費。這種情況,直到清代前期,沒有根本變化。
另一方面還應看到,一個區域市場的自給自足,在某種勢力下,也會成為封建割據的依據,以致關卡封鎖,阻礙流通。邊遠省區尤多這種情況。
第四,突破區域范圍的大市場,亦可稱為全國性市場。這種市場,和形成這種市場的長距離販運貿易,才是促進資本和資本主義產生的最重要的歷史前提。海外貿易,也是一種大市場,歐洲資本主義的萌芽,首先是在海外貿易的基地出現的。但我國從來不是一個海上國家,明清兩代又受禁海政策的,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依靠國內市場。我們的考察,一般也限于國內市場。
我國長距離的販運貿易很早就有發展。但在宋代以前,除了官營和專賣品外,發展最盛的是那種“奇怪時來,珍異物聚”[8]②的奢侈品貿易,其次是由“任土作貢”遺留下來的土特產品的貿易。這兩種貿易經營的都是已生產出來的(不是為市場而生產)的東西,其消售對象又限于貴族、官紳小范圍,不是生產者之間的交換。所以盡管琳瑯滿目,對生產關系的改變,卻極少作用。大約從明中葉起,我國的販運貿易才逐漸以民生用品為主了。
我國又很早就有鹽、鐵以及漁、獵產品的貿易,其中也大部分是長距離販運的。這種貿易,除有些是受官府控制外,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從生產上看,鹽民、爐戶、漁民、獵戶等都可說是小商品生產者。但是他們這種地位純粹是由自然條件決定的,所謂“只緣海角不生物,無可奈何來收鹵[9]①。他們是由于鹽、鐵等不能當飯吃才進入交換的,為買而賣,目的在取得口糧。因此,我寧愿稱他們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經濟,而不是真正的商品生產者。事實上,自有自然經濟,就必須有鹽、鐵等貿易作補充,否則也談不上自給自足。[10]②這種貿易,乃是自然經濟題中應有之義;除非它們生產方式改變,對我們研究的目的來說并不起多大作用。
鹽鐵以外的民生用品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發展,主要是從明代開始的。這就使得我國國內市場,在市場結構和交換性質上,發生一種定向性變化,這種變化一直延續到清代前期。本文的目的即在考察這種變化,同時也要說明其變化的局限性和狹隘性。
市場,從來就有個量的內容。但是在明代史料中,還很難進行定量的。本文只能從商貨路線的增辟、新商業城鎮的興起、主要商品的運銷和商人資本的積累這幾個方面,來考察市場的發展和變化。也盡可能提出一些量的概念,而撇開那些“舟車鱗次”“店肆櫛比”等無具體內容的。以后關于清代市場的考察中(它將成為本文的續篇),我希望盡可能作一些計量分析,并試圖探索鴉片戰爭前我國國內市場的結構。
對于市場和商品流通的上述觀點,只是個人在中不成熟的看法,謹先縷出,以求教于賢明。
二 商路的增辟和新興商業城鎮
二十世紀鐵路修筑以前,國內商運主要是靠江河和沿海水運。長江歷來是我國最重要的一條商品流通渠道。宋代的長江貿易主要是集中在下游。明初也還是這樣。宣德間,明廷設三十三個征收商品注通稅的鈔關,其中十五個在長江沿線,即上游的成都、瀘州、重慶;中游的荊州、武昌;而有十個集中在下游,即揚州,鎮江、儀征、江寧、常州、蘇州、嘉興、杭州、湖州、松江,并限于江、浙兩省。但在正德以后,鈔關劇增,蕪湖、寧波成為新興商業城市,就是說,這個最繁盛的貿易區向東南兩方面延伸了。長江中游的荊州、武昌,本來都是軍政重鎮,武昌雖已“四方之賈云集”[11]①,但比清代的漢口鎮還相差遠甚。不過一明后期,沙市、九江成為新興商業城市,這樣就與長江下游珠連起來了。這是一個重要。至于上游的成都、瀘州、重慶三鈔關,主要還是處理本區域貿易,這時無糧食出川,與下游主要是絲、茶等細貨貿易,貿易量有限。
總之,明后期長江貿易有了發展,不過主要還是在下游和中游,這主要是由于江、浙兩省桑、棉和手的發展所致。這時兩湖丘陵地帶和川、滇尚未大力開發。據我看,明代國內市場的開辟恐怕更重要的是南北貿易方面,尤其是大運河的暢通,以及沿贛江南下過庚嶺到兩廣一路的開通。
大運河自元代開會通河后,補救了黃河改道的困難。但元代漕糧仍以海運為主。明永樂九年(1411)重開會通河,運河才暢行無阻。運河原為漕運(不屬商品流通),但官船都帶私貨,而商船亦可包攬一位官員剩坐,即可沿途免稅,所謂“官家貨少私貨多,南來載谷北載鹽,憑官附勢如火熱,邏人津吏不敢詰。”[12]②所以實際是一條重要商路。
大運河自北京(通州)至杭州全長一千余公里,河漕(利用黃河一段)以下,航運尤繁,并由河漕東走濟南,西走開封。明初人孫作說:“自杭走汴,水陸二千里,如游鄉井,如入堂奧,如息臥內。”[13]①宣德間,沿北河在北京、德州、臨清、濟寧和濟南、革封設六個鈔關。其中臨清是元代興起的商業城市,濟寧又是明代官商會聚之地。中葉以后,北部的天津、南部的淮安,又都是新興商業城市。又有通州和天津之間的河西務,臨清和濟寧之間的張秋鎮,成為新興商埠。再如北直隸的中定、清苑、河間、景州,雖不是臨河,但也因漕運關系,“商賈肩相摩”[14]②。又如山東的清源,原屬荒村,正統間因戰事筑成,但隨著淮北水運的發展,到嘉靖時就又筑新城,成為“商旅往來,日夜無休”[15]③的商業城市了。
明初,贛江水運已頗盛,設有南昌、清江、臨江、吉安四個鈔關。其后,九江設關;饒州、景德鎮商旅日繁;而鉛山縣的河口,由二、三戶人家“而百而十”,到嘉、萬時已“舟車四出,貨鏹所興”,成為“鉛山之重鎮”[16]④。贛江貿易的發展,又是和大庚嶺山路的開修分不開的。這樣一來,贛州成為一大商業城市,庚嶺路上,“商賈如云,貨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17]⑤,和蘇軾過庚嶺時“一夜東風吹石裂”“細雨梅花正斷魂”的景象不大不相同了。
明人李鼎說:“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南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18]①南北貨運的流暢,大約是明代市場擴大的一個特征。下面在敘述商品運銷中,還可見到。不過,明代運河貿易的發展,多半還是因為中心在北方,以及北邊多事、行開中制等原因;南貨北運者多,北方出產有限,故漕船常回空。因而,這種市場的擴大,并不完全反映地區分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
以上是長距離販運的主要商路。此外,如北邊宣化,主要是兩淮、長蘆鹽運集中地;湖北襄陽,主要是西南木材集中地;各有局限性。西北太原、平陽、蒲州,早設鈔關,但主要是處理本區域貿易。后期發展起來的西安,則“西入隴蜀,東走齊魯”[19]②,使西北商路稍暢。更遠的到遼東一路,商貨多由山東臨清轉運,限于細貨,為量有限,而海路在明代反衰落。近人常引宋應星“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游薊北”,那顯然是夸張了[20]③。
縣以下商業鎮市的興起,卻是值得注意。因為這些鎮市,除上述河西務、張秋、河口等外,都是在作物和的手工業品商區,貨量不太多,但都遠銷,實際是長距離販運貿易的起點。不過,大都是集中在江、浙一隅之地,如蘇州的楓橋,湖州的菱手工業鎮市。如蘇州的盛澤鎮,明初是五、六十家的村,嘉靖時成為百多家的市,居民“以綾紬為業”[21]④;震澤鎮,元時僅數十家,嘉靖時已七、八百家,“競逐綾紬之利”[22]⑤。嘉興的濮院鎮,萬歷時“日出錦百匹”,“人可萬家”[23]⑥。這些鎮上的居民已由農業分離出來,或者雖未分離但也是為市場而生產了,這些地方就成為商品生產的基地,商賈云集。嘉興的王江涇鎮,“多織綢收絲縞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務耕績多”[24]①。七千多家,多數不耕地、不績麻,不從事自給性的生產了。因而“國方商賈俱至此收貨”,“做買做賣的挨擠不開”[25]②。
最后,結合海外貿易,看一下福建、廣東的海運。
我國海外貿易在宋代有較大發展,通商五十余國,進出口商品數百種。明代絲織、瓷器、棉布、漆器、糖等出口品的生產都有發展,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宋代基礎上也有改進[26]③,正是發展海外貿易的良了時機。但是,明開國之初,即嚴海禁,“敢有私下諸蕃互市者,必寘之重法”[27]④。雖設廣州、寧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實行所謂朝貢貿易,對外使橫加限制,兩三年甚至八年十年始準來華一次。永樂后,馳禁之儀屢起,但總是以禁為主。到隆慶初(1567),始“除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這種政策不能阻止經濟發展的要求,私人海上貿易并未斷絕,但未能得到應有的發展則是肯定的的。
明代的海外市場主要是南洋,次為日本。南洋有二商路,稱大西洋和東洋。大西洋以越南(安南)、柬埔寨(占城)、暹羅為主,進口主要是蘇木、胡菽、犀角、象牙等天然產物,而出口則以工藝品為主,以及銅、汞等礦產品,這又是貿易上的一個有利條件。東洋指呂宋(佛郎機),進口品種有限,多是以銀換取中國物產。外貿利潤很厚,“湖絲百觔,價值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28]①。輸往日本者,更多系日用工藝品,絲綢、瓷器之外,棉布、布席、扇、脂粉等都能暢銷。明庭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因而在貿易上“東之利倍蓰于西”[29]②。
明代的海外貿易,由于正德至嘉靖間一度嚴格海禁,到萬歷以后才有較大增進。這對廣東、福建兩地經濟頗有。明代經濟作物最發達的地區是福建,又接近江、浙手工業產區,外貿中心也由南宋時的廣州移到福建來了。萬歷時,有人說:“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延之鐵,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30]③話雖如此,福建的商品性生產,究竟運銷海外的只是一小部人,大部分是運銷售內陸以換取糧食。福建的關稅收入萬歷初年只有二萬兩,崇禎最高時也不過五、六萬兩[31]④,而南宋紹興時廣州市舶司的稅收曾年達110萬貫。明代的海外市場,恐怕是比宋代縮小了。
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大量借助于海外市場,在地中海沿岸和北歐低地,尤其是這樣。當時我國開辟海外市場的能力,從出口商品看,從航海技術看,從鄭和七下西洋的路線看,都是很大的。而明(以及清)王朝的禁海政策,起了很大的阻塞作用。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只能依靠國內市場。
三 主要商品的長距離運銷
市場擴大,只是商品流通的一個側面,它的性質和作用,還要看進入流通的是什么商品,以及其交換的對象。明代長距離的商品運銷,就我所見,重要的有:(一)糧食;(二)棉花和棉布;(三)絲和絲織品。鹽和茶也是長距離運銷的重要商品,但都屬專賣性質,我把它們放在下節論商人資本中去考察。
(一) 糧食的運銷
糧食是封建最重要的商品,不公因為它流通量大,而且糧食商品率(指對產量而言)的大小,是測量結構演變的最重要的指標。
如前所說,在考慮糧食的商品流通時,首先要排除田賦、加派等非商品部分。這以外,在封建社會,糧食的交易就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場上的品種調劑和在區域市場內供城鎮人口的需要。前者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實際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供城鎮人口需要的,也主要是來自附近的。糧食體大價低,原是不適于遠銷的。以明代而論,大約每年的漕糧和開中納粟,已可供洋畿官吏、工役和北邊駐軍所需,此外并不需要南糧北調。有些地方,如河間府,需糧食調劑:“販粟者至自衛輝、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帶,間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皆輦致之。”[32]①這種有來有去的情況大約相當普遍,并且多半還是區域內的運銷。較長距離的運銷,主要是供應東南經濟作物地區的農民和手者的口糧,也只有這種交換,最能反映地區分工的社會分工。這在明前期,尚未見記載,估計主要是明中葉以后起來的。
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地區,常患糧食不足。不過,這個地區本來是魚米之鄉,有糧外運,宋人所謂“蘇常熟,天下足”[33]②。到明后期,常州米仍然外調浙江[34]③,湖州米接濟杭州[35]④,常山米取給于附近的玉山、西安[36]①,寧波米取給于鄰府臺州[37]②,就是說,區域內的調劑甚繁。但整個區域仍有未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于江、楚、廬、安之粟”[38]③。說“半仰食”可能夸大了,我們沒有可靠材料,估計每年運入幾百萬石也就夠了。
福建是經濟作物發展最早的地區,這時煙草尚少,但甘蔗已普遍,又有茶、麻、苧、蠟、藍靛、果木等。手工業也發達,前引《閩部疏》已見。和江蘇、浙江不同,福建地多山陵,糧食本非豐腴,這樣一來,必難自給。其中溫州米運福州[39]④,尚屬近距離調劑,甘蔗產地泉州,則需“仰粟于外,上吳越而下東廣”[40]⑤。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米海運入閩,據說“往者海道通行虎門無阻,閩中白艚、黑艚盜載谷米者歲以千余艘計”[41]⑥,這就怕有上百萬石了。況且,廣東食米原是靠廣西接濟[42]⑦,而“盜載”(因朝廷禁海運)如此之巨,可見福建米缺。而自江、浙輸閩之米,恐怕又多于廣東。福建省大約可以說是當時自然經濟受到破壞最多的省份,但也是全國發生這種情況的唯一省份。
安徽南部的徽州一帶,是個茶、木材和紙、墨產區,其土地貧瘠,糧食不足。這個地區雖小,購買力則較高(大約經商之故),糧食運至頗遠,在明后期,“大半取給于江西、湖廣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賈從數千里轉輸。”[43]⑧
以上是糧食輸入的主要地區。
糧食輸出的地區就我所見資料,只有兩個。一是江西南部。“贛〔州〕亡他產,頗饒稻谷,自豫章、吳會咸取給焉。兩關轉谷之舟,日絡繹不絕,即儉歲亦櫓聲相聞。[44]①”另一個是安微江北一帶。“六皖皆產谷,而桐〔城〕之輻輿更廣,所出更饒。計繇(由)樅(川)陽口達于江者,桐者十之九,懷〔寧〕居十之六,潛〔山〕居十之三”[45]②。這兩個地區都米谷豐饒。到近代還是這樣。不過供應江、浙需要,恐怕還未足(贛米還要供應本省南昌)。長江中游一帶即湖廣的米,在明后期大約已有東運,唯史料未詳,或者數量還有限。
總看上述,明代商品食的運銷,主要還是在長江下游,即九江以下的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五省,其中又很多是本區域內部調劑。象清代的湘米大量東運、川米出川、東三省豆麥南下等大規模運銷,明代尚未出現。在明后期,較長距離的糧食運銷,包括廣東米北上,恐怕不超過一千萬石。按嘉靖間米價每石零點八五兩計,約值銀八百五十萬兩。[46]③
糧食是農民個體生產的。進入長距離運銷的糧食,部分是小生產者的余糧,大部分是來自地主的租谷。無論何者,都不是商品生產,而是由于商人資本的運動而使已生產出來的產品變成商品。所以,糧食販運,是當時最大量的商品流通,但也是最典型的封建商業,在當時條件下,無助于改變生產關系。但是,糧食的長距離販運主要是輸往東南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產區,它反映了后者的發展,并對這種發展起著保證作用。
(二) 棉花和棉布的運銷
棉花的種植是在明代推廣的,而這時農民織布還不普遍,主要集中在江蘇南部一帶,因而棉花和棉布都有較繁的長距離運銷。徐光啟說:“今北方之吉貝(木棉)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泛舟鬻諸南,布則泛舟而鬻諸北。[47]①”這是總的流向。
當時北棉南運,主要是河南、山東的棉花。萬歷間鐘化民說。“臣見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盡歸商販,民間衣服率從貿易”[48]②。又有記載說南陽李義卿“家有地千畝,多種棉花,收后載往湖、湘間貨之”[49]③。這是河南棉花。山東植棉,“六府皆有,東昌尤多,商人貿于四方,其利甚溥。”[50]④東昌府的棉花以高唐、恩縣、夏津為集中地,“江淮賈客,列肆齍收”[51]⑤。兗州府也多棉,“商賈轉鬻江南”[52]⑥;而鄆城是另一集中地,“賈人轉鬻于江南,為市肆居焉。”[53]⑦
江蘇省太倉州所產棉花,也向南販[54]⑧,而嘉定的新涇鎮,遂為棉花交易市場,“每歲棉花入市,牙行多聚”[55]⑨。不過,太倉州的棉花不少是運銷福建。福建在宋代是最早的值棉區,到明代則甚少栽培了。“隆萬中,閩商大至〔太倉〕州”購棉,吳梅村曾詠其盛況[56]⑩。
江西棉花,生產未詳,但有棉經大庚嶺運銷廣東。廣東惠州,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57]⑾。明代湖廣的江花,產量亦豐,但少見外銷記載[58]⑿,可能有運往廣東者[59]⒀。
明代棉紡織業,集中在松江、嘉定、常熟三地,有松江布、嘉定布、常熟布之稱,而以松江產量最大。但松江府原系產棉區,從后來產布最盛時情況看,其所需棉花可以自足,并有余花供毗鄰的浙江嘉興、嘉善一帶織戶。由北方南運的棉花,大約主要供應濱海各縣,那里農民也多織布 。嘉定位于太倉州產棉區,棉花亦可自足。常熟缺棉,大約須由北棉接濟。
松江布的運銷,葉夢珠《閱世篇》所記最詳。他是記清初上海縣(屬松江府),但兼及明代;“棉花布,吾邑所產,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飛花、尤墩、眉織不與焉。上闊尖得曰標布,……俱走秦晉、就是邊諸路。每匹約值銀一錢五、六分,最精不過一錢七、八分至二錢為止。……其較標布稍狹而長者曰機,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價與標布等。前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貲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中機客少,資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無幾。至本朝,而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全,少年或二、三千斤,利亦微矣。而機之行轉盛,……更有最狹短者曰小布,……單行于江西之饒州等處,……又憶,前朝更有一種如標布色稀松而軟者,俗名漿紗布,……今亦不復見矣。”[60]①
棉布是農民家庭分散生產的。由于商人收購,有了一定規格,又因銷地不同,織成不同品種,說明松江的織戶已多半是為市場而產生了如尤墩布 ,“輕薄細白”,用以制暑襪,屬專用布。又有高級布,如三紗布、番布、兼絲布、藥斑布等,多銷京師,皇室、貴族所用[61]②,俱為量不大。明代松江主要商品布是標布,這是一種比較厚實、幅面較闊的布[62]③,銷往西北和華北。清人褚華也說,松江“標布,關陜及山右諸省設局于邑收之”[63] ②,他的六世祖在明代即做棉布生意,“秦晉布商皆主于家”。浙北嘉興,嘉善一帶與松江相連,所產可能也是標布一類,有“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之諺[64]②。
嘉定布,“商賈販鬻,近自抗、歙、清、濟,遠至薊、遼、山、陜”[65]③。常熟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輸行賈于齊、魯之境者常什六”[66]④。這兩種布規格未祥,主要也是北銷。
大約明代南方用麻布還相當普遍。麻主要產在南方,麻布也北運。棉布興起,御寒較勝,首先在北方代替麻布。不過,福建、廣東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棉布也已盛行。福建“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吳越重”[67]⑤。但福建所產青麻布,“商賈轉販他方亦廣”[68]⑥。福建惠安的北鎮還有一種精制的布很有名氣,“北鎮之布行天下”[69]⑦。廣東,“冬布多至自吳楚,松江之稜布、咸寧(在湖北)之大布,估人絡繹而來”。但廣東所產“蕉布與黃麻布,為嶺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70]⑧。
其他地區,也有布販售。乃至甘肅的“洮蘭之間小民,制造貨販以糊口”[71]⑨。不過恐怕都行銷不遠,不贅述。
明代棉花、棉布的運銷頗為活躍。但這并不說明已經有了高度社會分工或紡織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72]⑩,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棉紡織業生產力落后所致。我國漢族的棉紡織業本來發展較遲,又都是農民家庭副業,其推廣落后于棉花的種植,所以要運棉就織[73]①。“北土廣樹藝而昧于織,南土精織紝而寡于藝,故棉則方舟而鬻于南,布則方舟而鬻諸北。”[74]②明末徐光啟看到河北肅寧的織布業興起[75]③,即預見到松江布北運將衰。果然,入清以后,如前引葉夢珠所說,在松江就“標客巨商罕至”,棉花南運自然也減少,甚至“東北絕無至者”。但松江的織布業并未衰落,因改向中南和東北銷售,反達最盛。
還應看到,我國手工布的生產,從來不是家家紡織的,據考察農村織布戶最多時(十九世紀中葉)也不超過全國農戶的一半,因而,他們生產的布總要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拿出來賣給非織布戶,以換取口糧。這種糧布調劑,正是我國小農經濟耕織結合的一種形態。這里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商品率”是一種虛假現象。因此,我總是把重點放在長距離運銷上,這種地區間的運銷才代表真正的商品流通[76]④。在它的集中產區,即松江一帶的織戶,才大體可以說是小商品生產者。松江府的棉布上市量,在清代盛時年不超過三千萬匹[77]⑤,以此估計明代約不超過二千萬匹,按每匹一錢六、七分計,約值銀三百三十萬兩。
注釋:
[1]① 《資本論》第三者卷,第167頁。
① 十一世紀以后西歐集市的興盛,主要是為了逃避城市行會的限制;集市是大商人集中進行批發的、集中的貿易的地方,大集市都是國際貿易中心。
[2]② 王建:《汴洛紀事》:“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
[3]③ 西歐大陸的羅馬城市,大部分在日耳曼人南下時荒廢。封建城市,主要是十一世紀以后,由手工藝人和從莊園中逃亡的農奴和商人恢復蔌新建的。手者和商人是城市的主要居民,因而其市場上的流通主要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另有些城市是海外貿易的基地。在西歐,十六世紀初才有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出現;我國則在唐代即有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十余座,北宋時有四十余座。
[4]① “在亞洲各中,君主是國內剩余產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圖亞特的用語)相交換,結果出現了一批城市”。在亞洲:“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及其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產品)同勞動相交換,把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馬克思:《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466、474頁。)
[5]② “商人資本的相對量……是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但在這里,零售商人的資本作為一種雜種,是一個例外)”:不過,“隨著商人資本越來越容易擠進零售商業,……不執行職能或半執行職能的商人資本會增加。”(《資本論》第3卷,第320、347頁)。
[6]① “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產生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此外,它還要以家庭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前提。”(《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在自然經濟下,社會是由許多單一的經濟單位(宗法式的農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領地)組成的,每個這樣的單位從事各種經濟工作……。”(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列寧全集》第3卷,第17頁。)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于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換。”(毛澤東:《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587頁。)
[7]① 農產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市場范圍宜小不宜大,因運輸里程增加一倍,常會使運費增加二倍。若是工業品參加交換,情況就不同了。因工業品運輸費用所占比重不大,并且大量生產會降低成本,這就會引起市場的延伸。
[8]② 《管子·小匡》。中世紀歐洲的長距離販運貿易也主要是奢侈品貿易,但其主要奢侈品香料、絲綢等是來自東方,屬于東西方貿易,正是這種貿易,促進了意大利、佛蘭德等地城市的紡織、玻璃、五金工業和礦業的發展,最早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9]① 林正清:《小海鹽場新志》。
[10]② 歐洲的領主制經濟,也需要這種貿易作補充。不過,歐洲的莊園有較多的公用林區、牧地、漁場和狩獵場,有的領主還規定所屬農民繳納一定的鹽和鐵。
[11]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12]② 李東陽:《懷麓堂文后續編》卷一,馬船行。所說是江浙馬船,據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三,運河情況亦然。
[13]① 孫作:《滄螺集》卷二,鄭淮南省椽梅擇之序。
[14]② 查志隆:《金臺郡城西北二橋記事》,載民國《清苑縣志》卷五。
[15]③ 周思兼:《周叔認錯先生集》卷五,二城記。
[16]④ 費元祿:《量采館清課》卷上。
[17]⑤ 桑悅:《重修嶺路記》,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
[18]① 李鼎:《李長卿集》卷十九,借箸編。
[19]②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20]③ 宋應星:《天工開物》序。此語下文:“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其實是說信息傳播,不是指。
[21]④ 嘉靖《吳江縣志》。
[22]⑤ 乾隆《震澤縣志》卷四,疆土;卷二五,生業。
[23]⑥ 楊樹本;《濮川所聞記》卷四。
[24]① 萬能膠歷《秀水縣志》卷一,市鎮。
[25]② 《石點頭》卷四。
[26]③ 明代出海以廣船、福船、消船、沙船為主。廣船、福船是尖底船,能用多段龍骨,創于宋代。沙船是平底船,用平板龍骨,靠兩舷大擸(木字邊)加固,寬敝,干舷低,穩性好,比較安全。沙船之名,明代始見,日本稱南京,當是明造。但宋代即有防沙平底船。元明代的改進,大約在于用披水板(橇頭)和升降舵,使船能逆風行駛。又這種船,元代載重達八、九千石,鑫桅多帆。明代一般載二、三千石;并由多帆改為二、三帆,帆下寬,以隆低風壓中心;這都增加了穩性和靈活性。鄭和下西洋大約即用沙船,其大者稱寶船,長150米,張12帆。在船海技術上,明代改進牽星術,除北極星外,并觀測方位星。又廣用羅盤,創更香計時,制成方向與時間結合的針路圖。
[27]④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一。
[28]① 傅元初:《清開洋禁疏》: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冊。
[29]② 王勝時:《漫游記略》卷一,閩游。
[30]③ 王世懋:《閩部疏》。
[31]④ 傅元初:《清開洋禁疏》: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冊。
[32]① 萬歷《河間府志》卷四,風土志。
[33]② 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常州奔牛閘記。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乙集、吳泳《鶴林集》卷三十九均作“蘇湖熟,天下足”。
[34]③ 常熟“每歲杭、越、徽、衢之賈皆問糴于邑。”嘉靖《常熟縣志》卷四,食貨志。
[35]④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州]……,人無擔石之儲”。《肇域志》第九冊,浙江。
[36]①常山“米谷豆面之類,茍菲玉山、西安通權,則終歲饑饉者十家而七矣。”王士性:《廣志繹》卷四.
[37]② 寧波食米“常取足于臺[州]”。王士性:《廣志繹》卷四。
[38]③ 吳應箕:《樓山堂集》卷十。
[39]④ 福州食米“常取給于溫[州]”。王士性:《廣志繹》卷四。
[40]⑤ 何喬遠:《閩書》卷三十八,風俗志。
[41]⑥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四,食語,谷。
[42]⑦ 王士性:《廣志繹》卷五。
[43]⑧ 吳應箕:《樓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平物價議。
[44]① 天啟《贛州府志》卷三,與地志三。
[45]② 《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十八,稻部,引明方都韓:《樅川榷稻議》。
[46]③ 據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皇明經世文編》卷二六一、三一二,《云間雜志》卷中,鄭曉《鄭端簡公奏議》卷六,采九德《倭變事略》卷二零,所記嘉靖二年至四十五年米價平均,為每石零點八五兩。
[47]① 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十五,木棉。
[48]② 《救荒圖說》,載《荒政叢書》卷五,鐘中惠公賑豫記。
[49]③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十七。
[50]④ 萬歷《山東通志》卷八。
[51]⑤ 《肇域志》第三十二冊,山東。
[52]⑥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十三,兗州府部,風俗考。
[53]⑦ 萬歷《兗州府志》卷四。
[54]⑧ “九月中,南方販客至,城中男子多軋花生業”。崇禎《太倉州志》卷五。
[55]⑨ 萬歷《嘉定縣志》卷一,市鎮。
[56]⑩ “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韈鳥言賈,腰下千金過百灘。”《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
[57]⑾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一三○,惠州府部,物產考。
[58]⑿ 《花村談往》卷二記有正德間“荊湖川蜀遠下客商所帶板枝花俱結算在主”一例,板枝藥是絮棉,主指京口牙行主人。
[59]⒀ 廣東“冬布鞋多至自吳楚,……與棉花皆為正貨。粵地所產吉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葛布。
[60]① 葉夢珠:《閱民編》卷五,食貨五。
[61]② 見正德《松江府志》卷五,正德《大明會典》卷三十二,戶部十七。
[62]③ 近代松江布分為標布(東套)、清水、銷北方;東稀,銷兩廣、南洋;北套、扣套,銷南北二路。
[63]① 褚華:《木棉譜》。
[64]②雍正《浙江通志》引萬歷《嘉善縣志》。
[65]③ 萬歷《嘉定縣志》卷六,田賦考,物產。
[66]④ 嘉靖《常熟縣志》卷四,食貨志。
[67]⑤ 王院:《漫游記略》卷一,閩游。
[68]⑥ 弘治:《興化府志》卷十二,貨殖志。
[69]⑦ 何喬遠:《閩書》卷三十八,風俗志。
[70]⑧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葛布。
[71]⑨ 明《神宗實錄》卷三○九。
[72]⑩ 只有福建的以精制的北鎮布換江、浙江,廣東的以蕉布換冬布,才是真正的地區分工。
[73]① 褚華:《木棉譜》說:北方“風日高燥,棉納斷續,不得成縷”,要在地窖中“借濕氣紡之,始得南中什之一二”。乃至乾降《樂亭縣志》卷五還有“女紡于家,男織于穴” 的記載。其實,這只是技術未熟練而已。后來事實證明,北方產棉區農戶大都自已織布,而樂亭還是個小的棉布集中產地。
[74]② 王象晉:《木棉譜》,載《元明事類鈔》卷二十四。
[75]③ “肅寧一邑所出布匹,足當吾松十分之一。初優莽莽,今之細密幾與吾松之中品埒矣。”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十五,木棉。
[76]④ 這里還沒考慮官布。明代除宮庭用布和賞賚用布外,最大量為軍服用布,明初年平均在一百萬匹左右,又西北易馬的布每次十萬匹左右。但官布并非都出自官課,尤其明后期,主要還是商人所販。開中制的“納布中鹽”也是這樣,所謂“秦晉大賈”其實很大部分是販運官用布匹的。我這里都視同商品布了。
[77]⑤ 見本書《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