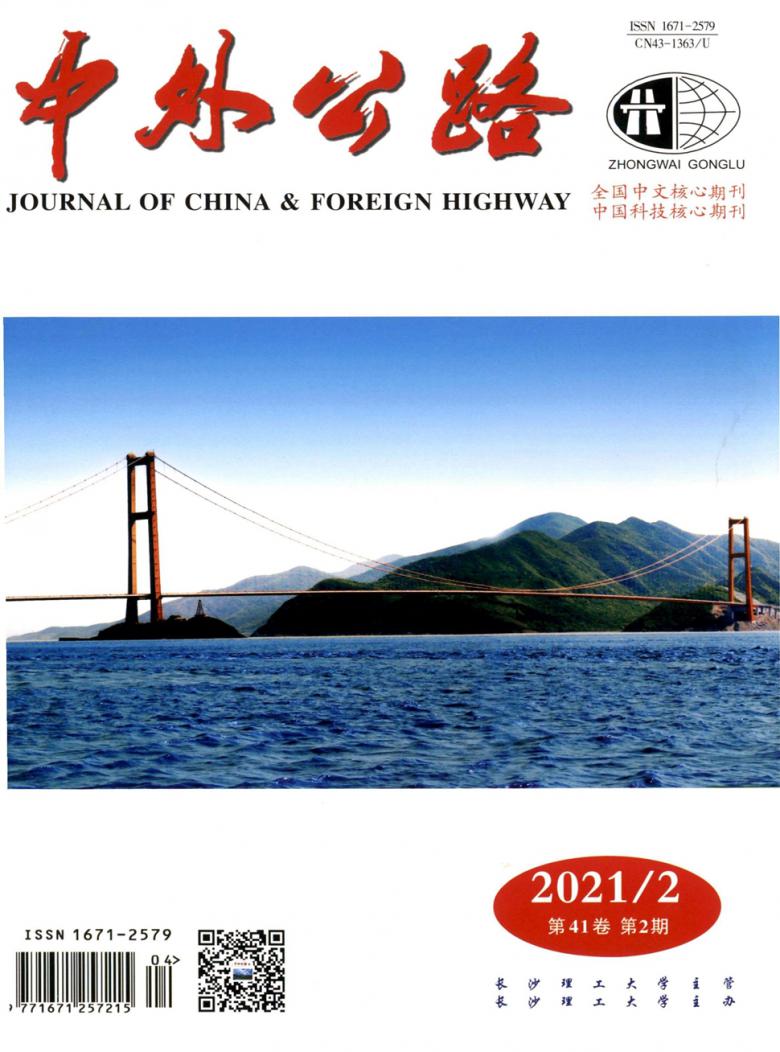明代大都督府略論
李新峰
大都督府,創始于朱元璋所部成為相對獨立政權的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消亡于極端君主專制體制奠定的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存在僅二十年。古今論者若談及制度變遷,多以之為五軍都督府體制的萌芽形態或初級階段,而論及其變遷在政治史中地位,又往往以為其初乃元末江南紅軍粗率體制之一環,明朝建立后亦不過專制制度完善前之權益設置。故《會典》、《明史》記載有關職官、軍事制度,均以明中、后期的情況為準,詳細介紹五軍都督府-兵部體制,而對體制的形成過程語焉不詳。其中對大都督府在二十年間的興衰分合、作用地位等,不過沿襲明中后期學人泛泛之論,而遂長期為論明代制度者繼承。此類結論不但失之簡略,而且往往流于表面認識或想當然,實不足據以了解制度變遷的實情,更無從探究隱藏于制度變遷背后的權利分配變化實質。當代學者雖不乏爬梳《實錄》資料對大都督府的演變進行較深入解釋者,但尚無人專以大都督府的變遷為中心展開論述。本文目的,即剖析大都督府變遷中的三個關鍵環節“改”、“權重”、“分”,揭示其變遷的政治、時代背景。
“改”
關于大都督府的創設,詳細如《實錄》也不過是:至正二十一年三月,“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1 所以《會典》、《明史》有關記載均含糊記為“改”字了事。南炳文根據《實錄》前后記載,證明所謂原“樞密院”是“行樞密院”訛稱,誠為確論;又推測,朱元璋不滿龍鳳羈絆而欲自建王業,所以不再使用帶有地方機構含義的行樞密院名義,而避免過分刺激龍鳳政權故沒有徑稱樞密院,而是采取了改稱大都督府這種麻痹視聽的巧妙手段 2。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分析,“改”字的背景、意義尚不止此。
關于朱元璋的“不滿”,一般以劉基大罵韓林兒、感悟朱元璋的傳說為依托。《明通鑒》將其發生歸于本年正月 3,而錢謙益指出當時劉基“不應孟浪若此”4。故將改名原因歸為朱元璋“不滿”,尚顯勉強。
至正二十一年(1361)初,朱元璋被龍鳳政權授吳國公 5,隨即對所部體制進行重大改革,行樞密院改大都督府就是這次大改制中的關鍵環節。《實錄》為避諱此事不惜把吳國公之事提前到五年前,編造眾將擁戴的謊言。所以對改制具體環節、背景的記載極端混亂,幾乎湮沒了這次重大事件。
此前,朱元璋以江南行中書省平章乃至丞相的身份總攬軍民事務,即行中書省是以朱元璋為首的最高機構,其下稍低的行樞密院則是各將領任官之所。現在朱元璋是高踞行中書省之上的吳國公,隱然一國之長,遂模仿元代中央體制,來設立具有獨立性質的機構體系。元代中央與行省的機構設置、權力分配大體相似,但中央有皇帝總攬全局,控制中書省和樞密院,地方卻僅以行省平章或丞相等為首,節制行樞密院。朱元璋從行省首腦(平章乃至丞相)升為相對獨立政權的首領,改變機構設置以適應形勢,在龍鳳政權內部當具合法性,而非“不滿”的體現。只有從此角度,才能認識這次改制的背景。
單從名義上看,行樞密院的“行”并不見得為朱元璋不能忍受,因為同時行中書省的“行”字此后還一直沿用了數年。都督府在元代有其淵源:權相燕鐵木兒曾設之,用以統領各衛軍 6。參與定制的劉基、宋濂等人必然通曉這一點,故而“改”不妨看作朱元璋地位上升、成為龍鳳“權臣”的標志。但名義的措辭尚僅僅是表面文章,從原行樞密院和大都督府的下屬機構、權力運作、任官情況等方面的差異,可以看到改名的目的是:調整權力分配體制。
此前,朱元璋所部的“中央”機構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中書省的正官一般僅朱元璋一人,各武將皆任官于樞密院;地方則在原元各路府設立統軍元帥府和府,分統軍民事務,后于其上設分樞密院,統攬一府軍民事務。這樣形成了行樞密院-分樞密院-府(管民之府和元帥府)的上下統屬體制。與元朝由行省下統路府州縣和各軍府的體制不同,朱元璋所部各地的上屬機構是行樞密院而非行省。當時朱軍每占一大城市,即需以高級武將鎮守,而武將們皆由總管、元帥升任行樞密院的院判、僉院、同知等,自然形成以各級武將官位構成的中央-地方鎮守體系。而行中書省雖我中樞指揮機構,與行樞密院的主次高低關系并未破壞,但與各地無明確統轄關系。
改制首先就在地方統屬體制層面開始:二月“改分樞密院為中書分省。”7 分省顯然有“行”行中書省之意,元朝于至正十八年(1358)在福建行省下開設分省 8,當為剛剛占領浙南的朱元璋部所仿用。分樞密院本來是統攬地方軍民事務的機構,改為中書分省,比照了元代地方體制中以行中書省為地方最高機構、軍政合一的制度 9。五月,“胡大海為中書分省參知政事,鎮金華,總制諸郡兵馬。都事王愷為左右司郎中,掾史史炳為照磨。”10 胡大海本來是分樞密院官,現改任中書分省;王愷本是行中書省都事 11,現改任中書分省郎中。這樣還從制度上解決了各地文官與武將統屬關系的問題。從此,各地的軍民府由屬行樞密院-分樞密院系統改屬行中書省-中書分省系統,行樞密院即后來的大都督府成為純粹的“中央”機構。這是行樞密院改大都督府的第一個實質性變化。
原行樞密院雖然名義上是各級武將的任官之所,但并無任何處理軍務的權力。據《實錄》記載,常州、鎮江、金華、揚州、太平、諸全甚至連婺源州都設樞密分院,但是以行樞密院官鄧愈鎮守的重鎮徽州則未見設。時居徽州(興安)的唐桂芳記:“明年,開行省……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12 《實錄》載鄧愈由院判升遷直至僉院的過程中,一直作“行樞密院”官而非“樞密分院”官。可見,行樞密院至正十七年(1357年)確隨鄧愈“遷置”,所以才不用在徽州設立樞密分院。鄧愈“丁酉年(按:1357年)十月領兵至郡,往來江浙,以徽為駐軍之所。”13 又并不強調行樞密院的地位,史料中也從未有樞密院下屬文職機構和首領官的職名出現。上述情況說明,行樞密院只是名義上的最高統軍機構,各級官職用來排定諸武將級別而已,其能隨不很重要的將領鄧愈“遷置”,就絕非擁有處理軍務權力的最高統軍機構。
處理軍務的機構是行中書省。有關陶安的一份書札說:“江南等處行中書省。龍鳳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參議府、左右司等官奉鈞旨:仰本省首領官、掾史分派房分,掌管事務……兵房……事件:守御各翼,關防盤詰,調遣征進,各項功賞,招諭榜文,申報公務,守御門禁,軍前報捷,勾取官軍,設置急遞鋪。”14 龍鳳四年即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月底正是朱元璋“親征”婺州路的前夕,分派首領官等分管各房事務,與元朝中書省下屬各房相似,應是朱元璋在外時加強控制中書省事務的臨時措施,其后來是否為定制則不得而知。當時朱元璋為行省丞相,其下最高文官李善長不過是參議府參議,則參決軍政事務的機構必為參議府和左右司。通過兵房處理的事務,與元制中書省右司兵房所設邊關、站赤、鋪馬、屯田、牧地五科比較,范圍廣闊得多,幾乎涵蓋了軍事行動的所有方面,證明朱元璋并非通過行樞密院,而是通過行中書省的下屬機構處理軍務。
改設大都督府時,“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中書省參議李善長兼司馬
事,宋思顏兼參軍事,前檢校譚起宗為經歷,掾史汪河為都事。”15 比照行樞密院清一色武將,大都督府有文官加入。而且司馬、參軍等職寄甚重,并非虛銜:“歷代設兵政而或參軍,實助君之慎密也……非其人,不獨失機誤事,而軍士強弱之不分,混淆艱用,賞罰不精,月支無別,弊出多端。”16 郭景祥還曾以參軍身份“出鎮和陽”17。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謝再興在諸暨叛變,挾持的最高官員就是“參軍李夢庚”18。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即吳王位定制,在中書省系列中提到“參議府參議正三品,參軍斷事官從三品。”19 有些斷事官乃低級官吏,而此參軍斷事官位高至從三品,當系宋思顏所兼參軍職孑遺。時朱元璋長期倚重的胡深由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授任“王府參軍”20,亦應即此。至正二十五年(1365)胡深甚至以參軍領軍作戰 21。后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革參議府,但至洪武三年(1370)四月,仍有“大都督府參議”之名 22。可見大都督府長期設文臣處理高級事務,或中書省臣兼任或專任,確擁有處理軍政的權力。大都督府較行樞密院的又一變化就是:隨著文臣的加入擁有處理軍務的實權。
改制當年十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照磨各一人。”23
從官職名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與行樞密院官職的相似,說明設大都督府有繼續作為武將任官機構的意圖。但此時并無其他武將任左右都督、同知等的記載,潘檉章據以認為,樞密院改大都督府應晚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定官制時 24。結合《實錄》雖混亂卻未加系統篡改的大量記錄看,“改”的事實無可懷疑,無人就任都督等職實另有原因。
早在改設大都督府之時,“樞密院雖改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舊。”25 但“在內”的高級武將也并未改大都督府官,而是改任行中書省。早在年初,“以僉院鄧愈為中書省參政,仍兼僉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26 首次授武將以中書省官銜,而且地位之高,超出任參議的李善長等人。而在設立大都督府同時,“以樞密院同知邵榮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同僉常遇春為參知政事。”27 四月文臣之首李善長也升為參知政事 28。年內還“以樞密院同知徐達為中書右丞。”29 后來如上述,也長期未見有任都督等職者,而由原行樞密院官改任行中書省的武將卻層出不窮。
當時的形勢是,朱元璋一方面要敷衍龍鳳政權,采取與元朝地方行省相似的官制,另一方面則盡量模仿元朝中央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其各地中書分省的體制就是元朝行中書省總攬軍民政務的翻版,而元朝中央政權的制度是以中書省統攬軍政,而以樞密院分制其權。朱元璋就是按照元朝中央制度中樞密院的位置來設立大都督府的:最高級武將邵榮、徐達等任行中書省高官,地位偏低但為朱元璋侄子的朱文正則掌大都督府。恰好此時朱元璋地位的變化提供了可能性:當朱元璋任行省平章、丞相時,除了曇花一現的郭天爵任右丞,其他只有各文官如李善長等能任屬官,即只能任參議以下的郎中、員外郎等;而現在朱元璋本人已從行中書省脫身,他人無論文臣還是武將,就都可以任行中書省正官。行樞密院改大都督府的第三個變化就是:改名同時高級武將改任行中書省,大都督府不再是各級武將任職的機構。
元朝的樞密院雖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地位低于中書省,通常要受宰相的節制。宰相干預樞密院事務和兼領衛軍,使樞密院的分權作用一般不能實現 30。可能鑒于元代宰相的強橫,朱元璋注意使大都督府對行中書省高官們的獨立地位受到一定保護。大都督府名義上是由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而由朱元璋直接控制的職位稍低的文臣如參議、參軍等兼理其事務。這樣,大都督府充當了朱元璋通過行中書省文臣管理軍務的辦事機構,大都督朱文正外出駐守江西,并無機會參與最高權力的分配。由此,朱元璋可以通過行中書省的中樞機構和以無下屬武將的大都督府名義兩種各自獨立的渠道處理軍政事務。總之,通過使地方機構改屬行中書省和使大都督府無下屬機構擁有一定軍權,朱元璋所部完成了由行省體制向模仿元朝的相對獨立政權體制的過渡;通過使高級將領改任行中書省和以親信文臣兼理無武將任職的大都督府事務,朱元璋既避免了武將在最高統軍機構的專擅,又限制了高官對軍事分權機構的干涉。所謂行樞密院“改”大都督府,實質內容不僅是名義上的升格,而是包括統屬、任官、權力分配等各方面的變化,處處體現出朱元璋在建立政權過程中對權力分配的處心積慮。
“權重”
從至正二十一年(1361)大都督府設立時,除大都督外未見武將任職。半年后增設左右都督等各職位,仍無人任職。至正二十四年(1364)初,朱元璋稱吳王,建立以中書省為標志的獨立政權,三月,“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31 仍無任職記錄。至正二十五年(1365)初,唯一長官大都督朱文正被朱元璋罷黜 32。
朱文正被罷黜不久,開始零星出現任職大都督府的記錄。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以神武
衛指揮使康茂才為大都督府副使。”33 年底出兵淮東,“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規取淮東。”34 次年三月“徐達拔高郵……遣馮副使即軍中搜問。”35 馮副使應即馮國勝,應系此間改任大都督府副使。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軍攻克蘇州,開始有若干將領升為大都督府左右都督以下各官 36。不久再次“定大都督府及各衛官制。”37 次年正月羅列諸將,除徐達、常遇春、湯和等少數最高武將,絕大多數武將為大都督府官或其屬官 38,較上年九月賞平吳功時又大為增加,定系上年十一月“定大都督府官制”時所授。至此,大都督府由基本無人變為各級武將任職的重要機構,
洪武三年(1370)底,大規模統一戰爭結束,明朝大封功臣。此前任各省平章、左右丞、參政諸將,大多數回到京師任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等,其中地位僅次于徐達的李文忠、馮勝分任左、右都督。駐守各地諸將也紛紛改任都督僉事兼行省官,以行都督府掌管地方軍政。至此除丞相徐達以外,各高級將領均任職于大都督府。
此間,大都督府的職官設置和級別也有所變更。至正二十四年初的定制是:“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都護從二品……統軍元帥府元帥正三品……各位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正三品。”新官制表明,無論親軍、駐京主力軍還是各地駐守軍,均在名義上歸大都督府統領,而不再分屬各中書分省的長官或親軍都指揮使司。這時,大都督府地位上升,又成為最高統軍機構,而且所統包括朱元璋親軍,范圍超過了原行樞密院。
到至正二十七年底建國前夕再次定制,“大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大都督府級別上升至與中書省平等,突破了元朝樞密院品級低于中書省的舊制。
隨著其統屬各元帥府、衛所制度的確立,隨著諸武將由任職(行)中書省再轉任大都督府,隨著其級別升為與中書省平列的正一品,大都督府在明朝建國前后,成為超越故元中央樞密院地位的顯赫機構。這與其至正二十一年初設后無下屬、基本無長官的情景形成了鮮明對照。其間的轉變,從表面上看以建國前夕的任官定制為關鍵。但從幾位將領的黜陟情況看,轉變遠在此之前。
如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康茂才任大都督府副使前,原任金吾親軍都護府都護,都護府取消后改任神武衛指揮使 39,旋改此。按至正二十四年(1364)定制,都護階從二品,親軍指揮使正三品,副使正三品。康茂才旋任旋改,當因改任降級不當,故最終改任副使。則此副使已高于舊制的正三品。
又如至正二十六年(1366)初高郵戰役中,馮國勝輕信敵言導致失利,被朱元璋召回痛毆 40。潘檉章認為,馮國勝在此戰前后由同知樞密院而副使,是因此過“貶一官”41。按由俞廷玉“己亥(1359)……九月……贈龍虎上將軍、上護國、同知樞密院事”42 知同知樞密院為正二品。如果馮國勝降官,較正三品副使,所降尚不止一級。但馮國勝向來為朱元璋寵將,委任尤深,雖遭重責,不致降官兩級,況且未見降官明證。蓋馮國勝不過在回京期間改官而已,此時的大都督府副使,不僅如康茂才初授時高于正三品,而且可能已經是與原同知樞密院同級的正二品。
再如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論攻克蘇州功,“召右相國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廖永忠、左丞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參政薛顯、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于戟門。”從同條載功賞情況看,諸臣排列順序不是按功績高低,而是以名位排序。如果按至正二十四年(1364)官制,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都督三種官職分別與行省平章、左右丞、參政平級 43。都督馮宗異位于從一品的平章序列中,則“都督”是從一品的大都督,但馮宗異(即馮國勝、馮勝)從未任大都督;而都督副使為正三品,怎能位于從二品參政之上?顯然,此時大都督府官品已升為正一品衙門,都督馮宗異應為從一品的同知都督,都督康茂才位于正二品的右、左丞下,當為正二品的副都督即都督副使,故諸都督副使皆位于諸參政之前。
綜合上述三例,不妨認為,大都督府從以從一品大都督為首改成以正一品左、右都督為首,并非始于至正二十七年底建國前夕的“定制”,而是始自至正二十五年(1365)初的廢黜朱文正事件。
論者多以朱文正被廢一事證明朱元璋對大都督府勢力的防范。朱文正在南昌之戰中統帥鄧愈、趙德勝諸高級將領,其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雖僅名義,但作用亦不可忽視,遭朱元璋清除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朱文正個人的功高震主與大都督府權重并非一事。大都督被罷黜,大都督府地位卻迅速提升,證明朱元璋極力壓制的,只是大都督這個容易被利用的官職,而非大都督府本身。
大都督府的地位從設立開始即持續上升,所謂分割、限制其權力的說法不合事實。鄭曉“國初立大都督府……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44 的論證多被后人引用。所言為至正二十一年間事,而直到建國前并無任左右都督者,大都督卻早在至正二十五年初就廢黜不設。既然兩種官職從未同時授任,就不能認為左右都督等官乃為分大都督權所設。至正二十四年定制,雖定大都督為低于中書省的從一品,畢竟不低于元代樞密院的地位,而且還正式將統領所有軍事機構包括朱元璋親軍的權力劃歸大都督府。朱文正被廢黜后,大都督雖不再設,大都督府的級別卻迅即上升為與中書省等同,并非至正二十七年底方為定制。從大都督府級別改變的真實時間看,廢黜朱文正,不過是為朱元璋提高而非壓制大都督府地位掃清了道路。
朱元璋真正需要控制防范的,不是大都督府,而是擁有最高權力、有大量高級將領任職的中書省。把諸將由中書省改任大都督府的工作,從廢黜朱文正時就由諸親信將領開始了,至攻克蘇州始大規模進行。隨即在定制建國的過程中,大都督府成為高級將領任職的唯一機構,地位自非昔比。而中書省除地位特殊的丞相徐達外,完全消除了武將的痕跡。至于武將任官由中書省轉回略相當于樞密院的大都督府,除體現朱元璋提高大都督府地位以分中書省之勢的策略外,應與大量武將占據中書省名義下的平章、參政等正官職位,必然引起統屬關系混亂有關,而這倒是紅軍草創制度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偶然因素影響大局之一例。
大都督府為正一品衙門,與中書省平級,意味著大都督府已經成為參預軍國事務的中樞機構。高啟回憶道: “洪武三年四月,制以大都督府參議瑯琊樊公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僉都督事濮陽吳公遣其掾吏致言曰:……當王師定中原……之秋,凡邊書之所奏論……期會嚴迫而案牘繁滋。公度緩急之宜,審利害之勢,參畫處裁。……吳嘗貳掌樞管,實與公共事。”45 從這位“樊公”處裁邊書、參畫利害的工作看,大都督府雖事務由文臣操作,但畢竟是處理軍務的主要機構,與以往軍政由中書省下屬諸房處理不同。而都督僉事吳某更引參議文臣為同僚,也間接證明大都督府武將擁有議論軍政之權。沐英于洪武四年(1371)“升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壅,詒出聲生,稱上意旨”46,即為明證。
明初重臣如中書省丞相、封公爵武將例有加銜。建國前夕常遇春任中書省平章,加銜“掌軍國
重事”47,可能是強調其具有與中書省丞相李善長、徐達同樣重要的總攬事政之權。洪武元年(1368)正月,三人均加銜“錄軍國重事”48。洪武三年(1370),丞相李善長、徐達均加銜“參軍國事”49。旋胡惟庸任左丞相為“總理軍國重事”50,汪廣洋任右丞相,可能無加銜 51,或稍低為“知軍國事”52。諸公爵中,李文忠授任左都督,“同知軍國事”,右都督馮勝與御史大夫鄧愈為“同參軍國事”53,另外一位御史大夫湯和到洪武十一年(1378)封公任左都督,也加銜“議軍國事”54。諸名號互有高低,且稍卑于丞相。
加銜不過是沿襲元朝乃至歷代加官名號而來,諸將權力顯然不能如加銜字面顯示者 55,但擁有加銜既不按照品級職務,又按地位高低而稍有參差,至少表明擁有者的地位。特別是洪武三年封公侯后,加銜均置于爵位之后,與先前漫置于階官、勛管行列中相比,似稍顯其重要性。而明朝建國后,大都督府二都督以李、馮、湯等封公勛貴充任,當與中書省二丞相、御史大夫等同為擁有議政、執政大權的最高級官僚 56。
洪武十二年(1379年),李文忠出征回京,受命提督大都督府事。朱元璋告誡說:“大都督府掌
天下兵馬,其遷選、調遣,辨強弱,知險易,發放有節,進退信期,非止一端,于斯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其于機也甚密。特以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馬,謂裁其事耳……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府一應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后一同來奏。” 57 這時的大都督府擁有遷選、調遣大權,不但武官遷選,連軍事機構中低級官吏也由大都督府“選除”58,是真正的“總內外諸軍事”59 的最高軍事機關。
歷來所謂大都督府“權重”、大都督被分權之說,在大都督朱文正在任時,由于無其他武將任職、品級低于中書省、大都督本人駐守外地,是無從談起的。大都督府本是朱元璋直接以文臣控制處理軍務、限制中書省權勢的工具,其地位隨著確立對各級統軍機構的統率關系而提高,隨著大都督被廢黜,其他武將逐漸任職于級別上升了的大都督府,最終使大都督府成為幾乎所有武將任職的唯一機構,擁有參與軍國大政和掌管全國軍務的權力。其“權重”始于明朝建國,地位與元代樞密院相比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種局面,恐怕是本欲以之限制中書省權勢的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分”
洪武十三年(1380)初,胡惟庸案爆發,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 60,從此一蹶不振。但胡黨案針對的主要是過重的相權,牽連進胡黨案的唐勝宗、陸仲亨等功臣宿將也不算是大都督府的關鍵人物,大都督府作為對中書省起分權作用的機構,似乎本不應受到沖擊。結合當時形勢看,“分”即一分為五是地方文武分統體制導致大都督府統軍權過分膨脹的后果,而“分”背后的內容,當因大都督府議政施權重招引皇帝的打擊,又不僅僅是一分為五所能涵蓋的。
對明代的地方文武分統體制,即布政司與都司分統府州縣和衛所,分別上統于中書省(后為六部)和大都督府(后為五軍都督府),歷來有詳盡的介紹。而對體制的形成過程,特別是早期以大都督府為特色的原江南紅軍所部體制如何影響、促進了分統體制的建立,則還有待考察。
從至正十六年(1356)攻克南京建立江南行省,到明朝建國前夕的至正二十七年(1367)稱吳元年,朱元璋一直奉龍鳳政權號令。在此期間,經歷了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超越行省擢升吳國公,與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稱吳王建國,朱元璋所部由龍鳳下屬行省逐步演化為獨立政權。其江南行省的名義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才由中書省代替,而此前從至正二十一年(1361)開始朱部在制度上已經開始模仿元朝中央體制,其標志就是建立制約行中書省的大都督府。所以在朱部建立明朝的過程中,各地行省體制因系模仿原江南行省,往往受其中央化體制影響。原模仿元朝而有所強化的、已實行于中央的文武分統體制,遂被推廣到地方體制中。
按制度,至正二十一年(1361)大都督府建立時,地方統軍機構應隨樞密分院改中書分省而屬中書省系統。不過,地方改樞密分院為中書分省的措施并未完全貫徹。除浙東分省,找不到關于改設其他分省的記載。但這并非指各地仍維持樞密分院,而是朱元璋部地盤急劇膨脹,使地方機構迅速面臨新的改革。就在同年(1361年)底,朱軍突臨江州,進占江西。次年初,朱元璋以保留原編制為誘餌,勸降南昌守將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諸降將“各仍舊官”。61 迅即調離大部降軍,“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平章,留守洪都。”62 朱元璋盡管已是吳國公,所統本還是江南行省所屬,而江西是元朝、陳友諒部的原元朝一大行省,不能把它簡單納入江南行省,而必須設立與江南省并列的行省。如此,江南行省雖然名義上為行省,實際上卻成為包括管理其他行省在內的朱元璋整個轄區的“中書省”。而江南省的“中書省”化,又使中書分省的名義失去意義,故幾天后,將唯一的浙東分省更名為浙東行省。63 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稱王時,江南行省更名為中書省,又順理成章地在新占地盤設立了江淮、湖廣行省。64
湖廣、江淮等前線地區偶見分省記載,65 其它行省則并未仿照江南行省舊例轄樞密分院或中書分省。浙東分省初設時“總制諸郡軍馬”,胡大海遇害后旋改行省,“升同僉李文忠為左丞……總制衢、處、廣信、嚴、諸全軍馬。” 66 其轄區應與舊時胡大海所轄相同,而這些地方大多為樞密分院治所,并未改分省。蓋朱元璋部崛起江南之際,每下一大城即為重大戰果,在毗鄰張、陳之地每城屯駐重兵,故樞密分院濫設過度,需要事權歸一,乃欲上設分省以總領之。而今新下江西、湖廣成為戰略后方,每城駐守少量軍隊即可,如 “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德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聽江西行省節制……參軍詹允亨總制辰、沅、靖、寶慶等處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67 臨江等都是府城,若按舊例需設樞密分院,如今千戶所足矣。從諸多軍事行動的記載看,新設行省不再設樞密分院或分省,而是直接統轄守衛一城一地的翼元帥府或稍后的衛所,即便需要統一管轄多處城市,也只是設臨時性的“總制”或由行省官駐守。68 隨著大量舊設于江南行省的樞密分院不久在整編軍隊的過程中煙消云散,樞密分院改中書分省的制度在中書省轄區完全來不及實施,在外地行省更無必要實行了。
在樞密分院向中書分省、行省的“放大”過程中,武將一直占據著各高級官職。各行省的平章、右、左丞、參政等均由武將占據,而文官僅能擔任郎中、員外郎乃至經歷、都事一類。這證明戰時新設的各行省,仍如舊時樞密分院和中書分省體制,由武將總攬軍民事務,下統各衛所。其上統關系比較模糊,以洪武元年初情況為例:“在逃軍人,在內申奉大都督府,在外申奉行中書省明文,方許勾取……凡有軍情,在外各府軍民官司,申行省,行移各道按察司;行省一咨中書省,一咨大都督府,各道按察司申御史臺。在內直隸都督軍民官司,一申中書省,一申大都督府,一申御史臺……在外軍人告給行省管軍官及指揮司文引。”69 可見中書省轄境內軍務與衛所事務直接屬中書省和大都督府處理,外地均先經行省,而后上報中書省和大都督府。而從至正二十四年(1364)定制開始,大都督府已經統領各級軍事機構。故各行省向上除統于中書省,在軍事事務尤其是軍事機構的統領關系上,則應統于大都督府。
這樣,大都督府──行省──衛所(翼元帥府級的駐守一城一地的單位)式的地方統軍體系取代了行樞密院──樞密分院──翼元帥府結構,以及來不及推廣的行中書省──中書分省──翼元帥府體制。至此,軍民分統體制在地方尚未見端倪,但最高統軍機構既然不再是中書省而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與統領衛所的行省之間又缺乏明確的隸屬關系,改變統領方式是必然的趨勢。
隨著行省軍事事務的減少,行省高級官員中開始出現文臣。汪廣洋于“甲辰,立中書省,改左司郎中……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遂知贛州,尋升江西行省參政。”70 而于“丙午夏,以中書參議召還。是年冬參議西省。”71 西省即江西,參議西省應即擔任江西行省參政。常遇春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即乙巳年初攻克贛州,72 汪廣洋似即此后不久任江西參政。所謂“以中書參議召還”,當指從江西參政召還,即至少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夏已有文臣在外地行省任參政。而汪廣洋第二次赴江西任參政時,“壬午年……九月五日,吳左丞自臨川以詩見寄。” 73 朱元璋部下大將吳姓者僅吳良、吳禎、吳復,但一直守衛江陰或為偏裨,從未高升左丞,而從與汪廣洋唱和一事看,這位吳左丞定亦為后來湮沒無聞的行省高級文臣。贛州是陳友諒殘部的最后據點,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后,江西全境已無敵蹤,行省最高武將不過任參政 74。以文臣任行省參政,與駐守武將相同,標志著行省民政事務漸顯重要,武將總攬事務、獨統軍民的體制已經不適應形勢。
洪武元年(1368),明軍北進中原、南下嶺表,各地相繼開設行省和行都督府(或行大都督府、分都督府),使地方統軍體制發生重大變化。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冬攻克山東后,朱元璋說:“今兵入中原,得山東,欲少健者開省山東,經理諸事。以南昌郡西省參政汪廣洋者,其人不貪而純粹,可職山東。” 75 從諸史籍中均無武將任職山東行省記載看,這次與過去江西、湖廣乃至情況模糊的江淮省不同,一開始就以文臣而非武將掌管新設行省事務,顯示出新政權對行省民事性質的新界定趨勢。
洪武元年(1368年)攻克開封,“立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留徇未下城堡。” 76 攻克北平,“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以都督副使孫興祖領府事,升指揮華云龍為分府都督僉事。” 77 洪武二年(1369年)夏,戰爭告一段落,建立山西、陜西、福建、廣東、廣西、河南行省。78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即擊敗擴廓帖木兒后,“設陜西、北平、山西行都督府。” 79 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往臨濠開行大都督府。” 80 至此,北方五省中除不臨邊境的山東外,臨邊的北平、山西、陜西與北京所在的河南,以及中都,均相應設立了行都督府,而南方無論舊設還是新設三省,均無行都督府。
從設置地點看,行都督府是處理陪都、邊方軍務的大都督府派出機構,與地方統軍體制尚非一
事。行省與行都督府大體同時設立,但各省的任官情況已與建國前迥異。武將繼續任職行省,如曹良臣洪武元年(1368年)任山西平章,81 “以指揮曹興才為山西行省參政,兼領太原衛事。”82 “以廣西衛指揮使蔡仙為廣西行省參政。”83 但武將的行省職務多以大都督府、衛所官或他官兼任,而非專任,洪武三年(1370年)后更是如此。84 文臣除前見汪廣洋在不設行都督府的山東省任參政外,楊憲更于洪武元年(1368年)已任河南參政,85 此后一般文臣包括各地降臣、親信駙馬都尉等越來越多地任行省參政。高級武將有兼任行省高官者,但逐漸匯集到大都督府和行都督府任職,而自然節制各地衛所。這樣,行省尤其是北方行省,掌管軍務的職能正在隨著武將任職機構的變化而讓位于行都督府。
文臣于行省任職,最高為參政,與武將可任行省平章、右、左丞不同。名為防止民眾“困于供給”,86 而使行都督府武將地位高于行省文臣,不過因戰爭未了需以行都督府限制行省權力。戰爭結束后,高級武將紛紛回京,行都督府未見裁撤,而所剩高級武將不過都督僉事等。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詔定各行省、行都督府官與按察司官會見位次……按察使、副使、僉事俱坐于參政、僉都督之下。” 87 至此,行都督府基本已經由大都督府派出的臨時軍務機構,演化為常設于若干重要區域與行省并列的軍事機構。
從最初的樞密分院到后來的中書分省、行省,僅次于中央的大區級機構均統攬軍民之政。自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大量設置的衛所,在外地行省者均統于行省,再上統于大都督府。行都督府的出現及其與行省的并立,則標志著初步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民分統體制。大都督府--行都督府--衛所的格局終于在統一戰爭中形成,大都督府以下構成了獨立的上下統屬的體系。
此后,與行省并列的行都督府于洪武四年(1371年)后開始,過渡到節制一省衛所的都衛,再過渡到取消直接統軍職能的都指揮使司,最終穩定下來。在此過程中,統攬軍民之政的行省逐漸由文臣掌管,演變為僅管民政的布政司;而新設行都督府、都衛、都司單管軍政,軍民政務最終分離,大大強化了大都督府在擁有處理軍務權前提下的從中央到地方的統軍之任。
作為大都督府派出機構的行都督府,由大將掌管,統率轄區內軍隊作戰,而一開始就具有地方機構的性質;但隨著大規模統一戰爭的結束,地方軍政迅速由都衛這個具有濃厚地方性質的機構接管,都衛作為直接統率省會軍隊的衛,節制其它衛所軍隊;隨著對內對外戰爭告一段落,都衛這個統軍單位又讓位于單純的管理機構都司。可見,隨著大規模戰爭結束,地方統軍機構的職權在逐步縮減,以大都督府為首的軍事機構體系也在向統軍體系轉化,權力正逐步縮減。但經由普及全國的獨立統屬體系強化的大都督府的權力,與其統領幾乎所有武將、擁有參與軍國大政之權等配合起來,必然也使專制皇帝在打擊相權時,順便從分割事權和取締實權兩方面削減大都督府的權力。
大都督府分為五軍都督府后,各都督府的長官左右都督,不再全由高級勛臣出任,不再擁有“同知軍國重事”之類的加銜,十位都督人數眾多,又皆出自中級將領,不可能如過去李文忠、馮勝等都督那樣議政,即原大都督府長官的最高議政權不復存在。這樣,都督府僅剩下執行命令的資格,而無參預決策的權力。
大都督府執行軍務命令,除直接來自朱元璋外,多通過中書省發布。如朱軍進攻張士誠部檄文稱:“總兵官準中書省咨。”88 后來隨著大都督府和中書省平級的地位得到確定,應可直接發布來自皇帝的命令或自行處理一般事務。中書省廢除后,五軍都督府執行的命令除來自皇帝,還可以由皇帝通過兵部發布。兵部的地位不但低于原中書省,在級別上也低于都督府。朱元璋在分割大都督府的當天,甚至決定把五軍都督府降低到正二品即與六部同級的地位,后來可能覺得都督府實在已無威脅,才于兩天后改回一品 89。這樣,都督府要受制于級別更低的機構。
五軍都督府既不再“總天下兵馬”,也不再掌管“遷選、調遣”。大都督府廢除的第二天,“以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衛職掌守衛宮禁,凡有支請徑行六部,不隸五軍。”90 大約二十年前,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撤銷,一切統軍權歸大都督府。現在親軍又脫離最高統軍機構,而直接歸屬皇帝,并通過兵部掌握。武官遷選、軍隊調動之權歸兵部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取消后,諸勛貴重臣勉強維持地位。李善長與李文忠有可能繼續“議軍國政”,李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91。但這種“特批”權力即便比過去的加銜較有實效,卻無實職配合,即最多有議政之權,而無施政之力。隨著李文忠迅速去世,大都督府的痕跡最終消亡了。
總之,大都督府改五軍都督府,使都督府在保留最高統軍機構地位的同時,喪失了議政權,而僅能執行皇帝和兵部的命令;喪失了統率所有軍隊的權力,而與親軍各衛并列;喪失了武官黜陟權與調兵權,而受制于兵部。
在明朝建國前后的戰爭中,隨著各地從樞密分院到分省到行省體制的建立,大都督府行使對軍事機構的統率權和對各地軍務的指揮權,促進原江南行省的中央化體制推廣到行省,從而形成大都督府--行都督府(都衛、都司)--衛所的地方文武分統體制和獨立的上下統屬體系。所謂大都督府的“分”為五軍都督府,首先是分割大都督府涵蓋全國的獨立統軍體系,而不僅僅是分割高級武將的事權;而在“分”的過程中,由“總內外諸軍事”的中樞機構變成處處受制于兵部的單純執行命令的機構,則是一分為五背后都督府實權削弱殆盡的事實。
1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史語所校印本。
2 南炳文:《明初軍制初探》(續),《南開史學》,1983年第2期,109-110頁。
3 (清)夏燮:《明通鑒》前編卷二,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一○二《太祖實錄辨證》,癸卯三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 (清)潘檉章:《國史考異》卷一,第五條,《叢書集成初編》本。
6 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79─180頁。
7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二月癸巳朔。
8 《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中華書局,1976年。
9 蕭啟慶:《元代的鎮戍制度》,載《元代史新探》,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125-127頁。
10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五月甲戌。
11 (明)宋濂:《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墓志銘》,載《宋文憲公全集》卷五,《四部備要》本。
12 (元)唐桂芳:《送萬元信知江淮府》,載《唐氏三先生集·白云文稿》卷一,明正德刻本。
13 (明)彭澤等輯:《弘治徽州府志》卷四,《名宦》,《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14 (明)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卷首,《陶學士先生事跡》,明弘治刻本。
15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
16 (明)朱元璋:《參軍府參軍誥文》,載《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三,《中國史學叢書》本。
17 (明)吳樸:《龍飛紀略》卷一,丙申年十月,明嘉靖刻本。
18 (明)劉辰:《國初事跡》,載(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75頁。
19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甲辰年正月丙寅朔。
20 (明)王祎:《縉云郡伯胡公行狀》,載《王忠文公集》卷二二,明刻本。
21 《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乙巳年六月壬子。
22 (明)高啟:《送樊參議赴江西參政序》,載《鳧藻集》卷二,《四部叢刊》本。
23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十月戊寅朔。
24 潘檉章:前引書卷一,第九條。
25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
26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正月辛酉。
27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三月丁丑。
28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四月。
29 《明太祖實錄》卷九,辛丑年末。
30 張帆:前引書,173─180頁。
31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甲辰年三月戊辰。
32 《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乙巳年正月甲申。
33 《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乙巳年五月甲申。
34 《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乙巳年十月辛丑。
35 《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丙午年三月丙申。
36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吳元年九月辛丑。
37 《明太祖實錄》卷二七,吳元年十一月乙酉。
38 《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辛巳。
39 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五,甲辰年十月末;同書卷一六,乙巳年二月末。
40 劉辰:前引書,載鄧士龍:前引書,80頁。
41 潘檉章:前引書卷一,第九條。
42 (明)焦竑:《河間郡公俞廷玉傳》,載《獻征錄》卷六,上海書店,1986年。
43 《明太祖實錄》卷一四,甲辰年三月戊辰。
44 (明)鄭曉:《今言》卷一,第五十條,《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中華書局,1984年。
45 高啟:前引文。
46 (明)王景:《西平侯沐公神道碑》,載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卷七三,《四部叢刊》本。
47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吳元年十月甲子。
48 《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辛巳。
49 《明太祖實錄》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
50 朱元璋:《罷李善長相胡惟庸詔》,載《孝陵詔敕》洪武四年正月初一日,《中國史學叢書·明朝開國文獻》本。
51 朱元璋:《命左右相詔》,載《皇明詔令》卷二,《元明史料叢編一輯》本。
52 《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藝海珠塵》本。
53 《明太祖實錄》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
54 (明)黃金:《湯和》,載《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一,明正德刻本。
55 洪武二十三年(1390),馮勝還“同參軍國事”,但要真正參與軍國大事,必須朱元璋批準。例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二,洪武十年五月庚子。
56 丁玉于洪武十二年底任都督(黃金:《丁玉》,前引書卷一七),玉功著譽隆,未知有否加銜,而位高權重則同。
57 朱元璋:《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敕》,載《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九。
58 劉辰:前引書,載鄧士龍:前引書,105頁:“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選除,于本府考滿。”
59 朱元璋:《大都督府僉事陳方亮誥》,載《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三。
60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
61 《明太祖實錄》卷十,壬寅年春正月辛酉。
62 《明太祖實錄》卷十,壬寅年二月辛卯。
63 見《明太祖實錄》卷十,壬寅年二月丙申。按潘檉章:前引書卷一,第八條辯《實錄》鄧愈本傳癸卯年(1363)任參政之載,認為鄧愈任江西參政在壬寅年(1364)正月,要之皆浙東改行省之前。
64 設江淮行省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五,甲辰年七月己卯,吳樸前引書卷三系于同年四月。但《實錄》卷一三,癸卯年十月癸卯載“贈張德勝為光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蓋癸卯年(1363)夏龍鳳政權被張士誠擊破,朱元璋北援安豐,挾小明王南下,張德勝官為以小明王名義所贈。而來年朱元璋即吳王位,小明王形同虛設,朱元璋乃設立自己的江淮行省。湖廣行省之名最早見于《實錄》卷一六,乙巳年二月辛丑,可能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占領湖廣后即設立。
65 《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乙巳年十一月己酉:“命中書省掾劉大昕往湖廣荊州分省參贊機務。”卷二二,吳元年三月壬午:“湖廣分省參政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撫。”從楊璟的活動地點看,其即湖廣荊州分省參政。(可參吳樸前引書卷三,吳元年二月:“以楊璟為湖廣行省平章……仍于荊州分省署事。”)《實錄》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戊申:“改河南分省為行省”。河南分省僅見于此,蓋明軍攻克開封后所設,隸屬江淮行省。河南升行省與山陜閩廣等設省同時,可視此為分省設置的結束。
66 《明太祖實錄》卷十,壬寅年二月丙申。
67 《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乙巳年二月辛丑。
68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吳元年九月丁亥:“岳州參政張彬還建康。”黃金:《張彬》,載前引書卷一五:“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守御岳州。”可互證。
69 《大明令·兵令》,《北圖古籍珍本叢刊·皇明制書》本。
70 (明)汪廣洋:《鳳池吟稿》卷首,《郡志本傳》,明刻本。
71 汪廣洋:《召赴京師別豫章》,載前引書卷七。
72 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乙巳年正月己巳。
73 汪廣洋:《會吳左丞見寄登滕王閣詩韻并序》,載前引書卷七。按壬午年當系丙午年(1367年)之誤。
74 (明)劉崧:《孫先生傳》,載《槎翁文集》卷二,明嘉靖刻本:(何文輝)“調守江西。乙巳,拜行省參知政事。”
75 陶安:前引書卷首,《陶學士先生事跡》引《太平郡志》朱元璋語。
76 (明)高岱:《鴻猷錄》卷五,《北伐中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7 《明太祖實錄》卷三五,洪武元年九月壬寅。
78 潘檉章:前引書卷二,第四條。
79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壬申。按:北平行都督府當即洪武元年設大都督府分府。又《實錄》卷一零六,洪武九年六月壬辰《何文輝傳》:“從戰定西,使攝安西分都督府事。”焦竑:《大都督府同知何文輝傳》,載前引書卷一零七引《實錄》,以“安西”作“西安”。但時隴右實為重鎮,于河州或鞏昌等地設以“安西”為名的行府并非不可能。況當時陜西行都督府的首領乃耿炳文,并非何文輝。見(明)劉三吾:《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銘》,載《坦齋劉先生文集》卷上,明萬歷刻本。《實錄》載洪武三年(1370年)設行府時未提,姑置不論。
80 《明太祖實錄》卷六四,洪武四年四月甲申。
81 黃金:《曹良臣》,前引書卷六。
82 《明太祖實錄》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己巳。
83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戊辰。
84 如耿炳文以秦王府武相兼陜西行省右丞(《明太祖實錄》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庚辰)。華云龍于洪武三年(1370)底前為“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燕王府右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宋濂:《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載前引書卷一四)
85 《明太祖實錄》卷三二,洪武元年五月癸巳。
86 (明)張以寧:《送周參政行省廣東序》,載《翠屏詩文集》卷二,清抄本。
87 《明太祖實錄》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丙申。
88 (明)夏原吉:《一統肇基錄》,《叢書集成初編》本。(明)陸深:《續停驂錄摘抄》,《叢書集成初編》本。
89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丙午。
90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正月甲辰。
91 (明)李贄:《太師丞相韓國李公》,載《續藏書》卷二,中華書局,1959年;《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前引書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