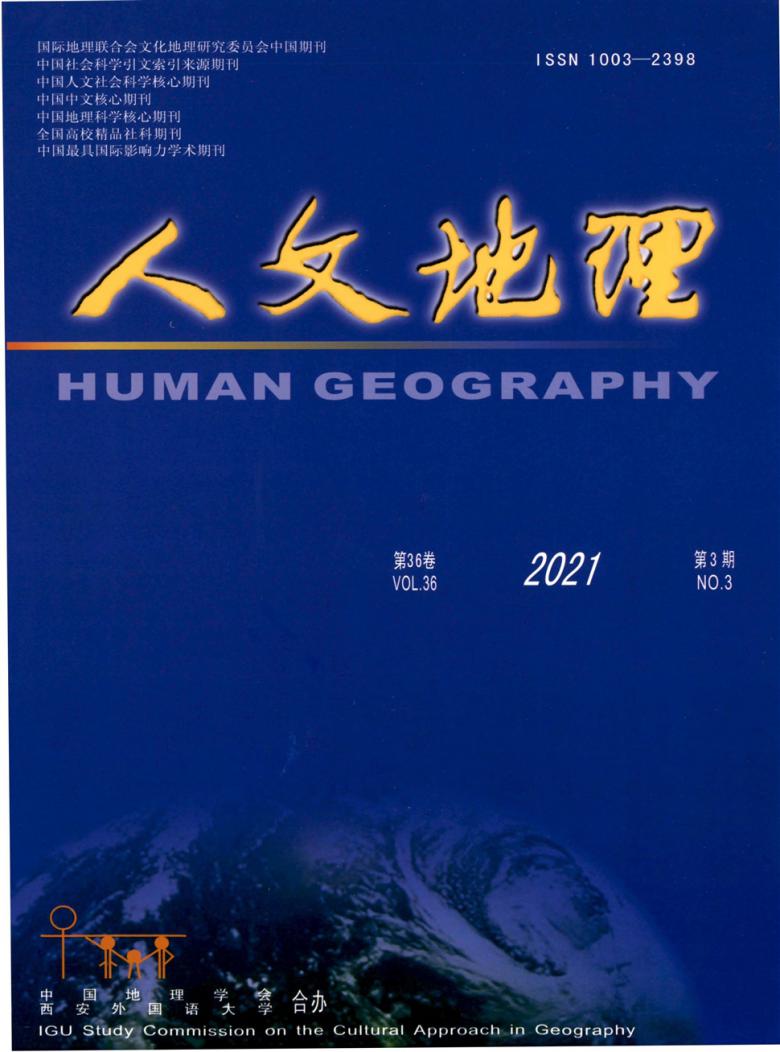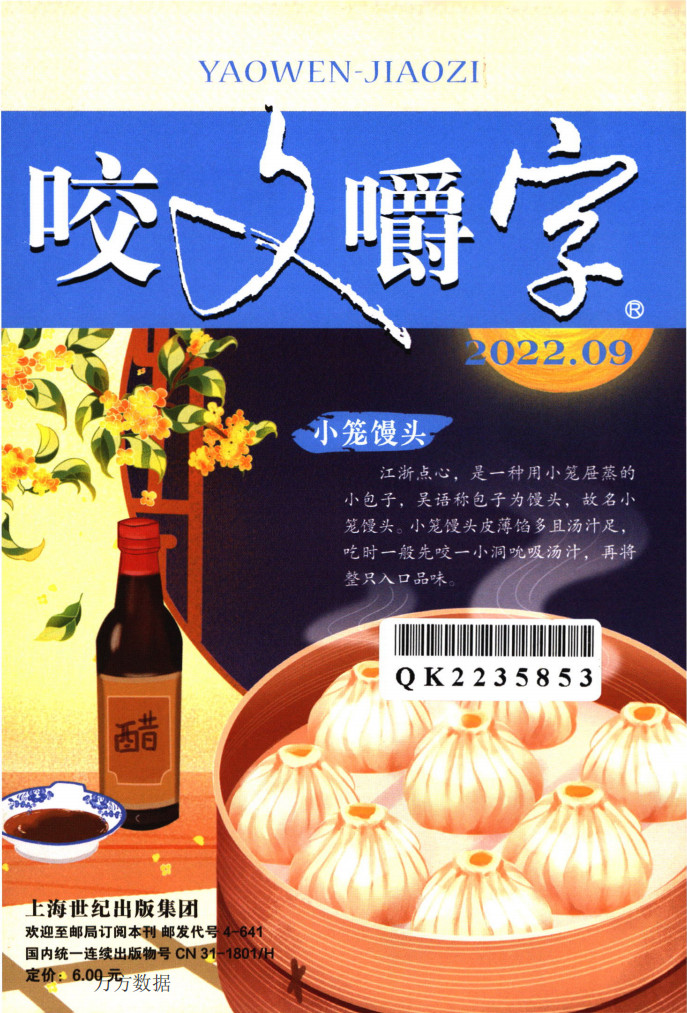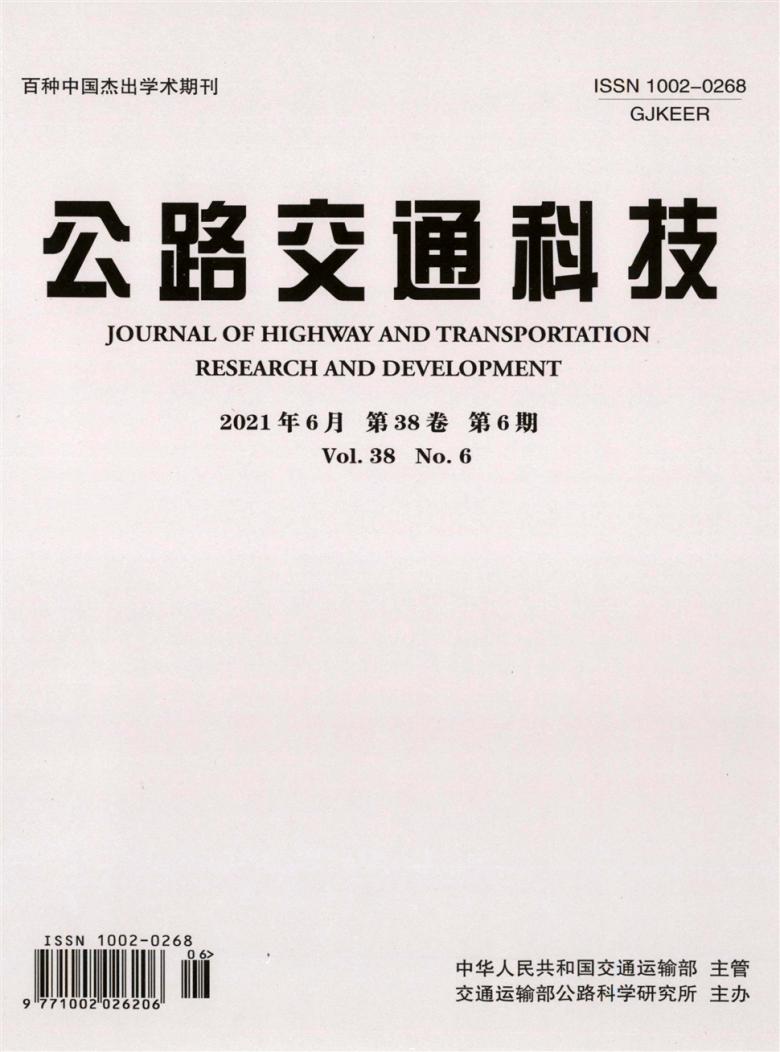明代歷史定位問題新探
佚名
內容摘要:傳統至今,史學界都把明朝當作一個統一王朝,即統一了中國的王朝,如“元——明——清”說,這種做法欠妥。其實,明朝只是統一了漢族和多少數民族,但并未真正統一中國。因為明朝的前政權——元并未被真正消滅,北元及蒙古諸部與明以長城為界,一直處于對峙之勢,形成了事實上的南北朝。而史學界關于1368年“元朝滅亡”、1387年“中國再度統一”等說法,都根據不足。明朝的真正歷史地位,應定為“元季南北朝”的南朝之大明。 關 鍵 詞: 金山之役;北元;漠北;元季南北朝;九邊;邊墻(長城) 傳統至今,史學界包括整個理論界,對明代歷史定位都持“元——明——清”說,即將明直接與元、清等朝并列。如《簡明中外歷史辭典》附錄的《中國歷史年代表》[1]: 封 建 社 會 元 1271年—1368年 明 1368年—1644年 清 1644年—1840年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想談點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能將1368年作為“元朝滅亡”的時間嗎? 傳統至今,所有的史書,較早如《明通鑒》,遲如現代的各種史學著作、教科書等都認為:1368年,明軍北伐,“元朝滅亡”。[2] 關于明軍北伐,據《明通鑒》和《續資治通鑒》載: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今江蘇省南京市)稱帝,國號大明;隨后開始北伐。七月,明北伐軍“扼直沽河……元丞相伊蘇左次海口,望風而逃,燕都大震。癸亥,大軍至河西務,敗元平章之兵,擒其知院等三百余人。丙寅,遂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布顏特穆爾戰死之。是日,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于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慶通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3]“左丞相實勒們及知樞密院事赫色、宦者趙巴延布哈等諫,以為不可行,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奈何棄之?臣等愿率軍民及諸集賽出城拒戰,愿陛下固守京城 。’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走。”八月,明軍進占北京。[4]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明軍北伐確實取得了重大利,但認為這是“元朝滅亡”的標志則值得商榷。第一,明軍并未俘獲或殺死元順帝。明軍北伐,元順帝主動撤離北京,返還元朝的另一首都——上都。(元朝當時有兩個首都,一個是大都,即北京,另一個是上都。)元順帝撤到上都,有戰略退卻含義在里邊,目的是東山再起。而且,此時明軍雖占領了北京,但全國大多數地區如山西、陜西、四川、云南、貴州等,仍在元朝統治者手中。 第二,1369年,元順帝還組織了對明軍的反攻。1369年,即明軍占領元大都的第二年,元順帝乘明軍主力進攻山西之際,派丞相伊蘇反攻通州,企圖重新奪回北京。元的這次軍事行動,被明將曹良以計破之,并用精騎窮追一百余里。[5]可是,順帝的這次軍事行動表明:元并未滅亡。 第三,元朝最后取消國號的時間是1404年。元朝退回上都后,又建都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史稱北元,如《簡明中國歷史》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見下表)。[6] 北元:公元1370——1403年,共34年。建都和林。 昭宗愛猷識理達臘 宣光 公元1370——1378年 脫古思帖木兒 天元 公元1379——1388年 恩克卓里克圖 公元1388——1391年 額勒伯克 公元1392——1400年 坤帖木兒 公元1401——1403年 鬼力赤帖木兒 本年去元國號 公元1404年 應當指出,《簡明中國歷史》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記載不科學。北元是上承元順帝的,元順帝逃出北京后,死于1370年。事實上,北元的起點應為1368年,因為1368年閏七月順帝即逃往上都。即: 順帝妥帖睦爾 至正 公元1368——1370年 另外,還應指出,從順帝北逃后,北元到底歷經幾帝、帝號及在位年數,說法已難于詳聞。如《明實錄》、《明史》等載:“順帝后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或言“敵自脫古思帖木兒后,部帥紛拏,五代至坤帖木兒,咸被殺,不復知帝號。”[7]不過,北元的存在則是錚錚鐵史,不容抹殺。 第四,史論的體例不統一。傳統至今,史學界一方面認為元的滅亡時間在順帝撤離北京之年,另一方面,又認為南宋的滅亡在1279年——宋最后一個小皇帝的投海自殺。如《新華字典》附錄的《我國歷史朝代公元對照簡表》(見下表)。[8] 宋 北 宋 960——1127 南 宋 1127——1279 元 1279——1368 《簡明中國歷史》也說:“元軍于1276年二月不戰進取臨安,俘南宋恭帝趙顯及謝、全兩太后,文武官員人等北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同是字)為帝(端宗),繼續抗元……陸秀夫和張世杰在1279年(祥興二年)退至廣東崖山,被張弘范追及。陸秀夫背著南宋小皇帝趙昺(同丙字,1278年二月昰死,衛王趙昺被擁立為帝)投海而死。……南宋亡。”[9]事實上,1276年,元將伯顏兵臨皋亭山,南宋就獻上了降表。降表明確說:“……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元人也接授了宋皇室的投降,并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說:“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10]后陸秀夫等少數人所擁立的南宋皇室的兩個小兒皇帝,至多是個流亡政府,既未得到人民的承認和支持,也未在抗元中有所作為,充其量是茍延殘喘。史學界為什么非要將在1368年沒有滅亡的元朝強行宣布為“滅亡”,而將明明在1276年就滅亡了的南宋非要拖延到1279年才宣布其“滅亡”?這在史論體例上是前后矛盾,是對元朝不公! 二、1387年的“金山之役”能否標志“中國再度統一”? 史學界一直認為:1387年,明軍的“金山之役”,標志“中國再度統一”。如《簡明中國歷史》明確說:“1387年(洪武二十年),馮勝、傅友德、藍玉諸奉命北上,包圍金山,納哈出勢窮請降,遼東全部平定,中國再度統一”;[11]《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四卷也說:“自朱元璋起義至納哈楚降,前后三十五年,全國方統一。”[12] 明軍的“金山之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通鑒》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載:1387年“春,正月癸丑,上以元故將納克楚擁眾數十萬屯金山,數為邊患,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二十萬眾征之。” 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偵知敵騎有屯慶州者,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其平章郭勒,擒其子布喇奇,獲人馬而還”; “三月,辛亥,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筑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馮勝等謀趨金山,留兵五萬守大寧,自率大軍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百人,馬四百余匹。” 六月,“進師駐金山之西。臨江侯陳鏞率所部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死。癸卯,大軍壓金山。先是鼐喇固北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驚曰:‘爾尚存乎?’鼐喇固因諭以朝廷德意。納克楚喜,遣其左丞劉特默齊來勝軍獻馬,且覘我軍。勝受而送之京師,趣率師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和通。于是納克楚見大軍奄至,度不敵,丁未,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之。先是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畜牧繁盛。至是為大軍所逼,遣使陽納款而陰覘兵勢。洎藍玉至一禿河,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大懼,仰天嘆曰:‘天不復使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都督耿忠……亟擁納克楚見勝,勝曲加拊慰……凡降士卒四萬余,羊馬駝驢輜重亙百余里。”[13] 應當指出,明軍的“金山之役”確實取得了成功,也降服了故元將納哈楚,但不能以此作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標志。第一,不要過高估計納哈楚降明的意義。歷史明載,納哈楚是元故將。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統治區出現了多個蒙古割據政權,納哈楚只是其中的一個。納哈楚降明,只能說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實力的蒙古割據政權,解除了其對明朝的威脅,但不代表蒙古諸部都已降明。事實上,除納哈楚外,蒙古諸部仍在反明。而且,此時北元政權還健在,納哈楚也代表不了北元政權,北元也仍在反明。 第二,納哈楚降明能否說明“遼東全部平定”?明軍的“金山之役”,在軍事上采取的是奔襲的方針,奔襲勝利后,立即回師,并未對遼東進行直接管理。就是說,明軍這次行動的戰略方針,旨在解除納哈楚對大明的軍事威脅,并未真正平定遼東。不要忘記,納哈楚是蒙古部落,遼東是契丹和女真族聚居地。降服納哈楚,只是把契丹和女真族從蒙古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但要使契丹和女真族正歸順明朝,還尚需時日。直到1403年,明才在東北設奴兒干衛,對女真等少數民族進行統治。尤其是,雖然納哈楚降明了,但遼東的其他蒙古部落仍在反明。就在明軍撤退時,殿后的明軍將領濮英,還遭遇蒙軍的伏擊,被俘后自殺身亡。[14] 第三,即使“遼東全部平定”了,能否說明“中國再度統一”?從以上分析可知,遼東為契丹和女真聚居地,其地理在政治上無特殊意義,即使“遼東全部平定”為真,也不代表蒙古地區全部平定,不能說“中國再度統一”。因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根本在蒙古諸部,因為蒙古諸部是明的前政權,不平定蒙古諸部,很難說“中國再度統一”。 第四,“金山之役”后,北元和蒙古諸部仍在對明進行反攻,而明亦仍在對蒙古進行統一戰爭。如:1387年底,朱元璋以故元帝孫脫古思貼木兒“屢屢擾邊”,遣藍玉為大將軍攻之。藍玉率軍至捕魚兒海(今內蒙古呼盟巴爾虎左旗西南之貝爾湖),俘元皇次子地保奴(又作迪保努)及妃嬪公主百二十余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元君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及臣屬數十騎逃走,將依丞相耀珠于和林。[15]又如,1390年,朱元璋以元故丞相耀珠等尚為邊患,命晉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師北伐,并命傅友德率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率山西兵從晉王,受二王節制。又命齊王朱榑率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北伐。……傅友德、燕王出古北口,乃爾不花、耀珠等降。[16]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朱棣除派將進攻蒙古外,還五次親征。第一次:1410年,成祖經興和,過大伯顏山、小伯顏山,到清水源(即今內蒙馬塔八海子)一帶,敗本雅失里于斡難河;又經闊灤海子(今內蒙呼倫湖)敗阿魯臺。[17]第二次:1414年,成祖至飲馬河(今克魯倫河),前鋒劉江敗瓦刺兵于康哈里孩;到忽蘭忽失溫(今蒙古烏蘭巴托東附近),又敗瓦刺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部,窮追至圖拉河(今蒙古境內)。[18]第三次:1422年,成祖經雞哆山、云州、獨石、度偏嶺,至開平(今內蒙多倫),出應昌、威遠至沙琿原,將阿魯臺趕到漠北。[19]第四次:1423年,成祖至西陽河,聞阿魯臺遠遁,班師。[20]第五次:1424年,成祖至開平,阿魯臺又遠遁,在班師途中,崩于榆木川(今內蒙烏珠穆沁東南,多倫北)。[21]元(即北元與蒙古諸部)、明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沒有停止,怎么能說1387年的“金山之役”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標志呢?
內容摘要:傳統至今,史學界都把明朝當作一個統一王朝,即統一了中國的王朝,如“元——明——清”說,這種做法欠妥。其實,明朝只是統一了漢族和多少數民族,但并未真正統一中國。因為明朝的前政權——元并未被真正消滅,北元及蒙古諸部與明以長城為界,一直處于對峙之勢,形成了事實上的南北朝。而史學界關于1368年“元朝滅亡”、1387年“中國再度統一”等說法,都根據不足。明朝的真正歷史地位,應定為“元季南北朝”的南朝之大明。
關 鍵 詞: 金山之役;北元;漠北;元季南北朝;九邊;邊墻(長城)
傳統至今,史學界包括整個理論界,對明代歷史定位都持“元——明——清”說,即將明直接與元、清等朝并列。如《簡明中外歷史辭典》附錄的《中國歷史年代表》[1]:
封 建 社 會
元 1271年—1368年
明 1368年—1644年
清 1644年—1840年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想談點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能將1368年作為“元朝滅亡”的時間嗎?
傳統至今,所有的史書,較早如《明通鑒》,遲如現代的各種史學著作、教科書等都認為:1368年,明軍北伐,“元朝滅亡”。[2]
關于明軍北伐,據《明通鑒》和《續資治通鑒》載: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今江蘇省南京市)稱帝,國號大明;隨后開始北伐。七月,明北伐軍“扼直沽河……元丞相伊蘇左次海口,望風而逃,燕都大震。癸亥,大軍至河西務,敗元平章之兵,擒其知院等三百余人。丙寅,遂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布顏特穆爾戰死之。是日,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于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慶通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3]“左丞相實勒們及知樞密院事赫色、宦者趙巴延布哈等諫,以為不可行,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奈何棄之?臣等愿率軍民及諸集賽出城拒戰,愿陛下固守京城 。’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走。”八月,明軍進占北京。[4]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明軍北伐確實取得了重大利,但認為這是“元朝滅亡”的標志則值得商榷。第一,明軍并未俘獲或殺死元順帝。明軍北伐,元順帝主動撤離北京,返還元朝的另一首都——上都。(元朝當時有兩個首都,一個是大都,即北京,另一個是上都。)元順帝撤到上都,有戰略退卻含義在里邊,目的是東山再起。而且,此時明軍雖占領了北京,但全國大多數地區如山西、陜西、四川、云南、貴州等,仍在元朝統治者手中。
第二,1369年,元順帝還組織了對明軍的反攻。1369年,即明軍占領元大都的第二年,元順帝乘明軍主力進攻山西之際,派丞相伊蘇反攻通州,企圖重新奪回北京。元的這次軍事行動,被明將曹良以計破之,并用精騎窮追一百余里。[5]可是,順帝的這次軍事行動表明:元并未滅亡。
第三,元朝最后取消國號的時間是1404年。元朝退回上都后,又建都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史稱北元,如《簡明中國歷史》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見下表)。[6]
北元:公元1370——1403年,共34年。建都和林。
昭宗愛猷識理達臘 宣光 公元1370——1378年
脫古思帖木兒 天元 公元1379——1388年
恩克卓里克圖 公元1388——1391年
額勒伯克 公元1392——1400年
坤帖木兒 公元1401——1403年
鬼力赤帖木兒 本年去元國號 公元1404年
應當指出,《簡明中國歷史》的《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記載不科學。北元是上承元順帝的,元順帝逃出北京后,死于1370年。事實上,北元的起點應為1368年,因為1368年閏七月順帝即逃往上都。即:
順帝妥帖睦爾 至正 公元1368——1370年
另外,還應指出,從順帝北逃后,北元到底歷經幾帝、帝號及在位年數,說法已難于詳聞。如《明實錄》、《明史》等載:“順帝后愛猷識理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或言“敵自脫古思帖木兒后,部帥紛拏,五代至坤帖木兒,咸被殺,不復知帝號。”[7]不過,北元的存在則是錚錚鐵史,不容抹殺。
第四,史論的體例不統一。傳統至今,史學界一方面認為元的滅亡時間在順帝撤離北京之年,另一方面,又認為南宋的滅亡在1279年——宋最后一個小皇帝的投海自殺。如《新華字典》附錄的《我國歷史朝代公元對照簡表》(見下表)。[8]
宋
北 宋
960——1127
南 宋
1127——1279
元
1279——1368
《簡明中國歷史》也說:“元軍于1276年二月不戰進取臨安,俘南宋恭帝趙顯及謝、全兩太后,文武官員人等北去。……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同是字)為帝(端宗),繼續抗元……陸秀夫和張世杰在1279年(祥興二年)退至廣東崖山,被張弘范追及。陸秀夫背著南宋小皇帝趙昺(同丙字,1278年二月昰死,衛王趙昺被擁立為帝)投海而死。……南宋亡。”[9]事實上,1276年,元將伯顏兵臨皋亭山,南宋就獻上了降表。降表明確說:“……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元人也接授了宋皇室的投降,并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說:“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10]后陸秀夫等少數人所擁立的南宋皇室的兩個小兒皇帝,至多是個流亡政府,既未得到人民的承認和支持,也未在抗元中有所作為,充其量是茍延殘喘。史學界為什么非要將在1368年沒有滅亡的元朝強行宣布為“滅亡”,而將明明在1276年就滅亡了的南宋非要拖延到1279年才宣布其“滅亡”?這在史論體例上是前后矛盾,是對元朝不公!
二、1387年的“金山之役”能否標志“中國再度統一”?
史學界一直認為:1387年,明軍的“金山之役”,標志“中國再度統一”。如《簡明中國歷史》明確說:“1387年(洪武二十年),馮勝、傅友德、藍玉諸奉命北上,包圍金山,納哈出勢窮請降,遼東全部平定,中國再度統一”;[11]《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四卷也說:“自朱元璋起義至納哈楚降,前后三十五年,全國方統一。”[12]
明軍的“金山之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通鑒》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載:1387年“春,正月癸丑,上以元故將納克楚擁眾數十萬屯金山,數為邊患,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二十萬眾征之。”
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偵知敵騎有屯慶州者,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其平章郭勒,擒其子布喇奇,獲人馬而還”;
“三月,辛亥,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筑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馮勝等謀趨金山,留兵五萬守大寧,自率大軍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百人,馬四百余匹。”
六月,“進師駐金山之西。臨江侯陳鏞率所部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死。癸卯,大軍壓金山。先是鼐喇固北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驚曰:‘爾尚存乎?’鼐喇固因諭以朝廷德意。納克楚喜,遣其左丞劉特默齊來勝軍獻馬,且覘我軍。勝受而送之京師,趣率師逾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和通。于是納克楚見大軍奄至,度不敵,丁未,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之。先是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畜牧繁盛。至是為大軍所逼,遣使陽納款而陰覘兵勢。洎藍玉至一禿河,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大懼,仰天嘆曰:‘天不復使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都督耿忠……亟擁納克楚見勝,勝曲加拊慰……凡降士卒四萬余,羊馬駝驢輜重亙百余里。”[13]
應當指出,明軍的“金山之役”確實取得了成功,也降服了故元將納哈楚,但不能以此作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標志。第一,不要過高估計納哈楚降明的意義。歷史明載,納哈楚是元故將。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統治區出現了多個蒙古割據政權,納哈楚只是其中的一個。納哈楚降明,只能說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實力的蒙古割據政權,解除了其對明朝的威脅,但不代表蒙古諸部都已降明。事實上,除納哈楚外,蒙古諸部仍在反明。而且,此時北元政權還健在,納哈楚也代表不了北元政權,北元也仍在反明。
第二,納哈楚降明能否說明“遼東全部平定”?明軍的“金山之役”,在軍事上采取的是奔襲的方針,奔襲勝利后,立即回師,并未對遼東進行直接管理。就是說,明軍這次行動的戰略方針,旨在解除納哈楚對大明的軍事威脅,并未真正平定遼東。不要忘記,納哈楚是蒙古部落,遼東是契丹和女真族聚居地。降服納哈楚,只是把契丹和女真族從蒙古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但要使契丹和女真族正歸順明朝,還尚需時日。直到1403年,明才在東北設奴兒干衛,對女真等少數民族進行統治。尤其是,雖然納哈楚降明了,但遼東的其他蒙古部落仍在反明。就在明軍撤退時,殿后的明軍將領濮英,還遭遇蒙軍的伏擊,被俘后自殺身亡。[14]
第三,即使“遼東全部平定”了,能否說明“中國再度統一”?從以上分析可知,遼東為契丹和女真聚居地,其地理在政治上無特殊意義,即使“遼東全部平定”為真,也不代表蒙古地區全部平定,不能說“中國再度統一”。因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根本在蒙古諸部,因為蒙古諸部是明的前政權,不平定蒙古諸部,很難說“中國再度統一”。
第四,“金山之役”后,北元和蒙古諸部仍在對明進行反攻,而明亦仍在對蒙古進行統一戰爭。如:1387年底,朱元璋以故元帝孫脫古思貼木兒“屢屢擾邊”,遣藍玉為大將軍攻之。藍玉率軍至捕魚兒海(今內蒙古呼盟巴爾虎左旗西南之貝爾湖),俘元皇次子地保奴(又作迪保努)及妃嬪公主百二十余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元君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及臣屬數十騎逃走,將依丞相耀珠于和林。[15]又如,1390年,朱元璋以元故丞相耀珠等尚為邊患,命晉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師北伐,并命傅友德率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率山西兵從晉王,受二王節制。又命齊王朱榑率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北伐。……傅友德、燕王出古北口,乃爾不花、耀珠等降。[16]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朱棣除派將進攻蒙古外,還五次親征。第一次:1410年,成祖經興和,過大伯顏山、小伯顏山,到清水源(即今內蒙馬塔八海子)一帶,敗本雅失里于斡難河;又經闊灤海子(今內蒙呼倫湖)敗阿魯臺。[17]第二次:1414年,成祖至飲馬河(今克魯倫河),前鋒劉江敗瓦刺兵于康哈里孩;到忽蘭忽失溫(今蒙古烏蘭巴托東附近),又敗瓦刺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部,窮追至圖拉河(今蒙古境內)。[18]第三次:1422年,成祖經雞哆山、云州、獨石、度偏嶺,至開平(今內蒙多倫),出應昌、威遠至沙琿原,將阿魯臺趕到漠北。[19]第四次:1423年,成祖至西陽河,聞阿魯臺遠遁,班師。[20]第五次:1424年,成祖至開平,阿魯臺又遠遁,在班師途中,崩于榆木川(今內蒙烏珠穆沁東南,多倫北)。[21]元(即北元與蒙古諸部)、明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沒有停止,怎么能說1387年的“金山之役”為“中國再度統一”的標志呢?
從以上的分折中可以看出,史學界所謂1368年“元朝滅亡”、1387年“中國再度統一”等說法,根據都不充分。可是,傳統至今,史學界都認為明代是一個“統一王朝”,并將其與元、清并列,稱“元——明——清”。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明到底重新統一了中國沒有?即明朝是不是一個“統一王朝”?另外,我們怎樣判定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王朝是 “統一王朝”,還是“不統一王朝”?也就是說,史學界判定“統一王朝”的標準是什么?
我們先看史學界關于判定“統一王朝”的標準問題。應當指出,傳統至今,史學界對中國古代“統一王朝”問題的判別,標準混亂,至少是雙重的。如他們判定秦為統一王朝,標準是秦“統一了六國”,掃除了中國領土上的割據勢力,恢復乃至擴大了前一統一王朝——西周的版圖;又如,他們判定元為“統一王朝”,標準是元不僅滅掉了當時中國領土上的各割據政權,如金、西夏、宋、大理等,還滅掉了他們的所有殘余勢力,恢復乃至擴大了前一個統一王朝——唐的版圖。然而,在判定明為“統一王朝”的問題上,史學界的標準顯然變了:不需要滅掉前一統一政權及其衰微后出現的各割據政權,也不需恢復前一統一政權的版圖。因為有明一代,明都沒有滅掉前一統一政權——元及其衰微后出現的各割據政權,也沒有恢復前一統一政權——元的版圖。
筆者認為,史學界對中國古代王朝是否為“統一王朝”,在判別標準上是錯誤的,即雙重標準要不得,是非理性史學。尤其是,對漢和對少數民族應一視同仁,不能有大漢史學民族主義之嫌。這里標準一定要統一,應具體為三點:1、要真正消滅了前政權包括當時的各割據政權;2、要恢復前一統一政權的疆土或至少要恢復前統一政權之前的那個統一政權的疆土;3、統一后要有一段和平期——哪怕是短時間的和平。用這三點來衡量,毋庸置疑,中國古代秦、西漢、東漢、西晉、隋、唐、元、清為“統一王朝”,而明則無論如何都不能算“統一王朝”。因此,筆者同史學界在明是否為“統一王朝”上的分歧,主要是標準的分歧。
這里還需申明幾點:第一,不能以宋為尺度來衡量明。有人認為,說宋朝不是“統一王朝”好理解,說明朝不是“統一王朝”恐怕難理解,明朝至少統一了漢族。誠然,明統一了漢族,宋未統一漢族,統一中國不能以統一或未統一漢族來論。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統一王朝”應是多民族的統一,不能只以漢族的統一為基準。
第二,不能用“基本統一”來代表“中國再度統一”。有人認為,明雖未恢復元的版圖,但已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如:朱元璋在將元順帝趕回上都后,命北伐軍西進,山西廓帖木兒北逃;北伐軍轉戰陜西,守將李思齊被迫投降;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命湯和等南下四川,降明升;明軍又由四川、湖廣西路進入云南,攻陷昆明,梁王自殺;至“金山之役”,明已基本上統一了所有漢族地區以及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地區。所以,說“中國再度統一”并不過分。其實,這種說法也欠妥。這里,統一就是統一,沒統一就是沒統一,“代表”和“基本統一”是不行的。必須承認:蒙古各政權都屬中國,都是中國的兄弟民族,剝奪他們的中國資格是不對的。文革當中鬧過個政治笑話:“全國河山一片紅”的郵票,上面沒有臺灣省,后被當成了有政治問題的錯票。當今的人為什么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因為我們的史學家們就經常大筆一揮,將漠北劃到了中國以外,用“基本統一”來代表“中國再度統一”,這是不對的。如果按這些史學家的觀點,我們今天可以不談統一臺灣,可以不談港、澳回歸,因為我們比明朝的“基本統一”還“基本統一”——沒有回歸中國的疆土遠比明朝少得多。這顯然是荒謬的。
第三,“蒙藩”的出現不能算“中國再度統一”。明在對北元包括蒙古各政權的戰爭中,雖然消滅了一些對抗性的蒙古政權,但更多的蒙古政權都成了明的藩國。如:《蒙古族簡史》說:“在一三六八年以后的二十年間,故元勢力和明朝之間發生了多次戰爭,經過戰爭,故元勢力大為削弱,遼東、漠南蒙古、甘肅和哈密地區處于明朝統治之下。明朝隨即在這里授官設治,先后建立福余、泰寧、朵顏(以上合稱兀良哈三衛)、察罕諾兒、東勝赤斤、哈密等蒙古衛所二十多處,其長官都督、指揮、千戶、百戶和鎮撫等,均由蒙古封建主充任,對哈密衛長官則授以忠順王的封號。這些蒙古封建主作為明朝的地方官吏統領各自的部眾。”[22]《簡明中國歷史》說:“明于永樂年間,封瓦刺部三個首領為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封韃靼部首領為和寧王使之成為明政府管轄下的地方長官。”[23]這里有個問題:就是“蒙藩”的出現,能否意味“中國再度統一”?筆者認為不能。藩國不是一個統一王國的一部分,藩國跟統一王國的關系是隸屬關系,不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關系。不過,現代的中國歷史著作都用“蒙藩”來說明明朝是“統一王朝”,他們都將蒙古諸部寫成明的蒙古族。這種做法欠妥。不要忘記:中國古代的漢族政權宋,曾是金的藩國,可是我們的史學家卻一直將宋作為中國的正統,而貶抑其宗主國金。如果用“蒙藩”來說明“中國再度統一”,那么,這在體例上又出現了問題。還不要忘記:在明朝以前,蒙古已是統一王國的一部分,現在僅僅是藩國,明與蒙古的關系顯然較前代退步了。而且,蒙古各藩與明的隸屬關系極不穩定,今天歸順,明日反叛,叛了又歸,歸了又叛,反反復復。有些藩國,歸順只為要拿好處——“歲幣”, 如《明史·外國傳八》載:“……炒花復合宰賽、暖兔以三萬騎入掠,至平虜、大寧。既求撫賞,許之。”當年“明朝為了對付努爾哈赤,便與蒙古察哈爾部長林丹汗相約,共同抵御后金。條件是增加明朝對林丹汗的歲幣;并將原由明朝直接給予漠南東部蒙古諸部的歲幣統統撤銷,轉交林丹汗控制。”[24]如果不給“歲幣”,蒙人不僅不愿做藩國,還要刀兵相見。如《明史·外國傳八》載:“ ……兔復擁眾至延綏紅水灘,乞增賞未遂,即縱掠塞外。”另外,“蒙藩”只是蒙古的一部分,不是蒙古的全部。如前所述,在元帝國衰微后,蒙古分化成了多個相對獨立的政權。雖然多數蒙古政權都活動在漠南,但有些則逃到了漠北——今蒙古及前蘇聯境內——當時這些地區都屬中國領土。明朝的北伐,事功最卓著者當是成祖朱棣,朱棣五次親征,其大軍前鋒最遠也只到過今蒙古境內的圖拉河北,再遠的地方,則從未到過。就是說,在漠北,仍有一定數量的蒙古政權,未接受明的統治。如《簡明中國歷史》也承認:“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貴族殘余勢力逃往塞外。”[25]
那么,我們今天應如何對明的歷史地位進行重新定位?筆者認為,明應定為中國歷史上的非“統一王朝”。就是說,明是與北方蒙古各政權并存的政權,只不過比他們大。因此,這一歷史時期應叫“元季朝北朝”,編制《中國歷史年代簡表》應是:
封
建
社
會
元 1276年——1368年①
元季南北朝
南朝:大明 1368年——1644年
北朝:北元等少數民族政權 1368年——1644年
清 1644年——1840年
注: ①1276年才是元朝統一中國之年。(20)
為什么要將明定位成“元季南北朝”之南朝大明呢?第一,這是實事求是的需要。從上面的分析中已知:元朝并未真正滅亡,明也并未真正統一中國——既未恢復元代的疆土,也未恢復元代之前的統一王朝——唐代的疆土。漠南、漠北的蒙古政權都屬中國的割據政權,明代遺老遺少編寫的《明史》,將蒙古諸部列入《外國傳》[27],這是完全錯誤的。蒙古從不認為他們是外國,他們一直在同明進行斗爭,明也一直試圖統一蒙古。蒙古編寫的《黃金史綱》,還胡說明朱棣皇帝是蒙古嗚哈圖噶之子,北京的明政權仍是元朝皇室后裔的延續,即事實上的蒙古政權。[28]由于與蒙古一直處于斗爭中,明的邊患不斷,從未有過真正的平安。
第二,明與北元包括蒙古諸部的南北對峙。明朝一方面在沿蒙一線大設衛、鎮進行屯防,另一方面,又在沿蒙一線大修邊墻(長城)。如《簡明中國歷史》說:“明朝為防止蒙古進擾,在遼東(遼寧遼陽)、宣府(河北宣化)、大同、榆林(延綏)、寧夏(銀川市)、甘肅(張掖)、薊州(河北遷西縣西北)、太原(偏關東北)、固原等‘九邊’重鎮屯駐重兵。又在沿邊重新修筑長城;成化(1465——1487年)年間,修筑東起清水營(陜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馬池(寧夏鹽池西)的西段長城。長城的修筑,加強了防衛能力。長城以北有明初建立的大寧衛(遼寧寧城縣西)、開平衛(內蒙古正藍東閃電河北岸),東勝衛(內蒙古托克托北)三個軍事重鎮,以統治長城以北的廣大地區。”[29]這是典型的南北朝格局!與蒙古對峙,耗費了明朝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
第三,蒙古諸部及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反明斗爭。蒙古一直擾邊,大小戰事連年不斷,最有名的戰役是“土木之役”。 如《簡明中國歷史》說:“1449年[正統十四年)七月也先舉兵自大同,宣化甘州、遼東四路攻明,英宗拒絕臣下的勸阻,在王振的挾持下倉促親征,明軍五十萬出居庸關,經懷來宣化抵大同這時前鋒已全軍覆沒明軍不得不退出大同南返,行至土木堡[河北懷來西南),為瓦刺軍擊潰,王振被殺,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30]另外,長城以北的其他少數民族也在反明,其中后來最有影響的是女真族的努爾哈赤,他多次打敗明軍,最后成了明的心腹之患。
第四,對蒙古諸部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應予充分肯定。傳統至今,史學界否認北朝存在的客觀性,不妥。要知道,北朝時期蒙古諸部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是整個中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當時社會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將北朝史提升到中國史的地位,即不是作為外國史或明史的補充來寫,才是科學的。北朝時期,無論是蒙古諸部,還是西域或女真諸部,當時的社會都有較大發展。如,蒙古的達顏汗,曾恢復汗權,一時重新統一蒙古各部,與明朝對抗;女真族的努爾哈赤,重建大金[后金,后又改稱清),不僅統一了女真,而且統一了北朝,以至后來入主中原,建立了統一的清王朝。
五、對明的歷史地位進行重新定位的意義
對明代的歷史地位進行重新定位,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它能使我們科學地認識明朝的真正歷史地位。我們必須明確:明朝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我們常說的“元——明——清”,欠妥。傳統至今,史學界講的1368年“元朝滅亡”與1387年“中國再度統一”,都子虛烏有。
第二,它能使我們公正地評價明史。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又一個(前一個是宋)極端專制的王朝,明朝的專制主要表現為:取消相權——設內閣,閣臣為皇帝的參謀;然后實行太監專制——有的太監如魏忠賢總攬朝綱、有的太監機構如東廠等就是特務組織,所有官員都得仰太監之鼻息等。明朝也是一個最腐敗的王朝,有些皇帝根本就不上朝辦公,整天淫樂于豹房或崇道設醮,等等。明朝還是一個最反動的政權,冤獄重重,荼毒忠良,如于謙、袁宗煥的慘死;同時,農民、士兵和工人以及少數民族起義不斷,等等。現在,史學界有人一直在大肆宣揚明朝如何“強盛”,明連中國都未統一,究竟“強盛”在哪?
第三,它能使我們徹底地清算史學領域的大漢史學之弊端。長期以來,史學領域被漢族人壟斷,無論是史學觀,還是史學文獻,均出自漢族之手。宋、明以來,漢族的史學觀基本是公羊筆法,即將漢族政權寫成正統,將少數民族寫成漢人的尾巴;而且在敘事中,也是側重漢人,忽略少數民族。明史尤為如此。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欠妥。我們應從重新定位明朝的歷史地位入手,客觀地記敘和評價少數民族在中國古代的歷史地位及作用,正確對待歷史。這樣,才更有利于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
[1]武漢師范學院歷史系《簡明中外歷史詞典》編寫組.簡明中外歷史詞典[Z].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403.
[2][6][9][11][23][25][29][30]《簡明中國古代史》編寫組.簡明中國古代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386、51-352、546-547、386-387、397、397、397、403.
[3][13][14]明通鑒:第1、9、9卷[M].改革出版社,1994.
[4][10]續資治通鑒:第220、182卷[M]. 改革出版社,1995.
[5][12][15][16][17][18][19][20][21]張習孔等.《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4卷[Z] .北京出版社,1987.261、296、297、299、340、347、359、360、361.
[8]新華字典[Z].商務印書館,1957.644.
[7][28]朱風、賈敬顏.漢譯蒙古黃金史綱[M] .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53頁注③、46-50.
[22][24]《蒙古族簡史》編寫組.蒙古族簡史[M]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37、48.
[26]孫景壇.關于宋代的歷史定位及總體評估新探[J] .南京社會科學,2004,(8).
[27]明史:第326-327卷[M] .岳麓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