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明代的州縣吏治
佚名
摘 要:明代州縣處于官僚和社會夾擊的兩難境地,是吏治腐敗的滋生溫床。國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誘導(dǎo),使催科賦稅虐民過甚;饋送賄賂和過客索要,成為填不滿的黑洞;進(jìn)士舉監(jiān)分途,對州縣吏治消極影響極大;獄訟的黑暗和吏胥鄉(xiāng)官生員對政務(wù)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嚴(yán)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縣的殘暴和貪賄。
關(guān)鍵詞:明代;州縣;吏治
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縣為界,上下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州縣以上,其政治形態(tài)為官僚政治,有著一套以典章制度為規(guī)范的行為準(zhǔn)則,而在州縣以下,其政治形態(tài)為鄉(xiāng)紳政治,有著一套以人情關(guān)系為規(guī)范的行為準(zhǔn)則。州縣為這兩種規(guī)范的結(jié)合點(diǎn),其矛盾尤為突出。中國的封建社會發(fā)展到明代,州縣的吏治產(chǎn)生了極大問題。明代的腐敗,首先是州縣以下直至鄉(xiāng)里的官吏腐敗,直接危害社會,引發(fā)了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導(dǎo)致了明朝的敗亡。而州縣腐敗的癥結(jié),就在官僚政治和鄉(xiāng)紳政治的銜接上。
州縣實(shí)為國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縣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員問題,是明代政治的重大問題,而史學(xué)界以往多有忽視。論及明朝的政治問題,多著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實(shí)際上,皇帝專權(quán),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轄六部,以及宦官專政等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卻不可能立即引起民變。而州縣吏治卻與老百姓息息相關(guān),值得引起史學(xué)界的高度重視。
一、州縣守令的兩難處境
明代的知州(俗稱太守)知縣(俗稱縣令)在整個(gè)國家的官僚體系中十分特殊。他們處于官僚體制和基層社會接壤的邊緣,在整個(gè)官吏隊(duì)伍中屬于外圍,離決策中樞較遠(yuǎn),因而除了個(gè)別時(shí)期外,通常得不到權(quán)力中心的重視。但他們所在的基層政府,又是整個(gè)王朝大廈的支撐者,承擔(dān)著負(fù)載上層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視州縣建制的職能。對州縣守令的輕視和對州縣建制的重視,使守令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作為州縣長官,一方面是遠(yuǎn)離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職責(zé)的繁重和壓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層社會,深知州縣的難處及其對穩(wěn)定政治統(tǒng)治的重要,極重守令之選。但好景不長,從立國到仁宣之時(shí),制度初立,已有內(nèi)重外輕的跡象,當(dāng)官者視州縣為畏途,為宦者視京師為要津。由于明初以嚴(yán)刑治官,使內(nèi)重外輕的弊端不過于顯,吏治尚稱循良,不過,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師和中央,已經(jīng)留下了產(chǎn)生問題的空隙。弘治以后為了強(qiáng)調(diào)地方親民官的重要性,規(guī)定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拜禮,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職,但其調(diào)節(jié)內(nèi)外關(guān)系的著眼點(diǎn),局限在官僚體制內(nèi)部的上下關(guān)系上,而對政府與社會的官民關(guān)系缺乏足夠的重視。而正統(tǒng)至弘治,盡管朝廷越來越重視地方親民官的職司,但主要考慮其對國家財(cái)政的供應(yīng)能力,州縣官員的職責(zé)轉(zhuǎn)向催科為主,且受多方牽制,為政不易,吏俗漸猾。正德以后,嘉靖、萬歷時(shí)期,州縣不僅不復(fù)撫恤鄉(xiāng)里,反而變本加厲,盤剝地方。州縣守令上有督撫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鄉(xiāng)宦、生員、胥吏把持地方,州縣難作,動輒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壞,終于激起民變。明末農(nóng)民大起義,小半出自天災(zāi),大半出自人禍。以往史學(xué)界所重視的宦官專政問題,黨爭問題,主要影響上層,進(jìn)而波及吏治,與社會底層并無直接聯(lián)系。而州縣吏治敗壞,則是釀成社會動蕩的直接原因。
天啟年間的禮部尚書趙南星,列舉了當(dāng)時(shí)政治“四害”,其中兩害就在州縣,其余兩害也與州縣間接相關(guān)。“救時(shí)要?jiǎng)?wù)事,除四害為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jìn)之害,而曰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鄉(xiāng)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療矣”(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臣處閭閻三十年,習(xí)見有司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為盜”,“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縣之內(nèi)”(《明經(jīng)世文編》卷459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本來,從宋以后到明代,州縣衙門都立有戒石,銘文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但百姓卻將其改為:“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zhuǎn)吃轉(zhuǎn)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趙翼《陔余叢考》卷27《戒石銘》)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殺”,“迎闖王,不納糧”,立即從基層動搖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優(yōu)劣,必須重視其州縣問題。
由于身處兩難之地,明代的守令難當(dāng)。其繁難程度,可從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見到一斑。萬歷二十三年,二十七歲的袁宏道出任吳縣知縣。作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體會到了知縣的苦辛。他在給友人丘長孺的信中說:“弟作令,備極丑態(tài),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對上司就像奴仆,對過客就像妓女,管錢糧就像賬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縣難當(dāng)?shù)纳駪B(tài),躍然紙上。更麻煩的是,知縣面對的,不是習(xí)文知禮的鴻儒,而是目不識丁的愚民,與他們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處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對者,鶉衣百結(jié)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虱滿身之囚徒耳。”而事務(wù)之繁忙,處斷之艱難,更是躋進(jìn)官僚集團(tuán)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給同為知縣的朋友楊廷筠的信中道:“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xiàng)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在給好友沈鳳翔的信中也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吳令,則苦萬萬倍,直牛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谷如海。朝夕趨承檢點(diǎn),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qiáng)精神,錢谷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也,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fēng)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均見《袁中郎全集》,香港,廣智書局)顯然,年輕氣盛的袁中郎,書生氣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復(fù)雜的縣政看得太簡單了。在躬身實(shí)踐中,才識得箇中愁滋味。
在上下夾擊之中,州縣只得上結(jié)長官,下虐小民,成為吏治腐敗的滋生溫床。到明代中葉以后,州縣的腐敗已經(jīng)達(dá)到“普及”程度,從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貪賄者蟻聚蜂集,成為政治痼疾,無藥可救,終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敗的表現(xiàn)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饋送、仕進(jìn)分途、獄訟、胥吏鄉(xiāng)官干政等方面。 二、賦稅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務(wù),保證正常賦稅亦無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卻演變成了害民之政。從明朝全盛時(shí)期的宣德年間開始,上解稅糧就已經(jīng)成為地方官吏考課的“硬指標(biāo)”。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者,所欠稅糧,立限追征。九年考滿,任內(nèi)錢糧完足,方許給由。”(《萬歷會典》卷12《考核一》)成化起,凡受災(zāi)地區(qū),納糧即可在三年大計(jì)時(shí)免除朝覲。“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選完須知功績牌冊,并通關(guān)差人繳部而已。”(黃榆《雙槐歲鈔》卷1《給由賑濟(jì)》)從此開始,考課地方官吏實(shí)際不再重視教化撫治,唯以催科為事。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員三六年考滿,務(wù)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但有錢糧未完者,不許給由。”(《萬歷會典》卷12《考核一》)。嘉靖時(shí),也有同樣規(guī)定。“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yán)核任內(nèi)租稅,征解足數(shù),方許給由交代。”(《明史》卷78《食貨二》)萬歷時(shí)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贊譽(yù),但卻忽視了其副作用。考成法開了“帶征”的先例,即除完成當(dāng)年錢糧外,還要帶征隆慶以來拖欠賦額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則處以降罰。對這種惟以催科為務(wù)的作法,也有一些官員痛責(zé)其弊。如萬歷時(shí)戶科給事中蕭彥就曾奏請道:“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為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歷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fù)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撲。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并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賜也。”(《明史》卷227《蕭彥傳》)但是,這種批評并未得到執(zhí)政者的重視。崇禎時(shí),要求科道官必須從地方州縣官中行取,同時(shí)又規(guī)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選科道。“時(shí)有令,有司征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后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于是(熊)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并貶二秩調(diào)外。”(《明史》卷258《熊開元傳》)史謂“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矣。”(《明史紀(jì)事本末》卷72)
在種種壓力下,州縣官吏的職責(zé),惟以催科為要。“日夜從事,惟急催科”。所謂教化,所謂賑濟(jì),所謂安民,所謂恤獄,全部被擱置一旁。嘉靖時(shí)顧鼎臣上疏稱催科之弊曰:“有司不復(fù)比較經(jīng)催里甲負(fù)糧人戶,但立限敲撲糧長,令下鄉(xiāng)追征。豪強(qiáng)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chǎn)補(bǔ)納。至或舊役侵欠,責(zé)償新僉,一人逋負(fù),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幾數(shù)百人。且往時(shí),每區(qū)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shí)收掌管糧之?dāng)?shù)少,而科斂打點(diǎn)使用年例之?dāng)?shù)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chǎn),害莫大焉。”隆慶時(shí)吏科給事中賈三近曾上疏道:“今廟堂之令不信于郡縣,郡縣之齡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jì)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fèi),雖欲損毫厘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jiān)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yǎng)之心漸移于苛察,撫字之念日奪于征輸,民安得不困。”(《明史》卷227《賈三近傳》)至于萬歷時(shí)的考成帶征,其弊尤大。“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征,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征折色矣。”(《明史》卷78《食貨二》)本色的折算,又由官府任意為之,極大加重了民眾的負(fù)擔(dān)。親歷帶征的李樂直言道:“天下極冤最枉之事,莫如帶征錢糧一節(jié)。凡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nèi)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責(zé)備后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著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歷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歷四五年也要兼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個(gè)百姓,百姓只有這些皮膚,前面太寬,后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李樂《見聞雜記》卷2)
州縣的催科,一方面是國家政策和官員考課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稅制下經(jīng)手官吏有利可圖。如上引顧鼎臣疏所言:“其實(shí)收掌管糧之?dāng)?shù)少,而科斂打點(diǎn)使用年例之?dāng)?shù)多”。只有通過催科,官吏自己才能從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澀。因此,催科不僅有來自上面的壓力,還有來自自身的動力。明代晚期,如海瑞一般可廉己自律者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shù),而算計(jì)仕宦收入者則比比皆是,遍及州縣。正如高攀龍所言:“矻矻然朝夕之所望,與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過多得金錢。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裝已可耀妻兒,了無悔憾。而民之視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驅(qū)出其里,亟須臾以為快。”(《高子遺書》卷9《送陳二尹序》)州縣正官如此,佐貳首領(lǐng)雜職更是如此。“今佐領(lǐng)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撲,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2《鼓舞士氣安民生疏》)地方官在京待選,多方打點(diǎn),往往淹滯數(shù)年,資用乏絕,常有借貸。等到授職,焉有不大撈一把之理?特別是出任邊遠(yuǎn)地區(qū)的地方官,多有瑕疵,升遷無望,更是以搜刮為事。邊遠(yuǎn)之官,“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yuǎn)處無能之輩,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日知錄》卷8《選補(bǔ)》) 三、饋送和過客招待造成的額外負(fù)擔(dān)
州縣的上司之多,監(jiān)控之嚴(yán),不僅導(dǎo)致州縣動輒掣肘,而且導(dǎo)致州縣饋送之弊。凡任州縣者,不饋送就無法做官。饋送的對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質(zhì)的巡按督撫,三是過往客人,四是京司。晚明李樂談到地方上送禮行賄時(shí)說:“公等但見郡縣官受賄至四五百金遂目為貪官,這眼眶太小了。我在廣中,見取珠送要地者,巨細(xì)不等,中有如豆之大者,以斗計(jì)不以升計(jì),又非一次而止。”(李樂《見聞雜記》卷5)可見饋送賄賂之嚴(yán)重。
知府是州縣的直接上司,因此,也是州縣送禮的首要機(jī)構(gòu)。海瑞稱:“縣百事統(tǒng)于府,舊例,小有故必參謁。”即使清如海瑞,在他任淳按知縣時(shí),一分一厘的算計(jì),在朝覲之年也要科派二百四十兩銀子作為饋送之用,其中九十兩就用于府衙(《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吏屬》)布按二司也同府衙相仿,是州縣的主要饋贈對象。
督撫巡按之饋送,更是不能少的。永樂時(shí),就有人指出這類饋送問題。“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yǎng)活之計(jì),誅求責(zé)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yīng)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yīng),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驟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fēng)應(yīng)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忌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fēng),恬不為怪。”(《明經(jīng)世文編》卷21鄒緝《奉天殿災(zāi)疏》)巡按御史考察地方,有舉有劾,被舉者則有謝薦之金,或百或千,其數(shù)不等,而且自稱門生。隆慶時(shí)僉都御史管志道曰:“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jīng)保薦,則終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門生。有以厚帛相酬者,是以寧負(fù)朝廷,不負(fù)舉主也。”(《明經(jīng)世文編》卷399管志道《直陳緊切重大機(jī)務(wù)疏》)萬歷十一年,左副都御史丘橓一上任就疏陳八弊,即考績、請讬、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教職、饋遺。幾乎全部與督撫御史巡按州縣有關(guān),而且多數(shù)都涉及到饋贈送禮。其中談到巡按舉薦時(shí)說:“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dú)冒為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yáng)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于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dú)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明史》卷226《丘橓傳》)崇禎時(shí),一名御史遣差巡按一次,所獲饋遺謝薦就多達(dá)二三萬兩,可見饋送問題多么嚴(yán)重。
過往客人涉及面廣,情況多樣,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貴子弟經(jīng)過,還有中官派遣,故舊私訪。因此,驛傳供給費(fèi)用以及地方衙門招待費(fèi)用成為州縣的一大開支。明初,這一現(xiàn)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往常布政司及諸有司,但聞是朝廷差遣人員,不問有無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軍遣行,各衛(wèi)勾軍,如此數(shù)等不辨,一概阿從。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貴賤,所到衙門,徑由中道,直入公廳,口出非言。諸司阿奉,略不奏聞。布政司聽六部囑,府州縣聽布政司囑,州縣聽府囑,縣聽州囑。”(《大誥續(xù)編·妄立干辦等名第十二》)崇禎時(shí)御史毛羽健曾陳言驛遞之弊道:“兵部勘合有發(fā)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bǔ)數(shù)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明史》卷258《毛羽健傳》)海瑞在對待過往客人上之嚴(yán)格是出了名的。總督胡宗憲之子過淳安,辱驛吏,遭海瑞嚴(yán)懲;都御史鄢懋卿路過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時(shí)至今日,史界還對其剛直贊譽(yù)不絕。但就是海瑞,也承認(rèn)招待過往客人的重要性,言及州縣重過客的原因說:“寧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寧可薄下,不可不厚于過往。”“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于上;過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輒顛倒是非,謗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為之也。”(《海瑞集》上編《淳安縣政事序》)
至于京司,州縣主要是在三年朝覲之時(shí)需要饋送賄賂。海瑞曾感嘆道:“朝覲之年,為京官收租之年。”需要說明者,向京司饋遺,以督撫藩臬為主,州縣與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撫藩臬所饋,無一不是出自州縣。仁宣之世,號稱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饋贈為其收入的重要來源,其后可知。于謙巡撫山西,曾以手帕線香等地方特產(chǎn)抵制饋贈金銀,可見其普遍。地方官員饋送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是饋送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請承行吏胥,奉數(shù)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駁。”(《明經(jīng)世文編》卷185霍韜《第三札》)特別是戶部吏員,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萬歷以后,地方賦稅全操于戶部吏員之手。“時(shí)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手為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時(shí)謠言有‘違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誚。”(李清《三垣筆記·上·崇禎》)賄賂與胥吏政治相結(jié)合,使政治益發(fā)黑暗。 四、仕進(jìn)分途對州縣吏治的影響
明代仕途大勢,內(nèi)重外輕,士人特別是進(jìn)士對州縣官職不屑一顧,致使州縣官吏多不得人。永樂以后,隨著科舉制的完善,州縣官員,不是進(jìn)士,就是舉監(jiān)。但就知縣來說,以舉監(jiān)居多,佐貳則雜用舉監(jiān)和吏員。萬歷年間曾任宛平知縣的沈榜,列舉了永樂到萬歷十八年宛平縣二十四任知縣,其中二十二人為舉人,一人為歲貢,一人為官生;四十六任縣丞,貢監(jiān)四十人,舉人一人,吏員三人,主簿升一人,余一人不詳;主簿十九任,貢監(jiān)十一人,吏員四人,余四人不詳;典史十七任,吏員十六人,余一人不詳。宛平為地位非同一般的京縣,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縣,則基本是舉監(jiān)之職無疑。而明代舉人和進(jìn)士在仕途上差別極大,對地方政治有著重要影響。“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yuǎn)簡小之缺。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jìn)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云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趙翼《陔余叢考》卷18《有明進(jìn)士之重》)舉貢與進(jìn)士,判若天涯。進(jìn)士即使擔(dān)任同知、通判或知縣,也視為過渡臺階,而不以政事為意。
進(jìn)士和舉監(jiān)分途,使地方政治深受其害。隆慶時(shí)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天啟時(shí)吏部尚書趙南星,都曾從官吏考察升遷的角度指出過這種危害。賈三近說:“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xiāng)舉。同一寬也,在進(jìn)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yán)也,在進(jìn)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jìn)。”(《明史》卷227《賈三近傳》)趙南星稱:“各處司道進(jìn)表官至,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xiāng)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為,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只堪覆瓿。吏治之虛偽如此,小民何由得安?今甲科之途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其中又有鄉(xiāng)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鄉(xiāng)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tài),巧立于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又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quán)豪之所囑讬,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jī)術(shù)鋒俠足以起風(fēng)濤、成斗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以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為不肖者甚少。”這種以科甲論優(yōu)劣虛偽考察,是地方上省府州縣“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2《朝覲合行事宜疏》)。崇禎時(shí),為了改變這種只重甲科、不重舉貢的風(fēng)氣,曾下令從州縣行取科道,不分進(jìn)士舉監(jiān)一體考選,本意不錯(cuò),但一執(zhí)行卻只是加劇了催科弊政。崇禎時(shí)吏科給事中李清道:“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jīng)竟絕跡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經(jīng),無人不催科,正餉雜項(xiàng),無一不考成。其實(shí)甲科初選,半系腴壤,間補(bǔ)瘠邑,不久輒調(diào)。若乙榜明經(jīng),大約瘠邑多于腴壤。以錢糧難完之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三垣筆記·上·崇禎》)
在內(nèi)重外輕的局勢下,萬歷以后,知縣乃重。但只是進(jìn)士以其為登身之階而重,以其能交接關(guān)系而重,以其能搜刮錢財(cái)而重,而舉監(jiān)之輕如故。不但于地方政局無補(bǔ),而且有害。“如程篁墩之言,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以第三甲進(jìn)士為之。然久襲重內(nèi)輕外之說,自任其勞,受人之脞,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羅一峰之言曰:人中進(jìn)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鹓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dāng)時(shí)邑令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驟重,而就中邑令,尤為人所樂就。蓋宦橐之入,可以結(jié)交要路,取譽(yù)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墻桃李,各樹強(qiáng)援。三年奏最,上臺即以兩衙門待之,反祈他日之陶鑄。而二甲之為主事者,積資待次,不過兩司郡守,方折腰手版,仰視臺省如在霄漢。其清華一路,惟有改調(diào)銓曹,然必深締臺省之歡,游揚(yáng)擠奪,始得入手。而三甲進(jìn)士,綰墨綬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羨,亦可以觀世變矣。”(《萬歷野獲編》卷22《邑令輕重》)顯然,嘉靖、萬歷以后的進(jìn)士謀任知縣,志在行取科道,而不在撫治一方,著眼其宦橐所入,而不著眼其為民興利,看重其門生黨援,而不看重其舉賢貢士。至崇禎時(shí),其弊更顯。新科進(jìn)士初任知縣,“受任時(shí),竟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甲申朝事小記》初編,陳啟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 五、獄訟的黑暗
刑名獄訟是州縣常事,按照明制,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逐級陳告,越級即為違制。徒流以下,府州縣即可決斷,徒流以上,府州縣審判后解部定案。而明代州縣獄訟,往往操之于吏書之手,為其生財(cái)捷徑。海瑞曾言,民間俗語有“種肥田不如打瘦官司”(《海瑞集》上編《示府縣嚴(yán)治刁訟》)。刑獄生財(cái)之道主要為刁難、滯獄、重刑和指攀富戶。從州縣長官到吏員胥役,借刑獄刁難百姓均是拿手好戲。“一詞才入,非銀數(shù)錢,不差人。及至問詞,大約官須五六錢,書手二三錢為例,實(shí)情稍大者賄及二三兩。”“刁民大戶,獄逞豪勢,以酒食結(jié)納,授詞凌虐。此官在鎮(zhèn)一日,官與積書、弓兵非日八十兩不充其欲,一年不下七八百金。”(李樂《見聞雜記》卷10)永樂時(shí),已有滯獄現(xiàn)象。“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正統(tǒng)時(shí),評事馬豫述指攀富戶之弊:“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強(qiáng)盜,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bào),死傷者甚多。”嘉靖時(shí),給事中周瑯說滯獄索賄之狀道:“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系,案無新故,動引歲時(shí)。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況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獄為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徙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均見《明史》卷94《刑法二》)林烴為知州,斷案迅速,獄無拘滯,得到了“林一升”的贊譽(yù),謂其審案無羈候之苦,只費(fèi)米一升。然而卻使其屬下吏員皂隸大失所望(見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
州縣正官,由于不能盡悉事例,辦案只好憑良心。海瑞就曾把獄訟分為“爭產(chǎn)業(yè)”和“爭言貌”兩類,按照“鄉(xiāng)宦小民有貴賤之別”的原則區(qū)別對待。事在爭產(chǎn)業(yè),“與其屈小民,寧屈鄉(xiāng)宦,以救時(shí)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xiāng)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刑屬》)。海瑞尚有幾分憫民之心,遇上只算計(jì)宦橐所入而不顧小民死活的官員,則同吏書上下起手,以飽私囊。更有一等糊涂官員,則糊涂辦案。萬歷時(shí),李樂曾目睹烏程知縣餓死罪囚的辦案方法。“余為舉人時(shí),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余答曰甚多,現(xiàn)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五日,蔣令獄禁絕其食而死。”(李樂《見聞雜記》卷8)
六、吏胥、鄉(xiāng)官、保甲和生員對地方政務(wù)的干涉
明代州縣正式官員極少,屬州與縣衙,其職官最多不過四人,政務(wù)主要靠吏員辦理。清人稱:“官治之實(shí),皆吏治之耳”。吏“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手”(阮葵生《茶余客話》卷7《吏之重要》)。“郡邑庫藏,往往不明,而官亦受其累。蓋緣初至,為吏所欺,衙內(nèi)費(fèi)數(shù)皆取辦,且有受其饋遺者。久之,官長短反為吏把持,噤莫敢出聲。”(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有的吏員,不但從政務(wù)上控制州縣長官,而且還靠發(fā)其陰私來脅迫長官。“能持人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即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蛇蝎。”(《萬歷野獲編》卷11《異途任用》)吏員之下,又有胥役。吏胥之弊,在明代成為一個(gè)老大難問題。
州縣衙門,一般有承發(fā)房管理文書,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對口處理政務(wù)。承發(fā)房和六房,都由吏員管理。胥役則從當(dāng)?shù)丶{糧二石以上三石以下的民戶中差點(diǎn),充任祗候、禁子、弓兵、捕快、門子等。據(jù)沈榜《宛署雜記》載,宛平縣吏員為三十八人,分充各房。官不諳政事,只有靠吏。“儒官初任,政未諳練,拱手仰成,以吏為師。吏滿三年,金箱玉囊,動盈千數(shù)。”(《明經(jīng)世文編》卷185霍韜《第三札》)州縣吏員十倍于官,而胥役又十倍于吏,吏員尚有微俸,胥役則完全自理,惟有敲剝民眾。致使食利于官府者為數(shù)眾多。明末李樂言此道:“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安然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痛惜,一大害也。”(李樂《見聞雜記》卷5)顧炎武曾指出:“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shù)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日知錄》卷8《胥吏》)
正因?yàn)槔魡T胥役有來錢之路,故充當(dāng)吏員胥役要出錢買,謂之“頂頭銀”或“頂首銀”。州縣之吏,頂頭銀各有例價(jià),據(jù)海瑞所列,縣吏頂首銀為:吏房十兩,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承發(fā)房各五十兩,胥役中的鋪長、書手、皂隸、門子,頂首銀低于吏員,各有差等(見《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吏屬》)。萬歷間林烴任知州,裁撤了吏員檢驗(yàn)稅銀成色的鍛爐,遭到吏員“叩頭固爭”,硬行裁撤后,吏員“怏怏不樂曰:吾輩其餒死矣”(林烴《林氏雜記·宦游記》)明末朱國楨曾說:“書算一涂,最為弊藪。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jì)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此輩積數(shù)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duì)窟B,而戶工部特甚。”(朱國楨《涌幢小品》卷11《禁入試》)
明代晚期,地方長官為了駕馭吏胥,掌握政務(wù),又逐漸興起了文友幕賓。萬歷年間,李樂任淦令,“家人以其不諳政務(wù),請一老主文同行”。李樂亦自稱:“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見聞雜記》卷8)。這種文友,遂成為清代幕賓的前身。
州縣境內(nèi)有居鄉(xiāng)閑退致仕之官,亦成一弊,人稱鄉(xiāng)宦、鄉(xiāng)官。清代趙翼論鄉(xiāng)宦之害道:“前明一代風(fēng)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xiāng)者,亦多倚勢恃強(qiáng),視細(xì)民為弱肉,上下相護(hù),民無所控訴也。”(《廿二史札記》卷34《明鄉(xiāng)官虐民之害》)
各州縣的保甲糧長制度,使得地方上催科之害,吏胥之弊,獄訟之苛,鄉(xiāng)宦之霸,與土豪士紳結(jié)合為一體。縣下十戶為一甲,設(shè)甲首一人,一百一十戶為里,設(shè)里長一人。糧長則負(fù)責(zé)催科,里甲則負(fù)責(zé)聯(lián)保治安調(diào)停訟毆。里甲糧長交結(jié)鄉(xiāng)宦,包攬獄訟,與吏員胥役內(nèi)外勾結(jié),表里為奸,形成了一種龐大的社會勢力。州縣正官,清者斂手,貪者肆虐,遂使明代的地方政治積重難返。
另外,各州縣學(xué)校的生員,也對地方有著重大影響。顧炎武有《生員論》,極言生員之弊。稱:“天下病民者有三,曰鄉(xiāng)宦,曰生員,曰吏胥。”甚至說:“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xí)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xiāng)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為大患。”
綜上所述,明代的州縣吏治,對封建統(tǒng)治的穩(wěn)定起了極大的負(fù)面影響。明朝之亡,根源實(shí)在于州縣的殘暴和貪賄,此不可不為治史者鑒。滿族入關(guān)后,之所以能夠維持?jǐn)?shù)百年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攤丁入畝、耗羨歸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催科之弊和饋遺之弊,并通過京官與外官的交流,部分解決了仕進(jìn)分途之弊,還對吏胥進(jìn)行了整頓,鄉(xiāng)官、生員干政問題也得到了較好的克服。當(dāng)然,清朝有清朝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依然照舊,特別是幕僚形成制度,分掌錢糧與刑名,與吏胥結(jié)合為一體,使其弊端成為無法克服之痼疾,獄訟的黑暗亦不亞于明朝。但是,畢竟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對明朝遺留下來的州縣弊政進(jìn)行了一些改良。因此,雖然清承明制,但在州縣吏治問題上還是有區(qū)別的,所以盡管清朝有比李自成、張獻(xiàn)忠更為兇猛的太平天國起義,但畢竟沒有亡在農(nóng)民手里而是亡在西方列強(qiáng)手里。弄清這一點(diǎn),有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rèn)識明清制度的同異。



業(yè)科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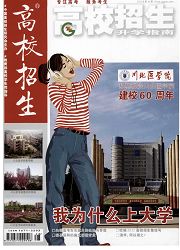
院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