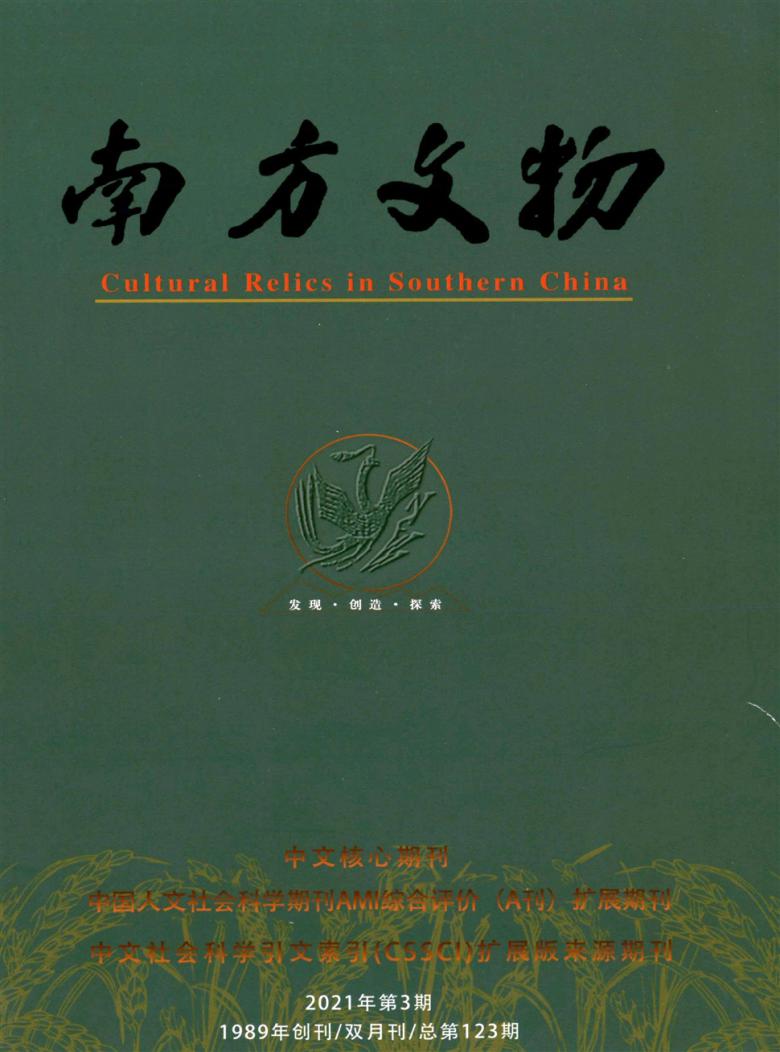清代學者焦循獨特的易學構架
楊 效 雷
關鍵詞:焦循;易學;象數;義理;聲訓
A particular I Ching learning structure established by JIAO Xun of 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textual research on JIAO Xun's theories of Pangto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mpletely opposite hexagrams), Xiangcuo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exagram and its inversion), and Shixing (conducting with time). Basing on th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at first, i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JIAO Xun's regarding the 64 hexagrams of Zhouyi as a interrelated, everchanging, dynamic system departing from views of universality of inter re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lines of a hexagram, than studying a hexagram or a line in isolation. Secon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O Xun's particular I Ching learning structure is based on textual research with objective analysis. So, it is not advisable to negate it arbitrarily. Thirdly, JIAO Xun's I Ching learning does not base merely on images and numbers, but take advantage of them as a carrier to elaborate his political ideal with Confucian virtues and self cultivation. At last, it is worthy of discussing on whether i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or not to acoustically explai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2 or more hexagrams by JIAO Xun, yet, it is regretful that his acoustic explanation lacks of adequate documentary prop.
Key words: JIAO Xun; I Ching learning; image-number;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acoustic explanations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經學家,“于學無所不通,于經無所不治”[1](卷六),尤以對《周易》用力最勤,成就也最為卓著。焦循提出的獨特的易學構架問世以后,在易學界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波。褒揚者稱其“石破天驚”“鑿破混沌”(王引之、阮元、梁啟超等持此說。),貶斥者則譏其“附會難通”“支離破碎”,乃至于全盤否定。(尚秉和、李鏡池、高亨等持此說。)筆者仔細研讀了焦循的易學論著。在對其易著的研讀過程中,筆者逐漸形成了一些認識。現將這些認識提出,以就正于方家。
一
焦循在《易圖略·敘目》中說:“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恒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為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后知比例之義出于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為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為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后知變化之道出于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于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于全《易》,覺經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實測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夫祖沖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為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2](卷首)
由上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1以旁通、相錯、時行三說通釋《周易》,是焦循所構建的獨特的易學框架;2此構架不是出于焦循的主觀臆測,而是通過十余年對《周易》的“實測”、歸納所得;3焦循對此構架非常自信,認為只有此構架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并將此構架比之于“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希望后人“益加密焉”。以下我們就具體考述焦循的旁通、相錯、時行三說。
(一) 旁通
關于“旁通”,阮元在《通儒揚州焦君傳》中說:“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3](卷首)焦循在《易圖略》中說:“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初必之四,二必之五,三必之上,各有偶也。初不之四,二不之五,三不之上,而別有所之,則交非其偶也。”[2](卷一)
根據以上兩段引文,我們可以對焦氏“旁通”做出如下表述:1.焦氏“旁通”與三國陸績、虞翻等人的“旁通”名雖同而實相異。2.焦氏“旁通”,簡而言之,即陰陽爻互易,具體包括一卦自身的陰陽爻互易和兩卦之間的陰陽爻互易。3.是否旁通互易取決于是否當位。當位之爻不動,不當位之爻方與他爻旁通互易。4.旁通互易的原則是初爻與四爻互易、二爻與五爻互易、三爻與上爻互易。5.旁通互易的目的是使不當位之爻當位。
為了說明“旁通”是《周易》作者之本意,而非焦循自己的杜撰,焦循在《易圖略》中列舉了三十個例證,并在三十例證后說:“《易》之系詞全主旁通,略舉此三十證以例其余。”[2](卷一)通觀焦循所列之三十例證,不乏說服力,即使不正確,起碼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后世學者譏之為“附會難通”“支離破碎”以至于全盤否定,無乃太過。為節省篇幅,以下僅從焦循所舉三十例證中摘取數例以說明之:
1.《周易》同人卦九五爻辭:“同人,先號啕而后笑,大師克,相遇。”《周易·象》:“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焦循認為其中的“師”由師卦而來。同人卦九五爻辭之所以言“師”,是由于同人卦九四爻與師卦初六爻旁通互易的緣故。他說:“若非師與同人旁通,則師之相克、師之相遇與同人何涉?”
2.《周易》艮卦六二爻辭:“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周易·象》:“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焦循認為其中的“隨”由隨卦而來。艮卦六二爻辭之所以言“隨”,是由于艮卦六五爻與兌卦九二爻旁通互易后,兌卦變成了隨卦。他說:“兌二之艮五,兌成隨。……若非艮兌旁通,則‘不拯其隨’之義不可得而明。”
3.《周易》小畜卦卦辭:“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卦六五爻辭:“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焦循認為,“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所以復見于小畜卦和小過卦,是由于小畜卦上九爻與豫卦六三爻旁通互易后,豫卦變成了小過卦。他說:“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辭又見于小過六五。小畜上之豫三,則豫成小過。……解者不知旁通之義,則一‘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
4.《周易·雜卦》:“大過,顛也。”《周易》頤卦六二爻辭:“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兇。”六四爻辭:“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焦循認為,大過為顛,但“顛”不見于大過卦,卻屢見于頤卦,這是由于大過卦九二爻與頤卦六五爻旁通互易的緣故。他說:“《雜卦傳》‘大過,顛也’,而大過經文不稱‘顛’,頤六二、六四兩稱‘顛’,……非大過與頤旁通,何以經之‘顛’在頤,而傳之‘顛’在大過?”[2](卷一)(文中所舉之第一例、第二例亦為原焦循所舉三十例證中的第一例和第二例,文中所舉之第三例為原焦循所舉三十例證中的第十六例,文中所舉之第四例為原焦循所舉三十例證中的第十九例。)
(二) 相錯
相錯指組成兩個別卦(六爻卦)的經卦(三爻卦)重新交錯組合成另外兩個別卦。如:困卦上卦為兌,下卦為坎;賁卦上卦為艮,下卦為離。困卦之下卦坎與賁卦之上卦艮交錯組合為蒙卦,困卦之上卦兌與賁卦之下卦離交錯組合為革卦。按焦氏“相錯”說,則“蒙、革為困、賁之相錯”。 [2](卷四)
焦氏“相錯”具體而言,可分以下四種情況:1.兩旁通卦之相錯。如,乾卦的上卦與坤卦的下卦錯為否卦,乾卦的下卦與坤卦的上卦錯為泰卦。2.兩旁通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形成的兩新卦之相錯。如,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同人卦,坤卦變成了比卦,同人卦的上卦乾與比卦的下卦坤錯為否卦,同人卦的下卦離與比卦的上卦坎錯為既濟卦。3.兩旁通卦四爻與初爻互易,或上爻與三爻互易后形成的兩新卦之相錯。如,乾卦四爻與坤卦初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小畜卦,坤卦變成了復卦,小畜卦的上卦巽與復卦的下卦震錯為益卦,小畜卦的下卦乾與復卦的上卦坤錯為泰卦。又如,乾卦上爻與坤卦三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夬卦,坤卦變成了謙卦,夬卦的上卦兌與謙卦的下卦艮錯為咸卦,夬卦的下卦乾與謙卦的上卦坤錯為泰卦。4.兩旁通卦先二爻與五爻互易,再四爻與初爻互易、或上爻與三爻互易后形成的兩新卦之相錯。如,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同人卦,坤卦變成了比卦,同人卦的四爻再與比卦的初爻互易,則同人卦變成了家人卦,比卦變成了屯卦,家人卦的上卦巽與屯卦的下卦震錯為益卦,家人卦的下卦離與屯卦的上卦坎錯為既濟卦。又如,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同人卦,坤卦變成了比卦,同人卦的上爻再與比卦的三爻互易,則同人卦變成了革卦,比卦變成了蹇卦,革卦的上卦兌與蹇卦的下卦艮錯為咸卦,革卦的下卦離與蹇卦的上卦坎錯為既濟卦。 (焦氏“相錯”所分四種情況乃吸收復旦大學陳居淵先生的研究成果。其中的“旁通”乃用三國陸績、虞翻等人的“旁通”之義,非焦氏“旁通”之義。)
為了說明“相錯”亦為《周易》作者之本意,焦循在《易圖略》中也舉了不少例證。如:蒙卦、革卦為困卦與賁卦之相錯,故蒙卦六四爻辭有“困蒙”之語;睽卦、蹇卦為旅卦與節卦之相錯,故蹇卦象辭有“中節”之語;家人卦、解卦為豐卦與渙卦之相錯,故豐卦上六爻辭有“蔀其家”之語;鼎卦與屯卦相錯為噬嗑卦,噬嗑,食也,故鼎卦九三爻辭有“雉膏不食”之語;大壯卦與觀卦錯為小畜卦,故小畜卦九三爻辭言“輿說(脫)”,大壯卦九四爻辭則言“壯于大輿之 ”;臨卦與遁卦錯為履卦,故履卦卦辭言“履虎尾”,遁卦初六爻辭則言“遁尾”;咸卦、損卦為艮卦與兌卦之相錯,故艮卦六五爻辭言“艮其輔”,咸卦上六爻辭則言“咸其輔”,咸卦六二爻辭言“咸其腓”,艮卦六二爻辭則言“艮其腓”,損卦六三象辭言“一人行,三則疑也”,兌卦初九象辭則言“行未疑也”,損卦六三爻辭言“得其友”,兌卦象辭則言“以朋友講習”。[2](卷四)
(三)時行
關于“時行”, 阮元在《通儒揚州焦君傳》中說:“先二五,后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易》之道,唯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此所謂‘時行’也。”[3](卷首)焦循在《易圖略》中說:“《傳》云:‘變通者,趣(趨)時者也。能變通即為時行。時行者,元亨利貞也。”[2](卷三)
焦循認為,兩旁通卦先二爻與五爻互易,叫做“元”,繼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四爻與初爻或上爻與三爻互易,叫做“亨”,四爻與初爻互易叫“下應”,上爻與三爻互易叫“上應”,最終變通為咸、益二卦叫做“利”,變通為既濟卦叫做“貞”。 “元亨利貞”即焦循所謂“時行”。焦循“時行”說具體而言,可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二五先行當位變通不窮
焦循說:“乾坤坎離生同人、師、比、大有,震巽艮兌生漸、歸妹、隨、蠱。上應之成蹇、革,下應之成家人、屯,而家人、屯又變通于鼎、解,而終于既濟、咸,蹇、革又變通于睽、蒙而終于既濟、益。咸損益恒四卦循環不已。”[2](卷三)
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后,乾卦變成了同人卦,坤卦變成了比卦;坎卦二爻與離卦五爻互易后,坎卦變成了比卦,離卦變成了同人卦。同人卦旁通于師卦,比卦旁通于大有卦,因此焦循說:“乾坤坎離生同人、師、比、大有。”巽卦二爻與震卦五爻互易后,巽卦變成了漸卦,震卦變成了隨卦;兌卦二爻與艮卦五爻互易后,兌卦變成了隨卦,艮卦變成了漸卦。漸卦旁通于歸妹卦,隨卦旁通于蠱卦,因此焦循說:“震巽艮兌生漸、歸妹、隨、蠱。”繼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或坎卦二爻與離卦五爻互易后,同人卦上爻與比卦三爻互易,同人卦變為革卦,比卦變為蹇卦;繼巽卦二爻與震卦五爻互易,或兌卦二爻與艮卦五爻互易后,漸卦上爻與隨卦三爻互易,漸卦變為蹇卦,隨卦變為革卦。此即焦循所說“上應之成蹇、革”。 繼乾卦二爻與坤卦五爻互易,或坎卦二爻與離卦五爻互易后,同人卦四爻與比卦初爻互易,同人卦變為家人卦,比卦變為屯卦;繼巽卦二爻與震卦五爻互易,或兌卦二爻與艮卦五爻互易后,隨卦四爻與漸卦初爻互易,隨卦變為屯卦,漸卦變為家人卦。此即焦循所說“下應之成家人、屯”。家人卦又旁通于解卦,解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再以三爻與家人卦上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應之),解卦最終變成了咸卦,家人卦則變成了既濟卦;屯卦又旁通于鼎卦,鼎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再以上爻與屯卦三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應之),鼎卦最終變成了咸卦,屯卦則變成了既濟卦。此即焦循所說“家人、屯又變通于鼎、解,而終于既濟、咸”。蹇卦又旁通于睽卦,睽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再以四爻與蹇卦初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應),睽卦最終變成了益卦,蹇卦則變成了既濟卦;革卦又旁通于蒙卦,蒙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再以初爻與革卦四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應),蒙卦最終變成了益卦,革卦則變成了既濟卦。此即焦循所說“蹇、革又變通于睽、蒙而終于既濟、益”。益卦又旁通于恒卦,恒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繼之以益卦三爻與上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上應),則益卦成既濟卦,恒卦成咸卦,咸卦又旁通于損卦,損卦二爻與五爻互易后,繼之以咸卦初爻與四爻互易(二五先行而下應),則咸卦成既濟卦,損卦成益卦,益卦又旁通于恒卦,恒卦成咸卦后,咸卦又旁通于損卦,損卦又成益卦,生生不息,循環不已,因此焦循說:“咸損益恒四卦循環不已。”
2.初四或三上先行不當位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按照“變通不窮”的爻位運動規律,必須二五先行,初四、三上應之。如果初四先行,二五、三上應之,或三上先行,二五、初四應之,就會變成兩個既濟卦。如前所述,陰陽爻是否互易取決于是否當位,當位之爻不動,不當位之爻方與他爻互易,既濟卦“六爻皆定”,不具備旁通互易的條件,爻位運動至兩既濟卦而終止,違背了“生生之謂易”的原則,故須變通以補救之,補救以后,仍能“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卦四爻與坤卦初爻互易后,乾卦變為小畜卦,坤卦變為復卦;小畜卦二爻與復卦五爻互易以應之,小畜卦成家人卦,復卦成屯卦;屯卦三爻與家人卦上爻互易以應之,屯卦和家人卦就都變成了既濟卦,爻位運動因此而終止,故須變通以補救之。乾卦變為小畜卦后,小畜卦旁通于豫卦,小畜卦二爻與豫卦五爻互易(二五先行)后,按爻位運動規律,應繼之以四爻與初爻互易,但小畜卦四爻與豫卦初爻皆為陰爻,陰陽屬性一致,不具備互易的條件,爻位運動似乎無法繼續進行下去,然而就在此時,“柳暗花明又一村”,豫卦四爻與其初爻互易以補救之,爻位運動又可以繼續進行下去了。此即焦循所說:“小畜之失在四,通于豫以補之。……小畜二之豫五,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也。”[2](卷三)
焦循以普遍聯系和爻位運動的觀點研究《周易》,把《周易》六十四卦視為具有內在聯系的“生生不息”的動態系統,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易學構架。一種理論正確與否是一回事,其是否有意義是另一回事。例如天堂地獄之說雖然出于宗教的虛幻理念,然而它有利于勸人向善、杜人作惡,可以給善良者以美好的心靈寄托,給邪惡者以一定的心理威懾,其所具有的積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焦循的易學理論雖然不一定正確,但比之孤立、靜止地研究《周易》一卦一爻,在方法論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周易》六十四卦究竟是雜亂無章的“偶然拼湊”,還是有機聯系的整體,是易學史上的一大懸案。清代學者戴震說:“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以己自蔽。”筆者認為,因為自己沒有看到《周易》六十四卦之間的內在聯系,就武斷地把六十四卦卦爻辭視為“雜七雜八”“顛三倒四”的占卜結果的“拼湊”,犯了“以己自蔽”之病。以焦循的學力,如果僅僅研究《周易》一卦一爻,很容易迅速拿出成果,而且一般不會招致別人的非議,但焦循卻避易就難,潛心研究《周易》六十四卦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爻位運動的規律,“盡屏他務,專理此經”,[4](卷首)“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5](《焦循傳》),這正是學術發展所必需之文化精神。盡管焦循提出的易學構架是否《周易》所固有,尚有商榷余地,然而他畢竟提出了許多不乏說服力的例證,其得出結論的方法是科學、嚴謹的,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說:焦循的易學研究“非憑空臆斷,確是用考證家客觀研究的方法得來。”[6](第298頁)
二
《周易》研究的傳統格局中分象數和義理兩大流派。焦循因其獨特的易學構架,被歸于象數一派。其實,焦循探究象數的目的,在于闡發義理。另外,焦循為了論證其易學構架,常以“聲訓“之法尋求卦與卦之間的關聯,這是被人譏諷為“附會難通”的重要原因。下面,筆者就對這兩個問題加以探討。
(一) 焦循易學構架的道德義理詮釋
縱觀中國士人史,不難發現,中國大多數士人都有著揮之不去的入世情結。這種入世情結肇源于“任重而道遠”的使命感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患意識。這種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是從孔子那里一脈相傳的文化傳統。(關于孔子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筆者曾做過專題研究。為節省篇幅,在此不做展開論述。)前人往往評價乾嘉學者“一頭鉆進故紙堆,不問世事”。我常懷疑這一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對乾嘉學者的這種認識,實在是低估了文化傳統的影響力。焦循作為一名乾嘉學者,盡管潛心于六經注疏之學,然而“修齊治平”的中國傳統士人的理想在他心中并未泯滅。焦循提出的易學構架絕非純象數的研究,而是以象數為載體,闡發儒家的道德義理和自己“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
焦循在論述其“旁通“體系時說:“成己所以成物,故此爻動而之正,則彼爻亦動而之正,未有無所之自正不正人者也。枉己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各正,未有變己正之爻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2](卷一)此段話中“成己所以成物”即孔子所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7](《雍也》)“枉己未能正人”即孔子所說“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之意;[7](《子路》)“未有變己正之爻為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即孟子所云“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之意。[8](《滕文公上》)
焦循在《易圖略》中又說:“《易》之一書,圣人教人改過之書也。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故曰為衰世而作,達則本以治世,不得諉于時運之無可為,窮則本以治身,不得謝以氣質之不能化。”[2](卷三)這段話充分表達了焦循“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躍然紙上。焦循認為,按照爻位運動規律,先二五,后初四、三上則為吉,不待二五,初四、三上先行則為兇。然而吉可變兇,兇可化吉。吉何以變兇?焦循舉例說:“乾二先之坤五,四之坤初應之,乾卦成家人,坤成屯,是當位而吉者也。若不知變通而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其道窮矣。”[2](卷二)也就是說,本來是吉,如不知及時“遷善改過”而變通,也會變為兇。兇何以化吉?焦循舉例說:“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是失道而兇者也。若能變通,以小畜通豫,以復通姤,小畜、復初四雖先行,而豫、姤初四則未行,以豫、姤補救小畜、復之非,……此兇變吉也。”[2](卷二)也就是說,本來是兇,如果能夠“遷善改過”而變通,也會轉化為吉。最后,焦循總結說:“惟兇可以變吉,則示人以失道變通之法;惟吉可以變兇,則示人以當位變通之法。”[2](卷二)失道時“遷善改過”以求吉,當位時“遷善改過”以避免轉化為兇,這充分反映了中國傳統士人憧憬、追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理想。在《易話》中,焦循更是明確指出:“圣人治天下,欲其長治而不亂,故設卦系辭以垂萬世。……圣人處亂則撥亂以反乎治,處治則繼善以防乎亂。……大抵氣化皆亂,賴人而治。治而長治者,人續之也;治而致亂者,人失之也。……怠于政教,人民乃紊,……故否泰皆視乎人,不得委之氣化之必然也。”[9](《陰陽治亂辨》)一個憂國憂民,希冀國泰民安的“故紙堆”中的乾嘉學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二) 焦循易學構架與“聲訓”
在中國訓詁學史上,清代可稱是黃金時期。清代訓詁學的最突出的成就是“聲訓”的發達。“聲訓”也稱“音訓”,是從字的讀音著眼,根據音近義通的原則,取音近之字互為解釋。“聲訓”的起源很早,《周易·說卦》:“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坤以申為聲符,申與順疊韻;坎以欠為聲符,欠與陷疊韻。)《周易·彖》:“夬,決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在上古音韻系統中,“序”為邪母魚部,“射”為船母鐸部。邪母為舌尖音,船母為舌面音,兩者發音部位相近;魚部和鐸部是陰入對轉,即主要元音相同,只是有無輔音韻尾的區別。“序”與“射”聲母和韻母都相近,具備聲韻相鄰通假條件。參見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這些都是“聲訓”。至清代,以音韻學的成就為依托,“聲訓”形成了系統的理論。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自序中說:“竊以詁訓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段玉裁為《廣雅疏證》作序時也說:“圣人之制字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10](卷首)這些論述十分精辟,成為清代學者研究訓詁的準繩。
焦循深受《廣雅疏證》的影響,他說:“循近年得力于《廣雅疏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冰釋,因嘆聲音訓詁之妙,用以解他經,固為切要,而用以解《易》,尤為必不可離。”[11](《寄王伯申書》)在論證其易學構架時,焦循常用“聲訓”之法探求卦與卦之間的關聯。如,萃卦初六爻辭有“一握為笑”之語,鼎卦九四爻辭有“其形渥”之語,焦循注萃卦時說:“握與渥同。鼎‘其形渥’,渥,足也。足則終,終則亂,惟有孚于萃不終。”[12](卷二)通過“握”與“渥”的假借,論證了萃卦與鼎卦的關聯。這種假借之法常被譏評為“穿鑿附會”。針對這種譏評之語,阮元曾為之辯駁說:“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無文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文字未造以前,……故口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口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此道也。淺識者立乎其后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為‘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為‘據疾’哉?”[13](卷首)在晚清易學界對焦循的一片非難否定聲中,皮錫瑞也表明了他支持焦循的鮮明立場:“假借說《易》并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14](第39頁)筆者認為,“聲訓”本是一種科學的訓詁方法,卦與卦之間的關聯也可備一家之說,但“聲訓”與兩卦(或數卦)關聯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邏輯關系,換言之,《周易》作者是否有意識地用“聲訓”來暗示卦與卦之間的關聯,則大有疑問。此外,運用“聲訓”時,最忌主觀臆測,最好有比較充分的文獻旁證,而焦循在其易學論著中所論之假借雖然基本上都符合古音通假的條件,但缺乏比較充分的文獻旁證,終覺美猶有憾。
[1]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M]. 長沙:岳麓書社,1998.
[2]焦循.易圖略[M].續修四庫全書本.
[3]焦氏遺書[M].光緒二年(1876)重刻本.
[4]焦循.易通釋[M]. 續修四庫全書本.
[5]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
[6]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7]論語[M].十三經注疏本.
[8]孟子[M].十三經注疏本.
[9]焦循.易話[M].續修四庫全書本.
[10]王念孫.廣雅疏證[M]. 叢書集成初編本.
[11]焦里堂先生軼文[M]. 鄦齋叢書本.
[12]焦循.易章句[M]. 續修四庫全書本.
[13]焦循.雕菰樓易學三書[M]. 焦氏叢書本.
[14]皮錫瑞.經學通論[M]. 北京:中華書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