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發(fā)·蓄發(fā)·剪發(fā)——清代辮發(fā)的身體政治史研究
佚名
清朝是一個(gè)與辮發(fā)糾纏在一起的朝代。單是男人頭上盤旋的一條辮子,其存廢留剃就與清王朝的政治命運(yùn)緊密相連。盡管已有學(xué)者對(duì)于清朝的辮發(fā)史作過相關(guān)研究(注:研究中國(guó)辮發(fā)史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學(xué)者桑原騭藏《中國(guó)辮發(fā)史》,美國(guó)學(xué)者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guó)妖術(shù)大恐慌》,中國(guó)學(xué)者王冬芳《邁向近代——剪辮與放足》等。陳生璽在《明清易代史獨(dú)見》中的《清初剃發(fā)令的實(shí)施與漢族地主階級(jí)的派系斗爭(zhēng)》、《剃發(fā)令在江南地區(qū)的暴行與人民的反抗斗爭(zhēng)》等文,對(duì)清初剃發(fā)令進(jìn)行過集中闡釋。李文海、劉仰東在《太平天國(guó)社會(huì)風(fēng)情》一書中,深入探討了太平軍的蓄發(fā)問題。嚴(yán)昌洪在《中國(guó)近代社會(huì)風(fēng)俗史》、《西俗東漸記——中國(guó)近代社會(huì)風(fēng)俗的演變》等書中,深入探討清末剪發(fā)易服等問題。黎志剛在《中國(guó)近代的國(guó)家與市場(chǎng)》中,有《想象與營(yíng)造國(guó)族:近代中國(guó)的發(fā)型問題》一文,剖析了近代中國(guó)發(fā)型變化。張亦工、夏岱岱的《割掉辮子的中國(guó)》,集中探討辮發(fā)與時(shí)人的心理。),但截至目前還很少有人從身體史的角度切入,將辮發(fā)與有清一代歷史的發(fā)展變化聯(lián)系起來展開論述,并且透過“辮發(fā)”這一身體符號(hào)來對(duì)清代政治與文化進(jìn)行解讀。
一、江山易主的“剃”
滿族男子剃發(fā)留辮,實(shí)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風(fēng)俗習(xí)慣。在戰(zhàn)爭(zhēng)中,辮發(fā)漸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種標(biāo)志。投降或歸附滿族者要剃去四周頭發(fā),扎成辮子。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進(jìn)入廣寧,傳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輕人必須剃”(注:《滿老文檔·太祖》卷三十四,遼寧大學(xué)1979年譯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因?yàn)閴讯‘?dāng)兵,要求較嚴(yán)。此時(shí)辮發(fā)還未完全成為一種政治符號(hào),至多是滿族對(duì)于投降或歸附者發(fā)式服飾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極繼位,采取了某些緩和滿漢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卻要求被征服地區(qū)的漢人剃發(fā)。清軍每到一處,便要當(dāng)?shù)厝瞬环掷仙僖宦商臧l(fā)。隨著對(duì)明戰(zhàn)爭(zhēng)的日益擴(kuò)大,剃發(fā)的范圍也逐漸擴(kuò)展,剃發(fā)逐漸演變成一種固定的制度。
在滿族貴族看來,只要漢人肯剃發(fā),就會(huì)棄明忠清。而明官和漢人則把不剃發(fā)作為保持民族大義的表現(xiàn)。許多被迫剃了發(fā)的漢人在從遼西逃至關(guān)內(nèi)的途中,被明軍妄殺。有沒有剃發(fā),成為區(qū)別滿漢的首要身體依據(jù)。隨著滿族與明朝之間戰(zhàn)爭(zhēng)的加劇,“剃發(fā)”也開始逐漸上升到有關(guān)民族、文化層面的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發(fā)”最終成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與文化符號(hào)的歷程卻是相當(dāng)復(fù)雜的。
清順治元年(1644年),隨著清軍入關(guān),剃發(fā)制度也從關(guān)外推行到關(guān)內(nèi)。多爾袞強(qiáng)令官民剃發(fā)的舉措引起漢人的普遍不滿,甚至因此改變對(duì)清軍的態(tài)度。“入關(guān)之初,嚴(yán)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dú)為此剃頭乎?”(注:池內(nèi)宏:《清代滿蒙史料·李朝實(shí)錄抄》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發(fā)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不久, 在吳三桂等降清漢臣的建議下,鑒于強(qiáng)行“剃發(fā)”所引起漢人的抵制情緒,多爾袞下令罷除剃發(fā),以收買人心。此舉收到奇效,極大地減少了清軍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復(fù)多爾袞的書信中也說:“且罷剃發(fā)之令,示不忘本朝。”(注:蔣良騏:《東華錄》卷四,林樹惠、傅貴九校點(diǎn),中華書局1980年版。) 因不用剃發(fā)而對(duì)清產(chǎn)生某種好感。而清在辮發(fā)問題上的暫時(shí)妥協(xié),則緩解乃至削減了滿漢雙方的矛盾與沖突。
然而,剃發(fā)令行而復(fù)罷既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shí)也造成了新的矛盾。這種新的矛盾表現(xiàn)在:先期歸順者已經(jīng)剃發(fā),后來投降者則不用剃發(fā),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某些混亂。清軍南下時(shí),又實(shí)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進(jìn)一步加劇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歸降的漢官中引起了爭(zhēng)端:沒剃發(fā)者主張一體從漢,以保留捍衛(wèi)禮儀之邦的尊嚴(yán),對(duì)剃發(fā)所象征的“蠻夷”有某種排斥心理,尤其是對(duì)于那些先期歸降的“剃發(fā)者”懷有一種鄙夷的心態(tài)。而已剃發(fā)者則要求一統(tǒng)從滿,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時(shí),也可以釋緩后歸降者保留發(fā)式的心理壓力。不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發(fā)與否成為了王朝之間政治斗爭(zhēng)的犧牲品。在常熟,剃發(fā)者與未剃發(fā)者雜處,“清兵見未剃發(fā)者便殺,取頭去做海賊首級(jí)請(qǐng)功,名曰‘捉剃頭’,海上兵(明兵)見已剃發(fā)者便殺,拿去做韃子首級(jí)請(qǐng)功,號(hào)曰‘看光頸’。途中相遇,必大家回頭看頸之光與不光也”。社會(huì)上彌漫著恐慌心理:“福山數(shù)十里遺民,不剃發(fā)則懼清兵,剃發(fā)又懼明兵,盡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遺編》第57回,轉(zhuǎn)引自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dú)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頁。) 此時(shí)的辮發(fā)已無關(guān)乎民族風(fēng)俗,其所代表的降清還是附明的政治含義被進(jìn)一步凸現(xiàn)出來,由此拉開有清一代“辮發(fā)”與政治糾纏史的序幕。
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進(jìn)入南京,多爾袞遂改變剃發(fā)與否“聽其自便”的政策,命禮部向全國(guó)發(fā)布“剃發(fā)令”。在剃發(fā)令的罷而復(fù)行中,部分降清漢官起了很大作用。清軍南下旨在奪取明朝江山,使被統(tǒng)治者從滿俗、廢漢俗,以免觸發(fā)人們的故國(guó)情思。辮發(fā)既然是滿漢習(xí)俗在身體外觀上最顯著的差異,又具有這么豐富的政治內(nèi)涵,所以多爾袞接受了這些漢官的意見,重新實(shí)行強(qiáng)制剃發(fā)的政策。至此,辮發(fā)完全成為了一種政治符號(hào),多爾袞視剃發(fā)為征服漢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漢人是否接受滿族統(tǒng)治的突出身體標(biāo)志。為此,清軍不惜采用血腥鎮(zhèn)壓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監(jiān)督剃頭匠挑著擔(dān)子上街巡游,強(qiáng)迫束發(fā)者立即剃頭梳辮。稍有反抗,當(dāng)場(chǎng)殺害。有的還被割下首級(jí),懸在剃頭擔(dān)子上示眾。這樣一來,漢人由反對(duì)滿族的象征——辮發(fā),進(jìn)而反抗?jié)M族統(tǒng)治。所謂“江陰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發(fā)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事件。無奈強(qiáng)令難違,男人從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辮,十天一剃頭”(注:邵廷采:《東南紀(jì)事》,“中國(guó)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99頁。)。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因“剃發(fā)”而發(fā)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慘事件,不僅在當(dāng)時(shí)的明、清戰(zhàn)爭(zhēng)中影響巨大,更成為滿漢民族沖突的痛苦的文化記憶,貫穿于有清一代。
報(bào).jpg)
刊.jpg)
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jpg)
械文摘.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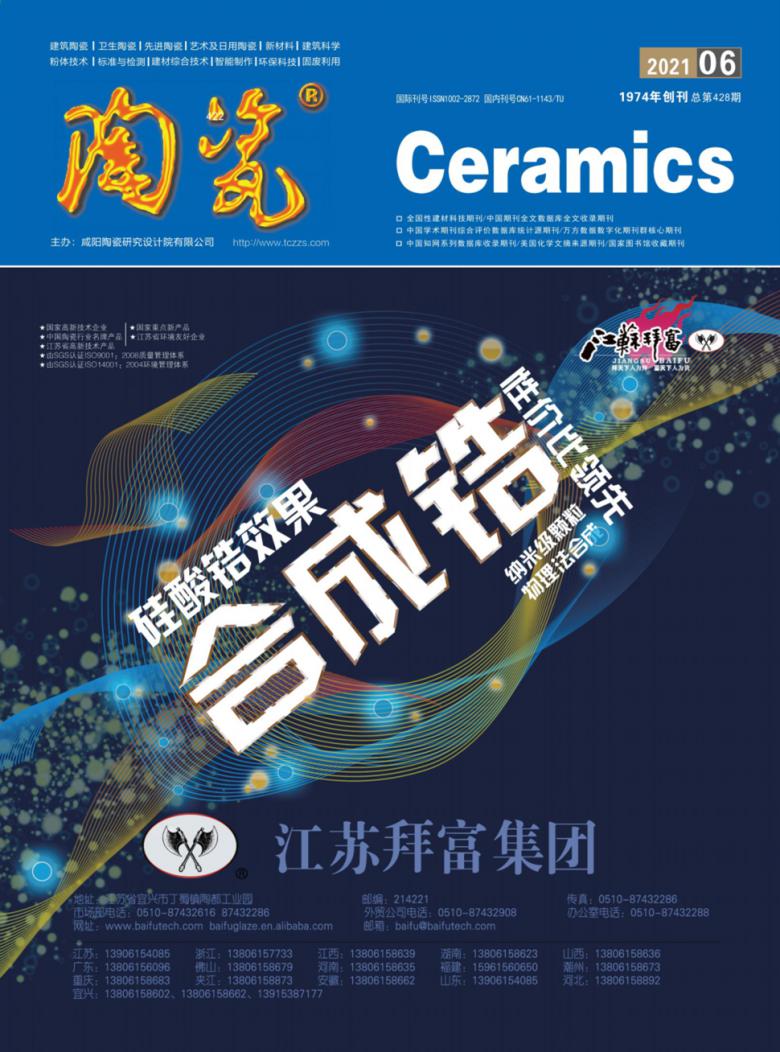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