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維體系
佚名
在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實現(xiàn)高度的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治,必然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yīng)的龐大的官僚組織系統(tǒng)。然而,自秦以來,尤其是在逐漸地建立健全科舉取士制度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僚,按人口比例算是少而又少的。于是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的封建官僚組織系統(tǒng)里,始終摻雜著一類沒有官位,卻能夠一方面主掌地方事務(wù),一方面又能溝通地方紳衿的另一群人。明清以來,特別是清代幕府趨向制度化以來(注:幕府制度并不是一種嚴謹?shù)恼f法,但在清代以其實際構(gòu)成的幕友與官僚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被認為是無待朝廷典章之規(guī)定的制度。對此前輩學(xué)者鄭天挺、繆全吉等人均有過討論。),在地方政府之中實際形成了官僚、幕友、胥吏這樣一種三維體系。它在世界性地踏入工業(yè)化時代時,仍然能夠使中國社會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探討清代地方官、幕友、胥吏三個階層的形成及其相互關(guān)系,以及這種關(guān)系在地方政府的運作,對認識清代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或許不無幫助。
一、關(guān)于胥吏
關(guān)于胥吏的研究,在中國政治史、制度史以及賦役制度等研究中早已引起人們的重視。60年代末,即有臺灣學(xué)者繆全吉的《明代胥吏》問世[1], 而后日本學(xué)者宮崎市定又著有《清代的胥吏與幕友》一文[2](卷一四)。1994年又出版了北京師范大學(xué)趙世瑜的專著《吏與傳統(tǒng)社會》[3]。他們皆較詳盡地介紹了胥吏的產(chǎn)生、作用以及弊害等內(nèi)容。此外,鄭天挺在討論幕友時,對此也有涉及[4]。為避免重復(fù),本文盡可能省略有關(guān)胥吏的概念性敘述,僅就清代胥吏的狀況及在行政體制中的地位作進一步考察。此外,關(guān)于此類人的稱呼,因有掾吏、書吏、司吏、典吏、都吏、通吏、獄典、撰典、攢典、驛吏、提控等,如果再加上“供奔走驅(qū)使,勾攝公事”的皂隸、快手、弓兵、仵作、門子、庫子、斗級等役職,較難把握。因此,除史料照引之外,本文按近年來學(xué)術(shù)界的習(xí)慣,采用胥吏一詞,用以囊括吏役之各級各等。
1.清代胥吏的投充經(jīng)緯及其來源
清代胥吏的來源基本上沿襲明代舊制。明代的胥吏投充大概有兩條途徑:一為僉充,一為謫充。關(guān)于僉充,《大明會典》中有明確規(guī)定:“凡僉充吏役,例于農(nóng)民,家身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者選用。”洪武二十八年又奏準(zhǔn):“正軍戶,五丁以上可僉一丁充吏,四丁不僉!水馬驛站、貼軍、雜役、養(yǎng)馬等人戶,四丁以上可僉一丁,三丁不僉;民戶,兩丁識字,可僉一丁。”[5](卷八,《吏部七,吏役參撥》)
從定制來看,吏役本來應(yīng)該是一種義務(wù),但是,隨著胥吏權(quán)益的擴大,到了明代中后期,吏職被視為肥缺,自愿投充者日增,于是形成了不成文的充吏者捐納之例。嘉靖南宮縣知縣葉恒嵩對當(dāng)時的狀況也有描述:“自大司農(nóng)告竭,賣官鬻吏之令屢下,富農(nóng)巨商爭相輸粟納銀,為良家,為郡邑掾胥。”[6](卷二,《田賦》) 明隆慶遼東巡撫都御史魏學(xué)也曾上言:“本鎮(zhèn)自開納例行,衛(wèi)所軍舍余丁多援納吏役,規(guī)免徭賦。”[7](卷九,隆慶元年六月) 到了明季,捐納之額更高,自初年之幾十兩,中葉之幾百兩以致季世之幾千兩,以致形成胥吏僉充,貌似義務(wù),而實為行市的局面[1](p.97)。
入清以來,雖然康熙二年曾經(jīng)一度復(fù)準(zhǔn):“停止援納,俱令各衙門召募,給予執(zhí)照,開注姓名年歲,著役日期,并地方印結(jié),按季匯冊咨部。”但六年又復(fù)準(zhǔn)“內(nèi)閣供事暨各衙門書吏召募考補,或貼寫內(nèi)遴選掣補”。十四年又題準(zhǔn):“書吏承充仍照舊例援納。”雍正二年及乾隆三十九年又分別兩次題準(zhǔn)“至貼寫、幫差人等,亦擇忠誠樸實之人充役”;吏缺“即照各部院之例,于貼寫內(nèi)揀選年久歷練者補之”[8](卷一四六,《吏部·書吏》)。可見, 在清代胥吏的納充事實上仍然是沿用明制。除了朝令以外,在一些奏章中也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如雍正五年二月一日,廣東布政使常賚的《奏報所得養(yǎng)廉與各項費用摺》中即提到:“投充吏役給發(fā)執(zhí)照,向有督、撫、司紙札之費,今亦照股分銀二千八百余兩。”[9] 同年閏三月初七,蘇州巡撫陳時夏的《請滿役吏胥捐銀選職疏》中也提到:“竊照定例,各衙門吏攢,歷事五年役滿,情愿捐納者,捐銀選職。”[9] 這里所謂的“竊照定例”,應(yīng)該是指清初的“舊例,書吏承充,按納銀數(shù)多寡,分送各衙門辦事。”[8](卷一四六,《吏部·書吏》) 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以來,本始于役法的吏役,到了明季及清初不過是只存其名而已,更無僉充召募之實。如果說清較之明代在胥吏納充時有所變化的話,并不是改援納為召募,而是給胥吏的繼承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甚至可以說,已然存在的胥吏繼承問題,到了清代更趨向合理化。到了道光朝,福建漳州知府周鎬已明確地看到了這一事實:“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為授受,州縣特其佃戶耳。買定之后,則以此缺為傳家之寶。官有遷調(diào),而吏無變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10](卷二四,《上玉撫軍條議》)
至于所納金額尚未見史書明確記載。康熙朝進士儲方慶在其《馭吏論》中說:“吏胥之役,不過入數(shù)十金,數(shù)百金之資于官已耳。”[10](卷二四) 足見捐納金額在清初已然不低。如果按前引常賚《奏報所得養(yǎng)廉與各項費用摺》中提到的數(shù)額推算,督、撫、司三股之一的紙札之費即有二千八百余兩,那么,督撫衙門一年可收紙札之費即有八千四百余兩。這里需要順便提及的是,這條史料同時說明清代胥吏捐納盡數(shù)歸于地方,且已構(gòu)成地方官收入的相當(dāng)成分。因此,這是不是康熙年間改援納為召募旋又改回的理由尚有待考證,故于《清會典》中不再見其數(shù)目。據(jù)日本學(xué)者宮崎市定考證,在雍正朝胥吏的平均捐納銀數(shù)在三百兩左右[2]。
明代的胥吏僉充條例中即有“能書者選用”,清代又有“通曉律例,或能寫算,文理通順”,“有熟于律例,工于寫算者,赴該衙門報名,取縣同鄉(xiāng)甘結(jié),定期考試,擇取拔補:……其各省有通曉律例,或能寫算,情愿充當(dāng)部辦之人,亦令赴地方官報明試驗,取具同鄉(xiāng)甘結(jié),開明年貌籍貫,申報該督撫,咨部拔用”[5](卷一四六,《吏部·書吏》) 之定制。將這些規(guī)制與前述援納綜合考慮, 我們大致可以了解投充胥吏者,“大抵皆有產(chǎn)業(yè)之人也”。“一無恒產(chǎn)之民,不但不能掛名于官,并書役亦不肯與之為儔”[10](卷二四,《復(fù)陳書吏不必定額疏》)。


濟.jpg)

與開發(fā).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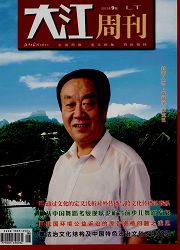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