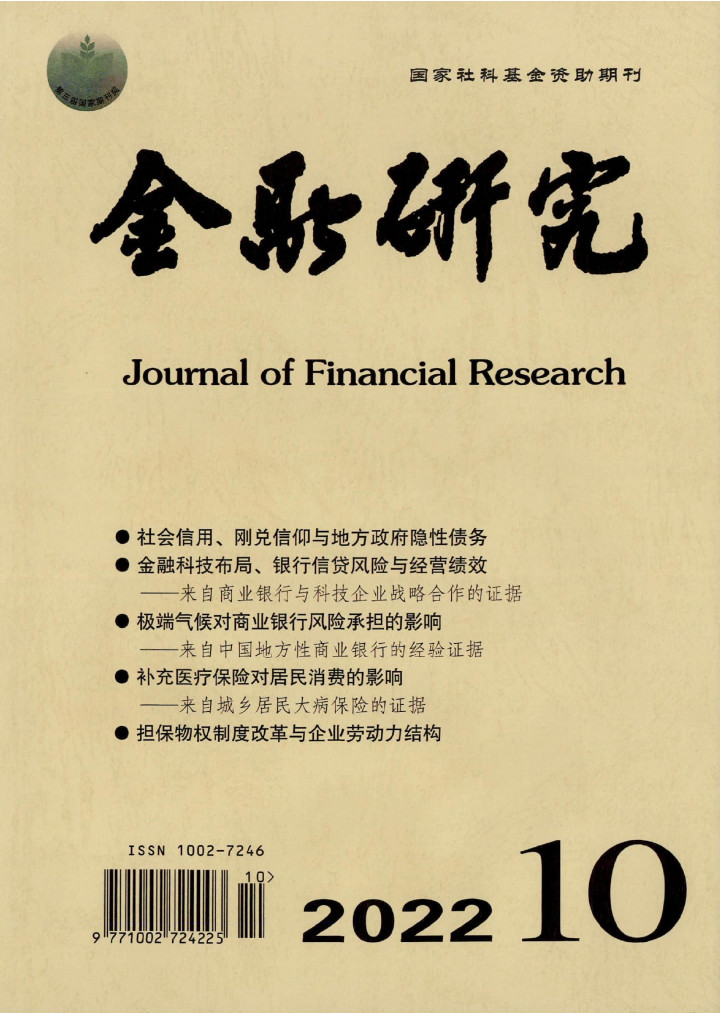“后假定性”美學的崛起——試論當代影視藝術與文化的一個重要轉向
陳旭光
【內容提要】假定性是藝術的一種重要特性。影視藝術具有真實性與假定性的兩面,對這兩面的不同側重代表了不同的藝術觀念。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影視領域出現了一種強化假定性特征,有力沖擊“真實性”原則的假定性美學潮流——一種“后假定性美學”趨向。本文總結歸納了假定性的歷史與由來,認為假定性大致經歷了廣義假定性、現代主義假定性、后假定性等三個階段,并通過對中國當下影視藝術現象的分析,論述了后假定性美學的種種表現。本文認為當下中國的后假定性美學是全球化語境中多元文化因素復雜制約的結果,它有一個與中華民族審美心理深層契合,以及中西文化融合、對話的廣闊發展前景。
【摘 要 題】觀點與流派
【關 鍵 詞】假定性/后假定性美學/當代影視藝術
【正 文】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定時間意義上的新時期所擁有的諸如啟蒙的理想、反思的豪情、現代性的焦慮等等,都逐漸凝定成為一個空洞的姿勢。一個可以稱之為平民化、大眾化、多元化的文化轉型時代已成為我們的生存現實。 觀之以五光十色、豐富而駁雜的影像世界,我們會發現種種世事滄桑:視覺化追求、寫意性的影像風格,戲說風的盛行,對歷史與現實的顛覆解構和娛樂化,荒誕不經、顛覆解構的無厘頭文化品格,類型化、符號化的演員,臉譜化的表演,假定性很強的戲劇性沖突,戲劇化或游戲化的情節結構,舞臺化的對話臺詞,服裝、道具、美術的舞臺化和裝飾性化……諸如此類藝術表征,是后現代文化的影響?是戲劇化的回歸?是中國式寫意性美學傳統的回歸?是文化轉型的必然?不是剛剛電影界還在主張“丟掉戲劇的拐杖”,“與戲劇離婚”嗎?怎么丟掉的一切又改頭換面而卻似曾相似地回來?難道影視是在向戲劇回歸嗎? 也許,一種強化影視藝術假定性美學特征,強勁地沖擊顛覆原先藝術所恪守的所謂“真實性”原則的假定性美學在崛起。這種美學決不避諱甚至有意強化某種廣大觀眾心領神會的假定性,就像情景劇中那些隨處可起的附加上去的笑聲一樣,它反而是要把假定性暴露給觀眾,明白無誤地告訴觀眾,你是在娛樂、在消費,我是在表演,千萬別把我當真! 從美學的角度看,我們不妨把它歸納為一種“后假定性美學”的崛起。 一 影視藝術是一種能創造最大的真實感的藝術。這種真實感是由影視的技術特性決定的。巴贊認為,電影的本性是復制和還原現實的真實性,電影是通過攝影機記錄下來的,是照相的延伸。因此電影的本體論就是一種影像的逼真性特征。電影的使命就是用運動、空間、聲音和色彩去完整地再現世界,以實現“完整世界的神話”。而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得以實現,都是因為攝影機的介入。巴贊特別強調攝影與繪畫及其他藝術的不同即在于一種“本質上的客觀性”,由于攝影機的鏡頭代替了人的眼睛,使得“原物體與它的再現物之間只有一個實物發生作用,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嚴格的決定論自動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預,參與創造。一切藝術都是以人的參與為基礎的;唯獨在攝影中,我們有了不讓人介入的特權”。(注:[法]巴贊《“完整電影”的神話》,崔君衍譯,《電影是什么?》,小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頁。)克拉考爾也認為,電影按其本性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與我們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親近性。因此正如普多夫金指出的,“電影是一種給逼真地再現現實提供了最大可能性的藝術”。 影視的真實性首先源于視聽的真實感。它借助于現代化的攝影錄音設備,以直接的形式將物質現實訴諸于人們的視覺和聽覺,從而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而由于攝影機鏡頭與觀眾視點的一致性,更能使觀眾產生身臨其境的真實感。 從某種角度說,影視藝術的真實性源于攝影機前面的對象都必然是真實的這一簡單的道理,雖然這一道理在虛擬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受到嚴峻的挑戰。 但另一方面,影視作為藝術,又滲透或洋溢著藝術家的主體創造精神,凝聚著藝術家的審美理想和思想情感,體現出藝術家個體鮮明的藝術風格和個性,而藝術家個性的發揮正需要最大限度地克服藝術媒介對其創作的限制和壓抑,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而對表現對象進行主體投射,乃至因為主體性過于強烈而進行一種變形夸張的非常態表現。這就是影視藝術相應的假定性的一面。 事實上,對于電影藝術的假定性這一問題,即使是極為強調電影藝術的真實性一面的巴贊也發現了真實性無法完全概括電影藝術的特性。他曾表達了這樣一種困惑:“藝術的真實顯然只能通過人為的方法實現,任何一種美學形式都必然進行選擇。但是這種選擇構成美學上的基本矛盾。它是必不可少,因為只有通過這種選擇,藝術才能存在。它又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選擇畢竟會削弱電影旨在完整再現的這個現實。其實,電影藝術就是從這些矛盾中得到滋養。它充分利用了由銀幕目前的局限所提供的抽象化與象征性手法。”(注:[法]巴贊《“完整電影”的神話》,崔君衍譯,《電影是什么?》,小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巴贊在這里表露的困惑實際上涉及到影視藝術如何處理真實性與假定性關系的問題。與這一對范疇大致相應,還有諸如紀實性電影美學/戲劇化電影美學、寫實性/寫意性,路易斯·賈內梯所區分的現實主義風格/形式主義風格等。(注:參見[美]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第2—6頁的有關論述,胡堯之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版。) 二 在具體藝術門類中,假定性與戲劇藝術的關系最為密切。假定性術語在中國的確定,源于前蘇聯戲劇導演奧赫洛普科夫1959年發表的《論假定性》一文。這“是戲劇理論文庫中我們所知道的唯一一篇關于‘假定性’問題的專著。它對中國戲劇界曾有過特殊影響。首先,隨著此文被翻譯成中文,中國的戲劇導演藝術詞典中開始有了明確統一的‘假定性’的概念。在此之前,‘условность’這個含義廣泛的俄文詞匯有著很多譯法,諸如‘虛擬’、‘程式’、‘程式性’、‘有條件性’等等,張守慎在此處一律譯成‘假定性’或‘假定性手法’,則顯得最為貼切并得到了一致認可”。(注:王曉鷹《戲劇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頁。) 然而,假定性不僅僅只關涉藝術手法技巧的層面,它還是一個根本性的藝術觀念的問題。正如王小鷹在論及演劇方法的假定性問題時指出:“但是在演劇方法這個層面上,每個具體的戲劇演出創造,每個具體的演劇流派,對于如何理解、看待、處理需具的‘假定性’本質,卻可能有著南轅北轍的巨大差別:或是顯露這個‘假定性’,擺脫現實生活的邏輯制約,充分發揮演出和欣賞兩方面的創造想象力,在與觀眾建立‘約定俗成’的默契時直言其‘假’;或是掩蓋這個‘假定性’,盡量利用戲劇演出讓人產生‘真實幻覺’的可能性,使演出從外部形態上趨于‘逼真’,并在此基點上與觀眾簽署‘協約’。”(注:王曉鷹《戲劇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 因而,假定性原則堪稱藝術再現或表現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于這個幾乎無法回避的藝術原則,對其態度卻是不一樣的。有的是要有意掩飾這一原則或者說是有意無意地遺忘或無視這一原則,沉浸于真實性幻覺,真心或假意地相信藝術所表現的是真實的。但有的則有意無視真實性原則,反而夸大假定性原則,常常把假定性暴露給受眾,明白無誤地告訴受眾:你所看到的是假的。戲劇中的布萊希特表演體系、中國戲曲等,都可以說是實施藝術假定性原則的代表。 電影也是這樣,偏于紀實形態的電影,恪守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電影,在真實性與假定性這一對對立統一范疇中,偏向于真實性這一維度,恪守真實性原則。電影初創伊始如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英國的布賴頓學派等等,都盡量隱去藝術假定性。二次大戰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興起,巴贊等人關于長鏡頭、關于物質現實的復原等理論的總結,使電影對真實性的追求更是風行一時。 而偏于表現性美學的電影,則偏向于假定性維度。德國室內劇和表現主義電影、歐洲先鋒派電影運動、法國新浪潮等現代主義電影美學,包括“德國新電影”都是如此。比如,羅伯特·考克爾在談到法斯賓德時曾指出法斯賓德受到了提倡間離效果也即假定性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影響。這影響到法斯賓德對經典的連貫性剪輯方法的反叛和更新。“因為經典連貫性剪輯方法的主要作用是讓觀眾意識不到這些剪輯方法的存在,布萊希特利用并改革了這種方法,使之發揮了相反的作用,其結果是使觀眾意識到影片和它的故事都是編造、制作的,而不是真實的、自在的、現實存在的直接呈現。”(注:[美]羅伯特·考克爾《電影的形式與文化》,郭青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頁。) 因而,假定性是藝術觀念一個非常重要的試金石和分水嶺,無論是電影藝術還是戲劇藝術都是如此。毫無疑問,戲劇領域著名的斯氏表演體系與布萊希特表演體系之分就是因為處理和看待戲劇表演中真實性與假定性的關系的不同而產生了兩種根本不同的演劇觀念體系。 在中國戲劇界,可以說,新時期以來戲劇藝術的繁榮發展是以假定性對真實性這一至高無上的表現原則的突破,打破一元格局而多元共存為前提的。 實際上,假定性與真實性的矛盾在戲劇藝術中可謂古已有之。正如黃佐臨認為的,“歸納起來說,二千五百年話劇曾經出現無數的戲劇手段,但概括地看,可以說共有兩種戲劇觀:造成生活幻覺的戲劇觀和破除生活幻覺的戲劇觀;或者說寫實的戲劇觀和寫意的戲劇觀;還有就是,寫實與寫意混合的戲劇觀”。(注:黃佐臨《漫談“戲劇觀”》,轉引自胡星亮《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思潮》,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頁。) 這種“造成生活幻覺”與“破除生活幻覺”的矛盾在新時期中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中還曾經成為論爭的焦點。在當時,“跳出‘斯坦尼模式’,借鑒一切可能借鑒的戲劇流派,成為戲劇家眾所首肯的‘藝術戰略’;而突破‘寫實’、‘造成生活幻覺’的戲劇觀,嘗試‘寫意’、‘破除生活幻覺’的戲劇觀,也成為戲劇界最熱門的話題。中國劇壇到處都可以聽到推倒‘第四堵墻’的轟隆隆聲”。(注:黃佐臨《漫談“戲劇觀”》,轉引自胡星亮《二十世紀中國戲劇思潮》,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頁。) 從新時期以來的戲劇實踐看,以1985年《WM》的演出為標志,一股標舉形式探索的“青年探索戲劇”潮流登上了舞臺,包括一大批此間開始探索的戲劇如《車站》、《野人》、《絕對信號》等。他們實施對假定性的有意暴露和生活幻覺的打破,顯露出日常生活化乃至粗鄙化的風格。進入90年代,“小劇場戲劇”在市場困境之下,以標新立異的實驗探索而頑強生存。《思凡》、《與艾滋病有關》、《零檔案》等,都把強化假定性的“反故事”、“反情節”、“反戲劇”的形式與戲謔反諷、調侃解構的反文化意向推到極致。 的確如王曉鷹指出的,“隨著‘新時期戲劇十年’成為歷史,‘現實主義’戲劇已經不再具有‘唯我獨尊’的一統天下,‘假定性’在戲劇演出中的‘合法地位’已經不再成為問題”。(注:王曉鷹《戲劇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國戲劇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頁。)新時期戲劇藝術的巨大成就是伴隨著假定性、寫意性美學的合法化與崛起,真實性美學的衰落而取得的。 電影的假定性與戲劇有關但又有自己的獨特性。 《電影藝術詞典》在闡述“假定性”時說,“假定性制約著電影,使它不可能是物質現實的刻板、機械的翻版和模擬,而使它具有記錄、取舍、揭示等多方面的藝術功能。電影藝術家能夠根據特定的創作意圖去汲取電影素材,選擇和概括生活中為每一部作品所需要的形象,挖掘出這些形象間的對應及互相關系”。(注:《電影藝術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版。) 就此而言,電影藝術的假定性是指電影通過獨特的電影媒介和手段對客觀對象的非原樣的表現,即所表現的東西大于原來的東西。 德國心理學家魯道夫·愛因漢姆曾指出:“電影,和戲劇一樣,只造成部分的幻覺,它只在一定程度上給人以真實生活的印象。電影不同于戲劇之處,在于它還能在真實的環境中描繪真實的——也就是并非模仿的生活,因而這個幻覺成分就更加強烈。”(注:[德]魯道夫·愛因漢姆《電影》(修正稿),楊躍譯,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頁。)因而不妨說,電影、電視更容易造假,它更容易給人以真實性幻覺,因而面臨著比之于戲劇藝術更為艱難的破除真實性幻覺的任務。 從根本而言,影視藝術也是一種獨特的話語方式,它不是現實或歷史本身,而是對現實或歷史的敘述(用影像和影視語言)和虛構。因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非敘述的,非再現的……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注:[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政治無意識》,康尼爾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 但這只是一種廣義的假定性,或者說是屬于現代主義美學階段的假定性。這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幾乎一切藝術都具備的本質的假定性。就影視藝術而言,出現在銀幕或熒屏中的影像,它既然已經經過了攝影機的選擇、攝錄和再創造,已經不是現實本身而是一種話語方式,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假定性——更不用說經過藝術家的匠心獨運之后。正如普多夫金所說,“實際發生的事件與它在銀幕上的表現是有區別的”,正是這種區別形成了影視藝術的假定性。因而這是寬泛的廣義的假定性,也是最根本最本質意義上的藝術假定性。 但我在這里關注的不是寬泛意義上的,無論影視制作者自覺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實際上都在作品成品中或觀眾接受時要產生假定性,它不是現代主義階段風格化的主體表現,而是一種編、導、演創制群體有意追求,甚至是有意進行夸張性表現的假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假定性浸潤了濃郁的大眾文化、后現代文化色彩,具有強烈的解構顛覆性和反諷、戲擬色彩和娛樂化、消費性指向,是后現代文化語境的產物。 綜上所述,我認為假定性有三個層面的含義或曰大致的發展階段: 其一,如前所述廣義的幾乎伴隨著電影藝術的發生而來的藝術假定性。 在此階段,假定性與真實性的關系基本和諧或曰平衡,且假定性還常常從屬于真實性,常常被“視而不見”地掩飾在真實性幻覺之中。盧米埃爾的“活動照相”,就是以對日常生活的記錄為其特征并從而奠定了紀實主義美學傳統。稱得上是對紀實美學的理論總結和提升的巴贊也堅持認為影像可以真實再現現實。 從以梅里愛為開端的戲劇化電影美學開始,電影開始向戲劇學習,甚至創造一系列純屬幻想的甚至荒誕的影片,表現出向假定性美學一端的靠攏,假定性與真實性開始相抗衡。 其二,現代主義美學范疇的假定性。 電影中現代主義美學范疇內的假定性或表現性美學,也可謂歷史悠久。如有論者認為:“強調電影假定性的美學流派,從梅里愛開始,經歷了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和歐洲‘先鋒派運動’,在法國新浪潮電影中得到發展,后來的‘新德國電影運動’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注:彭吉象《影視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頁。)這種假定性既表現在色彩表現、影像構圖等方面,也表現在銀幕形象的怪異、非現實性等方面,如德國表現主義電影中著名的“吸血鬼諾費杜拉”、“卡里伽俐博士”等形象。 實際上,在電影史上,帶有現代主義意味的假定性美學也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美學追求。電影史上像《黨同伐異》對線性敘事的打破,對不同時空的共時性并置,也可以視作一種假定性很強的電影結構方式,因為這種結構方式體現了導演強大的主體性對現實的干預和重新結構。《公民凱恩》、《羅生門》等對全知視角(全知視角是一種較為典型的強化或執迷于真實性幻覺的視角,它相信攝影機是萬能的,鏡頭所攝都是真實的)的打破、各個分段結構之間的矛盾互否和歷史的虛無主義思想;《紅色沙漠》中通過人為上色,實施對影片中物象的空間邏輯的破壞,營造出一種非現實的、心理化的表現性空間;《八部半》中費里尼通過對時間的非理性聯系來營造非現實的時空,以及“自我”和“本我”的不斷搏斗而形成的“復調對話”的結構,等等,均是假定性美學之一定程度的表現。 路易斯·賈內梯曾區分過現實主義風格/形式主義風格兩種電影,其中的形式主義風格比較接近現代主義的表現性追求,“在風格上是十分絢麗的。形式主義影片的導演們注重以他們的主觀經驗來表現現實,而不考慮別人對此有何見解。形式主義者由于把自我表現看得至少與主題本身同樣重要,因此也常常被稱作表現主義者。表現主義者所關心的常為精神的和心理的真實,為了對此作最好的表達,他們就將題材加以變形。攝影機成了評論主題的手段,強調內在實質超越客觀外表。在形式主義影片中,存在著高度的修飾和對現實的重新塑造”。(注:參見[美]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第2—6頁的有關論述,胡堯之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版。,第4頁。) 其三,“后假定性美學”階段。 在此階段,假定性美學浸潤了大眾化、娛樂化和商業性色彩,是假定性對真實性美學的絕對勝出,從某種角度看也是通常我們所說的真實性/假定性辯證關系的錯位與失衡,歷史與現實、虛擬與真實被并置,時間空間不再遵循理性原則,真實的幻覺被徹底打破。 從哲學和文化的層面上看,與現代主義的假定性美學相比,在后假定美學中,主體的位置發生了嚴重的移置,主體不再是理性化、中心化的主體,而是非主體性甚或反主體性的。主體常常被假定為一種無生命無深度的符號,一種空洞的能指,它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命運,也喪失了對社會現實主動介入、干預的主體擴張式的意向動力,陷入一種喪失主體之主觀能動性的不確定之中。與此相應,導演非但不試圖在影像中寄托強大獨立的主體性,而是有意顛覆、反諷理性主體,既嘲笑別人又嘲笑自己,體現出一種游戲解構的反理性文化的另類文化姿態。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后假定美學的哲學觀與現代主義假定性有了很大的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不同,這一美學原則屬于后現代美學而非現代主義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