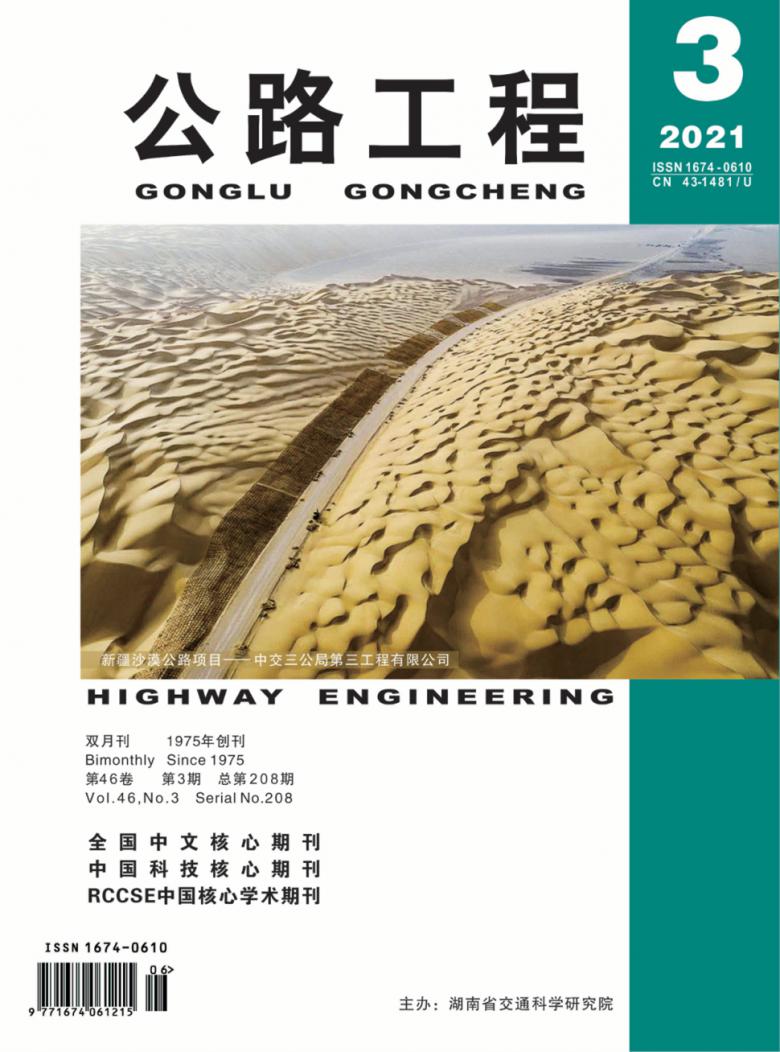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
左 鵬
【內容提要】本文以宋元時期的瘴疾為討論對象,意在揭示歷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與華夏文化擴散之間的關系。根據宋元時期史書的記載,瘴疾的分布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區域;其分布地區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各地區瘴情的輕重差異,反映了此地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淺程度。宋元時期醫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論上有深化,證治上有提高,最終使傳統中醫理論得到突破,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在瘴疾的預防方面,醫家不僅強調習其風土的重要性,而且開始以中原醫學知識改變南方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這一時期有關瘴疾的記載表明,疾病對人體自然機能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文化形態變遷的表現。
【關 鍵 詞】瘴疾/宋元時期/南方地區/文化變遷
【 正 文】
有關瘴、瘴氣、瘴病的研究,學者們已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別值得提出。(注: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頁。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地理學報》第48卷第4期(1993年4月),第304-315頁。范家偉:《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漢學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7-58頁。關于“瘴”的研究成果的綜述,可參看范家偉上引文及拙作《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的有關論述。)蕭璠闡明其著述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對南方的疾病、醫療衛生情況的梳理、分析,探討其“對當時人們的活動,特別是南遷北人的影響,藉以增進我們對歷史上中國向南方的發展這一重大課題的一個側面的了解”。因此,蕭氏利用大量的文獻,重建了漢至宋時期南方的自然環境、生活習俗與某些地方流行疾病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疾病對南方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此文雖然在某些細微之處還可以商榷,但是他提出的觀點令人信服。龔勝生除了描述瘴病的分布變遷以外,還集中探討了瘴病對南方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并且指出,兩千年來中國南方的土地開發史和瘴域變遷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此文是大陸學界較早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疾病的成果。范家偉則從人口遷移與疾病感染的角度,以瘴氣病為例,探討了六朝時期北人南遷進入嶺南地區時所面對的疾病威脅,對六朝時期瘴氣的論述頗為全面。總之,這三篇從醫療與社會的角度來研究瘴氣的文章,都對后來的研究者有著積極的影響。上述三位學者對于瘴疾的看法,都是以現代醫學對疾病的認識為基礎而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瘴疾作為一種地方性疾病,同樣也是某種觀念形態的反映。筆者曾從這一角度,闡釋了漢唐時期的瘴疾,(注:左鵬:《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257-275頁。)本文擬對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景觀馴化:宋元文獻記載中的瘴疾
兩宋時期文獻中記載的瘴疾,主要集中在今廣東、廣西、福建、四川、重慶、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區,以及越南等地。其中以廣東、廣西為主的嶺南地區的記載最為多見,但行文中使用的地名往往不一樣,有廣南、南方、嶺海、嶺外、嶺表等稱呼,譬如“廣南瘴癘之鄉”,(注:《宋史》卷196《兵志十》。)“南方夏秋毒暑煙瘴”,(注:(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8,神宗元豐六年八月乙亥。)或“嶺外瘴毒”,(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30,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丙申。)等等。因此,朝廷對任職嶺南的官員優渥有加,規定“嶺南官除赴以時,以避炎瘴”;(注:《宋史》卷7《真宗紀二》。)史書表彰關心民瘼的官員“在嶺表時,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浸”。(注:(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19,神宗熙寧六年“周敦頤卒”條。)諸如此類關于嶺南地區瘴情的記錄,反映了這一時期嶺南一帶是人們所公認的瘴域。
具體而言,廣南東路的春州(治今廣東陽春)、梅州(治今廣東梅州),史書稱其“炎癘頗甚”,(注:《宋史》卷90《地理志六》云:“廣南東、西路……山林茂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另,因所引各條資料有時間先后之分,而各代政區及名稱亦廢置不一,為簡便計,概以所引資料之地名為準,不另考其沿革。)其他的地方如恩州(后改名南恩州,治今廣東陽江)、循州(治今廣東龍川)、新州(治今廣東新興)、英德府(治今廣東英德)等州也是瘴癘嚴重之區,而以英德府和春州最為厲害,英德府被稱為“人間生地獄”;(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春州在當時更是聞名遐邇的瘴毒之地,當地的志書謂其“與夷獠雜居,瘴癘以春州為首”,(注:(宋)祝穆:《方輿勝覽》卷37《南恩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0頁。)《宋史》卷270《李符傳》的記載則代表了當時普遍的看法:“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熙寧六年(1073)春州被廢為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里的瘴毒可畏,獲罪貶官至此的人大多無以生還。(注:(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有《改春州為縣》條:“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豐(當為熙寧)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中華書局,1997年,第7頁。)
廣南西路的賓州(治今廣西賓陽南)、桂州(治今廣西桂林)、高州(治今廣東電白)、雷州(治今廣東海康)、化州(治今廣東化州)、欽州(北宋時治今廣西靈山,南宋時徙今廣西欽州)、容州(治今廣西容縣)、宜州(治今廣西宜山)、邕州(治今廣西南寧)、廉州(治今廣西合浦)、昭州(治今廣西平樂)等地的瘴疾也多見于記載。(注: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7、65;《宋史》卷196《兵志十》、卷300《徐的傳》;《方輿勝覽》卷42《高州》、《容州》,卷159《選舉志五》;《新安志》卷10《定數》。)周去非(1135-1189)亦曾詳細描述嶺南之瘴地,說明的是南宋初期的情形,從中可以看出嶺南各地瘴情輕重程度的一些變化:“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為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廣東以新州為大法場,英州為小法場,因并存之。”(注:(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4,楊武泉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第151頁。)徐夢莘同樣記錄了當時官員的看法:“雷雖在廣南,其地瀕海,絕無煙瘴,土風不異于中州。”(注:(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54,靖康元年九月壬申。徐氏是書成于紹熙五年(1194),所載史事起自政和七年(1117),迄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由此可知廣西各地之瘴是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變化的。)這說明在濱海一帶地方瘴疾的分布較少,已大不如前人的記載了。另外,今貴州之瘴地較少見于載記,宋時在大觀年間(1107-1110)只短暫地建立過黔南路,但“時雖建城塞,其地荒瘴,遣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注:《九朝編年備要》卷27,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條。)故很快就并入了廣南西路。
福建路所記載的瘴地集中在劍州(治今福建南平)、泉州(治今福建泉州)、汀州(治今福建長汀)、漳州(治今福建漳州)。荊湖南路一些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如辰州(治今沅陵)、澧州(治今澧縣)、全州(治今全州)、邵州(治今邵陽市)、道州(治今道縣)、永州(治今零陵)、潭州(治今長沙市)、武崗軍(治今武岡)等都有瘴疾的記載。(注:參見《宋史》卷191《兵志五》、卷193《兵志七》、卷331《周沆傳》;(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丑。)
江南西路靠近嶺南的地方,瘴疾的記載也是史不乏書,如南安軍(治今大余)、虔州(后改名贛州,治今贛州市)等。(注:關于南安軍瘴的記載,參見(宋)陳次升《讜論集》卷5。)虔州又以龍南、安遠二縣瘴疾最甚,宋代方勺在《泊宅編》卷中中說:“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為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宋史》卷473《秦檜傳》的描述也為此提供了確鑿的例證:“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
川蜀一帶的瀘州(治今重慶瀘州)、黎州(治今重慶漢源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維州(后改威州,治今四川理縣東北)、茂州(治今四川茂汶)、戎州(后改名敘州,治今四川宜賓)、達州(治今四川達州)、咸淳府(治今重慶忠縣)、長寧軍(治今重慶萬州區)等從唐代以來就是有名的瘴地,盡管這些州前后的轄境有很大變化,可是“地苦瘴毒”的記載未曾減少。(注:參見《新唐書》卷180《李德裕傳》;《方輿勝覽》卷55《雅州》;《宋史》卷7《真宗紀二》;《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4,神宗元豐四年七月壬子。)越南,宋時稱交趾或安南,曾是宋王朝開疆拓土的對象,但由于山險路僻,霧潦瘴毒,宋軍死亡頗多,在朝廷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最后只得作罷。(注:據《宋史》卷270《許仲宣傳》載:“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因此,許多大臣對出兵交趾持反對態度,稱“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宋史》卷293《田錫傳》)。又(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6神宗熙寧十年十二月甲辰“張方平上書”條,載:“復發于安南,使十余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
兩宋時文獻記載的瘴域大體集中在以上地區。《元史》記載簡略,但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川蜀、越南等地依然是人所憚行的瘴域。江西、福建與川蜀一帶都只記載部分地區存在著瘴。另外,文獻新增加的一個瘴地是云南,《元史》卷196《也速答兒傳》中就記有官員游宦云南染瘴而逝之事:“武宗時,(也速答兒)由四川遷云南……南征叛蠻,感瘴毒,還至成都卒。”其實,早在唐朝時云南就出現過很多瘴的記載,但由于這一地區先有南詔的崛起,后有大理的建國,其與唐宋王朝的官方交往遂甚為寥落,因而在中原王朝所修撰的史書中,此一時段的狀況鮮有反映。(注:《宋史》卷488《外國傳四》記載大理國的情況僅寥寥數行,卷204《藝文志》中所錄有關云南的地理類著作亦不多。)元朝統一后云南重新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往來增多,遂使瘴疾的記載又出現在官方的記錄中。這個現象所隱含的意蘊似乎值得揣摩。理論上,如果云南在唐朝前期、元朝時都是瘴地,那么唐末兩宋時自然也不例外,而偏偏這一時段的資料中不見云南有瘴疾,換言之,瘴疾在文獻中的記載與其實際的分布區域之間發生了某種游離,果如上文之言,將其歸于記載的缺失固然簡潔,但假使考慮到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史料都出自中原人士之手,表達的是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觀點,或者說是一種偏信之言,則讀者也許會有新的想法。綜觀古籍中記錄的南方各地瘴疾的起伏變化,至少可說明如下問題:
其一,在古人心目中,瘴疾既可以是致病之因,又可以是某種疾病,它產生于暑濕的風土之中。根據這樣的觀點分析,瘴疾應該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分布區域,且在整體的醫療衛生條件沒有突破性的改變之前,這個區域不會有所謂的逐漸南移或縮小的趨勢。
歷史時期文獻所記載的瘴疾的地域范圍其實并無多大的改變。如果將筆者對漢唐時期的瘴疾的研究、上文的論述以及龔勝生之文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就可看出不同時期瘴疾的分布大體都以今兩廣、福建、云南、貴州以及江西、川蜀的部分地區為主(注:前引蕭璠之文在論述南方的瘧疾時,將古時之瘴疾徑指為瘧疾,亦認為“古代人已明白地觀察到:南方,相對于北土來說,是個瘧疾盛行的地區。”接著他又具體地描述了漢宋間文獻記載的南方各地瘧疾流行的情況,可參看。不過,筆者認為,瘴疾有多方面的含義,應該分成不同的層面來闡釋。),各時期的差異只是體現在整個區域內部的變化上,即漢唐時期由點到線到面地擴展,宋元以后則有了輕重程度之別,或者某些地方在某時段不見錄于史冊。這些既反映了北人或華夏文化向這些地域擴張的進程,也符合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過程。另外,盡管現在已有學者研究證實,瘴疾包含了多種不同的疾病,(注:參見馮漢鏞《瘴氣的文獻研究》,載《中華醫史雜志》1981年第11卷第1期,第44-47頁。)但在瘴疾主要是指瘧疾特別是惡性瘧疾這一點上,學者們并沒有多大的分歧。現代流行病學對瘧疾流行區域的調查表明,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有瘧疾分布,且由北而南越來越嚴重,總的趨勢與緯度相平行;(注:參見耿貫一主編《流行病學》(下)(人民衛生出版社,1980年)第183頁。)這樣的區域流行態勢,從古至今應該是相對穩定的。(注:當然,不能排除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對于我國南北分界線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會造成疾病分布區域的南北推移。但氣候的變化是相當緩慢的,而且文獻不足征,故氣候的波動對疾病流行范圍的影響只能暫不列為本文討論的對象,作前后一致處理(前引蕭璠之文也是如此做法)。龔勝生認為氣候的變化是引起瘴疾分布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此筆者存有異議,認為無論其前提或結論都尚需再加推敲。龔文所持氣候冷暖變遷的理論是以竺可楨先生的研究為基礎的,這一研究迄今已有多位學者補充修正,例如就唐代的氣候而論,滿志敏的研究(見《歷史地理》第8輯,第1-15頁)就表明隋唐時期并非是一個溫暖期,而可分冷暖不同的前后兩期。如果此論不虛,那么不同類型的瘧區也會相應地隨之進退,而并非是一味地南移。在這一方面,前引范家偉之文亦有與此類似的看法,見其文中注72。)既然這樣,那么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瘴疾在近兩千年來呈現出逐漸南移的趨勢。在采用現代醫學手段進行大規模地預防和消滅瘧疾以前,中國的高瘧區大致分布在北緯25度以南的地區,也就是南嶺以南和云貴高原南部地區。(注:參見上海第一醫學院、武漢醫學院主編《流行病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年)第356、183-187頁。書中根據地理緯度的流行特征,將我國劃分成了四個類型的瘧區,分別是:北緯33度以北地區,北緯25-33度之間地區,北緯25度以南地區和西北地區。)以此對照筆者所劃定的瘴疾的范圍,當可發現兩者具有較高的擬合度,瘧疾高度流行的高瘧區和中度瘧區的山地基本上可歸入歷史時期文獻所記載的瘴地之中。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古代瘴疾的分布區域應當是大體穩定的。
其二,文獻中瘴疾在各地分布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上文闡述的云南史料對此已有所說明,與此相似的是青海一帶的“瘴氣”,(注:需要指出的是,文獻中青海一帶的“瘴氣”的性質與南方的完全不同,可參考筆者在《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中的闡述。)在唐以前亦屢有所見,兩宋時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就不再出現在史書的記載中。比如貴州,唐以前的文獻中貴州地區甚少有瘴疾的記載,其地基本上是少數民族所聚居的羈縻州縣,為中原王朝勢力所不及。宋朝時曾短暫地設置了黔南路,但不久即廢入廣南西路。其時王祖道以虛辭徼富貴,遂促成此事,被蔡京譽為“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實際情形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根本不曾歸服款化。(注:《宋史》卷348《王祖道傳》。)元代對貴州的記載明顯增多。明朝永樂十一年(1413)正式設立貴州布政使司,此后該地區瘴疾的記載的分布也比前代更為廣泛。(注:參見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和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布與變遷》(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2期)兩文中的有關說明。)故大體可以認為,史書中所記錄的瘴地的分布情況,大體折射出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消長變化。
其三,在華夏(漢)文化占主導地位以前,瘴情在南方各地的輕重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地為華夏(漢)文化所涵化的深淺。到宋元時期,華夏(漢)文化滲透、改造這些地區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之中。從上文所引述的資料中,可以尋繹出某些蛛絲馬跡。如以雷州為例,北宋時的人們“說著也怕”,到南宋初期產生“瘴乃稍輕”的看法,再后來則認為“絕無煙瘴,土風不異于中州”。這就是說,瘴明顯地減輕直到消失之后,地方的土風就逐漸與中原地區的類似乃至相同了。如此說來,則瘴疾與中州之氣就是相對應的事物且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瘴情的輕重有無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華夏(漢)文化對南方各地影響程度的大小。換言之,是歷史時期北人南遷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影響,(注:參見黃濱《歷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動的主流變遷初探》,載《廣西師院學報》1995年第1期。)才使嶺南的一些地方呈現出了與往日氣質迥異的景觀。
再以桂林為例。雖然唐代白居易在詩中稱“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注: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全唐詩》卷442。)但實際上白居易并沒有到桂林生活的經歷,不能知其詳情,再說這樣的送別壯行之詩,一般都是褒揚勸勉之辭,不宜將目的地說得一無是處,因此詩中之語不能全然置信。根據前文摘引之史料,北宋時期本應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荊湖南路轄境內的全州與永州了,這意味著此時來自北地的戍卒并不適應桂林的風土,但是到南宋以后,士大夫們卻認為:“自荔浦以北為楚、以南為越。今靜江(即桂州,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氣,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鄉,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注:(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3《輿地考九》。)所謂的“有中州清淑之氣”,在北來士人眼中,就是指此地已歸化于中原華夏(漢)文化之中,不再屬于異族的瘴鄉蠻土了。不難想見,與唐代一樣,宋元時期的“瘴”依然與“蠻”有著不解之緣,“瘴”的深淺是與“蠻”的生熟聯系在一起的。(注:史書中多有以是否熟悉漢文化為標準來判斷少數民族歸化程度的稱呼,如熟夷、熟黎、生黎、生獠等。)另外,梅莉等在分析明清時期瘴疾的分布與變遷時,集中討論了北方移民的南遷與瘴區的南移、縮小之間的關系,認為經濟開發是瘴區縮小、瘴病減輕的主要原因。假使換一種說法,應可作如是理解,即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逐漸成熟,也就是中原華夏文化不斷地涵化少數民族文化的過程。既然如此,則將瘴的輕重有無看作是一種觀念的變遷,就算不得唐突了。換言之,由于人們以華夏(漢)文化為準繩持續地影響、馴化南方各地的景觀,使得這些地方逐漸與中原的風氣趨同,因此人們認為是“中原清淑之氣”沖淡、疏減了瘴氣。這一文化變遷同樣反映在宋元時期的醫書醫方之中。 二、風土改良:宋元醫家視野中的瘴疾
宋元時期的醫書醫方是以另外的方式來表述嶺南一帶的文化變遷的。在醫家的眼中,瘴疾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疾病,或者至少是致人患病的因素。在面對瘴疾的威脅時,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如何解釋其病因病機,以及采取積極的措施進行救治并阻止其蔓延。然而這種努力要受到醫家的知識背景和醫療水平的制約,醫家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他認識疾病的方式,其醫療水平則決定了疾病救治的有效程度。唐以前的醫家對瘴疾還處于感性認識的階段,在治療方面也顯得比較粗略;而兩宋時期的醫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大有進展,在此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其一,醫家根據《內經》等醫典中的風土觀對瘴疾的原因給予了合理的解釋;其二,醫家對瘴疾在治療上的爭論與改進;其三,醫家面對瘴疾所提出的風土馴化與改良的要求。
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肇基之地,在宋以前這里一直都是文明的中心地所在,其周邊的民族則處于相對落后的階段,這使黃河流域的人們認為他們所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國”,是文物豐盛的禮儀之邦、世界的中心。這里地處暖溫帶,四季分明;有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草木豐茂,因而造就了發達的農耕文明。在如此優越的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中,人們所形成的風土觀,就是認為這里土厚水深,陰陽合和,最利于萬物的生長發育,即所謂“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眾和之氣,產育庶物”。(注:《鹽鐵論·輕重》,王利器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100頁。)其四周則是蠻夷戎狄所生活的地方,為積陰或積陽的“不毛之地”,不利于人的生存,特別是南方地區,陽氣常泄,水土惡弱。這一風土觀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構成了中醫理論的基礎,(注:此亦可參考前引蕭璠之文的有關論述。)并且始終影響著醫家對地方風土的評價。(注:梁其姿在《疾病與方土之關系: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一文中,談到了元以后醫界的方土觀經歷了從五方觀向南/北或東南/西北二元模式的轉變,洵為的見。梁文進一步指出:“元以后醫家的方土觀強化了西北與東南的對比,他們認為西北水土高爽,外在致病因素較少,人的稟賦又較強,不易產生疾病。而東南方人的稟賦較弱,容易被卑濕水土所產生的各種致病因素影響……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直至明清仍以西北及北方為文明的起源,雖然當時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東南、甚至嶺南地區已是較發達的地區,但是歷史上的政治與文化中心仍然被視為有最強元氣的地域。”(載《性別與醫療》,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年,第165-212頁)筆者以為,北方之所以一直被視為元氣最強的地區,是因為中醫早期的理論體系、治療方法,以及由此撰成的醫書如《黃帝內經》等,都是以北方的氣候、地理環境為依據的,它們被后世的醫家奉為圭臬,從而使北方的風土成為了人們認識的“原型”。)
南方的瘴疾從其出現之日起就被認為與外部環境的暑濕密不可分,如《后漢書》卷54《馬援傳》、《隋書》卷31《地理志下》說“下潦上霧,毒氣重蒸”,“自嶺已南二十馀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醫書中則說瘴疾的產生是因為“南地暖,故太陰之時,草木不黃落,伏蟄不閉藏,雜毒因暖而生”,(注:(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10,溫病諸候之瘴氣候條。)都表達了類似的思想,所以瘴氣最初多指山嵐溪源蒸郁而生的毒氣,到北宋末年時,這樣的認識隨著醫家對瘴的了解增多而不斷深化。如宋徽宗時編撰的《圣濟總錄》,就詳細地論述了瘴氣發生的原因、時間及拯治方法,其中對瘴氣原因的分析,顯示出編撰者極力將它嵌入傳統中醫理論框架內的企圖,其文曰:“傳言:瘴氣乃山川毒厲之氣,又云江山霧氣多瘴,凡以其氣郁蒸而然也……且陽生于子,盛于巳;陰生于午,盛于亥;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長。而廣南位當巳午,則陰陽之氣蘊積于此可知矣。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西北陰也,土地高厚;東南陽也,地土卑下,而廣南屬東南,則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土地卑下而陰陽二氣所蘊積,是以四圍之山,崇高相環;百川之流,悉皆歸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蟄蟲不伏藏,寒熱之毒,蘊積不散;霧露之氣,易以傷人,此岐伯所謂南方地下水土弱,蓋霧露之所聚也,故瘴氣獨盛于廣南。”(注:(清)程林:《圣濟總錄纂要》卷5,瘧疾門之瘴氣條。)這一段話先轉述了前人關于瘴疾的種種傳言,繼而按照宋代官方所推重的五運六氣學說和《內經》的思想來闡述瘴之緣由,雖然將廣南劃歸到東南部顯得有些削足適履,但它不再僅僅以南方暑濕的特性一言以蔽之,而是從經典醫書中找尋依據進行解釋,使之較為圓滿地進入了中醫理論體系,為后來的醫家進一步的探究指明了一條合理的路徑。至南宋初期,李璆撰成《瘴瘧論》,開篇即論述瘴氣所生之由:“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以作也。”接著他又從嶺南的氣候環境與人體病理之間的關系上仔細加以論證,強調要根據西北、嶺南之人不同的體質狀況來用藥:“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類,病者多宜發散轉利,傷寒、溫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斃者,氣常收斂故也;嶺南陰氣不收,又復卑濕,又人食檳榔之類,氣疏而不實,四時汗出,病者豈宜更服發散等藥,此理明甚!”(注:《嶺南衛生方》,中醫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0頁。)這就完全立足于中原傳統醫學理論,使人們對瘴疾有了清楚的認識,從而為臨證治療確立了基本原則。
在瘴疾的治療方面,隋唐以前就有針對嶺南的風土、疾病而編撰、搜集的醫方見于著述,從流傳至今的有關醫書中可知,直到唐朝初年,瘴疾依然被分列于不同的疾病證候類別,似乎表明醫家對瘴疾的了解還很模糊。當然,六朝時有的醫家已將某些瘴病與瘧疾相比照,稱之為“山瘴瘧”,其病癥與瘧疾類似,主要表現為使人“發寒熱,休作有時”,隋朝時醫家則提出“夫嶺南青草、黃茅瘴,猶如嶺北傷寒也”的說法,(注:《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11,瘧病諸候之山瘴瘧候條;卷10,瘧病諸候之瘴氣條。又,“山瘴瘧”之稱,南朝宋陳延之《小品方》已有提及。)這說明醫家是從癥狀,而非病因上來推定兩者之間的聯系的;而且他們遵循《內經》的思想所建立的中醫理論,在面對新的氣候環境時,還不能合理地解釋瘴疾與瘧疾的關系。《素問·瘧論篇》認為:“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夏傷于暑,秋必病瘧”,認為瘧疾是由于人感“六淫”之氣而產生的病癥,瘴瘧則是因“山溪源嶺嶂濕毒氣”而引起的,兩者的病因不一樣,所以隋唐乃至北宋時期的醫書,譬如《外臺秘要方》和《圣濟總錄》等,雖然都把瘴疾大體歸為瘧病之一類,但往往對其病因另有說明,并不將瘴疾徑直指為瘧,正好反映出這種理論的斷層。應該指出的是,王燾的《外臺秘要方》卷5《瘧病·山瘴瘧方》曾摘引前代佚書《備急方》中的觀點,認為瘴與瘧實際上是同一種疾病,而且所論頗詳。(注:王燾《外臺秘要方》卷5之《瘧病·山瘴瘧方》云:“備急:夫瘴與瘧,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后熱,或先熱后寒,嶺南率稱為瘴,江北總號為瘧,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然南方溫毒,此病尤甚,原其所歸,大略有四,一山溪毒氣,二風溫痰飲,三加之鬼癘,四發以熱毒,在此之中,熱毒最重。”高文鑄校注,華夏出版社,1993年,第84頁。)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來看,兩宋時的醫家似乎沒有把二者等量齊觀,如《圣濟總錄》認為:瘧疾“或本于痰,或本于瘴癘,或本于鬼神,或本于邪氣”,即瘴癘只是感染瘧疾的原因之一,瘴包含在瘧之中;而瘴同樣包括了多種疾病,在治療上也有種種不同,《圣濟總錄纂要》卷5說“閱諸方論,治瘴氣之法不一,或謂其癥與傷寒相類,有在表可汗者,有在里可下者,有在膈可吐者,或以治瘧法治之者”,這說明在當時的醫家看來,兩病各自包容了對方的一部分,不能互相代替。
或許是基于上述的認識,兩宋時的醫家對瘴疾的治療顯示出了一個提高、細化的過程。比如,蘇軾、沈括的《蘇沈良方》卷3中記載了一條治療瘴疾的方子,此方認為“瘴疾皆因脾胃實熱所致,常以涼藥解膈上壅熱,并以此藥通利,彌善;此丸本治嵐瘴及溫瘧,大效”,大概是把瘴疾看作了外感病邪化熱入里,壅滯脾胃而產生的病癥,與溫瘧稍有差別。稍后唐慎微在《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卷5《水氣》中提出瘴疾是由濕所引起之疾,并可以與它病同治:“江湖間露氣成瘴,兩山夾水中氣瘧,一冷一熱相激成病癥,此三疾俱是濕為,能與人作寒熱,消鑠骨肉,南土尤甚,若欲醫療,須細分析,其大略皆瘴類也,人多一概醫之,則不差也。”這樣的觀點到南宋時就不再被認為正確了,此時的醫家指出,瘴瘧病“雖是時行之疾,然老少虛實,受病有淺深,大率不同”,應當“隨癥用藥,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萬一不能取效也”,(注:(宋)陳師中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指南總論》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指南總論》為南宋許洪所撰,主要簡述藥物合和、炮制及幾十種病癥、治法和用藥。)因此,醫家按照瘴病癥狀的不同,將其加以細分,且對癥各有療治之法。
具體而言,南宋至元初醫家對瘴疾的看法,可從宋末元初的醫僧繼洪所編之《嶺南衛生方》中窺見大概。書中輯錄有李璆《瘴瘧論》、張致遠《瘴瘧論》、王棐《指迷方瘴瘧論》、汪南容《治冷熱瘴瘧脈證方論》、(注:《嶺南衛生方》之“前言”疑王棐與汪南容同為一人,蕭璠之文中雖認為此說尚待考,但亦認為“是極有可能的”。筆者曾略加考證,認為此說當可信從。)章杰《嶺表十說》、繼洪《衛生補遺回頭瘴說》、《治瘴用藥七說》、《治瘴續說》等,全書探討了嶺南瘴瘧的病因病機,在防治原則上主張重用溫法、慎用清法。此書各篇所作時間不一,如能考定其大致作成之年代,當可見出當時醫家認識上的進步。據有關資料,筆者粗略推算,李、張二文當作于南宋紹興年間,(注:李、張二人傳記分別見《宋史》卷376、377。)王棐的《指迷方瘴瘧論》要稍微晚出一些,然亦當寫成于周去非撰寫《嶺外代答》之前。(注:南宋初期宦游嶺南者如范成大、周去非等人對瘴的記錄,已為人所熟知,但如果比照王氏與周氏之作,就會發現兩書中有關瘴疾的文字頗多雷同,周氏大概是在參考王氏文字的基礎上,綜合他書而作。)關于章杰《嶺表十說》的時間問題,前引蕭璠之文中提到一條線索似可作參考。(注:前引蕭璠之文曰:“《宋會要輯稿》卷一六四《刑法》一之三六記紹興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杰言……’,撰《嶺表十說》者或許即是其人。”)又據《嶺表十說》的內容推測,章杰可能與李璆、張致遠為同時代人或稍后一點。釋繼洪為宋末元初人,然其所述,大抵踵事增華而已。
從李璆和張致遠兩人的《瘴瘧論》來看,南宋初年醫家在辨證施治時,都非常強調異法方宜的原則,這可說是對嶺南陋醫的撥亂反正,此前嶺南的醫家全然不顧地方的風土以及民眾的體質迥異于北方,盲目執守成方,將嶺南之瘴與嶺北之瘧視作同種疾病進行療治,結果常常造成誤診,甚至葬送患者的生命,所以李璆感慨萬分,嘆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章杰的《嶺表十說》比較注重瘴疾的預防,他抨擊了當時嶺南之民喜食檳榔、北來之人往往飲酒避瘴的做法,同時認為嶺南之病不能全都概括為瘴疾,“嶺外雖以多暑為患,而四時亦有傷寒、溫疫之疾,其類不一,土人不問何病,悉謂之瘴,治療多誤,天閼者何可勝數。”“仆觀古方,飲溪澗水中毒,令人失音,則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注:《嶺南衛生方》,第4、58、60頁。)王棐的《指迷方瘴瘧論》是他游宦桂林等地時,在研究嶺南的方書和李、張二文的基礎上,以自己的醫療經驗對瘴病的救治和預防作了一番評價。在他的時代,嶺南的醫療水平已大有提高,醫家不再將所有的病都稱為瘴了,往日的瘴瘧也被細分為冷瘴、熱瘴和痖瘴,只是在治療方面還不如人意。王氏認為冷瘴就是嶺北的痎瘧,熱瘴乃熱氣蒸郁或飲食積熱所致,痖瘴疑為傷寒失音之證或中風失語之證;周去非則說“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痖瘴以失音傷寒治”。從這些病名和治則的比照可以看出,瘴疾不斷地向著瘧疾、傷寒等嶺北的疾病靠攏,這就在無形之中拓寬了醫家對瘧疾的認識。到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許洪編纂《指南總論》時,又對傷寒與瘴瘧等疾病進行細分和區別,它提出了十六條傷寒之證,濕溫、溫毒、熱病、溫病、溫瘧、晚發疫癘等名列其中,繼而特別指出:“中暑、傷痰、食積、虛勞、瘴瘧、腳氣與傷寒相似,而實非傷寒。此證人不曉,皆言即傷寒也。”(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指南總論》卷中。)這種精細的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又出現由博返約的趨勢,南宋末年時,醫家對瘧疾進行了理論上的歸類整合,如楊士瀛的《仁齋直指》卷12在闡述痎瘧時,就只把瘴瘧與風瘧、寒瘧、暑瘧、濕瘧、牝瘧、食瘧等數種平行列出,而于其總論曰:“風寒暑濕,邪自外來;飲食居處,邪由內作,此痎瘧感受之胚胎也,豈特夏傷于暑,秋必為瘧哉!古人蓋以其受病最多者言之耳。”雖為古人開脫,其實表達了醫家對痎瘧病因認識的突破,它不僅是對傳統中醫理論的更新,而且暗示著中醫所涵蓋的地域范圍的擴大和環境適應性的加強,其中北人南遷所帶來的文化的擴張與包容,當不可小視。
當然,按照《素問》中的思想,高明的醫家應該“治未病”,即提醒人們既要亡羊補牢,但更應未雨綢繆,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攝節有致,未病先防。北方人認為南方水土惡弱,極不利于人的健康,故而在南行時,往往采取很多措施來防治可能侵害人體的疾病,如隋唐時期有人佩帶絳囊防治瘴氣,(注:參考范家偉《中國中古時期絳囊系臂與辟疫觀念》,《“潔凈”的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2000年,第275-302頁;《從醫書看唐代行旅與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05-228頁。)兩宋時醫家強調要講究修養之法,避色節欲等等,這些旨在馴化風土的措施,多以中原醫學的防病養生思想為依據,注重增強南來北人的抗病能力。無論效果如何,其所提示的思想,乃是積極地適應地方風土,以求與土著居民一樣,“久而與之俱化”。當然,這并不是說土著居民從來不會罹患疾病,而是說“生于凌者安于凌”,(注:《圣濟總錄纂要》卷5,諸瘧統論之瘴氣條。)土人已經適應了生在其中的風土。其實,據史料記載,直到宋元時期,嶺南依然是缺醫少藥的地方,當地居民也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意識,“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9,紹興十九年六月辛酉。)針對這種信巫不信醫的習俗,或有任職嶺南的官員請求朝廷頒賜醫書醫藥以接濟百姓,此乃中原醫學知識漸被南方的要因,與醫家的愿望相當一致:“夫民雖至愚,而孰不能趨利避害?況性命所系,曉然易見,若醫者能愈人疾,彼何若不用?蓋嶺外良醫甚鮮,凡號為醫術者,率皆淺陋,又郡縣荒僻,尤乏藥材,會府大邦,間有醫藥,且非高價不售,豈閭閻所能辨,況于山谷海嶼之民,何從得之!彼既親戚有疾,無所控告,則不免投誠于鬼,因此而習以成風者也。近歲北醫漸至,長吏父老,倘能使之轉相傳習,不亦善哉。”從這些呼吁中可以感受到,北醫南至對于改善嶺南的醫療衛生條件當功不可沒,雖然這些人在治療瘴疾時可能因率爾操觚,“用北方傷風、傷寒法,或汗或下”,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畢竟慢慢地改變了“過桂林以南無醫藥”的狀況。不僅如此,在改善生活條件以幫助當地居民抵御疾病侵襲方面,醫家也提出了建議:“嶺外雖以多暑為患,……間有一歲盛寒,近類中州,而土俗素無蠶績,冬不挾纊,居室疏漏,未嘗塞向墐戶。忽遭歲寒,則次年瘟疫必興。醫者之治瘟疫,當以本法治之,而隨其風土氣候,與夫人之強羸,少出入焉可也。長吏父老,當化其民俗,使有御寒之具,庶不蹈于疾疢。”(注:《嶺南衛生方》,第60、10、14、58-59頁。)這些改良南方風土、化成民俗的建議是否得到實施已經不得而知了,但它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而喻。醫家既協助北人適應南方的自然條件,又在努力改善南方居民的生存環境,二者相輔而行,結果就是重塑了南方的社會文化景觀,或許南遷之北人所見所感的“中州清淑之氣”,就呈現在這樣的景觀之中。
總之,宋元時期的醫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顯示出這樣一條軌跡,即在理論上不斷調適深化、在證治上逐漸提高細化,最終使傳統中醫理論得到升華,具有了更強的解釋能力;在瘴疾的預防方面,醫家不僅強調習其風土的重要性,而且更多地表現出以中原醫學知識改造南方風土的熱情,這種嘗試對于促進南方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的改變,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疾病流行與社會文化變遷
宋時的字書往往將瘴疾解釋為“癘”或“熱病”。(注:如《原本廣韻》卷4、《類篇》卷21、《六書故》卷33、《集韻》卷8、《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卷4等均是。)言瘴為癘,實沿襲前代人的看法。宋人已經認識到冷瘴“專與痎瘧相類,秋來則多患此,天涼及寒時少有之,卻與傷寒不同,不傳染,不傳經,無變證,所以易醫”;(注:《嶺南衛生方》,第18頁。)釋瘴疾為熱病,是將瘴疾看作流行于嶺南一帶的地方病,故宋人云:“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于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注:(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10。)又云:“六十七里至興安縣,十七里入嚴關,兩山之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相傳過關即少雪有瘴。”(注:(宋)范成大:《驂鸞錄》,二月二十七日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側面揭示出瘴疾在古人心目中有著相對穩定的分布區域,現存的史料與現代的研究亦已證實這一點。根據前文的分析可知,瘴疾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一個文化符號,其分布狀態的改變以及在南方各地的輕重差異,折射而出的是嶺南地區文化上的變遷。這樣的變遷,同樣透過人們對瘴疾本身的認識過程表現出來,瘴疾在病因病機上被納入中醫理論的范疇,瘴疾在辨證施治時被視作嶺北的瘧疾、傷寒,醫家在瘴疾的防治方面改良風土的努力,揭示出嶺南地區的土著文化逐漸為中原華夏文化所濡化的內涵。
借助現代醫學的眼光來分析宋元時期的瘴疾,也是一件饒有興味的事情。筆者的研究認為,瘴疾是北人南遷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所罹患的疾病,誠如其他學者所說,它雖然包含了某些外感熱病,但主要是指惡性瘧疾。根據瘧疾的流行病學分析可知,瘧疾有兩種流行形式:一是地方性流行,一是爆發性流行。地方性流行常見于高瘧區(即穩定性瘧區),這些地區具備瘧疾流行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相對穩定,導致瘧疾經常性流行,但除嬰幼兒童外,一般人群免疫水平高,因此在穩定性瘧區較少出現爆發性流行。爆發性流行多見于低、中度瘧區,人群免疫力較低,其誘因常常有以下幾種:第一,輸入傳染源;第二,無免疫力人群進入瘧區或由低瘧區進入高瘧區;第三,由于自然或人為條件導致按蚊孳生地增加,或增加了按蚊吸血的頻度;第四,前次流行后的人群的免疫力水平已自然降低。(注:參見耿貫一主編《流行病學》(下),上海第一醫學院、武漢醫學院主編《流行病學》。)中國的低瘧區,即北緯33度以北地區,或者說大體處于淮河以北地區的居民,一般都不具備瘧疾的免疫力,而我國歷史上的移民主體,都是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人群。當這些來自低瘧區又無免疫力的人陸續遷移到南方的高瘧區時,他們很快就會因受到傳瘧媒介——按蚊的攻擊而感染瘧原蟲,發生瘧疾也就在所難免了。但瘧原蟲在人體內還要經過一段潛伏期才出現臨床癥狀,間日瘧通常為8-27天,平均14天;惡性瘧6-25天,平均11天,所以按蚊的叮咬很少引起人們的重視,故古籍中記述瘴時鮮有提及蚊蚋者;再者限于當時的科技水平,人們根本無法弄清致病之由,只好歸之于山林草莽河湖之間的輕煙薄霧,且一概稱之為瘴疾。既然如此,則瘴的流行形式應與瘧疾相似。可是,仔細地分析相關資料,就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某些差異,即瘴疾的爆發性流行,往往由無免疫力人群進入瘧區后引起,多發生在高瘧區。這就是說,上述四條導致瘧疾爆發性流行的因素中,只有第二條與瘴疾最有干系,而其他幾條甚少與焉。
輸入傳染源的問題,從瘧疾的流行動力學來看,一般是瘧疾患者或無癥狀帶蟲者進入無瘧區或低瘧區而引起瘧疾的爆發,高瘧區不應有從低瘧區輸入傳染源的說法。由于古人眼中的瘴疾是流行于南方的熱病,與北方的瘧疾不同,所以在史料中很難找到瘴疾流行于北方的記載,(注:筆者僅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8神宗元豐六年八月乙未條中找到一個例子:“先是,子淵獻議,后五萬人開修溫縣大河陂直河,以回河流。既而雨水、瘴疫繼作,死亡者甚眾。”溫縣即今河南省溫縣,屬于低瘧區,這可能是一次瘧疾的爆發性流行,從何而起已無從得知了。)即使有嶺南的瘧疾患者或無癥狀帶蟲者來到了嶺北,如果他因瘧疾而死亡,當時人們會說他是“染瘴而亡”,但是由他所引起的瘧疾的爆發流行,則不會被人稱為瘴病,而只會看作瘧疾,故第一條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第三條因文獻闕載,也就無法討論。至于第四條,史料記載中有“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注:(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63《仕宦嶺南》。)之說,或許與瘴疾的周期性爆發流行有關,卻難以證明其緣由是人群免疫力的降低,況且寥寥數語,用以立論似乎過于單薄。歸根結底,文獻中所記載的一次次瘴疫的爆發性流行之所以出現在高瘧區,是因為北方經常有大量的人口向南遷移,使得瘴疾呈現出這樣的流行模式,即隨著人群不斷地進入嶺南,瘴疾就因此頻繁地爆發;隨著人群所至之地點的逐漸增多,瘴地的分布也就會越來越密集。
瘧疾的流行病學分析還表明,感染瘧疾之后,身體對瘧原蟲產生一定的免疫力,這種免疫力會隨著再感染和反復發作次數的增多而加強,最終達到動態的平衡而使瘧疾由爆發性流行轉化為地方性流行,就現癥病人的數量來比較,地方性流行的要遠遠低于爆發性流行的,個中原因自不待言。但以此來考量宋元時期人們對瘴的論述,結論卻大不一樣。盡管當時人們早已觀察到,“凡往來嶺南之人,無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謂南人生長其間,與水土之氣相諳,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輕重之異,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可免矣。”(注:《嶺南衛生方》,第18-19頁。)換句話說,人們到達嶺南后至少會感染一次瘧疾,致使身體產生免疫力,表現在整個人群中,就是瘴疾患者減少乃至消失,瘴地疫情嚴重程度的降低。然而人們并不知道這是自己的身體產生了免疫力的結果,在他們以南方水土溫暑、風土惡逆等來解釋瘴疾的原因時,瘴疾的減輕被他們認為是因有“中州清淑之氣”相通,而使其“土風不異于中州”。在這里,人體的生物病理性的改變表現的是社會環境的變遷,疫情的有無表述的是文化的野蠻與馴服;疾病對人體自然機能的影響,實質上反映了社會文化形態的變遷。這大概是瘴疾的流行模式的另外一面。然則,綜觀瘴疾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疾病,其發生、擴張、減輕乃至消失的整個過程,無不以社會文化的演進為其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