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謝勇
據(jù)以上研究,這些暫時(shí)性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將轉(zhuǎn)化為儲(chǔ)蓄,提振消費(fèi)的效果并不明顯。 由于儲(chǔ)蓄率與居民收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我們初步認(rèn)為高收入家庭的儲(chǔ)蓄率高于低收入家庭,因此收入分配的格局可能會(huì)對(duì)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產(chǎn)生重要影響。為了進(jìn)一步考察這種影響,本文根據(jù)人均實(shí)際收入的高低將城鎮(zhèn)家庭分為低收入(P11)、中低收入(P12)、中等收入(P13)、中高收入(P14)和高收入(P15)等五組,并分別設(shè)置為虛擬變量(是=1;否=0),然后使用以上虛擬變量替代持久收入和暫時(shí)收入,并重新對(duì)方程5進(jìn)行了估計(jì)(表3)。 在表3中:以中等收人家庭(P13)為參照組,模型5中的中低收入、中高收入組家庭的儲(chǔ)蓄率與其沒(méi)有顯著差異,但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家庭的儲(chǔ)蓄率分別顯著地低于或高于中等收入家庭;在模型6~8中,SRl、SR2隨著收入分組的上升呈現(xiàn)出依次增加的趨勢(shì),并且均是統(tǒng)計(jì)顯著的。以上結(jié)果進(jìn)一步說(shuō)明高收入家庭的儲(chǔ)蓄率相對(duì)較高,也是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的主要擁有者,因此收入差距的擴(kuò)大將會(huì)導(dǎo)致城鎮(zhèn)居民總體儲(chǔ)蓄率上升。 (二)戶(hù)主年齡與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 在表2的模型1~4中,戶(hù)主年齡及其平方項(xiàng)的系數(shù)分別顯著小于0和大于0。因此我們初步認(rèn)為,中國(guó)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具有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即隨著戶(hù)主年齡的增加,儲(chǔ)蓄率先下降、后上升。這一特點(diǎn)和建立在西方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條件下的倒u型特征存在明顯差異,但和萬(wàn)廣華等人(2003)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村居民的相關(guān)研究是一致的。為了進(jìn)一步考察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的生命周期特征,我們將戶(hù)主年齡分成十組并分別設(shè)置為虛擬變量(是=l;否=0),然后用分組年齡變量替代方程5中的headage和headage2,并重新進(jìn)行了計(jì)量檢驗(yàn)(表4)。 表4顯示:儲(chǔ)蓄率在四個(gè)模型中均表現(xiàn)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且戶(hù)主年齡在45~49歲的時(shí)候達(dá)到整個(gè)生命周期的最低點(diǎn)。南于儲(chǔ)蓄等于收入與消費(fèi)之差,而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收入一般呈現(xiàn)出先上升,后下降(由于年老所導(dǎo)致的勞動(dòng)能力下降以及退休年齡的到來(lái))的生命周期特征。 對(duì)于SR1而言,南于僅考慮了基本生活費(fèi)支出,因此在戶(hù)主年齡在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中,盡管收入水平可能并不高,但子女一般處于幼年甚至還沒(méi)有子女,家庭的生活費(fèi)支出也較少,從而SIR1較高。但隨著子女的成長(zhǎng),生活費(fèi)支出也逐漸增加,其增幅往往超過(guò)家庭收入的增幅,從而導(dǎo)致SR1開(kāi)始下降,隨著子女的成長(zhǎng)并逐步離開(kāi)家庭,家庭生活費(fèi)支出的降幅將超過(guò)收入的降幅,因此SR1又呈現(xiàn)出上升的趨勢(shì),其中戶(hù)主年齡在65歲以上的家庭SR1甚至顯著高于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 而在考慮了教育和醫(yī)療支出以后,SR2表現(xiàn)出更加明顯的u型生命周期特征,對(duì)應(yīng)的u型曲線的底部比SR1更寬、更深,這主要是因?yàn)榧彝ピ诮逃矫娴拇罅恐С鏊鶎?dǎo)致的。并且由于醫(yī)療支出的存在,70歲以上老年家庭的SR2與戶(hù)主年齡在30歲以下的年輕家庭之間沒(méi)有表現(xiàn)出顯著的差異。 (三)家庭人口年齡結(jié)構(gòu)與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 在表2中,家庭O~5歲人口的比例(rchildl)與SR1、SR2之間表現(xiàn)出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主要是學(xué)齡前兒童的基本生活費(fèi)、教育支出都相對(duì)較低,從而導(dǎo)致家庭的儲(chǔ)蓄水平較高。盡管6~11歲、12~14歲子女的生活費(fèi)和教育支出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由于仍處于義務(wù)教育階段,rchild2對(duì)SR1和SR2沒(méi)有產(chǎn)生顯著影響,rchild3對(duì)SR1沒(méi)有顯著影響,但與SR2之間存在一定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模型4),這說(shuō)明初巾階段的教育支出已經(jīng)逐漸開(kāi)始影響城鎮(zhèn)家庭的儲(chǔ)蓄行為了。 隨著子女年齡的進(jìn)一步增加,基本生活費(fèi)和教育支出也開(kāi)始出現(xiàn)了較為明顯的上升,并且由于高中階段(包括中專(zhuān)、技校等)不屬于義務(wù)教育,rchild4與SR2之間表現(xiàn)出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并且對(duì)SR2的影響程度明顯超過(guò)對(duì)SR1的影響,其中城鎮(zhèn)家庭在15~17歲人口教育方面的支出顯然是造成以上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 家庭中18~21歲人口的影響較為復(fù)雜:南于已經(jīng)結(jié)束義務(wù)教育甚至完成相關(guān)的職業(yè)教育,因此部分18~21歲人口已經(jīng)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這將會(huì)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撫養(yǎng)比,進(jìn)而提高家庭的儲(chǔ)蓄率;但由于近年來(lái)中國(guó)高等教育的迅速擴(kuò)展,也有很大比例的18~21歲人口選擇進(jìn)入大學(xué)繼續(xù)學(xué)習(xí),這又將給家庭帶來(lái)沉重的教育支出負(fù)擔(dān),從而對(duì)儲(chǔ)蓄率尤其是SR2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表2的結(jié)果與我們以上的分析基本一致:rchild5與SR1之間甚至存在一定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模型3)。但在考慮了教育支出以后,rchild5與SR2之間卻表現(xiàn)出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以普通的城鎮(zhèn)三口之家為例,如果有一個(gè)18~21歲的子女(即rchild5等于三分之一),將導(dǎo)致家庭的SR2下降O.1或0.075,降幅相當(dāng)于平均儲(chǔ)蓄率的30-40%。 此外,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rold)與SR1、SR2之間均表現(xiàn)出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與我們的直觀認(rèn)識(shí)基本是一致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對(duì)較低,并且面臨著較高的醫(yī)療費(fèi)用支出,因此贍養(yǎng)老人的負(fù)擔(dān)越重,家庭的儲(chǔ)蓄率也相應(yīng)越低。 (四)財(cái)富水平、戶(hù)主特征與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 根據(jù)LC—PIH模型,財(cái)富水平與儲(chǔ)蓄率之間一般存在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本文選擇人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積作為財(cái)富水平的代理變量,但實(shí)證研究的結(jié)果卻與以上結(jié)論并不一致。在表2中:隨著人均自有住房的建筑面積的增加,城鎮(zhèn)居民的儲(chǔ)蓄率沒(méi)有發(fā)生顯著變化,甚至還表現(xiàn)出一定的上升趨勢(shì)。 針對(duì)以上結(jié)論,本文認(rèn)為需要結(jié)合我國(guó)住房制度改革的現(xiàn)實(shí)背景,對(duì)住房狀況與居民儲(chǔ)蓄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更加細(xì)致的研究。例如,對(duì)擁有自有產(chǎn)權(quán)住房的城鎮(zhèn)家庭,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獲取的不同方式(市場(chǎng)購(gòu)買(mǎi)或繼承等)可能會(huì)對(duì)儲(chǔ)蓄率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即使是同樣的產(chǎn)權(quán)獲取方式,對(duì)于不同年齡家庭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對(duì)以上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作為以后進(jìn)一步研究的方向。 從表2的結(jié)果來(lái)看,戶(hù)主的性別、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程度對(duì)居民儲(chǔ)蓄的影響與前文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戶(hù)主為男性、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其儲(chǔ)蓄率也相對(duì)較高;而戶(hù)主為中共黨員的家庭儲(chǔ)蓄率則相對(duì)較低。 五、主要結(jié)論 本文使用CGSS2006的微觀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在綜合考慮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說(shuō)以及預(yù)防性?xún)?chǔ)蓄理論的基礎(chǔ)上,對(duì)中國(guó)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的影響因素進(jìn)行了實(shí)證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jié)論: 首先,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確定性與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將會(huì)導(dǎo)致城鎮(zhèn)居民總體儲(chǔ)蓄率的上升。因此,降低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以及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措施都是提高居民消費(fèi)、降低儲(chǔ)蓄等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重要出發(fā)點(diǎn)。 其次,本文基于截面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顯示:與建立在西方國(guó)家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所得到的倒u型曲線不同,中國(guó)城鎮(zhèn)居民的儲(chǔ)蓄率顯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其中戶(hù)主年齡在45~49歲之間的中年家庭的儲(chǔ)蓄率處于整個(gè)生命周期的最低點(diǎn),而在考慮了家庭的教育、醫(yī)療支出以后,這一特征表現(xiàn)得更加顯著。 第三,與戶(hù)主年齡對(duì)儲(chǔ)蓄率的影響相對(duì)應(yīng),家庭的人口年齡構(gòu)成對(duì)于儲(chǔ)蓄率也產(chǎn)生了顯著的影響,而產(chǎn)生以上影響的內(nèi)在機(jī)理在于不同年齡人口所對(duì)應(yīng)的教育、醫(yī)療支出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中國(guó)目前的教育和醫(yī)療體制下,這種差異直接影響了家庭的儲(chǔ)蓄和消費(fèi)行為。 第四,城鎮(zhèn)居民的住房財(cái)富水平與其儲(chǔ)蓄率之間基本沒(méi)有顯著關(guān)系。但戶(hù)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別對(duì)城鎮(zhèn)居民儲(chǔ)蓄率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jpg)
題.jpg)
發(fā)展.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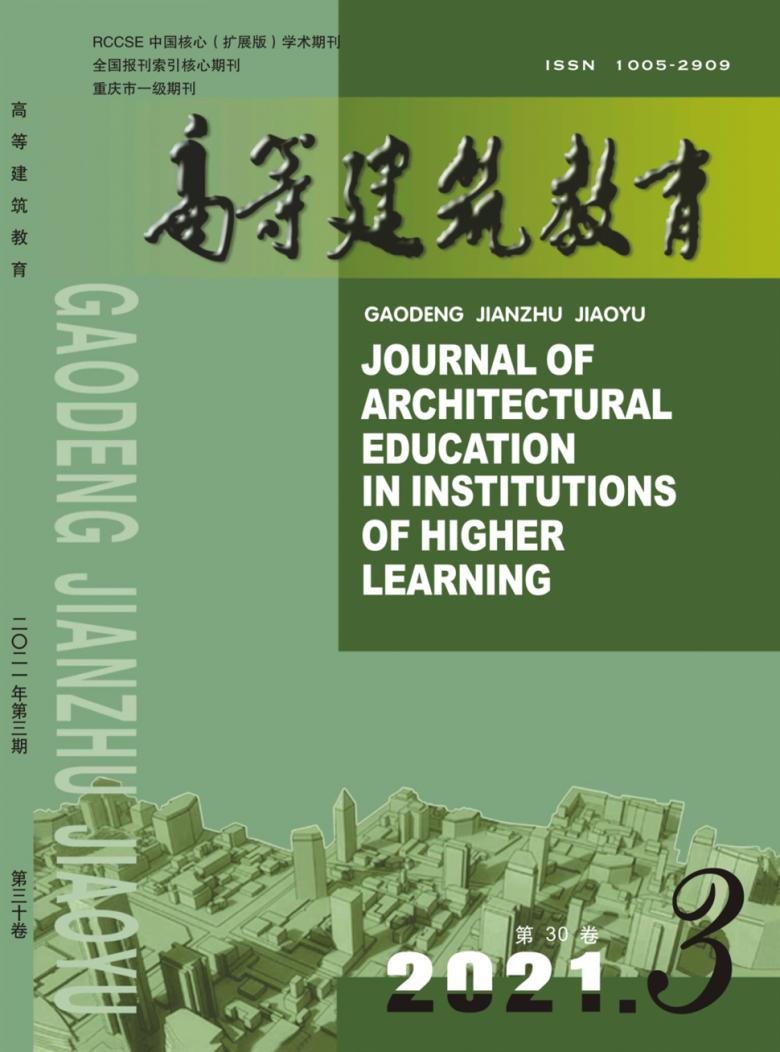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