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首例公民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案之法理分析
周 威
案情: 南京江寧區(qū)美亭化工廠長楊春庭于2003年3月接到通知,該化工廠要拆遷,但在補償數(shù)量上存在嚴重分歧,原因在于雙方所依據(jù)的法律根據(jù)不同,政府根據(jù)1996年發(fā)布的《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補償130萬,而原告楊春庭根據(jù)現(xiàn)行的《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應得到補償是400多萬。經(jīng)研究發(fā)現(xiàn),1996年發(fā)布的《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被媒體稱之為地方政府規(guī)章)是依據(jù)1996年3月《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制定的,然而該辦法已于2000年3月廢止。上面提到的南京市的有關(guān)規(guī)章是根據(jù)2000年國務院的行政法規(guī)制定的。原告于2003年4月23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之訴,狀告南京市江寧區(qū)政府不按上位法規(guī)及時修改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致使自己損失慘重。南京市中院依據(jù)有關(guān)規(guī)定將此案移交江寧區(qū)法院審理,2003年5月26日江寧區(qū)人民法院向原告發(fā)出受理通知書,并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裁定,駁回起訴。理由是政府發(fā)布的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差遣管理辦法》是屬于抽象行政行為,被行政訴訟法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同時向江寧區(qū)政府提出司法建議。[1]
由于該案件被定位于“首例”,近來多被媒體關(guān)注,更重要的原因是該案涉及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行政立法已成為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點,行政不作為也是行政法學的新領(lǐng)域,所以對行政立法不作為的研究會給中國法治建設(shè)以深遠的影響。本文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該案:行政機關(guān)有立法權(quán)嗎?權(quán)力與責任有什么關(guān)系?行政立法的特征和形式是什么?行政立法如何控制?對本案應采取什么態(tài)度?
一 行政機關(guān)有立法權(quán)嗎?
對于該案人們也許首先要問“行政機關(guān)能立法嗎?”的確,按照古典自由主義下的三權(quán)分立理論,行政權(quán)﹑立法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相互分立和制約,任何兩權(quán)的結(jié)合都會產(chǎn)生腐敗,尤其是對行政權(quán)易于膨脹的恐懼,對此洛克和孟德斯鳩有經(jīng)典的論述。洛克曾經(jīng)指出:“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zhí)行法律的權(quán)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quán)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于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執(zhí)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于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們就與社會的其余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 ”[2]孟德斯鳩也告誡人們:“當立法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guān)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執(zhí)行這些法律。”[3]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權(quán)利意識的提高,人民主權(quán)原則和分權(quán)原則逐漸確立,并成為國家政權(quán)正當存在的基礎(chǔ),在行政管理領(lǐng)域必然衍生出依法行政的要求。作為代表人民行使主權(quán)的議會居于優(yōu)越地位、立法權(quán)優(yōu)于行政權(quán)是民主政治發(fā)展初期的最大特征。議會的優(yōu)越便意味著民主勢力的優(yōu)越。在此背景下,人們要求行政機關(guān)的一切活動都要嚴格遵循議會所制定的法律,一切行政決定的作出都要以議會立法為依據(jù),行政機關(guān)必須忠實地執(zhí)行議會的法律,不能有所逾越和偏差,否認行政機關(guān)有自由裁量的權(quán)力。正所謂“無法律便無行政”。有人曾說:“直到1914年8月,除了郵局和警察以外, 一名具有守法意識的英國人可以度過他的一生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政府的存在。”[4]在19世紀之前,這一理論影響深遠,人們對之奉若神明。
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社會關(guān)系愈益復雜,市場失靈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政府僅作為“守夜人”已不能滿足需要,“如果國家對公民從嬰兒照管到死,保護他們生存的環(huán)境,在不同的時期教育他們,為他們提供就業(yè)、培訓、住房、醫(yī)療機構(gòu)、養(yǎng)老金,也就是提供衣食住行,這需要大量的行政機構(gòu)。相對來說,僅僅靠議會通過的法律,……那只能做些微不足道的事。”[5]“管的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這一格言越來越受到挑戰(zhàn).為解決這一難題,功能主義的憲政理論應運而生,大量的行政立法出現(xiàn),彌補了議會立法的空白和滯后,實現(xiàn)了行政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立法權(quán)的結(jié)合。下表表明,從19世紀末委任立法數(shù)量呈急劇上升之勢。美國行政機關(guān)不僅不斷擴大行政權(quán),還心安理得地在行使著立法權(quán)和司法權(quán)。“權(quán)力統(tǒng)合主義”的趨向在行政機關(guān)身上表現(xiàn)得極為明顯。"行政立法并沒有因為其有違傳統(tǒng)原則之虞而停止或放慢自己的步伐。"[6]行政立法的實踐早已把傳統(tǒng)的理論拋在了后邊。于是行政機關(guān)有了立法權(quán)。
1760——1979年美國委任立法情況[7]
年代 新頒布法規(guī)數(shù) 年代 新頒布法規(guī)數(shù)
1760-1769 4 1870-1879 10
1770-1779 16 1880-1889 10
1780-1789 8 1890-1899 14
1790-1799 7 1900-1909 14
1800-1809 10 1910-1919 57
1810-1819 7 1920-1929 31
1820-1829 6 1930-1939 48
1830-1839 9 1940-1949 80-
1840-1849 5 1950-1959 41
1850-1859 5 1960-1969 73
1860-1869 18 1970-1979 125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1986年世界發(fā)展報告》﹑《1994年世界發(fā)展報告》
二 權(quán)力與責任是什么關(guān)系?[8]
在專制主義時代,皇帝或國王擁有絕對的權(quán)力,因此就不會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quán)的劃分.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因此,在中國長時期皇帝言出法隨,所言皆金口玉律;在西方國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沒有人懷疑"國王不能為非"的不當。這樣,權(quán)力和責任就處于完全分離的狀態(tài),享有權(quán)力者不可能犯錯,當然就談不到責任的承擔。各級官僚作為國王的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權(quán),在社會中就形成一個特權(quán)階層,并且有相應的制度作保障,一如唐代的八議﹑官當﹑請﹑減﹑贖﹑免等制度。
但隨著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朕即國家”被“人民主權(quán)”所取代,國家的一切權(quán)力被認為來源于人民的讓與,任何統(tǒng)治者違背人民的意志將被人民拋棄,對此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中有經(jīng)典的論述,人所共知,不在贅述。但要統(tǒng)治者服務于人民,就必須給予一定的權(quán)力,統(tǒng)治者處于絕對的束縛之中就不能實現(xiàn)目標;要統(tǒng)治者更好的服務于人民,解決的辦法就是把權(quán)力和責任聯(lián)系起來,享有權(quán)力就必須承擔責任,讓他們"帶著鐐銬跳舞",權(quán)力與責任同在,于是乎“權(quán)力即責任”。聯(lián)系到本案的主題——行政立法,《憲法》第107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管理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經(jīng)濟﹑教育﹑科學﹑文化﹑衛(wèi)生﹑體育事業(yè),城鄉(xiāng)建設(shè)事業(yè)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jiān)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fā)布決定﹑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 鄉(xiāng)鎮(zhèn)民族鄉(xiāng)的人民政府執(zhí)行本紀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上級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管理本行政區(qū)域的行政工作。”由此可見,當前中國行政立法主體多元層級多種,然而僅規(guī)定權(quán)力無責任者有之,權(quán)力多責任少者更多。更可惡的是某些行政機關(guān)出于自身利益故意殆于行使法定職權(quán),該立的不立,該廢的不廢,該改的不改,結(jié)果致使行政相對人的權(quán)利嚴重受損。本文所討論之案例即為明證.該問題涉及“責任”一詞的含義。
三行政立法的特征和形式是什么?
從世界范圍來看,行政立法制度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近代以來政府職能發(fā)生巨變的產(chǎn)物。對其認識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對其含義的表述也是眾說紛紜[9]。這里我不想也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不過,我認為,理解行政立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行政立法是行政主體的行為,行政主體以行政職權(quán)和相應職責為標志,行政職權(quán)包括固有職權(quán)和授予職權(quán),但并非所有行政主體的抽象行政行為都屬于行政立法的范疇,這涉及行政立法的范圍問題;其次是行政立法的范圍,行政立法必須有憲法法律的授權(quán),近來有學者提出"不違背"[10]原則,并被實務界接受,而且授權(quán)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否則立法機關(guān)過度授權(quán)必將將導致"自殺"[11],因為行政立法只是一種從屬立法,受制于議會立法,不得與議會立法相抵觸,不能取代議會立法的主導地位,比如對于涉及人身權(quán)利等方面的問題,許多國家仍堅持議會立法的原則;再次,行政立法要有明確的根據(jù)行政機關(guān)在行使所授之權(quán)時,要受到授權(quán)法的制約,必須符合授權(quán)法所規(guī)定的目的、內(nèi)容、范圍和標準,接受委托者的審查和監(jiān)督;再其次,行政立法應包括廢﹑改﹑立三個方面,大家通常理解行政立法僅為“立”,而“廢”和“廢”往往被忽視,其實后兩者同樣對中國法治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中國剛剛加入WTO,很多不合時宜的規(guī)范性文件需要清理。聯(lián)系本案,該過時失效的“規(guī)章”因被"忽視",已經(jīng)造成幾百萬的損失(可能是一個人一生的心血)。憲法理論告訴我們,個人財產(chǎn)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得剝奪,這里的法應是良法;西諺說“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過錯受益”,因此本案中四百多萬和一百三十萬之間的差額就不應該留在(江寧區(qū))政府手里。
四對行政立法如何控制?
自由主義時代,控制行政機關(guān)的手段是三權(quán)的徹底分離和相互牽制;19世紀末之后,社會關(guān)系的復雜化,給行政權(quán)的膨脹提供了契機,加上議會對行政機關(guān)的授權(quán)往往過于寬泛,有的授權(quán)實際是漫無邊際的一攬子授權(quán),行政機關(guān)據(jù)此所享有的立法權(quán)幾乎沒有什么限制,致使議會通過授權(quán)法對行政立法進行限制的期望逐步落空,同時,面對議會的模糊授權(quán),由于缺乏明確的審查標準,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保持對行政立法的高度克制。致使司法審查的功能受到抑制。這使得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受到挑戰(zhàn)。面對此種形勢基于功能主義的憲政理論,對行政權(quán)實體的控制轉(zhuǎn)為對程序上的控制,從程序的啟動,到事中參與,到事后監(jiān)督審查全方位的控制,這就是行政程序法倍受關(guān)注的背景,關(guān)鍵是引入司法審查制度。目前,中國行政立法存在的問題是,立法過程缺少充分而完善的公眾參與渠道和利益協(xié)調(diào)機制。雖然行政機關(guān)也往往通過咨詢、協(xié)商等方式收集民意,進行利益協(xié)調(diào),但行政機關(guān)一般對此并不負有法律上的義務,公眾能否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往往取決于行政機關(guān)的單方意志,而且行政立法的程序啟動主體范圍太窄,一般的民眾很難啟動一項行政立法,更多是部門之間利益的協(xié)調(diào)和瓜分,受損的更多是沒參與機會的群眾。這使得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公正性大打折扣,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自利性。
對行政立法的監(jiān)督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是,立法機關(guān)監(jiān)督和制約行政立法的主要方式,就是在授權(quán)法中明確規(guī)定授權(quán)的范圍,行使所授之權(quán)的目的、條件、方式、原則、程序,從而保障基本的政策性決定由直接向人民負責的機關(guān)規(guī)定,使行政立法在符合立法機關(guān)所定的標準之下進行。“除非有法定標準的限制,否則國會不能授出它的任何立法權(quán)。”[12];第二,鑒于議會的授權(quán)標準已變得越來越不可捉摸,司法審查作為一種經(jīng)常性的、局外的、有嚴格程序保障的、具有傳統(tǒng)權(quán)威性的監(jiān)督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它在對行政立法的制約體制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三,行政監(jiān)督,我國憲法第89條第14項規(guī)定(國務院)改變或撤消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不適當?shù)臎Q定和命令;第108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所領(lǐng)導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權(quán)改變或撤消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shù)臎Q定。
對中國目前行政立法現(xiàn)狀的監(jiān)督,可發(fā)揮多渠道的優(yōu)勢,立法機關(guān)應積極規(guī)范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啟動主體,備案報批程序,司法審查的范圍,上級行政機關(guān)也應負責相關(guān)規(guī)范性文件的清理.
五對本案的總體態(tài)度和具體分析
結(jié)合法律理論和實踐,我認為,法院的裁定是不違反現(xiàn)行法律的,應該受到尊重.但政府應為自己的懈怠承擔責任,而且原告在現(xiàn)行的法律框架內(nèi)尚有其他救濟途徑。會涉及以下法律問題: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規(guī)章的外延;行政復議法對規(guī)定的附帶審查。
本案被稱為全國首例對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案,就意味著對現(xiàn)行體制的突破,其實的確達到一定的效果,引起公眾的廣泛關(guān)注,對政府的約束已有成效(據(jù)悉,江寧區(qū)有關(guān)部門已經(jīng)開始著手起草新的管理辦法)。
但法院只能以法律為準繩,只能服從法律(一般情況下是形式上的法律)。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第12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二)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或者行政機關(guān)制定發(fā)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第41條規(guī)定:提起行政訴訟應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quán)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四)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很明顯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正如該案法院的裁定所說,它是為將來的能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guī)范性文件,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原告不適格,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所以法院的裁定符合現(xiàn)行法律,無可厚非。對此,部分人士表示異議,認為法院不敢公正裁決。我認為這是對法院的誤解。從實體說,從感情上,每個人都會認為政府不對,而原告的合法權(quán)益受到了侵害,是因政府的過錯。但他們沒有想到,如果法院“勇于”突破現(xiàn)行訴訟體制來保護這一個體價值,將會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法律權(quán)威的徹底喪失,因為我們法院的根本功能就是解決糾紛,而且是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是法律權(quán)威的最堅定的守護者.
在所有相關(guān)媒體上都將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定位于“規(guī)章”,我很不以為然。《立法法》第73條規(guī)定: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jù)法律行政法規(guī)和本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guī),制定規(guī)章;第64條第4款規(guī)定:本法所稱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區(qū)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jīng)濟特區(qū)所在的市和經(jīng)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由上述兩條規(guī)定,可看出,地方規(guī)章是有特定的內(nèi)涵的,外延也是確定的,可以斷定縣級人民政府不屬于較大市的人民政府,也就沒有規(guī)章制定權(quán),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當然也就不能稱為規(guī)章。那么,它是屬于什么性質(zhì)呢?我國《憲法》第107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管理行政區(qū)域內(nèi)的經(jīng)濟﹑教育﹑科學﹑文化﹑衛(wèi)生﹑體育事業(yè),城鄉(xiāng)建設(shè)事業(yè)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jiān)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fā)布決定﹑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 鄉(xiāng)鎮(zhèn)民族鄉(xiāng)的人民政府執(zhí)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上級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管理本行政區(qū)域的行政工作。;第108條規(guī)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所領(lǐng)導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權(quán)改變或撤消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shù)臎Q定。從此可知,該規(guī)范性文件不可能屬于行政措施和命令,而只能屬于決定。
然而讓人難以琢磨的是,《行政復議法》第7條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guān)的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jù)的下列規(guī)定不合法,在對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時,可以一并向行政復議機關(guān)對該規(guī)定的審查申請:(一)國務院部門的規(guī)定;(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guī)定;(三)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的規(guī)定。 前款所列規(guī)定不含國務院部委員會規(guī)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規(guī)章。規(guī)章的審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規(guī)辦理。這里的“規(guī)定”是什么含義呢?同憲法里涉及到的“行政措施,決定,命令”是否有對應關(guān)系?如果有對應關(guān)系的話,就是說,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屬于行政復議法里的“規(guī)定”,那么就可以提起行政復議,對原告來說,或許是最合算的方式,不管從時間金錢方面還是法律上.
另外,還想提出本案程序上的一點瑕疵.據(jù)報道,對于原告起訴時間,有兩種說法,一個是2003年3月份,一個是2003年4月份,但立案的時間是一致的,即2003年5月26日.也就是說,本案從起訴到立案最短花去一個月的時間.然而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訴狀,經(jīng)審查,應當在七日內(nèi)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一個月同七天相距甚遠,所以這明顯是違反法律程序的。
余論
大凡研究案例,目的不外乎兩個:一是理論的研究和拓展;二是實務方面,具體說就是,為當事人尋找更好的救濟途徑.在這部分我想提出自己的想法,涉及到對《行政訴訟法》第53條中"參照"的理解.第53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部委根據(jù)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guī)決定命令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以及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省自治區(qū)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jīng)過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人民法院根據(jù)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guī)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 人民法院認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與國務院部委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部委制定發(fā)布的規(guī)章之間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從效力上看,法律高于行政法規(guī),行政法規(guī)又高于規(guī)章,行政規(guī)章又高于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從立法原意上看,對法院審查案件適用各類規(guī)范性文件的要求隨效力層級的遞減而遞減.
參照是什么意思呢?是參考并仿照之意嗎?我想不是,當然也不是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合理的解釋應是,原則上要用,但是若該規(guī)范性文件明顯違法,可以適用更高一級的規(guī)范性文件,而這一文件不置可否.我的論據(jù)是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第62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應當在裁判文書中援引 ,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規(guī)章及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從該規(guī)定中可推論,人民法院已經(jīng)獲得一定程度的"規(guī)章及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的判斷權(quán).
基于上述理解,我可以給本案原告提議:直接對被告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原告肯定會答辯說:他的拆遷及補償是有根據(jù)的,根據(jù)就是1996年《江寧縣城鎮(zhèn)房屋拆遷管理辦法》.這時,法院就可以行使法定的參照權(quán),將該規(guī)范性文件束之高閣,而直接適用現(xiàn)行南京市的有關(guān)規(guī)范性文件.這樣原告的正當權(quán)益得到維護,而且又不能說突破現(xiàn)有法律體制,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
在文章的最后,我還想提一個問題,就是關(guān)于行政案件的移轉(zhuǎn)管轄,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把自己管轄的一審行政案件移交給下級人民法院審判(第23條)。我想知道,再什么情況下移交,如果是上級法院是為了規(guī)避棘手的案件,可否移交?研究該案,我們會發(fā)現(xiàn),原告是起訴到中級人民法院,然后又移送到基層法院的,這樣合適嗎?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本轄區(qū)內(nèi)重大復雜的案件(第14條),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又對重大復雜作出解釋,其中一項是“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層人民法院不宜審理的案件”(第8條)。該案作為全國首例影響不能說小,被告恰是縣級人民政府,案由是行政立法不作為行政訴訟之全新領(lǐng)域不能說不棘手,完全應該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為什么中院又要移交呢?
[1]該案例源于法制日報2003年3月-6月的相關(guān)報道.
[2]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9頁。
[3]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6頁。
[4]轉(zhuǎn)引自(英)威廉?韋德:《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5]轉(zhuǎn)引自(英)威廉?韋德:《行政法》,徐炳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6]苗連營:《行政立法及其控制》,載《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6期 .
[7] 蔡立輝著《政府法制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月,第174頁.
[8] 這一問題由于缺乏直接的論著深感力不從心.
[9] 參見王學輝主編《行政法學論點要覽》,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200-203頁.
[10] 應松年﹑袁曙宏主編《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論研究與實證調(diào)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77頁.
[11] 陳端洪著《中國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73頁.
[12](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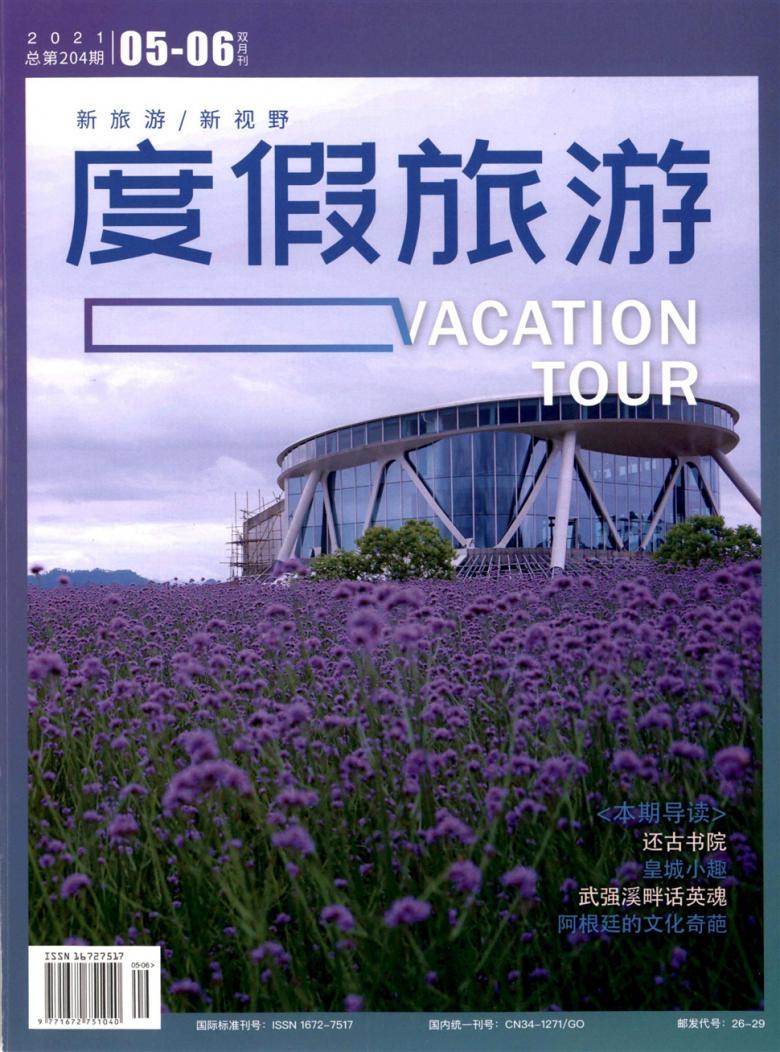

研究.jpg)
濟信息.jpg)
境管理.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