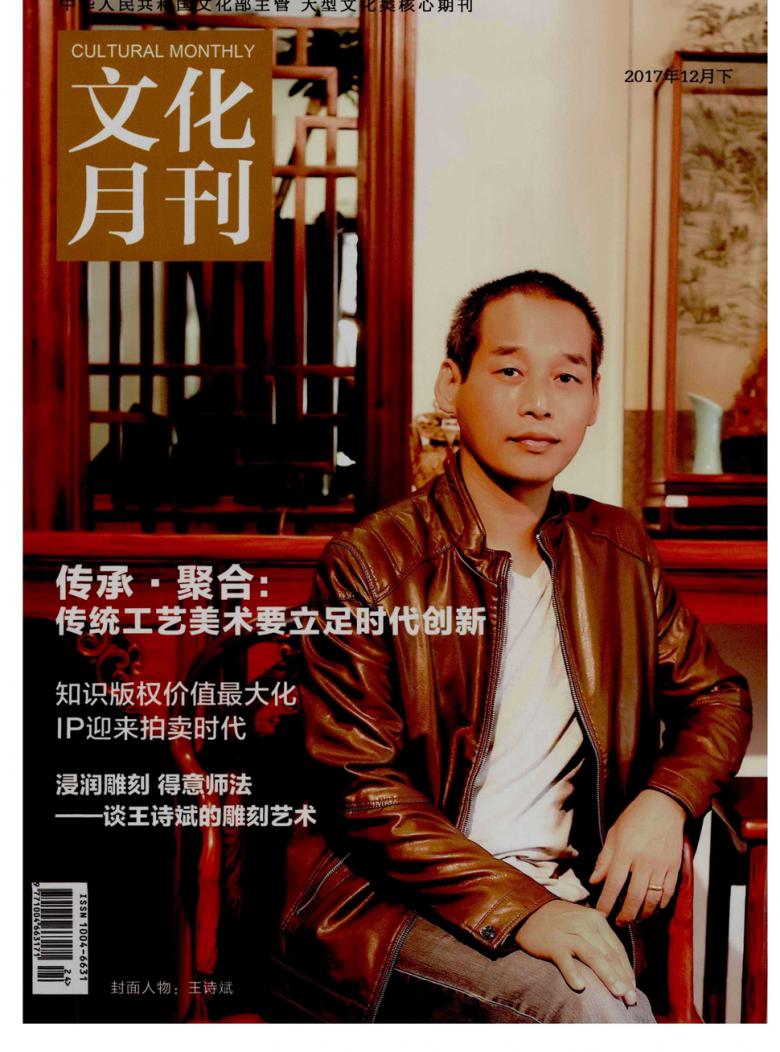關于農地糾紛、村民自治與涉農信訪——以北京市調研為依據
張紅
關鍵詞: 農地糾紛;村民自治;涉農信訪 內容提要: 涉農信訪在整個信訪總量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基本上以農地糾紛為內容。以保障農民自治為己任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被誤用或濫用,這成為諸多農地糾紛的作俑者。法院面對農地糾紛止步不前,農民轉而求諸信訪,但信訪無法亦不應該成為解決農地糾紛的主要渠道,信訪不能代替司法。信訪工作當前面臨制度困境與功能異化的現狀,要從確厘定其與司法的關系出發,使回歸本位,并發揮最大功效。 一、問題及研究背景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首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在《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又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些論斷已經成為指導法律、政策制定及開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不可否認,當今中國正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當中,在這場持續、激烈的變革中所出現的諸多問題,在人類文明史上并無現成經驗可供參考。由此決定了當下中國學術界更應該眼睛往下看,深入中國社會調查研究,直面現實的中國問題,構建問題之中國理論體系和研究進路,進而有所作為。歷史一再證明,真正懂得中國國情的人,才能獲得對中國事務的話語權。 目前中國最大的國情在于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且發展不均衡,農業、農村和農民是一個關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根本性問題:農村土地征收問題、戶籍制度對農村發展的制約問題、農村的糧食生產安全問題、取消農業稅所引發的農村利益再分配問題、農民的貧困與社會保障問題、農民受教育程度低及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農業拋荒問題以及農村集體資產流轉等皆屬于此范疇。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其在不斷的積壓下將嚴重威脅社會穩定,進而威脅黨的執政地位。研究表明,從信訪作為反映社會矛盾的這一窗口來看,由“三農”引發的信訪問題在社會矛盾數量中占有絕大比重,如果“三農”問題解決得不好,其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甚至將成為中國未來維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1]對此,有學者亦曾言:“農村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農民信訪問題解決了,信訪問題同樣也就解決了一大半。”[2]在“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的大背景下,維護社會穩定與發展經濟,成為政治生活的兩架馬車,二者互為表里,共同構成各級政府工作的主要內容。 并非所有的“三農”問題都會導致信訪事件并影響社會穩定。事實上,只有那些關涉農民切身利益,在既有的司法體系中無法得到救濟或救濟不到位,農民集中通過非正常信訪來表達不滿甚至憤慨的問題,才可能影響社會穩定。[3]在這些問題當中,圍繞農村土地而發生的爭議是重中之重。[4]當前,由農村土地糾紛引發的眾多涉農信訪問題已經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所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并引起最高司法機關的高度重視。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關于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做好涉農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37號)第10條指出:“要結合當前形勢,認真做好農村涉訴信訪工作,努力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涉訴信訪案件的發生。”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及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今天,我們必須直面以農村土地糾紛為主要內容的涉農信訪問題,分析農地糾紛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此化解涉農信訪矛盾,維護農村社會穩定。[5] 本文以課題組在北京實地調研所得素材為依托,但本文的研究方法仍然注重于對現行法制及其運作的分析,采解釋學的進路,對根據課題組調查所得的農地糾紛進行類型化處理,特別是針對主要的農地糾紛,提出法律上的解決方案。本文不打算細究信訪體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也不涉及當前維穩體制問題。本文研究解決主要農地糾紛的法律對策,是為了通過法律手段消解因農地糾紛而產生的矛盾甚至上訪。此種法律對策無論是對于法院的判決,還是對于信訪工作部門有關處理意見的出具,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因為,本文研究的法律對策是從現行法制解釋出來的結果。在依法治國成為治國理政根本方針的前提下,在依法辦事成為基本共識的基礎上,這種法律對策將能夠很好起到息訴與息訪的作用,并具有在化解矛盾上的終局意義。 二、農地糾紛與涉農信訪 (一)農地糾紛之一:“新老戶” 在農村,由于人口流動,會發生外村人(新戶)加入本村落戶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新老戶之間會因權利義務不平等而發生糾紛,即俗稱的“新老戶”問題。一般來看,根據加入時的政策以及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委員會的決議,新戶通過繳納一定的“集體份子錢”等方式取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并約定今后與老戶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過程中,面對高昂的征地補償款分配,新、老戶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引發了大批涉農信訪。下文將以在北京市懷柔區北房鎮北房村發生的一起群體性訴訟案件為分析樣本。這個案件涉及到41戶村民,人數上百人,懷柔區法院為此做出了41份判決書。[6]此類案件處理稍有不慎,很可能引發重大的群體訪或群體性事件。下面舉一例說明[7]在該案中,原告于忠奎、吳春芹、于珊系1998年1月1日前入戶北京市懷柔區北房鎮北房村的非政策性搬遷戶。2004年9月18日,北房村委會、合作社公告:凡1998年1月1日以前來我村入戶的人員(政策搬遷的除外),已經將承包土地交回戶口遷出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必須按每人補齊5000元集體積累后方可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否則不能享有。2005年1月28日,原告按上述規定,向被告繳納了5000元積累款后,原告取得了每人0.7畝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2006年6月28日,北房村召開社員代表會通過民主程序形成決議:1998年1月1日以前來北房村入戶的人員,已經將承包土地交回遷出村集體經濟組織,并按北房村規定交齊5000元入戶費,可取得每人0.7畝口糧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但不享受每人0.7畝以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確利(確利款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據每年的土地收益情況,每年定期向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放的村集體土地收益)。二被告依據該社員代表會決議,不再向三原告發放2006年及以后的確利款。而北房村其他老戶則于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別享受了每人610元、990元、810元的確利款待遇。三原告于2009年4月21日訴至法院,要求二被告按照老戶的標準給付相應的確利款。 法院認為:2004年北房村委會、合作社所屬土地確權領導小組以入戶表決方式,制定了《北房鎮北房村推進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流轉方案》(以下簡稱《確權和流轉方案》),并就全體村民關于1998年1月1日以前落戶北房村人員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問題及《確權和流轉方案》的公決結果上報北房鎮政府,之后北房村黨支部、村委會、合作社亦聯合向北房村村民發布公示公告書。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7條的規定,召開村民會議,應當有本村十八周歲以上村民的過半數參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戶的代表參加,所作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通過。上述《確權和流轉方案》經入戶表決通過,取得了超過法定人數的村民的認可,符合法律規定,合法有效。 三原告系1998年1月1日以前入戶北房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依據村委會、合作社的公示公告書,交納了入戶積累,具備了享有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資格。根據上述方案,其權利既包括確地權也包括確利收益的分配權,且2006年6月5日,村委會、合作社制定的《北房鎮北房村關于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確利分配辦法》,確定了以北房村1998年1月1日二輪延包簽訂土地承包合同的時間及取得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人員作為該村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確利的范圍。根據該分配方法,三原告理應享有確利款。2005、2006、2007、2008年北房村確利款的發放,亦是依據《確權和流轉方案》進行的,2006、2007、2008北房村委會、合作社未發放給三原告確利款,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權益。 北房村委會、合作社認為,按照北房村2006年6月28日的社員代表會議決議,三原告不享受每人0.7畝以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確利。因該決議內容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積極推進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流轉的意見》及《中共北京市懷柔區委、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政府關于積極推進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流轉的意見》中“已將承包土地交回戶口遷出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并按照現戶口所在地集體經濟組織的規定繳納了集體積累,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或成員代表大會討論同意后,取得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政策精神相違背,也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村民委員會應當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承包經營戶、聯戶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財產權和其他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及第20條“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的規定不符,故不能據此否定經入戶表決形成的《確權和流轉方案》。二被告依據北房村2006年6月28日的社員會決議不向原告發放確利款的行為不妥,本院予以糾正。綜上所述,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9條之規定,判決被告北京市懷柔區北房鎮北房村村民委員會及被告北京市懷柔區北房鎮北房村經濟合作社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給付原告于忠奎、吳春芹、于珊2006年至2008年的確利款共計7230元。 本案關鍵問題在于,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社員代表大會的方式,經過民主表決,認為不應該給新戶分得與老戶相同的確利款,此種行為是否合法?其引申的問題是:法院能否撤銷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如能,則撤銷之后,應當如何處理:直接改判抑或責成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重新表決?此涉及到一項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即如果法院糾正村民大會的決議,是否干預了村民自治,使村委會自治法流于形式? (二)農地糾紛之二:“衍生人口” “衍生人口”問題主要是指,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大會通過民主決議方式決定,將征地補償款按照村集體經濟組織原有人口分配,而對于新生的人口不予分配,由此在新生人口與原有人口之間引發征地補償款分配不均的矛盾甚至沖突問題。北京市在2004年普遍進行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但是在確權后實行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政策對農民的影響非常大。根據此政策,在一輪土地承包經營期內,農地不得調整,這與《物權法》的規定是相契合的,但是在30年的耕地承包期內,特別是在2008年以后實施土地承包經營權長期不變的政策后,很容易產生“衍生人口”的問題。農民家庭一般會因為婚嫁、生育等產生人口上的變動,而且一般是增加人口。“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導致農民家庭人口增加而承包的耕地,或者在村集體土地被征收以后的補償款分配上卻沒有得到相應增加的矛盾。對這部分新增加人口而言,由于喪失了土地資源作為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因而情緒極為不穩定,并導致經常性上訪,要求政府解決這類問題。對于這類案件,可以北京市昌平區小湯山鎮講禮村案件為例。[8] 這起案件的基本案情如下:2004年8月1日,昌平區小湯山鎮講禮村根據相關政策及法律規定采取確權確利方式落實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向全村符合條件的村民進行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確利登記,并核發了證書。原告系該村2004年8月以后出生的村民,后經其所在的昌平區小湯山鎮講禮村經濟合作社進行登記,確認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2007年前后,講禮村委會將村內土地進行合作開發進行新村建設,并由此獲得了一定數額的土地補償款。針對該款項的分配方式,村集體內部成員產生爭議,后由被告多次征求村民意見,并組織村民代表及黨員進行表決,結果一致同意按照該村2004年8月1日登記的確權確利人數分配該土地補償款,每人分得33550元。 對此,原告等部分村民因其確權確利登記發出生于2004年8月1日后,不符合被告通過表決程序確定的分配條件,未能獲得分配款項。為此,原告等人些后向昌平區小湯山鎮政府及昌平區政府信訪部門提出信訪意見。信訪部門答復為,講禮村委會雖經細致的民主程序決定分配方式,但其結果明顯有悖于市委、市政府《關于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流轉的意見》,區政府《關于印發昌平區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占用收入管理使用暫行辦法的通知》及《小湯山鎮講禮村土地確權方案》的規定,將2007年土地出租補償款按2004年7月31日確權人口進行分配顯然是不妥當的,認為應當將講禮新村土地補償款納入2007年土地收益收入,并按2007年土地確權人口進行分配。針對上述信訪答復意見,被告并未再次組織進行民主方式修改分配方案,原告等人遂提起本案訴訟。 法院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共同所有。本案雙方訴爭的土地補償款實際系土地使用權出讓獲得的土地收益款,雙方爭議焦點在于,村集體通過土地使用權出讓獲得的土地收益款項分配方案是否合理。為此,應當審查土地補償費收益分配方案中涉及訴訟主體收益分配權的內容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合法有效。具體講,應當按照我國法律及相關政策的規定確定,對農村集體組織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應按照以下原則進行審查: 首先,應當符合民主議定程序的原則。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實行自治決定重大事項的機構。其討論土地收益款分配和各項村務事項的決定、決議必須遵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9條所規定的民主議定原則,做到程序合法。 其次,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的原則。農民集體所有權的主體是通過一定組織形式整合的全體農民集體成員,一定范圍內的全體農民集體成員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方式對集體所有財產的使用、分配作出決策,形成集體意志,這就是法律賦予的村民自治權。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是村民行使自治權的體現,在充分尊重村民自治權的前提下,村民成員收益分配的確定應當平等合法。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所作出的收益分配方案等決定、決議不僅應符合民主議定程序,其在內容上必須合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0條第2款亦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否則,應認定收益分配方案無效。 最后,應當符合村民待遇平等的原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屬于村民集體成員共同所有。所以,來源于農村集體組織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收益,屬于全體村民。土地補償費的分配,如果沒有法律的特別規定,就應由享有村民待遇的全體村民共同平等參與分配,即基于集體組織成員資格而分配的土地補償費就應當均等,不能以權利義務相一致為由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 綜合上述,原告通過確權確利登記成為講禮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一,依法與該村其他成員一樣享有同等權益,該權益不允許也不能夠任意由當事人的多數表決加以剝奪。雖然被告講禮村委會在款項分配前后組織實施了民主議定程序,但是作出的決議即土地收益款的分配方案卻對原告及其他部分已經被確認享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員不予分配,該方案侵犯了原告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獲得同等收益分配的權利,該方案不利于維護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的穩定,應予糾正。鑒于原土地收益款分配方案系被告組織進行民主決策程序作出,故糾正途徑亦應通過被告通過民主程序予以糾正,以符合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相關規定。由此,原告的請求已有相應合理救濟方法,故本院對于原告直接訴求給付土地收益款的請求不予支持。 本案與懷柔區北房村案件案情較為類似,因為“新戶”與“衍生人口”在這種案情下,法律地位是相同的。[9]但不同的是,在懷柔區法院的判決中,法院直接判令村委會給予原告確利款;而在昌平區法院的判決中,法院認為確利款的分配應當通過民主程序決定,法律只能糾正違法的民主決議結果,而不能代行民主程序直接判令村民大會給予原告確利款。這兩份不同的判決書,反映了當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對現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存在理解分歧,而這些重大問題的存在恰恰又增加或激化了本已十分棘手的農地糾紛與涉農信訪矛盾。 (三)以農地糾紛為主的涉農類信訪問題日趨嚴重 當前,涉農信訪量一直高位運行,并且持續攀升,對農村社會穩定之維護極為不利。以課題組在北京市調查所得的數據為例,即使在城市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北京,“三農”問題在全市信訪總量中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排在各類信訪問題的第三位,“三農”問題所引發的群體訪更是排在第一位。這些涉農信訪主要圍繞著征地補償款的分配、土地承包經營權糾紛和集體資產的處置而展開。由于這些問題皆與農村土地密切相關,故涉農信訪絕大部分是以農村土地為議題的。[10]根據北京市信訪辦公系統提供的數據,近五年來北京市涉農類信訪從數量上看呈遞增趨勢,涉農類信訪受案量從2006年的3279件上升到2010年的5263件。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涉農信 訪類總量(件) 3279 3949 4402 4483 5263
年份 信訪量總計 來信合計 來信比例 來訪合計 來訪比例 2006 3279 2499 76.21% 780 23.97% 2007 3949 3098 78.45% 851 21.55% 2008 4402 3695 83.94% 707 16.06% 2009 4483 3763 83.94% 720 16.06% 2010 5263 4500 85.50% 763 14.50%
年份 來訪總計 個體訪 集體訪 重訪 重復個體訪 重復集體訪 2006 780 595 185 235 70 2007 851 608 243 506 67 2008 707 569 138 459 35 2009 720 564 156 499 49 2010 763 562 201 844 60
需要說明的是,此數據來源于北京市信訪辦公系統中按內容分類的數據,其中的涉農信訪類總量包括來信、來訪,此辦公系統根據信訪的內容將信訪劃分為19類,但其對涉農信訪范圍的界定較為嚴格,將其他一些涉農信訪歸于社會建設類、拆遷安置類、歷史遺留問題類等,因而其數據統計顯示涉農信訪類總量較少。通過我們的調研實證考察,涉農類信訪的總量遠不止上述統計的總量。因為,因征收、拆遷、集體資產處置等亦在涉農類信訪中占有較大的比重。 表2顯示,近5年北京市涉農信訪,來訪總量較少且其基本呈遞減趨勢,但涉農信訪中非常態化來訪逐漸增多。表3的數據顯示,近5年來北京市涉農信訪中個體訪從數量上看,其占涉農信訪總來訪的較大比重,且其變化不大、表現較為平穩。但總的來看,非常態化來訪,從數量上看逐漸增多,尤其是重復訪表現得不穩定、不具有規律性,這給基層涉農信訪工作的展開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通過調研課題組發現,一些農村因政策落實不到位或者政策的不穩定而產生的集體訪,如果在基層無法得到有效的處理,容易引發越級訪;一些村民因歷史遺留性問題得不到解決而堅持長期訪;還有個別信訪人為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過極端手段上訪。集體訪、重復訪和極端訪等非常態化來訪是涉農信訪工作部門和信訪工作人員目前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此類信訪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容易激化社會矛盾,進而引發一系列具有綜合性的社會問題。 三、村民自治與農地糾紛 (一)如何理解《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1.村民委員會與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為了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根據憲法而制定的法規。該法第10條規定:“村民委員會及其成員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遵守并組織實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執行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決議,辦事公道,廉潔奉公,熱心為村民服務,接受村民監督。”[11]由此可見,村委會是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決議的執行者,村民大會類似于股東大會,村民代表大會類似于股東代表大會,村委會類似于董事會。[12]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4條全面規定了村民會議的權力范圍:“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經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二)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業的興辦和籌資籌勞方案及建設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經營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九)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由此可見,凡涉及到農地收益、農地承包、土地征收等土地問題,都必須由村民會議決定,村委會不能決定農地問題。此為授權性規定,授權范圍之外的事項村民會議不享有權力,但同時亦表明,對于授權范圍之內的事項,村民會議具有排他性的權力。因此,村民會議才是引發一切農地糾紛的始作俑者。 綜上可知,村民委員會是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涉及農村土地的一切問題,決定機構只能是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大會。而且,人民法院只能撤銷村民委員會及其成員的決定,而無法撤銷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 2.政府與村民自治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這說明鄉鎮一級人民政府無法解決“衍生人口”和“新老戶”合法權益被侵害問題,因為這一級政府對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只能“指導、支持和幫助”,而不能撤銷。因為村一級不是行政機關,其決議不適用行政復議,上級政府對其決議無可奈何。而作為村民會議執行機構的村委會對于鄉鎮一級政府的“指導、支持和幫助”,是否接受,法律并無明文規定。依據法理,不服從指導、不接受支持和幫助,皆難謂有法律責任承擔之后果發生。 另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7條第1款規定,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該條第2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該條第3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違反前款規定的,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36條第1款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事項的,由上一級人民政府責令改正。上述規定表明,鄉鎮一級政府主要是為村民自治服務的,村民決議只需報鄉鎮一級政府備案;即使村民自治過程違反了憲法、法律,侵害了他人合法權益,該級政府只能責令改正,而絲毫沒有采取更強制的措施的權力。相反,如果鄉鎮一級政府干預依法進行的村民自治,上級政府可以責令改正其干預行為。 通觀《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鄉鎮一級政府對于村民自治范圍之內的事項,如該法第24條所規定的農村土地處置問題,實際上是沒有決定權的。“責令改正”后面沒有人事與財政權力安排的支持,只能是淪為具文。這說明,如果村民自治成為侵害少數人權利的手段,政府似乎亦如同法院一樣,在法律明文規定的制度安排上,是無能為力的。 3.法院與村民自治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7條第2、3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或者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從上述規定看,如果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違法,或者侵害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只能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責令改正。而人民法院并無此項權力,這從基本法律的層面說明了法院無權受理此類農地糾紛。 此外,《村名委員會組織法》第36條第1款規定,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成員作出的決定侵害村民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責任人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根據這一款,村委會決定或村委會成員的決定,法院享有撤銷權。但是,遍查該法,并未發現該法授予了人民法院享有干預甚至撤銷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決議的權力。綜合以上兩條規定,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北京市懷柔區發生的“新老戶”問題裁判中,懷柔區人民法院直接改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法院能否受理不滿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引起的糾紛 1.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兩項答復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人民法院對農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分配糾紛是否受理問題的答復》(2001年7月9日法研[2001]51號)和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問題與村民委員會發生糾紛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答復》(2001年12月31日法研〔2001〕116號)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因收益分配產生的糾紛,屬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當事人就該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只要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上述兩項司法解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因收益分配產生的糾紛,法院應當受理。須注意,這兩則司法解釋適用的情形是村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糾紛,而非成員之間的糾紛。而在本文上述兩則案例中,其糾紛實際上是在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發生的,并不是集體經濟組織或村委會不愿意給“新戶”和“衍生人口”分配收益,而是其他的多數村民通過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這一合法的形式不給此兩類特殊人群平等分配利益的機會。一如前述,村委會和村經濟經濟組織只不過是這一決議的執行者而已,而并非始作俑者。因此,在上述兩則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兩項司法解釋沒有適用的可能。 2.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05]6號)第1條規定:下列涉及農村土地承包民事糾紛,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糾紛;(二)承包經營權侵權糾紛;(三)承包經營權流轉糾紛;(四)承包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糾紛;(五)承包經營權繼承糾紛。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未實際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對于這一條的理解,有令人費解之處。該條第1款第(二)項“承包經營權侵權糾紛,應予受理”,與第3款“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有明確的界限?如在上述“新老戶”問題中:(1)村民會議決議不給原告分配確權確利款,是屬于第1款第(二)項規定之情形,還是屬于第3款規定之情形?(2)村民大會決議,就征收補償費用,給“老戶”每人8萬,給“新戶”每人2萬,是屬于第1款第(二)項規定之情形,還是屬于第3款規定之情形? 在第一種情形下,確權確利款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孳息,剝奪權利之孳息,應屬于侵害此種權利本身。因為,擁有權利的目的在于使用、收益和處分,此種情形應屬于侵犯土地承包經營權之收益,自應屬于侵害該權利本身。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1款第(二)項,法院應該受理,這也正是懷柔區案件中所指向的事實。但是,遺憾的是,對于調研中發現的懷柔區“新老戶”問題則屬于第二種情形,由于根據該司法解釋第1條第3款,“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即拒絕受理此類案件。因此,本項規定非常值得質疑。所謂“土地補償費”,應是指農村土地被征收或征用之后,由征收或征用方補償給集體的費用。這部分費用應屬于集體內所有成員所有,應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制定分配標準,由村委會執行分配任務。如果村民對分配數額有異議,應屬于普通的民事爭議,緣何法院不予受理呢?這與兄弟姊妹按份共有的房子被拆遷了,而其中一位就多數兄弟姊妹制定的補償費分配標準有異議而訴至法院的情形有什么實質性區別呢?難道,兄弟姊妹之間的這種糾紛法院也能不受理嗎? 在昌平區發生的“衍生人口”案中,原告系2004年8月1日以后出生的村民,但出生后即獲得了村民資格,與其他村民一樣,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2007年,該村一部分土地用于合作開發進行新村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收益。村民代表會議認為應按照2004年8月以前的人口來分配收益,于是原告這部分人的土地收益權被剝奪了。那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的司法解釋,這種情況屬于哪一類糾紛呢?根據上面的分析,此種糾紛既可能屬于第1條第1款第(二)項中所指的“承包經營權侵權糾紛”,因為這是侵害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之孳息;又可能屬于該條第3款規定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的情形,而且從文義上說更加符合這一款的規定。但是,法院還是受理并審理了這起案件。由此證明,該條的適用是比較混亂的。 3.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做好涉農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 根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進一步做好涉農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37號)第7條的規定,按照《物權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等法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妥善處理好征地補償費用分配等糾紛。在審理因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實行差別待遇,侵害當事人利益引發的糾紛案件中,要依法充分保護農村集體成員特別是婦女、兒童以及農民工等群體的合法權益。 這是迄今為止最高人民法院就農地糾紛所作出的最新司法解釋。該條明確強調要妥善處理好征地補償費用分配等糾紛,并針對因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實行差別待遇的案件,指出要依法充分保護農村集體成員特別是婦女、兒童以及農民工等群體的合法權益。這證明,目前實踐中因農村土地補償費用分配不均而引發的問題確實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且在此類案件中,婦女、兒童等“衍生人口”處于弱勢地位。 但是,該司法解釋并未正視該院前述司法解釋以及實踐中就此問題所產生的亂象,并未提出技術性的新規定,以終結此種混亂情形。或者,這仍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尚未覺察到的一個重大問題。 4.2004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 在北京市,法院拒絕受理此類案件最直接的依據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4年12月10日作出的《關于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京高法發[2005]68號)第8條第1款規定:在土地征用補償案件中,村民認為補償費用偏低而起訴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的案件,如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通過民主議定方式形成分配決議,并無截留、扣繳、挪用或分配不公情形的,應裁定駁回村民的起訴。但是,該條第2款又認為,因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對土地征用補償費截留、扣繳、挪用或分配不公等原因,村民認為沒有實際得到補償費用的,應以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為被告。在審理中,有證據證明確有截留、扣繳、挪用或分配不公事實的,村民要求返還收益的,法院應予支持。但在這一款的情形下,由于決議是村委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作出的,因此委會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當然的被告。但是,本文所討論的兩則案例,都是由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作出的決議,因此不是上述《指導意見》第8條第2款中所指情形。
注釋: [1]參見北京市信訪矛盾分析研究中心與北京市領導科學學會:《關于對北京市十年來信訪特點及發展趨勢的研究》,2010年11月。 [2]李昌鳳:《轉型時期農民涉法信訪問題探析》,載《人大研究》2005年第1期。 [3]根據朱芒的統計,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將維護“社會穩定”作為立法目的之一的有:《武裝警察法》第1條、《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第1條、《農村土地承包法》第1條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部分)等法律;將維護“社會穩定”設置為政府責任的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8條、《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條;將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程度規定為法律事件的構成要件的有《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28條第2款。將破壞“社會穩定”規定為行為后果程度要件的有《郵電法》第37條第3項。從明文規定的內容和方式來看,《郵電法》第37條第3項的“社會穩定”概念或許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8條的“社會穩定”概念的規定較為相近。參見朱芒:《什么是或者不是“社會穩定”———(2010)滬二中行終字第189號行政判決評析》,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4]從國家制度建設層面看,有學者指出:“對于一個農民大國來說,恐怕沒有任何制度的重要性可與土地制度相提并論。”靳相木:《中國鄉村地權變遷的法經濟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 [5]近年來,信訪工作成為黨和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作。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中共中央[2007]5號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眾性事件聯席會議(關于領導干部定期接待群眾來訪的意見)等三個文件的通知》(中辦發[2009]3號)及《中央政法委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中辦發[2009]22號)。 [6]參見如下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懷民初字第02193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6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7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8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9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10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11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12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17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22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23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24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80號,(2009)懷民初字第02387號,(2009)懷民初字第02388號,(2009)懷民初字第02389號,(2009)懷民初字第02390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61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1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3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4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5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6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7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8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89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0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1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2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4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5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6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7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8號,(2009)懷民初字第02199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0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1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2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3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4號,(2009)懷民初字第02205號。 [7]北京市懷柔區民事判決書(2009)懷民初字第02193號。 [8] 參見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如下民事判決書:(2009)昌民初字第10458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7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6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5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4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3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2號,(2009)昌民初字第10451號。 [9]此類人群的法律地位問題實際上是農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參見韓松:《農民集體所有權主體的明確性探析》,載《政法論壇》2011年第1期;高飛:《論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之民法構造》,載《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高飛:《論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立法的價值目標與功能定位》,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6期。 [10]參見陳小君、高飛、耿卓等如下系列論文:《后農業稅時代農地權利體系與運行機理研究論綱———以對我國十省農地問題立法調查為基礎》,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1期;《農村土地法律制度運行的現實考察———對我國10個省調查的總報告》,載《法商研究》2010 年第1期;《農地流轉于農地產權的法律問題———來自全國4省8縣(市、區)的調研報告》,《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這些調研報告都詳細指出了目前在中國農村廣泛存在的農地糾紛樣態及其在農村社會糾紛中所占巨大比重。 [11]學者認為:“村民自治就是農村特定社區的全體村民,根據國家法律法規的授權,依照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機關,確定行為規范,辦理本社區內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村民自治應當包括如下要素:自治的法律依據、自治體、自治機關、自治權和自治行為規范。”崔智友:《中國村民自治的法學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類似的描述性定義,參見徐勇:《中國農民村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頁。 [12]在村民自治的組織體系中,村民會議是村民自治的最高權力(一種公共權力)機關,它可以依法決定其他自治組織包括村民委員會、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小組的組織形態,是其他自治組織的產生源泉,同時,它也是村民自治的意思機關,享有最高的自治決定權。參見周葉中、韓大元主編:《憲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頁。 [13]實踐中,北京市即有按照該意見判決的案件,如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2007)房民初字第6342號原告劉志歧訴被告北京市房山區大石窩鎮廣潤莊村村民委員會案。法院認為:原告劉志歧、劉志國、李學芝以補償款過低為由起訴村委會,庭審中查明,村委會就占地補償款如何分配問題,于2006年3月19日召開了黨員、村民代表大會,黨員、村民代表在村民代表大會決議上簽字通過補償方案。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說明》的規定,村民委員會通過民主議定方式形成分配決議,并無截留、扣繳或分配不公情況的,村民僅認為補償費用不符合法律、政策規定的,應駁回原告起訴。 [14] 參見陳小君:《我國婦女農地權利法律制度運作的實證研究與完善路徑》,載《現代法學》2010年第3期;高飛:《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困境與對策探析》,載《中國土地科學》2009年第10期。 [15] 實踐中,有的地方法院即使受理此類案件,也是以村民委員會為被告,訴訟內容多因土地糾紛而起,特別是因農轉居、出嫁女、離婚女、新生兒等問題而引起的訴訟。在此類訴訟中被告勝訴率非常低,且存在執行難的困境。參見駱曉明、周慶:《村委會官司纏身現行初探———基于臨安市青山湖街道的實證調查》,載杭州市法學會編寫:《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決機制理論與實踐》,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第324頁以下。 [16] 國務院《信訪條列》第6條第2款: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機構是本季人民政府負責信訪工作的行政機構,履行下列職責(一)受理、交辦、轉送信訪人提出的信訪事項;(二)承辦上級和本季人民政府交由處理的信訪事項;(三)協調處理重要信訪事項;(四)督促檢查信訪事項的處理;(五)研究、分析信訪情況,開展調查研究,及時向本級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進工作的建議;(六)對本級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機構的信訪工作進行指導。 [17]關于信訪“倒逼”機制的研究,參見李芝蘭、吳理財:《“倒逼”還是“反倒逼”———農村稅費改革前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 [18]參見張泰蘇:《中國人在行政糾紛中為什么偏好信訪》,載《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 [19]林莉紅:《論信訪制度的定位———從糾紛解決機制系統化角度的思考》,載《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1期。 [20]參見吳超:《新中國六十年信訪制度的歷史考察》,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1期;李秋學:《新中國建立后中共信訪權利觀的生成:情境、語境與困境》,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4期;倪宇潔:《我國信訪制度的歷史回顧與現狀審視》,載《中國行政管理》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