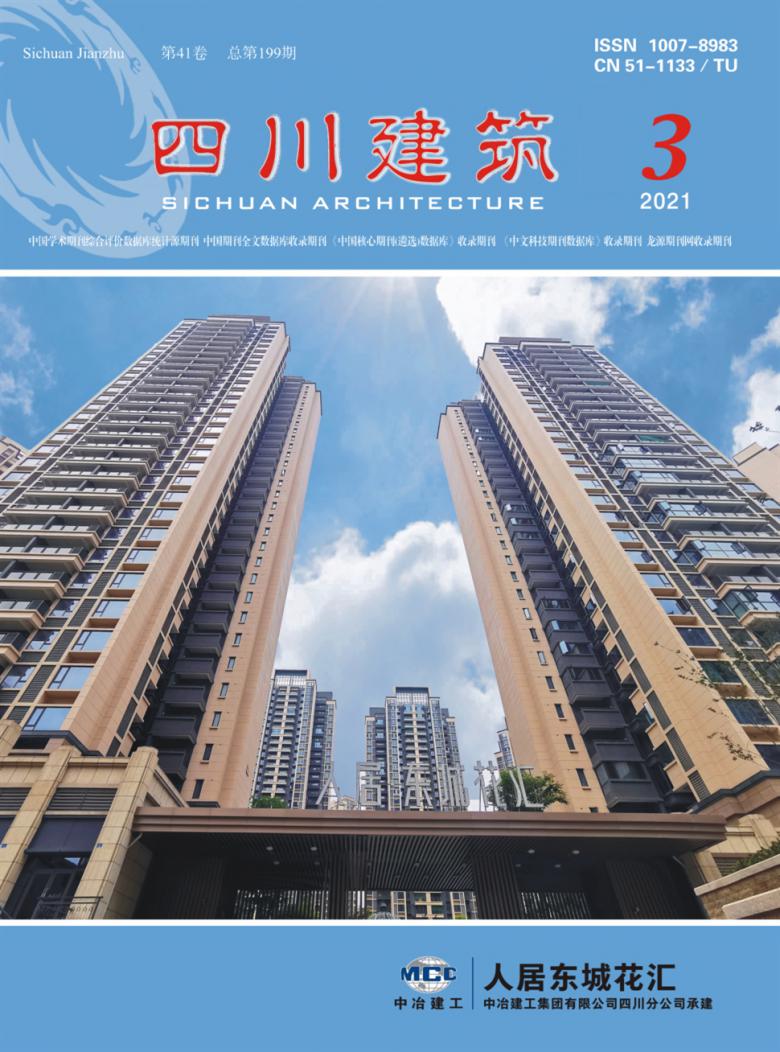日本監獄法的新發展——《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評介
陳海平
關鍵詞: 日本/監獄法/刑事收容設施/被收容者/處遇
內容提要: 日本于2006年6月8日頒布了《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施行近100年的《監獄法》全面退出了歷史舞臺。其出臺經歷了一個極為漫長和艱難的歷史歷程。該法內容相當完善,實現了刑事設施、留置設施、海上保安留置設施在管理運營上的統一,實現了服刑者、未決拘禁者、死刑確定者、被留置者在收容處遇上的平衡。立法用語中性、收容處遇人道、法律規則精密、救濟機制完善為該法鮮明特色。無論是從法律文本分析還是對施行實踐考察,該法都是極為成功。在轉變理念、立法技術、法律落實等方面它對我國立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日本《監獄法》頒布于1908年3月28日(明治41年法律第28號),2005年5月25日(平成17年法律第50號)頒布了《關于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等的法律》(以下稱《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法》)①,作為刑務所②、少年刑務所③ 執行刑罰的基本法源,實現了刑事設施④ 在法律適用上的統一;原《監獄法》被更名為《關于收容于刑事設施的刑事被告人等的法律》(以下稱《刑事被告人等收容法》)⑤,繼續作為管理羈押于拘置所⑥ 的未決拘禁者和死刑確定者的基本法律。之后于2006年6月8日(平成18年法律第58號)頒布并于2007年6月1日實施了《關于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等處遇的法律》(以下稱“《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⑦,統合了前述兩部法律,并將留置設施⑧、海上保安留置設施⑨ 等代用監獄正式納入進來,實現了刑事收容設施⑩ 在法律適用上的統一。簡言之,該法既是已決犯行刑法,又是未決犯羈押法;既是收容設施管理法,又是被收容者處遇法。本文試圖簡要介紹該法,并對其作初步評價,以探求對我國相關立法的啟示。 一、《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制定歷程 正如龐德所言:“法律必須穩定;但又不能靜止不變”。[1]日本《監獄法》自1908年頒行后,在經歷了最初幾年的穩定之后,其“修改工作自1922年就開始著手”,但因“尋求與刑訴法修改的適應性以及世界大戰的爆發”,未能進行實質性的修改,致使“監獄法體系極為混亂”。[2]二戰后,刑務所過剩收容激增,收容秩序混亂,這與強調尊重并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的和平憲法嚴重沖突,[3]監獄法的修改被再度提上議事日程,甚至提出了“修正監獄法的法律(矯正設施法)草案”,但終因日本政府態度轉變而未能頒布。[4]1976年開始,日本法制審議會就監獄法的修改進行了再度努力,并設置了監獄修正委員會,學術界亦積極參與并開展了極為深入的研討,[5]監獄修正委員會于1980年提出了《監獄法修正綱要》,在此基礎上制定并于1982年向國會提交了《刑事設施法案》和《拘留法案》,后因次年政治局勢變化(眾議院被解散)而成廢案,雖然該法案經修正又于1987年、1991年兩度被提交國會,同樣因眾議院被解散而兩度流產。[6]極低的犯罪率與國民的安全感被認為是未能修改的時代背景。[7] 2002年,隨著“名古屋刑務所暴行事件”(11) 的曝光和升級,監獄服刑人員生活題材電影(12) 的上映,日本監獄存在的問題不斷被推向臺前,犯罪率的飆升也使國民開始關注和反思監獄的管理及運營。在此時代背景下,監獄法修改工作自2003年全面展開,日本開展了監獄調查,公布了有關監獄運營的報告,設置了社會各界充分參與的行刑改革會議,提出了《行刑改革會議提要》,并結合法務省、警察廳、日本律師聯合會等各方的意見,于2005年頒布了《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法》。[8]該法的頒布全面改善了服刑者的處遇,而適用《刑事被告人等收容法》的未決被拘禁者和死刑確定者之處遇并未改善,法律地位的不同造成了各種被收容者在處遇上的極大差別。[9]此外,都道府縣警察及海上保安廳設置的留置設施一無明確法律依據、二無相關處遇規定,《監獄法》之下固有的問題由來已久、積重難返,[10]這便成為修改關涉未決拘禁者和死刑確定者處遇的《刑事被告人等收容法》之理由。在法務省、警察廳、日本律師聯合會等的積極努力下,2006年6月8日《關于部分修改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法的法律》得以頒布,修改了《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法》,修改后的法律名稱為《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廢止了《刑事被告人等收容法》,實現了服刑者與未決拘禁者、死刑確定者、被留置者在處遇上的平衡,使替代性收容設施(13) 獲得了法律依據并構建了相關制度。至此,《監獄法》之全面、實質的修正終于完成,施行約100年的《監獄法》全面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內容結構 《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14) 在形式上分為總則、被收容者等的處遇、補則三編,另有附則,前三編總計293條(15);其實質內容包括“刑事設施管理法”和“刑事被收容者處遇法”兩個部分,“管理法和處遇法復合特征非常明顯”。[11] 總則由通則、刑事設施、留置設施、海上保安留置設施四部分內容組成。通則規定了本法的目的,明確了相關術語的定義;刑事設施、留置設施、海上保安留置設施三個部分在形式上頗為相似,就各自的設立依據、組織結構、工作人員、被收容者分管分押、監督監查機制等內容分別進行了規定。 第二編“被收容者等的處遇”分為四章,第一章分別規定了對服刑者、未決拘禁者、死刑確定者的處遇原則,后三章按照收容設施的不同分別規定了刑事設施中被收容者的處遇、留置設施中被留置者的處遇、海上保安留置設施中海上保安被留置者的處遇。關于刑事收容設施中被收容者的處遇,整體而言,這三章在內容及體例上共通之處頗多,差異僅在于因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身份而異所致的特定內容之增刪與調整。基本內容包括:收容的開始(權利告知、識別性身體檢查)、處遇的形態(單間收容原則、相互接觸的限制等)、作息時間、物品的借用及自費負擔、貴重財物的處理(檢查、保管、扣存(16)、移交、交付、遺留物處理等)、衛生保健及醫療、宗教行為、書刊閱覽、維持紀律及秩序(遵守事項、身體檢查、制止措施、武器及警械等的使用等)、矯正處遇(僅適用于刑事設施中的服刑者(17),具體包括通則、勞動(18)、各種指導、外出及外宿等內容)、外部交往(會見及限制、外國語的使用、電話的使用與限制)、獎懲(“獎”只適用于刑事設施、“懲”對于所有刑事收容設施均適用)、不服異議(申請審查、申請再審查、申告事實、申訴、保密、禁止不利益處分等)、釋放、死亡、死刑執行(僅適用于刑事設施)、與法務大臣磋商(僅適用于留置設施)。 補則分為五章,分別規定了替代收容及其法律準用、勞役場(19)與監置場(20) 及其處遇、刑事設施長官及其職員代行司法警察職員職權、有關條約的優先效力、法律責任。 三、《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鮮明特色 (一)立法用語趨于中性 《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頒行,法律名稱、法律用語都有了明顯變化,更多地使用中性詞語,以往因歷史原因給人以被拘禁與痛苦感的用詞消失了,如“監獄”、“病監”改為“刑事設施”,“監房”改為“居室”,“監獄官吏”改為“刑事(或留置)設施職員”;意味著恥辱與差別對待的“囚”字用語也被剔除了,被收容者的稱謂發生了變化,如“拘留囚”、“禁錮囚”、“懲役囚”統一改為“服刑者”或“被收容者”,“在監者”改為“刑事被收容者”,“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統一被改為“未決拘禁者”;調整了一些具有濃厚權力及強制色彩的用詞,如“請愿”改為“申訴”,“斥責”改為“警告”;具有歧視色彩的一些用詞做了中性化處理,如“不具者(21)”改為“身體障害者”,“精神病(者)”、“傳染病者”等詞也被調整為罹患“疾病”、“傷病”之人。 (二)法律規則更為精密 1908年頒行的日本《監獄法》由總則、收監、拘禁、警戒(戒護,指用強制力保障獄內秩序)、勞動(作業)、教誨及教育、給養、衛生及醫療、會見與通信、扣存、獎懲(賞罰)、釋放、死亡共13章組成,總計75條。可以說,日本《監獄法》雖然明確了行刑的基本框架,并規定了行刑處遇的關鍵規則,但只有75條的簡單法律,其本身的可操作性確實很差,因此,長期以來只能借助于修改、廢除、制定省令及府令(22) 等方式來保證落實。現行《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與《監獄法》相比,不但條文多(除附則外,共計293條之多),而且法條信息含量大(大量的法律準用性規定使得法條的容量更大),法律規則更為精密、明確,可操作性更強。例如第275條關于海上保安被留置者申請審查的規定,(中譯條文)長達847字,其中對申請審查的受理主體、申請事項、申請期限、申請方式、法律準用等都做了極為詳細的規定;如對于刑事收容設施日常管理的規定也極為嚴謹縝密,明確規定了被收容者保持清潔、洗浴、閱覽書報、理發、剃須、識別性身體檢查等各個方面,都屬于可以直接操作落實者;再如總則中對于刑事設施、留置設施、海上保安留置設施設置及運行方面的規定,基本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總則”式條文,而是力求將相關制度及措施最大可能地明確規定,以便能夠直接操作落實,如對“刑事設施視察委員會”的規定精密到了明確規定委員人數、選任、任期等極為微觀的程度。 (三)收容處遇趨向人道 《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核心內容就是被收容者的處遇問題,本法使被收容者尤其是未決拘禁者的處遇有了極大改善,被日本學者譽為“迎來了行刑的新時代”,[12]與《監獄法》相比較而言,無論是處遇原則、處遇方式還是懲罰性處遇,都更為人道。簡而言之,其人道化努力有以下表現: 第一,處遇原則體現著對人道的追求。如第30條將被收容者的處遇原則規定為:“服刑者的處遇應結合其資質和環境,以激發其自我反省及改善更生的愿望、培育其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為目的實施。”再如第32條將死刑確定者的處遇原則規定為:“死刑確定者的處遇,應當注意使其情緒穩定。” 第二,具體處遇方式的設置體現著人道理念。例如盡可能地使用單間收容,制定符合常人生活習慣的作息時間表(23),專門規定對老年、孕產婦、身體虛弱者及其他有保健必要的被收容者的特別養護措施,保障并支持宗教活動,明確規定勞動條件、勞動時間及休息時間、設立勞動獎勵及補貼制度,保障會見通信權并在一定條件下允許服刑者使用電話等現代通訊方式進行交流等。對死刑行刑日期的規定也集中體現了人道關懷,該法第178條第2款規定:“星期日、星期六、《關于國民節日的法律》(昭和23年法律第178號)規定的假日(24)、1月2日、1月3日以及12月29日至31日,不得執行死刑。”當然,最體現人道精神的莫過于允許女性被收容者養育子女的規定,該法第66條明確規定了允許養育一歲以下子女的一般原則、一歲以后繼續養育的申請及條件,以及確保該被養育子女健康成長的生活用品保障及其他必要措施。 第三,一些不人道的處罰措施被廢除。對于被收容者違反收容管理制度的處罰,本法廢除了《監獄法》規定的一些不人道的如“禁閉”(25)、限制或減少食物(26) 等方式,代之以文明、人道的處罰措施。 (四)權利救濟更加完善 《監獄法》中被收容者的權利救濟主要有向法務大臣或巡閱官請愿、刑務所長接見兩種方式。請愿并不屬于強制異議權,是否受理及處理完全依靠法務大臣或巡閱官的判斷,而且在近年請愿數量激增的情況下,事實上是不可能全部受理及處理的;刑務所長接見在本質上亦非純粹的行政救濟措施,而更像是領導的勸慰和開導。[13] 在此種情況下,亟須改革因時代變革而業已失去實際意義的請愿、接見制度,確立能夠確保公平、公正、迅速處理的第三方權利救濟機制。為此,《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設計了申請審查、事實申告、申訴三種救濟途徑。 申請審查是指刑事被收容者對收容設施做出的特定處分(如禁止或限制宗教行為)不服時,可以在被告知該處分之次日起的30日內向特定官署(因收容設施之別而異,如在刑事設施為矯正管區長官)提請審查,該受理官署即應盡可能在90日內做出裁決并通知申請人;該申請人如對前述裁決不服,還可以在收到裁決之次日起的30日內向更高官署(因收容設施之別而異,如在刑事設施為法務大臣)提出再審查的申請(即“申請再審查”),該更高官署即應盡可能在90日內做出裁決并通知申請人。 事實申告(27) 是指刑事被收容者對收容設施職員實施的關涉自己的特定行為(如違法或不當地使用手銬)有異議時,可以在該申告事實形成之次日起的30日內向特定官署(因收容設施之別而異,如在留置設施為警察本部部長)提出申告,該官署即應盡可能在90日內確認該申告事實的有無及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將此結果通知申告者;該申告者如對前述處理不服,還可以在被告知該處理之次日起的30日內向更高官署(因收容設施之別而異,如在留置設施為公安委員會)提出申告,該更高官署即應盡可能在90日內做出處理并通知申請人。 申訴(28) 是指刑事被收容者對收容設施采取的措施以及自己所受處遇(如禁止或限制收發書信)不服時,可以向監查官、所屬刑事收容設施長官(刑事設施長官或留置業務管理者或海上保安留置業務管理者)及主管長官(法務大臣或警察本部部長或海上保安廳長官)申訴,對此申訴,受理者應當誠實處理,并將處理結果通知申訴者。 四、對《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簡要評價 《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更新了明治以來的舊監獄法體系,開創了行刑的新時代,廢除了累進處遇制度、創設了緩和限制(29) 和優遇(30) 制度,貫徹了處遇個別化(31) 的理念與制度,積極促進服刑者復歸社會,實現了刑事收容設施運行的透明化、被收容者權利義務的明確化,尊重被收容者的主體地位并推進行刑的民主化,合理設計了收容生活,充實了服刑勞動的內容,擴充了外部交往的規定,完善了不服異議制度。對此,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藤本哲也教授以服刑者處遇的改善為例說明本法頒行的積極意義時,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本法“不僅充實了服刑者的社會復歸處遇,還明確了被收容者的權利義務、明確了(刑事收容設施)職員的權限、保障了被收容者的生活水平、保障和擴充了被收容者的外部交往權、設置刑事設施視察委員會確保行刑設施的透明運用、確立了不服異議制度等,通過立法解決了監獄法100年來存在的諸多難題、實現了近代化、法律化、國際化。”[14] 《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施行兩年來,日本刑事法理論界與實務界開展了積極的探討和對話,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本法的實施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例如有關被收容者權利救濟的不服異議制度,運行伊始效果便極為明顯,“兩年來,受理不服異議年均九千余件,與本法施行前一年相比,件數增加一千有余,同比增長約16%~18%,……處理迅速化、制度合理化的效果顯而易見。”[15]再如作為服刑者矯正處遇核心內容之一的勞動(刑務作業),本法施行后改觀頗多[16]:由于強調其他處遇(各種指導)及運動的重要性,為確保其他處遇及運動的必要時間,法務省縮短了年勞動日數,并限定日勞動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服刑者的勞動安全及衛生保障有了明顯改善,服刑者參與勞動的積極性及參與人數(32) 也有了顯著提高;勞動工種的調整與增加也為服刑者掌握新技術提供了可能和條件,職業訓練(技術培訓、資格認證等)的種類和成效也逐年走高;勞動時間的縮短、其他處遇時間的延長在勞動收入上亦有反映,2006年的勞動收入較4年前有大幅度縮減,但勞動獎勵或預算還是穩中有升。通過對權利救濟機制與服刑者勞動在運行現狀的描述,關于本法施行的實際效果,應該可以得出《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的制定與施行)是成功的這樣一個初步的結論。 當然,隨著被收容者權利的擴大、權利保障的完善、收容處遇的改革,與之相伴的問題也不少:[17]如刑事收容設施職員數量及收容能力不足導致的超負荷運轉、民間刑務所(33) 的嘗試及運營面臨的問題、矯正處遇的科學實施與外部協助、矯正處遇和社會復歸的銜接、財政預算的支持等,都尚需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① 日文名稱為《刑事施設及び受刑者の処遇等に関する法律》,直譯為《關于刑事設施及服刑者處遇等的法律》,在日本常被略稱為《服刑者處遇法》(受刑者処遇法)。該法之全文、修改理由及新舊條文對照等可參見:法務省のホ一ムベ一ジヘ(http://www.moj.go.jp/HOUAN/houan31.html)。 ② 日文名稱為“刑務所”,系(懲役和禁錮)自由刑的執行機構,相當于我國的監獄。日本自由刑主要有懲役(須服勞役之監禁,1個月至15年的有期或無期)、禁錮(不需服勞役之監禁,1個月至15年的有期或無期)、拘留(1日至30日的拘禁)三種。 ③ 日文名稱為“少年刑務所”,系未成年人刑罰的執行機構,相當于我國的未成年人管教所。 ④ 刑務所、少年刑務所、拘置所在日本統稱為刑事設施。 ⑤ 日文名稱為《刑事施設ニ於ヶル刑事被告人ノ収容等ニ関スル法律》,直譯為《關于收容于刑事設施的刑事被告人等的法律》,在日本常被略稱為《舊收容等法》(舊収容等法)。 ⑥ 日文名稱為“拘置所”,系羈押未決拘禁者以及關押死刑確定者的機構。 ⑦ 日文名稱為《刑事収容施設及び受刑者の処遇等に関する法律》》,直譯應為《關于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等處遇的法律》,基于中文表達習慣的考慮,筆者譯為《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在日本常被略稱為《刑事收容設施法》(刑事収容施設法)、《刑事被收容者處遇法》(刑事被収容者処遇法)等。該法之全文、修改理由及新舊條文對照等可參見:法務省のホ一ムベ一ジヘ(http://www.moj.go.jp/HOUAN/houan31.html) ⑧ 日文名稱為“留置施設”,系各都道府縣警察本部、警察署設置的用于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臨時羈押、被羈押者的代為羈押機構,以及拘留刑、罰金刑的代用執行機構。 ⑨ 日文名稱為“海上保安留置施設”,系海上保安廳設置的用于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臨時羈押以及被羈押者的代用羈押機構。 ⑩ 刑事設施、留置設施、海上保安留置設施在日本統稱為刑事收容設施。 (11) 2001年12月以來,名古屋刑務所發生數起工作人員虐囚事件,致多人死傷,引起了國民的公憤,多名工作人員以涉嫌特殊公務員暴行凌辱罪而被逮捕、追訴。以此為契機,國會議員反復質詢監獄管理問題,此后發生了法務省矯正局長被撤換、監獄長辭職、原監獄長自殺等一連串事件,該刑務所4名工作人員也于2007年3月30日被名古屋地方法院認定有罪。 (12) 崔洋一導演的電影《刑務所之中》(Keimusho no naka),全面介紹了日本高墻內犯人們的日常生活。 (13) 在《監獄法》時代稱為“代用監獄”,是指隸屬于都道府縣警察的留置設施(留置埸),長期以來作為大多數未決拘禁者的羈押機構,雖無明確的法律依據但事實上作為普遍性的收容設施運行。據統計,1971年被羈押于拘置所者僅占全部被羈押者的18.5%,這一數字在2004年為16.8%,其余均被羈押于各替代收容設施。參見:小池振一郎「代用監獄問題と未決拘禁法」、『自由と正羲』57卷9號[2006.9]、17頁。 (14) 本文中涉及的該法中文譯文均來自筆者與(西南政法大學)馮濤副教授合作翻譯的中文版本(待發表)。 (15) 日本法律大多附有較長的附則,主要規定施行日期、過渡措施、相關法律的修改、新舊法的適用等等問題,而且會隨著相關法律的修改不斷增加,如本法目前已有5個附則近百個條文。其內容多為技術性規定,故有關日本法律法令的數據庫、出版物基本不會完全收錄附則,僅擇其要者收錄。 (16) 日文名稱為“領置”,直譯有“扣留”、“沒收”、“保管”等含義。在本法中的基本含義為“對被收容者不便或不能自行保管的財物,由收容設施暫時扣留并代為保管,特定情形出現時歸還被收容者”。在日本《監獄法》之中文譯本中,對“鎮置”的翻譯有“收管”(楊小川譯:“日本監獄法”,《國外法學》1986年第5期,第71頁)、“扣存”(前引《勞動改造法學參考資料第三輯》第158頁)、“保管”(黃秉心譯:“日本監獄法”,《法學雜志》(東吳大學法學院主辦)1935年第2期,第61頁;又見于蕭榕主編:《世界著名法典選編刑法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頁)等,基于其立法原意及中文表達習慣的考慮,筆者以為“扣存”更為合適。 (17) 特指在刑事設施中被執行自由刑(懲役和監禁)刑罰者,不包括被判死刑等待執行者(死刑確定者,被收容于拘置所)、留置設施中作為服刑者的被留置者(被留置服刑者),后二者不執行矯正處遇。 (18) 日文名稱為“作業”,直譯有“工作”、“勞動”、“作業”等含義,基于中文表達習慣的考慮,筆者通譯為“勞動”。 (19) 日文名稱為“労役場”。日本刑法第18條規定:對被判罰金刑或科料刑者,不能繳納或不能完全繳清罰金、科料時,應在一定期間(罰金刑1日以上2年以下,科料刑1日以上30日以下)內將其留置于特定場所(附設于刑事設施的勞役場)強制勞動以充抵罰金、科料。 (20) 日文名稱為“監置”、監置場”。監置是指《法庭等秩序維持法》(“法廷等の秩序維持に関する法律”(昭和27年7月31日法律第286號)規定的,對違法法庭(包括法庭外司法場合)秩序、妨害法院執行職務或明顯冒犯司法權威的行為進行制裁的措施之一,即指將有前述行為者留置于特定場所(附設于刑事設施監置場)并限制20日內的行動自由。 (21) 日本名稱為“不具者”,同意詞有“片輪者”,日文原意為:身體殘疾者、畸形人、畸形兒、廃人等等,由于有歧視的語感(差別表現とされる理由でめる),二戰后逐漸開始使用中性的“身體障害者”一詞,日文原意為:出生、疾病、外傷所致的身體殘疾者(生れつき、または疾病?外傷にょり身體に障害を有する者),略稱為“身障者”。有關該詞的使用演變可參見:熊田政信:“「障害」は「障礙」(「障礙」)と表記すべきでめる”,資料來源:http://www.rehab.go.jp/rehanews/japanese/No226/5_story.html。 (22) 指各相關行政部門(如法務省、內閣府、國土交通省)依據法律授權制定的實施細則。《刑事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法》頒行后制定的省令、府令如:《刑事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規則》(刑事施設及び被収容者処遇規則,平成18年5月23日法務省令第577號)、《刑事收容設施法施行規則》(刑事収容施設法施行規則,平成19年5月25日內閣府令第42號)等。 (23) 具體作息時間本法授權由主管當局以省令、府令的形式規定,如法務省的《刑事設施及被收容者處遇規則》第12條明確規定了就餐、就寢、運動、洗浴的時間區間:如早餐時間為6:30—8:30,午餐時間為11:00—13:00,晚餐時間為16:00—19:00,就寢時間為晚9點至早8點之間連續8小時以上。各收容設施只能在此時間區間內制定具體的作息時間表,如日本最大的(定員3 030人)大阪刑務所即規定9:00就寢,6:40起床。 (24) 該法規定了包括元旦、成人日、憲法紀念日、天皇誕辰紀念日在內的15個法定假日。 (25) 見《監獄法》第60條,日文名稱為“屏禁”,指將人在明室(有窗)中連續拘禁2個月以內(“軽屏禁”),或在暗室(無窗、無臥具)連續拘禁7日以內(“重屏禁”)。 (26) 見《監獄法》第60條,具體包括兩種:其一為在15日內禁止食用自費食物;其二為在7目內減量配給食物。 (27) 與申請審查的主要區別在于:申告只針對事實行為,不存在撤銷處分的可能,相對于申請審查是一種“間接”的救濟手段。參見:青山純「新法における被収容者の不服申立制度」、『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32頁。 (28) 日文名稱為“苦情の申出”,有“投訴”、“提出請求”等含義。本法之“苦情の申出”由《監獄法》之“請愿”轉化而來,指刑事收容設施被收容者就關涉自己的處遇向法務大臣、監查官、收容設施長官提出處理請求,其請求事項范圍同申請審查及申請再審查,對提出及處理期限沒有嚴格要求,與我國的“申訴”頗為相似,故筆者將其譯為“申訴”。 (29) 指本法的第88條規定的,為培養服刑者的自覺性和自律性,對于因維持刑事設施的紀律和秩序而對其實施的生活、行動方面的限制,根據其矯正情況逐漸放寬(如在開放性場所服刑)的一種矯正措施。 (30) 指本法第89條規定的,為喚起服刑者改善更生的愿望,將特定處遇(如增加物品配發數量、會見次數等)的實施與服刑態度的評價相掛鉤的一種矯正措施。 (31) 指根據服刑者資質、生活環境等個人情況因人而異地制定矯正方案,通過勞動技能的培育、社會生活知識的灌輸、生活習慣的養成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防止再犯罪和促進服刑者順利復歸社會的一種矯正措施。 (32) 在日本,監禁(禁錮)刑、拘留刑服刑者不以參加勞動為義務,但可以允許自愿參加勞動者。 (33) 即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刑務所,允許民間投資介入刑事收容設施建設,并在政府監督下通過運營管理回收投資,是近年來日本為緩和刑事收容設施過剩收容而采取的對策之一。
【參考文獻】 [1][美]羅斯科·龐德.鄧正來譯.法律史解釋[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2. [2][7][日]山口昭夫.日本的監獄法的修正與今后的動向[A].張小寧譯.武大刑事法論壇(第3卷)[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296-297,297-298. [3]石塚伸-「戦後監獄法改正史と被収容者処遇法——改革の到逹點としての受刑者の主體性」、『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53頁。 [4]何勤華.日本的監獄法制改革[A].何勤華.法律文化史論[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9-150. [5]王泰:“日本的監獄法修訂研究概況介紹”,載北京政法學院刑法教研室、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勞動改造法學參考資料(第三輯)》,1983年印,第370-371頁;[日]前野育三:“關于修改監獄法的討論總結”,王泰譯校,載前引《勞動改造法學參考資料(第三輯)》,第372-376頁。 [6]石塚伸-「戦後監獄法改正史と被収容者処遇法——改革の到逹點としての受刑者の主體性」、『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53頁。 [8][10]林眞琴「刑事収容施設及び被収容者等の処遇に関する法律の成立」、『ジュリスと』1319號[2006.9.15]、44頁,45頁。 [9]名取 俊也「刑事収容施設及び被収容者等の処遇に関する法律の概要」、『ジュリスと』1319號[2006.9.15]、52-53頁。 [11]長沼 範良「刑事収容施設及び被収容者等の処遇に関する法律の意義と今後の課題」、『ジュリスと』1319號[2006.9.15]、4頁。 [12]松村 憲一「受刑者処遇の基本制度はどのょに変わったのか」、『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13頁。 [13]青山 純「新法における被収容者の不服申立制度」、『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30-31頁。 [14]藤本 哲也「刑事収容施設法の意義と課題」、『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58頁。 [15]青山 純「新法における被収容者の不服申立制度」、『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32頁。 [16]詳見:大橋哲「刑務作業の現狀と課題」、『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22-23頁。 [17]詳見「特集 行刑の現狀と課題——刑事収容施設法施行後の検証」、『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 [18]參閱:「特集 刑事収容施設?被収容者等処遇法の成立と課題」、『刑事ジャ一ナル』2006年5號;「特集 刑事収容施設及び被収容者等の処遇に関する法律」、『警察學論集』59卷9號[2006.9];「特集2:未決拘禁者処遇法の改正」、『ジュリスト』1319號[2006.9.15];「特集 刑事施設の現狀と課題」、『犯罪と非行』155號[2008.2];「特集 施設內処遇から社會內処遇へ」、『刑法雑誌』47卷3號[2008.4];「特集 暴力的性向を有する者の処遇」、 『更生保護』59卷6號[2008.6];「特集 性犯罪者の処遇」、『更生保護』59卷6號[2008.8];「特集 行刑の現狀と課題——刑事収容施設法施行後の検証」、『法律時報』80卷9號[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