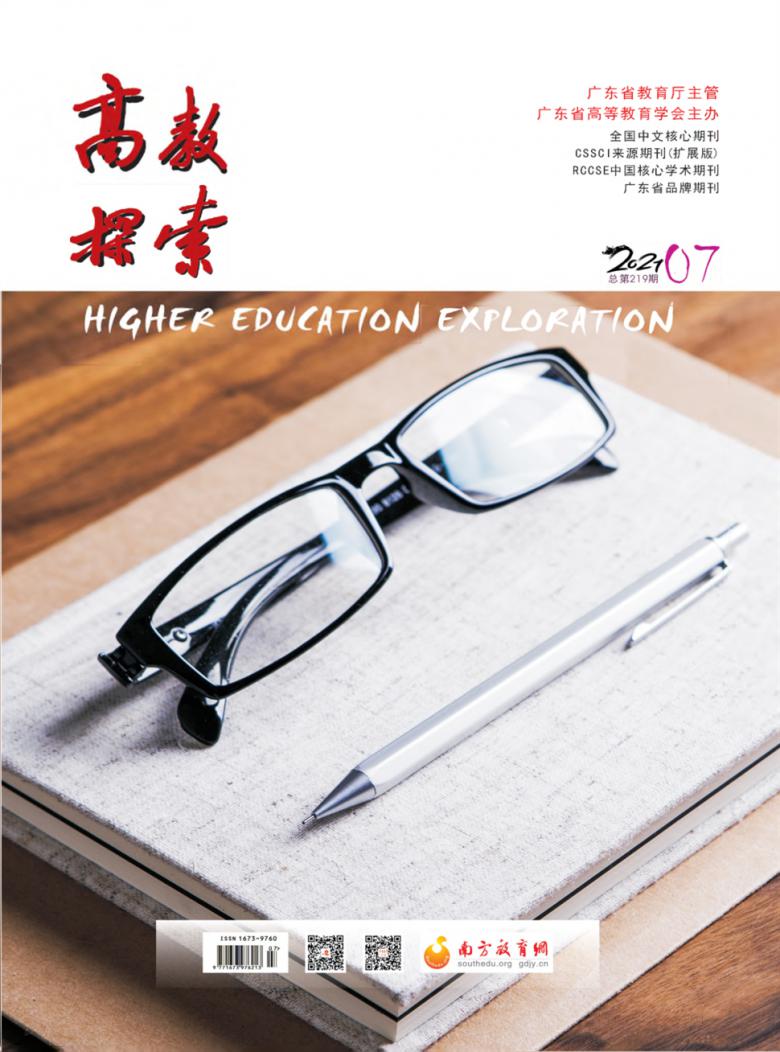《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
郭齊勇
摘要:新出楚簡《恒先》以“恒先”為“道”,討論了“道”“恒”“恒先”的先在性、超越性、終極性,及其與“域”“恒氣”“有”“始”的關系。道之體、道之靜為“恒”“恒先”,道之用、道之動為“域”“恒氣”。元氣是自己生成、自己運動的。《恒先》重點討論了:域→有→性→音→言→名→事的系列,尤其是言名與政事、無事與有事的關系,肯定名的作用。本篇與戰國末年至漢初文獻如《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及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中有關道論的文章及有關審合形名的文章相接近,可會通。作者可能是歸本黃老的道法家或形名學家,或者是“撮名法之要”的黃老道家。作品成書可能早于《淮南子》與《黃帝四經》。
關鍵詞:恒先;域;言;事;道法家;形名思想
我們終于在2004年4月15日始見期盼已久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三冊。其中有一篇令世人矚目的道家文獻----《恒先》,頗有深意,讀起來興味無窮。《恒先》由李零先生精心整理。近日從我校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簡帛研究網站上已見好幾篇討論文章。在此基礎上,我想粗略地談一點體會,就教于方家。
我總的想法是,這是戰國末年至漢初道法家論道的一篇論文,作者以道為背景,用以論政,肯定君道無為,強調審合形(事)名(言)。該篇主旨與《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黃帝四經》(黃老帛書)的有關篇章相接近,特別與其中論道、原道的文字適相會通與補充。
《恒先》全篇共13支簡,保存完好。李零先生的釋文,如把異體字換成通行字、繁體字換成簡體字,這一首尾完具的道家作品全文如下(字間數碼字指竹簡編號)[①]:
恆先無有,質、靜、虛。質大質,靜大靜,虛大虛。自厭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1有作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獨有與也。或,恆焉,生或者同焉。昏昏不寧,求其所生。翼生翼,畏生畏,愇生悲,悲生愇,哀生哀,求欲自復,復3生之生行,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異性,因生其所欲。察察天地,紛紛而4復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復以不廢。知既而荒思不殄。有出于或,性出于有,音出于性,言出于音,名出于5言,事出于名。或非或,無謂或。有非有,無謂有。性非性,無謂性。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詳宜利主,採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為,事庸以不可更也。凡7多採物先者有善,有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于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8有剛。先有圓,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長。天道既載,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恆氣之生,因9言名先者有疑,巟(下加心)言之后者校比焉。舉天下之名虛樹,習以不可改也。舉天下之作強者,果天下10之大作,其 尨不自若作,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舉天下之為也,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為也。11舉天下之性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恒,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恒而果遂。庸或12得之,庸或失之。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與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慮?13
一、“恒先”與“道”的形上、超越、絕對、無限性
本竹書“恆先無有”之“先”字與“無”字字形上有明顯差別。馬王堆《黃帝四經》(又稱《黃老帛書》或《黃帝書》)的原整理者因其中《道原》篇首“恒先之初”的“先”字字形與“無”字相近,以“恒先”為“恒無”,見1980年文物出版社《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陳鼓應先生著《黃帝四經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亦用“恒無之初”。李學勤先生據同一帛書圖版前二行“柔節先定”句,定“恒無之初”為“恒先之初”,并在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之《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公布。在此前后,余明光、魏啟鵬先生等均釋“恒無”為“恒先”。李零在此次竹書《恒先》釋文中,同意李學勤“恒先為道”說,并進而指出“恒先是終極的先”。
本竹書1至3簡與帛書《道原》篇首數句有一定的理論聯系。《道原》篇首:“恒先之初,迥同太虛。虛同為一,恒一而止。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靜不熙。故末有以,萬物莫以。故無有形,大迥無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載。”[②]關于“恒”字,黃老帛書中多見,如恒先、恒一、恒常、恒事、恒位等等。《恒先》與帛書《道原》一開始都講天地未形之前太虛的混混沌沌狀態,“濕濕”即“混混”,兩書均用“夢夢”(即蒙蒙),均有“虛”“靜”的表述。《道原》“迥同太虛,虛同為一”,《恒先》則謂“虛”“虛大虛”。“迥同”是通同,無間隔的狀態。至于“靜”,李零隸定為“寈”,釋為“靜”,李學勤釋為“清”,直接講清、虛、一、大[③]。我以為還是依李零釋“靜”為好。無論是《恒先》所說的未有天地之前的“靜”“靜大靜”“虛靜”“出生虛靜,爲一若寂,夢夢靜同”,還是《道原》“神微周盈,精靜不熙”,都是講天地萬物未形之前的太虛的至靜至寂狀態,也是講終極的“道”體在沒有作用、動作之前(“未有天地,未有作行”)的形態,講“道”的根本特性即是靜止、靜謐。此處“靜”比“清”好。參之通行本《老子》第16章“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與第26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等內容,可知“靜”所反映的是超時空的“道”本體的絕待的與普遍的特性,圓滿自足(“自厭”),無為無言。而《老子》第39章“天得一以清”云云,是講天、地、神、谷、萬物離不開道,“清”只是道下的“天”得“道”之后的狀況。“清”又是“氣”的一個特性。所以,“靜”與“樸”“虛”等價,是直接表述整一未分化的、末動作的、根源性的、超越性的“道”的。這里還有關于“ ”的釋讀。李零指出字形似“樸”,但有區別,不妨釋為“質”。李學勤、廖名春等釋為“樸”[④],李學勤認為可以釋為“全”,“大樸”即是“大全”。方之《老子》第32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之”,第37章“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等,似以釋“樸”為上。首句三個“大”字,李學勤、廖名春釋為“太”,其實不必。此二字可互通,但《老子》凡言“大”字處亦不必改為“太”,如“大道”“大白”“大音”“大象”等,似仍如第25章“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云云。
故首句似應為“恆先無有,樸、靜、虛。樸,大樸;靜,大靜;虛,大虛。”這句話并本體論與宇宙論一起說,是中國特有的“本體--宇宙論”的講法,即現象世界的形而上的根據(就本體言)和根源、動力(就宇畝生成言)是“恒先”即“道”。“道”是“恒常”“恒在”“永恒”的普遍的,是永遠遍在的、與現象界同在的那種存在,同時在邏輯上與時間上都是先在的,故說“恒先”。“恒先無有”句,“無”是動詞。這四個字講“恒先”與“有”的區別。即是說,“恒先”是“無”(名詞),無形無名,是超乎“有”的。“恒先”是世界的本根、本體、本源、總動力,是在邏輯上獨立于、超越于“有”的現象界之上,又在時間上早于有形天地萬象之前的,是產生天地萬象的母體。這種獨立不茍、渾樸、靜謐、虛廓、無所不包的“道”,是樸、靜、虛的極至。與渾樸相對的是明晰與分化,與靜謐相對的是活化與躁動,與無限虛空相對的則是有形有限的雜多、實有。在一定意義上,“道”就是“大樸”、“大靜”、“大虛”,即非分化、非運動、非實有、非有限性的整體。“大樸”等既是道之特性又是道之名相(強為之名)。《恒先》首句偏重于講道的原始性、絕對性、無限性、先在性、超越性、終極性,是最高的哲學抽象,偏重于講道之體。以下第二三句則講道之用。當然體用并不能割裂。
二、“或”(域)范疇及“域”與“恒氣”之自生自作
“或”字全篇有12個:
第1簡兩個:“或作。有或焉有氣”;
第2簡兩個:“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第3簡兩個:“或,恆焉,生或者同焉”;
第5簡一個:“有出于或”;
第6簡三個:“或非或,無謂或”;
第12至13簡兩個:“庸或得之,庸或失之”。
李零先生指出:“‘或’在簡文中是重要術語。它是從‘無’派生,先于‘氣’‘有’的概念,從文義看,似是一種界于純無(道)和實有(氣、有)的‘有’(‘或’可訓‘有’),或潛在的分化趨勢(‘或’有或然之義)。”[⑤]李零謹慎地表達了他的看法,又講氣從“或”生,“或”指將明未明、將生未生的混沌狀態,又講“或”屬于“恒”,創造“或”的力量來自“恒”。廖名春、李學勤、朱淵清、李銳等將“或”釋為“域”。[⑥]廖名春認為,“或”即“域”之本字,即四方上下之“宇”,即空間,即《老子》第25章之“域中有四大”,又說《淮南子 天文》“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相當于《恒先》之“恒先無有”、“域作”、“有域,焉有氣”。
關于第二簡“而未或明、未或滋生”之兩“未或”,我同意廖名春、李銳的看法,看作習語,視為“未有”,此處兩“或”字不是哲學范疇的“域”。至于第12至13簡的兩“或”者,整理者并未視為哲學范疇,亦仍作“或”。
現在看來,可以作為哲學名相“域”的,有第1、3、5、6簡的八個“或”字。我們依次來討論。
第1簡:“自厭不自忍,域作。有域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我認為,“域”是一個“場”或“場有”,不僅是空間,而且是時間。這里說的意思是:“道”自圓自足、不變不動,同時也可以發作、自己運動,“道”之發動即為“域”,亦是“域”之作興。“域”在這里是“不自忍”、初發動的“道”。《老子》第25章講“域中有四大”,作為宇宙的“域”包涵了道、天、地、人。可見,“域”與“道”是可以互換互涵的,“域”是靜止不動的“道”的發動狀態。道之體、道之靜為“道”,道之用、道之動為“域”。有了“域”就有了時間、空間,有了時空就有彌淪無涯的氣充盈其間,有了作為物質與精神之一般的“氣”,就有了作為現象世界的一般之“有”即總有、大有,這就標志著宇宙的開始,有了開始就有了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運動。此即為:
道之用、動(域之作)→域→氣→有→始→……(往復運動)。
第2至3簡:“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獨有與也。域,恆焉,生域者同焉……3”氣是自己生成、自己運動,是本篇最重要的思想。前面說“域作”,上文已解域之作即道之作,當然是道自己內在張力產生的運動,而不是超越上帝等外在力量之推動、使動。這里說的是,氣也是如此,自生自動。氣不是他生的,不是外在力量使然,甚至也不是道(恒)使它生使它動的。“恒氣”,李零說是終極原始之氣,本原之氣,可從。“恒氣”就是“元氣”。在這里,我們要注意本篇前三支簡所說恒先、恒、道、域、恒氣、氣,基本上是等質等價的概念,在一個層次上。域、氣、恒氣,更好地表示出道(特別是道作興時)的場域、場有、微粒、力量、能量、流動、化育的意涵,是這些意涵的抽象。《恒先》其實也是一篇“道原”或“原道”,是對《老子》(特別是通行本第1章等)的闡發,必然涉及“道”的意涵及其表達,道與名的關系。本篇后半段直接說及名與言,其實在一開始就把“道”之別名指示了出來。從體而言,道是“獨”,可稱為“恒”、“恒先”,是靜止的,寂然不動的;從用而言,道作興、運動、實現之狀況,感而遂通,則可稱為“域”、“恒氣”。“域”、“恒氣”、“氣”等則不是“獨”,“不獨,有與也”。它們相伴隨而起,但它們也是“道”,是“道”內在的不同能量相感相動使然,故都是自生的,不是他者使生的。域、元氣是道的別名,是恒常恒在的,亦可稱為恒。故不能說是道、恒產生、化生出域、元氣。要之:
道(道之體、靜)--恒、恒先(圓滿自足,寂然不動)
道(道之用、動)--域、恒氣、元氣(自生自動,感而遂通)
有關5至6簡的四個“域”字,說見下。
三、《恒先》之重心在于審合言事
第5至7簡:“有出于域,性出于有,音出于性,言出于音,名出于5言,事出于名。域非域,無謂域。有非有,無謂有。性非性,無謂性。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詳宜利主,採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7”上文說到道、恒、域、恒氣、元始之氣是同一層次的、同一等級(形而上)的概念,是并列的非從屬的,不存在道使之生的問題;域、恒氣、元氣只是道、恒的別號、別稱。這里講的卻是“某出于某”的系列:
域→有→性→音→言→名→事……
域←有←性←音←言←名←事……
域之后顯然是另一層次(形而下),在這一層次內有從屬、派生的系統,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有”源出于“域”。“有”是萬象大千世界(包括精神、物質、社會等)的抽象一般,并非具體之物。至于以下的性、音、言、名、事則是具體的個別的物事、事體、東西(特別是人)及其屬性或特性、音樂或音聲、言說或理論、名相或稱謂、社會事務的相互關系等。這當是先秦思想家名實關系討論的發展,一方面強調名相、名言、概念的自身同一性(某非某,無謂某),另一方面引伸到社會人事管理上,含有循名責實、各當其位、各守其份的意蘊。這也是孔子以降正名思想之本旨。
《管子》的《九守》篇曰:“修(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于實,實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當。”與老子之“名者實之賓”與上引《九守》“按實而定名”的路數有一點不同,《恒先》在名實相生的基礎上更強調名的規定性及名對實(事)的反作用。
除《九守》與《恒先》一樣有“某生于某”的論式外,郭店楚簡諸篇,特別是《語叢》四篇,有不少“某生某”、“某生于某”的論斷。這里,我只想舉《語叢一》之一例:“有生乎名。”
關于“性出于有”,“性非性,無謂性”。《恒先》在這里指物之性,也特指人的性情,道與人性的關系。相類似并可用來參考的材料,見《淮南子》之《原道》:“……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于道者,返于清靜,究于物者,終于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又說:“嗜欲者,性之累也。”該篇提倡護持、反諸人的清凈本性。《俶真》:“圣人之學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于遼廓,而覺于寂漠也。”《泰族》則主張因人之性予以教化、引導,“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
關于“音出于性”,“音非音,無謂音”。《呂氏春秋》提倡正位審名,并以正音為譬。“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圜道》)該篇進而論證治國立官,各處其職。《淮南子》指出,豐富的樂音源于五音,五音又取決于處于中道之宮音。“有生于無,實出于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原道》)足見道與性、音之關系的討論與名實、名形關系的討論,在當時都很常見,且可以引向政治論說。戰國末期、秦漢之際道法家習慣于這種方式。帛書《經法》之《名理》篇講執道者虛靜公正,“見正道循理,能舉曲直,能舉終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聲,聲實調合,禍災廢立,如影之隨形,如響之隨聲……”帛書統說形名聲號,依此而定位并貫徹始終。
關于“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言非言,無謂言。名非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言、名、事的關系,《韓非子》有一些討論:“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南面》)指言與不言都必承擔責任。“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形名;形名者,言與事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二柄》)“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定法》)受申不害影響,韓非說:“圣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揚權》)又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主道》)。“名”字可以是名詞,指名相,也可以是動名詞,指言語所表達的,其內容指道理或名稱。“形”即表現。在一定場合,“名”就是言,“形”就是事。在另外場合,形名泛指言事。“情”指真實狀況,實情。“參同”“參驗”“參合”指驗證、檢驗、證明,使所表現(形)與所言說(名或言)相符合,或者形名指導社會實踐。言自為名,事自為形,審合形名,結果是名至實歸,名當其實,如此,君主才可能如“道”的品格,無為而治。這是道法家形名思想的要點。《恒先》篇顯然是與這些思想可以相通的。又《呂氏春秋》曰:“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審分》)這都是一樣的主張。當然,在帛書《黃帝四經》中,關于“形名”,不再分開理解為“形”與“名”,而是籠統指事物的表徵,指言事、名號、政治法律制度,其所強調的是“形名”及其作用的重要性。在韓非那里也已有了這種意涵。
關于第6簡“詳宜利主,採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為,事庸以不可更也。”有了以上關于形名思想的討論,這句話就比較好理解了。李零先生的解釋,基本上是準確的。“有事”與“無事”,見上引《韓非子》之《主道》的材料。《恒先》此句意即:詳查審于事,得其所宜,利于主上。“採物”即禮制、政務諸事等,都是有為,作為,乃有事,乃臣道,此與無事之君道不可同日而語。此外,“有事” 即舉名,以名舉而責事。帛書《經法》之《道法》有“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形名聲號矣。”又曰:“凡事無大小,物自為舍。逆順死生,物自為名。名形己定,物自為正。”黃老帛書諸篇有物恒自正、形恒自定、名恒自命,事恒自定自施的思想,《道原》的“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尤為突出。
《恒先》第7簡以下講的天之事、人之事、治亂問題等等。第7至8簡說天之事是自作為的,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人主、明君亦應效法,不可直接挿手具體事務,反而搞亂了政事。此關乎人世之治亂。君道無為無事,臣道有為有事。如《淮南子》的《主術》所說,人主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清靜無為,清明不暗,虛心弱志:“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于己。”(《主術》)關于第8至9簡的“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剛”等,可參《淮南子》:“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原道》)“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臟寧,思慮平……”(《原道》)除《原道》《主術》外,《恒先》與《淮南子》的《精神》《齊俗》亦可相通。
第9簡中“天道既載,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與帛書《十六經》《成法》篇“循名復一”的思想相接近。復一就是復道。
這里順便指出,第10簡“言名先者有疑,巟(下加心)言之后者校比焉”,疑仍是講的審合名形、言事的。“校比”也有審合之意。
第10至13簡,總體意思仍然是以虛御實,以靜制動,以無為統有為,以無事統有事。這里指出,舉天下之事,之作,之為,不要用強力,不要多干預,不主動地改變習俗,不主動去興起、參與什么或廢止、舍棄什么,“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為也”,使萬事萬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司其職,各守其份,自興自舍,自主自為又不相妨礙。第13簡“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更加重名,即在道之下,以名統事,社會政務在名言制度下自然運轉,反而不會紊亂。如此,言名、事務均不可廢,天子、諸侯、士君子各行其道而能相輔相成。這些思想可與黃老帛書會通,但黃老帛書比《恒先》說得更明確,更豐富。
《恒先》與《太一生水》關系不大,《太一生水》主題是宇宙生成的圖式,而《恒先》主要是論述道、名、言、事。當然,《太一生水》后半也涉及道、天、地、名、事等,講天道貴弱。
《恒先》全篇布局與黃老帛書《道原》相似,由恒先、道談起,由道的超越、普遍性、無形無名、獨立不偶,講到其對社會人事的統帥,推崇圣人無欲寧靜的品格,得道之本,抱道執度,握少知多,操正治奇,以一天下。道是人間秩序、人的行為的形上根據。當然,帛書《道原》沒有詳論名言形事等。《恒先》與黃老帛書《經法》中的《名理》、《道法》篇更為接近。帛書的形名思想強調天下事物在名物制度下,自己按本性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恒先》并沒有如《淮南子》與《文子》的《道原》那樣鋪陳,比較古樸;其形名思想也沒有如《黃帝四經》那樣展開,甚至沒有提到“形”字。我揣測,作者可能是歸本黃老的道法家或形名學家,或者是“撮名法之要”的黃老道家,作品成書可能早于《淮南子》與《黃帝四經》。
近讀簡帛網站上龐樸先生的大文[⑦],很受啟發。龐先生在竹簡編聯上有改動,即把第8至9簡排在第1至4簡之后,5至7簡之前。全篇竹簡排序改為:1-4、8-9、5-7、10-13。這種編排,頗費匠心,足資參考。
拙文粗疏,不當之處,敬請各位學者、專家批評指正。
注釋:
[①] 李零:《恒先釋文考釋》,載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87—29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實為2004年4月正式發行)。
[②] 詳見余明光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第203頁,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3月。本文所引《黃帝四經》均據此書。
[③] 李學勤:《楚簡〈恒先〉首章釋義》,見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2004年4月下旬。
[④] 李學勤文見上注。廖名春:《上博藏楚竹書〈恒先〉簡釋》,見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2004年4月下旬。
[⑤] 詳見注1,288—290頁。
[⑥] 李學勤、廖名春文見注3、4。朱淵青:《“域”的形上學意義》,李銳:《〈恒先〉淺釋》,兩文均見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2004年4月下旬。
[⑦] 龐樸:《〈恒先〉試讀》,見簡帛研究網站www.jianbo.org,2004年4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