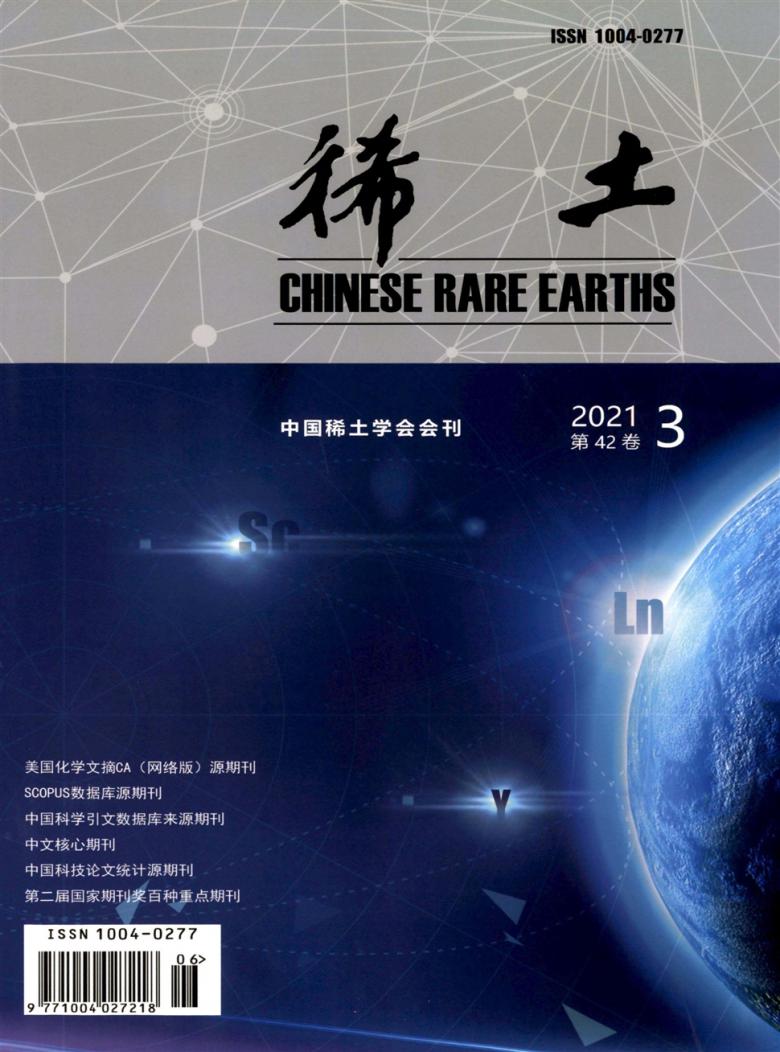教育個人回報率計量研究缺陷及調整方法綜述
佚名
【摘要】對于教育個人回報率的OLS回歸估計結果通常存在“能力偏誤”和“測量偏差”兩種計量研究缺陷。本文總結并詳細討論了國內外學者為克服計量偏誤而采用的各種計量改進手段,主要可以分為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外生制度性變遷尋找工具變量法和運用雙胞胎數據分離能力變量方法三類。最后,作者對于這些精確估計教育個人回報率的計量方法和結論做出了評價。
關鍵詞:教育個人回報率、明瑟模型估計、能力偏誤、測量偏差、工具變量法
中圖分類號: F064.1 文獻標記碼:A
Estimating the private return to schooling: A overview of the econometric methods
Abstract: The ordinary least-squares estimation could not provide an accurate estimate of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because the education on earnings can’t prove causality as well as the reporting error in estimating the years of schooling. This paper overview the key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tackle this problem, which includes controlling the ability directly,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and taking twin data to eliminate the unobservable ability. The author also evaluates the pro and con of these methods and interpret the results.
Key words: Private Return to Education, Mincer Model Estimation, Ability Bias, Measurement Error,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勞動經濟學領域發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論—人力資本理論,該理論認為,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行為,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并為勞動者帶來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發達國家微觀層面數據的大量出現,以及計量經濟-方法的發展,為檢驗人力資本理論提供了便利。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教育確實能夠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當前學者研究的重點是精確測度教育回報率的大小(Card,1999)。
這一實證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對經濟的貢獻、個體教育投資決策行為、不同性別和種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異、教育資源分配等諸多問題,幾乎與勞動、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有密切聯系(邢志杰,2004)。因此,對于教育收益率的計算也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討論對于轉軌國家還具有特殊意義,眾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時間趨勢特征(李實和丁賽,2000;Zhang et.al ,2005),并將教育回報率的變化作為判斷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經濟轉型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賴德勝,2001; 孫志軍,2004)。
教育回報率包含教育個人和社會回報率,雖然一些政策報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慮教育社會回報率,但主流文獻更多討論的是教育個人回報率的問題,因此,本文也研究重點定為教育個人收益率的內容。本領域已經有一些優秀的綜述文獻,國外如(Card,1999),國內如(孫志軍,2004)。本文的特色是從計量研究方法的角度總結研究脈絡,總結并討論國內外學者為克服普通OLS回歸估計可能產生“能力偏誤”和“測量偏差”兩種計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種情境下的工具變量法、運用雙胞胎數據分離能力三類計量調整方法。最后,作者對于這些精確估計的方法和結論做出了評價。
二、明瑟模型的設定和基本結論
學者通常依賴明瑟回歸模型(Mincer,1974)估計教育回報率。該模型在控制個體工作年限、性別、種族、所在區域及行業的影響基礎上,估計教育水平對于收入的貢獻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連續變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學歷啞變量兩種度量方法。運用在校年限進行估計,回歸結果的含義是勞動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該回歸結果簡單且直觀,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資回報呈現邊際遞增或遞減趨勢時,無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對于收入邊際的貢獻。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勞動者的最高學歷作為教育啞變量進行估計,計量結果的含義是,勞動者達到某一學歷水平的額外收入增幅。這種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勞動者達到某一學歷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異,從而計量估計容易引起偏誤。兩種度量方法的估計結果具有不同的意義,多數研究會同時考慮兩種模型設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對于全世界70多個國家的教育回報率進行了估計,帶給讀者對于教育回報率估計值的直觀認識:(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國教育回報率的平均水平為10.1%,亞洲地區非OECD國家為9.6%;按國家的收入水平進行劃分,中高及高收入國家的教育回報率較低,分別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國家的教育回報率達到11.7%和11.2%。 而利用我國80至90年代數據,絕大部分研究顯示教育回報率在6%以下(孫志軍,2004),這大大低于亞洲地區以及同收入檔次國家水平;(2)用最高學歷的啞變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國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分別為29.1%、18.1%和20.3%。亞洲區域內非OECD國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分別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國家的收入水平進行劃分,收入較低的國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較高,橫向比較來看,各國教育投資總體上呈現邊際遞減傾向(Psacharopoulos, 1994)。將這些數據與針對我國80至90年代的研究結果比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亞洲地區以及同收入檔次國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卻較高,如(Li et.al ,2005)估計發現高等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為61.2%,另外,與在其他國家發現的情況正相反,我國教育投資總體呈現邊際遞增趨勢(孫志軍,2004;Li et.al ,2005)。
三、模型估計中的常見問題
從Becker(1964)開始,學者們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計存在著“能力偏誤”(ability bias)問題:教育程度并不是一個外生的客觀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們選擇的結果,顯而易見能力較高的個人學習更輕松,可以理解為他們接受教育的邊際成本較低,因此更容易選擇較高的受教育程度; 另一方面,能力較高的個體也會因為工作能力強而得到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觀測到的,個體的能力是很難衡量和觀測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變量的缺省。在這種情況下, 由于能力較高而帶來的較高收入,就會因為能力變量的缺省和能力與教育水平的正相關,而轉嫁為教育對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說,教育水平較高的個體獲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歸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實際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離均衡模型,則具有諷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無法貢獻于生產力,僅僅是雇主篩選高質量人才的信號時,我們同樣可以觀測到教育程度與收入之間的相關關系。這些模型均是在內生考慮教育程度選擇下,發現明瑟教育收益估計存在偏誤。 (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型之上,構建了內生教育投資模型,本質上也是服務于更好精確的測度“能力偏誤”。從教育投資回報的早期文獻開始,“能力偏誤”一直是該領域中備受關注的研究重點,學者們開發出各種手段解決該問題,權威綜述可見(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計中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被稱為“測量偏差”(measurement error)問題。測度偏差的來源包含以下幾種情況:一些研究用勞動者的最高學歷來推測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樣是高中學歷的勞動者實際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這就造成了測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勞動者的年齡和工作年數來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勞動者入學時間的差異以及失業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測量結果與實際情況也會產生偏差。另外,問卷中直接詢問勞動者受教育年限,調查所得的數據難免與實際數據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從計量經濟學理論不難得知, “能力偏誤”問題會引起估計結果產生正的偏誤,而“測量偏差”問題將引起估計結果產生負的偏誤Griliches(1977)。學者們當前研究的重點是解決各種計量偏誤問題,從而精確測度教育回報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誤問題的主要方法
1. 直接衡量能力
解決能力偏誤問題的一個思路是尋找衡量勞動者能力的變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測試成績作為度量變量。這種方法的最大弱點,是很難找到一個不與教育程度相關的能力測試指標,當控制變量與教育程度存在正相關時,估計結果同樣會存在偏誤。因此,近期文獻很少直接采用該種處理方法。
2.尋找工具變量解決能力偏誤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誤問題,通常的解決辦法是尋找工具變量,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回歸。具體到明瑟模型估計,問題的難點是,如何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工具變量,該變量必須與勞動者的個體收入無關,而與個體的教育程度相關。
2.1利用勞動者家庭成員的教育程度作為工具變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變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為工具變量,這種處理方法背后的假設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與本人教育程度相關,但與其收入無關。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與子女的收入無關,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結論,因此,運用家庭背景情況作為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難以保證(Bound et. al ,1996)。從邏輯上來看,家庭背景情況確實具有潛在影響勞動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將反映家庭背景情況的變量作為收入回歸控制變量是比較合適的。
2.2 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異作為工具變量
為了解決能力內生性問題,學者們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變遷的“自然實驗”方法尋找工具變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為工具變量。兩位學者注意到,在美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學校入學政策,它法定的入學時間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須要在入學時達到六歲,其二是強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學生在年滿16或17歲才能夠離校成為勞動力。結合兩項政策,對于期望離開學校從工的學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學生在較大的年齡入學(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學,其時她已經達到了6.9歲,但因為離校的年齡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學校逗留的時間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時間也就短一點。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數據,發現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時間確實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與人口的能力是不相關的話,出生季度就可以作為一個教育年限的工具變量。作者在控制了種族、出生地區等因素后,分別估計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報率,IV估計結果基本與OLS估計比較接近,表明OLS估計中的能力偏誤問題并不嚴重。該研究由于方法新穎而備受關注,學者們沿此思路開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離校年齡變化的教育制度變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時間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異構建工具變量。英國1947年出臺的教育法案,將最低離校年齡從14歲提升到15歲,1973年,該法案又將最低離校年齡提升到16歲。這就意味著,在英國,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臨14歲的法定最低離校年齡,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臨15歲的法定最低離校年齡,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臨16歲的法定最低離校年齡。作者利用英國男性數據,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IV估計的教育回報率超過15%,遠遠高于OLS估計的6%。
(Meghir&Palme,1999) 同樣利用教育制度變革中法定最低離校年齡的變化,而由于發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漸進的,同一時間內地區之間的改革進程是不同的,學生法定最低離校年齡存在差異,這樣,就可以在相似的經濟環境背景下,運用自治區是否參與教育改革構建工具變量,得以更加精確地估計教育回報率,瑞典在1949年開始啟動教育體制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將最低離校年齡從7或8歲提高到9歲,該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國各個自治市推廣開來。作者就關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參與到教育改革的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親教育變量后,得到的IV估計約為3.6%,而OLS估計約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亞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設計劃的教育制度變革事件。印度尼西亞初等教育建設計劃的目標是在281個區中建立指定數量的初等學校。以計劃新建學校數與適齡初等教育學生的比值作為初等教育建設計劃實施強度的衡量標準,Duflo發現,在實施強度較高的地區即新建學校-學生比例較高的地區,勞動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長比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數據,利用出生年份與各區初等教育建設計劃強度的交叉項工具變量,得到教育回報率OLS估計值為7.8%,意味著在校年限每增長一年,工資平均增長7.8%,而IV估計值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異作為工具變量
(Card,1995) 利用美國青年人口數據,將個人成長地是否相鄰于大學作為工具變量。其背后的邏輯是,若學生成長地與大學并不相鄰,學生就讀大學無法在家中居住,特別是對于比較窮困的家庭,就會潛在提高了教育投資的邊際成本從而減少教育投資縮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數據證明了,相鄰于大學的個人教育年限確實較高,而且地理因素對于貧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影響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鄰大學的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OLS估計結果為7.3%,而IV估計結果為9-19%。值得說明的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學生在教育投資上具有主動權,教育年限體現了學生選擇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資的成本會直接影響到投資的決定,而不似教育資源比較缺乏的發展中國家,比如我國,基本是學校設置門檻選擇學生,首先學生需要入學成績足夠高被大學錄取后,才會有大學投入的成本-收益決策來決定是否去上大學。
利用類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發展中國家的背景下,運用菲律賓農村家庭調查數據,考慮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將個人成長地是否相鄰于高中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他們將個人與最近的高中的距離以及在當地是否存在一個高中的啞變量交叉項作為工具變量,OLS估計結果為5.7%,而IV估計結果為6.4%。
2.4 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異作為工具變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戰爭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尋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戰爭中,大多數美國青年并非自愿參戰,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參戰人員從年滿20歲的青年中根據抽簽選取。每個青年會隨機獲得一個抽簽號碼,幾個月之后,在某個號碼以下的人就會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簽號碼數字較低的人群就會有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辦法延遲逃避服役,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入學。抽簽號碼較低的人群因為預計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較大就會在獲得號碼的幾個月內盡快去注冊入學,這樣就造成了抽簽號碼的大小導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簽號碼與后來的收入水平則不存在關系,因此抽簽號碼可以作為適齡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Angrist&Krueger 獲得教育年限回報率的OLS估計值為5.9%,而IV估計值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事件對于適齡人口教育水平的影響,尋找到了工具變量。利用奧地利和德國兩國男性人口的數據,作者發現兩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顯著影響。這樣,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為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后,針對奧地利的IV估計為9.5%,高于OLS估計的5.2%,針對德國的IV估計為5.9%,高于OLS估計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事件尋找到了工具變量。他們考慮了戰爭對于加拿大英語地區和法語地區退伍軍人的不同影響,他們注意到,世界大戰后,法語地區退伍軍人很少能夠就讀魁北克法語學校,而英語學校卻允許那些甚至沒有完成高中的英語地區退伍兵人就讀大學。因此,戰后法語地區退伍兵人基本沒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語地區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屬于英語地區人口與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項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運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OLS估計為6.2%,而IV估計為7.6%。
2.5 利用家庭性別結構對于教育行為的影響作為工具變量
(Kristion.F.Butcher&Anne Case,1994)利用美國家庭性別結構對于女性教育行為的影響,構建了針對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作者注意到,美國家庭似乎比較重視“獨生女”的教育,如果一個女性在家庭中擁有一個或多個姐妹,其教育程度就會顯著的降低。而對于男性從數據上就沒有表現出這種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數據進行估計,當運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啞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在控制家庭規模影響的基礎上進行估計時, OLS估計為9.1%,而工具變量估計為18.4%。
3.利用雙胞胎數據分離能力因素
勞動者不可觀測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會影響收入,然而,對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雙胞胎來說,他們之間收入的差異就不會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利用雙胞胎數據差分明瑟模型能夠分離能力因素,從而解決能力偏誤問題,這通常被稱為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 model)處理方法。沿著這種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數據分離能力因素,之后學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雙胞胎數據,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難度造成樣本數量較少,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難以保證。隨著數據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較大的雙胞胎樣本量以提高估計的精確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帶來的計量方法創新,使得利用雙胞胎數據的估計得以更加精確。兩位學者從理論上證明了,利用傳統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雖然能夠解決“能力偏誤”,但“測量偏差”的問題卻更加嚴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設計的調查問卷,增加了讓每個雙胞胎報告互報教育年限的一項。一種考慮是,由于互報報告的數據與真實數據相關,而與自己報告的數據偏誤不相關,我們可以用互報教育年限的差作為自報教育年限的工具變量進行回歸。但這種修正方法僅在互報教育年限相比自報教育年限誤更小時,才能夠改進估計的精確度。另一種考慮是,如果某人自報和報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誤差上存在正相關時,可以利用這個特性改進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受到測量誤差的影響應當較小。兩位學者通過數據研究發現,雙胞胎自報和報告別人教育年限的相關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種修正模型比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運用OLS估計結果為8.7%,傳統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的教育回報率為11.2%,而固定效應修正模型估計結果為13.2%。之后的雙胞胎數據研究均將修正的固定效應模型視為理想的估計方法。(Card,1999)在總結幾篇利用雙胞胎數據解決能力偏誤問題的文獻后,總結出普通OLS估計一般會高估10-20%。
五、針對我國教育回報率的精確估計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國家庭重男輕女的特殊社會背景,巧妙地尋找到工具變量。作者認為,在中國社會中,男子承擔照顧父母的重任,而女兒終歸是別人家的人,兒子女兒實際上對于家庭的貢獻相差很大。所以,兒子的存在會造成對于女兒教育的歧視。作者將是否存在親兄弟的啞變量作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對于女性教育回報率的OLS估計為9.8%,而利用工具變量的GMM估計結果為16.9%。
(Meng&Gregory,2007) 和(Gile,Park&Wang,2007) 均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找到適當的工具變量。(Meng&Gregory,2007)發現,發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其不同階段對于不同適齡教育程度的學生入學和教育都產生了明顯影響,但總的來說,1966年到1977年的適齡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顯著得降低了。作者據此找到了兩種工具變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為控制變量。這種方法的問題是,由于各時間段人口的教育環境可能存在系統性差異,不考慮這些差異估計結果就會引起偏誤。另一種做法,由于文化大革命主要對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產生了影響,可以利用農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時間變化趨勢,排除時間趨勢對于第一種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響。但這種方法的主要問題是,農村與城市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存在系統化差異,而且由于農村勞動力市場中高等教育學歷的人口較少,數據方面只允許研究高等教育學歷以下人口的教育回報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種思路設計工具變量,作者運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調查數據(IDS)和中國城調隊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數據,工具變量估計的教育回報率為7.6-7.8%,而OLS估計結果為5.4-5.9%。
(Gile,Park&Wang,2007)從另外的角度,他們發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子女能否獲得教育與父母是否擁有管理職位有很大關系,而與父母的教育程度相關性變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對于政治上存在問題的學生是壁壘。作者首先從數據上驗證了這種說法,并以此事件作為工具變量,運用2001年5個城市的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CULS),發現工具變量估計的教育回報率為7.5-7.7%,而OLS估計為8.3-9.6%。
(Li et.al,2005)進行了運用雙胞胎數據分離能力方法展開了的研究。他們運用OLS估計得到的教育回報率為8.4%,運用雙胞胎組合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教育回報率下降到2.7%,而運用修正的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為3.6-3.8%,但仍與OLS估計有很大差距。這與利用其他國家數據發現的調整能力偏誤后,估計值略微下降的結果頗為不符。另外,OLS方法進行估計,高中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為7-10.5%,大學畢業生的額外收入增幅為61.1-61.3%,職業學校畢業生的額外收入增幅為32.4-34.4%,在工具變量估計中,高中教育的額外收入增幅為3.1%,大學畢業生的額外收入增幅為40%,職業學校畢業生的額外收入增幅為22%,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高等教育回報較高而高中教育較低。李宏彬等人將此現象歸咎于中國考試導向的教育體系:在中國,由于大量的人口準備進入限額的大學,高等教育入學的競爭非常激烈。中國采取的方式是統一入學考試。只有很少的很聰明的學生能夠進入大學。這樣,能力偏誤問題非常嚴重。另外,為了準備大學資格考試,中國的高中教育是考試導向型的,包括學校、教師的激勵都是入學考試成績導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識和工作能力,而學習內容根據大綱而定,學科固定,因此該教育體制只是選擇了更有能力的學生,而不是提供知識和實際工作能力,最終造成高中教育回報率很低,而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回報率較高。
六、精確估計的基本結論及評價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難以奏效,學者們克服偏誤問題的主要方法是雙胞胎分離能力法和工具變量法。
從利用雙胞胎分離能力的處理方法來看,雖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計量方法創新,大大提升了利用雙胞胎數據進行估計的精確度。但無論計量估計手段多么高明,雙胞胎樣本占人口比例過低的事實,使得雙胞胎樣本估計的教育回報率難以具有普遍意義,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學者們難以逾越的。
工具變量法似乎是一個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難以得到精確的估計結果。(Card,1999)在總結了數篇利用工具變量法估計教育回報率研究后,發現工具變量估計通常比OLS估計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變量法主要解決的是能力與教育程度相關性的問題,工具估計應當比OLS估計偏低,那么實際估計結果偏高就比較出乎意料了。總結來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變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個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參軍人員的數量未知,即使編號較高也面臨被抽中的威脅,因此,事實上大部分適齡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來逃避戰爭,由此造成彩票編號與受教育程度之間的相關性很差,這時候利用彩票數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就難以準確,理論計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變量可能會比OLS估計將引起更大的偏誤(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運用教育系統變更的事件,用特定時間段的啞變量作為教育程度的工具變量。由于各時間段間還存在其他影響教育環境的事件,因此各時間段人口的教育環境可能存在系統性差異,不考慮這些事件影響的估計就會引起偏誤。
(2)計量方法不夠考究。(Card,2001)總結了工具變量法在計量方法的上的幾種潛在問題。其一是測量偏差問題。(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認為,雖然工具變量法解決了能力偏誤問題,但如果測量偏差問題的問題非常嚴重,非有效的工具變量可能會放大測量偏差的問題而使得估計結果反而偏小。第二種是模型設定問題。(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發現,在工具變量法估計的模型設定中,學者們通常選擇給出教育回報率最高t檢驗的模型形式。如果這種模型設定的調整對于工具變量估計的精確性影響不大,但對于估計區間產生了很大影響,那么工具變量估計的結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種是估計樣本選擇性偏誤問題。(Card,1995)強調教育回報率在個體間異質性所引發的估計偏誤。根據教育系統變更事件而開發的工具變量,比如建立在強制就學或學生地理位置的工具變量研究,通常對于低教育人群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如果這些人群選擇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為就學的邊際成本較高,而不是邊際收益較低,那么,工具變量估計結果就會高于實際平均邊際教育收益率。
另外,運用工具變量法來進行精確估計,遇到的另一個困境是方法和結論難以推廣。上述工具變量計量研究通常也被稱為“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方法,經濟學家根據特定的經濟背景環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變遷絞盡腦汁找到的工具變量,一般難以推廣到其他國家運用。比如,由于中國教育制度背景與美國迥異,無論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異作為工具變量,還是(Card,1995)將個人成長地是否相鄰于大學作為工具變量,均不適用于中國。然而,中國利用獨特如文化大革命等環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變量,但也難以推廣到其他國家。
[1]. 李實、丁賽(2003):《中國城鎮教育收益率的長期變動趨勢》[J],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2]. 賴德勝(2001):《教育與收人分配》[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3]. 孫志軍(2004):《中國教育個人收益率研究:一個文獻綜述及其政策含義》[J],中國人口科學,2004年第5期
[4]. Angrist. Joshua D. and Alan B. Krueger(1991),“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979-1014
[5]. Angrist. Joshua D. and Alan B. Krueger(1992),“Estimating the payoff to schooling using the Vietnam-Era draft lottery”,NBER Working paper
[6]. Angrist. Joshua D. and Alan B. Krueger(1994),“Estimate of the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for a new sample of twi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1157-73
[7]. Ashenfelter,Orley and Cecilia E.Rouse(1998),“Income, schooling and ability: evidence from a new sample of identical twi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 Ashenfelter, Orley, Colm Harmon and Hessel Oosterbeek(1999),“A review of estimates of the schooling/earnings relationship, with tests of publication bias”,Labor Economics,6, 453-470
[9]. Becker. Gary.S(1964),“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 Bound, John, and David A. Jaeger(1996):“On the Validity of season of Birth as an instrument in wage equations: a comment on Angrist and Krueger’s‘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 ?”,NBER Working paper
[11]. Card, David(1995):“Using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college proximity to estimate the return to schooling,” In L.N. Christofides, E.K. Grant, and R. Swidinsky, editors, Aspects of Labor Market Behaviour: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Vanderkamp.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12]. Card, David(1999):“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ume 3A
[13]. Card, David and Thomas Lemieux(2000):“Dropout and enrollment trends in the post-war period: What went wrong in the 1970s?”Natinan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4]. Duflo, esther(2001),“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 evidence from an unusual policy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795-813.
[15]. Griliches,Zvi(1977),“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some Econometric problems”Econometrica,52,1199-1218
[16]. Hausman, Colm and Ian Walker(1995):“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for the United Kingdo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5,1278-1286
[17]. Ichino, Andrea, and Rudolf Winter-ebmer(1998):“The long-run educational cost of World War Ⅱ:An example of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estimation,”
[18]. John Giles, Albert Park, Meiyan Wang(2007),“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Disruptions to Education,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Working paper
[19]. Kristion.F. Butcher,Anne Case(1994):“The Effect of Sibling Sex Composition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Earning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109, No.3. (Aug, 1994),pp.531-563
[20]. Kling,Jeffrey(1999):“Interpre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es of the return to schooling”Working paper
[21]. Maluccio, John(1998):“Endogenously of schooling in the wage function:evidence from the rural Philippines”
[22]. Psacharopoulos (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325-1343.
[23]. Li, Haizheng; Luo, Yi(2004),“Reporting Errors, 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9: 3,pp. 191–207
[24]. Li,Hongbin,Pak Wai Liu,Ning Ma, Junsen Zhang,“Does Education Pay in Urban China?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working paper
[25]. Lemieux, Thomas, and David Card (2001): “Education, Earnings, and the Canadian ‘G. I. Bill”,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2), 313-344.
[26]. Meghir,Costas and marten Palme(1999):“Assessing the effect of schoolings on earnings using a social experiment, Working paper
[27]. Mincer, Jacob(1974):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8]. Staiger, Douglas and Jame H Stock(1997):“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Econometrica,65,557-586
[29]. Xin Meng, Robert Gregory(2007),“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terrupted education on earnings: the educational c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Working paper
[30]. Zhang, Junsen, Yaohui Zhao, Albert Park and Xiaoqing Song (2005).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88 to 200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730–752
[31].免費免費論文下載中心http://www.100ppa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