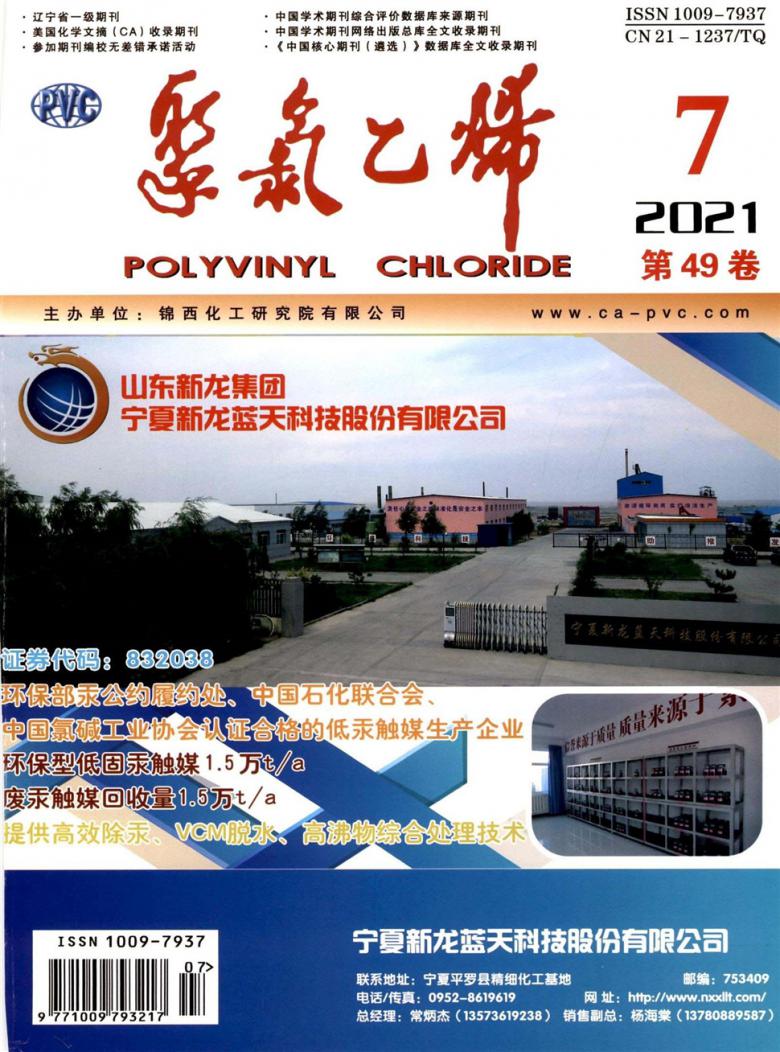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比較
馬宏佳 周志華
摘要:由于文化傳統的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以及意識形態的區別,不同國家研制的科學教育教學策略體現出不同的傾向和特色。對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的比較研究將更好地促進科學教育的發展。基于有限案例的研究表明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存在三方面主要差異: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在教學內容載體選擇上明顯不同;價值取向上差異顯著;研發方式與途徑風格迥異。
關鍵詞: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比較研究
一、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的界定
科學教育教學策略(science education strategy)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頻繁出現于西方科學教育研究文獻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漸成研究熱點。這里的“科學教育”通常指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學科,這幾門學科的共同特點是:研究對象是客觀世界、研究方法體現實證特征。
“教學策略”的定義比較復雜,不同的研究者對“教學策略”有不同的定義。邵瑞珍主編的《教育心理學》一書對教學策略的定義是:“教學策略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達到一定的教學目標而采取的相對系統的行為。”李曉文等認為:教學策略具有動態的教學活動緯度和靜態的內容構成緯度。[1]較早研究課堂教學策略的美國學者埃金等人認為,教學策略就是“根據教學任務的特點選擇適當的方法”。[2]
一般而言,我國學者傾向于認為:策略是比方法更上位的概念,策略比方法更高遠一些、更抽象、更概括些。策略既有技能特性又有系統特性,因而具有普遍意義。而西方學者則常將教學策略看做具體的教學方法。不過,他們通常在特定的教育理念和教學環境中談教學策略。如Borich著、易東平譯的《有效教學方法》(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一書中,有專章介紹“直接教學策略”“間接教學策略”“提問策略”等非常具體的教學方法。新西蘭配合1—9年級《科學》的教學編制的“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中,詳細介紹了許多具體教學方法,且都冠名以“某某策略”,如“郵箱策略”“毛線團策略”等。
鑒于以上分析,本文將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暫時界定為:“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導下的科學教育具體教學方法及應用。”
二、關于科學教育的共識
在近期的世界科學教育發展中,已經基本確立了一些共識,它們是中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不約而同提倡的。[3,4]其核心內容包括以下幾點。
●科學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科學素養不僅包括科學知識與技能,還包括科學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科學是面向所有學生的。科學課程應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注意知識技能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的運用,重視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科學課程要反映作為當代科學實踐之特點的理性傳統與文化傳統。
●科學學習是一種能動的過程。學習科學是學生親自動手而不是別人做給他們看的事情。科學探究是學習科學的重要途徑,也是學習科學的重要內容。
這些關于科學教育的共識構建起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比較的前提和基礎。對科學教育目的、內容和途徑之認識的一致性,使得各國在設計和運用科學教育教學策略中有了許多共同的追求;不同的人文、地域和歷史背景又賦予各國的科學教育教學策略鮮明的特色,使比較成為可能。
三、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比較
(一)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在教學內容載體選擇上明顯不同
教學策略設計要選擇適當的教學內容作為載體,有些教學內容的學習和傳授需要特殊的教學策略。中外教學策略設計所選擇的學科內容載體明顯不同。我們先看以下兩個案例。
案例1 哪種炸薯片含有的熱量更多
這是新西蘭科學教師Azra在中國為某高師課程與教學論(化學、物理)研究生演示的一個教學片段。教師給出兩種不同品牌的炸薯片,要求學生通過實驗判斷它們中哪一種含有的熱量更多?在讓學生討論各種可能的方案后,演示了其中的一個方案:用回形針將薯片固定在軟木塞上,點燃薯片,用薯片燃燒產生的熱量加熱盛有50 mL水的大試管,根據試管中水溫上升的多少比較薯片含有熱量的多少。
然后,討論上述實驗是否“fair”。盡管“fair”一詞的本意是“公平的”,但觀看Azra演示的中國的這些未來的科學教師顯然認為這個實驗不夠科學,他們在發言中將自己所認為的此實驗的所有不合理之處都講了出來:
① 兩薯片的厚薄、大小可能不同。
② 兩薯片的質量可能不同。
③ 兩薯片燃燒的完全程度可能不同。
④ 加熱水時熱量的散失多少可能不同(火苗的穩定性不一樣)。
⑤ 兩只被加熱的試管管壁厚薄可能不同。
⑥ 如果將薯片弄得更碎,甚至變成粉末,燃燒會更充分,結果會與燃燒整個薯片不同。
⑦ 食物含有的熱量是在體內消化時釋放出來的,用燃燒的方法所得結果是否代表食物含有的熱量,值得懷疑,等等。
Azra肯定了聽眾的質疑,并自然地過渡到下一個問題:“在這個實驗中,我們需要保持哪些量不變?”以及更進一步的問題:“如果全班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都做上述實驗,還可得出不同的結果,怎樣看待這種不同,它為什么會產生?應該如何處理?如果將各組測得的水溫上升值平均后再代入公式算薯片的能量是否比依據單獨的一組數據算更準確?”
案例2怎樣形成噴泉
這是我國某中學化學教師的一個教學片段。她首先演示了如圖1所示的氨氣溶于水的“噴泉實驗”。先將膠頭滴管中的水擠一點進入燒瓶,燒瓶中就會因為氨氣的大量溶解而形成負壓,導致燒杯中的水進入燒瓶,形成噴泉。然后教師給出了圖2所示的裝置,要求學生討論怎樣利用此裝置產生噴泉。
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實錄如下。
學生1:可以用嘴向下面錐形瓶中吹氣。
教師:吹的目的是想增大錐形瓶中的壓強,是吧?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增大下面的壓強?想一想。吹氣的話,這個氣壓還是有限度的,能不能采用其他方法,作為化學實驗這種方法(用嘴吹)不太妥當,是不是?
學生2:可以通過加熱錐形瓶的方法。
教師:很好。加熱錐形瓶,就會使下面的壓強增大,那么液體就由下往上噴。剛才這位同學提出的方法是通過加熱來增大下面的壓強,那么我們能不能從上面著手呢?想一想。
學生3:可以通過用冷水澆在上面的圓底燒瓶上,形成內外壓強差。
教師:可以通過用冷水澆在上面,形成內外壓強差。我覺得還可以換一種方法,例如用冷的毛巾來敷,這樣就會使上面的壓強減小,從而形成噴泉,非常好。剛才同學們是設法增大下面的壓強或者減小上面的壓強,我們能不能通過增大上面的壓強來形成噴泉呢?大家考慮一下,如果上面的壓強增大了,就會出現什么現象?氨就會怎么樣?會沿著導管進入下面的水中。是不是能引發噴泉?好,也可以。那怎樣去增大上面的壓強呢?同學剛才說用冷毛巾敷,那現在怎么辦?對,用熱毛巾敷,這樣就可以增大上面的壓強了,同樣可以引發噴泉。
上例中新西蘭教師選擇的作為教學策略載體的教學內容與生活關系密切,更注意科學過程、方法的引導,且對所討論的內容在原理上作了適當的近似處理和簡化;中國教師選擇的教學內容是重點學科知識,邏輯推理嚴密,但在生活中不常見,有點像實驗室中的智力游戲。
這種差異在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研發中普遍存在,相關的例證還有很多。比如測定香煙煙霧中的有毒物質、用紙上層析法鑒別支票簽字的真偽、比較電池的性價比、比較不同洗滌劑的去污能力和毒性等,是常見的國外教學策略設計的載體。而我國設計的教學策略則更注重教學難點和重點的突破,如讓學生通過實驗探究原電池形成的條件、用實驗探究外界條件對化學反應速度的影響、推測和想象CH4分子的空間構型、探究利用“守恒法”“十字相乘法”解題的規律等。
教學策略研發在教學內容載體選擇上的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基礎科學教育傳統的不同。較長時期以來,我國的科學教育以傳授科學知識為主要目標,加之激烈的升學競爭,教師自然比較注重如何更有效地傳授知識。一些西方國家比較早地注意到科學內涵的豐富性和科學教育的人文性,認為“科學不僅是需要學習的一堆知識,同時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或方法”[5]“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去領略一番因領悟和探明自然界的事理而可能產生的那種興奮之情和自我滿足感。”[3](1)因而,在設計教學策略時比較注意選擇過程性的和與生產、生活密切聯系的內容作為載體。另一個重要認識差異還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例通常是復雜的、受多種因素影響的,而我國科學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視知識的邏輯關系和推理的嚴密性,由于擔心出現科學性錯誤而不敢也不善于將日常生活中復雜的科學問題簡單化、將結構嚴謹的知識趣味化。比如,有一種國外初中科學教材在介紹鹽的性質時,設計了不用冰箱制造冰激凌的活動。在我國大多數教師看來,其中涉及“鹽使水的凝固點降低”的知識,是超過教學要求的,因此,大多數教師可能就不能接受,更不會設計類似活動。
也許對教學策略研發在教學內容載體選擇上比較理智的認識應該是:傳授知識和體驗過程、方法都需要精心設計教學策略。做關于過程和方法教學的策略設計時,要允許或應該在原理上做適當的簡化和近似處理,以突出過程和方法的本質特征。做關于知識內容教學策略設計時,要努力尋找生產、生活的實際情境,以體現科學知識的真正價值。
(二)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在價值取向上差異顯著
教學策略研發的價值取向反映了設計者對“教什么最有價值”問題的思考和判斷。有限的教學時間用在哪里?策略實施的預期是什么?這些方面中外教學策略也有較大的不同,請看以下兩個案例。
案例3 關于地圖的學習
“關于地圖的學習”是美國科學教材FOSS ①設計的一個完整的單元教學策略。學習約持續3個月。從畫山的等高線開始,學生得到一座泡沫塑料制的大山模型,山被平行的切成6層,每層1 cm厚。教師要求學生保持山的中心位置固定,用筆沿著每一層的邊緣移動,將每一層的邊緣線畫在紙上。當6層的邊緣都畫出來后,紙上出現了由等高線構成的山的地圖。再對照山的模型和等高線圖,教師引導學生發現等高線的意義、等高線疏密的意義、等高線區間的意義等。
接下來畫山的輪廓圖并與此山的風景照片對照。然后教師拿出該山區真正的地圖。讓學生尋找南北方向、研究地圖上的顏色(應該能找到五種顏色:藍色、褐色、綠色、黑色和紅色,分別代表湖泊、陸地、植被、建筑和公路信息或測量信息)、研究地圖上的符號(交叉的箭頭表示采石場、虛線表示四輪車道、雙虛線表示沒有改造的公路、周邊有一條曲線的小藍圓圈表示噴泉、旁邊寫有數字的×或△表示海拔、黑色實方塊表示建筑物等)、觀察等高線和等高區間、確定該山的海拔、根據描述在地圖上找到相應的路線(如從海拔為10 800英尺和11 200英尺之間的一個小冰川出發,開始向西南方向走到最近的瀑布,它位于10 400英尺的地方。然后又向西走,到達一個小湖)、根據地圖提出到一個神秘地方的路線等。
案例4設計對比實驗證明乙醇能使蛋白質變性
這也是我國某中學化學教師的一個教學片段。乙醇使蛋白質變性是乙醇用做消毒劑的化學原理。教師要求學生利用雞蛋清、無水乙醇、蒸餾水、淀粉、淀粉酶、碘水等試劑設計對比實驗,證明乙醇可使蛋白質變性。
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實驗,要用乙醇讓淀粉酶這種蛋白質變性,失去對淀粉水解的催化作用,來說明乙醇能使蛋白質變性。淀粉酶催化作用的失去可通過淀粉遇碘水變藍的實驗現象來表征。實際施教時,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出如下的一種可能的實驗設計。
(1)向7 mL淀粉溶液中加入碘水6滴,分成甲、乙兩等份;
(2)向甲中加入淀粉酶的水溶液5滴,乙中加入淀粉酶乙醇溶液5滴;
(3)同時水浴加熱半分鐘;
(4)同時冷水浴冷卻,觀察現象。
實驗結果應該是甲中的藍色褪去(淀粉酶使淀粉水解了),乙中藍色不褪去(淀粉酶在乙醇作用下變性,失去了使淀粉水解的作用)。
然后是學生的實驗和觀察。實驗現象是明顯的。整個活動用時約12分。
筆者認為,這兩個案例很典型地反映出教學策略設計價值取向的不同。美國學者認為,使用地圖是基本科學素養的要求,因而投入相當長的教學時間(大約半個學期的地理課),精心設計教學策略,以教會學生認識、理解、使用地圖為目的。整個過程的教學策略是從模型開始,經歷一系列的動手活動:測量、繪圖、比較山的地圖和真山照片、認識地圖上的各種符號、根據要求在地圖上標出相應的路線等。將非常抽象的等高線、等高區間等概念經由學生親自動手畫,再反復觀察、辨認、應用、比較,變得具體而生動;從模型、草圖、風景照片到真實地圖,要求步步提高;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最后達到使學生會讀、看懂、能使用真正地圖的目的。中國教師意識到要讓學生有科學探究活動的訓練和體驗,精心設計了上述很有創新性的探究課題,但給學生開展探究活動的時間卻只有12分,學生沒有充分的時間討論原理、設計實驗,教師稍加引導便給出了實驗方案,目的是留出時間讓學生做相關實驗和完成本節課的其他教學任務。原本非常好的探究活動令人惋惜地異化為“照方抓藥”的簡單操作。如果讓學生自己設計、實施實驗方案,讓他們犯那些可能的錯、上那些難免的當:比如沒有對照實驗、對照組溶液的量、濃度等與實驗組不一致等。可能更有利于學生在犯錯、改錯、預測、檢驗、反思、討論中獲得探究的體驗,學到科學的真諦。但若要做到這些,可能至少要1節課甚至更多的時間。
教學策略研發價值取向的不同產生于不同的知識價值觀。盡管笛卡兒在1637年發表的《方法論》中就已指出最有價值的知識是科學研究方法的知識,斯賓塞在1861年寫的《教育論》中也強調:學習實驗科學和訓練科學的實證精神最有價值,[6]人們還是很難超越“知識就是事實、概念、原理、定律”的認識。中外的科學教育都存在這樣的現象,但近期國外改變的速度似乎更快一些。
我國科學教育的傳統觀念通常認為,保持課堂教學內容的高密度是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關鍵之一,如果教師在課堂上讓學生活動多而自己講的少,就會有不負責任的嫌疑。例如,我國的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要遠遠長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中學生在校學習時間。我國有些學校一天9節課,寒暑假還要補課。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的中小學生通常早晨9點到校,下午3點放學,若3點后教師要將學生留在學校必須得到校長批準。但我國教師在設計教學策略時,卻不太舍得讓學生在探究性、自主性學習中花太多的時間,就如上例所示。有些很好的教學策略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保障而得不到應有的效益,有時便落入為探究而探究或探而不究的俗套。不讓學生從事探究活動就如同不讓學生下水,又怎么能奢望他們學會游泳、學會探究呢?在教學中讓學生高質量地“動”起來,教師要做的事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教學中教師講的少了,也不等于學生學的少了;因為學生需要在探究的過程中學習探究,在感受科學的同時學習科學,這無疑需要教師有更高的水平,更好地設計和運用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設計的價值取向的不同和變化啟示我們,應該將有限的教學時間用于讓學生做最有價值的事情。教學策略實施的預期目的應該是讓學生實現最充分的發展,因此,在課堂的教師講授時間和學生活動時間上必須有所取舍;在傳授知識、發展能力和形成正確觀念上必須尋求平衡。
(三)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的研發方式與途徑風格迥異
中外都研究和開發科學教育教學策略,但研發方式和途徑卻風格迥異,各有所重。總體上說,國外的研發表現出團隊運作、系統性強和注重理論指導的風格;而我國的研發則體現出個體鉆研、經驗性強和注重與學科內容密切聯系,思維強度高的特色。
在美國,有若干研究教學策略的團體,他們通常以大學的某研究中心為核心,聯合中學有經驗的教師并爭取國家基金和社會力量的資助。他們將教學策略研發與教材編寫同時開展,在編寫和改進教材的同時研究開發相應的教學策略,使得教材推廣的過程成為新教學策略應用的過程,二者相得益彰。如:美國科學教材FOSS及其一整套教學策略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研究中心經歷25年不懈研究的成果。另一套美國科學教材STC/MS(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cepts for Middle School)的研發與FOSS相似,而且,STC/MS教材中3/5以上篇幅的內容是學生的探究活動,學生通過完成一個一個的探究活動來學習科學。這些活動中的每一個都經過學生的試做和教師的改進。教材本身就是個由許多小的教學策略有機組合的系統的教學策略設計。由于是團體運作,又持續多年,并有經費支持,他們所研究開發的科學教育教學策略往往涵蓋某一學科或某一課程的全部內容,而不僅僅是某些教學片斷。
另一方面,國外研發教學策略比較注重理論的指導。除了建構主義等學習理論之外,還將腦科學等探討人類學習的理論應用于指導教學策略的研發,將腦科學和心理學的一些實證研究方法應用于教學研究。如FOSS的主編Laurence Lowery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曾在中國以“人是如何學習的:腦的研究”“腦發展的研究”“繼續發展研究”作過專題報告。他了解典型的探測腦信息加工過程的技術,如:EEG(腦電圖)、MEG(腦磁波)、MRI(核磁共振成像)和PET(正電子X射線斷層攝影)等。在報告中,他出示了一張照片,顯示一個小女孩在看到一個小動物和看到并用手觸摸到小動物時的兩張PET圖。他用“exploding”這個詞來表示腦某一區域血流量突然增大的現象,并解釋說:“PET圖顯示小女孩的手觸摸到小動物之后,她腦中前部的血流量突然增大,說明此時大腦接受到一個強烈的刺激。更多的研究表明,腦細胞的任何區域都不會儲存圖像。腦,既不像照相機那樣記錄圖像,也不像錄音機那樣記錄聲音。腦將一個事物或事件分成許多部分,儲存在腦的不同區域。形狀儲存在一個地方,顏色儲存在另一個地方,運動、順序、情緒、狀態也分別儲存。這一分解策略的優點在于,一個腦細胞可以被激活多次來識別相似的因子。腦的內部只有無數不斷變化的聯結模式。當受到刺激時,已構建的聯結會將各個部分組合成一個整體(一個概念、事件、物體等)。組合的質量取決于原始輸入的質量。這就是我們提倡‘learning science by doing science(通過做科學來學科學)’的理論依據之一。讓大腦能獲得豐富的、高質量的原始輸入信息。”在國外,有一批具有高學歷和高職稱的博士、教授等熱衷于基礎教育教學策略的研發,因此,其研發相對而言更注重理論的指導。
我國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的研發在現階段主要還是許多教師的個體行為,這些教師大多直接從事教學工作,他們的研究往往更依賴于個人經驗,并以部分教學內容和片斷的教學策略研發為主。例如,2001、2002、2003三年中,在《課程·教材·教法》上發表的、內容涉及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的文章分別為27、23、27篇,分別占當年該刊總文章量的12.6%、9.5%和13.4%。均為個人署名,其中的絕大部分是個體研究成果,涉及小組探究、問題解決、課堂提問、閱讀教學、研究性學習、合作學習、案例教學等方面。我國教師個體進行的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研發亦不乏高水平的成果。如,南京某中學教師利用STELLA軟件研制了系統思考教學策略,其相關論文曾被美國2003年系統科學學會年會接受,并應邀赴美做年會分主題報告。但可能是因為許多科學教育研究者正承擔著繁重的教材編寫工作,也可能對教學策略研發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充分,我國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研發還缺乏團體的、有戰斗力的隊伍,因而不易產生系統的、有廣泛影響力的成果。
我國科學教育教學策略研究的另一特點是注重與學科內容的聯系,有較高的思維強度。如就化學學科而言,重點學科知識:電解質溶液、氧化還原反應、未知物性質和結構推導等是教學策略設計時被頻繁涉及的主題。探究活動中問題設計、過程要求通常有較高的思維挑戰性。圖 3如,在講解微粒運動時,我國某教材設計了如下教學策略:首先,學生看到圖3裝置中A燒杯的溶液片刻后由無色變為紅色。然后,要學生對上述變化作出解釋,并設計實驗驗證自己的解釋。顯然,這對學生的思維要求是相當高的。實踐證明,在科學學習中,當學生面臨具有挑戰性的、通過努力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時,即處于最近發展區,是最佳學習情境之一。我國有注重學科知識傳授和思維能力培養的傳統,這種傳統也自然成為教學策略設計的特色,這是值得保持和發揚的。
綜上所述,中外科學教育教學策略有許多共同之處,更有許多不同特色。若能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定會相得益彰,使科學教育水平更加提高,使學生的科學素養得到更好的發展。
①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Full Option Science System.Delta Education.
參考文獻:
[1]李曉文,王瑩.教學策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埃金,等.課堂教學策略[M].王維誠,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0.
[3]〔美〕國家研究理事會.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M].戢守志,等,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化學課程標準(實驗稿)[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5]Center for Science,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nquiry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A Guid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M].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0.
[6]周天澤,胡定熙.化學和科學精神的弘揚[J].化學教育,2004,(2):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