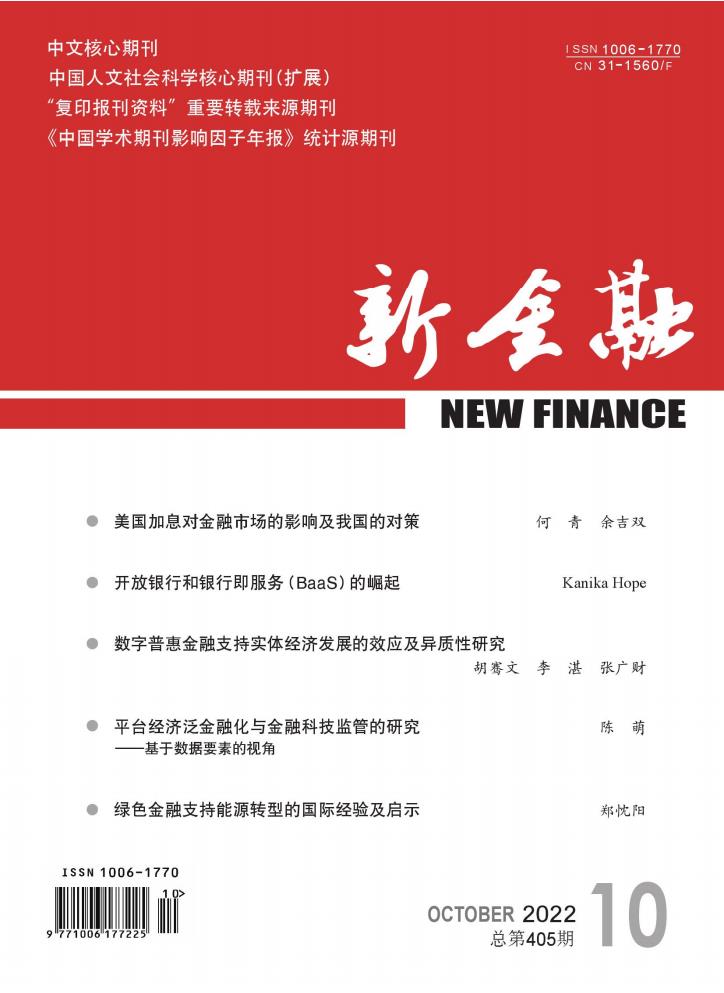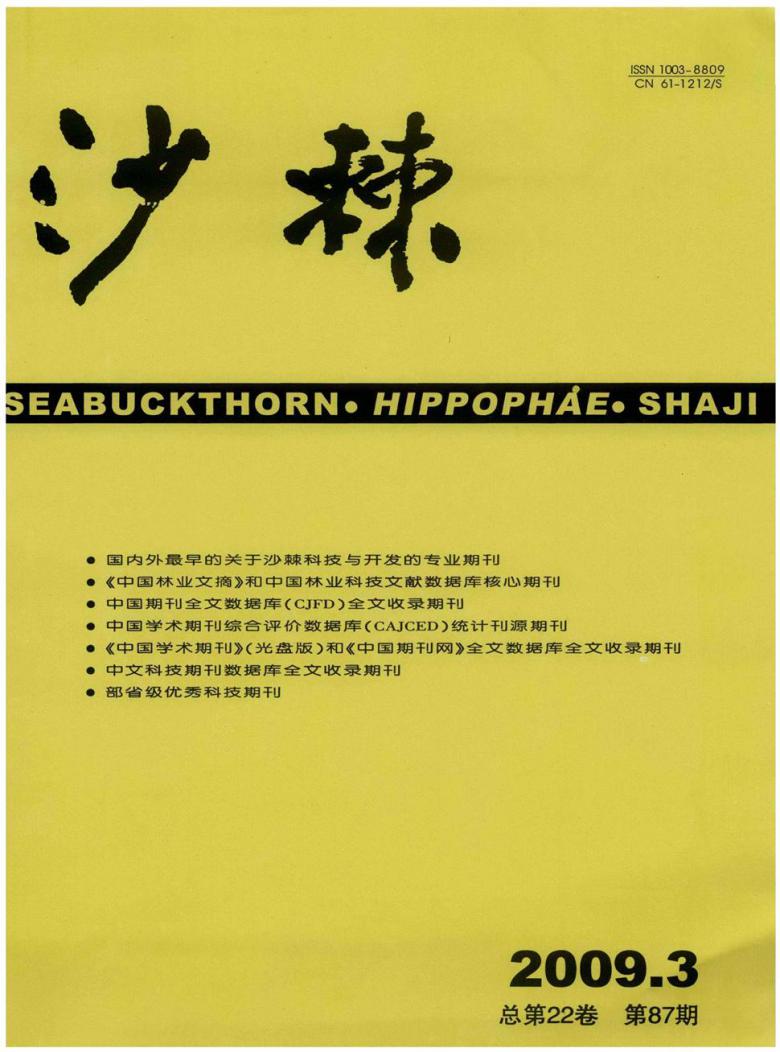佛教文化
關于“蒙古化”的藏傳佛教文化
〔摘要〕16世紀末17世紀初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后,取代薩滿教成為這一地區的主流信仰,藏傳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對蒙古地區影響深遠。〔關鍵詞〕藏傳;佛教;“蒙古化”。16世紀末17世紀初藏傳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以前,傳統的薩滿教文化駕馭著蒙古族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蒙古人中的少數“榜式”(教師)以私塾的形式在民間教書,且沒有任何專門的文化教育場所。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傳播和普及,藏傳佛教已經成為蒙古民族供奉的唯一的宗教,并在清朝的尊崇和扶植下,蒙古王公貴族和廣大蒙民篤信藏傳佛教的程度比藏族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清一代,藏傳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佛教的教義經典成為人們處理一切事情的準則。“人生六七歲即令習喇嘛字誦喇嘛經”。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祭祀祖宗或天地均離不開喇嘛。喇嘛集智慧、學問、美德于一身,是社會上深受敬仰的人們。“男女咸欽是喇嘛,恪恭五體拜袈裟”。從上層王公貴族到下層普通牧民,男子均以出家為榮。“男三者一人為僧”。所以,藏傳佛教作為蒙古多種文
試論“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從《受戒》看汪曾棋的佛教文化意識
論文關鍵詞:汪曾棋《受戒》佛教文化人性歡樂論文摘要:和尚戀愛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是一個禁區.汪曾棋的《受戒》卻將宗教與愛情,佛性與人性和諧地融為一體.《受戒》消解了佛教作為信仰的嚴肅性,漠視佛教的清規戒律,張揚人性,倡揚人們充分地享受生活,回到“人間佛教”中,構建了一個“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美好世界。這是《受戒》中體現的佛教文化意識,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儒道佛教精神共同構成的藝術化的人生.汪曾棋的代表作《受戒》發表于1980年們匕京文藝》,講述了一個小和尚明海和農家少女小英子的純真戀情,概而言之,就是和尚戀愛的故事。和尚戀愛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是一個禁區,有違教義,作家往往避開或者持一種貶斥的態度。在佛教教義中,現實的人生是一片苦海,“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有的只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僧會苦、求不得苦以及五陰盛苦。造成諸苦的原因在于“無明”(愚迷暗昧,不明佛理)和“渴愛”所引起的貪和欲,從而導致生死輪回。因此就要念經、修行、持戒、徹底斷滅人在世俗中的欲望,達到無苦“涅架”的境界。顯然,佛教是主張克制、壓抑、甚至消
基于SWOT的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發展對策分析
摘要:天臺山位于浙江中東部的天臺縣境內,佛教文化旅游資源豐富,經過多年的開發和建設,目前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業已開始步入蓬勃發展的階段。文章采用SWOT分析法,對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發展的優勢、劣勢、機遇和風險進行了綜合分析,提出了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開發的發展對策。從而為合理開發利用旅游資源提供服務,發揮旅游資源的最大優勢,促進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關鍵詞: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SWOT分析;發展對策佛教是人類文化的源泉之一,對人類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佛教文化與旅游結緣己久,以佛教為目的旅游活動,古己有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和國內旅游的興起,我國佛教文化旅游得到迅速發展。并且隨著旅游的大眾化發展,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天臺山,位于浙江中東部的天臺縣境內,素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聞名于世,它以濃厚的宗教特色和優美的自然環境,吸引了國內外的佛教信徒和眾多游客,成為我國重要的佛教旅游勝地。一、天臺山佛教文化旅游SWOT分析SWOT分析是廣為應用的一種機會—風險分析方法。SW是指內
佛教文化對包公文學的影響
摘要:明清時期,佛教教義逐漸深入中國社會底層,成為公眾的倫理規范。受其影響,小說、戲劇中的包公形象塑造明顯地打上了佛教的痕跡。首先,包公被塑造成佛教的“閻羅王”最為流行。其次,受佛教倫理的“因果律”的影響,包公故事里存在大量關于“報應”的敘事,而且很多作品往往伴有相應的道德“勸誡”意圖。佛教因果報應說強調善得善報,惡得惡報,來世的命運由今世的善惡行為決定,這就結合人們的性命大事、切身利益,引導人們去惡從善,從而推動人們的道德意識的自覺和個人修養的完善。受佛教拯救故事的影響,包公故事有了游歷冥府的故事。無論是游歷冥府所見各種陰森恐怖的“果報”,還是親見閻羅王冥府判案,其實質都暗含著“天理昭彰”的內容,只是地獄審判和佛教的修行觀、儒家的天命觀相聯系,更能表現出正義的超驗屬性。關鍵詞:佛教文化;明清戲劇;明清小說;包公文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到“六朝之鬼神志怪書”曾謂:“會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后來講到宋話本、人情小說等多次談到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明清時
從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看中國道教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的對話
人類因民族、地域、經濟、政治等的不同而有了文化的差異,并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文化體系。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交往既促進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發展,又在相互的對話中實現著相互的融合與進步,并時還常常激發出種種新型的文化形態,從而不斷豐富人類的文化寶庫。歷史上,文化對話保持了不同文化體系的持久生命力,今天,文化對話則成為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繼續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前提。不善于對話的文化將是沒有生命力的文化,拒絕對話的文化則更是充滿自我毀滅危機的文化。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是東方最有影響的兩種文化體系,兩千多年以來兩種文化始終存在著密切的對話與交流。正像這兩種文化體系是由許多不同的領域構成的一樣,它們之間的對話也表現在宗教、哲學、藝術、文學、民俗、倫理等許多不同的方面。特別是宗教文化方面,中印兩種文化體系在中國進行了長期的對話,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還從許多方面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固有的文化。本文則以中國民間觀音信仰這種重要而普遍的文化現象為例,說明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道教文化的對話及其深遠影響。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的研究始終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更沒有人從中印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