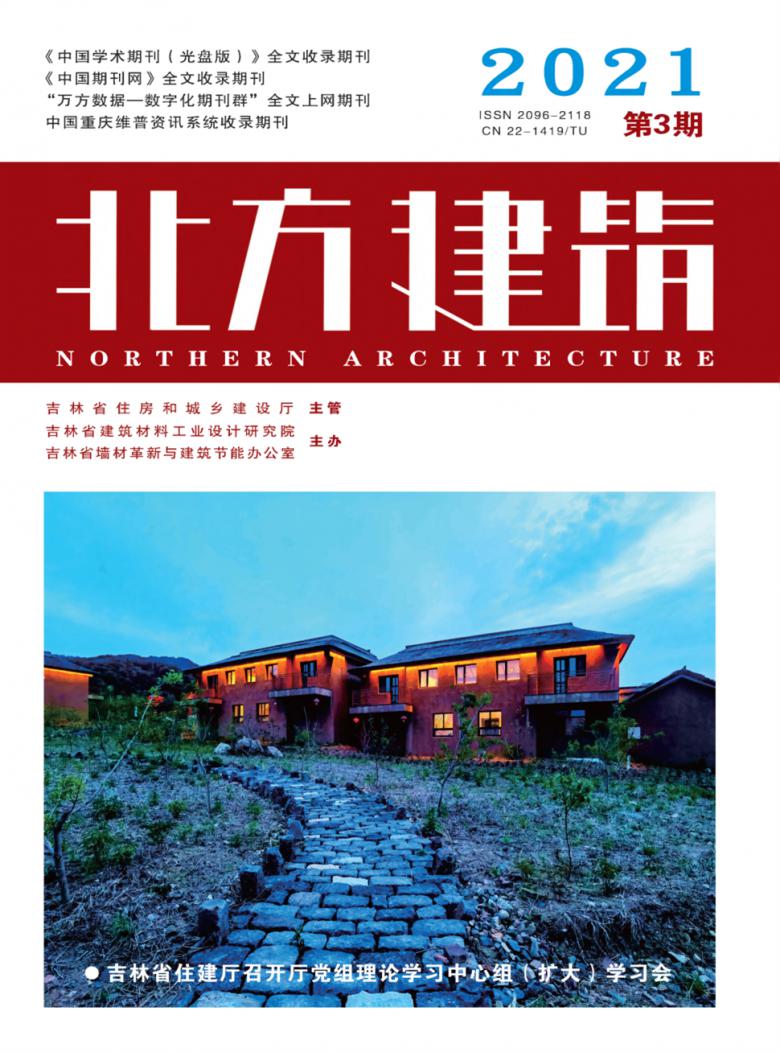明清之際松江幾社的文學命運與文學史意義
朱麗霞
【內容提要】 在文學和史學的研究視野中,晚明復社一直是研究者持續關注的焦點,并將與之同時誕生的許多其他文學社團湮沒了。事實上,明清之際與復社大致同時的松江幾社,無論其成立及活動時間、成員構成、文學思想還是文學創作、文學史地位等諸方面均獨立于復社之外,它以迥異于復社的存在方式、生存特征、學術背景和文學史影響,體現出晚明文人社團豐富的精神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松江幾社不僅是與復社并駕齊驅的文人團體,而且是較復社具有更長久的生命活力和進取精神的文學社團。
近年來,關于文人結社的問題日益成為晚明文學研究一大學術熱點,而且多聚焦于晚明復社。由于復社人數眾多的壯觀“聲勢”和幾欲搖動朝政的“權勢”,使研究者步入了一種理解的“誤區”,似乎晚明所有的文人社團皆可納入復社的研究體系之中。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如松江幾社,就是與復社并駕齊驅的文人團體,并顯示出長久的生命活力和獨特的個性。本文擬以文獻資料為依據,對幾社的興衰作一探討,以期跳出晚明文學研究的“復社中心主義”,喚醒文學史“真實的記憶”。
一、幾社成立及活動時間
關于幾社的成立,歷來文學和史學研究存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幾社為復社分支。如廖可斌認為,幾社是“從復社中相對獨立出來的一個社團”①。何宗美也將幾社視為復社旁支②。李圣華亦曰:“復社成立,幾社為其重要一支。”③ 由此將幾社納入復社研究體系之內。其二,認為幾社為呼應復社的立社宗旨而成立,如楊鐘羲《雪橋詩話》云:“云間幾社,李舒章與陳臥子承復社而起。”鄧實《復社紀略跋》言復社“上繼東林,而下開幾社”④。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言幾社“與復社相呼應”。此后,章培恒、郭預衡、袁行霈等所主編的文學史均承此說。上述觀點產生的原因在于多數幾社成員同時又是復社名士,如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等。但這種“兩屬”的事實并不能證明幾社即是復社的分支,因為在明末社事紛紜的文學環境中,許多文士可同時參加幾個社團而屬于自由身份⑤。事實上,幾社與復社均成立于崇禎二年(1629年)。兩者的前身皆是崇禎元年(1628年)成立于北京的“燕臺十子”社。從時間上說,幾社甚至早于復社。其后,因對于社事發展的構思兩社不相統一,復社主廣大,幾社主簡嚴,兩者分歧日漸顯露。杜登春《社事始末》曰:“兩社對峙,皆起于己巳(1629年)之歲。”是年,復社即有尹山大會,其后又有金陵大會、虎丘大會以壯其聲勢,而幾社則悄無聲息地在松江一地切磋古文時藝。凡此可見,幾社既非復社分支,亦非為呼應復社宗旨而成立,而是與復社并駕齊驅的文學社團。因而晚清朱彭年《論詩絕句》論吳梅村詩學淵源即曰:“妙年詞賦黃門亞,復社云間孰繼聲?”即將復社、幾社等量齊觀。錢仲聯為太倉縣博物館張溥故居題寫楹聯,其下聯曰:“繼東林,匹幾社,千秋山斗仰天如。”亦將復社與幾社并舉。 從立社宗旨看,兩社都旨在恢復“古學”。但復社意在廣大,重視文章氣節,以提拔獎掖后進為務。因此,關于恢復“古學”的立社宗旨自開始就沒有嚴格貫徹和認真執行,而是熱衷于“政治”問題。“古學”旗幟僅是復社人士進行“政治”謀略的一種詮釋策略。甚至可以說,復社自開始集會便偏離了其“古學”的文學軌轍。復社,“以朝局為社局”⑥,以參預朝政作為結社終極,⑦ 以至于美國學者艾維泗也認為,復社“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與最靈活的政治組織”⑧。也正由于對政治的熱衷,復社很快煙消云散。而幾社則在相當長時間內研習時藝,嚴格限定入社成員的身份,而且自開始即嚴格遵守立社宗旨。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幾社六子,自三六九會藝詩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門戶是非,謂非草茅書生所當與聞,以聲應氣求之事,悉付之婁東、金沙兩君子。吾輩偷閑息影于東海一隅,讀書講義,圖尺寸進取已爾。”認為“政治”非“草茅書生所當與聞”,疏離于政治問題。所以,謝國楨在《幾社始末》中說:“幾社雖然與復社合作,但是復社對外,幾社對內。復社整天的在外邊開會活動,幾社的同志,卻閉戶埋首讀書。”⑨ 崇禎末年,嚴峻的時事形勢使幾社的文學主張也轉向了對政治的熱衷,體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對政事和軍事流露出極度的關切。如陳子龍《兵垣奏議》、《江南鄉兵議》,宋征璧《左氏兵法測要》,宋存標《秋士史疑》等,體現了幾社文士敏銳和成熟的軍事思想及深廣的歷史意識。由此,當清兵下江南,“諸君子各以其身為故君死者忠節凜然,皆復社、幾社之領袖”⑩。盡管如此,讀書科舉卻始終是幾社堅定不移的社事宗旨。所以閹黨專權時,幾社能夠幸免于難。而易代之后,幾社事業又得以在新的政治環境中茁壯成長。 復社規模至巨,成員遍及十余省,“聲氣遍天下”(11)。但到南明弘光(1644年)時,閹黨阮、馬掌握朝柄,大量抓捕復社人士,“復社名流或死或亡,又值清兵南下,社事遂告中止”(12)。復社前后活動時間共十六七年。 而當復社事業已成過眼煙云之后,幾社事業正如火如荼。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復社之大局雖少衰,而吾松幾社之文則日以振。”復社首領張溥病卒的同年(1641年),幾社分裂為“求社”和“景風社”。崇禎十五年(1642年)冬,周茂源成立“雅似堂社”;彭賓成立“贈言社”;何我抑成立“昭能社”;盛鄰汝成立“野腴樓社”;王玠右成立“小題東華會”。崇禎十六年(1643年)春,杜登春與夏完淳成立“西南得朋會”。當復社的余火已成灰燼,幾社之爝火經短暫的間歇卻很快恢復了往日的隆興。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廷開科舉,宋征璧等部分幾社文士應薦入仕。多數幾社文士繼續在松江唱和揣摩以備應舉。順治四年(1647年),宋征輿、張安茂等進士中舉。順治五年、順治六年,王廣心、許纘曾等并舉進士。松江幾社以“舉業”為指歸的創社理想并未因陳子龍、夏允彝諸子的殉國而改轍。所以,屢次為幾社社事提供集會場所的重要人物、幾社六子之一彭賓也毫不猶豫地做了“大清順民”,其子彭師度本幾社名流,仕清后在京師周旋,努力汲汲于名人援引,其《上嚴灝亭書》表達了效忠新朝的意圖和決心:“聞朝廷新令許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而先生有薦賢為國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口俯聽。……先生以蓋代之鴻名,當邦憲之重地,其所保舉者,當必有瑰異之行。奇特之才,久蓄于夾袋中,而某則愿有請者。”(13) 并反復表示,一旦被舉,“茍得名位”,將“懷忠肝蓄義膽,奮不顧身,以赴國家之急”,定不負所薦,以報所知。這個事實盡管不免令亡者靈魂難安于九泉,但卻恰好提供了一個幾社始終以“科舉”為歸的有力佐證。 清順治六年(1649年),“滄浪社”分為“慎交社”和“同聲社”。二社均與“幾社”血脈相傳,而“同聲”皆為松江文士。 清順治七年(1650年)松江王印周等成立“大召社”。同年,“驚隱詩社”亦在松江成立。 清順治十年(1653年),十郡大社會于虎丘,盛況空前。松江彭師度參與虎丘集會,并以其《虎丘夜宴序言》而嶄露頭角。此前,松江社局由“武宣、孝力、冰修、古晉交主之,尚無歧途”(14),但當彭師度從虎丘歸,松江社局很快便發生變化,彭師度網羅一郡之人,大會于“須友堂”中,開始廣收門徒,擴張聲勢。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杜登春、張淵懿、施授樟等十人上紹“西南得朋會”而立松江“原社”,于是有《原社初集》之刻。是時,早已身仕清廷的宋征輿、李素心皆居家丁憂。宋征輿作為幾社元老,率子弟從游,宋楚鴻、宋泰淵、宋祖年等與原社諸子錢寶汾、張守來等堅持三六九講藝不輟。因此,鼎革后的云間社(按:云間乃松江別稱,又稱華亭,故幾社又稱云間社)實悉由直方、嗇齋主壇坫。宋征輿仍然熱衷于社事,成為新一代社事的首領。原社士子唱和之作結集為《振幾集》,取“重振幾社往日雄風”之義。不久,有《原社二集》之刻。其后,林古度等又從“原社”分化出“恒社”。后“原社”又再次分化出“春藻堂社”、“大雅堂社”。 松江社事的風起云涌激發起虞山錢謙益的參與熱情,已經十六年足跡未至云間的錢翁于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作云間之游,感慨曰:“近來南國興文章,云間筆陣尤堂堂。”(15) 其所言“筆陣”即指松江社事的隆盛。“始信出門交有功,橫眉豎目皆駿雄。”(16) 新一代的才俊正菁華爛漫,松江幾社后繼有人。 清順治十四年(1657),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科場案,江、浙文人涉及此案者不下百人。但由于宋氏兄弟等一部分松江士子已經仕清,幾社得到庇護,“江上之得免者,賴主盟皆在朝列”(17)。順治十五年(1658年),松江“同聲社”張友鴻輩又“漸入仕版”。順治十六年(1659年),杜登春母舅葉方藹高中探花。因此,盡管有科場案對江南文士的清掃,松江社事卻依然盛如昔日。 松江幾社幾經分化,持續了數十年。直到清康熙前期,幾社才逐漸消歇。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順治九年(1652年)、十七年(1660年)兩次禁社之詔,社事被迫消歇。二是順治十八年(1661年)“奏銷”一案,使松江懷才抱璞之士淪落無光,家弦戶誦之風忽焉中輟。三是作為領袖的人物均過早離世而后繼乏人。宋征輿既是原幾社的后起之秀,又是松江新社事的領袖,但他于康熙六年(1667年)便告別人世,終年方五十歲;其兄宋存標誓為不仕新朝的隱士,于順治十五年(1658年)即離別人世;宋存標子宋楚鴻,鼎革后“涉身戎馬”(18) 而殞身于平亂之中。宋征輿的四個兒子均是幾社的活躍成員,但除了幼子宋舜納外,其余三子長子宋泰淵、次子宋祖年、三子宋泰麓,均早于其父而夭亡。 盡管如此,幾社的文學活動持續時間幾達“六十年”(《社事始末》),較之于復社十六七年的短暫生命可謂長久得多。清初,松江幾社詩文歷數十年而流風未墜。
二、幾社成員構成與社集
松江幾社之所以能持續較長久的時間,至關重要的原因是始終與科舉緊密相聯,并由家族作為社事活動的背景和支撐。復社成員遍及全國,其人員多達數千,對于入社成員沒有任何身份限制和規定。而幾社社員最多時也僅百余人,嚴格限定入社社員身份——“非師生不同社”。 成員構成方面,復社追求一種人氣的旺盛,并一直為此而艱辛努力,力圖擴大到全國各地,人數多達“三千二十五人”(19)。張溥在日,“稱門下士從之游者幾萬余人”(《社事始末》)。收羅門徒不遺余力,終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噪進,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竄于其中”(20)。人員龐雜,良莠不齊,這正是復社受到閹黨鎮壓時不堪一擊的重要緣由。幾社則力主簡嚴——追求志同道合,非望擴大規模。因此,復社《國表》初刻,盡合海內名流,所入選者達七百余人。而《幾社會義》初刻,則只限于幾社六子。后擴至二十余人,到《幾社壬申合稿》所選亦只有李雯、彭賓、陳子龍等十一人的詩文。杜登春的原社,到《二集》之刻規模擴大,所收社事作者亦共五十二人,較之于復社《國表》所收相距甚遠。幾社最多達百余人,亦僅占復社人數的百分之一。盡管幾社人數不及復社,但幾社成員構成卻有自己的鮮明特色: 一是幾社成員多以家族作為支撐:父子、兄弟,或師生或姻親。松江宋氏家族,宋存標、宋征璧、宋征輿、宋轅生、宋祖年、宋楚鴻、宋漢鷺等一門父子兄弟子侄十余人皆為幾社成員,參與并多次主持幾社的社集集會;幾社六子之一杜麟征,其弟杜麒征、杜駿征,均幾社成員,他的三個兒子——杜端成、杜登春、杜恒春亦均幾社名人;徐孚遠及其弟徐致遠、徐鳳彩,鳳彩子徐麗沖均為幾社成員。當晚明弘光立朝,閹黨掌權之日,一直操持《幾社會義》之選的領袖徐孚遠謝事以避黨魁之目,而以選事委之于徐麗沖。徐麗沖受任于危難之際,在國勢艱難之日,使幾社選刻事業得以傳承而不輟。 二是幾社成員還有不少屬直系師生關系。王默公、陳正容為陳子龍之師,而陳子龍又是邵梅芬、張處中、王勝時、徐桓鑒諸子之師;夏允彝是侯玄涵、蔡嗣襄之師。“云間六子”之間也構成一種相互關聯的師生網絡。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六子之昆弟、姻婭、及門之子弟競起而上文壇”,“非游于周、徐、陳、夏之門,不得與也”。謝國楨《明清之季黨社運動考》論幾社曰:“明季幾社的成立,他們只師生通家子弟,在一塊結合,外人是不能參加的。” 另一方面,在幾社的文學活動中,科舉始終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們熱衷于選文,將朋友唱酬的作品隨時選刻出版。通過選集的傳播,作為典范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指導士子的應舉文章,最終有益于科考。復社由于對政治的過度熱情和極力強調權力的重要,對選事意興闌珊,《國表》共出版五輯便告終止。而《幾社會義》前后共刻七輯,其后所分化出的各個社團也均將“出版”作為社事要務。崇禎十四年(1641年),幾社分裂為求社和景風社,仍于刻印之事朝夕不倦。次年(1642年),談敘、張子固有《求社會義》之刻,彭賓、顧震雉有《贈言初集》之刻,而李原煥、張子美則有《幾社景風初集》之刻。 即使在幾社倡導經世救國、社事由揣摩舉業發展而為議論時政、其政治色彩日益濃重之日,幾社與復社的救國“策略”亦有區別。復社人員在千方百計“遙控”朝政,而幾社則力圖以文學救國。為此,陳子龍、宋征璧等二十余人于崇禎十一年(1638年)“網羅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務國政者,為《皇明經世文編》”(21),以此來體現幾社文士的國事關懷。 鼎革風云過后,清廷于下松江的同年詔開科舉,匯征人才,南國文人,競赴賓興之會。結果,乙酉(1645年)、丙戌(1646年)兩秋之闈,幾社諸君子聯袂登選。中舉者多為“明末孤貧失志之士”,如張九徵、周茂源、李延渠等“皆以復社、幾社名家中舉上南宮”。到戊子(1648年)科,社中伏處草間的大批文士終于“盡出而應秋試”,松江王廣心、杜登春、王印周、姚彥深等皆高中榜首。到松江原社,中舉者日益增多,令社事元老宋征輿深為感慨,曰:“吾輩幾社文會十余年,困于諸生無一雋者,公(杜登春)等五年中中五人,又與明經選者,皆是社中人,可謂勝前輩遠矣。”(《社事始末》)為此,杜登春曰:“前輩諸先生,時文外兼事古文,學不能專精舉業。今日新進皆不事詩古文,殫心括帖。”詮釋了幾社士子以舉業為指歸的結社動機。
應試科舉尚不能完全滿足幾社文士的內心渴求,他們認為,“括帖不足以逞志傳世,遂倡為古學”(22)。他們將恢復古學作為社事宗旨,作為自己的文學使命,自視為文學傳統的傳播者。因此,他們除對本朝詩文進行擇優篩選外,也依據經典的標準進行創作,并將所作詩文結集為《幾社壬申合稿》,其中包括詩、文、詞等各類作品。由于幾社文士的創作努力,不僅“一時文體、韻體靡不精研”(23),而且“高才輩出,大江南北爭奮于大雅”(24)。其創作傾向,大抵可概括如下: 其一,詞尚南唐北宋。 明興以來,由于曲的盛行,詞作為宋代獨盛的一種詩體已經被“邊緣化”了。鑒于詞道式微,幾社文士倡為“小詞”。他們回思詞史的盛衰,認為,“詩余始于唐末,而婉暢秾逸,極于北宋”(25)。南唐北宋詞意辭并茂、高澹渾厚,實為詞之極境。南渡以后,詞道體格精神漸趨消歇。宋征璧《倡和詩余·序》云:“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26) 他們認為,南唐北宋詞已經樹立了填詞的美學規范,南宋詞則失去了詞體的獨特風神和抒情活力。因此,他們將南宋以后的詞全然“放棄”了。 幾社對南唐北宋詞的揚幟表現于對詞體的怨刺精神與社會價值的自覺認同。他們認為,詞之傳統乃風騷之旨,當曲折幽深,以寄托沉至之思。為此,幾社文士以詩人的巨大活力,首先在詞體格調上進行追古,同時融入時代的聲音,于是,消歇已久的南唐小令至此復活。從幾社文士的創作可以發現他們追尋古典的努力。如宋征輿《望江梅》:“無限意,花月自春秋。芳草半隨游子夢,東風偏惹玉人愁,愁夢幾時休。”(27) 詞境純凈憂怨,以成功的小令體式抒寫游子的羈旅愁懷。小令正是詞體誕生之初的流行范式,無怪乎徐珂評其“不減馮、韋”(28)。李雯《浪淘沙·楊花》:“金縷曉風殘,素雪晴翻。為誰飛上玉雕闌?可惜章臺新雨后,踏入沙間!沾惹忒無端,青鳥空銜。一春幽夢綠萍間。暗處消魂羅袖薄,與淚偷彈。”語言清麗,寄托弘遠,徐珂謂:“語多哀艷,逼近溫、韋。”(29) 而從神韻和抒情技巧方面看,李雯詞更似秦淮海。陳子龍詞寄意深厚,胡允瑗評其《小重山·憶舊》曰:“先生詞凄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舊諸什。”(30) 況周頤言其“含婀娜于剛健,有風騷之遺則”(31)。在上述文士的倡導下,幾社諸子幾乎無人不染指詞翰,相互唱和。填詞,在幾社人士手中終于形成一場聲勢壯觀的文學運動,并由此改變了文學自身發展的命運——清代,不僅詞體中興,而且總體成就超越清詩。詞,由明代的邊緣文體轉化為清代的主流文體。 詞體在清初的全面復興,幾社功不可沒。吳綺《湘瑟詞·序》云:“昔天下歷三百載,此道幾屬荊榛,迨云間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說明云間派力辟榛莽、重振詞體的貢獻。云間詞派上承南唐北宋詞路,下開清詞中興之局,成為明清詞運的轉捩點。然盡管如此,幾社文士最大的文學成就仍在詩而非詞。 其二,詩宗漢魏盛唐。 明末公安、竟陵詩風吹遍詩壇之時,幾社文士重揚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旗纛,以恢復詩歌審美和道德涵養的雙重職能。宋征輿《酉春雜吟·序》曰:“夫風雅之澤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作者一二人患之而無以易之,于是一謝耳目之見而專求諸古。其始也,泛濫于三唐;其繼也,盤桓于漢魏六季;其終也,推極原本,斷之三百篇,既獲所要歸。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賢微言之后,且為天下唱率。”公然提出以《詩經》為規范。宋征璧自評己作“固風雅之翼”(32),并以“青蓮后身”自譽(33)。幾十年間,幾社文士負英雄之資,肆力著作,三百篇以外,二京六代以及三唐無不探源別派。他們認為,古詩的價值正在于托興之深、性情之真,而《詩經》在深至的情感與雅麗的形式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統一。于是,他們提出“情以獨至為真”的作詩法則,主張情辭統一,而在此方面的典范之作即漢魏盛唐詩。竟陵、公安摒棄了漢魏、盛唐的主流傳統。為此,宋征璧力排竟陵,認為“竟陵之所主者,不過高、岑數家耳,立論最偏,取材甚陋,其自為主詩,既不足追其所見,后之人復踵事增陋取侏儒木強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猶齊人之待客……吾只患今之學盛唐者粗疏鹵莽不能標古人之赤幟,特排突竟陵以為名高。”(34) 相對于明季的國運,竟陵詩風確實不合時宜,其清幽孤僻的詩境不能體現出盛大氣象,尤不能振奮人心,以至于朱彝尊詆為“亡國之音”(35)。 由此,幾社文士倡導復古,古詩則躡跡漢魏,近體則聯鑣開寶。其群體創作成為其詩學觀點的“釋證”:吳六益《長安清明》:“獨上高原發浩歌,支離南北奈愁何。樽前病起清明過,客里花開夕照多。閩海羽書連紫塞,江淮歸雁渡黃河。遙憐彈瑟三山外,細雨扁舟傍薜蘿。”高音亮節,頗得少陵氣骨。李雯《寒食》:“誰能寒食不思家,御柳紛紛欲作花。天下何曾接煙火,京師不解重龍蛇。傷春滿目風塵異,作客深愁云霧遮。憶得故園歸夢好,飛飛燕子向人斜。”格清氣老,秀亮淡逸,楊際昌謂其“詩宗王弇州、李于鱗”(36)。宋征輿《七夕宴吳興陳司理署樓同臥子及州守陸君》:“高座涼風百尺樓,烏程美酒客銷愁。云霄月上天河澹,牛女星前花霧收。河朔主人能獨醉,江南游子共傷秋。夜深玉漏無消息,五斗高談四座留。”體格高渾,首句顯然化用王昌齡《從軍行》“烽火樓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之句,結響宏亮,得風雅之正則。陳子龍論宋征輿詩,“大而悼感世變,細而馳賞閨襟,莫不惜思微茫,俯仰深至,其情真矣。上自漢魏、下訖三唐,斟酌摹擬,皆供麾染,其文合矣”(37)。認為宋子之詩做到了性情與形式的統一,這正是古詩規范。 在遵唐的途轍中,幾社文士體現了主體精神的一致。陳臥子“文高兩漢,詩軼三唐”(38);田茂遇“兼青蓮、少陵之勝,而軼駕于北地、濟南之上”(39);董蒼水“究極于風雅正變之間,爰及漢魏,下訖三唐”(40)。所以,幾社名士彭賓言明季詩壇“詩亡之后,力砥狂瀾,功在吾郡”(41)。由于迥異于竟陵詩風,至清初詩壇,“一時作者如繁星之向辰極,百川之赴滄海”(42)。故吳梅村亦稱,松江幾社于明季詩壇深具“廓清摧陷之功”(43)。 在詩詞復古的同時,幾社文士主張“文以范古為美”(44),“賦本相如,騷原屈子”(45)。他們認為,前代古文典范唯有兩漢,陳臥子在《幾社文選·凡例》中昌言:“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確立了文規兩漢的創作準則,并以此標準進行古文研摩。他們的創作風格與時代風氣迥異,顯示出對二京之文的強烈愛好。杜麟征《壬申文選·序》:“文章起江南,號多通儒,我郡為冠。”宋存標主筆選刻《幾社壬申文選》“開史漢風氣不趨時畦者”(46),所選古文皆異于竟陵時流,結果“海內爭傳,古學復興”(47)。 幾社文士在創作方面的諸多努力,很快發展為一種趨勢,朱鶴齡云:“文場建鼓,夙仰云間。大雅扶輪,群推海上。”(48) 明清之際,“稱文章者,必稱兩社(復社與幾社);稱兩社者,必稱云間”(49)。這說明,幾社的創作不僅已經廣被認同,而且獲得了普遍的感染力。至清初,終于使“天下無論知與不知,詩文一道皆推云間”(50)。
四、幾社文學史地位
在文學史上,對于晚明文人社團的研究多聚焦于復社,先后有陸世儀《復社紀略》、吳梅村《復社紀事》、楊彝《復社事實》等,而專門記載幾社的只有杜登春《社事始末》,近人亦僅有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由于缺少相關文獻記載和歷史的誤讀,幾社的文學史地位幾乎被忽略了。事實上,幾社作為一個嚴格的文學社團,以其長久的文學生命在文學史上開辟了屬于自己的重要席位,尤其在清初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朱培高曾云:“云間派詩、詞不但在明末具有極大影響,在清初也是開一代風氣的重要流派。”(51) 所言即云間派詩詞文于清初的全面影響。 詞的創作并非云間派主流,但恰是詞為云間派贏得文學史上的至高聲譽。“云間詞派”既挽明詞衰微之局,同時又直接開啟清詞中興之勢。清初詞壇群宗晚唐的趨向即源于云間派的倡導。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言云間詞派以晚唐、北宋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52)。以致清前期百余年的詞壇都充斥著云間派的流音遺響,清初詞壇紛紜的諸流派幾乎無不遵循云間路徑、沾溉云間詞風,如浙中詞壇的“西泠十子,皆云間派”(53);陽羨派宗主陳維崧早年學詞即從“云間”入手,其所效法者“在云間陳、李賢門昆季”(54);主持康熙詞壇近半個世紀的王漁洋詞亦“沿鳳洲、大樽緒論,心摩手追,半在《花間》”(55)。云間派被清初詞壇普遍接受的事實說明,清詞之“復興”,云間派功勞卓異。近人龍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中說,云間詞派“開三百年詞學中興之盛”。云間詞派作為詞史上第一個深具典范意義的詞派和清初影響最大的詞學流派,成為歷來詞學研究的主要立足點。 詩學方面,云間派首開清詩之特色,繼承七子衣缽,倡導秦漢文章、盛唐詩歌,揭開了清代詩史宗唐的序幕,成為有清一代唐、宋詩之爭的源頭。凌鳳翔為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作序論明末詩派之衰有云:后七子之后,“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弘道、鐘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號云間體”。顧景星《周宿來詩集序》曰:“當啟、禎間,詩教楚人為政,學者爭效之,于是黝色織響橫被宇內。云間諸子晚出,掉臂其間,以大樽為眉目,追滄溟之揭調,振竟陵之衰音”(56),清掃了晚明詩壇的衰颯之氣。云間派是“‘七子’詩風得以歷晚明而入清延續不斷的一個關鍵的中介”(57)。晚明,“鐘、譚之名滿天下”和“天下群趨于竟陵”致使“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七子之學已被擠向詩壇邊緣而漸趨消歇之際,云間詩人挽救了七子詩學的危機。因此,全祖望評曰:“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于厄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58) 從云間詩人對七子的捍衛和以七子自詡的層面看,漢魏風骨、盛唐精神經由云間的播揚而在詩史上保持了詩的激情,從而使中國文學精神的重要一脈得以延續。吳梅村《宋直方〈林屋詩草〉序》曰:“(清初)天下言詩者輒首云間”。直到近代的南社,其詩學宗旨仍以云間為鵠的。陳去病、柳亞子等20世紀的反清詩人皆推重云間,柳詩曰:“平生私淑云間派”(59)。當時,南社詩人多以云間派剛勁雄渾、英雄并美的詩風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過程中,云間派再次體現出導夫先路的生命價值。 呂留良《刻陳臥子稿記言》云:明季文壇“風氣為之一變者,莫如云間之幾社,為極盛一時”。其所言即幾社古文在晚明清初的廣泛影響。明清之際,散文被竟陵文風所統攝,但其“幽情單緒”的審美風格已不合時宜。云間文士率先“變當時蟲鳥之音,而易以鐘呂”(60),在審美范式和創作標準方面均構成對竟陵的反撥。在時人眼中,云間派的藝術追求幾近完美地切合了儒學詩教典范——《詩經》“風”、“雅”道統。在云間群體的倡導下,明末詩文高華雄爽,“海內言文章者必歸云間”(61)。 云間派致力于復古,清掃了竟陵之弊,然而也流露了自身的缺憾。宋琬在《周釜山詩·序》中言,云間派“持論過狹,泥于濟南‘唐無古詩’之說,自杜少陵《無家》、《垂老》、《北征》諸作,皆棄而不錄,以為非漢、魏之音也”。其批評到位,頗具服人之力。王漁洋《花草蒙拾》亦曰:“云間數公論詩拘于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為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所言亦切中其弊。盡管如此,缺點并不能掩蓋其曾有的文學貢獻。中國文學忠君憂世的大雅傳統,正是經由幾社文士等一代代文學精英的堅持不懈才得到維系和光大的。 幾社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社團,在社團構成、活動創作等諸方面均與復社有很大差異,體現出明清之際社團的復雜性,其中亦折射出文士們微妙而豐富的內心價值取向。就文學成就而言,云間派作為明末影響最大又極具明顯地域特征的文學流派(復社終究是否可稱得上一個文學流派,至今尚爭論不已。而云間派的流派意識自其成立之日便已確立,并貫徹始終),對后世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成為一個“文學時代”的“代言”:明清之際,“海內翕然稱云間之學”(62)。云間派詩文并未因復社的“影響”而消弭自己的光彩。在清代文學史上,作為一個成熟的文學流派,云間派所開創的閱讀傳統和審美原則將成為歷史中永恒的聲音。
注釋: ①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第35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緒論》,第13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③李圣華:《晚明詩歌研究》,第29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④《東林始末》,第257頁,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36年(1947)。 ⑤如錢光繡即一連參加了六個地方的八個社團,參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錢蟄庵徵君述》,《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94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⑥⑩杜登春:《社事始末》,《昭代叢書》本。 ⑦黃宗羲:《南雷文定·陳定生先生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⑧胡秋原:《復社及其人物》,臺北,中華雜志社,1968。 ⑨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5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11)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上海,國學保存會,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 (12)郭紹虞:《明代文人結社年表》,見《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第51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彭師度:《上嚴灝亭書》,見《彭省廬先生文集》卷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14)(17)杜登春:《社事始末》。 (15)(16)錢謙益:《次韻答云間張洮侯投贈之作》,見《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8)陳維崧:《宋楚鴻古文詩歌·序》,見《陳迦陵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19)據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二載,吳應箕《復社姓氏》二卷,吳應箕孫《補錄》一卷,所收復社人數共三千二十五人。 (20)陸世儀:《復社紀略》。 (21)《陳子龍詩集》附錄二《臥子自撰年譜》“崇禎十一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2)(23)彭賓:《二宋倡和春詞·序》所附彭士超評語,見《彭燕又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24)宋徵璧:《上吳駿公先生書》。見《抱真堂詩稿》,清順治九年(1652年)刻本。 (25)陳子龍:《三子詩余·序》,見《陳子龍文集·安雅堂稿》,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影印本)。 (26)宋征璧:《倡和詩余·序》,見《云間三子新詩合稿·幽蘭草·倡和詩余》,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27)《云間三子新詩合稿·幽蘭草·倡和詩余》。 (28)(29)徐珂:《近詞叢話》“詞學名家之類聚”,《詞話叢編》本。 (30)《陳忠裕全集》,卷二十附,見《陳子龍文集》。 (31)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詞話叢編》本。 (32)宋征輿:《酉春雜吟·序》所引,見《林屋文稿》,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33)宋征璧:《與周介生書》,宋存標《情種》所附,《四庫未收輯刊》本。 (34)宋征璧:《與吳子論詩書》,見《抱真堂詩稿》。 (35)朱彝尊:《明詩綜》“譚元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影印本)。 (36)楊際昌:《國朝詩話》,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37)陳子龍:《佩月堂詩稿·序》,見《陳子龍文集》,卷上。 (38)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叢編》本。 (39)嚴沆:《水西近詠·序》,見田茂遇《水西近詠》,《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40)宋琬:《董蒼水詩·序》,見《宋琬全集》,第34頁,濟南,齊魯書社,2003。 (41)彭賓:《王崍文詩·序》,見《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 (42)吳梅村:《宋直方〈林屋詩草〉序》,見《吳梅村全集》,第67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3)宋琬:《周釜山詩·序》,見《宋琬全集》,第13頁。 (44)陳子龍:《佩月堂詩稿·序》,見《陳子龍文集》,卷上。 (45)張溥:《幾社壬申合稿·序》,見杜騏徵等輯《幾社壬申合稿》,明末小樊堂刻本。 (46)(47)杜登春:《社事始末》。 (48)朱鶴齡:《寄王玠右書》,見《愚庵小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9)《陳子龍詩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0)宋征璧:《抱真堂詩稿》所附張洮侯語。 (51)朱培高編著:《中國古代文學流派辭典》,第288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52)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詞話叢編》本。 (53)楊鐘羲:《雪橋詩話初集》,第220頁,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二輯。 (54)陳維崧:《與宋尚木論詩書》,見《陳迦陵文集》,卷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55)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56)顧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57)嚴迪昌:《清詩史》,第43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8)全祖望:《張尚書集·序》,見《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1210頁。 (59)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第8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0)董以寧:《顧天石詩集·序》,見《正誼堂文集》,《四庫未收輯刊》本。 (61)宋琬:《尚木兄詩·序》,見《宋琬全集》,第18頁。 (62)宋徵輿:《林屋文稿·云間李舒章行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