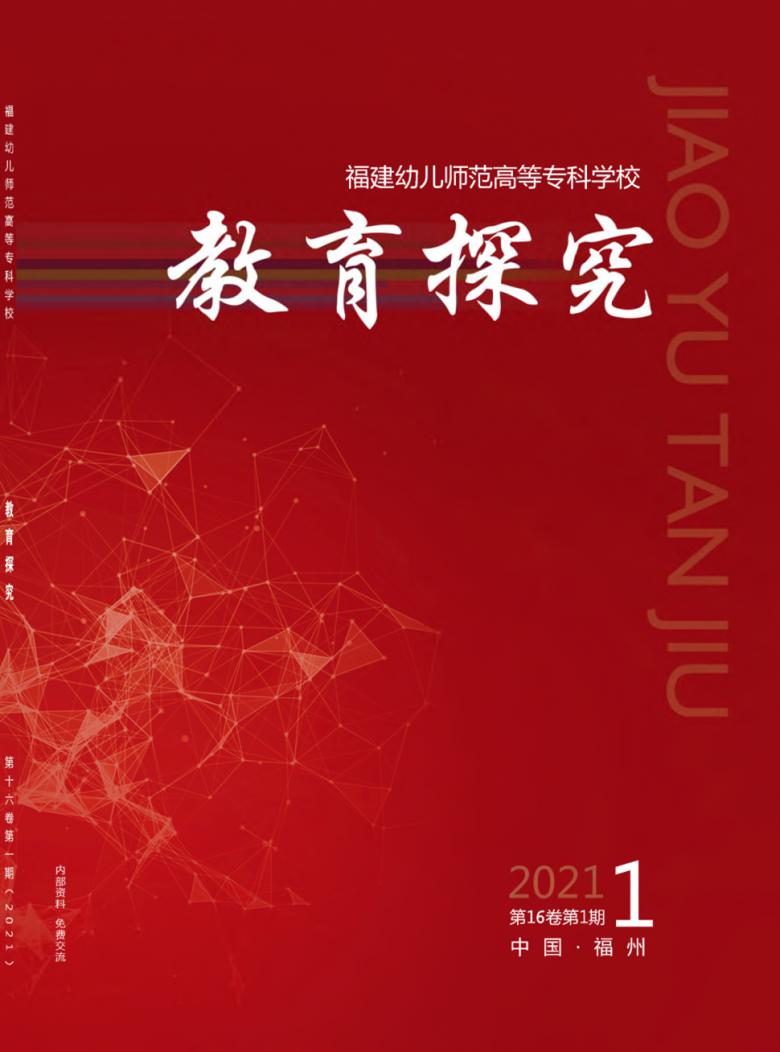至情人性的崇拜——明清文學佳人形象詮釋
郭英德
在明代末年荑秋散人的《玉嬌梨》小說第5回中,主人公才子蘇友白對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佳人,發表了一番別具一格的見解。他說:
有才無色,算不得佳人;有色無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與我蘇友白無一段脈脈相關之情,亦算不得我蘇友白的佳人。
這可以代表明清文學家對佳人形象的基本認識:作為一種理想人格,佳人形象應該具有“色”、“才”、“情”三種要素,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色、才、情三者并存,這既是文人的自我形象的本質特征,也是理想的至情人性的文化意蘊。
那么,色、才、情的具體內涵是什么呢?
先看色。色,當然首先是外表的美麗,包括秀美的面貌、嬌柔的體態等。美色本來就是男女性愛的主要觸媒,中國早在《詩經》時代就有“子都”、“碩女”的美稱。明清文學作品中的佳人形象,也大多有著美麗的外表和風流的體態,即首先是個美女。
雖然明清文學家往往習慣于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櫻唇柳腰”之類的諛詞,塑造千人一面的西施、王嬙,大多未能刻畫出每一個佳人形象獨具個性的美貌。然而,在他們對美色的揄揚之中,卻也跳躍著閃光的時代思想火花。
例如,唐代傳奇作家一般認為,“郎才”和“女貌”是男女雙方相愛時各自的標準,如許堯佐《柳氏傳》稱:“(韓)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蔣防《霍小玉傳》里李益也說:“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而明清文學家卻明確地提出,無論是才子還是佳人,都必須才貌兼具,缺一不可。吳門拼飲潛夫《春柳鶯序》說:
情生于色,色因其才,才色兼之,人不世出。所以男慕女色,非才不韻;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稱佳話。
明清文學家首先充分肯定人情必好色,說:“美色當愛也,美色而不愛,非人情也。”(天花才子《快心編》)而且他們還認為,美色不僅僅是傾國傾城的相貌,更是美好的內才與中情的顯現:“人只患無才耳,若果有才,任是丑陋,定有一種風流,斷斷不是一村愚面目”(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佳人的美,不僅僅在于嬌美的相貌,更在于豐贍的才情,即使相貌略遜一籌,若才情洋溢,也能形之于面目,流之于體態。明清文學家的這一認識無疑比唐傳奇作家大大前進了一步。
所以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瑞云》篇中寫道,像瑞云這樣貌美才高的女子,即使相貌由美變丑,“蓬首廚下,丑狀類鬼”,才子賀生也不因此鄙棄她,反而說:“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這事使和生深為感動,贊嘆道:“天下惟真才子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才子之所以能做到“不以妍媸易念”,正因為超越皮相之美丑,而關注內在的才情。由于具備了才情的內蘊,明清文學作品中佳人形象的美色便賦予一種準宗教的圣潔色彩,與只有“肉”沒有“靈”的世俗的美艷判然而別。
次看才。中國有一句古訓,說是“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人們往往認為女性舞文弄墨,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連才華橫溢的女性自己也往往這么認為。例如,唐代進士孟昌期的妻子孫氏,有一天突然將代夫創作的詩稿焚毀,說:“才思非婦人事。”(《全唐詩》卷七九九)到明清時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仍然像一把利劍懸在婦女的頭上。如清代長洲人韓韞玉,“少承家學,博極群書,病歿前取稿盡焚之,曰:非婦人事。”(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卷二)所以,在曹雪芹的《紅樓夢》小說中,素有大家規范的薛寶釵,雖然才華出眾,博覽群書,卻一再勸告姐妹們,吟詩作賦不是閨中女子的正業,有工夫還是多做點女紅才是。
盡管凜冽的寒風一直剝蝕著女子的才華,但是在明清時期,對才女的肯定和稱揚,畢竟已經沖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漸漸形成風氣了。明萬歷間謝肇浙在《五雜俎》卷八中,一反成見,認為歷代史書中的《列女傳》只收貞、節之類的婦女,成了“烈女傳”,這是不合適的,應該將“才智”、“文章”之女也列入傳中。清順治間鴛湖煙水散人在短篇小說集《女才子書》中,對什么是“美人”更提出了新穎別致的看法。他認為,“色莊語寡”者,未足為“艷”;精于女紅,而不讀書、不會吟詠者,不能稱“雅”;行坐不離繡床,不會“倚欄待月”,怨春傷時者,不為有“韻”。這樣的美人,“形如木偶,踽踽涼涼”,“大失風流之致”,算不得真正的美人。真正的美人應該是:“賢也,智也,韻也,斯為上也”;“膽也,識也,是其次也”;“情也,又其次也”。而最完美的美人,應該是“膽識和賢智兼收,才色與情韻并列”。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佳人必為才女,無才不是佳人,成為明清文學作品的一個普遍現象。佳人之才,主要是一種“文人之才,詩人之才”:
此種才,謂出之性,性誠有之,而非性之所能盡賅;謂出之學,學誠有之,而又非學之所能必至。蓋學以引其端,而性以成其靈。茍學足性生,則有漸引漸長,愈出愈奇,倒峽瀉河而不能止者矣。(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
可見,明清文學家所肯定的才,不只是生而有之的天資稟賦(“性”),也不只是學而有之的知識技能(“學”),而是以智慧為核心,融匯了天資稟賦、知識技能的個體能力,是構成個性人格的基本要素。
當時人們通常認為才有兩種:一種是詩詞曲賦之才,一種是八股時文之才。在傳統的看法里,經世致用是實學,八股時文是要務,而詩詞曲賦則是浮華之學,并非有用之才。如吳敬梓《儒林外史》小說第四回中周進說:“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第十一回中魯編修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而明清文學家卻主張,一個人有無才能,首先不是看他能否博取功名利祿,也不是看他能否安邦治國,而是看他作詩吟詞時內在的靈氣如何,才華如何。他們認為,才能是自身的價值,自身的財富,是不待外求、不須外附的獨立自足的東西。這種菲薄“學而優則仕”,重才輕學,重內才輕事功的人格觀點,表現了明清文人對不依附于外在社會的個體人格的空前重視。
而且,在明清文學作品中,作家常常才情并稱,與德性相對立。德性如“忠孝節義”是人皆有之的,而才情卻“千秋無幾”,“有得有不得焉”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是人的個體能力。這種能力源于心靈而發于詩文:“或膾炙而流涎,或噦心而欲嘔,其情立見,誰能掩之?始知性情之芳香,齒牙之靈慧,出之幽而幽,出之秀而秀,種自天生,不容偽也。”(天花藏主人《兩交婚小傳序》,《兩交婚》卷首)人們正是因為內賦風流靈秀的本性,才激發了言情寄意的詩賦之才。因此才情是人格本體的感性顯現,是個人生命力的迸發,它比德性更切近人性的本質。
清順治間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小說,便是一曲才女的贊歌。小說寫明朝大學士山顯仁的女兒山黛才華過人,撰寫的《白燕》、《天子有道》等詩清新可讀,皇帝讀后欣喜異常,賜她“弘文才女”四字匾額,并玉尺、如意等物。一時山黛名重京師,四方文士紛紛前來求詩。皇帝又命山黛在玉尺樓同翰苑名公對陣,考較詩文。山黛才壓群英,赴考的舉人、進士都成了她的手下敗將。無獨有偶,江都縣的一位平民女子冷絳雪,也是美貌多才,被推薦為山黛的女記室。皇帝讀了冷絳雪的詩,賞鑒稱異,賜她“女中書”的名號。最后,山、冷二女,分別嫁給絕世奇才燕白頷和平如衡。天花藏主人刻意頌揚女才子,把山、冷二女描繪得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和她們相比,那些翰苑公卿、玉堂學士、詞壇宿彥、詩社名公,通通相形見絀,丑陋不堪。在小說中,作者開宗明義說:“富貴千年接踵來,古今能有幾多才?”才遠遠高于富貴。又說:“道德雖然立大名,風流行樂要才情。”才又非道德能比擬。以才傲視富貴,鄙薄道德,這在當時是需要有相當的勇氣的。
佳人的才,不僅僅是文學之才,還包括她們的膽識和賢智,甚至包括經世之才。鴛湖煙水散人在《女才子書》中贊嘆道:“文士之膽,不如女子更險;文士之心,不如女子更巧。”(《女才子敘》)佳人的膽識和賢智,甚至連文人才子也自愧不如。明萬歷間徐渭在《雌木蘭》和《女狀元》兩部雜劇中,塑造了花木蘭和黃崇嘏這一武一文兩位女扮男裝的奇女子形象。花木蘭決定代父從軍時唱道“休女身拼,緹縈命判,這都是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么男兒漢!”黃崇嘏決定改裝應舉時唱道:“詞源直取瞿塘倒,文氣全無脂粉俗。”她們自豪地把自己比作男子,甚至還不把男子放在話下。花木蘭直搗敵營,生擒敵將;黃崇嘏當庭對曲,穩勝須眉。徐渭極力表現她們在文事武功、精神氣概上超過男子,熱情地歌頌道:“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
明清文學作品中這些具有才識膽智的佳人形象,是前此以往的文學作品并不多見的,鮮明地披示了時代的新風貌。但是,在謳歌佳人曠世奇才的同時,明清文學家還深刻地揭示了才稟給佳人帶來的悲劇。曹雪芹《紅樓夢》小說里最富才智的,不是那些須眉男子,卻是一些閨閣女子。且不說王熙鳳的才干,也不談薛寶釵和林黛玉的文采,單說那位“帶刺的玫瑰”賈探春,就是一位不同凡響的女中豪杰。她為人的精明,處事的老練,看問題的洞若觀燭,再加上知書識禮,在賈府的眾千金中確是首屈一指。然而,賈探春卻無法擺脫庶出的命運,最終落得遠嫁的結局。小說第五回中給賈探春下的判詞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這不僅是對賈探春的悲嘆,也是對所有才女的悲嘆。才稟給佳人增添了多姿多彩的魅力,同時也給她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
在古代中國,像山黛、冷絳雪那樣施展才華、蒙膺殊榮的才女,畢竟是鳳毛麟角;而像花木蘭、黃崇嘏那樣女扮男裝、博取功名的奇事,更是世所罕見。更多的才女,卻空有才華,枉為遺棄,只能禁錮在深閨之中,老死在蓬門之內。在封建社會文化的重壓之下,才女們只能聽憑無情的歲月漸漸消磨自身秉賦的天姿才華。因此,明清文學家對才女悲劇的感嘆,實際上也蘊含著他們自身懷才不遇的深沉感慨。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序》,便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
顧時命不倫,即間擲金聲,時裁五色,而過者若罔聞罔見。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既自短其氣而又不忍,計無所之,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其黃粱事業。……凡紙上之可喜可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平山冷燕》卷首)
因此,明清文學家對佳人之才的歌頌乃至崇拜,實際上是對他們自身才華、自身價值的歌頌乃至崇拜,是以虛幻的理想之夢與嚴酷的現實社會相抗衡:“雖無異乎游仙之虛夢,躋顯之浮思而已, 潑墨成濤,揮毫落錦,飄飄然若置身于凌云臺榭,亦可以變啼為笑,破恨成歡矣。”(鴛湖煙水散人《女才子書》) 最后看情。
唐代韓愈、李翱等人首先明確區分情與性,認為性是理性道德,情是感性情欲,并提出“性善情惡”、“復性滅情”的主張。宋代理學家如程頤、程顥、朱熹等人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性與情、天理與人欲、義與利、道心與人心等一組矛盾對立的命題。從明代中期開始,由于程朱理學的惡性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普遍反感,從王守仁心學標舉“心即理”、“致良知”的命題開始(《王文成公全書》卷六),提倡以內在的自然、情感、欲求為人性本體,而反對以外在的天理、規范、秩序為人性本體,成為一股來勢洶涌的思想文化新潮。文人士大夫紛紛引用經書的舊典成說,如“食色,性也”(《孟子·告子》),“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斷章取義,并加以片面的推衍和發揮,注入時代的內容,從而高度肯定人的自然情欲、需求和愿望。
明清文學家雖然大多受到宋明理學家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他們出自于文學家獨具的審美感受,對情與性、情與欲的關系卻另有別解。
第一,理學家以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之“理”作為人的本性,而明清文學家卻大多以個體的感情欲望之“情”作為人的本性。湯顯祖更把情與理、情與性的對立,一度推到了前人與時人都未能達到的極端的地步,他說:“諸公所講者性,仆所言者情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一五)“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湯顯祖詩文集》卷三三《牡丹亭題詞》)在他看來,“講情”就是標舉人的自然欲求、自然本性,“講性”或“講理”就是強調社會的規范、理念的制約和倫理的羈絡,情與性、情與理的邏輯出發點和人性內涵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理學家主張理義是性情的基礎,而明清文學家卻主張:“性情者,理義之根柢也”(陳洪綬《嬌紅記序》,孟稱舜《嬌紅記》卷首)。明清時期的理學家和文學家雖然都追求情與性、情與理的和諧統一,但文學家的立足點卻更多地偏向于情。他們一方面反對以理節情、以理代情或以理扼情,肯定情的真實性、合理性、正當性,說:“乃知老成端重,其貌尤假;風花雪月,其情最真”(赤城臨海逸叟《鼓掌絕塵敘》,金木散人《鼓掌絕塵》卷首);另一方面又主張理在情中,情即是理,情之至即理之至,“天下之貞女必天下之情女”(孟稱舜《鸚鵡墓貞文記題詞》)。
第三,與此相關,明清時期的文學家與理學家大相悖逆,從不諱言色欲,甚至將色欲作為情的生理基礎,以為色欲原本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生大欲,男女一般,縱是窈窕淑女,亦未有不慮摽梅失時,而愿見君子者。”(闕名《定情人》)但是他們卻從不將欲等同于情,而是嚴格地區別欲與情,說:“使天下之人,知男女相訪,不因淫行,實有一段不可移之情”(吳門拼飲潛夫《春柳鶯序》)。
總之,在明清文學家看來,性是情的倫理基礎,欲是情的生理基礎,而情則是超出于性、欲之上的人性真諦。因此,在明清文學佳人形象中,“脈脈相關之情”被擺在色、才、情三者的第一位,成為佳人之所以為佳人的最本質的人格要素。
佳人形象的“脈脈相關之情”,首先是一種本源于內心自然情欲的生命力量和人生追求。在湯顯祖的《牡丹亭》傳奇里,《詩經·關雎》那動人的詩句使杜麗娘發現:連堂堂圣人也不諱言男女之間的戀情,圣人之情居然和自己內心中勃動的青春之情相通!后花園中明媚的春色又使她發現:如火如荼的春光竟會被人遺棄,就像自己的青春被人遺棄一樣!所以,杜麗娘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大膽的懷春之夢,又不由自主地背著人到花園去尋夢。“驚夢”、“尋夢”,并不是杜麗娘一時的生理沖動或心理沖動,而是她在自然情欲原動力的推動下對青春的生命的執著追求,對真實的人生的執著追求。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的追求,她可以獻出生命,可以魂游幽媾,還可以起死回生。王思任熱情地贊嘆道:“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瞑,獠牙判發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必不肯使劫灰燒失。”(《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這是何等濃烈的情感,又是何等執著的追求!
其次,佳人形象的“脈脈相關之情”,又是佳人對才子人品才華的傾心仰慕和對才子體貼入微的柔情。明末荑秋散人的《玉嬌梨》小說中,兩位佳人白紅玉和盧夢梨,都知書能詩,而且愛才憐才。白紅玉和她父親一樣,認定的擇婿標準是:“不論富貴,只要人物風流,才學出眾。”在風聞蘇友白的才貌人品以后,她并不輕陷于情,不但要親見其人,還要親試文墨。一旦了解了蘇友白的才情,她不僅以心相托,還為他出謀畫策,讓他明媒求婚,揭穿了惡人張軌如的騙局。蘇友白感動地稱贊她是“深情慧心”。盧夢梨也是愛才如渴的,她在蘇友白患難時,慧眼識英雄,大膽地吐露熾烈的情意。當聽說蘇友白另有一頭親事時,她并沒有流露出偏狹、嫉妒之情,而是真摯豁達,出銀相贈,并且送給蘇友白金鐲和明珠,作為愛情的信物。這種善解人意的少女,不正是文人心中朝思暮想的理想偶像嗎?
再次,佳人形象的“脈脈相關之情”,還是青年男女肝膽相照、生死相許的深情。明崇禎間孟稱舜的《嬌紅記》傳奇里,王嬌娘深深地感慨:“婚姻兒怎自由,好事常差謬,多少佳人錯配了鴛鴦偶!”因此她決心大膽地“自求良偶”,說:“寧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無學李易安之終托匪材。至或兩情既愜,雖若吳紫玉、趙素馨,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王嬌娘所謂的“良偶”,就是“同心子”,即志同道合的人。她和表哥申純兩相愛戀,經過相互試探和痛苦相思,終于私自結合了。后來在權勢煊赫的帥節鎮的脅迫下,王嬌娘和申純的婚事終成泡影,她抱恨成疾,臥床不起。人們為了勸說她嫁給帥家,騙她說申純已經另娶他人了。她絲毫不懷疑申純的愛情,她說:“相從數年,申生心事我豈不知?他聞我病甚,將有他故,故以此開釋我。”果然,當王嬌娘自盡以后,申純悲憤地說:“我與嬌娘情深義重,百劫難休。她既為我而死,我亦何容獨生?”所以他也絕食身亡,相從嬌娘于九泉之下。
總之,在明清文學作品中,情成為佳人形象的生命本體。這種情,包含著對所向往的愛情理想的執著與追求,對所認定的理想人格的專注與珍重。而且,這種心心相印的愛情極深、極廣、極強,湯顯祖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詩文集》卷三三《牡丹亭記題詞》)吳炳說:“天下只有一個‘情’字,情若果真,離者可以復合,死者可以再生。”(《畫中人》第五出《示幻》)隨緣下士說:“天下有情人大抵如此,情得相契,則死亦如生;情不得伸,則生不如死。”(《林蘭香》)佳人形象這種為愛情而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表現出一種對至情人性的宗教般的頂禮膜拜。
但是,從湯顯祖開始,明清文學作品中便出現了一種導情入理、情理合一的潛在趨向。在《牡丹亭》傳奇里,杜麗娘還魂回生后,首先想到的便是:“鬼可虛情,人須實禮”,因此,婚姻事“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們對至情人性的充分肯定,最終還必須落實到現實社會中,還必須符合于傳統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湯顯祖所說的:“豈非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也哉?”(《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四《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這種潛在趨向與明末清初哲學思潮的變遷是相互表里的。如清初王夫之主張“理欲合性”說,認為:“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讀四書大全說》卷八《孟子·告子上篇》,《周易外傳》卷一)。清乾隆間戴震也說:“理者,存乎欲者也”,“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義疏證》卷中《性》)。
明清文學家普遍主張要正“性”定“情”,即以傳統的倫理道德約束個人的自然感情,使“情”歸附于“性”,同化于“理”。清初天花藏主人為《定情人》小說作序說:
情一動于物,則昏而欲迷,蕩而忘返,匪獨情自受虧,并心性亦未免不為其所牽累。故欲收心正性,又不得不先定其情。……而情定則由此而收心正性,以合于圣賢之大道不難矣。(《定情人序》)
這不正是明白地宣稱要以封建正統觀念和道德規范,即所謂“圣賢之大道”,來自覺地約束自由不羈的個人自然感情嗎?
因此,明末清初的文學家認為,真正理想的佳人形象,應是好色而不縱淫,深情而不佻達,風流而不輕薄,這就是所謂“才子佳人得七情之中道”(晴川居士《白圭志序》)。于是,我們看到了孟稱舜稱贊王嬌娘“始若不正,卒歸于正”(《嬌紅記序》);李漁塑造“道學風流合而為一”的理想人格(《慎鸞交》第二出《送遠》),等等。到清中期,文學作品中的佳人形象身上,情越來越趨于道德化,個人的自然感情與社會的倫理道德幾乎相合無間,佳人形象已經漸漸演變為淑女形象,如乾隆間蔣士銓所歌頌的“得乎性情之正”的貞女節婦(《香祖樓·自序》)。即使像曹雪芹《紅樓夢》小說里的林黛玉,在人生歷程中,她雖然內心一直向往著自由與幸福,并且把對賈寶玉的一片深情視同生命本身,甚至更重于生命,但她卻只能始終把這份深情深藏在心中,不敢、也不能像明中期至清前期文學作品中的佳人形象那樣,大膽地、主動地追求自由與幸福。因此,她的情感追求,從行為方式本身來說,無疑是并不違背倫理道德的。連林黛玉都是如此,遑論他人!由此可見,時至清中期,文學家對至情人性的頂禮膜拜,已經越來越多地滲透了對倫理道德的真誠信仰。
綰結而言,在明清文學佳人形象的基本要素中,色即自然美是人的外在美,才即才能美是人的內在美,而情即情感美是貫穿于內外、流蕩于心靈的人性底蘊之美。色、才、情三要素交相滲透,構成鮮明的人格美、人性美,這是佳人形象主體自身的追求與完善,而不外求于社會功能與社會規范。明清文學家借助于佳人形象的構造,把歷來諱言的色、欲抬出來作為人性構成的生理基礎,把浸透著肉體追求和感性欲望的情標舉到至高無上的地步,而把性、理貶抑為情的附庸、情的外現或情的歸趨,從而以情為媒介把人的自然本性和倫理社會性粘合起來,并且把才能作為人性構成的基本要素,追求人性的“雅”、“韻”、“艷”、“風流”之美,這種色、才、情三者并存的理想人格,實現了在古代意識所允許和可能的范圍內的人性完善。明清文學家對人性自我完善的汲汲追求,不僅反照出文人對理想的社會人生的心靈幻設,更映射出文人對理想的至情人性的精神崇拜。
然而,明清文學佳人形象虛幻的光輪,固然聊以慰藉古代文人失意于仕途、見棄于社會的落寞情感,但卻深深地消蝕了他們積極進取、百折不撓的精神。明清文學家在崇拜理想的至情人性的同時,卻淡忘了完善現實的至情人性;在超升到自由自在的“太虛幻境”的同時,卻屏絕了現實人生的苦難歷程;在沉迷于以文學自娛的“白日夢”的同時,卻放棄了“士志于道”、“利安元元”的神圣職責。因此,他們獲得的僅僅是一種虛幻的自我實現,一種淺薄的自我價值。在任何時代里,文人要真正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只有投身于社會,貼近于民生,而不是幻設種種佳人或別的什么文學形象,用以自慰或自解,難道不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