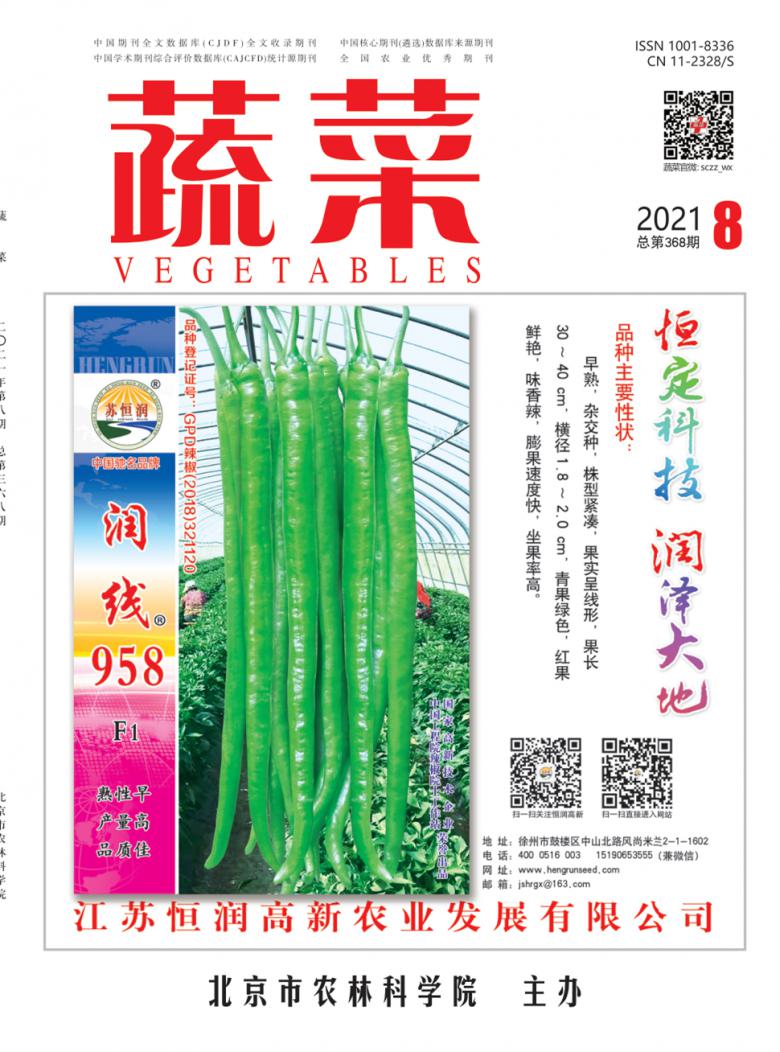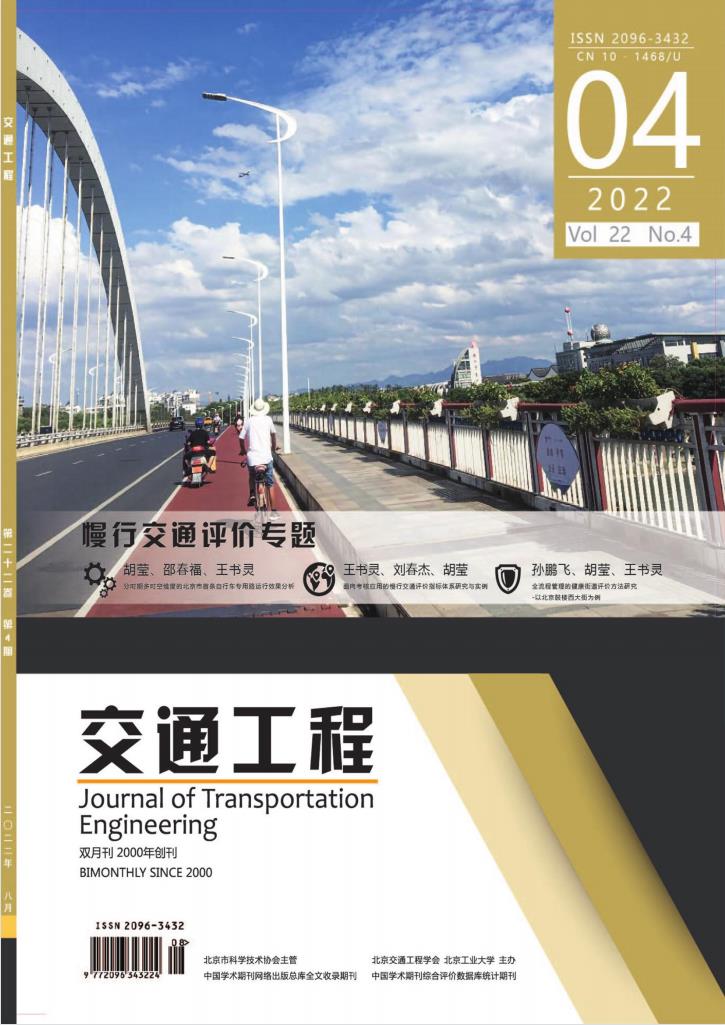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穆木天——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左翼文學論(一)
佚名
【原文出處】北華大學學報:社科版
【原刊地名】吉林
【原刊期號】200503
【原刊頁號】11~16
【分 類 號】J3
【分 類 名】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復印期號】200601
【作 者】陳方競
【作者簡介】陳方競,汕頭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穆木天思想和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其核心體現了與“邊緣文化”相聯系的左翼文學的精神特征,與30年代左翼文學的靈魂——魯迅有著一致的精神趨向。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鋒性”,在這個問題上,穆木天的文藝思想既有重要的價值,又存在著局限性,這種局限是與他的“日本體驗”密切相關的。
【摘 要 題】思潮與流派
【關 鍵 詞】穆木天/左翼文學/魯迅/邊緣文化/先鋒性/日本體驗
【正 文】
一
我與穆木天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不解之緣,近二十年未曾中斷,成為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我與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上世紀80年代初,我還在吉林師范學院工作。這時候我遇到了索榮昌老師,他是長我近二十歲的老教師。他最初開的課是“魯迅研究”,但我很快發現他實際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與穆木天“同鄉”,是吉林省伊通縣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著那份別人不具備的“鄉情”。但我以為,當時在學術研究受“天時、地利”等諸多限制的情況下,他做出的這種選擇是十分明智的。80年代初是所謂“撥亂反正”時期,整個學術界關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幾人?索老師經過中國“傳統”的學術訓練,對資料極其看重,為搜集資料同時也是為了使這一研究得以更好地展開,他結識了楊占升等老先生,并得到了楊先生的支持。他與當時在學界埋頭于學科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且關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偉江、張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建立了純真的友誼,又與穆木天的女兒穆立立始終保持著聯系。在他們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資料的發掘和整理是極為豐富和完備的,這在當時更關注魯、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且又為郁達夫、沈從文等一個個新的研究“熱點”所影響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是很難想象的。《吉林師范學院學報》主編黃湛先生與索老師同樣有著把研究作為“事業”來做的堅韌品格和甚大氣魄,通過省社科重點項目“穆木天研究”的研究,他們在全國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在學報上開辟了“穆木天研究專欄”,持續不斷地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極大地提高了該學報的知名度。于1990年秋,他們主持召開了“全國首屆穆木天學術研討會”,會后又為《穆木天研究論文集》的編輯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被動”地走進了穆木天研究。所以說“被動”,是因為我這個有著江浙血統的北方人,當初正埋頭于魯迅研究,對穆木天研究多少有些不以為然,因而有一種“以魯視穆”心態,這是我的魯迅研究帶來的“陷阱”。應該看到,中國現代文學中任何一位具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豐富而深刻的內心世界,都有自己的個性存在的位置。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是通過他的作品進入到他獨有的世界中。對我而言,走近穆木天是需要一個艱難過程的。“文革”后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研究者幾乎都是從作家研究起步的(這與后來的研究者有些不同),他們第一步的工作又幾乎都是從盡可能全面地搜集和閱讀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史料開始的,首先為這個作家編出年譜或生平傳略,這是研究的基礎。隨著研究的深化,對作家在文學史上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某種“情結”便不斷有所發現。對于研究者來說,他的研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夠真正走進作家的內心世界,是否能夠把作家留下來的文字轉化為自己生命的“血肉”,后者可能更為關鍵。后來,《新文學史料》邀我寫《穆木天傳略》,索榮昌老師把他多年來搜集到的穆木天的全部作品和生平史料毫無保留地給了我,這為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認真地閱讀了這些資料,真正地感到了進入穆木天本有世界的艱難,在我的感覺中,這好似一場“你死我活”的較量。當時,更觸動我深入思考的,是關于穆木天對早年生活的回憶及相關材料,閱讀過程中不由自主地時時被記憶中的一幅幅畫面所打斷,那些我熟悉的但又多少感到有些陌生的生活場景在撞擊我。那就是我曾經在吉林省的山區經歷的五年的“知青”生活,我真的是把自己的“根”扎在了那片土地中,它成為我一生中最能觸發思考力和想象力的“經歷”之一,成為我后來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精神資源之一,當然,這也是我為什么能對穆木天的早年生活產生一些感同身受的體驗的原因之一,而且,這種使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結”,又是我當時正在思考和寫作的《魯迅與浙東文化》一書的內在推動力之一,即魯迅作品中再現的他的早年生活,早年生活中蘊含著的貫穿于他的創作并為他有意或無意凸現的“浙東文化”對他的影響。我對這種影響的發現與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結”之間產生了惟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同構”。這對我的研究是相當重要的。
二
幾乎任何一位學者的學術研究,都不可能將穆木天與魯迅相提并論而提出他們身上存在著某種一致性,但在我的感覺中就是這樣的。首先,穆木天的藝術天分、知識結構、創作成就和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影響及貢獻,是遠不能與魯迅相比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中國現代文學所顯現的多元文化內涵中他們沒有相通之處。在我看來,要認識這一點,涉及當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涉及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內涵的認識。
文化是文學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礎,相對于文人的書面文學的人為性特點,文化(主要是民間文化)更多地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在性和自然生長性,它確立在發展變化極其緩慢的自然生態環境之上。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的文化中心的不斷轉移,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對相對優越的地域性自然生態環境的選擇。中國文化中心經歷了從中原至西北又不斷向江南轉移,逐步脫離了它形成之初與中國更廣泛地域的多元文化相依存的自然狀態。自宋代以后,江南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至清末,雖然帝都北京是政治中心,但文化最發達的地域仍然是江南,主要是江、浙、皖地區,中國文化版圖中邊緣省份的地域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逐步“邊緣”化了。清末中國文化所植根的地域文化的不斷縮小,江浙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又促使這種底氣明顯不足的文化偏于柔弱、纖細發展,這是一種充分“士大夫文人”化的發展趨向,只能依靠充分“經典”化以維持其“主流”位置。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就是這樣,到清末已然蛻變成與“邊緣文化”相絕緣的貧血兒,蛻變成根本無法自我更新而行將就墓的垂死者。“五四”先驅者就是這種“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學的掘墓人和送葬者,使維系中國文化的固有文化板塊破裂了,也就使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主體發展重新獲得了與能夠賦予它自我更新的血液的“邊緣文化”相聯系的可能。
王富仁先生近年來站在維護“五四”的立場上對“五四”的反思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區發生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廣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聯系的歸國留學生具體發動的”,這帶來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學建構中的“邊緣文化”的缺位,這種缺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二十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學”的“發展趨向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特定的發展趨向性”“有它不可能沒有的局限性”,使新文化運動僅僅“取得了表面的勝利”,“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學的危機”。這種“局限”和“危機”的突出表現是,一方面新文化、新文學形成了“以世界強勢國家的強勢文化為統一的價值標準”的“世界主義文化傾向”,另一方面則“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價值標準提高到一種普遍的、絕對的文化價值標準的高度,將其凌駕在世界各個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覺不自覺的將其作為統一世界文化的價值標準”,這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傾向”。[1](P9)
這就是說,“五四”新文化未能根本改變中國文化發展中“邊緣文化”缺位這一頑癥。“五四”新文化先驅者主要來自以江、浙、皖籍為主的知識分子,江、浙、皖等地域的文化的文化血脈無疑是前述那個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根基。家族血緣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文化氛圍使“五四”先驅者難以對“邊緣文化”有感同身受的體驗,難以通過“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比照來發現中國文化的癥結,他們主要依據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根本不同來展開文化變革——對西方文化的借助。在未能引起變革者對中國文化版圖中的“邊緣文化”的汲取以深化變革時,這種借助是難以使變革者倡導的新文化真正走出他們所攻擊的“主流文化”的頑癥的。
所謂“邊緣文化”,是一種“在人的原初性的存在中,靈和肉、文和武、情感和意志原本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文化,是人的這些不同方面還沒有被后來的書面文化和西學東漸之所謂“科學”及其創造的物質文化所分解的文化,是一種含有人的“天性”和“血性”的文化,這種文化造就的是“完整的人”,是完整地“表現出自己真實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的人,是所有這些都有機地結合為一個物質精神整體的人”。[1](P12)
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幾千年的發展對“邊緣文化”的不斷瀝除,其主流趨向的書面化以致人為化,成熟以致爛熟,導致文化在人的精神建構中使人本有的“天性”喪失。因此,面對這個“古國文明”,“五四”確立的“立人”思想不能不表現出一種“反文化”的特征,這在魯迅思想和創作中有突出的表現:他留學日本期間,由“日本體驗”激活的“中國體驗”使他與尼采產生精神共鳴,表現出某種“反文化”的精神傾向,提出的“氣稟未失之農人”的“厥心純白”具有他的生命本源上的意義,[2](P30) 這使他與“一意于禁止賽會之志士”相對抗,在文章中激烈地為他熟悉的故鄉農民迎神拜鬼活動辯護;[2](P30) 他1919年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進一步提出,在“未曾經過‘圣人之徒’作踐的人”身上,“自然而然”地能發現“一種天性”,并且說,“這離絕了交換關系利害關系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所以覺醒的人,此后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3](P133、135)
魯迅在“五四”退潮后更加明顯地表現出超出新文化視閾的追尋:1924年他到西安講學,在易俗社聽秦腔時提筆寫出“古調獨彈”,他神往的“漢唐氣魄”和“魏晉風度”就與這片土地相關;1926年他著手于《朝花夕拾》的寫作,該書很快結集出版。逝世前,他又飽含深情地寫出《女吊》。這些回憶性散文對自幼就滲入自己靈魂深處的“人與鬼相交融”的民間文化的重現,濃墨重彩地涂抹故鄉農民喜愛的“無常”鬼和“女吊”鬼,這自然也是對他生命的精神源泉的再現。魯迅更進一步表現出對北方的大自然景觀的由衷向往。他撰文贊頌“朔方的雪花”,說“在無邊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是雨的精靈”;[4](P181) 他1928年在上海“看司徒喬君的畫”,說自己“愛看”作者筆下的與“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迥異的“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認為其中顯現了“中國人”的那種“天然的倔強的靈魂”。[5](P72~73) 這實則是對自然生態環境相對惡劣而“邊緣”化的北方保留著充滿人的生命活力的生命形態的發掘和肯定。所以,魯迅極其重視來自邊緣省份底層社會的青年作家的創作,他竭力幫助因故土淪喪輾轉來到上海的蕭軍、蕭紅,還有來自湖南的葉紫,自費編輯出版他們的作品,起名《奴隸叢書》,并為他們的作品作序。在他看來,這些作品與那些“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迥異,別有一種意義,屬于別一世界。
三
如果我們認識到“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文學發展中“邊緣文化”的缺位,延續并進一步強化了北京尤其是江浙的文化中心位置,認識到這一“文化中心”的文化建構中的“邊緣文化”的缺位,是新文化、新文學發展中經“五四”沖擊的書面文化的士大夫文人化傳統復活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學建構中缺位的東北文化、西北文化和西南文化滋養、培育的作家,他們以自己的創作之介入“文化中心”,這種介入顯然具有突出的“邊緣文化”意義。這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中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的“都市文化”日漸明顯地表現出的士大夫文人化的致命缺陷,同時,也構成對造成這種復舊趨向的前述新文化、新文學的“世界主義文化傾向”和“狹隘民族主義文化傾向”的有力沖擊。
沈從文1924年末在《晨報副刊》上以《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出現,幾年后寫“湘西世界”充滿人的“天性”、“血性”和“蠻性”的《柏子》、《野店》、《旅店》等小說,使讀者眼睛一亮,心靈為之震動,即是一例。穆木天的情況較之沈從文顯然更為復雜:一方面,他始終并不以自己來自東北而自慚形穢,自認是“東北大野的兒子”、“東北大野”、“北國之人”一類詞匯經常出現在他筆下,他是最早一位帶著東北文化特征進入新文學殿堂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他的“進入”明顯有別于沈從文,與后來的東北作家群的出現更有明顯的區別。如果說,沈從文尤其是后來的東北作家群“介入”新文學,是在與新文化碰撞中凸顯他們創作的“邊緣文化”特征的,那么,穆木天步入文壇時較多地受到了“邊緣文化”缺位的新文化的淫染,使他與東北文化本有的聯系顯得模糊了,就像霧退而漸漸地亮出湛藍的晴空本色一樣,他是在相關背景下強化了他的創作的“邊緣文化”內涵和特征的。
這種狀況使穆木天“五四”后的20年代的創作與30年代轉向左翼文學后的創作,呈現出明顯的區別。研究者在“文革”前后曾經過分肯定后者而不屑于瞻顧前者的“靡靡之音”,近十多年來則恰恰相反,充分發掘前者對于(象征)詩歌本體建設的價值,而對后者已經少有人顧及了。穆木天的文章和創作中突出表現出的這種文學觀和文學批評觀念的大幅度變形,他的“覺今是而昨非”,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屢見不鮮。我們需要透過這些表面現象,具體感受所研究的對象,從中捕捉一些更內在的、在研究對象身上持續性存在的、更富有生命力的因素。我認為貫穿穆木天一生創作的核心“情結”在他的“故土家園”,但他對此的自覺以及從“邊緣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是與時代的影響和他投身左翼文學的經歷相關的。
穆木天15歲即1915年由吉林一中轉學到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其間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18年至1926年留學日本近8年,這一段時間是新文化、新文學的發生、發展期,他盡情地汲取新文化的養料,從確立“科學救國”的理想到做出“棄理從文”的選擇,啟蒙主義思想自然使他對生養他的故鄉文化中的愚昧、落后的東西產生反叛傾向,但他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順應新文化要求中剝蝕著或者改變著故鄉文化對他本有的影響。家庭的敗落,寄身異域的“弱國子民”的境遇,還有他與創造社同仁一樣的濃重的“懷鄉病”,以及青春期經不住失戀攪擾的情感波動,都促使他深深地沉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專業的氛圍中,“熱烈地愛好著那些象征派、頹廢派的詩人”,“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自認:“我讀了詩人維尼(AIfre de Vigny)的詩集”,“好像是決定了我的作詩人的運命了似的”,[6](P416~418)“在象征主義的空氣中住著,越發與現實相隔絕了”。[7](P428) 他選擇并認同的是法國19世紀的貴族文學傳統,他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法國象征主義鼎盛期地位“隱微”的年輕詩人薩曼,認為薩曼承繼了死于法國大革命斷頭臺的貴族詩人安德烈·舍尼埃開創的古典主義傳統。穆木天對法國貴族文學古典主義傳統的擇取,是與《新青年》倡導文學革命的法國平民文學取向相矛盾的,這使他1926年回國前后寫出的《譚詩——致沫若的一封信》、《寫實文學論》等文章較深地觸及文學革命倡導的一些癥結,他提出的“純詩”理論有助于“五四”白話新詩切合詩歌自身性質的發展。但是,穆木天的“純詩”理論及創作,在當時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就他自身而言,這種理論及創作也是“轉瞬即逝”的,他不久就宣布自己和這種理論及創作告別,他投身于左翼文學倡導和創作中。我認為,認識穆木天的這種“轉向”,必須結合他身上根深蒂固存在的“邊緣文化”特征,他始終沒有割斷與曾經生養他的“東北大野”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留日期間的法國貴族文學取向弱化了。這涉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留日知識分子身上的“日本體驗”與“中國體驗”關系問題。
對于中國的留日學生的“日本體驗”,應做出不同層面的分析,但這種分析不可抹殺其主導趨向和核心內涵。首先,日本與中國同在東亞,自古屬于同一文化譜系,這一文化譜系的中心無疑在中國。日本作為一個島國民族,地理位置又處在東西方之間,這決定了日本文化對于中國固有的漢文化明顯具有“邊緣”性特征。我認為這種“邊緣”性在近現代之交之于中國具有雙重內涵:日本文化與漢文化的關系不僅較之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于漢文化具有更為突出的“邊緣化”特征,而且,當“五四”中國開始掙脫“固有文明”的束縛,開始進行自身脫胎換骨的改造時,日本與中國的固有聯系以及日本業已形成的與世界的廣泛聯系,日本文化又成為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如魯迅所說:“日本雖然采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凌遲,宮廷中仍無太監,婦女們也終于不纏足”;日本雖然“并無固有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8](P243~244) 魯迅同時譯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學作品,認為這些作品“主旨是專在指摘他最愛的母國——日本的缺陷的”,[9](P251) “作者對于他的本國的缺點的猛烈的攻擊法,真是一個霹靂手”,[10](P250) 作品“所狙擊的要害,我覺得往往也就是中國的病痛的要害”,[10](P250) “多半切中我們現在大家隱蔽著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負的所謂精神文明”[9](P251)——“這是我們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0](P250) 其次,鴉片戰爭以后,中日兩國強弱不同,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泛濫,自恃強大,甲午海戰及“馬關條約”,使中國人蒙受了近代以來最嚴重的喪權辱國之恥,近現代之交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大事件,無一不與日本謀求在華利益相關,這帶來兩國關系的極度惡化。魯迅留學日本期間對此感受和體驗甚深。(注:魯迅在回憶性散文《藤野先生》中對藤野先生深切的懷念,是與這一感受和體驗直接相關的。)所以,留日知識分子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難者,一方面,“日本體驗”激活了他們自幼的生命歷程中的“中國體驗”,同時也深化了他們的“中國體驗”,使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和癥結有更加清晰和深入的感受和認識,批判矛頭明確指向“文明古國”的“文化不可更移”之論,主張“改造國民性”。他們的“立人”主張具有明顯的“邊緣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正是“日本體驗”使他們真正感受到來自這個民族的威脅,他們有著更加突出的民族危機感,變革意識強烈。我認為,這兩個方面決定了“日本體驗”在中國現代作家身上的主導趨向和核心內涵。
這就是說,中國現代作家的“日本體驗”一旦脫離了與他們身上根深蒂固的“中國體驗”,一旦消解了這種體驗中深切感受到的民族危機意識,他們的“日本體驗”就會發生蛻變。就前期創造社作家而言,他們的“日本體驗”應該近于魯迅,但由于他們自身的特點和境遇又表現出與魯迅的明顯不同。這種不同,一者表現在他們缺乏魯迅那代人更為深刻的“中國體驗”,另者,他們在日本更加突出地感受到民族危機,那種自我生存境遇中“弱國子民”的屈辱心態又弱化了他們的“中國體驗”,如鄭伯奇所說,他們在日本“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而使他們“對于祖國便常生起一種懷鄉病”,使他們在文學上“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去”。[11](P12) 如果說郭沫若和郁達夫在日本所學專業與他們的創作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他們更主要是在精神上感受“五四”中國,在精神上感受自己在日本的境遇,在這種境遇中感受歐美文學,那么,穆木天的法國文學專業的學習,則不具有這種精神感受特征,由其境遇滋生的“懷鄉病”,表現出的是濃重的“傳統主義的情緒”,[6](P419) 他由此而對法國貴族古典主義文學傳統產生強烈共鳴。他與出生于西北的鄭伯奇和王獨清,在這種相近的思想傾向中問難于國內的新文學的“反傳統”而提倡“國民文學”,反映出他們與自幼生活的那片土地上的“邊緣文化”并沒有切實的聯系。如穆木天的《給鄭伯奇的一封信》,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他與錢玄同的爭辯文章,他傾訴的愛國主義“情腸”是要求“復活起來祖國的過去”,[6](P419) 這“過去”對遠在異國的他是朦朧的。穆木天同時開始的象征詩的創作中也是如此。《旅心集》中的不少詩篇是寫他生活過的故鄉和日本東京的,但經過他的法國文學取向中的重朦朧、尚音韻、取印象的象征主義表現手法的一番涂抹,很難區分出他的故鄉景致與域外風情在外在表現和內在意蘊上有什么不同。如寫吉林市的雪花(《落花》)、北山(《北山坡上》)、天主教堂(《蒼白的鐘聲》)等,呈現出的是經他主觀變形過濾后的弱質化的物象,反映的是他特有的“日本體驗”中的纏綿、沮喪的情緒和那種依戀傳統的牧歌調。這些詩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詩歌藝術表現形式上的探索,被郁達夫推崇,是穆木天借鑒法國象征主義對中國新詩藝術形式的開拓。但詩中的畫面和情調缺乏精神的內涵,明顯不是那個根系于“東北大野”的穆木天的性格的體現,你從中感受不到“東北大野”賦予他的精神因素。
穆木天早期詩歌創作中的這種故鄉文化“變形走樣”的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具有典型性。這與“五四”后缺乏“邊緣文化”支撐的新文化相關。新文化不僅沒能為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新文學作家提供認識都市必要的思想文化資源,而且,當這些作家借助新文化而融入現代都市時,他們創作的“邊緣文化”特征隨之會被消解。我認為沈從文就有這種情況,他的植根于“湘西”而與他所置身的都市文化相撞擊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但讀他的這些作品也能感到,他缺乏蕭紅、蕭軍走進大都市上海后仍保持著與“邊緣文化”的聯系的那種精神定力,他與“湘西”之間是一種缺乏精神支撐的文化聯系,這使他在影響著都市的同時,都市也在影響著他。如他過分迷戀于兩性關系的寫作就是一個都市新文化所熱衷的話題,他主要通過這樣一個渠道逐步為都市所接納。又如何其芳,他走出西南巴文化區到北京求學,創作上一舉成名,但從他獲獎的散文集《畫夢錄》中能讀出他應該有的那種較少“文明”教化的故鄉“邊緣文化”特色嗎?
【
[1] 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東北作家群·端木蕻良[J].文藝爭鳴,2003,(2)、(3).
[2]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A].魯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A].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 魯迅.野草·雪[A].魯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 魯迅.三閑集·看司徒喬君的畫[A].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6] 穆木天.我的詩歌創作之回顧[A].陳惇、劉象愚編.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7] 穆木天.我與文學[A].陳惇、劉象愚編.穆木天文學評論選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8] 魯迅.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記[A].魯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9] 魯迅.譯文序跋集·從靈向肉和從肉向靈·譯者附記[A].魯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0] 魯迅.譯文序跋集·觀照享樂的生活·譯者附記[A].魯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1] 鄭伯奇.小說三集導言[A].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M].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